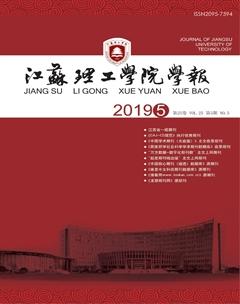进入“历史”:五四精英文人的政治叙事
班瑞钧 高菲菲 张海灵
摘 要:在五四运动“基座”下,现代性与历史主义的“历史”这对伴生体应运而发。经由社会想象和主体想象,精英文人通过进入“历史”的文本叙事转向在事实上实现了间接性政治参与,为中国社会重建新的意义关联域达致新政治样态付出了努力。这是中国结构性社会转换的先声与缩影,历史的重心开始迁转,中国从整体上进入了一种现代历史叙事,并借此展开历史想象与政治实践。在这一大潮的涤荡中,历史逐渐获得了自己明确的实践形式,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全面传播创造了条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政治叙事;五四;精英文人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9)05-0007-08
精英文人的政治参与始终是中国政治运作最主要问题之一。五四时期,大批精英文人通过进入“历史”的文本叙事转向在事实上实现了间接性政治参与。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孙中山在《复蔡冰若函》中就曾对此评价道:“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这种间接性政治参与的意义确实非凡:尽管作为认识论视角的整体主义研究方法认为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着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1],“但作为整体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自成一体的个体或个体集合,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对整体形成巨大的甚至是转折性的影响。每一种历史绵延中的文化,实质上都是某种、某类人格的无限扩大,独特的文化绵延模式必然造就出独特的国民性特征”[2]。
一、从“现代性”到“历史”
中国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早期经历政治体系大变局,又叠加现代印刷出版技术的突破、科举制度的废除,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等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爆发。这些变故从根本上瓦解和摧毁了出身于传统士大夫(身份的或精神的)的五四精英文人乃至整个传统中国赖以存在的意义关联领域。所谓“新的意义关联域”就是通过叙事建构一种指向“现代”的总体性“历史”,为社会个体和群体提供信仰选择与自我实现的意义根据。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的观念革新让五四精英文人的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产生了亨廷顿式的文化“撕裂”(torn),也更深刻地体验了现代、历史与个人、国家之间意义关联方式的巨大转变:“(使)吾人之精神界中,种种庞杂之思想,互相反拨,互相抵销,而无复有一物之存在,如斯现状,可谓之精神界之破产”[3]“破产而后,吾人之精神的生活,既无所凭依,余此块然之躯体,蠢然之生命,以求物质的生活,故除竞争权利、寻求奢侈以外,无复有生活的意义。”[3]“请放弃一切希望”这句曾被但丁鐫刻在地狱入口的格言,此刻俨然已经高悬于茫茫神州大地。
在此“基座”下,如何为块裂的中国社会重建一个意义关联域就成为最重要的时代主题之一。五四时期的重要性正在于其为中国社会重建新的意义关联域达致新政治样态的努力:“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巨变。”[4]“这一事实形成后就拥有了自身的演化逻辑,在表面上并未大规模改变既定的显性规则制度的同时实现了类似制度变迁的结果。”[2]
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现代性”理念与话语强势登场。作为一种社会思想,作为与“后现代”相对应的分析工具,现代(modern)和现代性(modernity)的核心是理性信仰,即相信人可以凭借自身的理性认识自然、改造社会乃至掌握自身的命运。其重要特征就表现为建构和追求“主体的自由”。其中“主体”既包括个人主体,也包括民族国家主体。五四运动之后,社会精英开始认识到“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5],“着力点在于将个体与类交融互摄”,“历史生成性地实现个体与类的相互规定性”。[2]这一通过完成民族国家的构建来达致个人解放的路径是解决当时中国政治的现实选择,也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等政治精英的共识。
以唯物史观回望五四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追索,五四运动初起时,中国“主要是以(西方)十八、十九世纪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为模仿和追赶目标后”[6],逐渐引致马克思主义在苍茫大地的隆重出场并渐主沉浮——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实现了本土逻辑规制下的中国化。五四精英文人的“现代性”认知,洋溢着强烈的启蒙理性,“人”觉醒的尖锐呐喊,而着力于对未来祖国的想象与叙述。“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性的‘启蒙,并不仅仅是指‘个人的觉醒,它同时还是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觉醒,‘救亡不但不是‘启蒙的对立面,而且是‘启蒙的一个基本环节。”[7]正因为这一原因,“‘个人就始终是民族国家中的‘个人,或者是作为民族国家变体的另一个‘想象的共同体——‘阶级中的‘个人”[7]。百年历史,它不仅表现为现代性启蒙意义上的文化觉醒史,而且是中国新现代性道路的开创史,更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史。
二、历史主义的“历史”
现代性与历史主义的“历史”在现代思想史上近乎伴生关系:一方面,正是由于启蒙理性的确立和人义论对神义论的取代,“历史”从传统(尤其是宗教传统或文化传统)时间观念中获得自己的形式;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有了“历史”这种特殊的表达形式,现代性才被人们深刻理解,才得以深入社会思想的各个横向与纵向的层面,甚至还因此成为时代价值的本原。学者们“不只培育出一种著述类型,而且提出了他们民族生活中的问题。他们意识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他们知道如何从几百年的历史遗产中开掘出活跃的现实性”[8]。
(一)“历史”的发生
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历史(如编年史),只有历史主义中的“历史”才是与现代性相伴而生的。在历史主义(historicism)视角下,“历史”指谓一种建立在单向度线性时间观念基础之上的对于人类过去生活的叙述(历史主义的“历史”在后文中一般将不再加引号,标题除外)。这种定性暗喻着理性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逆转。于是,历史就具有了目的性和导向性:追求“一种特殊的可理解性”[9],“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人类事件‘流水账式的百科全书,而是一种尝试,试图想在人类社会整个发展过程中发现一种有意义的模式”[10]。这种“有意义的模式”实际上就是把人类社会的发展解释成理性的和进步的过程,其结果是,“历史成了走向某种目标的进步过程”[11]。
五四运动时期,文本叙事要真正走进现代,不仅要拥有现代思想,而且还要能够通过时间、通过历史来表达这些思想。无法进入历史,就不可能进入现代。体现在叙事中,现代首先是指文本对理性、“人”的觉醒以及对民族、阶级解放等现代性思想的发现与认同;其次才是指对相应表达形
式——历史叙事的探索和运用。五四运动后,精英文人对现代性叙事结构的发现与建构,首先是与来自西方的现代线性时间观念密切相关的。“今之世界,所谓大通之世,处斯时世,倘欲有所树立,必应受世界教育,得世界知识,有世界眼光,具世界怀抱,并令身亲种种世界事业。”[12]“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后可云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13]建构在西方线性时间观念基础之上的历史叙事功能结构便成为文本叙事走向现代的首要问题。
(二)歷史与启蒙
历史主义的形成得力于启蒙理性。古希腊盛行没有历史感的循环论(中国也是如此,即黑格尔认为的“中国没有历史”之“历史”):时间周而复始,万物起于本原而最终又复归于本原,相同的事件将在时间的循环中重复出现。中世纪基督教末世论教义的崛起摧毁了历史循环论观,从上帝创世到基督受难再到末日审判,时间直线向前、永不重复。历史主义的“历史”则是启蒙理性的产物。理性的崛起源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其间,自然科学的空前成就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基督教的势衰,人的理性逐渐突破基督教神义论的限制,扩张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基督教规训人们等待上帝的拯救,但启蒙运动却教导人们运用理性“争取解放——人的道德自主,有勇气依靠自己”[14]。在科学领域,凭借理性认识自然、控制自然并有计划地改造自然的思想成为普遍社会信条。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由此发生。
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家认为,“建立有关历史与社会的科学——它由具有解释力的假设和法则(同物理学的理论所得出的假设和法则相似)组成——越来越重要。关于人间事务的、命运的、宗教的与形而上学的假设已经终结。现在的任务是以严格的可观察事实为根据去构造解释,它不仅可以使人类探究摆脱无知、不确定性和原始迷信,而且把预见和控制他们命运的工具交到人类之手。因而,创造一种普遍有效的社会科学,它可以根据堪与自然领域中使用的因果原理相媲美的因果原理来解释历史现象”[11]。人类不但要发现规律去控制自然,而且还要发现规律去解决社会问题。由此可见:历史主义既是启蒙理性的结果,同时各种启蒙观念也在历史中获得了充分的自身表达。这不但表现在历史的核心是理性与主体的自由,更突出地表现在历史将现代性的价值观念表述成了一切价值(个人价值、社会价值,等等)的本原。
(三)历史、理性、自由与价值
各种启蒙观念在历史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表
达——尤其是理性。“历史过程尽管显得杂乱无章,但可以被看作是体现了一种总的计划。历史哲学就是使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满足理性的需要。”[11]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的建构典型地表明了理性(黑格尔称之为“精神”和“观念”)在历史中的决定性意义,“一般说来,世界历史便是‘精神在时间里的发展,这好比‘自然便是观念在空间里发展一样”,“哲学所关心的只是‘观念在‘世界历史的明镜中照射出来的光辉”[15]。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修订”令人印象深刻,其进步性体现于将理性从精神转换为与人类经济活动相关的必然性。也正是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得以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前后的“民主与科学”的大潮中迅速传播开来。
主体在个人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历史中也获得了非凡的表达。梁漱溟先生曾说:“中国文化最大的缺失,是个人不被发现。”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第一点就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要求青年务必“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做是大自然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其目的“为的是要奠定一种对内的并且为此目的同时也就是对外的完美的国家宪法,作为大自然得以在人类的身上充分发展其全部禀赋的惟一状态”[16]。所谓“对内”,是政府与民众之间以契约形式保障个人自由,所谓“对外”是指国家与国家之间以主权形式保障每个国家的自由。可见,历史是对理性与主体的自由的阐释,也因此是现代性恰如其分的表述。
但更重要的是,历史不单是表达了现代性,它还把启蒙与现代性叙述成了价值,叙述成了现代人生活的意义之源、信仰的依靠。在基督教的时代,人们依靠对上帝信仰来生活。进入现代,“上帝死了”,人们又靠什么获得生活的意义呢?靠的就是“追溯”历史与“衍伸”历史,以及由此脱胎而出的美好未来。五四精英文人文本中的奋斗、努力和革命,正是因为连通着美好未来而显得意义非凡。之所以要不惜代价地追求个人的自由、之所以要献身于国家的独立,是因为历史使主体坚信这是进步的事业,是历史通向美好未来的必要环节。历史主体深信他们对历史的献身将获得丰富的和无限的人生意义。历史在现代生活中开始成为崭新且独尊的判断标准和价值体系:“某一事件在线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成为对之进行评价的重要标准。一个事件、一种制度、一个人物或一个观念应当根据其历史作用来衡量。”[17]31
三、进入“历史”的文本叙事
进入历史,既关涉五四精英文人是否具有新的时间观念和现代性的理性、个性主义、民族主义的理念,更关涉他们是否足以将这两者融合起来转化成一种新的叙事结构。在这种新结构中,文本中的社会、人物、故事情节等普遍“深深扎根于历史进程中”[17]34。
(一)进入“历史”的社会想象
在五四精英文人的文本中,现代历史主义观念对新叙事结构的建构首先从描写传统中国社会黑暗的甚至罪恶这一层面开始的。鲁迅的《故乡》《阿Q正传》等杰作表现的皆是宗法制下“老中国的儿女”[18]的阴暗生活。而陈独秀念念不忘的是要为中国找到一种“根本解决”的办法,他要求青年“发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19]。这类彻底“破坏”“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的决绝气概激荡了整个五四时代,人们是那样地渴望将传统的旧的社会迅即踢进历史的坟墓,一转身就创造一个“人人知之,人人慕之”的“美丽新世界”:“思想新,学问新,政体新,法律新,工艺新,军备新,社会新,人物新,凡全世界有形无形之事物,一一皆辟前古所未有,而别立一新天地。”[20]
这无疑对文本叙事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叙事结构要承担“利刃断铁”的任务,要彻底断掉传统社会的希望,彻底否定它的所有价值。进入“历史”前的旧叙事结构一般展现的是叙述者自身在既有“社会”之内选择一个理想的价值立场发言。但在五四精英文人的文本中,叙述者与既有“社会”是疏离甚至对立的,在价值认同上更是格格不入。叙述者的立场大都在既有“社会”之外冷眼旁观。既有“社会”被叙述者客体化了,它在整体上被批判、被诅咒,其历史命运就是等待被消灭。
古代精英文人也批判既有社会,但他们是在既有社会价值系统之内选择立场;而五四精英文人则是否弃既有社会价值系统,把既有社會变成了他者。五四精英文人的社会描写主要源于历史主义,是以非理性与理性、愚昧与文明、病态与健康、奴役与自由等两分对立想象和后者必然战胜并替代前者的历史主义叙事为基本根据。这是与传统中国的“治与乱”的两分对立结构截然不同的现代叙事。
(二)进入“历史”的主体想象
“一个人在历史的时间天平上的位置,对人们关于自我的概念(self-conception)和自我认同(self-identification)非常重要。”[17]35任何文本中的主体形象都是在某种价值观念的观照下凸显出来的。在传统文化文本中,主体形象一般是在儒道禅等价值体系的参照中出现。但在五四精英文人的文本中,主体形象的凸显就转而与历史主义内含的价值体系发生了联系。这和非理性的与理性的、愚昧的与文明的、病态的与健康的、受奴役的与自由的二分对立式社会想象相一致,五四精英文人的文本大都很自然地出现了分别附着于二分对立的两个想像社会的不同主体。如陈独秀提出的“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池坑中救起”[21]。在五四精英文人的文本中,各式人物虽然都是在共享空间体系(如乡村或都市)中展开自己,但他们并未共享同一个“时代”——即同样的时间体系。事实上,各式人物是生活在两种迥然不同的有着巨大“时间差”的思想模式与价值世界里。在鲁迅的文本中,一边是如“阿Q”般绝大多数“愚钝的”“暂时做稳了奴隶”的“众数”,另一边则是如“狂人”般少数甚至极少数的历史先觉者;前者混沌于愚昧的受奴役的世界;后者的身体虽溺困于前者的世界,思想和精神则“逍遥”于或近在咫尺或远在天边的未来新世界。这些叙事显然隐喻了社会“在黑暗中”的事实,以及这种“黑暗社会”在历史中未来必然被彻底埋葬的合理性。
在五四精英文人的文本中,由于主体的身体和精神分别处在历史发展里程上先后不同的世界,因而他们之间必然出现价值观念上的“落差”,导致一种价值张力。历史发展的意识使五四精英文人的文本最凸显的就是主体观念之间的差距、不同和冲突,以及由此造成的悲剧。比如《狂人日记》中“狂人”之“狂”的状态就与这种价值张力存在应激关系。正是因为历史的存在,于是有了处于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和人物,比如黑暗之社会与预想中的未来社会,比如愚民与先觉者。可想而知,既然文本可以表现不同历史阶段上的不同社会和主体,它就同样应该可以表现同一社会和主体在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发展和变化,而这些“不同”之间的反差直指一个共同未来。《新青年》最初三期连载高一涵写的《共和国家与青年的自觉》等文本便顺势高扬对国家社会与个人人格的道德自觉,力倡生命应以追求理想的社会与人格为依归。
(三)“历史”化的政治叙事
综上所述,五四精英文人的文本在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历史”化,既是政治思想观念的更化,更是政治叙事技术的创新。这种更化与创新常按照张灏先生所阐述的“三段结构”展开:首先是对现实日益沉重的沉沦感与疏离感;其次是强烈的前瞻意识,投射一个理想的未来;最后关心从黑暗沉沦的现实通向理想的未来的合理途径。反对旧文化旧道德的一批重要文章,如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差异》、易白沙的《孔子平议》、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思论》《说孝》等,都是深入国家政治和个人权利等诸多方面条分缕析地予以论证。
从思想内涵上看,五四精英文人的政治性文本叙事是“个人”的发现与族群、国家想象的凸显。五四精英文人对个人、族群与国家的重要性显而易见,陈独秀、胡适、周作人、郁达夫等五四精英文人都发表过这方面的看法。虽然当时他们尚未从主观上接受明确统一的政治理论指引,但实干的五四精英文人还是基本完成了利用历史观念建构叙事结构,从而实现间接政治参与的开创性工作。这种历史化的观察驱使五四精英文人创造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新话语结构来加以容纳:在社会想象层面主要显现为居于历史轴线上进步与落后的两个世界,在主体想象层面主要显现为附着于两个不同世界的大众。这种在历史背景下的观念、社会、主体上的冲突、纠缠与新陈代谢是五四精英文人文本中的普适模式,是故事和主体得以生长和展开的根据。这些特点使这种叙事结构可以随着社会历史语境的转换或质变而不断地调整与延伸。竹内好对鲁迅创作文本的评价具有对五四精英文人群体的普适性:“具有改写历史的意义,所以新人类的诞生以及随之而来的意识的全面更新在历史上出现了。”[22]
四、进入“历史”的政治意蕴
五四精英文人的进入历史的文本叙事其目的在于启蒙民众,是“要使今日少数人的信仰变成将是大多数人的信仰”[23],要“指引青年们一个大方针:怎样生活着、怎样动作着的大方针”[24],要促使民众重新认识并投身改造社会的运动中,从而发现并升华个人的或集体的人生意义。《曙光月刊》在宣言中即表示了这个意思,要“发愿根据科学的研究、良心的主张;唤醒国人彻底的觉悟,鼓舞国人革新的运动”,“想着另创一种新生活”。这种指向在文化界各领域都有同感浮现。周作人认为文学要担当起“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25]的责任。戏剧界也要求脱离中国旧戏剧“游戏本位”“娱乐本位”的传统,而以写实的风格从事这一事关政治的严肃事业。陈大悲认为戏剧“感化力格外伟大”,读者“都能于不知不觉之间被戏剧引诱他从发展底路上走”[26]。欧阳予倩称戏剧“必然代表一种社会,或发挥一种思想,以解决人生之难问题,转移误谬之思潮”[27]。蒲伯英还提出了“再生的教化”的追求:“原来社会底进步,以民众底精神为原动力。民众底精神,常常在自由解放之中,不甘受现实的禁锢,那社会自然会富于活气,常常能够发现光明向上的境界,这个理是不费说明的。所以对于民众最高的教化,不是具体的教训他做什么事好什么事不好,更不是指定一两种做人的方法教他去死学;是要借着戏剧对社会的反映,养成他促动他的创造的向上的精神,使他凭着这个精神,自己去发现光明的路,和自由的我”,“这种教化叫做‘再生的教化,就是说他能使民众精神常在自由创造的新境界里活动,譬如轮回再生的一样”[28]。
“鼓舞”“指引”“再生的教化”等,既是五四精英文人擎举的时代高标,也势必对五四精英文人形成反身挑战。因为这些时代高标要求文本不光要叙事,还必须创造一种新价值系统,并通过它向大众解释:为什么现实社会不好、必须给予彻底否定?为什么要另创一种新生活?为什么所谓“光明的路”和“自由的我”就一定意味着美好的生活?进入历史的五四精英文人的文本叙事就包含了这种凸显政治属性的新价值系统。它对愚昧与文明、病态与健康、奴役与自由等二分对立的描述,既是理性判断,也是价值判断。五四精英文人就按照这种价值系统对中国传统社会作出了定性:它“在黑暗中”,是非理性的、愚昧的、病态的、受奴役的;这样的传统社会、传统人生,在价值上是低于以民主和科学等理念为核心的现代社会、现代人生。因而,它也就不再具有继续存在的理由。新的生活必须按照民主和科学的法则去创造。
《新青年》等进步杂志在当时受到追求进步的社会精英和普罗大众的追捧和好评就具象化了这种政治意义。“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真是在黑暗的地方见到了曙光一样。”[29]“社会仍是这样黑暗,现在的青年要彻底明白旧社会的罪恶,立定不屈不挠奋斗的志向,决不反被旧社会战胜。中国的改造,才有望咧。”[30]巴金《家》中的年轻人,几乎是把《新青年》当作圣经来读的,他们差不多都抱着这样的思想:他们相信现在所处的社会正“在黑暗中”,是吃人的,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藉此,五四精英文人一方面将传统社会写成了彻底的黑暗,另一方面又激起了对光明的向往。这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五四时期的内在时代要求。这也就是胡适所述的“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31],也符合五四精英文人以“消极的文字”去做那“积极的事业”的自觉追求[32]。文本在此与传统发生了巧妙的融合:即传统儒学叙事善与恶之间的价值张力被“嫁接”到二分对立的历史结构中去的同时,西方与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空间性也借此传统价值张力获得了走向现代的历史性。
五四精英文人进入“历史”的政治叙事是五四运动前后“随之而起的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给旧思想以重大的打击”[33]。在它与同时代其他政治行动的历史合力下,“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的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的方向”[33]。“这新方向便是社会中最有革命要求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33]
五、结论
五四运动前后五四精英文人进入“历史”的政治叙事变化,是中国整体性结构转换的先声与缩影,即中国从整体上进入了一种现代历史叙事并借此叙事去想象与实践。在这一大潮的涤荡中,历史逐渐获得了自己明确的实践形式,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全面传播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逐渐建立起一套对于自然和历史的现实和未来的思想体系,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最具实践性的意义关联域,为深层次的社会改造提供了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形成了融明确思想信仰与严格历史原则于一体的宏大而锐利的现代性话语体系。也正是从五四开始,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成果所展示给世人的历史与未来缓慢但稳健地逐渐从精英向大众渗透,逐步成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精神依靠。
这些发展使历史的重心开始迁转:从包括整理“国故”、重读传统之类抽象的文本重构,逐渐转变为对自成一个意义世界(universe of meaning)的崭新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及文化伦理秩序等的具体创建。“制度的形成是历史的结果,是历史中的行动者运动的结果。”[34]当然,这种进一步的历史的创建已非五四精英文人所能担当。历史中的行动者逐步开始从精英文人转换为“冒着敌人的炮火”砥砺前进的坚贞革命者以及集聚在革命旗帜下的普罗大众;创造历史的主战场也逐步开始从“理论”性的文本转移到“实践”性的政治行动,最终经由一叶红船,发展到罢工游行的城市街道,再到工农割据的广袤农村,星星之火,终成燎原。
参考文献:
[1] 马尔科姆·卢瑟福.經济学中的制度:老制度主义和新制度主义[M].陈建波,郁仲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3-34.
[2] 班瑞钧.蒙元际君臣政治关系的隐喻转向[J].贵州社会科学,2014(9):38-54.
[3] 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J].东方杂志,1918,5(4).
[4] 张灏.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J].二十一世纪,1999(4):29-39.
[5] 陈独秀.谈政治[J].新青年,1920,8(1).
[6]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262.
[7] 李杨.中国当代文学史史学观念笔谈[J].文学评论,2001(2):1-10.
[8] 卡洛·安东尼.历史主义[M].黄艳红,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0:90.
[9] 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23.
[10]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學出版社,2003:61.
[11] 安希梦.历史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代译者序二.
[12] 张崧年.劝读杂志[J].新青年,1918,5(4).
[13] 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J].新潮,1999,1(1).
[14] 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北京:三联书店,1997:89.
[15] 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115,503.
[16]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5.
[17] 格鲁内尔.历史哲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8] 方璧(茅盾).鲁迅论[J].小说月报,1927,18(11).
[19] 陈独秀.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30.
[20] 梁启超.灭国新法论[M]//李兴华,吴嘉勋.梁启超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72.
[21] 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M].上海:三联书店,1984:484-485.
[22] 竹内好.何谓现代:就日本和中国而言[M]//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44.
[23] 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M].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24.
[24] 茅盾.读《呐喊》[M]//茅盾,陈之佛.茅盾散文集:第7卷.香港:天马出版社,1933.
[25] 周作人.人的文学[J].新青年,1918,5(6).
[26] 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现代戏剧集·导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27] 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J].新青年,1918,5(4).
[28] 蒲伯英.戏剧之近代的意义[J].戏剧,1921,1(1).
[29] 欢迎“新声”[J].新青年,1919,6(3).
[30] 何孟雄.过去的青年[N].时事新报,1919-10.
[31] 胡适.陈独秀与文学革命[M]//胡适学术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98:192.
[32] 冰心.我做小说,何曾悲观呢[N].晨报,1919-11-11.
[33] 陈独秀.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M]//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817-818.
[34] 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诊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90.
Entering “History”: Political Narration of the Elite Scholar in the
May 4th Movement
BAN Rui-jun1,GAO Fei-fei2,ZHANG Hai-ling2
(1.School of Marxism,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China;2.School of Marxism,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aotou 014010,China)
Abstract: With the “Gestell” of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history” of modernity and Historicism came into being. Through social imagination and subjective imagination, elite scholar realized indirec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fact by entering the “history” of text narrative, and made efforts to reconstruct a new meaning-related area of Chinese society and achieve a new political pattern. This is the forerunner and miniature of Chinas structur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The focus of history has begun to shift. As a whole, China has entered into a kind of modern historical narrative and used it to launch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nd political practice. In this tide, history has gradually acquired its own clear form of practice, thus paving the way for the comprehensive dissemin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Key word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history;political narration;May 4th movement;elite scholar
责任编辑 张栋梁
收稿日期:2019-03-15
作者简介:班瑞钧,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转型期政治文化;高菲菲,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 近现代史;张海灵,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