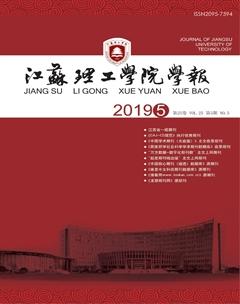论葛洪的子书观念
摘 要:子书观念在两汉魏晋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葛洪的子书观念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特征。葛洪在对子书价值高扬的同时,对子书的性质作了儒学化诠释,将创作子书诠释为体认儒者身份和立言助教的途径;他还推动了子书创作个人化的进一步发展,并将立身处世与立言之间的对应性分割开,为其后著述观念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葛洪的子书观念是东晋时期特殊时代文化背景的折射,不但在葛洪的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后世子书观念和子书创作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键词:葛洪;子书观念;子体自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9)05-0031-06
葛洪,字稚川,晋代丹阳郡句容人,是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道教学者。葛洪的著述很多,思想也包罗万象,其中以《抱朴子内篇》为代表的神仙道教思想历来为学界所重视,研究成果很多,葛洪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个“道教学者”。但事实上,葛洪的成就和贡献远不限于神仙道教理论的范畴,他在医药、化学、政治、文学等方面的贡献也不容忽视。在葛洪众多的思想遗产中,他的子书观念,也就是他关于“子书”的认识,在中古文体辨析和子书观念的演变中具有较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葛洪之前的子書观念嬗变
“子书”是诸子之书的简称,本是中国古代图书分类的一种,最早见于刘歆的《七略》。《七略》今已不存,但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有相关记载:“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1]1701根据班固的记载,在《七略》的图书分类中,“诸子”是与“诗赋”“术数”“兵书”等图书并列的一种书籍类别。但在两汉到魏晋的这个历史阶段,子书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开始从一种集体创作的学派文集逐渐转变成为由著书者独立撰成的一种文体类别。
早在汉代以前,就已有《老子》《庄子》《孟子》等先秦诸子文本传世,但据余嘉锡先生等人考证,这些诸子文本往往是“单篇独行”,并且“不题撰人”,所以并不完全具备后世所谓“书籍”的性质。到刘向等人校书时,将思想相近的诸子文献集中起来,就形成了后世所看到的“子书”。这些“子书”往往是一家之学的汇集,不仅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非成于一时,其中的文体类型很复杂,体现为文集性质。余嘉锡先生认为:“周、秦、西汉之人,学问既由专门传授,故其生平各有主张,其发于言而见于文者,皆其道术之所寄,‘九家之说,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不能相通,各有所长,时有所短。则虽其平日因人事之肆应,作为书、疏、论、说,亦所以发明其学理,语百变而不离其宗,承其学者,聚而编之,又以其所见闻,及后师之所讲习,相与发明其义者,附入其中,以成一家之学。故西汉以前无文集,而诸子即其文集。”[2]51-52这大概就是子书产生时的最初形态。
到了汉代以后,国家立五经博士,经学成为利禄之途。特别是武帝以后,实行尊崇儒术的国策,先秦诸子所赖以繁盛的师徒传承的一家之学的模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除了五经之外的其他学问,很难再以先秦诸子的模式生存下去,所以民间虽然可能仍存在类似传承,但很难再形成像先秦诸子那样的文集式成书模式。新的思想家因其思想缺乏足够的弟子传承,所以不得不寻求新的思想传承模式,著述文章就成了一种必然的选择。但经学的垄断性决定了即便是著述文章也未必能传承下去,除非这些著述的文章能够具备五经一样的地位。所以,汉人最早有意在辞赋等之外别有创制的思想家扬雄,在创作他的《太玄》《法言》时,并不是为了创作什么“成一家之言”的子书,而是试图模仿《周易》《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从而创作出新的“经”。扬雄虽然创制出了《太玄》和《法言》,但这两部书并没有能够成为新的“经”。刘歆就曾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1]3585他的《法言》有一定的流传,《太玄》却没有人能看懂,虽然桓谭认为扬雄的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1]3585但当时,也有人认为扬雄“非圣人而作经”是“诛绝之罪”[1]3585。所以到了王充作《论衡》,面对别人“圣人作,贤者述,以贤而作者,非也”的质疑时就不得不说:“非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山君《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3]
汉魏诸子所著书虽常以“成一家之言”自期,但一般并不自号为某子,而惯常以论为名,如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桓谭《新论》、曹丕《典论》、徐干《中论》等都是如此,这样一来汉魏诸子新创作的子书就具备了演变成一种“文体”的可能,但在当时这种文体仍然以“论”为名,并没有穿上诸子的外衣。如果将子书视为一种文体的话,那么在这个时期,这种文体的创作明显还没有成为一种自觉。
刘勰在《文心雕龙·诸子》篇中说:“若夫陆贾《典语》,贾谊《新书》,扬雄《法言》,刘向《说苑》,王符《潜夫》,崔实《政论》,仲长《昌言》,杜夷《幽求》,咸叙经典。或明经术,虽标论名,归乎诸子。”[4]162而余嘉锡先生则认为“汉以后著作名为‘子书,其实‘论也。”[2]74但其实无论汉魏诸子的论著是算作“诸子”还是“论”,都昭示着一个同样的事实:子书有了从图书类别转变为文体类别的可能。
到曹魏时,子书的地位越来越为世人所重。如曹丕在《与吴质书》中说:“伟长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子为不朽矣。”[5]1897曹植《与杨德祖书》也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5]1903-1904仔細体味曹丕和曹植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到三国时期,在辞赋文章之外撰著“成一家之言”的子书已经被视为一种通向不朽的极高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汉魏士人虽颇为重视子书创作,但如扬雄、王充等人往往是在晚年“道穷望绝”之后才开始创作子书;而曹植更是明言只有当自己“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的志向不能实现时,才会去创作子书。所以,可以说汉魏士人的子书创作仍然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第二选择,真正将创作子书作为一生事业的是葛洪,而子书的文体自觉在葛洪那里也更加明晰。
二、葛洪的子书观念
葛洪当然不是第一个创作子书的人,但他大概是第一个明确将著述一部子书作为一生事业的人。他在《抱朴子·自叙》中毫不避忌地说:“洪少有定志,决不出身,每览巢许、子州、北人石户、二姜、两袁、法真、子龙之传,尝废书前席,慕其为人。念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後世知其为文儒而已。”[6]710如果说汉魏诸子是“不能出身”迫不得已才著子书,那么葛洪则是从一开始就已经下定决心绝不出仕,而将著作子书作为自己一生的事业。因而葛洪的子书观念较之汉魏诸子又有新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子书价值的高扬,极为重视子书的价值,认为子书价值不但高于诗赋,也高于谶纬、术数等学问;二是对子书进行了儒学化,认为子书源自五经,是文儒身份的体认途径;三是子书创作个人化,认为子书创作完全是个人之事,不但独力完成,而且自分内、外篇,自定家派归属;四是将子书创作与立身之道的分离,认为子书的内容与作者的处世方式不必一致,隐逸和讨论政治并不矛盾。
(一)葛洪对子书价值的高扬
三国时期,曹丕、曹植等人就已经极为重视子书的价值,葛洪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子书价值进行了高扬。他不但将子书的价值放到诗赋杂文之上,甚至将其放置到汉代流行的神秘的谶纬、术数等学问之上。
首先,葛洪将子书与诗赋等进行比较,他说:“或贵爱诗赋浅近之细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书,以磋切之至言为騃拙,以虚华之小辩为妍巧,真伪颠倒,玉石混淆,同广乐于桑间,钧龙章于卉服。悠悠皆然,可叹可慨也!”[6]105葛洪将诗赋称为“浅近之细文”,而对子书则用“深美博富”来形容,并且认为贵爱诗赋而忽薄子书是“真伪颠倒、玉石混淆”,是“可叹可慨”的,其重子书轻诗赋的观点显而易见。并且在《抱朴子·自叙》中葛洪进一步重申了这一观点,他说:“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6]697与创作子书相比,葛洪甚至说作细碎小文是“防弃功日”的浪费时间的行为,很明显,葛洪是将子书的价值放在诗赋等文章之上的。虽然这与自扬雄以来鄙薄辞赋的传统一致,但葛洪将子书誉为“深美博富”,而将诗赋视为浅近细文,抬高子书价值的意图可谓不言而喻。
其次,葛洪将子书与汉代流行的谶纬、术数等学问进行比较,他认为子书的价值也高于这些学问。他说:“其河、洛图纬,一视便止,不得留意也。不喜星书及算术、九宫、三棋、太一、飞符之属,了不从焉,由其苦人而少气味也。晚学风角、望气、三元、遁甲、六壬、太一之法,粗知其旨,又不研精。亦计此辈率是为人用之事,同出身情,无急以此自劳役,不如省子书之有益。”[6]656河、洛图纬等谶纬、术数的学问,在汉魏时期被称为密不外传的“内学”,一向受当时学者珍视。但葛洪认为研习这些学问不但是“苦人而少气味”的无趣之事,而且从价值上看,也“不如省子书之有益”。很明显,葛洪将子书的价值置于这些谶纬、术数等学问之上,也是为了高扬子书的价值。
总之,在葛洪的子书观念的价值维度层面,葛洪认为子书的价值不但高于诗赋杂文,而且也比谶纬、术数等学问更有趣味、更有价值。而对子书价值的高扬,则为通过创作子书“立言助教”体认“文儒”身份提供了合理的理由。
(二)葛洪对子书的儒学化诠释
在葛洪生活的时代,儒学虽然已经受到道教和外来的佛教等思想的冲击,但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占据着统治的地位,有时候甚至成为统治者清除异己的借口。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氏杀嵇康等都是如此。葛洪要将子书创作作为合理合法的一生功业,就不得不解决子书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如果像嵇康那样“非汤武而薄周孔”当然是不行的,因此,葛洪在论述子书的性质时,对其作了儒学化的诠释。
1.葛洪从主旨方面对子书进行了儒学化的诠释
葛洪说:“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仰而比之,则景星之佐三辰也;俯而方之,则林薄之裨嵩岳也。虽津途殊辟,而进德同归;虽离於举趾,而合於兴化。故通人总原本以括流末,操纲领而得一致焉。”[6]98葛洪将儒家的五经称之为“正经”,比喻为道义的渊海,而将子书比作增加渊海深度的河流,其实就是说子书和五经本质上是一致的,是殊途同归的,子书不但无损于儒学,而且是正经的有益补充,是有助于“进德”和“兴化”的。这种“进德”和“兴化”的子书主旨表述正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班固对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描述相合,显然葛洪对子书的性质作了儒学化的处理。
2.葛洪从思想渊源方面对子书作了儒学化的诠释
葛洪说:“洪少有定志,决不出身,每览巢许、子州、北人石户、二姜、两袁、法真、子龙之传,尝废书前席,慕其为人。念精治五经,著一部子书,令後世知其为文儒而已。”[6]710我们看到,葛洪将著作“子书”建立在对“五经”的精治之上,这样一来,从思想渊源上讲,子书也是来源于五经,自然应该“属于儒家”。而且葛洪将著作子书视为文儒身份体认的方法和途径,无疑是将《汉书·艺文志》中分为九流十家的诸子统统纳入儒家的麾下,这样一来,子书所谓的“成一家之言”的“一家”,已不再像是先秦诸子那样与儒家并立的关系,而是成为儒家之中的一个思想分支。
通过对子书的儒学化诠释,葛洪将子书装扮成“兴化助教”的儒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虽然是汉代儒术独尊以后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正始以来的政治高压,特别是嵇康被杀、向秀入洛等事件对士人心态所造成的潜在影响,隐逸的合法性已经成为需要辩护的问题,而葛洪将子书儒学化,无疑为这种合法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三)子书创作的进一步个人化
葛洪子书观念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子书创作的个人化。这首先表现在子书的撰写方面,葛洪的《抱朴子》完全是由他自己独力完成,而且是自觉主动的创作。他在《自叙》中说:“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防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6]697根据这段论述,我们可以知道,葛洪从二十多岁时就已经开始自觉地起草撰写子书,历经十多年的时间到建武中定稿,在这个过程中全是葛洪独力创作,而且葛洪还自己对所作子书作了多次修订完善,他说:“他人文成,便呼快意,余才钝思迟,实不能尔。作文章每一更字,辄自转胜。”[6]696子书创作个人化趋向非常明显。
葛洪子书观念中,子书创作个人化还体现在对子书的归类方面。他在《自叙》中说:“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6]698《汉书·艺文志》将诸子之书归为九流十家,子书的家派归属乃是刘向、刘歆父子等后人根据一定的依据所定,而葛洪在《自叙》中,却是自己将所作子书作了家派归属界定,这种子书归类的自我界定,无疑说明了葛洪子书观念中的个人化倾向。
(四)子书创作与立身处世的分离
在葛洪之前,“立言”往往都是对立身处事之道的总结,言行一致是一种自然要求,孔子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但在葛洪的子书观念中,却将二者隔离开来,他一方面宣称“少有定志,决不出身”,另一方面却在所著《抱朴子》中讨论了大量的“君道”“臣节”等政治内容,所以在当时就引起了一些人的论难:“今先生高尚勿用,身不服事,而著《君道》《臣节》之书;不交于世,而作讥俗、救生之论;甚爱汗毛,而缀用兵战守之法;不营进趋,而有《审举》《穷达》之篇。蒙窃惑焉。”[6]408对此,葛洪回答说:“君臣之大,次于天地。思乐有道,出处一情,隐显任时,言亦何系?大人君子,与事变通。老子无为者也,鬼谷终隐者也,而著其书,咸论世务,何必身居其位,然后乃言其事乎?”[6]409葛洪认为子书的内容与立身处世是两回事,是隐居还是出仕是要根据时事决定,但无论是隐居还是出仕都“思乐有道”的“情”都是一样的,因此他的隐居与论政是“出处同归,行止一致”[6]411的 。
总而言之,葛洪的子书观念较之前一阶段又有了新的发展,葛洪一方面高扬子书的价值,以“深美博富”称扬子书,将之驾于诗赋等文章、学问之上,另一方面对子书作了儒学化诠释,将隐逸著述和立言助教结合起来,力图消弭汉代以来士人与政治的疏离关系,在进一步推动子书创作个人化的同时,也开始将子书创作与立身处世分离,使得创作子书进一步脱离了“身份”的束缚,为将来萧纲“立身之道,与文章异”观点的提出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葛洪子书观念的成因及其价值与影响
葛洪的子书观念是对其之前子书观念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也是晋代文学思潮发展的内在要求,不但在葛洪的思想体系构建中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葛洪之后子书观念的发展和子书创作的模式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我们考察晋代思想史和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观照视角。
(一)葛洪子书观念的成因
葛洪的子书观念当然是在前一阶段子书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但葛洪子书观念特性的形成,与晋代文学思潮和社会环境也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葛洪之所以特重子书,将子书凌驾于诗赋和谶纬、术数等学问之上,体现出一种求真务实的精神,与西晋崇尚玄谈的风气有关。葛洪著述《抱朴子》时,正当西晋由内争走向溃乱灭亡的时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观点倾向于将西晋的灭亡归结为玄谈之风的空谈误国,刘义庆《世说新语·轻诋》篇载:“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虚,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7]979王夷甫就是西晋玄谈的主要人物王衍,东晋桓温将西晋灭亡的原因归于玄学空谈,虽然未必完全符合事实,但至少表明西晋灭亡后,社会上开始有一种对玄学反思的潮流。葛洪在《抱朴子》中说:“常恨庄生言行自伐,桎梏世业。身居漆园,而多诞谈。好画鬼魅,憎图狗马。狭细忠贞,贬毁仁义。可谓雕虎画龙,难以征风云;空板亿万,不能救无钱;孺子之竹马,不免于脚剥;土柈之盈案,无益于腹虚也。”[6]411庄生就是庄子,葛洪批判《庄子》空虚无用,而《庄子》恰恰正是玄学家理论核心的“三玄”之一,葛洪在《抱朴子》中对玄学、放达和饮酒等现象的批判无不显示出时代风尚对葛洪子书观念的潜在影响。
西晋文学本不轻诗赋,陆机、左思、潘岳等人都以诗赋名家。陆机《文赋》说:“辞程才以效伎”,又说:“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5]763就是其诗赋观的极好注脚。但西晋的诗赋极重辞采,以繁缛为基本特征。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说:“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异班贾,体变曹王;缛旨星稠,繁文绮合。”[5]2218-2219明确点出了西晋文学重辞采的特征。葛洪以“深美博富”誉子书,以“辞赡义丰”为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均说明葛洪并不反对辞采,他将“深”置于“美”和博富之前,而将诗赋斥为“浅近之细文”,更多的可能是为了唤起对子书“义”的层面的关注,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文”的层面。
葛洪将子书儒学化,不但是汉代以来儒术独尊的发展结果,而且也与时代氛围息息相关。葛洪之所以不停地强调隐居著述是“立言助教”,与整个魏晋时期的政治形势也有关系。早在汉末时,由于政治的黑暗腐败,士人就与大一统政权产生了疏离;正始时期,司马氏与曹氏争权,导致“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8]而《世说新语·言语篇》的一段记载,将士人隐居不仕的危险描绘得十分真切:“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7]93司马氏杀嵇康的原因虽然比较复杂,但最明显的原因就是他“非汤武而薄周孔”,不与司马氏同流,所以嵇康被杀对天下名士的震动是很大的。没有正当理由的隐居不仕,实在是有“以自己的高洁,显朝廷污浊”的嫌疑,所以葛洪说:“仆所以逍遥於丘园,敛迹乎草泽者,诚以才非政事,器乏治民,……若拥经著述,可以全真成名,有补末化;……虽无立朝之勋,即戎之劳;然切磋後生,弘道养正,殊涂一致,非损(化)之民也。劣者全其一介,何及於许由,圣世恕而容之,同旷於有唐,不亦可乎!”[9]59而在《逸民篇》中士人的话更是这种危险的直接表述:“然时移俗异,世务不拘,故木食山栖,外物遗累者,古之清高,今之逋逃也。”[9]64在这种情况下,葛洪力辩自己之所以不出仕,是因为自己没有从政的才干,而且自己虽然不仕,但拥经著述,也是有补于教化的,这也是他将所作子书作儒学化诠释的又一原因。
(二)葛洪的子书观念在其思想体系构建中的理论价值
葛洪的子书观念对于他的思想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葛洪的思想其实是内神仙而外儒术的,他的思想核心是神仙道教的,但他在著述子书时,通过《外篇》的著述和将子书儒家化的诠释,获得了“立言助教”的合法外衣,他在《自叙》中说:“凡著《内篇》二十卷,《外篇》五十卷,……其《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6]698他通过将子书的创作和学派归属的个人自定,以及将立身处世与立言分离开来,进一步解放了“立言”的身份限制和社会限制,使得创作子书成为名正言顺的合理选择。
(三)葛洪的子书观念对后世子书的影响
葛洪的子书观念对其后的子书思想和子书创作也有较大影响。如萧绎在《金楼子序》中说:“盖以金楼子为文也,气不遂文,文常使气。材不值运,必欲师心;霞间得语,莫非抚臆。松石能言,必解其趣;风云元感,倘获见知。今纂开辟以来,至乎耳目所接,即以先生为号,名曰金楼子。盖士安之玄宴,稚川之抱朴者焉。”[10]249-250萧绎是将葛洪著作《抱朴子》作为自己的效法对象。另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以“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4]162将子体和论体区分开来,与葛洪崇博尚深子书价值观一脉相承,可见葛洪的子书观念对后世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 余嘉锡.古书通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3] 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1180-1181.
[4] 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 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6]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M].北京:中华书局,1997.
[7]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360.
[9] 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0] 柯庆明,曾永义.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料汇编[M].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249-250.
The Zishu Concept of Ge Hong
WU Xiang-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1,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the Zishu changed greatly in the Han Dynasty,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Ge Hongs concept of the Zishu showed some new characteristics worthy of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this change. At the same time, GE Hong made a Con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Zishu, interpreting the creation of the Zishu as the way to recognize the identity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way of teaching assistants. He also promo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the creation of the Zishu and separated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tanding up and speaking, which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of writing after the creation of the Zishu, which made a Con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nature of the books and interpreted the nature of the books as well as the nature of the books, and interpreted the creation of the books as the way to recognize the identity of Confucianism and the way of teaching assistants. GE Hongs concept of the Zishu is a reflection of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special era of Jin Dynasty, which not only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in Ge Hongs ideological system, but also ha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The concept of later
generation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Zishu have also had a certain impact.
Key words: Ge Hong;Zishu emphasize concepts;self-awakening of Zhuzi Style
責任编辑 赵文清
收稿日期:2019-07-15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空间维度的晋代江南文学研究”(2017SJB1737);江苏理工学院社科基金项目“葛洪研究”(KYY14524)
作者简介:吴祥军,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