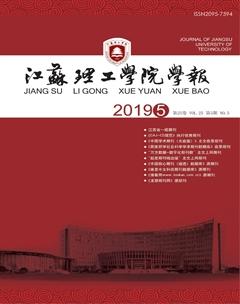南朝吴声曲辞的叙事色彩
摘 要:南朝文学作品中存有470余首乐府民歌,其中吴歌曲辞占有绝对比例。它们作为吴地文学的代表,展现出鲜明的叙事色彩。从吴声曲辞叙事性的成因入手,探究其在内容、结构、语言方面的叙事性表现,并分析南朝吴声曲辞叙事性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南朝乐府诗;吴地文学;吴声曲辞;叙事性
中图分类号: I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394(2019)05-0037-04
在南北朝文学史中,乐府歌辞定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时期的乐府诗歌已然发展到成熟阶段,它具有民间文学的蓬勃生气,出语天然而不加雕饰,内容质朴又贴近生活,情感真挚能打动人心,诗风明快朗朗上口。所以,乐府诗的创作模式很快就在全社会流传开来,从市井走向宫廷,从民间蔓延至上层,将新鲜的血液输入文人的创作中去。
南北朝乐府诗以南朝为重,而南朝乐府诗又集中发轫于长江流域,是历代江南文学的典型代表。从数量上看,南朝乐府诗近500首,全部存录于宋代郭茂倩编纂的《乐府诗集》中,其中绝大多数被归入“清商曲辞”一目,只有《西洲曲》《苏小小歌》《东飞伯劳歌》等不足10首诗列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类目下。“清商曲辞”又分为“吴声曲辞”和“西曲歌”两类,其中有“吴歌”326首,“西曲”142首。从地理位置上看,以六朝都城建邺(今南京)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自古为“吴地”,故此处的乐府民歌被称作“吴歌曲辞”。《晋书·乐志》有言:“吴歌杂曲,并出江南。”[1]675《乐府诗集》曰:“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邺。吴声歌曲,起于此也。”[2]570而长江中游的江汉地区是南朝西部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歌是为“西曲歌”。《乐府诗集》引《古今乐录》载:“西曲出于荆、郢、樊、邓之间,而其声、节、送、和与吴歌亦异。”[2]607由此可见:吴声曲辞在体例和内容上都是南朝乐府诗的缩影,是当时社会文化背景在文学中的投射,故而本文将探究吴声曲辞的叙事性成分,分析其文化价值下的文学特征。
一、吴声曲辞的叙事性成因
吳声曲辞的叙事性题材和内容,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它们或从文学的源流继承角度为吴声曲辞叙事打下基础,或从客观的外部社会环境为吴声曲辞叙事提供素材,两者共同作用下才形成了丰富的吴声曲辞叙事性。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以吴声曲辞为代表的南朝乐府诗,保留了古风诗歌的特征,沿袭了古体诗的叙事传统。从《诗经》到汉乐府民歌,其题材内容均来源于真实社会生活,行文以质朴自然为主,语言平实,不讲究严格的韵律规则,常采用动作描写、语言描写等手法突出叙事元素,具有鲜明的叙事性。南朝乐府诗与汉乐府民歌一脉相承,从文体类型到艺术特点,均保持了高度的相似性,从而构成了吴声曲辞叙事性的主要成因。
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角度而言,吴声曲辞发轫于六朝时期,学术思想较为开放,描写百态生活和真实情感就成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常态,所以叙事的元素也随之增多,叙事性亦增强。魏晋南北朝政权更替频繁,传统道德规范失去约束力,统治者对人民的思想控制较为宽松,追求人生的快乐、情感的满足,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趋势。如《晋纪·总论》载:“其妇女……先时而婚,任情而动,故皆不耻淫佚之过,不拘妒忌之恶。”[1]125这样的社会风气投射在文学中,导致文学创作并无太多避讳,涌现出大批描写男女爱情生活及情感的作品。
从地理经济和历史人文的角度而言,江南则是乐府诗歌成长、繁荣的沃土,它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为吴声曲辞提供了发展空间,可以入诗的事物层出不穷,同样促进了文学叙事性的发展。首先,江南地区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山川明媚,水土丰茂,物产丰富,气候温宜,拥有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东晋以后,吴地的商业、手工业也得到长足发展,让吴地更加富庶。优渥的经济环境,使江南人民生活得较为惬意,培养出他们温婉多情又细腻浪漫的性格特点。其次,吴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创作民歌的传统可以追溯至春秋的吴越时期,《汉书·艺文志》便记载汉乐府中有“吴楚汝南歌诗十五篇”。在这种天然美好的环境中,曲辞易于发达。悠闲又善感的男女们,常常为生活中的琐事而触动,生发出缠绵的喟叹。《南史·循吏列传》载:“(宋世太平之际)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永明继运……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3]
从创作群体的文学素养而言,吴声曲辞大多出自底层人民之口,主要反映中下层百姓的生活和感情,所以叙事的成分居多,形成了吴声曲辞的叙事性。南朝乐府诗的作者来源既有文化水平较高的文人群体,也有普通的平民百姓,且民间创作的乐府诗占绝大多数。由于受学识学养所限,底层人民对抽象化、艺术化的规范行文模式并不熟悉,只能用平实的语言和直白的叙述方式自由地浅唱低吟,歌唱的内容也是大家能接触到的日常生活和由琐事生发出的情感。所以,吴声曲辞不仅非常贴近百姓的心理,而且口语化色彩浓厚,作品的叙事成分比重大,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叙事性。
二、吴声曲辞的叙事性表现
吴声曲辞的叙事性在其题材内容、表达手法、情节结构等方面得到体现。
首先,吴声曲辞作为南朝乐府诗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缘事而发”的特征,在题材内容上表现出与事件的密切相关,呈现出的文本也是针对某一事件的概述。事件不仅是构成全篇的基础,也是作者抒发情感的主要动因。以吴声曲辞的代表作《子夜歌》为例。相传《子夜歌》的曲调是晋代一位名叫子夜的女子创作,抒写哀怨或眷恋之情,据《宋书·乐志》记载:“《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声。”故名。《乐府诗集》中收录五言四句式的《子夜歌》共42首,其内容是以一位女子的口吻,讲述了自己和情郎从甜蜜相依到被无情抛弃的过程,这些诗作既能够独立成篇,也可以合在一起形成组诗,与《子夜歌》曲调的内涵相合。全文从“落日出前门”起笔,点明时间和事件的起因;当男女二人相见时,“宿昔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这一场景描写展现出浓烈的柔情蜜意;待到分别时,女子不舍地问道:“今夕已欢别,合会在何时?”但随着分离的时日渐久,女子的生活充满了悲情,在“别后涕流连,相思情悲满”的同时,还要接受“郎为傍人取,负侬非一事”的现实,原本美好的愿望落空了,留给她的只有一缕织不成匹的乱丝。将全篇贯穿起来赏析该诗,更能看出叙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多个片断场景串联在一起,便于把握女主人公的情感波动,由叙事元素衍展出抒情话语的展开,解读更加透彻。所以,“缘事而发”的诗歌创作要求作者在构思中采用韵文的形式,将一个事件拆分开来,与抒情性的语句杂糅在一起,丰富了诗歌的意蕴层面。由此可以看出,吴声曲辞不仅具有乐府曲辞的音乐性、抒情性特征,而且还充盈着丰富的故事情节,呈现出浓厚的叙事色彩,是南朝乐府诗具有叙事性的有力佐证。
其次,吴声曲辞大量采用对话或独白的语言描写形式进行叙事。将语言描写引入诗句,是韵文叙事性的典型表现之一,它是将人物语言与情节发展融为一体,直接用故事主人公的口吻说明事件的节点,使诗歌的情节性更强,更具有感染力和说服力。吴声曲辞常为描写男女爱情题材的情歌,且以女性口吻居多,故而诗歌中存在大量的语言描写,它们或是对话,或是独白,大胆突破宗法礼教思想的束缚,热烈而坚定地唱出她们的爱情心声。在吴声曲辞中,常见人称代词“我”“妾”“君”“郎”等,皆是女性对自己的自称与对情人的昵称,是语言描写的独特标志。如“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子夜歌》)是女子在自言自语中抒发对爱情的渴望;“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子夜四时歌·冬歌》)是女子面对困境,坚定地表示对爱情的矢志不渝;“人传欢负情,我自未尝见。”(《子夜变歌》)是痴情的女子对于负心汉的盲目无视,自我欺骗。这些带有丰富感情的口语化表达方式体现出乐府歌辞率真自然、不加雕饰的风格特点。《大子夜歌》有云:“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这首本为点评子夜女悲情的歌谣,也从侧面点明《子夜歌》的语言特征,即“清音”“天然”,这正是以吴声曲辞为代表的南朝乐府诗所具有的叙事性表现。
再次,吴声曲辞中有很多对具体生活情状的描写,它们不仅成为记录当时社会现实的史料性依据,而且还具有曲折的情节性,构成了叙述事件的过程,这些带有“诗史”性质的文学叙述即为吴声曲辞叙事性的体现。如《读曲歌》中的两首诗:
家贫近店肆,出入引长事。郎君不浮华,谁能呈实意?
登店卖三葛, 郎来买丈余。合匹与郎去,谁解断粗疏?
从诗的首句即能看出主人公身份,“家贫近店肆”和“登店卖三葛”表明这是一位生活在城市底层的商家,并且生活不富裕;接着,诗中又出现了“郎君”“郎”等词,是女子对情人的昵称,进一步补充说明主人公是一位商户女子。而普通市民的主要衣料也是葛布,且购買力有限,“丈余”刚好是做一件衣服所需。由此可以得知,六朝时期,百姓的生活仍然非常艰苦,但封建礼教对人民的束缚较弱,女子能够抛头露面做生意,这与当时的政治是有关联的——六朝社会混乱,朝代更迭频繁,统治者忙于组织自己的势力,对于文化方面的控制还未顾及,所以对百姓而言,一方面生活艰难,另一方面思想却开放。通过这两首诗,即可窥见一斑。所以,吴声曲辞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历史现实,这是叙事性在文学中的巨大价值。
三、《子夜四时歌》的文学史影响
吴声曲辞所代表的缘事而发、语言质朴、记录现实的表达方式,对当时和后世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影响了后世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萧涤非在其《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书中谈及:“南朝乐府,以前期民歌为主干,梁陈拟作,则其附庸。然不有此种拟作,则民歌影响,亦莫由而著。溯自东晋开国,下迄齐亡,百八十余年间,民间乐府已达其最高潮;而梁武以开国能文之主,雅好音乐,吟咏之士,云集殿庭,于是取前期民歌咀嚼之,消化之,或沿旧曲而谱新词,或改旧曲而创新调,文人之作,遂盛极一时……”[4]由此可知,南朝的民间文学已形成一股诗歌思潮,极大地推动了文人诗歌的发展。
南朝时期的文人在接受乐府民歌的基础上,沿用旧题拟作新声,创作了大量文人乐府诗,将朴素的民间文学雅化、规则化,开始以文人的视角观察并叙述人民的生活风貌。其中,《子夜歌》是数量最多、流传最广、唱和率最高的乐府曲辞,同时代出现的《子夜四时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等多首变调,仅梁武帝萧衍一人,便沿用旧曲谱新辞,创制出7首《子夜四时歌》。乐府诗不仅从市井走入宫廷,还从江南地区深入江汉地区。《宋书·乐志》称:“随王诞在襄阳,造《襄阳乐》;南平穆王为豫州,造《寿阳乐》;荆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乌飞哥曲》,并列于乐宫。歌词多淫哇不典正。”[2]607这几篇作品即为“清商曲辞”类目下的“西曲歌”一类,是被朝廷乐官收集并整理后,进入宫廷音乐的乐府诗雏形。
吴声曲辞的叙事模式,还对后代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仿照南朝乐府《子夜四时歌》的基础上,创作了同名组诗《子夜四时歌四首》:
春歌
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素手青条上,红妆白日鲜。蚕饥妾欲去,五马莫留连。
夏歌
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
秋歌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冬歌
明朝驿使发,一夜絮征袍。素手抽针冷,那堪把剪刀。裁缝寄远道,几日到临洮?
诗人分别以春、夏、秋、冬四时情景分别叙述了四件事——《春歌》采用了檃栝手法,将汉乐府民歌《陌上桑》的故事进行了改写,以主人公秦罗敷在河边采桑的事件为起因,将罗敷拒绝使君的对话语言“蚕饥妾欲去”等叙事因素在诗中得到明显体现,叙事色彩浓厚;《夏歌》以绍兴鉴湖夏景为叙事背景,讲述了身为浣纱女的西施在若耶溪采莲的历史故事;《秋歌》写戍妇为征人织布捣衣之事,运用了独白式的语言描写“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体现出该诗的叙事性;《冬歌》承接上篇《秋歌》,也是描写戍妇为征夫缝制棉衣之事,诗中不仅运用独白体的语言描写,还加入了“抽针”“把剪刀”等动作描写,叙事元素更加丰富。通观四首诗,用四季形成组诗的串联方式妥帖且巧妙,层次分明,结构严谨。
综上所述,吴声曲辞作为南朝乐府诗的典型代表,其叙事色彩是不容忽视的一个研究方面。它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又反映了相应的社会现实,并且在文学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 郭茂倩.乐府诗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3] 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696-1697.
[4] 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284.
On the Narration of Wu Dialect Poetry in the Southern Dynasties
XU Meng-jie
(School of Human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101,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more than 470 Yuefu folk songs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literary works. Among them, Wu dialect poetry has an absolute proportion. As representatives of Wu area literature, they show a distinct narrative color. This thesis intends to start from the origin of Wu dialect poetrys narrative, explore its narrative
performance in terms of content, structure and language, and analyze the historical influence of the narrative of Wu dialect poetry in the Southern Dynasty.
Key words: Southern Yuefu poems;Wudi literature;Wu dialect poetry;narrative
责任编辑 赵文清
收稿日期:2019-08-12
作者简介:许梦婕,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