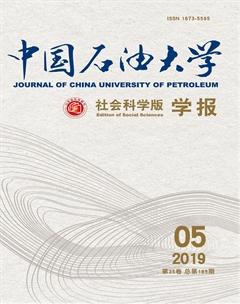《西游补》的“无名焦虑”与梦境书写初探
化萌钰
摘要:《西游补》的主旨,虽然历来被人们认为是批判社会现实,破情根立道根,但小说中透露出的潜意识焦虑同样值得注意。在与外部世界斗争受到阻挠时,主人公行者内心焦虑,行为延宕,并最终产生了幻灭之感,这种无名焦虑贯穿了小说始末。而受到焦虑情绪影响的行者形象,正是作者董说的自况。此外,《西游补》大篇幅的梦境描写,来源于董说的嗜梦情结和孤高个性。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得《西游补》成为了一部极具现代性,甚至有些意识流的作品,在中国古典小说中独树一帜,值得探究。
关键词:《西游补》;董说; 焦虑;梦境
中图分类号:I2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5008306
《西游补》作于明清鼎革之际,虽被列为《西游记》三大续书之一,实际却是作者巧借《西游记》的人物设定,重新编排的一出截然不同的故事。董说借行者以喻己,借鲭鱼世界以状晚明,其精彩绝伦的想象与独特的写作风格令人印象深刻。
在嶷如居士所作的序文里,行者所经历的幻境被分为“思、噩、正、惧、喜、寤”六梦,“约言六梦,以尽三世”。[1]2小说创作的目的似乎一目了然,即通过梦境世界来映射现实世界,剖析世相百态,达到揭示与讽刺的效果。从这一层面来看,《西游补》的确是一部批判性極强的小说,甚至被很多人认为是明清讽刺类小说的代表。但小说的深层含义显然不止于此,许多着眼于外部世界的刻画,最终都回归到了人物内心:行者的内心,亦即董说的内心,在与外部世界斗争、追求心中所想的过程中,董说及其笔下的行者都受到了来自大环境不可抗拒的阻力,内心焦虑,行为延宕,最终产生了幻灭之感。面对现实的焦虑感几乎贯穿《西游补》始末,使其成为了一部篇幅虽短,却有着浓厚悲剧性和复杂内涵的复调主题小说作品。《西游补》的创作与董说的生平和性格、嗜好息息相关,书中的“行者”,正是现实生活中董说的映射。因此,结合董说的一生来探究《西游补》的复杂主题是十分必要的。此外,除了主题的深刻性,《西游补》独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极具现代性的叙事模式,都使得它成为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异类”,颇富研究价值。
一、《西游补》研究简述
《西游补》诞生于明末清初,最早关于此书的研究也产生于这一时期。明代嶷如居士《西游补序》、静啸斋主人《西游补答问》、无名氏《续西游补杂记》等,都是这一时期文人对《西游补》所做出的评价式文章。近代有记载的《西游补》研究文献很少,且大多是概括性的简短介绍。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称其“造势遣辞,则丰赡多姿,恍惚善幻,奇突之处,时足惊人,间以俳谐,亦常俊艳,殊非同时作手所敢望也”[2],评价颇高。
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对《西游补》的关注度有所提高,但研究专著仍然很少。傅世怡《〈西游补〉初探》,探讨了《西游补》的作者、版本、取材、主题、创作技巧、优点及瑕疵等诸多方面的内容。[3]赵红娟《明遗民董说研究》一书,详细论述了董说的家庭背景、生活遭遇以及梦癖、香癖等诸多癖好,并分析了董说文学创作的独特风格。[4]
近年来,《西游补》逐渐为更多人所了解,相关研究著述也有所增多。有关《西游补》的论文约有近百篇。其研究方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西游补》的作者之争。自《西游补》进入研究视域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可其作者当为明遗民董说。刘复先生结合董说《漫兴十首》“西游曾补虞初笔,万镜楼空及第归”,认为《西游补》作者当为董说无疑。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此书作者当为董说之父董斯张。如高洪均以《西游补》署名为“静啸斋主人”,而董斯张斋号静啸斋为由,认为其作者当为董斯张。[5]
《西游补》与《西游记》之比较。一些学者认为,《西游补》名为《西游记》续书,实际却是一部独立创作的小说作品,与《西游记》关系不大。如赵红娟认为《西游补》适当处理了续书与原著的关系,内容上有所萦带,主题上有继承有超越,情节、人物都与《西游记》有所关联,是中国续书的最佳例子。[6]
《西游补》创作主旨。苏兴认为,董说是借梦境世界书写现实的生活经历和心态情绪。[7]童琼指出,《西游补》是通过佛家梦幻悟空的思想来表现作者不懈追求理想、又对现实失望、不得不寻求解脱的心路历程。[8]王厚怀认为《西游补》中的妖魔由“外魔”转向了“内魔”,从而引起了主题的翻新。[9]朱萍认为《西游补》是一部主题相当复杂的小说作品,不可仅将其视为讽刺小说或佛道小说。[10]
《西游补》创作技巧。刘雪真以西方的互文理论探讨了《西游补》的创作手法与创作意图。[11]赵红娟论述了《西游补》创作风格上的荒诞性和意识流色彩。[12]李梦圆探讨了《西游补》的现代性在视觉方面的体现。[13]
总的来说,关于《西游补》的研究著作不多且方向相对集中,而对主人公焦虑情绪则少有探讨。
小说中行者的心理状态非常复杂,其“无名焦虑”有很强的现代性,在明清古典小说中实属罕见。分析这一情绪的表现及背后的成因,对于我们理解《西游补》的复杂主旨以及深入了解董说其人,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荒诞梦境:投射于文字的焦虑
(一)《西游补》的梦境书写
《西游补》全书共分十六回,描写了三层梦境:第一层,新唐;第二层,青青世界;第三层,万镜楼。前三回写行者由现实世界进入新唐。第四回为过渡,行者由新唐进入青青世界,又由青青世界进入万镜楼。从第五回到第十回,行者都盘桓于万镜楼里的大小世界中。万镜楼中有头风世界、古人世界、未来世界以及行者一直追逐却最终未能进入的蒙瞳世界。第十一回至第十五回,行者重返青青世界寻找师父。直至十六回行者方才觉醒,重新回到现实世界。
在游历这三层梦境世界的过程中,行者一直处于茫然而焦虑的状态。这种焦虑有时会直接从他急躁的语言、动作中直接体现出来,有时则间接表现为消极的态度、奇怪的举动,等等,形成难以捕捉却又到处弥漫的“隐形焦虑情绪”。这种焦虑情绪是以累积的形式一直伴随行者的,随着入梦越深、时间越久,行者的焦虑情绪就显得越是浓重。行者的情绪变化大致遵循以下线索。
首先,是紧急而被动的入梦时刻。单从情节上来看,行者入梦的起始是一次再简单不过的化饭行为,入梦的原因似乎也与他的心理状态毫无关联。但作者早已在前章埋下了伏笔。
在入新唐之前,行者“打杀春男女”又心怀不忍,作下一篇“送冤文字”。点评称此举是“一念悲怜,惹起许多妄想”[1]5,这正是行者坠入梦境的起点,也是其入梦的真正原因。此回中还有唐僧说行者“牡丹不红,徒弟心红”一节,都表明事情的起因是行者动了情念,进而坠入情欲世界,惹起诸多纷扰。乍一入梦的行者短时间内遭遇了大量的否定与自我否定,无法理解眼前的景象:
行者此时真所谓疑团未破,思议空劳。他便按落云端,念动真言,要唤本方土地问个消息。念了十遍,土地只是不来。[1]7
不仅土地不来,而且行者还发现自己上不了天庭,转而又被诬蔑成偷天的凶手。种种谜团还未弄清,又闻得秦王有个驱山铎,行者便忘了化饭,也忘了不知真假的新唐,一心只想找秦始皇拿得此铎,助自己西天路上扫平妖寇。此念刚定,转眼又听得新皇要让师父做西天杀青大将军。行者恐其有难,想要飞身前去营救,又怕打草惊蛇连累了唐僧。种种异象在短时间内不断冲击行者的认知,使他往日的才智和法术全无用武之地,只能一次次地陷入怀疑与自我怀疑之中,“越发苦恨,须臾闷倒”[1]12。
其次,是万镜楼的离奇与荒谬。在这里行者的行为表现出更强的不连贯和不确定性。小说第四回题为“一窦开时迷万镜,物形现处我形亡”[1]15,仍是暗示万镜楼的种种遭逢都是情窦一开所引出的许多妄想。行者在无路可进的青青世界城门口左冲右撞,“撞开一块青石皮,忽然绊跌,落在一个大光明去处”[1]15,这去处即是万镜楼。在这座由宝镜砌成的大楼里,行者开启了长达七回之久的镜中游历。行者几次变换身份,先是眼见了头风世界可笑可悲的举子,慨叹文章气衰,一班名曰秀士之人却只会作“纱帽文章”;又化身虞美人,于古人世界目睹了耽于美色的霸王项羽,从他处问得秦始皇的下落;复又掉入未来世界,细数恶鬼秦桧的种种罪行;及至走至山东地方,遇见从蒙瞳世界回来的新古人,忽又生出“秦始皇未必肯松松爽爽将驱山铎拿出来”的想法,猛地就要跳出镜子。从入镜到出镜,行者的遭遇和选择皆是随机生发,无规律可寻,内容也尽是荒诞诡谲。
值得注意的是,在入镜之前,曾有行者的故人刘伯钦出现在一面兽纽方镜中,试图提醒行者这不是他平时所处的真实世界:
你在别人世界里,我在你的世界里,不同,不同![1]16
这里的刘伯钦实际是行者部分清醒意识的具象。行者在进入万镜楼后曾有过短暂的意识觉醒,但被当时处于懵懂状态的他忽略了。潜意识里,他把刘伯钦的出现当作了镜中世界对自己的邀请,再加上“此时将暗,也寻不见师父”[1]16,因此“不如把幾面镜子细看一回,再做料理”[1]16。入镜就这样变得顺理成章了。最终,当行者挣扎着跳出万镜楼,发现自己是为红线所困,情迷其中,才游历了过去未来世界时,又有一位老者出现,替他解下红线放他去救师父。
这位自称是孙悟空的老者和前篇中的刘伯钦,其实都是行者理性人格的短暂显现。董说将行者“入情”的过程处理成“入梦”的形式,而这种由其他人物呈现出的“出梦”的效果,即是理性暂时觉醒带来的“出情”的倾向。只可惜这种觉醒是极其短暂且混沌不清的,并不足以将行者带离这个庞大的鲭鱼世界。
最后,行者的爆发出现于第十五回末尾的五色旗混战。万镜楼之后,混战之前,他刚刚目睹了素日最为尊敬、拼全力保护的师父背叛取经大业,沉迷女色,甚至写离书赶走八戒、沙僧的可怕景况,又见到了自己不知从何而来的嫡亲儿子波罗蜜王。从初入新唐的无主无张到最后的奋起反抗,行者完成了梦境中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回击。
这次彻底的觉醒,源于行者已经陷入情欲至久至深,而梦境的发展也已到达最荒诞、最恐怖的阶段。自五行山下被救以来,行者虽然尽心竭力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但是其内心深处却并不能做到一丝杂念也无。对师父和师弟们有不信任,对取经事业有怀疑与动摇,甚至对情与性有欲望,这些都是我们在《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身上所看不到的阴暗面,却是董说想要竭力挖掘的东西,按照他的说法,行者至此便可由“入情”走向“入道”,认识到断绝情欲的重要性,从此破除情根,“认得道根之实”。“五旗色乱是心猿出魔根本”[1]71,此回混战之后,行者在虚空主人的召唤下逐渐醒转,跳出梦境之外,继续陪伴唐僧走上西天取经之路。
《西游补》呈现出的结局却并非如此积极——行者潜意识里的焦虑、怀疑和恐惧的确都被恢复的理智暂时压制了下来,却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更没有消失。醒转过来的行者并没有对这番荒诞的经历做出任何评价,也没有向师父或师弟中的任何一个吐露自己心中的困惑、恐惧与愤怒。直到故事结束,行者也并没有展现出大彻大悟的从容,而更像是一个做了噩梦的人突然被惊醒,又匆匆走上取经之路。行者最终靠这种逃避的方法重新获得了内心的平静。
(二)董说的焦虑困境
董说生于明泰昌元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五年,既经历了晚明光宗、熹宗的荒淫无度和魏忠贤阉党的独断专权,更见证了清军入关、明清鼎革的历史性事件,社会历史带给董说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
《西游补》中流露出的末世氛围和行者的焦虑情绪,很大程度上与董说在现实社会中承受和目睹的伤痛有关。
在进入新唐的第二个阶段,行者在绿玉殿留下了他对梦境世界的第一次批判:
朝廷有此等小臣,那得皇帝不风流?[1]8
这显然是在代董说发声。鲭鱼世界对行者来说是梦境,对董说却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晚明群臣党争和阉党专权导致国家政令极度不合理,导致民生凋敝。在董说的青年时期,晚明种种民生问题日趋严峻。在民间,持续饥荒威胁着普通百姓的生命安全,父子兄弟相食的事情随处可见。史景迁《王氏之死》记载过当时山东农村的这样两句谚语:
兄食其弟,夫食其妻,辄相谓曰:与其为人食,不如吾自食,稍延旦夕之命。
与其父子兄弟夫妻俱毙,不如食父食兄食夫,自延其命也天理。[14]24
在与清军抗争的军队里,将士们也常常拿不到军饷,甚至连吃饱肚子都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士兵加入打劫百姓的行列,造成了更加深重的灾难与恐慌。与饥荒相伴的,是晚明的盗匪和苛税问题。一方面,来自官府的高额税收压得百姓喘不过气;另一方面,来自地方的土匪强盗、士兵、难民一遍遍地洗劫着百姓们为数不多的财产和口粮,人性的恶在活下去的欲望面前被无限放大,晚明社会民变事件层出不穷。
种种乱象堆积成晚明朝不保夕的生活,使得人们的信仰纷纷濒临崩塌。
末世危机感开始在无数善于思考的文人士子心底生根发芽。
文人们也许不必像底层百姓一样担心明天的口粮,但内心的惶恐、愤怒与无力感却是摆脱不掉的社会生活副产品。董说作为乱世文人的一分子,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孤高正直性格的裹挟下,其背负的思想包袱和受到的情感折磨,无疑更重更深。
厌恶现实又心系现实,热爱梦幻又不忍耽于梦幻,不屑功名却又困于功名,董说背负了大半生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看作是晚明士子们集体心境的一个集中放大。
在个性解放之风盛行的晚明,世人思想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也走上了一个新台阶。在朝不保夕的日子里,满足物欲与情欲成了许多人发泄焦虑情绪的出口。董说虽然也深受焦虑的困扰,但他的纾解却有所不同。
(三)董说的嗜梦情节
《西游补》对梦的看重,很大程度来源于董说浓重的嗜梦情结。对“梦”的喜好,乍听之下难以想象,可董说却几乎将这份喜好发展到了极致。崇祯十六年(1643),年仅24岁的董说为自己刻下了“梦史”“梦乡太史”两枚印章,称自己是执掌梦国国政的太史,每日有意识地做梦、记梦,甚至主张成立“梦社”,要求入社的朋友把自己的梦写下来寄给他。他还编纂了《梦乡志》《昭阳梦史》二书,专门记录所做之梦,分别收录于《丰草庵前集》和《丰草庵全集》。董说还在自己所居的丰草庵刻梦乡碑:“禹篆学成人莫笑,草堂待勒梦乡碑。”[15]在《梦乡志》中,他曾把梦乡分为“玄怪乡、山水乡、冥乡、识乡、如意乡、藏往乡、未来乡”,与《西游补》中的“头风世界、古人世界、未来世界、蒙瞳世界”有异曲同工之妙。董说的《丰草庵集》亦随处可见记梦写梦的作品。《答西溪客用前韵四首(其二)》中,董说表达了自己喜欢用文字记录梦境的特点,“说梦无征随笔录,炼香依谱倒瓶埋”。《丰草庵诗集·人间可哀编》所载《梦乡词》一首,充分体现了董说对梦的喜爱与倚重:
合眼何曾是病夫,穿云屐子不教扶。春来五狱都游遍,笑煞宗家壁上图。人间底事觅封侯,梦国消摇也破愁。枕中一帙名山志,拣得仙崖次第游。客到柴观正夕陽,相逢莫说少年场。西窗对展流黄蕇,聊复同君梦石梁。[16]
董说对梦的嗜好及其厌恶功名、乐于隐逸的性格特点,很大程度上来自家族传统的影响。以董说祖父董道醇、大伯父董嗣成和父亲董斯张为代表的董家人,大多饱有才学,长于诗文,性格上刚直不阿,抱志固穷,董说继承了这一家族品格。董说孤僻的个性和对梦的嗜好,也是在现实中磨砺出的苦果。董说并非生来就厌恶世俗,他幼年好学,“星灿灿,且栉且沐”;“属先生令晚起,久之勿改”。青年时代的董说也曾走上了科举之路,但很快就对钳制文人思想的应制作文反感至极,放弃了科举致仕的道路。年轻时与复社文人的广泛交往又使得董说成为了一个民族感极强,对时事有强烈批判精神的现实关注者。然晚明内忧外患并重,凭借董说一己之力实难回天。目睹惨象的痛苦和有心无力的愤懑都使他不得不学会逃避。遁迹梦境、沉迷书海、香烟,在他逃避现实的过程中逐渐变成了习惯,并占据了他生活的绝大部分重心。
除嗜梦之外,董说还极好读书。董说一生都在和书打交道,自称“我除了六年,五十年读书”。钮琇《觚剩续编》称他:“每一出游,则有书五十担随之,虽僻谷之深,洪涛之险,不暂离也。”[17]不但爱读书,董说也爱写书。他年纪轻轻就遁入空门,几十年来笔耕不辍,一直试图用文学缓解其内心的挣扎与不安。最终,董说选择了文学作品中一个虚拟的人物来与他分担这份焦虑。董说在《西游补》中的人生态度和世界观,都透露出更为强烈的幻灭感。他不认为“情”是多么值得宣扬的东西,甚至故意让平日里耀武扬威的大圣历尽情劫,又在其中设下种种明喻暗喻,为的就是告诉世人:“情”不过是一场恼人的虚幻。董说在选择这位主人公时,绝不是没有考量地仓促行之。《西游记》里大名鼎鼎、无所不能的孙行者,天赋异禀,既能呼风唤雨降妖除魔,又有着十足的正义感,无疑是标杆式的正面人物;但他出身草野,在真正“定心”跟随唐僧取经之前,也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喜怒哀乐嗔痴贪怨,这就又使他同人间无限地接近了。董说十分准确地看到了行者身上这两种特质的纠缠,并将自己身上不可控制、无法摆脱的苦闷、迷茫与哀愁,通过梦境,悉数交给了行者。于是读者和董说都看到了行者的挣扎和痛苦:从前雷厉风行、一呼百应的齐天大圣忽然变成了一个纠结、拖延、小心翼翼的延宕者,总是想要抗争,又总是抗争无效。这是董说给自己的精神写照,也让读者借此能够了解到用情过深带来的副作用有多么强烈,足以让行者这样的英雄威风扫地。而董说自己,同样能够从行者的苦痛中分得一些自我麻痹式的精神慰藉:齐天大圣都要花好大一番精力才能挣脱的焦虑牢笼,凡人董说又怎能轻易逃得出来。可董说还是在小说的结尾为行者安排了一个较为理想化的结局,让他识破情魔,重获了内心的平静。行者的结局,无疑是董说自己也想要的。可现实却是,就在写作《西游补》的期间,董说依旧被这份焦虑苦苦纠缠,所以破情入道结局也并没有显示出太强的说服力,反添了一丝幻灭的意味。
从董说存世不多的诗文中也可以看出,他至死都没有真正逃脱现实的桎梏。民族气节与士人的社会责任感,董说内心深处受儒家为学致仕思想的浸濡,使得他一生都在入世与归隐之间苦苦徘徊。现实生活日复一日带来的无力感使他长期处于一种无名焦虑之中,这种焦虑也直接地影响到了其文学创作的风格。《西游补》中行者面临的困窘,正是董说其人的真实写照。董说敏感而特立独行的性格以及那个他深陷其中的焦虑牢笼,都是他能在青年时期创作出《西游补》这样充斥着灰色情绪、荒诞而富于想象的小说作品的重要原因。
三、理性退场:梦境书写与无序感
《西游补》艺术风格的与众不同,很大程度在于其梦境描写的荒诞与夸张以及由此带来的纯粹的艺术美感。传统中国文学中涉及梦境的描写,大多仍是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没有脱离合理的文学想象。《庄子》作为中国梦境描写的开先河之作,想象瑰丽奇特,其记载的梦境虽然也有内容完整、独立成篇的作品,但大多还只是略一提及,且借梦说理的痕迹较重。古典小说杂剧中还有一种较为典型的梦境描写,主人公在短暂的梦中经历了整个人生,而一觉醒来方知皆为虚幻。代表作有《枕中记》《南柯太守传》《太平广记》之樱桃青衣、马致远《黄粱梦》《邯郸梦》、蒲松龄《续黄粱》,等等。这类作品有关梦境的安排是为了借事说理,梦的内容也几乎完全依托现实世界的秩序与逻辑。
反观《西游补》,其十六回安排的核心,无过一个“情”字。为了展现“情”是最有力、最能迷惑人的形态,董说超越了中国传统梦文学精心编撰的、带有强烈目的性的“现实主义梦境”,将梦的描写带向了更加无序化、更加离乱的境地。而《西游补》的现代性特点,也正体现在整本小说中“理性”的退场。董说作《西游补》,原意是让人们认清“情”字之虚妄,重返“理”之根本。但董说采用的方法恰恰是将“情”与“感”在小说中无限放大。
这种放大首先体现在情节连缀上的无序性和内容本身的荒诞性。坠入头风世界、古人世界、未来世界的行者,一会儿目睹熙熙攘攘的举子争相看榜;一会儿变成项羽的爱妾,与其床畔交谈;一会儿又进入地府,变成审判秦桧的阎王……前后情節毫无连接性可言,仿佛真正的梦境。而“唐僧沉迷女色”“行者已有妻儿”这样的情节,对熟悉《西游记》的读者来说,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如此随意与夸张荒诞的特点,也正是有学者称它为“意识流小说”的重要原因。
行者焦急、无措的心理状态和延宕的行事作风,同样昭示着“理性”的让步。作为主人公的行者缺乏知晓一切的上帝视角,也失去了在《西游记》中“一人有难千人帮”的良好环境。从行者化饭入新唐一节起,他就是彻底孤立无援的,散乱无序的信息不断地冲击着行者的认知,使他愈发焦躁难安。这种焦虑很像人在做梦时面对荒唐的梦境束手无策而产生的惶恐和无力感。行者处于被动状态,浑浑噩噩;读者亦处于被动状态,感受着行者的焦急无措。
“理性”的退场,还体现在《西游补》全文视觉的纷乱性上。小说中有很多有关色彩、各类物件的大量罗列。例如,进入万镜楼后对各类镜子的排列铺陈等;在“五色旗混战”部分,青、紫、玄、黄、荔枝红、鸭头绿,种种颜色构成了一幅极其纷乱的混战图景,令人目不暇接。小说中使用到的表示色彩的字眼极多,据统计,仅“青”字就被使用过206次。这种通过文字直接对视觉产生干预的方法,冲击着读者的理性,加重了直观上的混乱感。
虽然《西游补》具有诸多古典小说不曾具备的现代性特点,但是我们仍然不应将它与纯粹的西方意识流小说等同。而其中的“现代性”与“意识流”,也只是介于西方意识流文学和传统中国叙事文学之间的一个特殊产品。总的来说,《西游补》是一篇优秀的文学作品,他投入了作者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众多煞费苦心的暗喻,而不仅仅是对真实梦境的一个简单复现。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中多次提及过人对自我梦境的稽查,以及大脑为使梦境变得不那么直白和羞于启齿而对梦境进行的伪装。董说的文学创作在这一点上和做梦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创作《西游补》,满足自己释放焦虑欲望的同时,董说也充分发挥了理智的监察和协调作用。《西游补》绝不是由一堆凌乱的意识符号堆砌而成,董说赋予了它完整而精彩的故事情节,并巧妙地将他对现实的讽刺与劝喻深藏其中。董说不是一个百分之百超尘脱俗的隐士,儒家士子的社会责任感始终深埋在他心中,这也直接导致了《西游补》的复调主题——它不是一部单纯为艺术而艺术的、表现无名焦虑的现代化意识流小说,而是既包含了饱满的个人情绪,又对现实有所关照的复杂而深刻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董说. 西游补[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63.
[3] 傅世怡.西游补初探[M].台北:学生书局,1981.
[4] 赵红娟.明遗民董说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5] 高洪钧.《西游补》作者是谁[J].天津师大学报,1985(6):8184.
[6] 赵红娟.《西游补》与《西游记》关系新探[J].浙江学刊,2006(4):96100.
[7] 苏兴,苏铁戈.《西游补》中破情根与立道根剖析[J].北方论丛,1998(6):4550.
[8] 童琼.从“真假猴王”到“鲭鱼世界”——《西游补》寓意浅论[J].中国文学研究,2001(1):5155.
[9] 王厚怀.《西游补》妖魔的突破与主题的翻新[J].明清小说研究,2010(2):5665.
[10] 朱萍.文人小说的理性高度——《西游补》的意蕴与风格初探[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2629.
[11] 刘雪真.交织的文本记忆——《西游补》的互文语境[J].东海中文学报,2007(19):111138.
[12] 赵红娟.一部可以和世界文学接轨的古典小说——《西游补》新论[J].明清小说研究,2006(3):184196.
[13] 李梦圆.论《西游补》的视觉现代性之维[J].理论界,2015(8):124129.
[14] 史景迁.王氏之死[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24.
[15] 董说. 丰草庵集[M]. 吴兴刻本,1650.
[16] 董说. 丰草庵诗集[M]. 吴兴刻本,1650.
[17] 钮琇.觚剩续编[M].临野堂藏板刻本,1700.
责任编辑:曹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