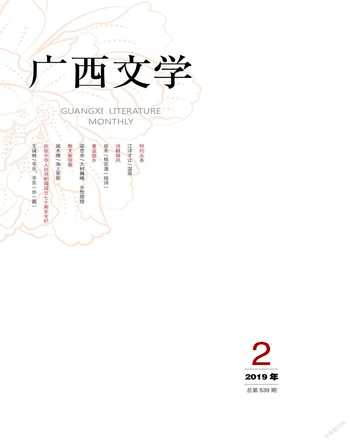想象的“极限”写作及其精神秘境
在当下诗坛,想象的“极限”写作在80后诗人群里并不鲜见,落葵算是较突出的一位。那么,想象的“极限”写作当然与精神秘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与想象的“极限性”所带来的真空地带有很大关联。是的,事物往往是这样,越有“极限性”便越有“弥漫性”。于是,像落葵这样的诗人就宁愿当一回“想象的囚徒”,能给万物“更多的新鲜与错觉”的弥漫状,使想象的“极限”写作及其精神秘境有了可趋近的“存在感”,这才是诗人最想达到的境地。
落葵的诗,我曾零零星星读过一些,这次读了他的《在待普僧,遇到一个骑马的人》(组诗)更加深了我对他作品的总体印象:他是一个能坚守住“精神职场”的诗人,他的诗一直在营造精神秘境的“存在感”。在他看来,世间万物都是他的精神“职员”,就看他自己是如何摆正这世间万物的位次与职守。正像“雨中的树,害怕失去风那样/害怕失去灵魂那样,害怕失去友谊/每路过一个人,便增加了体内的孤独”。由此可见,落葵一直在想象的“极限”中遨游,他寻访的秘境,或是所属的“精神职场”,各有各的精神“样态”,各有各的精神“操守”。一方面,他很喜欢给“秘境”自设“障碍”,这使得他的诗总是披上一袭“精神袈裟”:冷艳、沉潜、内敛、孤悬。是的,他诗歌的“冷艳、孤悬”常常积攒着“难以言说的情绪”。他不像有些诗人急于寻找情绪的“出口”,他宁可让那些“难以言说的情绪”,像他“更加熟悉黑夜”那样,藏匿着,包裹着,纠集着,发酵着,直到“时间的另一个节点”,他才来慢慢品尝个中滋味。可见,他不是那种“为了简单的事情而哭泣”的“情绪化”的诗人。另一方面,落葵还善于运用明暗分明的感情“色素”来呈现其精神秘境,但他的秘境从来不指向“非明则暗”或“非此即彼”的境地。他善于在明暗之间、矛盾之中、对峙之时寻找其中的“交错”“摩擦”“迂回”“胶着”的存在感:“那些雨激烈撞击到车窗上/饱含着赴死的决心。”
是呀,想象的“极限”写作来自秘境的“终极”诱惑。在落葵看来,秘境便是无人抵达的最圣洁的地方,而无人抵达的地方就是产生“寓言”的地方。于是,落葵“在无人采摘的苹果树下”,让“寓言”大行其道,一边“寓”出“一树红如灯笼的苹果树”,另一边又“寓”出“枝叶是聋哑人”。正是这个“寓言式”的辽远、冷僻、稀少、晶莹的精神“寓所”,使得落葵的诗一直处在“黑暗的轴心”。不过,这非但没有妨碍他的精神视线,反而通过“见证雾霾中的黑,用光泽唤醒/内心消退的激情”。由此可见,诗人不溺于“黑暗”,反而让“黑暗”提供了一个“看清浑浊的裂口”的端倪。同时,落葵以“孤悬”的姿态进行想象的“极限”写作,他的“孤悬”姿态,你可以说他是在“亮剑”,也可以说他是在“透视”芸芸众生。不管是“亮剑”也好,“透视”也罢,二者都有赖于落葵的知性、经验、阅历、审美得以“铅华洗尽”般的“淬火”。正如他写道:“一百年后,車来车往/满城尾气像亲人一样/包裹着孤独的人。”由此可见,离精神秘境越近的地方,心无比脆弱。那是一种渴望的“脆弱”,持久的“脆弱”,生动的“脆弱”,终极的“脆弱”。
→ 卢辉 诗人,诗评家。著有《卢辉诗选》《诗歌的见证与辩解》。现居福建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