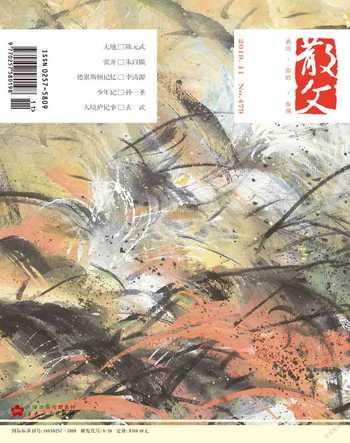德累斯顿记忆
李清源
在卡罗拉大桥上远远眺望,从那幅随车轮奔驰而游移的剪影里,也能感受到德累斯顿的独特和精美。欧洲老建筑到处皆是,随地一座房子可能都有三五百年的历史,但如此美好的建筑在一个地方如此密集地存在,却委实少见。借用一个俗气的比喻:一颗宝石已然夺目,忽有一大堆宝石堆砌眼前,再不爱财的人也会深感震撼。过于强大的视觉冲击往往能够惊动灵魂,这是一种生理上的反应,无关爱憎,但可能影响审美。
我们在导游带领下,穿过池塘边一小片树林,从森柏歌剧院和茨温格宫之间走进剧场广场。在国内见惯了一望无际的大广场,相比之下,剧场广场的面积就不过如此,但因平坦无物,唯中央高矗一尊带基座的青铜像,就显得相对开阔。铜像是骑马的萨克森选帝侯、兼任波兰国王的奥古斯特二世,据说他就是从这里出发,前往华沙就任国王,接收他名义上的新领土。广场正南方是大名鼎鼎的茨温格宫。欧洲的宫殿则是开放式的,没有宫墙,楼宇之外即是市街,打开窗台,就能与多情的游人彼此相看,互为风景。茨温格宫大门正在施工,几名工人站在铁架上修补穹顶,但有侧门可供出入。宫内无他建筑,只有一大片开阔空地,人工池塘和草地左右对称,仿佛一个广场。正前方的皇冠门和广场两侧的别殿雄伟华丽,甚是可观,但因暮色渐浓不能久留,草草浏览即匆忙离去。
接下去的景点同样是走马观花。德累斯顿王宫和宫廷大教堂一望而已,俱未细看,亦无多感,唯觉宫廷教堂精奇阔大,尤其是巍峨高耸的钟楼,尖顶上的十字架没入夜空,抬头观望,从动作到感受都令人仰视。宫廷教堂是天主教堂。我忘了是导游所述,还是在网上查到的资料:奥古斯特二世原本信奉新教,为接波兰国王之位而改宗天主,从意大利召来工匠,兴建起这座巴洛克式大教堂。关于这座教堂,还有个载入史册的八卦:奥古斯特二世好色嗜欲,死后身葬波兰,心脏则被带回德累斯顿,安放到宫廷教堂内。这枚心脏平时安静如石块,一旦有美女路过,就会活泼泼地跳动起来。看来不光记忆靠不住,信仰同样靠不住,在权力和女色面前,所谓的虔诚都是玩笑。
跟着导游进入奥古斯图斯街。街道窄而短,夹在高等法院和德累斯顿王宫之间,仿佛一段幽深的沟渠。宫墙上镶嵌一幅长卷式陶瓷壁画《王侯队列图》。壁画长达百米,刚好铺满这段宫墙。整幅画由两万七千多块瓷片拼成,图中人物,是韦廷王朝三十五名有为的君主和他们的士兵与随从,留小胡子的作者威廉·瓦尔特,也贱挫挫把自己画了进去,身穿礼服躲在队伍之后。灯光下看不清瓷画细节,但觉形象生动,气象不凡,虽不懂绘画,亦知是经典之作。
街道尽头是一座多面体独立建筑,米黄色砂岩石在周边灯光映照下一团暖意,其中夹杂一些黑色方石,仿佛缀在绫罗上的一块块补丁。是为圣母大教堂。教堂前有一尊马丁·路德的雕像,说明它属于新教。适逢教堂内做礼拜,我们跟随教众入内观瞻。进来后,我脑海立即浮出一个很土豪的形容词:金碧辉煌。这些天所见教堂可谓众多,宏大而精美者亦不乏其数,但其内部设施大多质朴庄重,色调偏冷,看上去肃穆而不奢华。这座教堂却截然不同,穹顶绘画与饰物皆用明暖的黄红二色,极其富美,祭坛上的雕塑和大理石栏杆则镶满黄金抑或是镀金。就连最上层巨大的管风琴,也围了一圈黄灿灿的金流苏。灯光也是暖色的,温和地照耀着满堂世俗的华丽。我觉得这很好,富贵是人们的现实期待,温暖是圣母的慈爱光辉,入世的宗教,才更打动人心,也更有生命的力量。
从教堂出来已经很晚,导游带我们去了最后一个景点:布吕尔平台。这是易北河南岸的一块平阔之地,原为军事要塞,后来辟为游娱之所,有树木水池,可以远眺休憩。凭栏西望,宫廷大教堂和高等法院在灯火通明的夜色里清楚可见。坦率讲,这平台固然不错,但有多好,也谈不上。然而它却有个阔气的称号:欧洲阳台。这口气似乎太大,让人联想到《围城》里的欧亚大旅社。当然,欧亚大旅社从未莅临过欧洲旅客,这个易北河畔的“欧洲阳台”,却实实在在光顾过欧罗巴乃至全世界的要人,比如普京。
此行之前,我对德累斯顿所知甚少,仅有一些破碎的常识,也多与历史有关。另外,因我家乡是所谓瓷都,曾经整理瓷器史,知道欧洲也有个瓷都,叫迈森县,隶属于德累斯顿行政区。更多——其实也很有限——的了解來源于俄罗斯总统普京。众所周知,这位在中国圈粉无数的政治强人曾经有个令人敬畏的工作:克格勃特工。而其工作地点,就在时属东德的德累斯顿市。他于1985年赴任,在这里发展线人,招募并培训间谍,监视敌对分子和亲密盟友,直到东欧剧变,单位关张,才于1990年返回苏联。2006年10月,普京以俄罗斯总统身份访问德国,特意来到阔别多年的德累斯顿,锦衣重游,想必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感喟与快意。网上有很多当时的留影,其中一张流传尤为广远:照片中的普京头已半秃,穿黑西装,打黑领带,站在一道齐腰的黑漆栏杆后,背景是远方的两座建筑,从高耸的尖顶钟楼和黢黑的圆顶塔楼可知,它们是宫廷大教堂和相邻的萨克森州高等法院。以视角判断,普京当时站立之处,正是我们此时所在的地方。
稍作停留,我们即原路返回,顺道把之前的建筑又复习了一遍。所有老建筑上都有许多黑黢黢的痕迹。此时夜更深,灯愈亮,斑斑黑渍在人造光明下有种别样的醒目。我以为那是风雨尘烟在漫长岁月里结起的污垢,抑或是这些建筑曾经集体走水,烟熏火燎,遂成这副模样。不料听导游讲,它们竟是炮火的印记。“二战”末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已将老城这一带的建筑夷为平地,眼前这些宫殿和教堂,都是战后——主要是两德统一后——按原貌复建的。在复建时,特意将残存的砖石和墙体重新利用,放回到它们原来的地方。于是就出现了那些黢黑如烟垢的痕迹。也就是说,我们所见这些老城建筑,其实都是做旧如旧的复制品。反而是易北河对岸的新城区,因为逃过轰炸,大多建筑得以保存,房龄普遍比老城古老得多。老城不老,新城不新,新即是老,老即是新,一场战争不仅颠覆了时光秩序,也混淆了空间名实。
德累斯顿大轰炸,应该是这座城市有史以来最大的劫难。1945年2月,英美空军以帮助东线作战的苏军为由,对德累斯顿发起猛烈空袭,巨量高爆弹和燃烧弹造成的火焰风暴摧毁了整个繁华的老城。战争打到此时,空袭屠城早已不是骇人听闻的罪恶,而最先这么干的,正是那些自视血统高贵的德国人。他们在战争之初,凭借空优把英国的伦敦和考文垂炸得稀烂,现在盟军反攻,要炸他们的城市,似乎也没话好说。但轰炸过后,纳粹政府立即将其宣传为针对德国平民的暴行,声称德累斯顿只有文化和医院,没有军队。友军苏联则认为,大轰炸对他们的战事并无帮助,他们认为更应该轰炸的是不远处的德军堡垒艾伯特市,而非德累斯顿。“二战”之后,铁幕开启,美苏两国由反纳粹的盟友变成全球争霸的对手,德国也在分裂之后分投两个阵营。东德与苏联既已成为湿吻兄弟,德累斯顿大轰炸的旧账,也便有了面向西方阵营的统一解说。而始作俑者的英美两国,自然也有他们的立场和坚持。于是一个真相,各自表述,并不久远的历史记忆,在两大阵营的各说各话中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但若抛开政治上的攻防算计和学术上的辨本求真,即以苏德旧说为是,德累斯顿所承受的那场历史悲剧,似乎也不能以“无辜”二字简单概括。当纳粹通过选举成为国会第一大党,授予希特勒绝对权力的全民公投也以接近九成的支持率获得通过,德累斯顿的公民已与全国民众一起,亲手选择了纳粹独裁,并交付了自己的命运。而当战争爆发,希特勒的侵略机器碾轧欧洲,德累斯顿同样没有置身事外,庞大的军工企业昼夜运转,源源不断地为战争提供军需。他们既然选择了纳粹,就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在为侵略战争做贡献的时候,也应该预备好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波兰诗人斯坦尼斯洛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觉得自己有责任。事实上,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几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或许可以拿来作参照。德累斯顿易北河谷以其优秀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入选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6年,市政府为解决交通压力,计划在易北河上修建一座桥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这将破坏易北河谷的自然面貌,建议停建,或改为地下隧道。市政府不敢擅作主张,搞了一次公投,让全体市民做决定。结果将近七成的市民支持建桥,地下隧道方案因成本太高而被否决。大桥在民意推动下如期完工,还被起了个诗意而典雅的名字:森林宫殿。教科文组织被激怒,他们并没有因为这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名字而放过德累斯顿,在2009年第三十三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公开宣布将易北河谷除名。
相信一定有不少德累斯顿市民感到委屈。想我河山何等秀丽,建筑何等壮美,仅仅因为一座桥就将我全盘否定,试问公理何在!再联系到法国的卢瓦尔河谷,尽管域内有座庞大的核电站,依旧获得教科文组织垂青,稳稳列在世界遗产名录里,更是令人气结。在人权主义者看来,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歧视,是对德累斯顿人民的公然羞辱。假如时光倒流八十年,愤怒的德累斯顿人民很可能会选出一个疯狂的独裁者,授权他带领大家去复仇。再往前推三百年,那位热爱文艺的“强力王”奥古斯特二世在位,也必定会为了捍卫荣誉而发动一场战争,广大的德累斯顿民众,也将是荣誉之战的狂热支持者。我们不妨推断一下结果:疯狂独裁者能带来什么,大家记忆犹新,无须多言。至于那位以路易十四为楷模的强力王,虽然喜欢打仗,却不擅长打仗。他曾经率先发难,主动进攻瑞典,引爆影响深远的北方战争,然而开战不久,这个引爆者就被打爆,波兰王位也一度不保。他若发兵攻打联合国,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围殴,联合国军也将如当年的瑞典军队一样长驱直入,兵临城下,火烧茨温格,血洗河两岸;然后强力王签约退位,量萨克森之物力,结联合国之欢心。因委屈而战的德累斯顿民众,再次沦为“无辜”的受害者。
所幸以上只是假设。历史时有轮回,但时光不会逆转。在这标橥和平的时代,德累斯顿做出了更理性,也更自信的选择:在虚名和民生之间,他们选择了民生,而当他们因为这个选择受到可能并不公允的惩罚,他们又选择了坦然接受。森林宫殿大桥开通时,德累斯顿市民载欣载奔,歌舞相庆,为自己的城市生活变得更美好而欢笑喜悦。提到除名之事,他们虽有遗憾,但不抱怨,更没有激烈的批评和仇恨。公民性格的成长与成熟,才是真正的文明进步。
德累斯顿的行程到此就该结束了。我们意犹未尽,恰好住处距此不远,于是约定明天早上再来一游。次日清晨,我們数人如约而往。一场夜雨将天空和阳光洗得格外干净,我们行走在街道,仿佛一群游弋在澄澈溪流里的鱼。几十分钟路程很快便到。阳光下的景象果然不同,昨晚隐藏在夜色里的建筑细节,被浏亮晨光召唤出来,一雕一镂清晰在眼。尤其是陶瓷壁画《王侯队列图》,色彩和光泽都很鲜亮,看上去生动了许多,也漂亮了许多。纵观画幅,簇然如新,两万七千多块瓷片无一破碎或损毁,难以想象它也经历过毁灭性的德累斯顿大轰炸。圣母大教堂也更见雍容与华贵,教堂顶上那枚造型独特的十字架沐浴朝日,散发出熠熠金光,在晴空下格外耀眼。那是教堂重建时,英国人按照原样复制捐赠的。鎏金穹顶的监造者也是英国人,其父是一名空军飞行员,曾经驾机参与当年的德累斯顿大轰炸。这也是圣母大教堂的特殊之处:它的重建,得到了全世界——尤其是英美两国——的慷慨资助,并因此被视为和解的象征。时间是条一维的河流,或许政治语境的变化并不能够澄清湮没已久的真相,历史记忆里缺失的部分也将永远缺失,对于生活在现实截面的人们,怎样选择——是逆流而往拥抱过去,还是顺流而前迎接未来——就变得异常重要。然而不论如何选择,和解,都是走出历史泥沼最好的通道。
站到布吕尔平台上,最后打量这片密集的克隆建筑,我想到万里之外的祖国。我的祖国也有许多美轮美奂的宫殿和寺庙,它们的雄奇和精巧,足以标识我们伟大的文明。与德累斯顿一样,它们也饱受战火的摧残。甚至没有战火,仅仅是要表达与前朝决裂,就可能将其付之一炬,烧完之后,再择风水宝地大兴土木,盖起新的宫殿与庙堂。但与德累斯顿不同的是,他们的战后重建,是原貌修复,做旧如旧,我们的战后重建,则往往是废旧立新,润饰鸿业。他们的重建是为了延续历史,我们的重建,则是为了改写历史。在史公看来,这种大异其趣的态度和行为,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只是这种差异,究竟是逻辑的果,还是宿命的因?或许这才是更为关键的问题,想衮衮史公,必有为之痛哭流涕长太息者。
反正我是没时间多想了。在九点钟,我们将准时出发,前往欧洲之行的下一站。至于下一站是什么地方,很惭愧,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责任编辑:田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