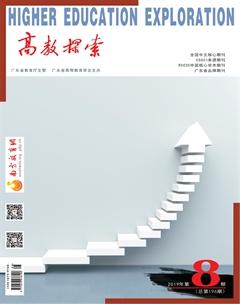从“脱域”到“再嵌入”
贺修炎
摘要:当前,现代学校规训制度下的书院教化意义缺失,学生生活场域异化为外在于其整全生命的物理空间,书院文化空间建设亟待加强。重建书院文化空间,理论上应“再嵌入”传统文化基因和通识教育理念,做到“体”“用”一致、“神”“形”兼备;实践中则应围绕导师制、通识课程和社团活动等方面开展制度创新,推进“书院-学院”双院制协同联动育人模式的落實。
关键词:书院;文化空间;脱域;再嵌入
一、“脱域”:书院文化空间建设的异化
现代大学书院理应成为集生活、教化诸多功能于一体的复合文化空间,而不仅是提供住宿的生活空间。事实上,现代学校规训制度下的书院教化意义缺失,学生生活场域异化为外在于其个体整全生命的物理空间,而非有意义的文化空间。这种教化意义的缺失甚至异化正是吉登斯(Anthony Giddens,2000)所谓的“脱域”现象在书院中的表现,问题的关键在于“古代传统书院的生活空间和教育空间是融合的,而制度化的现代化学校教育却使二者分离,现代大学书院制只是继承了传统书院的空间形式”[1]。学生仍然视书院为具备生活功能的物理空间而非文化空间,现代大学书院并未充分发挥文化育人的功能,书院精神及其蕴含的传统价值没有走进学生心中。
(一)原初教化空间与生活空间的融合
中国传统书院是集教化、研究与藏书诸多功能于一体,师生共同生活的文化教育场域。师生生活和学习都在书院的具体情境中发生,换言之,师生是作为主体嵌入到书院空间之中并相互交往的。师生读书的过程是用生命体验、践行圣人之训的过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均必须亲历其事,才能达到“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的最高道德目标。师生在修身、为学、处事和接物的过程中,生命体验的广度和深度得以扩展,其读书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道德生命的展开。
以中国古代书院为例,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早期书院的建设者们就已经体认自然对人的陶冶之功,特别重视人与周围环境的协调”[2]。书院在地理位置、园林布局和建筑结构等方面与儒家心理结构具有同构作用,环境本身就是道德伦理的“无言教化者”,具有伦理性、教育性和文化性的内涵,对浸润其中的师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有学者研究指出,书院创建者非常注重书院位置的选择,其选址可大致分为依山傍水型和历史古迹型。[3]“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书院建筑于自然山川之间,将山水草木形貌与人的品德意象化,使自然风貌与人的气质相通,体现了孔子的“山水比德”思想。如宋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前沿湘江之滨、后至岳麓之巅,亭台相济、山水相融,成为师生讲学论道的绝佳去处。历史古迹是书院选址的又一重点,书院建设者希望通过名流大师的声望使生徒们“见贤思齐”,习得榜样的力量,濡染圣人的精神气质。如鹅湖书院得自著名的“鹅湖之会”,朱熹和陆九渊兄弟在此就“理学”和“心学”的理论分歧展开过激烈辩论。此外,古代书院的箴碑、门楹、堂联和斋舍命名也都蕴藏着涵泳深厚的教育意蕴。
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欧美住宿学院也十分注重为学生创建全方位发展的育人环境。不同专业、年龄的学生混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和教化空间高度契合,处于一种“复杂性”之中,学生们具备不同场合转换自己的能力,“一个人有许多侧面,但还是一个完整的人,学生们必须在一种‘复杂性中生活,才能认识一个超越大学的世界”[4]。哈佛大学在20世纪初开始借鉴和引进英国的住宿学院模式,旨在把学生培养成社会性公民,“学生的性格不仅仅取决于所接受的教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良好同伴的氛围”[5]。时任校长洛厄尔建立起若干个学舍(house),每个学舍都有图书馆、餐厅和活动室等,由一名教授担任学舍长,若干名导师负责指导学生的生活和学习,学舍成为学生成长和生活的重要场所。哈佛大学的学舍使“学生们从相互间学到的东西比从教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作为一个群体,给每个成员的成长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6]。耶鲁大学的住宿学院计划使学生的生活空间和教育空间合二为一,将宿舍变成一个大讲堂,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仅仅提供住宿而不授课的建筑可以被称作学院(college)”[7]。
(二)“脱域”现象的社会历史原因
现代大学书院建设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学校对书院文化设施建设也十分重视,但学生还是感受不到书院与学院、宿舍有何区别,习惯性地将书院视为生活的物理空间而非文化空间。这种书院教学空间教化意义的缺失即吉登斯所谓“脱域”现象在现代学校的表现,书院成为学生攫取文化资本的客观化的抽象系统而不再是原初的嵌入学生生活空间之中并与之结合起来的有意义世界。通过知识与权力的共谋关系,现代学校“以生产、训练和造就驯服、有用的身体为目标,规训强迫身体完成某种任务、表现某些仪式”[8],原初充满教化意义的教养教育被冰冷的制度和法则所侵蚀。进而言之,当学生将书院抽象化为能够攫取学分和文凭等文化资本的场域,教化与生活世界合一的书院空间及学生在此情境中所体验的意义便不再凸显。
现代大学书院教化空间的不在场或生活意义的缺失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化席卷中国,在中西文明的冲突和碰撞交流中,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放眼看世界,主动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这不仅动摇了中国的封建政治、经济根基,而且带来了文化和教育的巨大变革。废科举、兴学堂,对西方文教制度的模仿和因袭成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主旋律,书院作为封建文化的糟粕也被一并抛弃,中国大学开始文理综合或分科设立的改革。分科设立的现代大学以传授科学技术知识为己任,过分强调知识的功利价值,视教育为谋生之工具,学生将学习定位于“器物”“技艺”层面,现代课堂离大学理想和传统书院精神越来越远,逐步沦为道德贫瘠的“名利场”。事实上,早在1921年,毛泽东便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比较了书院和学校的利弊得失,并系统阐述了他的教育理念,他认为“学校在使学生利于被动,消磨个性,毁掉性灵,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而书院则恰好相反,“一来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9]。
除却抛弃传统书院精神造成文化断层的历史性因素,现代学校规训制度则是书院教化意义缺失即“脱域”现象的社会性因素。在以主知主义为主导的现代大学中,学生受到课堂标准化和效率化的规训并时常遭受惩罚,知识学习不再是学生主动建构的过程,知识统帅、教师一言堂成为教学常态。教师俨然成为现代化语境中生产流水线上的“熟练技术工人”,只负责把知识加工为统一规格的产品并兜售给学生,而学生则只注重习得表层知识符号,对文本死记硬背、记诵标准答案而少有创新。单纯追求效率和标准答案的规训化教育“去情境”“去过程”“去发展”,只能培养出“两脚书橱”而无法培养学生整全的个性,这与传统书院人文精神以及通识教育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教育向人展示的只是一个‘科学的世界,而忘却了作为根本的‘生活世界”[10],学生的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疏离、重知识轻道德、重科技轻人文,课堂异化为外在于学生个体生命的物理空间。此外,大学教师“有课则来,无课则走”,教师与学生生活空间彼此区隔、鲜有交往,学生在课堂以外几乎没有和教师互动的机会,传统书院充满教化意义的文化空间在现代学校规训制度下“不在场”,学校沦为只能提供食宿的物理空间。
二、“再嵌入”:重拾书院传统文化基因
现代大学书院应以“学生为本”,培养整全而非割裂的人,然而至今并未开发出有效的课程和活动,人文精神日渐式微、通识教育识而不通。如何建设书院的文化空间,发挥书院的文化功能,“再嵌入”书院的传统文化基因和通识教育理念,在现代书院的更新和改造中既能尊重民族文化本身,又能借鉴欧美寄宿学院制度,创造性地传承和转换书院的文化空间而非单纯物理空间是现代大学书院建设的必由之路。
(一)书院文化空间建设应当“体”“用”一致
“体”与“用”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概念范畴,指本体和作用。“体”即本,最根本的、内在的、本质的,“用”是“体”的外在表象,“体”是第一性的,“用”是从属的第二性的。“体”“用”二词的意义到唐代得以明确,“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唐·崔憬《周易探元》)。
现代大学书院制度是中国传统书院与欧美寄宿学院有机糅合的统一体,二者各有其“体”“用”。对中国传统书院而言,“体”主要是指中国传统人文精神,而“用”则指向儒家的纲常名教等文化典籍。传统书院将儒家学说转化为以“道”为核心的人文精神,注重人格的养成,“强调人的价值和需要,关注‘生活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并且在现实生活中努力实践这种价值、需要和意义的精神”[11]。书院精神实与西方大学推崇的博雅教育或通识教育的理念有暗合之处,与其主张的个性养成、自由探究的精神相互吻合,这恰是现代大学的理想所在。然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急剧现代化的进程中将书院视作敝屣而抛弃,书院千余年积淀的文化菁华并未被汲取,中国传统高等教育与现代大学之间存在明显的裂痕。事实上,“五四”时期的书院研究就已经对20世纪初期中国大学的现代化转向进行过反省,将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倒,诚如胡适所言“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12]。文化的更新与改造不能脱离民族文化母体本身,大学的使命在于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和高贵的灵魂,现代大学书院文化空间建设应当从“本”“体”上加以衡量,汲取中国传统书院精神的精髓是重建书院文化空间的必由之路。
对国外寄宿制学院而言,“体”主要指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理念,而“用”则指向通识教育课程与活动。通识教育是对现代专业教育的批判和“人的一般发展”教育本质的回归,从源头上看,通识教育来自古希腊自由教育的理念,其专注于一般精神理念的追求,而非具体的专业教育和实用教育。就通识教育的目的而言,是要充分唤醒个体完整成人的意识,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和国家公民;就其内容而言,是要“超越专业局限而达到普遍知识,由普遍知识达到人对自我存在之整全的认识”[13]。现代大学书院使通识教育有了新的可能,或者说书院独有的文化空间极大拓展了通识教育实施的途径,学生通过体验参与的方式潜移默化地习得了具有整全意识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书院以学生为本,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学生混住,不同思维模式相互启迪,不同兴趣爱好彼此熏陶,通过设置各种实践体验课程和活动,旨在开阔学生的学术视野,促进其全人的发展,养成负责任的公民。
中国传统书院精神注重道德教育和人格养成,通识教育旨在人的整全发展和个性养成。就价值规范而言,书院精神和通识教育理念有着契合之处,二者均可视为现代大学书院的“体”;从知识论角度出发,儒家的纲常名教等伦理性知识以及西方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都可视为“用”。那么,如何正确处理现代大学书院的“体”“用”关系则需要向传统书院精神处求答案。中国传统书院有“教训合一”的传统,“自宋、元、明以迄清代,为时经数百年之久,关于书院之内容规则,虽不无变更添补之处,然其目的之在于讲学术以正人心,补国家学校之阙失,则始终一贯。亦即我国真正之书院教育,原系人格教育,至其倡导学术自由研究之风气及知识之传授,尚余事耳”[14]。传统书院将道德教育与知识教学结合起来,并将儒家的“道”作为知识教学的主要内容和目标,渗透到教学的每一个环节,这种“体用一致”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个体道德养成的具体手段,是现代大学书院精神文化空间建设值得借鉴、精神文化得以彰显的重要维度。
(二)书院文化空间建设应当“神”“形”兼备
何谓“神”与“形”?《荀子·天论》中说,“形具而神生”,人的躯体是自然界的产物,而人的心理是由躯体派生的,人的身形成了,也便有了心理。《管子·内业篇》说,“凡人之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形指形体、肉體,神指精神、灵魂。《神灭论》开篇说,“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也”,形是物质实体,神是形体的一种功能或作用。那么,书院的“神”与“形”究竟是什么,二者存在怎样的关系呢?书院的“神”即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大学之道可视作大学之为大学的本体追问,是一种精神和理念的追求;书院之“形”则是指符合大学理念和价值追求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书院文化空间建设应当“神”“形”兼备,现代大学书院制无疑是“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彰显大学精神的最佳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