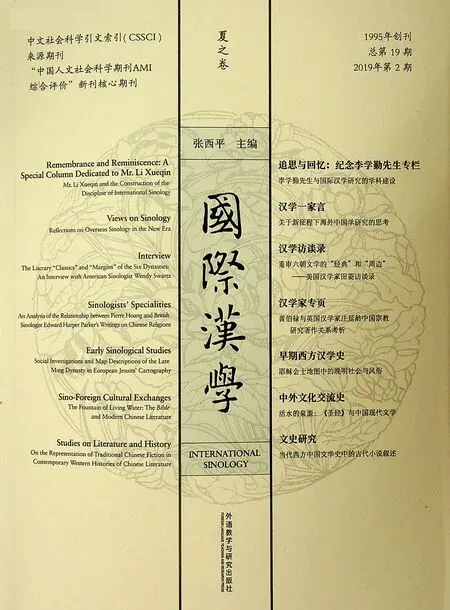李学勤先生与国际汉学研究的学科建设*
□刘国忠
李学勤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生前是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他一生致力于汉以前的历史文化研究,注重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学、出土文献资料相结合,在上古史、甲骨学、青铜器、战国文字、简帛学、学术史等众多研究领域均取得了第一流的学术成果,引领了这些学科的发展方向,是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的一面旗帜。
国际汉学研究也是李学勤先生一直非常重视和提倡的一个领域。所谓汉学(Sinology),是指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在西方,这一研究可以上溯到16世纪中叶,迄今已经历了数百年,并发展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学科。李学勤先生是国内最早倡导要对国际汉学进行深入研究,并将其作为一门学科来建设的学者之一,为国际汉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和顺利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积极倡导国际汉学研究的学科建设
李学勤先生对于国际汉学的重视,与他长期以来的学习及治学经历息息相关。
李先生从小就痴迷于读书,而且是越艰深的书他越爱读。从少年到青年时代,李学勤先生阅读了众多的汉学研究成果,熟稔汉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以至于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一位学者殷切建议他继承著名翻译家冯承钧先生的事业,专门从事海外汉学成果的译介工作。①见李学勤:《法国汉学·序》,载《法国汉学》第一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另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学勤先生曾立志从事比较文明史的研究,②见戴燕:《李学勤:“这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书城》2008年1月号。对于相关的汉学研究成果更为留意。虽然这些计划和心愿由于时代的原因未能得以实现,但是相关的学术积累使他具备了许多国内学者所缺乏的国际视野和学术情怀;加上他又通晓英、法、日、德、俄、拉丁等多种语言文字,能够直接阅读汉学家们用各种语言所撰写的学术著述,更使他的研究工作如虎添翼。
与此同时,对于汉学的发展历程,李学勤先生也极为留意,这其中,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有关汉学发展史的综述性著作《汉学发达史》一书,他很早就加以购买,并经常翻阅。③该书于1949年由北平文化出版社印行,作者为莫东寅。对于海外学者有关汉学研究动态的介绍与评论,他也一直持续关注。④李先生曾回忆说:“国际汉学这题目,我确实是很小的时候就注意了,因为我看外国人著作。有一个人的著作我很佩服他,是日本的石田干之助,他很重要的一本著作就是《欧美的中国研究》。……后来我又读青木富太郎、后藤文雄这些人的书,通过他们了解汉学的一些知识。”(见戴燕:《李学勤:“这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
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与西方的学术文化交流曾一度中断了很长时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这一交流才得以恢复。李学勤先生是改革开放之后最早有机会走出国门、与西方学者展开直接对话交流的学者之一,他利用这一难得的机会,走访世界各地的汉学机构和文博单位,与海外汉学家们展开了直接的对话与交流,掌握了西方汉学研究的第一手信息。在此基础上,他不仅在国内的刊物上积极报道访学收获,还开始与一些有识之士一起,提倡和呼吁国内的学术界关注国际汉学研究。
1979年三四月间,李学勤先生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访澳代表团,对澳大利亚进行了为期四周的学术访问。在澳大利亚期间,代表团访问了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人文科学院两个科研机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格里斐大学、昆士兰大学、墨尔本大学、摩纳什大学、拉绰布大学、阿得雷得大学、弗林德斯大学、悉尼大学、麦考瑞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等11所高校,以及澳大利亚国立维多利亚美术馆等文博单位。每到一处,李学勤先生除了与澳大利亚的汉学家们开展积极的对话和交流外,还仔细考察当地高校科研机构的组织形式、运作模式、研究特色、出版刊物、馆藏文物图书等情况,注重借鉴其长处。比如,澳大利亚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往往是跨系科的,以大学里对某一学科有专门研究的若干有权威的学者为核心,集合一批有共同兴趣的学者,进行多方面的研究,研究中心往往有自己的研究计划,有自己的出版物,也可以培养研究生。对于这一模式,李学勤先生指出:“这种组织形式比较灵活,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①李学勤:《澳大利亚的“中国学”》,《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7期。
同年的6月16日至7月30日,李学勤先生又受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和区域研究联合中心之邀,出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的马王堆汉墓工作会议;并由该中心安排,由美国国际交流总署(ICA)邀请,作为“国际学者”在美国各地进行访问,共走访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匹兹堡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华盛顿大学等10所大学,以及华盛顿国立美术馆、弗利尔美术馆、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芝加哥艺术馆等十几处文博机构。每到一处,他都与当地的汉学家们进行深入的对话与交流,并仔细考察各文博机构收藏的丰富的中国文物,写下了大量的考察笔记。有鉴于这次考察的收获,1979年8月,李学勤先生向有关部门提交了《访美报告》,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进一步扩大人文科学界的对外学术交流。二是加强图书情报工作。李先生忧虑地指出:“我们对海外学术研究情况,了解实在太少,太不够了。许多新的动向、新的成果,我们的研究人员不了解,不知道。要解决这个问题,单靠情报研究所或少数人出国,还是不够的。建议要求各所各室的专业人员都来做学术情报工作,最好能编出各学科的资料,先从最近五年着手。不要一搞就要求二三十年的情况,那样不及时、不实际。”②载《中国哲学》第1辑,1979年,题为《李学勤同志介绍美澳中国学研究情况》。三是进一步强调研究人员的外语学习,并希望给研究人员更多条件,提高外语能力,以便对外交流的进一步开展。
20世纪80年代以后,李学勤先生的对外学术交流更是全面开展,足迹所至,遍及英、法、德、意、日、瑞典、埃及、加拿大等国家和中国台湾、澳门等地区,这些访问、讲学和考察工作极大地丰富了李学勤先生对海外汉学的认识,并与汉学家们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同时,李学勤先生也深切体会到,中国的学术界不仅需要了解汉学史,还要尽快搜集当代汉学家们的研究成果,借鉴海外汉学的研究途径和方法。关于国际汉学的重要意义,李学勤先生后来在《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中有深刻的总结:
国际汉学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外国汉学家几百年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自有不少成果我们应当吸收借鉴,但由于语言隔阂等等原因,这方面成果大部分未能介绍到国内来。特别是前几十年,我们和外国的同行学者很少进行学术交流,他们的论著国内学术界罕能读到。国际汉学的发展状况,大家是相当不了解的。直到近十几年,外国汉学家几乎都来访中国,可是相对说来,我们对国际汉学界还是不够熟悉。这种情形,现在是必须加以改变了。③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
正是出于这种危机感与使命感,李学勤先生一直奔走呼吁,希望学术界关注国际汉学。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李学勤先生还主要是从学术情报的角度关注国际汉学成果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90年代,李学勤先生已经更进一步提出,要将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建设。李学勤先生公开提出这一主张,最早是在他的《汉学漫话》一文中:
国际汉学的研究,或者说是汉学史,应当被作为一个学科来开拓。发展这个学科的时机,当前已经成熟了。①李学勤:《汉学漫话》,《东方》1995年第1期。
把国际汉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来开拓,来建设,这在中国学术界是前所未有的认识,有着重要的指导性意义,并对后来国际汉学在中国的迅猛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我们觉得,李先生之所以在当时提出这样石破天惊的观点,应该与他当时正在倡导的“重写学术史”主张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李学勤先生也明确主张,国际汉学的研究最好采取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我认为研究国际汉学,应当采用学术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将汉学的递嬗演变放在社会与思想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和其他种种学科一样,汉学也受着各时代思潮的推动、制约,不了解这些思潮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原因,便无法充分认识汉学不同流派的特点和意义。尤其要注意,汉学家的思想观点常与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存在密切的联系。因此,即使是研究一位汉学家,甚至他的一种论著,也需要广博的知识和深入的分析。②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序》。
李学勤先生倡导的国际汉学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汉学史的研讨分析,而是同时强调对当代国际汉学成果的借鉴、分析与研究。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学勤先生又有意对“国际汉学研究”与“汉学史”二词做了更进一步的界定和区分。在1995年发表的《汉学漫话》一文中,李学勤把“国际汉学研究”等同于“汉学史”,但是到了1998年,李学勤先生给《汉学研究》第三集作序时,是这样来阐述二者的关系的:
汉学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也可叫做汉学史。③李学勤:《汉学研究》第三集《序》,见《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冬之卷。
这一论述与《汉学漫话》中“国际汉学的研究,或者说是汉学史”的表述有了一些区别,但是对于这两个词之间的差异之处,李先生当时并没有完全展开论述。
到了2001年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的“世界著名大学汉学系主任(汉学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李先生专门做了《作为专门学科的国际汉学研究》的讲演,这是一篇对国际汉学的学科建设有着重要指导意义的论文,文中对国际汉学的学科定义、研究内容做了全面的阐述。其中关于“国际汉学研究”与“汉学史”二词的关系,李先生是这样分析的:
“汉学史”便是国际汉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把重点放在汉学的过去。至于“国际汉学研究”,意思更为广泛,不仅研究汉学的过去,也包括汉学的现状,甚至未来。“国际汉学研究”,是对汉学本身所做的考察和研究。④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9月19日。
从这一论述可以看出,李学勤先生认为,“国际汉学研究”一词既包含了“汉学史”一词的所有内容,同时还体现了“汉学史”一词中不易体现的对国际汉学现状甚至未来的研究,更能概括这一学科的全貌。因此,李学勤先生一直主张用“国际汉学研究”一词作为这个学科的名字。
李先生对国际汉学研究的定义、内容和研究方法所做的详细分析,对于国际汉学学科的建设起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对国际汉学研究的大力提倡之外,李学勤先生还非常重视对流散海外的中国文物进行搜集与整理工作,他与著名汉学家艾兰(Sarah Allan)等人一起,对欧洲各地收藏的甲骨、青铜器资料加以搜集,编辑出版了《英国所藏甲骨集》《瑞典远东古物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等书籍,这些成果是甲骨学、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著作,从而为相关学科的深入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建设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①本部分的内容,改写自笔者的一篇小文《李学勤先生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的建设》,原载《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编委会主编:《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为了加强对国际汉学的研究,1992年,由李学勤先生牵头,清华大学成立了国际汉学研究所,从此开始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的艰辛建设历程。
熟悉李学勤先生的人都知道,他对清华大学有着特殊的感情。1951年,李学勤先生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意欲师从金岳霖先生从事数理逻辑的研究工作,但在当时的氛围下,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952年,由于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取消了文科,李先生因此离开了清华园,到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从事甲骨缀合工作,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虽然李先生在清华只有短短一年的求学历程,但是它在李先生的人生道路中镌刻下了极为重要的一章。用李学勤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在这里念书,认识了许多老师,向他们请教学习。实际上我研究甲骨文,还是从王国维这个传统来的。可以说我整个的学术知识道路,都是从清华这个传统来的,所以我对清华的感情很深。”②见程薇:《李学勤先生的清华缘》,《中国文化画报》2017年第6期。
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清华大学根据学校发展的需要,做出了恢复文科的重要举措。李学勤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他想,自己是从清华园里走出来的,理应为母校的文科建设做一些工作。清华大学校长张孝文教授听说后,极为嘉许李先生对母校的情怀,学校领导遂请李学勤先生出面,组织一个高水平的研究所,有鉴于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当时还不被国内一些学者认识,于是李学勤先生敏锐地提出了建立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的设想。经过多次协商,1992年,清华大学正式决定成立国际汉学研究所,请李学勤先生担任所长,葛兆光先生任副所长,并请老学长傅璇琮先生和钱理群先生共同担任导师。
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的建立,是当时清华文科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然而,根据当时学校的安排,国际汉学研究所暂时不设编制,不给经费,而是挂靠在清华大学中文系,由中文系给予一定的支持。因此,国际汉学研究所自成立伊始,就几乎可以说是白手起家,困难重重。然而,李学勤先生并没有气馁,在葛兆光先生等人的大力配合下,国际汉学研究所开始了艰难的创业历程。
根据李学勤先生的建议,国际汉学研究所成立后,立即在国外一些汉学研究通讯上发布了消息,介绍了国际汉学研究所成立的情况以及研究的目标和方向;李学勤先生还亲自与各国著名汉学家们联系,希望他们加强与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的合作。这一消息传出后,许多汉学家们纷纷来信,积极表达了合作的愿望。德国著名汉学家艾默力(Reinhard Emmerich)还专门联系李先生,愿意把珍藏多年的一整套汉学研究刊物《远东》(Oriens Extremus)③该刊由德国著名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等人创办。无偿捐献给国际汉学研究所,这套书也因此成为国际汉学研究所的第一批珍贵资料。1997年1月,国际汉学研究所还成功举办了“20世纪国际汉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国际学术研讨会,数十位海内外学者聚集在一起,探讨和展望国际汉学的发展历程及前景。通过李学勤先生等人的不懈努力,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与二十多所海外的著名大学以及众多的汉学家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根据李学勤先生的安排,国际汉学研究所成立以后,立即进行国际汉学的介绍和翻译工作。国际汉学研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以提要的形式,把国际汉学中一些比较重要的著作介绍给国内读者。由于时间和人力有限,当时计划先撰写一百部汉学著作的提要,这就是《国际汉学著作提要》一书的编撰缘由。经过努力,1996年6月,《国际汉学著作提要》一书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也成了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专刊的第一种。
李学勤先生在规划国际汉学研究所的工作时一再强调,国际汉学研究所当然要从事汉学史的研究工作,探讨汉学在西方的兴起和嬗变的过程,但是对于当前的中国学术界来说,迫切需要了解的,乃是当代国际汉学的状况和趋向,因此国际汉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应该把较多的精力放在当代汉学家及其成果方面,使我们能更好地与当代汉学家进行交流与合作。根据这一设想,国际汉学研究所把专刊的第二种定为编写《国际汉学漫步》,该书计划把当时一些活跃在各国汉学界的著名汉学家介绍给国内读者。经过数十位学者的共同努力,《国际汉学漫步》一书于1997年8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顺利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62万字,分别介绍了美、英、法、俄、德、日、加等国一些著名汉学家的生平、师承、研究方法和主要成果,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欢迎。
与此同时,国际汉学研究所也积极把当代国际汉学的研究成果翻译介绍给国内读者。经过酝酿,国际汉学研究所与辽宁教育出版社合作,共同推出了“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该丛书着重收录当今活跃在学术界的国外汉学家著作,目前已经出版了英国著名汉学家鲁惟一(Michael Loewe)主编的《中国古代典籍导读》、美国著名汉学家艾兰的《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比利时著名汉学家戴卡琳(Carine Defoort)的《解读〈鹖冠子〉:从论辩学的角度》以及日本著名汉学家蜂屋邦夫的《道家思想与佛教》等4部著作。另外,国际汉学研究所还曾多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书品》杂志上开辟专栏,对当代一些国际汉学研究成果加以介绍和评介,其中李学勤先生亲自撰写了《西周史三书小议》①《书品》1998 年第1 期。《介绍美国出版的一部中国古文字学导论》②《书品》1998 年第3 期。《国家起源问题的新探索——介绍德总统赫尔佐克的著作》③《书品》1999 年第2 期。等多篇研究文章,使学术界对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有了很好的理解。芝加哥大学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教授主编的《中国古文字学导论》一书,也是在先生的牵头下得以翻译出版的。
1994年,法国远东学院院长龙巴尔(Denys Lombard)来华访问,李学勤先生接待了龙巴尔院长一行,双方讨论了介绍和研究法国汉学的问题。经过反复研讨,中法双方决定合作编辑《法国汉学》辑刊,由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与法国远东学院一起从事编辑工作,这一合作一直延续至今,《法国汉学》也成为国内学者了解法国汉学成果的重要窗口。1997年5月31日,中法双方的有关学者在清华大学会商,决定从当年9月开始,举办“历史、考古与社会——中法学术系列讲座”(简称HAS),该系列讲座每年都要举行若干次,其目标是介绍中国和法国有关历史学、考古学及社会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在研究方法上强调跨学科研究和比较研究。其中第一讲即由李学勤先生主讲,题为“中国简牍帛书的新发现及其研究方法”。这个系列讲座也一直得以贯彻下来,成为中法学术合作与交流的一段佳话。
李学勤先生十分重视国际汉学研究所的科研工作和学生培养。在他的指导下,国际汉学研究所创办了自己的辑刊《清华汉学研究》,该辑刊强调以翔实的资料及细致的考辨从事文史研究,一共出版了3辑。另外,国际汉学研究所还与中山大学及泰国崇圣大学合作,出版了大型学术辑刊《华学》,本辑刊由饶宗颐先生担任主编,发表海内外研究中华文明的高水平成果。这些刊物都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反响。在培养学生方面,国际汉学研究所曾建立“历史文献学”硕士点,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生。对于这些工作,李学勤先生都给予了认真而细致的指导。李学勤先生还非常重视国际汉学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建设,把自己多年收藏的与国际汉学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悉数捐给了国际汉学研究所。
对于李学勤先生等人创办国际汉学研究所的这段经历,有学者曾深有感触地说:“大学者从来不为现行的观念所局限,他们总是在别人还没有意识到的领域提出具有时代意义的课题。”④徐葆耕:《四海寻珍·序》,载李学勤《四海寻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这句话很好地道出了李学勤先生提倡国际汉学研究和成立国际汉学研究所的重要意义。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白手起家,并在短短数年中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它在学校院系设置体系中,始终无法由“虚”变“实”,得不到相应的支持。在经过几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由于人、财、物方面的客观原因,国际汉学研究所后继乏力的问题开始凸显。而随着国际汉学研究工作的深入人心,其他众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意识到国际汉学研究的重要性,纷纷下大力气投入,进行国际汉学研究的学科建设,在这种外界形势一片大好的背景下,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逐渐不能赶上其他兄弟院校的发展步伐;加上一些人事调动,国际汉学研究所的工作遂陷于停顿,被其他相关单位的国际汉学研究机构超越。回想起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走过的坎坷道路,让人不胜唏嘘。但是无论如何,李学勤先生在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建设方面所投入的心血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而清华大学国际汉学研究所在国际汉学学科发展史上的地位,也一定会被大家长久铭记。
如今,李学勤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由他和许多有识之士倡导和开拓的国际汉学研究正在蓬勃开展,相信在中外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下,国际汉学研究一定可以取得更大的进步,绽放出崭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