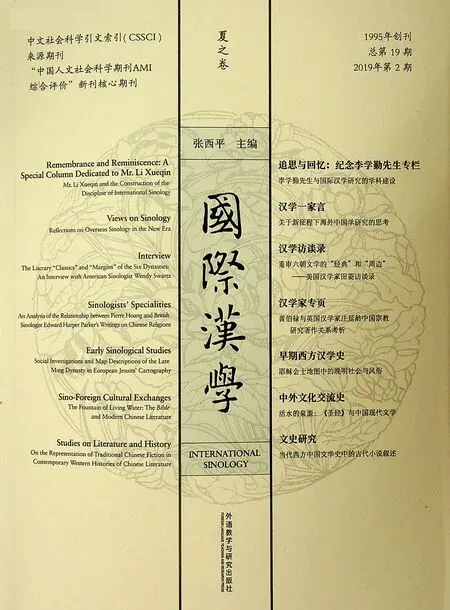欧洲与中国
——米尼尼教授2018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演讲
□李思佳 译
我之所以选择这个话题,是因为我深信地球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与欧洲将在未来建立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与欧洲是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两大文明,或者说两者在过去四个世纪间的关系深刻地影响了彼此文明的发展进程,并在如今也有所体现;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与欧洲可能是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个在当前的社会与政治体系中体现出明显历史连贯性的文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近四十年来,已经迅速跻身世界大国行列。
而欧洲作为一个强大的政治统一体,却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身份危机。换句话说,欧盟所有成员国都在追求同一个目标,即欧洲的统一。然而,欧共体部分成员国不愿让渡主权,更有部分欧洲国家脱离欧盟,欧洲不同区域的经济与社会状况也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另一个危机在于欧盟现行的司法与行政体制同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这也体现了一个真正的体制危机。当下的中国及其在世界舞台扮演的角色都能够并且应当成为推动欧洲政治统一的一种力量,我对此感到深信不疑。
如果不了解中欧两大文明在过去的关系,我们就无法对当下以及未来形成清晰的看法。所以在这有限的时间里,让我们以对历史的回顾开始讲座。
一、古时的联系
中国和古罗马通过安息帝国这个媒介相连接,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接触,然而我们今天无法获取有关安息帝国太多有用的信息。7世纪至9世纪,景教(聂斯脱利派)传教士进入中国,直到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时期仍有不少景教徒在中国驻留,关于这两点我们是可以找到大量信息的,但是这些不能作为中欧文化沟通的佐证。同样地,13世纪至14世纪方济各会教士的传教、中欧之间频繁的贸易往来也不能视作中欧文化交流的标志。马可·波罗是前往中国的商人之一,也是其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些商人以某种方式把中国介绍给了欧洲,比如说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Il Milione,1477),但是他们却没有成功地把欧洲文明带到中国的土地上。直到16世纪末,中欧之间真正的、双向的文化交流才成为现实。
二、中国和耶稣会传教士的欧洲
我在这里说的“耶稣会传教士的欧洲”有两层含义。它首先指的是“耶稣会士向中国介绍的欧洲”。这些耶稣会士把欧洲描绘成一个社会和政治的共同体,具有统一的文化。他们跟随利玛窦的脚步,致力于把自己打造成欧洲的形象代言人。而欧洲无论是在领土、国力方面,还是在历史、文明方面,和中国相比都毫不逊色。其次,通过这个词,我还想表达的是,耶稣会在扩大它的传教范围前,接纳了来自欧洲各主要国家的会士,已经实现了某种意义上欧洲的统一。这种“精神上的统一”在货币与民族统一之前已经得以实现。
耶稣会自1540年成立之后,一直在尝试与中国建立联系。神父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1539—1606)作为出使东方的耶稣会代表,于1578年抵达澳门,这可以视作这一尝试的转折点。当时葡萄牙商人刚刚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而正是在澳门,范礼安对中国的文化、语言、传统、宗教、政治与行政系统进行了深入了解。他意识到,在这样一个闭塞、排外的国度,采取新的传教方式是当务之急。范礼安首创被后人称作“文化适应”或“文化本土化”的策略:作为外国人的传教士必须融入对象国的文化之中,以获得当地人必要的信任,之后再传播其教义。很明显,在这种传教策略中,处于中心地位的是充当沟通媒介的文化知识。
为了实行这一传教策略,范礼安先后派遣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1543—1607)和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1588年,罗明坚被召回罗马,传教的重任因此落到利玛窦的肩上。利玛窦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欧双向跨文化交流。拉丁文版本的“四书”和中文版的《几何原本》正是这种非凡的、双向跨文化交流的代表性成果。想必大家对这个故事都很熟悉,我就不对此赘述了。
不过我想对两方面的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我认为,1742年传教士彻底摒弃中国的传统礼仪,接着耶稣会在1773年彻底瓦解,就这样,中国和欧洲间的交流暂时搁浅。自罗明坚、利玛窦,一直到乾隆时期最后一位欧洲传教士,这段传教的历史跨越了将近两个世纪,其最大特点就是中欧文明间知识的互通。我们在这里只需提及一些最具有代表性的欧洲传教士,他们大部分是耶稣会士,倾尽一生在中国传播来自西方的知识,并把中国的文化带入西方世界。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1575—1620)被利玛窦召到北京,身兼水利工程师、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多重角色,代表作是《泰西水法》(1612)。邓玉函(Johann Schreck,1576—1630)在欧洲更为人知的拉丁文名字是Terrentius,他在入教之前,曾经在灵采研究院工作。他在中国以天文学家和博物学家的身份开展工作,同时还致力于中国历法的改良。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在负责中国历法改良的同时,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执掌北京古观象台。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是一位史学家、地理学家、地图制图师,他是最早的汉语语法著作的作者,还写了一本评论友谊的作品(《逑友篇》)。来自比利时的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工程师,执掌钦天监,同时还曾尝试制造蒸汽机。他的这一实验得到了意大利传教士闵明我(Claudio Filippo Grimaldi,1638—1712)的帮助。闵明我也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同时由康熙钦点任出俄使臣,并在之后接替了南怀仁在钦天监的工作。德理格(Teodorico Pedrini,1671—1746)是康熙宫廷中的一位乐师、作曲家,他向三位皇子传授音乐知识,同时设计并修复乐器。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在1711年至1723年间担任康熙身边的画师、雕刻师,之后在那不勒斯创办了中国学院,也就是今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的前身。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给三位皇帝(康熙、雍正、乾隆)当过宫廷画师。法国的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也曾给乾隆当过画师。我们还需要提到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3—1693,1656年至 1680年在中国传教)、殷铎泽(Prospero Intorcetta,1626—1696)、恩理格(Christian Hertrich,1625—1684)以及鲁日满(François de Rougemont,1624—1676),他们共同把儒家“四书”翻译成了拉丁文版本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1687)。这套书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是欧洲人了解中国文化的重要文本之一。法国的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也是其中之一。他和同伴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在康熙的宫廷内教授数学和天文学。同时他还研究、翻译了《易经》,并在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往来的书信中对中国进行了描述。最后,我想提及的是《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1702—1776),这套34卷的著作讲述的是中国故事,于18世纪在法国出版,是当时西方接触中国的主要渠道之一。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对这套书籍的出版功不可没,他于1685年派遣了六名皇家数学家前往中国传教。这些传教士们引起了康熙皇帝的极大关注,并赢得了他的尊重。
莱布尼茨在他的诸多著作中,把中欧两种文明间无与伦比的信息交流称作“commercium lucis”(拉丁语,意为“知识互换”),我们可以翻译为“双方的知识互通”。但这并不意味着当时双方在经济、贸易方面的交流乏善可陈,只不过这两方面的交流不占主要地位,无法介入到文化交流之中,更无法实现文化的融合。而此后不久,中欧文化交流受到遏制,与之前繁荣的景象迥然不同。
其次我想强调的是,张西平教授建立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实在是一个明智之举,如此我们便可以搜集并出版收藏在梵蒂冈图书馆中的中文文献,这些文献对中欧知识互通进行了大量的记载。这一举措实在是高瞻远瞩,反映出中国人民对历史经验的把握,同时也要求我们集中精神,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再次振兴这种全方位的、以知识沟通为首位的交流互通。现在的欧洲被看作是政治共同体,但是在文化交流方面的战略部署却为数寥寥,我对此感到十分痛心。
然而,中欧跨文化交流这一话题举足轻重,牵涉到全世界人民的命运,因此我想强调一位天才人物的地位,这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就是莱布尼茨。
三、知识的互通:莱布尼茨关于耶稣会传教士的历史经验对欧洲与中国关系的分析
莱布尼茨关于欧洲和中国的关系和两者扮演的历史角色有三个主要观点。
首先,莱布尼茨不断强调,分别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欧洲与中国拥有同等的文明程度,他认为欧洲和中国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地区与国家。
其次,欧洲与中国作为平行和独立于大陆两端最先进的文明,两者的交流会在科学以及社会和平方面对整个世界造成重大影响。
第三,中欧之间进一步相互关注与了解的初步成果,莱布尼茨在这里使用了“伸出双手”的比喻,使得身处欧亚大陆中间的人们寻求更好的生活,这一点在广阔的沙皇俄国尤为突出。
莱布尼茨极其重视中欧关系,他甚至在同居住在中国的耶稣会士通信时,对中欧两大文化、社会与政治系统进行了精确的对比研究,将两者的优势与弱点一一进行比较。
莱布尼茨对两者的优缺点进行了衡量,并意识到在科技层面两个文明可以被认为是势均力敌的。因此他总结认为中欧是天平两端相等的两个重量:中国可被认为是东方的欧洲。然而,如果我们把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自然宗教纳入考虑范畴,那么胜利的天平将向中国倾斜。
此外,莱布尼茨深信中国是收割不同果实的理想之地,他这样写道:
我对中国投以极大关注,因为我认为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当下最重要的事业,这既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以及天主教的传播,也是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以及帮助中国人了解我们的科学知识。这其实涉及知识的交流沟通,对方也会在这个机遇下将他们延续千年的知识赋予我们,我们的知识也将因此加倍。这也是人们往往会忽视的。
而在自然知识层面,莱布尼茨指出应当尽可能快速并全面地收集中国的信息,以此抵偿中国从欧洲吸取的知识。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投向莱布尼茨于1689年7月19日写给耶稣会士闵明我的30个问题就可以发现,这位哲学家的兴趣十分广泛,包含了玄学、几何、陶土、采矿技术、能够抵御腐蚀性物质的染布技术以及养蚕技术。
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莱布尼茨多次抱怨由于战争以及“礼仪之争”,他无法实现知识交流的这一计划。
莱布尼茨自1700年的《论孔子礼仪》(“Sul culto civile di Confucio”)一文开始,对中国礼仪之争加以关注。由此一直到1716年,也就是莱布尼茨去世前几个月完成《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Discorso sulla teologia naturale dei cinesi”),他对这个话题进行了不断深入的分析,提出意见和建议,以避免中国的传教事业功亏一篑,因为中欧的知识沟通渠道也将因传教的终止而关闭。
毫无疑问,莱布尼茨认同圣保罗(Paolo di Tarso)与利玛窦有关“所有一切应当为所有人所共享”的方式,或者说一切人类的知识财富应当为人们所共有,这也是在中国唯一能够收获成效的传教方式。此种方法主要分为两种态度:第一,在中国人的“神”面前,效仿圣保罗在雅典人的未知神祭坛前采取的态度;第二,为中国人的做法和教义提供了与天主教相容的最有利解释。莱布尼茨通过这两点强调利玛窦与圣保罗的立场完全一致。我们可以通过《论孔子礼仪》举出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我赞美利玛窦,他是一个伟大的人物,他在天主教范畴内诠释了柏拉图和其他哲学家的思想。”
在此,我们没有更多时间细读莱布尼茨有关中国的文本,而目前我也正在着手进行莱布尼茨全集第一个意大利译本的出版工作。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欧关系的发展因种种原因——主要是欧洲方面的责任,包括天主教会以及欧洲国家——并没有朝着莱布尼茨希望的方向前进。
四、欧洲的背叛
根据最近的研究,中国自16世纪到19世纪初国内生产总值一直位居世界第一,而完全自给自足的经济使中国感到并没有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的必要。针对外国人来华经商,中国在有限的时间及严格的空间限制内有所开放,这一点极富中国特色并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安息帝国商贾或阿拉伯商人经海路抵达广东,而来自中亚和欧洲的商旅则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最终一部分葡萄牙商人获准在澳门定居。中国始终遵循将外国商人挡在国门之外的准则。朝廷允许来自南方的商人登陆广东,而自丝绸之路前来的商旅则被允许抵达北京,但同时严格限制外国商人们的在华时间,要求其形式必须为小型代表团,并对他们进行严密监管。就在外国商人们受到严格管控的同时,一小群外国学者却被允许在中国大陆开展活动,利玛窦也因此能在朝廷的庇护下创作人文科学著作。中国在知识传播与商贸往来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这条界限是如此清晰,以至于当时在北京活动的外国商贸代表团都被冠上了中国朝贡国使者之名,来华是为了朝拜天子。利玛窦也是借着“欧洲使者”之名,于1601年1月末被准许向皇帝奉献礼物。
直到19世纪初,中国对贸易的态度都没有改变。1792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1737—1806)率领的第一个大型外交商务使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代表团的诉求是签订友好通商条约,在北京建立一个外交代表处,开商埠,划广州附近一个岛供英国商人自由往来,不受禁止,以及其他一些请求。尽管外交使团在觐见皇帝时同意在英国舰船上悬挂中国国旗,但马戛尔尼拒绝面向皇帝的方向进行三次跪拜,因此此次出访最终以失败收场。
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后,日不落帝国已经失去了等待的耐心。英国除了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量种植的罂粟作物出口到欧洲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以外,还向中国走私。彼时的中国虽然有吸食鸦片的广泛习惯,但鸦片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英国一旦找到发动战争的借口,第一场鸦片战争就爆发了(1840年至1842年),中国最终战败并签署了屈辱的《南京条约》。在随后的1844年,中国与法国签订了《黄埔条约》,并同美国签订了《望厦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最为醒目的是其中的“最惠国”条约。此后不久,西方列强开始针对中国北方港口要求修改条约,但遭到了中国的拒绝。法国与英国以一个法国传教士的死亡和一艘英国船只船员被逮捕为理由,在1856年包围了广州港,第二次鸦片战争由此开始,北京圆明园也因此于1860年遭到洗劫。在签订《天津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后,中国被迫赔付巨额罚款,开放10个通商口岸,允许在华的外国商人和传教士自由活动,免除关税,允许外交公使在北京居住,同意内河航道供对外贸易之用,以及鸦片合法化。
显而易见,货币和商品贸易已经占据了知识交流的上风。中国的百年屈辱始于鸦片战争,随后日本入侵,义和团起义受到十个国家的暴力镇压,清朝灭亡,随后的内战。直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近代痛苦血腥的历史才得以终结。然而,中国的崛起还需等待“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之后,邓小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之上,结合了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开放市场,中国在此后的几十年间,重新成为全球舞台的主角之一。
五、地缘政治和文化前景展望
在这种背景下,中欧目前和未来的关系如何?欧洲又以何种身份面对这样一个中国?如果说如今的欧洲要比利玛窦和莱布尼茨设想中的欧洲更进一步,然而我们也无法否认,当下的欧洲对中国而言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对话者,而欧洲任何一个国家也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如今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及其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对欧洲而言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如果欧洲具有应对挑战的头脑,应当抓住时机,加速促成政治经济统一体的建设,并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活跃主体。否则,欧洲将不断衰落,最终沉没于历史长河中。
但我们乐观地认为,欧洲能够建立一个内政、外交、经济、国防的统一体。中国的政体给欧洲以启示,然而也对其提出了挑战:如何在欧洲建立一个同历史传统相吻合的政治社会机制(尽管无法尽善尽美),有效融合居民、安全、经济发展、社会正义与自由。此外,我们也应当集结多方力量在政府层面实现稳定与持续,并采取合理的选举制度来保障政府换届时必要的延续性。
同时,我们有信心实现欧洲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并为不同国家和机构在各领域同中国开展具体合作提供广阔空间。尤其是通过各类研究交流项目,继续利玛窦的未竟事业,实现莱布尼茨的知识互通构想,直到回归中欧之间曾经的知识文化交流状态,与此同时也不忽视商贸往来。
事实上,许多交流项目已在进行中,我们只需想一想为数众多的孔子学院以及许多参与其中的欧洲大学、欧洲与中国研究机构签订的大量双边协议,以及中国学生在欧洲,尤其是在意大利的留学情况。近些年来,我十分有幸在马切拉塔大学指导了六名中国年轻学者的博士课程,而其中有五人如今都在北京工作。这也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具启发意义,并且最令我感到欣慰的经历之一。
如果说我能为在座的各位人文科学、文学、历史与哲学领域的年轻学者们提出一些建议,为你们指出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的话,我将选择中欧人文主义的对比研究。事实上,这一领域早在四个世纪之前就已经被利玛窦及其传教士同伴们,以及中国文人所研究挖掘,其成果至今仍熠熠生辉。而中欧人文主义比较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成功与中国文化沟通的欧洲人文主义并非主要来源于天主教,其根源在于欧洲古希腊古罗马人文主义,以及文艺复兴和现代人文主义的某些方面。我们可以通过深入研究中欧文明的以上种种深层差异,一同追寻真理、改正错误,从而追求人类更高意义上的卓越与自由。欧洲人文主义作为人类文明的瑰宝,与中国人文主义相对照,能够且应当成为地球未来的一个重要文化之源。我并不想混淆中欧文化特征与传统的差异,而是为了突出两者在保持各自差异性的同时,彼此兼容而实现新的和谐。在此我们只需引用孔子《论语》中的警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