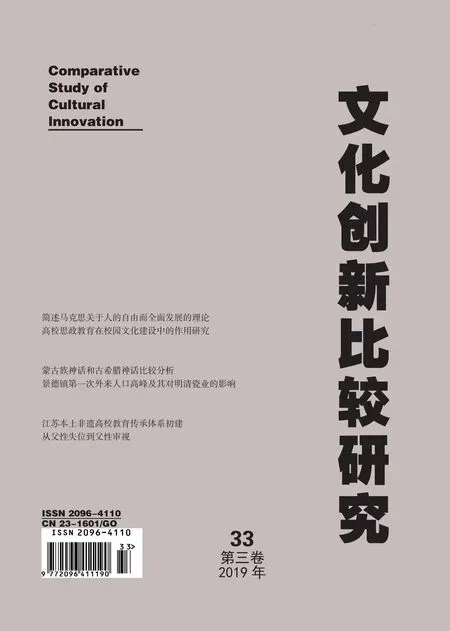从《河童》《傻瓜的一生》看芥川的“不安”
毛玉珩
(潍坊学院外国语学院,山东潍坊 261061)
芥川龙之介(1892-1927)是日本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被誉为“大正文学的象征”。他的文学生涯只有短短十一年,却留下了大量的小说、散文以及诗歌和评论等等。1935年以芥川之名命名的“芥川奖”至今仍为日本文坛的重要奖项之一。芥川的自杀更是被看作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终结,在他的遗稿中阐明了自杀动机:模糊的不安。
《河童》是芥川于1927年3月发表的一部中篇小说,于2月在帝国酒店完稿,距芥川自杀仅五个月,这部小说被视为芥川龙之介人生的“总清算”;《傻瓜的一生》是芥川的遗稿,在这部自传色彩的作品中,芥川对自己的一生做了回顾,可以说这两部作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芥川自杀之前的“不安”心境。本文以《河童》和《傻瓜的一生》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法,探讨芥川的不安,即无法改变的身世带给他的痛苦、家庭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以及芥川对当时整个日本社会环境的不安。
1 无法改变的身世
在《河童》中,芥川借精神病患者的口吻,构筑了一个“戏剧化的昭和初期的日本社会”式的与现实世界相反的河童国,描绘了滑稽、奇特的河童群像。不仅故事的讲述者“我”是精神病患者,就连河童世界里的渔夫巴古、诗人特库、法官佩普等都被设定成了有精神问题的角色。这种设定包含了芥川对其身世的无奈与痛苦。
芥川出生9个月后,其生母精神失常。芥川一生都在为自己是否会从生母那里遗传到精神病所不安,在作品中多次提到自己的母亲是个疯子。然而这种不安在奇幻的河童国中却以奇特的方式轻易得到“解决”。穿越到河童世界的“我”参观了渔夫巴古的妻子生产的场景,当巴古对着妻子的生殖器询问孩子是否想要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时,肚子里的孩子回答说:“我不想出生……我爸爸可能遗传给我的精神病就十分可怕。”听到这些话,助产妇将玻璃管子插进渔夫妻子的生殖器,注射一种液体,她的肚子就憋下去了。吉田精一曾评论说:“我们不得不首先讨论遗传,是因为芥川非常担心这种恶性遗传会遗传到自己身上,这就是在说他自己。”芥川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他对无法改变的身世的苦闷。在河童国的街头贴着的海报上面都“呐喊”出了芥川的心声:消灭恶性遗传。
关于分娩的场景,芥川也曾在自传式作品《傻瓜的一生》中有所描写,主人公“他”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的长子,那是一个很可爱的男婴,但是“他”没有一丝欣喜,心里想的居然是“‘为什么这娃娃也出生了呢?生到这个充满俗世之苦的世界上来。——为什么他命中注定要有我这个爸爸呢?’”他的内心充满了惆怅。对比“他”的妻子分娩和河童太太生产的场景,比起不想出生就可以不必出生的河童,永远不能选择自己身世的人类是多么可悲,芥川在自己构筑的河童世界中无声地呐喊着。芥川不仅怕母亲把精神病遗传给自己,也怕遗传到自己的下一代身上,在遗书中也就此对儿女做了叮嘱。
生母精神失常之后,芥川被舅舅家收为养子,与疯母相伴10年,他在回忆生母时,总会像在《点鬼簿》中写道的那样:“我的母亲是个疯子……她的脸总是毫无生气的灰色”,生母不仅没有给芥川“母亲般的慈爱”,她的精神失常、她的疯癫举止更使芥川背上了巨大的心理包袱,终其一生,芥川都在自己是否会遗传到精神疾病的不安中度过。他的性格也因此变得病态般敏感多疑。在芥川给朋友的书信中,他也曾多次流露出这种不安,例如给斋藤茂吉的书信中,他像是在问他人,又像是问自己:“为何我的母亲会发疯?”随后写道:“我害怕自己会发疯。”在遗书中也写道:“毕竟我是疯子所生的孩子。我对自己不必说,对一切的一切都感到嫌恶。”
特别是在芥川自杀之前的一个月,他的友人宇野浩二也因精神病发作住进病院,宇野住院后,芥川多次前去探视,在《傻瓜的一生》中,芥川写道:“他的朋友之一发疯了。他对这个朋友一向有某种亲近的感觉……他想起果戈里也是发疯而死的,不由得感到冥冥之中有一股力量在支配他们”,朋友疯癫的样子更加剧了芥川对自己是否也会发疯的恐惧,他甚至认为自己的“前途不是发疯就是自杀”。
2 家庭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
幼年起寄人篱下的精神压抑、家庭的经济负担都给芥川带来了很大的不安。
《河童》中关于家庭有这样的场景,年轻的河童脖子上悬吊着七八只河童,河童诗人特库对此评论说:“生活在一起的父子、夫妻、兄弟都以折磨对方为唯一乐趣。特别是家族制度,简直荒谬至极。”关于家庭生活的场景,芥川在《傻瓜的一生》中提到自己跟姨母吵架,思考:“为什么相爱的人要互相折磨”,回想跟异母兄弟经常“扭作一团”,是因为“弟弟由于他的缘故经常受到压迫,他也因为弟弟而失去了自由”,又写道:“在养父养母和姨母面前,他的日子依然过得很拘谨。这就使他的生活形成了阴阳两面。”在遗书中写道:“在养父母家里,从未说过任性的话,做过任性的事。(与其说是没说过、没做过,倒不如说是没法说、没法做更合适)”芥川自幼年起为养父母所收养,他对自己的养子身份十分敏感,没有跟养父母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在另一部自传式作品《大导寺信辅的前半生》中表现出对“由贫困而产生的虚伪”的父母的嫌恶之情,这样的他在养父母家中过得压抑、苦闷。
及至青年时期,芥川的初恋因养父母家的强烈阻挠而以失败告终,初恋失败后,芥川在给友人井川恭的信中曾痛苦地写道:“自私的爱无法冲破人与人之间心灵上的壁垒,无法治愈人生宿命般的痛苦与寂寥……我周围充满了丑恶,连我自己都是丑恶的,生存在这种丑恶之中是一种痛苦。”初恋的失败给芥川造成了极度的精神痛苦,也对芥川此后的人生观和文学观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然而芥川并非没有责任感的人,他仍对自己的养父母“怀着一种近似于孝顺的感情”,在决意自杀时对家人的愧疚,在《傻瓜的一生》的开头就有所体现,“我只是感到,有像我这样的恶夫、恶子、恶父的人们是多么可怜。”
正是因为芥川对家庭尚有责任感,家庭的重担才会导致他“精神上的破产”。养父母家的生活本不宽裕,其后生父和养父同时生意失败,更增加了芥川的经济负担。1927年1月二姐家失火,房屋被焚毁。姐夫西川不久前为家产投过巨额保险,因此被警察怀疑为诈取巨额保险而故意纵火。西川卧轨自杀,留下巨额债务,身为家中唯一有经济来源的芥川不得不拖着病体为此奔走。养父母家、生父家、姐姐家,几家的家庭重担都压在了“月收入最高也没超过三百日元”的芥川身上。《傻瓜的一生》中,他写道:“他的姐夫的自杀猝然使他受了打击。今后连姐姐一家人也得由他来照顾了。至少对他来说,未来就像日暮那样昏暗。他对自己精神上的破产有一种近乎冷笑的感觉。”为家人所累的年轻河童正是芥川自身的写照。家庭给芥川带来的来自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力,是其“不安”的重要来源。
3 对社会环境的不安
芥川生活的大正时代,正是日本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期。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小资产阶级的势力壮大起来,被称为“大正德谟克拉西”的民主运动和民主思潮兴起,政党政治得以确立。早在19世纪末期,日本工人运动兴起,20世纪初,随着日本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传到日本,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马列主义在日本的传播。1921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诞生。但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开始抬头,政府对内镇压工人群众运动,屠杀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对外实行侵略扩张。身处动荡中的芥川并没有脱离现实,正是因为关注,所以社会环境的动荡也造成了芥川的不安。
在《河童》中随处可见芥川对社会现实的描写与批判。比如河童国禁止演奏,在“我”去听演奏会时,遭遇了河童警察的粗暴镇压。而“我”质疑这样的审查是否太粗鲁了的时候,河童却说:“什么?应该比任何一个国家都文明。你就看看日本吧……”。又比如“我”很奇怪河童国中大量的工人被解雇,却没有“罢工”,是因为被解雇的工人都被吃掉了,而且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河童国有“职工屠杀法”。再比如河童国中的政党党魁受报社经理的控制,报社经理幕后又受玻璃公司老板指使,而玻璃公司的老板居然受制于他的夫人。
早在1900年,日本政府就制定了禁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的《治安警察法》。1924年成立的政党内阁,又公布了镇压革命运动的《治安维持法》。1923年关东大地震,统治阶级借机制造恐怖,大肆屠杀社会主义者和进步人士,资产阶级政治充满黑暗。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芥川“肯定社会主义,也不反对无产阶级文学”,受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他曾于1919年发表过《橘子》,这是其作品中为数不多的描写人间温情的一部。然而芥川作为小资产阶级太过软弱,“终未能循此一线光进而发现一个光明的大世界”。
在《傻瓜的一生》的中我们可以看到芥川的呐喊:“你为什么要攻击现代的社会制度?因为我看到了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罪恶。”又分析自己的“病源。那就是……害怕他们的心情。害怕他们——害怕他所蔑视的社会!”
综上所述,芥川一生都在为自己的身世苦恼,害怕遗传到生母的精神疾病;为家庭带来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所累;而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更使他无法跨越阶级的藩篱,在黑暗的社会现实中无法找到自我救赎的方法。最终,只能在这种“不安”中走上了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