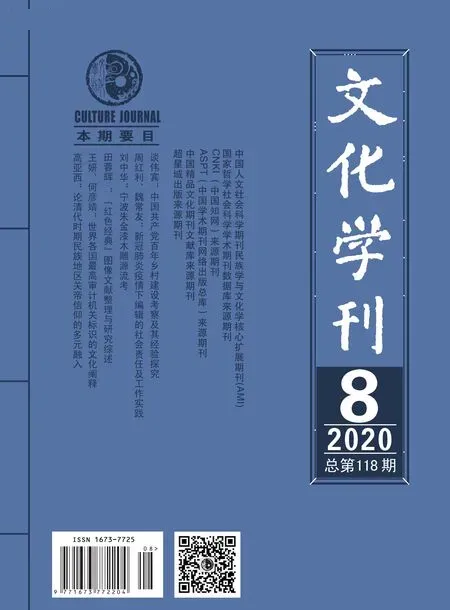时代、体制与社会的边缘
——孙频小说中的“边缘人”书写
周 倩 刘竺岩
“边缘人”的概念最早是在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1908年提出的“陌生人理论”中初具雏形。“陌生人”作为潜在的流浪者,虽存在却不属于当地的社会系统,并未融入其文化体系,保有某种自由和独特的客观性[1]。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正式提出“边缘人”概念:“‘边缘人’(marginal man)是对两个社会群体的参与都不完全,处于群体之间的人。”[2]他认为社会空间的变动对个体的人的心理会产生深远影响,社会地位与环境的变化会使个人的心理、性格及行为特征发生改变。美国社会学学者罗伯特·埃兹拉·帕克基于芝加哥移民问题与跨文化冲突的现象,在《人类迁徙和边缘人》中将“边缘人”定义为生活在未完全相融的文化边缘的个体。帕克的学生埃布莱特·斯通奎斯特在《边缘人》中将“边缘人”定义为一个来自两个对立民族或种族群体的人。此后,“边缘人”的概念得到进一步扩展延伸,泛指与“中心”相对,与主流不相容,最终遭到社会主流忽略、抛弃甚至打压的一类人。
“边缘人”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对于个体而言,现代社会空间频繁变化,包括社会地位升降、社会环境变化(城乡迁移或国际移民)等,都会导致“边缘人”产生。这类人因所处的社会空间发生变化,其属性变得不稳定,产生失去依仗的陌生感、失落感,以及无所适从的孤独感、紧张感,产生过分小心谨慎,甚至自卑自怜,对自己的天性进行抑制等特殊的行为表现。
当代作家苏童指出,不能依托社会阶层地位、社会分工标准和表面的职业身份来判断一个人物是否为“小人物”。人物的“大”与“小”是相对而言的,“小人物”的命运往往更易遭受时代变迁、社会发展等不可抗外力的裹挟,在这种远远超出其存在的浩大力量面前,“小人物”会体现出本质上的弱势[3]。同理,在孙频的创作中,其对人物的认知与理解也未因其表面的社会地位与职业身份以及社会的普遍认知而固化,对不同社会群体中“边缘人”的挖掘与对其命运的观照贯穿始末。孙频笔下的“边缘人”根据社会身份、产生缘由、人生经历的不同,大致可以分为特征明晰的三类人:意义失落笼罩下的知识分子、体制变革阵痛中的下岗职工,以及社会两极分化下的底层人物。这三类人的共性是,同样处于生活或精神中的灰色地带,苦苦挣扎于时代和社会的夹缝之中,但打压、撕裂他们的身份与存在的不可抗力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他们都具有自我毁灭式的悲剧结局,但道路并不相同。
一、意义失落笼罩下的知识分子
作为学院派作家,孙频对当下知识分子面临的困境尤为关注,其作品大量描绘的知识分子形象,除作家、大学教师、艺术工作者等脑力劳动者以外,还包含就读于高校的学生群体,或具有较高学历与知识素养的其他人物。他们是潜在的或自命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在作品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与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高速发展,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盛行。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知识分子群体难以找到栖身之地。“随着市场不断渗透到文化、媒体、教育、艺术、学术领域,社会的价值理念、评价标准越来越被市场所左右……坚守传统知识分子角色,却又遭受各式各样的困境,经费的短缺,公共空间的萎缩,话语权力的丧失,知识群体的分化,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边缘化。”[4]传统知识分子在士大夫精神的指引下,以道德为标准,以家国天下为己任,具有不同于常人且超越现实功利的理想追求与责任意识。他们是诉诸良知的宏大叙事的读书人。但因现代社会市场化经济所引起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巨大转变,知识分子陷入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张力的困境中,被边缘化的生存悲剧不可避免。
《光辉岁月》借梁珊珊与师兄的对话,道出这一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困境:“从前知识分子们的精神启蒙根本抵挡不了一个资本时代的普世价值。”[5]在资本主导下,知识分子的价值与目标被限定,自古以来坚守自我的士大夫传统逐渐消亡,知识分子的内心价值失去根基,话语权也被迫丧失,理想缺失且失语的知识分子被打回原形,曾经相较于普通人群的思想与话语优势被剥夺,与社会中的芸芸众生一道接受物质化的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审判——“即使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上如果到四十岁还没房没车也是没有尊严的”[6]。在这种生存与精神的双重困境中,失去抗争力量的知识分子只剩下两个选择,“要么随波逐流,要么在内心偏安一隅”[7]。但这两个选择都不能真正能引导他们突破困境,因此往往导向同样的精神崩塌与自我毁灭的悲剧。
这一类边缘人作为精神上的先行者,有自己独特的思想和信念,难以被普通人理解,他们常陷入精神上的苦闷与孤独,在生活中表现为颓废、内向,与周边社会格格不入。他们所具有的普遍特征是金钱地位上的卑微及性格上的桀骜不驯,所以这也注定他们与主流社会的隔膜,一方面不愿屈尊以降,另一方面又难以抗拒物欲的诱惑。《光辉岁月》中的女博士梁珊珊,曾度过三段分隔于不同时代的大学校园时光,即从最初自恃清高的女知识分子,历经性神话与物质神话的相继陨落,到回归生养她的小镇,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学老师,将沉溺于都市中肉欲和物欲泥淖中的自己打捞起后,她只是一个顶着女博士头衔的普通人。当弟弟被捕入狱时,她多年所受的教育、所学的知识都毫无意义,最终还是只能依靠物质甚至肉体的贿赂来求人帮忙。当她在文化局局长陈天东的办公室一件件褪下身上的衣服时,知识分子神圣的形象与光环也被剥离,赤裸的肉体展现出残酷的现实真相。
孙频善于通过这种祛魅的形式,剖出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苍白空虚且弱小无力的本真状态,并在其与物欲、肉欲的力量赤裸的对抗中,显示不堪一击的脆弱性。《丑闻》中的张月如是一名大学讲师,拥有标准的女性知识分子身份。她先通过与院长建立肉体联系,以求获得金钱与地位,欲望落空后,又沉溺于和小酒馆老板周小华的肉欲享受。但当周小华最终解构对她知识分子光环的崇拜,两人间情感的上下位对调,女神就降为女人,甚至降为女奴,成为卑微的祈求者。张月如、梁珊珊以及《祛魅》中的李林燕都体现了女性知识分子的特质:具有孤芳自赏式的骄傲心态,同时情感上又渴求着他人的理解甚至崇拜,而人性中难以克服的虚荣,又使得她们无法抗拒来自物质与肉欲的诱惑。李林燕身上的“被抛弃”状态体现得尤为明显,吕梁山区里方山中学的一孔窑洞是她唯一的栖身之所,将她长年与外界平常的社会世俗相隔绝。在其先后三段感情经历中,第一次被她所崇拜的旅美作家在一夜情后抛弃,第二次被平等对话的诗人获得名利后抛弃,第三次被崇拜她的、受她供养的学生在更年轻的肉体诱惑下抛弃。从单恋式的自戕,到女性平等意识的觉醒,再到母性情怀的泛滥,即便用“要爱情也要自由的新女性”身份武装自己,也逃脱不了被打上“作家的摇篮”耻辱烙印以及一再被抛弃的命运。三段感情经历既是祛除爱情的浪漫传奇色彩的过程,也是祛除李林燕具有的女性知识分子身份光环的历程。
孙频笔下的这类知识分子大都具有一个共性,即出身于贫困落后的偏远乡村或城镇,通过学习逃离家乡进入城市,因对物化社会的冷酷现状失望。这类人物有的继续游离漂泊于异乡,试图寻找一隅栖息之地,有的则主动或被迫回归原籍,但他们所受教育的感化以及都市社会赋予的印记,使其同原乡蒙昧的文化环境格格不入。因此,不论身处都市或乡镇,他们都沦为被抛弃的边缘人。“五四”时期,郁达夫在俄国文学“多余人”书写传统的影响下,塑造出“零余者”形象,指代彼时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因接触到新思想而清醒认知到社会的黑暗腐朽,宁愿穷困自戕也不同流合污,往往脱离故土与祖国去寻求救亡的途径,又因感受到时代压迫的不可抗力而陷入性和生的苦闷抑郁之中。孙频笔下的边缘人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存有共性,同是遭受时代的压迫而产生身份与生存危机,逃离了家乡与故土却又摆脱不了其文化加诸于身的印记,在去乡与返乡的双重困境中被边缘化。
不仅有上文提到的梁珊珊、李林燕,《无相》中,与后者同样出身吕梁山区的于国琴,则带有更深刻的家乡文化的精神胎记。她在大山里的家庭靠母亲做“拉偏套”(卖淫)的营生得以维系,这在外界社会文明审视下野蛮落后的风俗,在与世隔绝的山区中却是薪火相传、令人尊敬的职业,“拉偏套”的女人不仅不会遭受冷眼与歧视,还会因为成为家中的主要劳动力获得家里的其他成员甚至是丈夫与公婆的敬重[8]。在家乡社会环境中,“拉偏套”作为封闭文明中一套营生体系,既有尊严也有价值。但在走出吕梁山区、接触到更先进文化的于国琴的意识中,“拉偏套”脱离了原本庇护它的语境,成为烙印在她身上的耻辱的精神胎记,以至于她在老教授的要求下脱光衣服时,也不断用“妓女的女儿”的身份意识自虐式地鞭笞自己。“她是一个大山里的走失者,她回不去了,可是现在,就在此刻,她情愿回到吕梁山,情愿去做一个受人尊重的拉偏套的女人”[9]。在两种文明的夹击之下,挣扎生存于边缘地带的于国琴难以消除其出身赋予的耻辱感,浪漫化的宗教意义式结尾似为其提供了一条精神解脱的出路,在春日夜色中裸露身体的于国琴终于消解了加诸肉身的屈辱,经由“无相”的宗教思想达到形而上世界的圆满。宗教化的书写在孙频小说中十分常见,事实上书中人物往往不是在物欲肉欲的诱惑下沉沦堕落、走向自灭,就是从宗教或哲学中寻求解答、救赎与出路。“通过宗教的中介,孙频将具体的现实矛盾抽象为了纯形而上的论辩,从而我们切实栖身其中的现实世界的问题被完全递交到了理念世界予以解决。”[10]
小说也高度关注右派这类特殊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特殊的时代环境下退至社会边缘,他们的人生际遇与家庭关系也因此遭受极大影响。《松林夜宴图》中李佳音的外公宋醒石、《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的宋之仪夫妇都是个中典型,曾为江南画家的宋醒石被放逐至荒芜贫瘠的西北黄土地上,受尽饥荒、劳苦、孤寂的折磨,留下一幅《松林夜宴图》,也将艺术家式的孤高、漂泊与渴求传承给外孙女李佳音。宋之仪在丈夫不堪忍受迫害跳楼自杀后,为了拥有一个真实亲人的陪伴,与拾荒者生下私生子宋书青,特殊的家庭与出身使得宋书青成为与其母亲同样与世俗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物。这样,右派及其子孙都成为边缘人,时代刻印的伤痕伴随着苦难的记忆和孤独的存在写进这群人的命运中代代相传。
二、体制变革阵痛中的下岗职工
20世纪50年代,在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的背景下,“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宏观发展战略的双重力量推动下,工人成为一种集体化、组织化、行政化的‘单位人’”[11]。到20世纪9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终结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导致单位制瓦解的背景下,工人由‘单位人’变成‘市场人’,工人主体地位以及依附于此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格局被彻底打破”[12]。伴随国企改制的浪潮,下岗职工不但承受了从属于单位而构建的一体化世界崩溃的恶果,而且沦为较为廉价的劳动力商品,被迫面临着来自市场的残酷筛选与压榨。处于断裂状态中的他们在冷峻的现实境遇面前,无可挽回地迅速堕向社会边缘与底层,遭遇严重的生存危机与困境。
孙频的作品,不乏对这类下岗职工群体的关注。《我看过草叶葳蕤》详细描述了交城县在1997年的春天工厂倒闭、工人下岗,大多数人在一夜之间失业的景况。下岗工人被迫转型为街头起早贪黑、抢夺顾客的小商贩,造就了“卖东西的人比买东西的人还多”的情况。作为代言人的杨国红曾讲述其二十岁时怀着终老于此的愿景进入国营单位,却在十多年后就下岗,骤然失去生活依存之归宿的惨痛经历[13]。“国营”“单位”“体制”等金字招牌的神圣印象被消解了,剩下的只有生存压力下“小老百姓”的悲苦辛酸。结尾李天星携着年老衰败的杨国红归去一起看百货大楼被炸成废墟,也是对已然逝去的“草叶葳蕤”时代的祭奠。相较于他们的怀念与告别,《鲛在水中央》中的郭世杰则选择了一辈子被“体制”的废墟禁锢,在外摸爬滚打数年后,他回到深山中废弃的铅矿,将自己放逐至几近与世隔绝的社会边缘,让自己与当初被抛弃后于挣扎生存中所犯下的罪行永远地绑在一起。
《天体之诗》塑造了堪称孙频小说中最为典型的下岗工人形象李小雁。这部作品正如一首挽歌,记载且昭示已然逝去的大工厂的使命和秘密。李小雁穷其一生追随着社会的某种秩序、期许与认可,上学时努力做好学生,流行下海时跟随潮流去南方闯荡,但一个既少知识学历、又缺社会经验只身来到异地都市的打工妹,注定遭受社会黑暗面的残酷对待。在被欺骗、奸污后又孑然一身、无所依仗的李小雁,本能地渴求体制与群体的庇护,明知已经出现下岗潮的迹象,仍旧在三十岁时依靠父亲死于工伤的旧账进入工厂。她将工厂视为庇佑的港湾与最后的救命稻草,延续一贯的“好学生”作风,每日早到晚归、卖力干活,甚至开会都认真听讲、做好笔记,但仅仅两年后,下岗的信号就给她的生存亮起红灯。即将失去最后的生存与精神倚仗的她倾其所有去挽留,哀求哭闹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在厂长办公室脱光衣服,以献祭自己身体的方式期待命运的回转。当她意识到任何牺牲都无法阻止护佑她的体制的断裂,自己又将被抛向堕落丑恶的底层与边缘时,她宁愿选择认下莫须有的罪名,进入监狱,阻断时空的流转加诸她命运的毁灭性打击。
如果说李小雁选择了一种最极端的方式逃避被体制抛弃的命运,厂长和老主任则选择了另一种最极端的方式设法应对和解决这种困境。书中厂长的形象更是一种象征,即体制(工厂)的化身,他以集群的形式统领工人,使其拥有劳动和社会价值,甚至赋予其生命存在的意义。厂长因工厂生,随工厂死,在体制崩坏之时以生命为代价,最后为工人们博取一点同情和利益。通过制造杀人案的大新闻来使社会关注下岗职工的境况,这一看似幼稚而疯狂的举措,开始即牺牲了厂长的性命与老主任的良心,最后还搭上了李小雁的无辜岁月。一方消极逃避,一方积极应对,奋力的挣扎与惨重的代价最后只阴差阳错间换来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只有个中人物知其辛酸,下岗职工依旧在艰辛度日或默默死去。
“纵观下岗工人文学创作,无论是毕淑敏、高君、叶弥等站在平民立场的现实主义写作,还是曹征路、梁晓声等站在精英知识分子立场的批判现实主义写作,人道主义应该是他们创作共同的价值支撑。”[14]下岗工人文学的书写体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意识形态和市场的挤压下被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群体发声的努力,他们意图直面政治与市场,恢复知识分子的主体独立批判精神和启蒙作用,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指出社会问题。以《天体之诗》为例,孙频在小说中借主人公身份,寄托知识分子面对弱者的悲悯情怀,以平视的视角观察、描述李小雁这一典型下岗女工的人生经历,替下岗工人群体发声,对社会转型中的历史阵痛进行反思,再现知识分子的勇气、良知、担当与文学力量,在当下时代语境中秉持对人的发现与关怀,以及人道主义的价值取向。
三、社会两极分化下的底层人物
“从底层问题在中国的逐渐显现来看,中国知识界最早真正对底层的关注实际从小说开始”,“与‘新写实’小说同时,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真正的‘底层文学’,一些小说开始从社会结构的底层来定位农民,如田中禾《五月》(1985)、莫言《愤怒的蒜薹》(1987)、梁晓声《溃疡》(1985)、刘震云《温故1942》(1993)、李佩甫《乡村蒙太奇——一九九二》(1992)等”。这时知识分子对城市底层民众的关注还不凸显,“底层进入知识分子视野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经济不断发展,社会进入消费时代,贫富分化的出现使底层问题显现。直到2004年,才出现了被称为迟到的‘工人阶级的伤痕文学’的《那儿》(曹征路)”[15]。孙频小说对社会底层世界的关注涵盖乡村、城镇、都市三个地理空间,深入剖析底层人的生存困境、情感困境与精神困境,关怀其身体与灵魂存在,探询其悲剧性命运的出路,饱含对人性、人的存在的关怀与对人的生命意义的探寻。底层人物因其生存空间与社会地位属性,本就游离于社会边缘,而其中因社会两极分化、城乡差距扩大,处于城乡异质文化夹缝中的群体身上边缘化的特征则更加显现。
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使得长期冰封、隔绝的城乡空间冰释、交融,乡村遭遇“他者”从根本上的挑战,农民长期固守的文化空间受到撼动,开始跟随时代潮流或主动或被动地冲破空间壁垒,进入城市寻找新的出路。农民工群体中更为弱势的“进城女工”,不仅面临地理空间的变换、城乡异质文化差异的碰撞撕扯、压缩其存在与主体性的风险,还经受性别导致的区别对待所引发的危机。上文的李小雁就曾遭遇此种黑暗经历,留下精神上难以愈合的疮疤。于她而言,与其再次面对那种过去不如去坐牢。《万兽之夜》中作者对“亦人亦兽”者生活的描摹,正是都市打工妹的生存困境写照。作品跟随偷衣服的小秦的脚步,完整展现都市边缘人寄生的灰暗腌臜的城市角落,经由小秦自身身世真相的叙述,剖出底层人充满暴力与挣扎的悲凉酷烈的人生。在追债与躲债的小年夜,人物被围困于欲望和绝望之间,甚至濒于凶恶的兽的异化边缘,达到了近乎非人的状态。
进城女工在物化社会中,受制于直接的经济条件,在生存困境的压迫之下往往沦落风尘。由于性别的限制,城市中的底层女性相较于所具有的劳动力价值,出卖色相和肉体能够更直接快捷地获得更高的利润。这类女性暂时获得了生存条件,却又因内心自我的分裂而陷入情感困境。《恍如来世》中的丁霞靠卖淫养活一家老小,却无时无刻不忍受着内心自谴、自我撕裂的痛苦煎熬,维系生存的方式同时也在将她逼入死亡的绝望。在与另一生活模式的边缘人——丑陋且被孤立的博士生韩唐生的恋爱模式交往中,她短暂地获得了抱团取暖、寻求真爱的希望,但自处卑微的她早已宣判自己没有幸福和明天,在与韩唐生结婚后决绝地终结了受辱的一生。“虽然我是做这行的,可是谈恋爱却是头一次啊,我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是恋爱。”[16]丁霞最后一次内心的剖白,道出自知不得善终的风尘女子渴望真情与归宿的情感困境,肉体纯洁被玷污与心灵上孩童似的单纯如白纸形成强烈对比,辛辣地嘲讽物化社会中人的异变状态。“她好像还是有点不相信那个抛媚眼的是她自己……她的另一个自己似乎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她似乎正在忙于探究自己的身份,在费力地辨认自己究竟是谁。”[17]《不速之客》中的陪酒小姐纪米萍在陪客时灌醉自己的行为,也昭示所有都市风尘女共有的自我分裂身份与存在险境。纪米萍面对同样的情感困境,没有像丁霞一般决绝地以死突围,而是选择了一条扭曲挣扎的求生之路,她将自己沉溺进与同样生存于底层的讨债人苏小军的畸形爱恋中,任由女性的情感与母性的情怀如洪水猛兽般肆意泛滥,倾其所有纠缠、霸占这唯一的爱情与亲情混杂的“真爱”,以卑微至极的姿态渴求填补内心情感的空缺。
作者在《假面》中对被包养的“包子西施”王姝所处的困境书写则更为直白与极致。小说中的人物都戴着假面生存,王姝光鲜靓丽的外表下实质是两个社会阶层的中间物,是她的恋人与丈夫李正仪获取上层的利益滋养、摆脱下层辛酸、拥有优质生活的载体,也是李正仪实现对于将自己挤压至底层的社会与阶层的想象性反抗的施力点。“这女人倒好像成了他和另一个世界的唯一链接,那个和他本是阴阳两隔的世界,现在却不小心被他听到它的心跳声了。”[18]李正仪既憎恶唾弃被老男人玷污的王姝,又难以抗拒、舍弃王姝带来的虚荣与物的享受,两人陷入侮辱与受辱的扭曲恋情中不可自拔。王姝“一方面害怕别人知道她曾被包养过的经历,另一方面又害怕别人真的就把她当成了一个卖包子的女人。她在这双重的恐惧中挣扎着,却终究是不甘心的。”[19]既怕被社会抛弃,又妄图高于世俗,受过物质条件匮乏所携带的无尽苦难的她,不可避免地受着物欲的诱惑,同时鄙弃堕落的自己,希望从同样农村出身、纯朴贫穷的大学生李正仪处寻求精神的慰藉与归宿,结果却将其一起拉入物欲与自我的重重矛盾中,陷入只能戴着假面生存、走投无路的精神困境。这脆弱封闭的生存空间一经打破,便只能导向万劫不复的自我毁灭之路。
孙频小说中的底层人物多数具有家庭残缺的孤儿身份,其精神困境的构成也多与父亲缺位的因素息息相关。《因父之名》中的田小会因父亲田叶军的出走而被周围的人耻笑、孤立、抛弃甚至迫害,被同学笑话,被邻居看不起,被老师强奸,被所有人欺负,缺乏“父亲”庇护的她沦为任人宰割的社会边缘人。为求自保,她不得不自己塑造出“父亲”形象,作为精神的支柱。“她将在这被冷落的废墟中重新为自己挖掘出一个父亲来——一个强大的、高傲的、英雄式的父亲。”[20]瘸腿老头李段的出现,为田小会提供了塑造父亲的契机。表面上,他是保护与帮助小会走出困境的英雄父亲式的拯救者,实际上却是以小会被伤害的秘密绑架她的加害者。陷入更深层精神困境的小会无法摆脱对这虚假“父亲”的依赖,心甘情愿成为向李段献上吃喝供品的奴隶、被其圈养的宠物、发泄欲望的工具,如信仰崇拜般依附于他,使他成为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父亲”及整个世界。《去往澳大利亚的水手》中的男孩小调因父亲入狱,沦为妓女的母亲编织谎言为其塑造出一个远在澳大利亚的父亲形象。男孩终日逃课在桃园里独自游荡,只有同样父亲缺位、远离世俗的宋书青给予其同病相怜式的关照,最后精神困境中的彷徨演变为现实中幼稚冲动的举措,小调离家出走去寻找在澳大利亚的父亲,从此杳无音讯。
《东山宴》中的两个孤儿阿德与采采在冷漠的人世中抱团取暖,天生痴傻的男孩阿德在母亲去世后又遭再婚的父亲抛弃,女孩采采则在父母离婚、各自成家后成为没人要的累赘。在物质贫乏的偏远山区,正常成年人的生存都异常艰难,智障的男孩与“赔钱货”女孩在沦为孤儿后,自然被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淘汰至无人问津的社会角落,所幸有善良的奶奶白氏庇护、照顾得以勉强存活。无依无靠、亲情缺失的采采渴求关爱与安全感,求而不得的情况下选择扭曲极端的自贱自戕方式博取人们的一点关注。自小失去母亲的阿德渴求母爱,常去坟地寻找长眠在此的妈妈,陷入对死后世界的幻想、探询中,不再直面现世。在能让其感受到母爱的奶奶也去世后,他将头钻进奶奶的坟土,同死去的亲人团聚。生活无着、家人缺位的孤儿在悲凉人世中做着无奈无望的挣扎与抗争,行状凄怆壮烈却仍寻求不到生路。《九渡》中的孤儿王泽强在被生活被社会反复抛弃中一路倔强生存,他与同样被世俗孤立、于黑暗孤独中清醒的自闭者刘晋芳相互拯救、支撑着活下去。最终他以自我毁灭的方式达成了最后的救赎与爱,没能从死的此岸渡到生的彼岸,却从生的挣扎状态中脱出,完成精神上的超越与生命内在信念的实现。
肉身的自我毁灭而实现精神救赎与超脱,这并非底层边缘人的生路,却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乩身》中的常勇、杨德清亦是零落在世的孤儿,他们仿佛同一个人的男女两面,又同样在社会与生存的重压之下具有不男不女的身份属性。孙频对两人的书写触及底层人最极致的存在考验。盲女常勇为了存活被阉割了女儿身,性别的丧失将其置于混沌不清的灰色地带,看似获得了更好的生存保障,实则是身份的认知错位。这使其陷入更为边缘孤绝的夹缝中。为生存需求而压抑性别需求,也使其情感需求更为强烈。自小孤苦的流浪汉杨德清早已被排斥在常人之外,长期压抑的情感需求迫使其做出非人之举,被世俗阉割的他更被打上异类的标签,被弃至社会的更边缘。两个同样被阉割的、不男不女的、带有动物性的人命运相连,都通过自残自戕的方式从兽性的非人向神性的非人转化,以求获得在社会中的生存许可。小说对底层边缘人肉体与精神的痛的书写达到极致,结局杨德清自戕至死、常勇自焚而死,都是以肉体毁灭的形式实现精神上宗教意义式的出逃,正如杨德清在死前对常勇说的话:“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终于冲出了自己的地狱。你是,我也是。多么好,我们都不是饿死的,也不是被人打死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