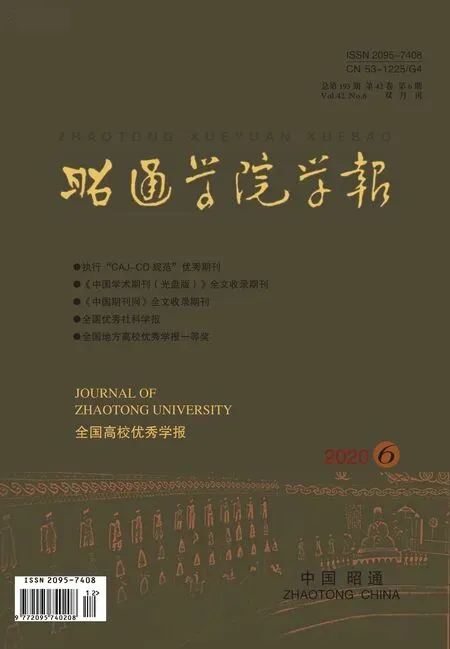徐则臣《北上》的叙事艺术解析
陈娟娟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北上》是徐则臣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自出版后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并于2019年荣获茅盾文学奖。小说以大运河为核心,讲述了一个贯穿历史与现实的故事。1901年意大利人保罗·迪马克因先辈马可波罗的足迹而仰慕中国的运河文明(故而他允许别人称自己为小波罗),因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与翻译谢平遥、船夫周义彦、挑夫邵常来、保镖孙过程等人开启了一段北上的运河之旅。这一路上,既有游山玩水与运河考察,也有对中外文明和历史的借鉴与反思。但由于当时正处于清政府的风雨飘摇之际,当他们沿运河一路北上到达通州时,迪马克先生却因义和团拳民的袭击意外离世。与此同时,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大运河由此开始逐渐走向衰落。一百多年后的2014年,当年北上人群的后人们因大运河又重新相聚,他们都从事着与运河相关的事业,共同为发掘大运河文明而努力。各个家族之间孤立、零散的运河故事又重新拼接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链条。这部小说洋洋洒洒三十万字,将宏大的历史与现实包含在其中,在艺术上它超越了中国传统小说所固有的叙事模式,使整部作品具有了陌生化的美感,使人读来耳目一新,掩卷仍意犹未尽。本文拟用叙事学的研究方法,从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角度对《北上》的叙事艺术进行解析,发掘其中蕴含的浓厚的叙事魅力。
一、交替出现的双重叙事视角
人类对世界的观察通常具有一个观察点,着眼点不同,对世界的认识必然存在差异,文学创作同样如此。当作者要展示一个叙事世界时,他不可能原封不动的照搬现实世界,而要用一定的叙事规范来观照世界,不同的作家观照世界的角度不尽相同,讲述故事时的立足点也具有各自的考量,因此反映在作品中就形成了不同的叙事视角。学者杨义曾言: “叙事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1]西方学者珀西·卢伯克在《小说技巧》一书中也提到:“小说技巧中整个错综复杂的方法问题,我认为都要受角度问题—叙述者所站位置对故事的关系问题—调节。”[2]《北上》作为一部长篇叙事作品,其中自然不乏叙事视角的运用,但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双重叙述角度的灵活运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
(一)全知视角的运用
通读小说不难发现,《北上》中的叙事视角可分为两类:即全知视角与限制视角。全知视角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上帝视角”,“叙述者所掌握的情况不仅多于故事中的任何一个人物,知道他们的过去和未来,而且活动范围也异常之大。”[3]209这种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叙述者犹如上帝一般的存在,能够自由的描写社会,知道事件发生的始末与细节,窥探人物内心深处的秘密。小说的开头就为读者展示了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很难说他们的故事应该从哪里开始,谢平遥意识到这就是他要找的人时,他们已经见过两次。”[4]3叙述者在开头就告诉读者故事发生在谢平遥与小波罗之间,并且坦然告知读者谢平遥与李赞奇的身份:“他们曾是江南制造总局下属翻译馆的同事,李赞奇专业是意大利语,谢平遥是英语。”[4]7而后又告诉读者谢平遥因梦想在当时的社会中“干点实事”而受到同事的嘲笑与上司的冷落,因此接受同事李赞奇的邀请陪同小波罗北上运河。在小说的开头部分,读者通过全知叙事者而得知小波罗来到中国并要北上运河的渊源:“小波罗从小跟父亲去威尼斯,对运河颇有些心得,威尼斯周围大大小小的岛屿全跑遍了。著名的马克·波罗在威尼斯待过多年,小波罗少年时代尊他为偶像。……小波罗要逆流而上,把运河走一趟,好好看一看偶像战斗过的地方。”[4]20全知视角的运用直接了当的将故事铺开来,更加能够驾驭宏大的叙事结构,总揽全局,充分地展现人物性格与作品的布局,实现了文本面向读者说话,使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直接感受文本中叙事走向。
(二)限制视角的运用
在《北上》中,作者不仅运用了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还采用了限制视角。限制叙事就是叙述者和人物知道的一样多,“叙述者寄居于某个人物之中,借助他的感官与意识在视、听、感、想”,[3]222人物不知道的事叙述者无权进行叙述。小说中第一部的第三小节“大河谭”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了谢平遥的后代谢望和为打造运河名片的故事。在这一小节中,叙述者看不到除了谢望和之外的故事发展,叙述者借助“我”的口吻讲述了筹备“大河谭”的种种困难和“我”为此所做的种种努力,并由此将“我”与摄影家孙宴临的命运结合在一起,通过第一人称限制视角将读者真正的带入到故事中去,读者的情感随着叙述者的讲述而起起伏伏。当叙述者“我”精心筹备的“大河谭”面临着被撤资时,读者像谢望和一样忧心焦虑;而当谢望和最终找到投资者并且收获爱情时,读者内心同样会感到欣慰和愉悦。“沉默者说”一节同样也运用了第一人称限制视角,这里的叙述者又寄居在小波罗的弟弟迪马克·费德尔(后改名为马德福)的身上。通过马福德的视角我们得知他在残酷的战争中侥幸存活,并在中国收获属于他的爱情,继而在风雨飘荡的近代中国三十年的人生历程。
(三)叙事视角的转换
《北上》中作者不仅重视不同叙事视角的运用,还成功地实现两种叙事视角的自由转换,突出其高超的叙事技巧。小说中共有三个叙述者,一个是具有上帝视角的全知全能叙述者,一个是作为谢望和的“我”以及作为马德福的“我”的限制叙述者。三个叙事者将故事内容分为三个不同层面:全知叙事者叙述了小波罗一行人北上运河的故事和他们一路之上所经历的种种波折;谢望和叙述了筹办《大河谭》以及孙宴临、邵星池、周海阔、胡念之等人因运河而相遇的故事;马德福叙述了他在中国扎根三十年间的人生经历和中国近代三十年的历史变迁。这三个叙事者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完美结合,始终围绕“运河”这一中心意象,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链条,故事整体曲折而流畅,使人们在领略运河魅力与欣赏曲折故事的同时而又不得不感叹作者的奇妙构思。这种叙述视角的灵活转换不仅使作品在整体叙述中呈现多层次、多角度的叙事层面,更有利于叙述者从多个角度把握人物、叙述故事,从而拉开作者与小说中人物之间的距离,突出叙述者的地位,使读者更加清晰地把握叙述者所讲的故事,使作品整体呈现出一种陌生化的审美感受,增强故事的真实性。作者在写作时不拘泥于一种叙事视角,而是双重视角交叉使用相互转换,使其作品读来拥有一种独特的美感,大大增加了小说的可读性,也是对传统叙事模式的一大创新。
二、丰富多变的叙事时间
时间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体现了物质运动的顺序性与持续性,因此任何事件的发生与发展都离不开时间这一关键要素。文学创作中的时间概念因呈现方式与现实世界有所不同而具有独特性,叙事时间成为叙事作品中不可回避的、令人津津乐道的要素之一。一部作品的写作与阅读过程都离不开时间这一关键因素,叙事过程也就是时间的发展过程,因此叙事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北上》作为一部叙事作品,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叙述的时间因素。
(一)叙事节奏
在小说研究中,叙事节奏的快慢问题与叙事时间紧密相关。叙事节奏可分为:“省略、概略、场景、减缓和停顿。”[5]英国作家伊丽莎白·鲍温认为:“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凡是我所能想到的真正懂得、或者本能地懂得小说技巧的作家,很少有人不对时间因素加以戏剧性地利用的。”[6]在一部作品的完成过程中实际上包括了两个时间概念,一是完成作品的时间,另一个就是故事内容所包含的时间。基于这两者的不同我们可以称它们为“文本时间”和“故事时间”。童庆炳给这两个概念分别下了一个定义:“‘文本时间’就是指故事内容在叙事文本中具体呈现出来的时间状态;‘故事时间’就是指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状态。”[7]也就是热奈特所说的“叙事的时间和被讲述事情的时间”[8]12《北上》中的叙事节奏看似是平稳进行的,就其主线“北上”而言,作者是按照故事“开始—过程——结束”的顺序进行讲述的,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大体上看是一致的,但其中还另有千秋。小说中整体故事时间前后共跨越了一百多年,从1901 的小波罗北上运河到2014年的大运河申遗成功,其中蕴含着宏大而丰富的社会历史与几个家族之间纷繁复杂的人事经历。而在文本叙述的过程中对每个家族上百年的故事都是用一定的篇幅进行大致概括,只对其中与运河有明确关联或在家族中有显著存在意义的人物进行简短介绍,在故事中有关时间的大量素材没有被明确显示于文本之中,很显然存在大量的情节省略,故事的时间长度要远远大于文本叙述的时间长度,由此可见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使故事叙述呈现出张弛有度的特点。除此之外,在大量对事件的描写过程中,《北上》的叙事节奏呈现出减缓和停顿的特点。在对意大利人马福德的详细介绍时,叙事时间停留在1901年时期中国的风云变幻,对马福德所经历的战争过程做了细致的描述,减缓了整体节奏,并且叙事时间在很多节点停留,体现了丰富的叙事时间特点。
(二)叙述的时序
叙事者对时间的操作,除了以文本的疏密度控制时间速度之外,还以种种时间运行方式,干扰、打断或倒装时间存在的持续性,使之出现矢向上的变异,值得注意的变异性态有四种:倒叙、预叙、插叙和补叙。[1]148如果说叙事文本是一条奔腾向前的河流,缓缓行于河道之间,那么这些时间顺序的变异形态就会使这条河流曲折蜿蜒,激起波澜壮阔的叙事浪花。《北上》所体现出来的时间变异的状态主要是预叙、顺叙和插叙。顺叙就是按照时间顺序反映人物的经历和事件发生过程,是中国传统古典小说中最为常见的叙述方式,作者借用这种方式统领全局,顺应故事本身所有的发展逻辑,使小说层次分明,符合人们的对事物发展的认识规律。预叙指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8]17预叙的叙事思路为文本提供了悬念和线索,补足情节和意境的完整性,极大的调动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插叙是指在人物事件原定的叙事线索适当的地方,交代某些情况的介绍,交代某些关系,或者是对事件做一些侧面的说明,引入新的人物。《北上》中的多种叙事时序极大的丰富了作品的层次感。
法国文学批评家热拉尔·热奈特说: “提前或时间上的预叙,至少在西方叙述传统中显然要比相反的方法( 指倒叙) 少见得多。”[8]38而在《北上》中,小说的开头就用预叙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了一次考古事件。在京杭大运河济宁段发现了一艘清朝时期的沉船,出土了若干文物,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封外国人写的书信。“这其中,尤需特别提出的,是一封写于1900年7月的意大利语信件。此信系当地居民个人发掘成果,品相完好,现存‘小博物馆’客栈”。[4]2这里交代的信件、小博物馆客栈都是对后文的描写对象的预叙,形成了动人心弦的审美张力,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伏笔。这封书信是一名改名为马福德的意大利人所写,从而引出马福德这一人物,交代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马福德的个人状况,与后文中小波罗来中国找寻弟弟这一情节构成呼应。与此同时,在《北上》中作者熟练的运用顺叙的方式,按照事件发生的前后顺序讲述小波罗一行人沿运河北上的种种轨迹,从小波罗从无锡开始北上,到途中换船、得到孙过程的保护、因义和团流民偷袭受伤再到最后不治身亡,是严格按照事件发展的顺叙进行描述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顺叙讲述的过程中运用插叙的手段讲述了几段一百年后的现代故事,将邵秉义家的船民生涯、谢望和的《大河谭》栏目、孙宴临的画与摄影作品、周海阔的小博物馆、胡念之的考古学家身份等情节穿插在小波罗北上的过程中,这些人的事业无一不与运河有关,仿佛在不经意之间将这些人与历史上的北上运河相联系起来。并且还使用插叙将小波罗的弟弟马福德在中国几十年的生存状态清楚地交代给读者,看似偶然的叙述方式却在缓缓的讲述过程中逐渐消解了读者心中的谜团,达到令人豁然开朗的叙事效果。通过顺叙、预叙、插叙的手段将故事完整的展现于读者,更使小说情节富有逻辑性,给读者带来丰富而新奇的阅读体验。
三、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
一篇作品的结构,由于它以复杂的形态组合着多种叙事部分或叙事单元,因而它往往是这篇作品的最大隐义之所在。《北上》独特的叙事魅力还在于两条叙事线索的相互交叉与碰撞,从而形成的一种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叙事线索主要指的是作家在某部作品中所采用的故事结构方式。即通过对小说叙事线索的考察,便于读者更好地厘清故事人物与故事情节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逻辑。”[9]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宝库中,双线叙事的手法被很多作家加以运用。如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一条线索是主人公祥林嫂的悲剧命运;另一条是“我”对这个故事本身的所见所闻所思,两条线索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小说的复调结构。《药》中也暗含着两条叙事线索,一是华老栓为患肺痨的儿子购买人血馒头治病,另一条是革命者夏瑜的牺牲却没有唤醒人们愚昧落后的思想,鲁迅将这两条叙事线索穿插、折叠于同一个艺术世界中,从中激荡出动人心魄的思想冲击。莫言的短篇小说《天下太平》中一条线索围绕主人公小奥展开,另一条线索更深层次的突出了人与世界万物的关系问题,两条线索的相互交织,共同促进了故事的发生与发展。双线叙事的手法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中陈旧单一的叙事模式,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小说的单调与无聊,丰富了故事内容,增强文本的结构特点,突出了小说内在的层次感。
在《北上》中,作者不仅巧妙的选取了两条叙事线索,更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实现两条叙事线索的互相交织,在叙述过程中始终以大运河作为联系古今的纽带,将历史与现在囊括在一个宏大的叙事空间之中,增强了小说的深沉的历史感与强烈的时代感。作品中的第一条线索是1901年意大利人小波罗集齐一行人沿运河北上,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经历了近代中国激烈的社会动荡,见证了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等风云变幻的近代社会历史以及大运河漕运的宏伟景象;第二条线索从历史延伸到当下,选择运河申遗作为叙事节点,讲述了与运河相关的几个家族之间紧密关联的故事。邵家自邵常来开始世代在运河上跑船,后代邵星池的船上婚礼引来了摄影家孙宴临的高度兴趣,并将这一热闹的运河景象保留下来;谢家后代谢望和选择居住在运河岸边,筹备运河栏目《大河谭》,深入挖掘运河文化。当面临撤资风险时,机缘巧合之下他找到孙宴临的资助,使栏目继续完善,并与孙宴临修成正果;孙家后人孙宴临喜爱画画与摄影,将宏观壮丽的运河人文与自然风景定格于某个瞬间,留存在时代的记忆之中;周家后人周海阔的小博物馆是对运河文化的探索与继承,邵星池要赎回卖到小博物馆的家传罗盘,让二人打通了与运河之间的关联;考古学家胡念之因讲述运河故事和他们相聚,而他的母亲马思意正是当年小波罗苦寻不得的弟弟马福德的女儿。故事发展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两条叙事线索并不是简单的平行推进,而是始终围绕着大运河这一叙事空间,实现了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相互穿插,产生时空交错的叙事魅力。在小说情节的安排过程中作者将小波罗北上这一事件放置在小说的开头和中间部分,其间裹挟着几个现代故事,看似造成一种时空的混乱,但其实正突出了时空交错之感,正如作者所引用的爱德华多·加莱雅诺的诗句: “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作者并不是在一开始就坦白告诉读者这几个家族之间的种种联系,而是将每个家族故事的前因后果娓娓道来,通过极具代表性的物件将北上的历史串联起来,最终向读者呈现了一个有头有尾、结构新奇的故事,原来他们都是当年北上运河那些人的后代,他们之间的联系可以追溯到一百年前,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隔空对接,给人以恍然大悟之感。正如有学者所说:“作者选取了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设置了历史与现实双线交织叙事模式,让读者在迷惑与眩晕中感受历史与现实的神秘相通。”[10]
西方学者戴维·洛奇认为:“叙事结构就像是一座支撑现代高层建筑的主梁结构,你看不到它,但它决定了你构思作品的轮廓和特点。[11]也就是说,作家构思作品的过程也是其叙事结构的形成过程,任何一个具备丰富创作经验的作家都会精心设计作品的叙事结构,借此展示其作品包含的独特叙事技巧。《北上》中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打通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脉络,建构了宏大的史诗性结构,以大运河这一叙事空间为核心,在双重叙事维度中讲述了曾经北上的几个家族与运河之间的故事,深层发掘运河所蕴含的深厚文化意义,不仅给人一种结构上的错综复杂之感,更重要的是在迷乱之后的豁然开朗,使作品体现了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总体而言,徐则臣的《北上》蕴含着丰富的叙事艺术。首先,他在作品中运用了交替出现的双重叙事视角,叙述者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讲述故事,这不仅是传统单一叙事角度的突破,而且使读者从多方面、多角度把握故事走向,全方位理解故事内容,提高了作品的可读性。其次,作品中丰富多变的叙事时间极大地丰富了故事的层次感。多重时序下的故事具备了深厚的文本内蕴,达到了张弛有度的叙事效果。最后,作者运用两条叙事线索的交织叙事构成了一种时空交错的叙事结构,将一百多年前小波罗等人的沿运河北上与今天的运河申遗成功巧妙的结合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也凸显了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以及对运河文明的重新审视,增强了文本的厚度与深度。以运河作为纽带,徐则臣不仅仅为人们再现了历史上大运河的宏大与壮阔,更是透过历史的足迹去探寻一条河流及其承载的深厚的文化意义,引发人们对历史与运河文明的深入思考。由此可见,《北上》不仅是一部极具艺术魅力的叙事作品,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