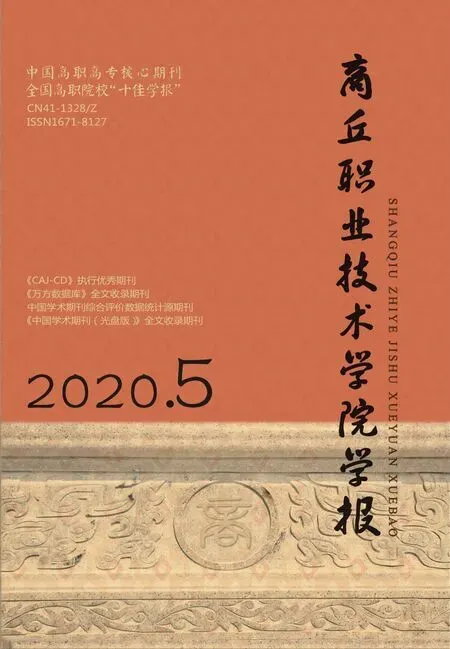归乡者眼中的故乡人
——以《故乡》与《等待摩西》为例
彭亚茹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从古至今,“故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不仅有明确的地理意义,是某个人出生、成长的地方,更是无数中国人的情感寄托之地,是离乡者心心念念、苦苦追寻的精神家园。在古人笔下,当阔别故乡多年的离乡者归来时,他们作为归乡者,心中既有“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亲切与怅惘,也有“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小心与胆怯。在中国现代作家笔下,“故乡”在更多情况下代表着闭塞与落后,是封建糟粕的储存室和散发地。“故乡”既是无数“祥林嫂”灵魂的葬身之地,也是诸多“闰土”麻木、愚昧的根源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寻根文学”应运而生,中国当代作家再次将故乡人和事置于笔端,寻找着故乡文化之“根”的闪光点,他们在以归乡者的视角观察着故乡人的同时,也有着对自我的清醒认识。
鲁迅先生在其标志着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呐喊》与《彷徨》集里,创造性地开创了具有启蒙意义的“归乡”模式,即“离去—归来—再离去”。这一“归乡”模式被诸多现代与当代作家学习和模仿,并以各种新的面貌呈现在文学作品里。直至今日,仍有作家在借鉴这一模式,例如莫言。著名学者孙郁说莫言是与鲁迅相逢的歌者。的确如此,鲁迅在自己的文学版图里创造了鲁镇,莫言则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创造了高密东北乡。在莫言的作品里,能够隐约窥见鲁迅的影子,也能深刻体察到莫言对现代社会、对百味人生的有别于鲁迅那一代人的新的思考,这是莫言作为新一代作家对鲁迅的尊敬、继承与发展。将鲁迅的小说《故乡》和莫言的小说《等待摩西》放在一起,旨在探究同样是在归乡者的视角下,鲁迅与莫言在各自的作品中所书写的不同时代的故乡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
一、 《故乡》中故乡人的愚昧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面对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炮火攻击,中华儿女开始探寻民族振兴之路。政治家尝试以西方政治制度来治理国家,实干家尝试以科学技术兴邦富民,文学家则尝试在国人心中打一针,以救治国民早已麻木的心灵。
《故乡》是鲁迅小说集《呐喊》中的一篇,也是鲁迅小说的“归乡”模式作品中的重要一篇。在这篇只有四千余字的短篇小说里,鲁迅向读者展示了“我”二十余年后回到故乡所看到的与“我”心心念念的故乡之间的强烈反差。就人物而言,闰土是“我”心中重要的故乡人,在重回故乡时,“我”非常期待能够与这位戴着“银项圈的小英雄”的重逢。在“我”的脑海中,闰土是这样的少年:“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戴)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地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闰土领略过“我”儿时不曾看到的广阔世界,也体验过“我”儿时所向往的有趣生活。在“我”的心里,闰土与“我”身边人不一样,他是没有被高墙束缚的少年。可当“我”再次遇到闰土,“我”便明白“我”和闰土之间已经有了不可穿透的隔膜。单从外貌与着装上来讲,岁月侵蚀着他的一切:“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缩着”,“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各种苦难的堆积使他的生活苦不堪言,“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
其实,闰土并不是特例。那时,在中国的大地上,有千千万万个如闰土一般的中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饱受着生存的煎熬。当一个人活着不易、连吃饱穿暖都是奢望时,谁还会有精力去在乎自己精神上的解放呢?从闰土的言谈举止上说,一个言简意赅的称呼说明了一切——“老爷”。少年时期的感情是最为真挚的,无论“我”还是闰土都没有忘记当年在一起的快乐时光,但是,岁月的磨炼早已将那真挚的感情包裹在层层厚茧之下。闰土再不能像儿时那般与“我”称兄道弟。在闰土的心里,尊卑有别,一句“这成什么规矩”便道出了他早已认定“我”是主他是仆的“规矩”。这里的“规矩”不就是那一套用来约束人的无形的封建礼教吗?身份的悬殊,经济的差距,最终导致闰土只能叫声“老爷”。
离开家乡去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的“我”常年辗转于各个城市,不知不觉间,精神中便浸染着来自西方现代的自由、民主气息,“我”的身体上的逃离异地,实际上是想逃离乡村生活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桎梏。闰土却在成长过程中,将自己的脚步更深地扎在这片古老且破败不堪的乡村社会里,深深地陷入了“我”不断反抗和逃离的桎梏中。他已然从一个英姿飒爽的少年变成了为生活苦于奔命的麻木存在。“我”与闰土渐行渐远,那隔膜就像两人手中拿着同极的吸铁石那般,越是想靠近,便越是疏离。闰土对待生活的麻木表现,在更深层次上是愚昧在作祟。千百年来没有人觉醒,更没有人反抗,正是基于人们心中积存已久的愚昧因子的不断发酵。
鲁迅的小说中有许多苦命的妇女形象,比如祥林嫂、单四嫂子等,她们本性善良,却命运悲惨,皆因封建礼教的压迫而默然离世。杨二嫂是《故乡》中作者颇费心思塑造的一位女性形象。与祥林嫂等人所不同的是,杨二嫂极为尖酸刻薄,没有给归乡的“我”留下多好的印象。如果说祥林嫂的遭遇使“我”心生怜悯,那么杨二嫂这个人却使“我”生出了惶恐之情。杨二嫂“薄嘴唇”里说出的话,正是人们对荣归故里的归乡者(特别是归乡的知识分子)的偏见认识,这同样是愚昧的一种表现。不必有亲眼所见的真实和道听途说的传闻,仅凭着这种执着的偏见,杨二嫂自然而然地会认为出门在外的“我”早已得了道台,飞黄腾达。可殊不知在外多年的“我”辗转各地,生活困顿不说,也失去了可寄托灵魂的精神家园。此次归乡与其说是被迫卖房,接家人到“我”所谋生的地方生活,不如说是主动归来,来生“我”养“我”的故乡寻找早已不知所踪的精神家园。可梦终究还是在现实中破灭了。打破这梦的,正是闰土和杨二嫂。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以《新青年》杂志为阵营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若想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必须先使中国人觉醒起来并反抗。他们以文章为媒介传播新道德、新思想,与旧道德、旧思想展开论战,希望引起国民的注意,并意识到自身的麻木与愚昧。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愤怒地指出,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个血淋淋的“吃人如麻”的社会里。但是,他也在作品中深刻地检讨着。他发现,他们所倡导的解放之风并没有吹到遥远的故乡,故乡人仍然生活在旧的社会、旧的观念中。作为觉醒者,他们同样深陷在故乡的泥土里:只露出头颅,半截身子仍藏在泥土里。作为一群提前觉醒的人,他们是孤独的,但随着觉醒的人越来越多,他们会越来越有力量,正如鲁迅在《故乡》里写到的“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一般。
二、 《等待摩西》中故乡人的迷失
《等待摩西》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新作之一,故事发生的地点仍然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1]的高密东北乡,讲述的内容仍然是作家最为熟悉的故乡人事。小说讲述的故事跨时半个世纪,莫言以“我”——归乡者视角来描摹“我”儿时的伙伴柳摩西的生活轨迹。柳摩西一生经历了“文革”时代与改革开放时代。在大起大落的时代背景下,他个人的命运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浮浮沉沉。柳摩西是紧跟时代潮流的人,“文革”时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改革开放时期敢为人先,率先下海。鲁迅《故乡》中的闰土,无论中国大地怎样动荡,仍然遵循着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规矩”,解放之风没有吹到他的心上,他依旧麻木、愚昧。柳摩西不似闰土那般守旧,当新鲜事物摆在他面前、新鲜思想在大地上流行时,他的脑海里也充斥着新思想,他也乐于接受新事物。但他在选择上的困难和道路上的纠结,致使他最终陷入迷失的怪圈。
整篇小说中,柳摩西更改了两次名字。名字的更替意味着柳摩西心中信仰的改变。一开始他的名字叫作“柳摩西”,是爷爷柳彼得(东北乡资格最老的基督教徒)给起的。“摩西”是公元前13世纪的犹太人先知,也是《圣经·旧约》前5本书的执笔者。无论是在《圣经·旧约》还是《圣经·新约》,“摩西”这个名字出现了很多次,可见摩西在教徒心中的崇高地位。爷爷给孙子起名叫柳摩西,一是希望孙子能够和自己一样信奉基督教,二是期盼孙子能够得到摩西的护佑,一生平安。但事与愿违,柳摩西的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大起大落。“文革”初期,柳摩西响应“打倒洋奴”“打倒帝国主义走狗”的时代强音,主动将自己带有宗教色彩的名字改为带有爱国情怀、时代特色鲜明的名字——柳卫东,并建议他爷爷柳彼得改名为柳爱东。同时,在批斗基督教徒柳彼得时,他非常卖力,又是喊口号又是亲自上手教训。柳卫东的行为明显违背了中华民族尊老爱幼、孝亲敬亲的传统美德,但柳卫东却因此赢得了信任,成了大义灭亲的英雄,可见,当时人们心中的价值观似乎已经颠倒。当柳卫东再次改名时,已是他消失30多年之后了。消失多年的柳卫东回家后就将名字从柳卫东改为柳摩西,并信奉了他爷爷柳彼得所信奉的基督教。前后两次改名,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特意为之。第一次是出于年轻时的政治狂热和一边倒政策的压迫,是为了紧随潮流,远离祸患;第二次是出于对过去生活的反叛和对未来生活的寄托。
鲁迅笔下的“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在《等待摩西》中被物象化为“柳摩西/柳卫东/柳摩西”,从文中可以看出,“柳摩西”这个带有宗教色彩的名字并不是柳摩西的自主选择,这个名字是爷爷柳彼得所赋予的期待,因此不能够代表柳摩西的信仰和精神所在。“柳卫东”是柳摩西在“文革”时期,基于爱国情怀和时代特色自主改名,但也不免有政策的压迫,动机并不单纯,因此仍然不能够代表柳摩西真正的信仰和精神。再次叫回“柳摩西”,此“柳摩西”是否能够代表柳摩西的信仰和精神?我们必须秉持严谨的态度表示怀疑。从柳摩西的弟弟柳向阳那里得知,消失多年终于归来的柳摩西的思维还停留在20世纪80年代,而80年代正是他飞黄腾达却突然消失的年代,那时他的名字还是“柳卫东”。在“他”消失的这30多年里,他在做什么,在思考什么,作者故意留白,供读者猜想和联想,所以读者对于柳摩西为何开始信仰基督教的原因不得而知,是否真的信仰基督教当然也不得而知。但柳卫东归来后的的确确改叫了“柳摩西”,也有信仰基督教的表现。大胆设想一下,既然柳摩西的思维还停留在80年代,说明从他开始消失的那天起,他就陷入了迷失之中,这30多年的杳无音信其实是柳摩西内心挣扎的外在表现。那么,归来后的柳摩西真的找到了他的精神家园吗?或者说,基督教就是柳摩西苦苦追寻的精神家园吗?其实不然,柳摩西的归乡与其说是找到了心中的精神家园,不如说是放弃了对精神家园的找寻。“神权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对称性形象,它并非人类的理想国。”[2]基督教的核心思想是福音,即上帝耶稣的救恩。它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可以使人在困惑中找到支柱,使人在艰难中得到慰藉。柳摩西最终选择皈依基督教,便是来源于对现实社会的失望。他希望能够在彼岸世界里找到精神的归宿,而这恰是另外一种避世的行为,与其消失的30多年相比并无本质不同。回归基督教的柳摩西不过是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自我安慰而已,实际上并没有找到真正的精神家园。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回家探亲时,知道柳卫东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好时机,摇身一变成为东北乡的首富。柳卫东热情地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为了显示他的与众不同,也为了在“我”面前不丢情面,他让我听收录机播放的正在流行的“靡靡之音”,而归乡的“我”仍然舍弃不了从小听到大的茂腔。可见,柳卫东虽然赶上了时代的潮流,却遗弃了自己的“根”;“我”虽然是个外来者,却一直思念着故乡的茂腔。值得注意的是,柳卫东播放的音乐中,除了有流行的靡靡之音外,也有家乡人耳熟能详的茂腔戏。这似乎传达着柳卫东将会消失的信息,预示着柳卫东在面对纷繁复杂的花花世界时心中的困惑与纠结。就像鲁迅在《在酒楼上》中所说的“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3]一样,柳摩西的一生一直处在迷失当中,无论是名字从柳摩西到柳卫东再叫回柳摩西的改变,还是整个人突然间消失又悄无声息地回来。作家希望通过一个人在真实世界的失踪来表达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这个人在精神世界里的迷失。
与柳摩西不同,柳摩西的妻子马秀美是一位从未出过远门的乡村妇女,即使在寻找柳摩西的过程中,她也只是在来往的车辆上贴有寻人启事的信息而已。长大后的女儿们想将马秀美接去养老,她也坚决不去,她固守在家里,是为了等待着柳摩西的归来。我们能够看出马秀美对待这段感情的忠贞,但在更深的程度上却透露出马秀美作为传统女性的愚昧一面,她的坚守更多地依赖于以男性为天的传统伦理思想上。马秀美为了爱情,毅然决然地追随着柳卫东,乍一看像是现代女性在追求自由爱情,实际上不过是跟在柳卫东的后面亦步亦趋,她从依赖父亲、哥哥,转向了依赖柳卫东,她心中的以男性为天的传统伦理思想并没有丝毫改变。马秀美是信主的,但谁才是她真正的“主”却值得深思。无论是墙壁上挂着的耶稣基督像的马秀美家,还是“我”外甥口中虔诚做礼拜、不断祈祷着“主”的马秀美,都在传达着马秀美信奉“主”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小说中还是隐隐约约地怀疑着马秀美心中的“主”究竟是谁。在小说的最后,马秀美看到“我”说了两句引人深思的话,即“主啊,您又显灵了……”和“还真被摩西说中了”。到底是“主”在显灵还是摩西说中了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从马秀美无意间说出的话中发现了她的“主”实际上一直都是柳摩西。从即使要悔婚也要嫁给柳卫东始,到两次生活窘迫的经历,再到一直等待着柳摩西的归来,马秀美之所以能够苦苦坚持到最后,正是因为她的信仰始终是柳摩西。在《等待摩西》中有一个类似于“杨二嫂”的人物形象——王超,王超是在村里开小卖部的。小卖部是消息的主要来源,“我”所知道的关于柳卫东的传闻大多出自这里。王超的言语中所夹杂着的感情色彩恰恰也是一种愚昧表现,既是对飞黄腾达的企业家柳卫东的讽刺,也间接地揶揄着作为小军官的“我”。
自21世纪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人民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是,物质生活的丰富却没有带来精神生活的愉悦,仍然有无数“闰土们”“祥林嫂们”陷在传统伦理思想的泥淖里,也有众多“柳摩西们”处于迷茫、焦虑状态。近些年来,人们一味地追求金钱和名利,忽略了自身的心理健康和精神状态,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精神上的不安。莫言在小说中做到了“以小中见大,以点线勾勒社会变迁后当下中国社会普遍的结构性心理状态”[4]。“柳摩西”这个人物形象就是莫言作为一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为我们敲响的警钟。
三、作为归乡者的故乡人身份
在鲁迅小说的“归乡”模式中,小说中的叙述人“我”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我”既是归乡者,更是故乡人。以“我”为参照观察故乡人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以故乡人为参照点,观察作为归乡者的“我”,这种关系是相互渗透又相辅相成的。在《故乡》中,作者写道:“我想到希望,忽然害怕起来了。闰土要香炉和烛台的时候,我还暗地里笑他,以为他总是崇拜偶像,什么时候都不忘却。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吗?只是他的愿望切近,我的愿望茫远罢了。”这段文字是在告诉我们,破除封建迷信、建立新的道德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同时,这也是“我”通过对闰土的观察来反观自己,“我”以为闰土是麻木的,是愚昧的,但“我”也没有彻底逃离麻木与愚昧的魔爪。这在《祝福》中表现得更甚。当祥林嫂问“我”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时,“我”的回答是“也许有罢,——我想”。虽然这么回答的本意是为了避免增添祥林嫂的苦恼,但是,这模棱两可的回答更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与挣扎。在祥林嫂的一再追问下,“我”溃不成军,最终发现“自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5]。作为启蒙者的“我”在面对启蒙的对象时,“我”处于尴尬的失语状态。“我”的背后隐藏着鲁迅本人的心理状态,“我”的再次离去是鲁迅对故乡的逃离,对故乡人生存困境的无可奈何,对知识分子为解放民众心灵所做出的努力的怀疑。
以鲁迅先生为首的知识分子力图通过文学来揭开“瞒与骗”的面纱,带领民众走出麻木与愚昧。如今,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观念侵扰着民众的心灵,民众迷失在日新月异的事物里逃离不开。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之一就是深入挖掘民众的心灵,尝试引导民众解决人生的困惑,寻觅真正的自我。《等待摩西》中的“我”始终在寻找失踪的柳卫东。开始,“我”是以朋友的身份介入了柳摩西的生活,并且“我”把摩西的生活越来越当成一个故事,在追求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我”渐渐地迷失了自我。小说的第三节里有王超和“我”的三段对话,前两段均是王超主动和“我”聊起柳卫东的情况,到了第三段对话时,“我”变被动为主动,率先向王超发问。这样一个转变,虽然有调侃的成分存在,但仍然能够看出“我”已经被这添油加醋所构成的故事深深吸引。在小说的最后,“我”为什么明明知道摩西在家、明明已经走到门口,却不与柳摩西见一面呢?那是因为“我”发现迷失的不仅仅是柳摩西,不仅仅是故乡人,还包括“我”在内的因为各种原因而逃离故乡的人。不听靡靡之音的“我”迷失在故事的漩涡里挣脱不开。
与鲁迅的《故乡》不同,《等待摩西》中实际上有两个归乡者,即“我”和柳摩西,这是莫言对鲁迅的继承与发展。“我”自不必多说,这是和《故乡》中的“我”属于同一位置的人物形象,前文已有所论述。而关于柳摩西,从马秀美的角度看,他归来后与马秀美生活在一起,将名字由柳卫东改成柳摩西并信奉基督教,俨然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和忠诚的丈夫角色;而从柳摩西的子女、兄弟的角度看,柳摩西是嘴里没一句实话,思维停留在80年代并到处找人投资“讨还民族财富”计划的不靠谱者。不同故乡人眼中的柳摩西形象竟然有如此大的不同,这有些不可思议,但只有将虔诚的基督教徒、忠诚的丈夫、不靠谱者等多个形象汇聚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归乡者柳摩西。
无论是明白“现在我所谓希望,不也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吗”的“我”,还是知晓“一切都很正常,只有我不正常”的“我”,鲁迅和莫言都在以归乡者视角观察着故乡人的同时,有着对自我的清醒认识。“从鲁迅到莫言,以‘我’来审视故乡,看到的‘我’与故乡的隔膜,以故乡来审视‘我’,暴露出的是‘我’身上摆脱不了的故乡印记。”[6]无论是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还是想尽办法逃离这片土地的人,每个人都与故乡有着不解之缘。“故乡”一词在人们心中不仅仅指的是自己真实的故乡,更多时候,“故乡”一词充满着感情色彩,意味着人文故乡、精神的寄托之地。作家们的文学故乡虽然是以真实故乡为蓝本的,但表达的内容却是更加广泛的,是以造福全人类为出发点的。
闰土和柳摩西都不是个例,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代言人。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为改造国民精神,弃医而‘治文学和美术’,看重的就是文艺的启蒙工具作用”[7],他通过刻画成年闰土与少年闰土之间的巨大变化指出了封建礼教吃人、群众麻木的事实,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莫言也以柳摩西离奇失踪多年这件事情,形象地表达出他对这个时代众多人内心迷失的思考与担心。作家正是通过典型形象来指出社会上存在的某些问题,因而具有介入现实的关怀意识和批判精神。但是,文学从来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它反映的是生活的多样和人性的复杂,作家虽然指出问题所在,可出现问题的原因仍然只是一种猜想,最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仍然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在鲁迅与莫言的作品中,我们能够看到解决问题的希望,闰土与“我”也许不能再有什么改变,但是,下一代的宏儿与水生“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