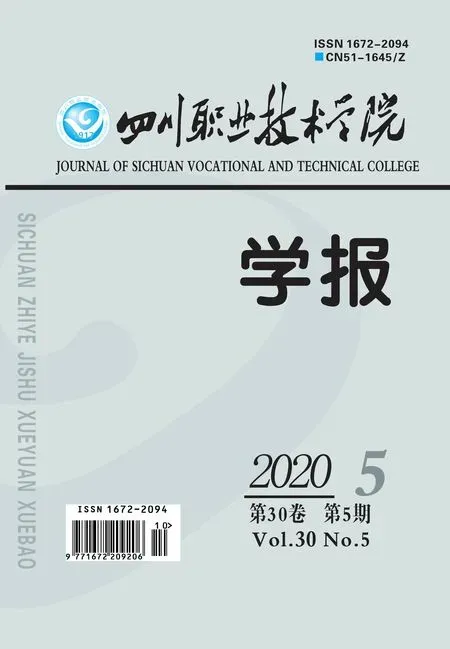论《云中记》中嗅觉书写的叙事功能
魏梦茹
(安徽大学 文学院,合肥 230031)
继2008 年完成故乡回忆系列长篇小说《空山》的创作以后,《云中记》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阿来酝酿十年精心打磨的又一部长篇作品。故事以2008 年汶川大地震为题材,主要讲述了遭遇地震灾难后一个祭师的消失和一个小村落的消亡。作品中阿来用文学话语写出了对生命的敬畏,对人性的尊重,笔端触及人们内心深处共有的灾难记忆和时代创伤,呈现出广阔的现实图景。阿来怀着对自然的虔诚之心和对人类生命的崇高敬意,写出了一部献给地震中死难者的安魂曲,不仅抚慰了逝去的人的亡魂,也从不同程度上修复了地震存活下来的人们的心理缺口,给了生者直面那场巨大灾难的勇气。在作品中,读者能明显注意到文本中出现频率极高的各种各样的气味描写,嗅觉书写是阿来结构小说的重要策略之一,他对气味的描写不单纯停留在感官表面,而是将身体反应融入整个文本的叙事框架里。从嗅觉书写的角度来看《云中记》,或许能发现这部作品不一样的价值蕴涵。
一、嗅觉书写在文本中的呈现
嗅觉相比于视觉、听觉等感官功能而言,更有一种霸道的主宰意味。呼吸与生命同在,当我们不能拒绝呼吸时,气味便从各种通道、入口甚至狭小的缝隙争先恐后地进入我们的身体,透着一股强权的气息,不论你接受与否,气味都将留下印记,成为自身身体记忆的一部分。不仅如此,嗅觉的记忆能力也天赋异禀,曾经接触过的气味再次相遇时很大程度上将唤醒你的感官去搜寻以往的经验并牵动脑部神经判定其产生的时间、地点,最终蔓延至节点式的个人经历。当与一种熟悉的气味相碰撞时,人们会回想到与其相关的种种事件,感受也不再单纯停留在嗅觉层面,而进入气味背后所隐喻的记忆符码。嗅觉诱发心理活动、触发回忆不可以刻意为之,它是一种直觉的特性与本能。
目前学界针对小说《云中记》中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故事的主旨内涵、深层思想意蕴,挖掘其背后闪烁的草木之心与人性光芒,并未涉及嗅觉书写的探讨,嗅觉书写虽不是文本的重要内容,却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意义。在《云中记》中,嗅觉本能主要通过各种不同气味的显现来反映,人的感官接触到这些气味的出场并表达出来。气味在小说中的出场次数并不多,屈指可数,并且其中大部分气味的识别都来自主人公阿巴,伴着返乡路途的进发变换身边的景象,周遭的气味也随着纷纭复杂。例如开篇第一天阿巴在山道上攀爬,“弓着腰向上的阿巴跟在两匹马后面,鼻梁高耸,宽大的鼻翼掀动,他闻到了牲口汗水腥膻的味道。”[1]2阿巴回到云中村晒树皮与枯叶,“树皮和枯叶在阳光下散发着浓烈的柏香”[1]7。云丹牵来的两匹马还在院子里便“散发着热腾腾的腥膻气息”[1]14。云中村人用动物油脂自制头油,散发出来的气味在村民们看来也是好闻的。马的腥膻味、树叶的柏香、动物油脂的芳香,阿巴和村民们感知到的气味几乎都来自动、植物,这是自然界与人类和谐共生的符号。在这和谐相处的另外一极,人类自我意识的强化和创造潜能的不断挖掘,包括动、植物在内的客体世界都成为被征服的对象,他们渴望用武力征服自然并获取驾驭自然的自信,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剑拔弩张。山上久违地出现了鹿群,阿巴本身没有恶意,并强调其“身上也没有火药和铅弹的味道”[1]143,因为这种气味在过去是动物濒临危险、命悬一线的信号,这种气味也不是浑然天成的,它是人类强大意志的反映。小说最后,当阿巴与云中村一同消失之时,“仁钦闻到了空气中充满了破裂翻滚的岩石互相碰撞而散发出的硝石味道。”[1]386山体崩塌、岩石翻滚的画面扑面而来。
《云中记》的叙事文本中,嗅觉书写所占篇幅并不多,但其存在却贯穿小说始终,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文本写作现象,气味在故事的各个章节、片段悄然出现,游走在各式各样的地点、人物之间,与小说的整体叙事紧密贴合。
二、嗅觉书写的叙事功能
除了从一般常见的听觉、视觉等角度对观察对象进行描叙以外,阿来在这部小说中还采用了以嗅觉为重要方式的一种叙事策略。阿来为何花费笔墨、如此细致地描写人类的嗅觉本能及其表现形式呢?采用这种叙事角度有什么样的叙事功能?这都是我们在阅读作品时会思考的问题,也是值得挖掘探讨的关注点。
(一)以气味作为行文线索,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阿来运用嗅觉作为小说叙事的一种角度和方式,除了让读者感受到人类嗅觉本能的独特魅力之外,还有效地提高了叙事效果,使故事的行文结构更加连贯,形成一个有机整体。
这部小说主要讲述的内容以主人公阿巴回乡为起点,云中村的最终消失为终点,其间穿插着阿巴关于云中村地震前的一些片段性的回忆,读者通过小说看到的不仅是一个祭师履行职责的故事,还包括一个传统村落在地震后的消亡史。在阿来的笔下,云中村被描写成一个气味丰盈又具体可感的村庄,生活在其间的村民们能敏感地捕捉到这些气味并为这些气味的显现感到自豪。在村民们的眼中,这些气味是云中村独有的,芳香的头油从动物身上的油脂提取而成,是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表征,村民们用这些气味的存在判定自身的身份——云中村人,离开云中村以后,这些气味都逐渐消失了,村民们也失去了评判身份的依凭,成了无根的漂泊者,村民与云中村之间依靠嗅觉建立的情感纽带出现长达三年的断裂。祭师身份所赋予的使命——祭祀神灵和安抚鬼魂,这是祭师应尽的责任义务,也是主人公阿巴在云中村的职责所在。阿巴在移民村的家具厂工作了四年,做着本不属于自己做的事,内心有着汹涌澎湃的回乡想法。阿巴的回村之路若从嗅觉的角度来说就是一场寻“味”之旅,而这个味道为云中村所独有,离开意味着失去,而回归代表着对这种味道的寻找。肢体对环境的感知能力经常先于大脑的神经思维,当意识无法确定周遭的安全性时,身体反映往往预先提供答案。阿巴还在返回云中村的路上,嗅觉感知便提前到达了这次路途的终点站,用身体反应告知他就要回家了。阿巴回到云中村以后,他的周围便充盈着各种气味,这些气味在阿巴心里都是云中村的味道。废墟上的云中村并没有死去,到处都是生命绽放的痕迹,各种纷纭复杂的气味是云中村鲜活的生活图景在嗅觉层面的表现,当这些气味缠绕着他,他便从心里产生了身份认同。包括祭师阿巴在内的所有云中村人在三年前因为这场毁灭性的灾难被迫离开了生活已久的故乡云中村,这是故事发展的开端,移民村的生活缺少了曾经熟识的气味,这虽然不是阿巴回乡的主要原因,却是启程的导火线,最终他重返云中村并与云中村同眠,像是选择了祭祀的方式将自己奉献给云中村以及村里残存的鬼魂,祭师是唯一也是最后的祭品。气味是这些线索发展变化的重要节点,它将几个主要情节贯穿起来,从起点到终点有机融合成一个整体。故事的整体情节脉络如果从嗅觉的角度来进行勾勒,便是“远离云中村的气味——踏上寻找气味的路途——到达目的地、回到气味产生的原点”,那么从这种文本表层结构来看,嗅觉书写便有着推动情节发展,连接上下,贯通全文的作用。
(二)诱发心理活动,塑造人物形象
人物的形象不仅可以通过人物本身的动作、行为、心理活动以及神态等描写直接达到精细刻画的目的,还可以通过环境、背景或者其他次要的表现因素来侧面烘托、间接塑造人物。在《云中记》中,嗅觉似乎只是角色一种条件反射的行为,与嗅觉相关的书写看似与主题内容的表达不存在什么必要的关联,但实际上很多情境下的嗅觉书写都引发了人物心理活动,自然而然地起到了塑造形象的作用。
小说开端主人公阿巴便说到自己远离云中村的味道已经三年了,云中村的气味残存在村民们的感官记忆中,一旦再度回到同样的环境,这种与气味之间的熟稔之感便会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来。启程对阿巴来说是一次义无反顾的尝试,态度十分坚决,抱着必死的心态,在安抚鬼魂的道路上与这些废墟上的鬼魂一同去往大化之途。阿巴第一次见到云丹安排的两匹马时,灵敏的嗅觉让他在一定距离以外便闻到了这种气息,灵敏源于对这种气味多年接触所培养下来的熟识。在回乡的路上阿巴与两匹马相依相伴,浓烈的牲口汗腥味包裹着他,这种阔别已久的气味再次袭来,无意识中便迅捷地诱发了心理活动,触发个人内心回忆:阿巴回想到地震前的日子里,他总是在这种气味营造的环境中生活。灾难来临,这令人安心的味道也离人远去,但这种气味却并不是虚无缥缈、来去无痕,在过去那么多年里阿巴与它互相触碰,身体与气味结合,嗅感经验像烙印一般深深镌刻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如同旁人无从理解的暗语。当周围的生活背景一点点接近过去的面目,内心的回忆在眼前也逐渐清晰。气味凭借似曾相识的嗅感经验最先牵引他回到三年前的村庄,阿巴明白那个魂牵梦萦的地方就快要抵达,那些曾经有过的经历也会再度发生。回到云中村不久,阿巴的嗅觉反应本能地表现出他对故乡的贴近与亲昵,熏香的气味、祭师行头的气味、就连尘土也是云中村的气味,本能的嗅觉力量实际上是阿巴内心想法的披露,这股远离了三年之久的气味终于再度回归。嗅觉是世间万物的本能特质,对人类而言,嗅觉本能包含着强烈的原始欲望与感官记忆,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直觉特性。阿巴选择留在云中村,安抚鬼魂的同时也在陪伴着这个随时被判处死刑的村落,或许理性思维警示过他这种行为的冒险和可能产生的代价,但嗅觉引起的身体反应又在潜意识中指引着他。嗅觉能够体现人物的心理活动,阿巴的嗅觉本能实际上反映了他内心的欲望,以嗅觉为契机产生的记忆追溯便是在脑海中对目标味道的搜索。嗅觉在阿巴的潜意识中产生了引导作用,带领他在自身真实欲望的指引下完成心灵的救赎与皈依。阿巴选择与云中村、与云中村的鬼魂同眠,不单是为了安抚鬼魂,如果针对个人来说,这种自我牺牲的行为让他完成了精神上的救赎,此处安心是吾乡,在云中村,心灵也得以皈依,生命于此时产生了永恒的价值。阿来着眼于嗅觉这个层面,表现的不单单是人类的本能感官反映,还包含了这种感官反映下真实的内心想法与心理欲望,嗅觉不仅是一种叙事角度,同时也是主人公行为的线索轨迹与内里诱因,这些相关的嗅觉书写不仅生动地将阿巴在各种情景下的心理活动展现出来,也起到了侧面烘托人物形象、使其更加饱满立体的效果。
(三)隐形的二元对立结构
嗅觉书写在文本中具有强烈的隐喻性,传统乡土生活与现代文明的激烈冲突通过嗅觉反映在其隐形层面,同样也采用这种方式暗喻了本地居民与云中村人之间的隔膜,于是在表层文本下便形成两个方面的二元对立结构。
1.人际交往的隔膜
云中村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村庄,村民们相信在一千多年前,他们的祖先带领他们的前辈来到这里并在这里生根发芽。对村民们来说,云中村便是他们的家乡,他们在这里世世代代生存下来,生活温馨,精神幸福。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不仅夺走了许多村人的生命,也摧毁了他们的家园。鉴于地质危害的潜在因素,幸存下来的村民们不得不搬离云中村,离开雪山,在移民村重新生存。在新的环境中生活并非易事,他们与本土居民之间总会存在人际交往的缝隙,无法做到真正的亲密无间。云中村的居民来到移民村和当地的人们之间也产生了隔膜,阿来从嗅觉的角度表达了这种间隙。村民们习惯并喜欢自己身上的气味,同样的气味当地居民却不喜欢,在他们看来这是“山上蛮子”的特有属性,同一种气味在不同人眼中出现了两种完全相反的特性。由这股气味产生的不同反应表明当地居民潜意识中并不把自己当老乡,言语间的关爱掩盖不了内在的隔膜。对村民们来说,他们的体味是在云中村时特有的,当他们离开云中村,这股气味伴随着时间、距离的拉长也逐渐消失了,身份特征的唯一确证不复存在,他们感觉自己不像是云中村人了。在内心他们都想要回到云中村,这个曾经的家园,村民们心中永恒不变的故乡,但他们不得不考虑现实条件,只能在这种隔膜中生活下去,它不是狭窄的缝隙,实际上是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阿来在文中并未赤裸裸地将这种矛盾展露并剖析,而是从叙事者的层面将其通过冷静客观的陈述来处理,反映事实,表现村民们内心的本真想法。虽然作者采取的是冷处理的方式,但通过嗅觉叙事来刻画这种间隙是十分尖锐并深刻的,嗅觉属于人类器官的本能,好坏、优劣的评价背后隐含的情感态度是最真实、不经掩盖加工的,本地居民无意识的感受更强烈地刺痛人心,这种对立来源于人际交往中的隔膜,也是一些现实的、传统的心理习惯使然。
2.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对峙
如果说人际间的矛盾尚不尖锐甚至经过时间的洗刷能够磨平其棱角,那么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冲突则会在历史的作用下得到凸显并且是无法圆满解决的。20 世纪后半叶萌生的信息革命带领人类进入到全新的电子智能时代,机器解放了人们的双手,催生了很多全新的产业和社会领域,同时,也有不少曾经辉煌的传统逐渐破败甚至消失。虽然阿来在小说中主要讲述的时间点与地震以前和地震之后相关联,但他通过阿巴的回忆让读者见证了云中村接受现代科技文明洗礼的整个启蒙过程,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云中村通上电一直延伸至21 世纪的现在。一大波新概念、新事物向云中村涌来,这都是村民们的认知里从未有过的,这种冲突很明显地体现在语言里,他们发现自己的语言好像没有办法描述出整个世界了。新东西的进入极大提高了村民的生活水平,但人们对这种技术文明并没有全盘接受,技术可以带来物质上的便利,却不能抚慰精神上的空缺,他们没有办法像过去那样一边劳作一边悠悠歌唱了。现代世界涌入传统王国,首先就是要摧毁最古老的那一部分历史与经验[2]。封建迷信的祭祀行为被明令禁止,与牛、马等动物之间的情感维系也消弭了,这些牲畜的作用因为机器的到来被代替,阿巴准备马匹上山之前也发现云中村已经有很多年不将马作为交通工具了。搬到移民村以后,人们的谋生方式也出现很大变化,许多村民变成了具有针对性工作的职业人员,传统农业成了商业性质的观光农业。阿来没有从生产、生活方式上的改变表现这种冲突、将其直接挑明,但从嗅觉叙事的角度也暗指了传统世界与现代文明的对峙。村民们用感官亲身体验两种文明的差异,移民村没有马的腥膻味,也没有柏树叶的馨香,所代替的是工厂里厚重的油漆味,穿着一身工装在家具厂工作的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也没有云中村的味道了,取而代之的是科技符码的现代气息。
传统与现代文明的对峙、移民村村民与云中村人的间隙是小说在人际交往和文化传统两个维度的二元对立结构,这种对立模式间接成为叙事的强大动力,正是这些异质因素的存在打破了生活本真的稳定状态,使主人公灵魂与肉体分崩离析,不得不踏上寻求生存本质意义的征途。
(四)营造静谧的叙事空间
与嗅觉叙事相比,小说创作中听觉叙事运用的频率往往更多,在很多作品中会用较多体量的对话、语言、声音描写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背景的介绍以及故事情节的展开,作家用听觉叙事构建了一系列声音景观。文学作品中,声音的先行出场不仅仅是定调子,还提供了时间、节令、主体所处位置、周边环境以及人物的精神状态、心情心境等相关信息[3]。在这类小说中声音作为一种媒介,读者通过对声音的捕捉将其转化为相对应的人、物意象,从而发现原始的文字编码空间。例如阿来之前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就是一个典型的声音文本,里面充斥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信息,宏大热闹,错落有致,读者通过听觉拓展对应的想象空间,整个场面可能是十分喧嚣的。嗅觉与听觉、视觉相比有自身不同的特征,嗅觉是一种远距离的感觉,但双方之间的内在感知是紧密的。传统创作中对审美对象的观照、主观审美感受的传达往往采用视觉描写的方式直接表现,这种叙事手段的确能让读者展开广阔丰富的想象空间,却没有完全深入客体的内里部分,停留在表层的描叙对读者的想象产生了一定的阻断。嗅觉相对于视觉、听觉、触觉、味觉而言,因缺少限制,因与呼吸同在,更能直达个体生命[4]。与单纯的视觉、听觉经验相比,用嗅觉探索自然的行为更加亲密,两者间的气味相互交织,双方达到了一种零距离的接触。嗅觉的表现形式是各种不同的气味,气味无形却又十分立体,对嗅觉主体来说,气味是一种强烈的氛围充盈在周围环境中,即便距离尚远但是已经亲密贴合,在还没有目睹之前,嗅觉能够提前预知,这种短暂的过渡可以让读者更好理解接触对象的内在蕴涵,通过嗅觉叙事创造出的灰空间去设想这种气味的来源以及它背后的面目。在这部小说中,声音出现的频率降低,人物对话的比重也减少了,对物、环境的描写占据很大篇幅。阿来侧重运用嗅觉书写将文本塑造成了一个静谧的叙事空间,这个故事不仅是写给地震死难者的安魂曲,也是给读者心灵上的一剂汤药。在小说中,声音的话语权被气味代替,沉默的文本空间更有利于读者在阅读时体会种种气味背后的具体意蕴与复杂内涵,理解语言文字背后的言外之意和韵外之旨,并将这种阅读体验在寂静中升华,从而引发对生命、自然的思考,这是阿来创作的目的也是这部作品的意义所在。正如阿来自己所言:“《云中记》这本书,在表现人与灵魂,人与大地关系时,必须把眼光投向更普遍的生命现象,必须把眼光投向于人对自身情感与灵魂的自省。”[5]他用冷静客观的文字直书灾难,疏解经历者们的伤痛,从绝望中生发出希望,通过个体的消失和一个村落的消亡达到对整个人类群体命运和精神的观照。阿巴的肉体虽死,精神永存,这个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不仅抚慰了小说里的鬼魂,也震撼了现实中的读者,启迪他们寻找物欲横流时代剪影下自身迷失已久的灵魂。
三、结语
对于人类而言,嗅觉与味觉、视觉等本领都是人们普遍存在的原始本能,正常情况下几乎所有人都具有这些能力,集体共有的经验特质不仅对群体日常生活有益,作家们还可以利用这个集体本能进行文学创作,因为文学作品的受众也是这个广阔的群体空间。阿来用《云中记》创造出一个生动丰富的嗅觉世界,以嗅觉书写作为小说叙事的独特视角与表现方式,凸显了嗅觉书写强大的叙事功能,呈现出全新的艺术体验,打破了已有的审美期待,有意让读者感受到人类嗅觉本能的强大魅力和嗅觉叙事的独特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