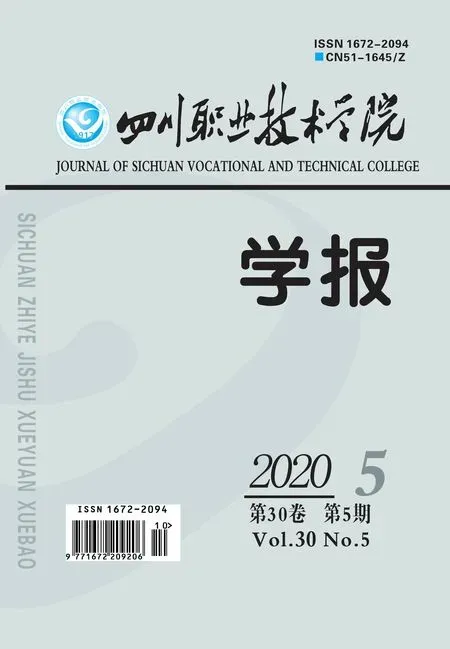警惕知识产权的过度保护
——以激励理论为视角
王 慧
(华东政法大学 知识产权学院,上海 200333 )
一、激励理论视角下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
知识产权的客体作为一种原本可以自由流通的信息,为什么法律会在这种无形的客体之上,赋予相关主体一项排他性的权利?知识产权制度发展至今,对于该问题,学术界已经有许多理论来解释知识产权制度存在的正当性①,如人格学说,劳动财产理论等①。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对于知识产权制度正当性的解释也有所不同,基于功利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倾向于将知识产权制度认为是一种激励创新的政策工具,正如林肯的一句名言,就是将专利制度评价为: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从自然法思想指引下理解知识产权制度,天赋人权的观念较浓厚。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舶来品,在法律移植的过程中,多是法律技术层面的借鉴,并且我国受到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双重影响,因此在法律文字背后就难以分析出一个从一而终的价值导向。但是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不断推进,从战略部署的各种文件中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更多的是将知识产权制度作为一种激励创新、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政策工具。
最早对知识产权的激励创新作用进行深入分析的是Arrow,Arrow 在其著作中指出,信息产品具有的非竞斥性和天然的非排他性,导致了“搭便车”的问题,其他生产者如果可以随意复制其产品,原生产者可能无法获得足够的回报,无成本的传播会造成思想产品的创新和激励不足,从而导致生产不足[1]。法国著名的民法学家菲利普·马洛黑和洛珩·阿奈斯在他们2005 年版的《财产》一书的封底上写道:财产权利是一项有关财富的权利,如果没有这项权利,就没有自由也没有繁荣,但若过分强调财产权利,这几乎会不可避免地降低人的价值。从可持续发展来看,西方的未来在于智慧财产权和非物质财产权。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法律的立法者所要关切的,需从传统的分配正义即如何将一块蛋糕分的公平合理,转向如何设计制度激励人们去创造更大的蛋糕。
当然,对于知识产权激励创新的正当性基础,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学者杨延超在其著作《版权战争》中就提出质疑,版权制度真的能鼓励创新吗?人类社会已经有5000 多年的历史,而版权制度是近300 年才出现的,试想在没有版权制度的文艺复兴时期还有中国的唐宋时期,大量的文学艺术作品层出不穷,甚至中国的很多诗人在其一生最穷困落寞的时期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作。如果没有著作权法,创新会停滞吗?学者杨延超最后总结:创新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本能,而并非是基于利益和法律的考虑,人们不会停止发明,人们不会停止写作,人们不会停止创新[2]。
从历史的角度看,在没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存在的时代,文学艺术作品仍然不断诞生,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但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时代在发展,现代社会的发展已经催生出不同的职业需要,社会的运转也越来越讲求效率。在没有著作权法的唐代,同样没有诗人这一类专门的职业,而在当今社会,有许许多多的作家,他们以写作为生;而当代人们的需求也已经从物质转向了精神文化,人们愿意用一般等价物来交换能使自己精神得到愉悦的知识产品,知识产品已经可以作为有价值的“物”在市场中进行交易。此时,如果不给这类“物”划定专有权的归属,在交易时没有普遍遵守的秩序,就会产生“公地悲剧”,导致有限的智力成果资源无法发挥其最大的经济价值。因此,为了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好的法律,应当通过对权利、义务、责任、信息和程序的有效安排,提高经济效率,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这也是法律经济学所追求用经济效率取代传统的公平正义[3]。此外,从个体的创作者角度出发,按照法律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成本收益分析,理性的创造者在进行创新时会考虑成本收益,如果其付出了时间或者金钱成本,最后因为无成本的广泛传播,其他使用者的无成本使用,导致最初的创新者收益甚微甚至没有收益,因为缺少激励不能收回成本,此时创新者很可能就会选择不再创新,等待搭其他人的便车,无成本地使用别人的创造成果,由此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社会总的创新产品会减少,优质的资源减少,更不用提资源的最优配置,这也是不符合法律经济学的效率原则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产品的产生需要制度激励。
(一)专利制度与激励理论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曾经震惊世界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活字印刷术,拿其中的一项活字印刷术来讲,其发明主体毕昇这一生就只有这一项发明;放眼国外,发明大王爱迪生一生有几千件发明,并且当时爱迪生生活的时代已经有了专利制度,爱迪生本人的专利权利意识非常强,每出现一件新的成果,他都会及时申请专利。从这个角度看,好的专利制度对于激励创新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商标制度与激励理论
在商标领域,商标制度创设的目的很难说是为了鼓励创新,因为很多商标标识都来源于公共领域的文字或者图形,但不妨碍将商标制度理解为一种为了提升效率而创设的一种激励措施。我国现行商标法第1 条明确了商标法的立法宗旨,其中有一处是“……以保障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商标制度关乎消费者的利益与市场的秩序;商标的首要功能是防止消费者混淆,这其实就是在减少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服务时的搜寻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另一方面,通过赋予经营者商标专用权,经营者才会在相关的商品或者服务上投入资金进行广告宣传、提升质量,通过赋权,整个社会的成本是最小的,而且资源得到了最优的配置与利用;相反,如果不给相关经营者一个专用权,因为他在产品或者服务上的投资无法让消费者识别,进而给他带来经济回报,他就没有任何动力在产品或者服务上投资,整个社会的资源与效率没有达到最优。因此,商标制度也是一种激励经营者的政策工具。
(三)著作权制度与激励理论
人生百态,人总会经历酸甜苦辣,进而产生情绪的波动;人又是一个社会性动物,需要与他人互动,因此就有了表达的需要,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使得人们的精神世界十分丰富;我国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西方国家更是十分注重保护言论自由,甚至很多时候会认定在自我表达的言论中使用版权材料是合理的,因此非经济激励因素可以解释人们从事某些创作活动的动机,因为人们有表达的愿望和自由;但是在如今的著作权诉讼中,主要的利益持有人不再是作者、作曲家,而是出版商、电影或音乐制作者,从版权制度的历史中也可以看到出版商为了垄断版权而做出的努力,他们的动机无一例外是获得经济回报,因为他们对原始的作品进行了投资与包装。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也是出版商或者电影制作人垄断书籍或者电影的版权,获取巨额的利益,而作者拿到的只是杯水车薪,当然也有很多作者因此大红大紫,拥有大量粉丝。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作者的力量有时比较弱小,最早只能通过在竹签上书写来传播思想,而现在的传播媒介极为丰富,出现了电影电视剧等多种作品的展现方式;原创作品的创作固然十分重要,但是更离不开出版商、电影制作者等媒体的投资,他们不断为作品的表达形式和传播方式进行新的探索,同时他们付出的投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获利。因此,著作权法也需要打造一套激励创新的制度。
二、知识产权过度保护的表现——以著作权为例
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扩张最为明显的就是著作权;因为著作权法为权利人创设了一个十分宽泛的“演绎权”,著作权人可以预见到他人可能对其作品进行复制或者演绎性使用,但在创作或者传播作品时,著作权人并不能控制所有周边的使用行为;虽然后来出现了“合理使用”规则来防止著作权不合理地扩张,但是在侵权与否的界限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原则可以指引,因此有必要将著作权侵权判定与其他民事侵权判定做一个比较。
与大多数侵权责任法和制定法不同,著作权法是通过授予权利人广泛的权利,他人未经许可实施这些权利控制的行为就构成著作权侵权,而不考虑这些行为是否对著作权人产生有意义的损害。我国法院在著作权侵权的认定中,经常不会要求证明被告使用版权材料的行为导致了影响原告创作激励的任何损害,在考察合理使用抗辩时可能才会考虑著作权人的损害,但通常这个时候证明责任转移到了被告身上,即由被告证明不存在损害。并且损害的认定成为一个循环论证的概念,几乎任何未向著作权人支付报酬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对其的损害,因为被告原本应当就其使用行为向著作权人支付许可费[4]。实际上很多使用作品的行为,并不会对著作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反而会带来正面效果。在美国就存在一些这样的案例②,在华纳兄弟娱乐公司诉RDR 图书公司案,哈利·波特图书及电影版权人起诉未经授权的《哈利·波特辞典》百科全书的出版人,法院驳回合理使用抗辩,认定该辞典会损害哈利·波特系列演绎作品的市场。但是来自亚马逊网站的证据表明了相反的事实,购买辞典的用户也购买了会受到损害的那些演绎作品;并且亚马逊网站会推出折扣活动,鼓励用户同时购买二者③。因此,著作权侵权认定中,如果不考虑损害要件的话,理论上会使很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使用行为受到不合理的限制。
至于何种程度的使用会给权利人造成损害,现阶段我国司法实践受到不当得利的理论影响,即认为如果有人通过使用他人的作品获利却没有支付报酬,他就获得了不当得利,必须予以规制方可实现公平;这样的价值导向就使得著作权人几乎可以禁止任何使用其作品而获得报酬的行为,即使是关系较远的市场上的使用也会给权利人造成损害。例如法院在功夫熊猫案中,创设了一个“商品化权”④,这无疑就使得著作权人可以禁止将其作品进行商业化使用的任何行为,这样的强保护确实极大地保护了著作权人的权益,但是强保护的同时应当防止过度保护,知识产权法还有促进创新的公共目标,在权利人的保护与公共福祉的增加上不可偏袒任何一方。同时“边际效用递减”的经济学原理给我们很好的启示,按照法律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著作权人是理性的经济主体,在进行成本收益分析时,他们投向创作和发行作品的边际投资取决于预期边际回报,并非他们无法预见到的报酬[4];通俗地讲,理性人只要能获得其预期的回报就能起到激励作用,除此之外多余的回报只能看做意外的收获,并不值得给予法律上的回报,因为这种限制对创新没有多余的激励,而且还可能不合理地限制公众的使用,削弱其他人借鉴该作品再次创新的热情。只有当侵权人进入的市场是著作权人在决定是否创作或发行作品时会加以考虑的市场,才可以直接推定损害的存在;对于将作品使用在关系较远的市场上时,认定侵权的存在还需要谨慎。在“功夫熊猫案”中,功夫熊猫电影和形象的创作者在创作时,能够预期的收益只包括在电影及其近似的市场中的使用行为,对于将功夫熊猫申请注册为商标,创作者是无法预料的,这常常是因为在原来市场的成功产生的经济溢出效应,这种类型的经济溢出效应在我们的社会中普遍存在,经常都没有得到报酬,比如买家穿着其购买的运动鞋参加比赛获得奖金,此时运动鞋的卖家无权要求其从中也获得相应回报。类似地在著作权领域,如果将某个较成功的影视作品中的形象用在其他领域比如衣服的图案上或者注册为商标,此时著作权人是否有权限制?我国法院一般认为将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注册为商标或者使用在与原作品关系较远的市场上,损害了原作利害关系人应当享有的商业价值和交易机会⑤。按照这样的逻辑,著作权人可以基本上就可以控制所有市场,即使是创作之初没有预料到的市场,也应该为权利人保留相应的交易机会;此种保护趋势带来的风险就是著作权人会垄断整个市场,但这并不是著作权法激励创新目标的最佳实现方式,因为创作者不可能因为其作品在服装市场中的成功而更有动力去创作一部电影或者影视形象。
三、警惕知识产权过度保护——关注创新激励的损害
我国学术界在既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普遍认同,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本质上就是权利人专有控制的财产权,类似于不动产,任何跨过栅栏擅自使用作品的行为都是对权利人专有控制的损害。但是知识产权制度作为舶来品,我们仍然应当保持价值中立的态度去分析,其实知识产品与传统的有形财产是存在本质的不同的;首先是知识产品具有非竞斥性,一个人的使用不会影响其他人的同时使用,也不会减损知识产品的价值;其次,不动产的边界十分清晰,而对于著作权法,保护的是一整部作品,那么多大程度上的复制或使用才是侵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加上合理使用制度,使得著作权的边界加模糊不清;再次,不动产权利的明晰与著作权的立法目的是不同的,不动产权利授予的背后是防止公地悲剧,而著作权的立法目的是促进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⑥。即使将著作权视为一种财产,它与传统的有形财产也存在本质的不同;因此,给予知识产权以专有财产权的保护并不是最优的选择。
确定知识产权的最优保护程度是一项极其困难的工作;一方面,如果创新带来的预期回报增加,会增加人们的创新激励;另一方面,如果借鉴他人的思想的成本增加,则可能会降低创新激励。总之,知识产权制度要以激励创新作为其重要关切,而不应该不加怀疑地将其视为权利人专有控制的财产权,给予其近乎垄断的保护;有些跨过权利边界的使用行为不但不会给权利人造成损害,反而会增加权利人的收益;因此是否有损害的发生在知识产权侵权的判断中应当予以考虑,同时这种损害的界定要围绕知识产权的价值目标——创新激励,以削弱创作者创作热情为价值导向,其他民事上的损害如名誉损害等产生的责任就不是知识产权侵权责任,应当交由侵权责任法而不是知识产权法来解决。因此考虑是否存在创新激励的损害是防止知识产权权利无限扩张的良好工具。
针对权利扩张日益明显的著作权,在侵权的判定中,法院应当重视损害要件的证明,在具体的规则设计上,允许被告证明其使用作品的行为增加了作品的销量,允许损益相抵,考虑这种情况下构成合理使用,而替代原作品销量的行为构成侵权,才更符合著作权的激励目标与最优保护。在一些疑难案件中,回归到著作权法激励创新的立法目的,并非所有的商业性使用行为对创作激励有害,也并非所有的个人使用行为都对其无害,因此必须考虑是否存在创新激励的损害,防止权利的过度保护与肆意扩张。正如金庸诉江南一案中,是否构成著作权侵权的问题,学者总结为同人小说侵权与否的问题,更多的是在著作权法本身的框架中讨论。如果回归著作权法激励创新的目的,同人小说如果仅仅是借用了原作中的人物名称,并不会对原作的市场产生替代,没有激励创新的损害,著作权侵权很难成立,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四、结语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仅有百年的历史,相较于历史渊源深厚的民法、刑法等,无论是制度的正当性基础还是价值追求都还在不断探索的道路上[5],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在我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提高国家竞争力的时代背景下,我们首先应当承认知识产权保护对于创新的激励作用,但是一味地加大保护力度会造成知识产权权利扩张的趋势,反过来会阻碍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创新。因此,担负激励创新任务的知识产权制度,应当牢记使命,时刻关注是否存在创新激励的损害,方能发挥制度的最优效果,实现利益平衡。
注释:
①有关知识产权制度正当性的讨论,参见冯晓青:《利益平衡理论为基础的知识产权制度》,载《江苏社会科学》,2004 年第1 期;胡梦云:《知识产权制的正义性思考——读冯晓青教授《知识产权法哲学有感》,载《电子知识产权》2004 年第1期;曹新明:《知识产权法哲学理论反思——以重构知识产权制度为视角》,载《电子知识产权》,2005 年第2 期;冯晓青:《公共领域视野下知识产权制度之正当性》,载《现代法学》,2019 年第5 期。
②相关案例:太阳信托银行诉米夫林出版公司案: See Suntrust Bank v. Houghton Miffl in Co. ( Suntrust I ),136 F. Supp. 2d 1357, 1383-86 ;圣杯与圣血 与达芬奇密码案:Baigent v. Random House Group Ltd, [2006]EWHC (Ch) 719 No. HC04C03092 (U.K.)
③See Warner Bros. Entm’t, Inc. v. RDR Books, 575 F. Supp. 2d 513,549-50,554.
④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等与梦工场动画影片公司商标异议行政复审纠纷,详见(2017)京行终3859 号行政判决书。
⑤相似的案例,金华大头儿子服饰有限公司与国家知识产权局行政纠纷:(2019)京73 行初1705 号行政判决书。
⑥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1 条:为保护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作者的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有关的权益,鼓励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和科学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根据宪法制定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