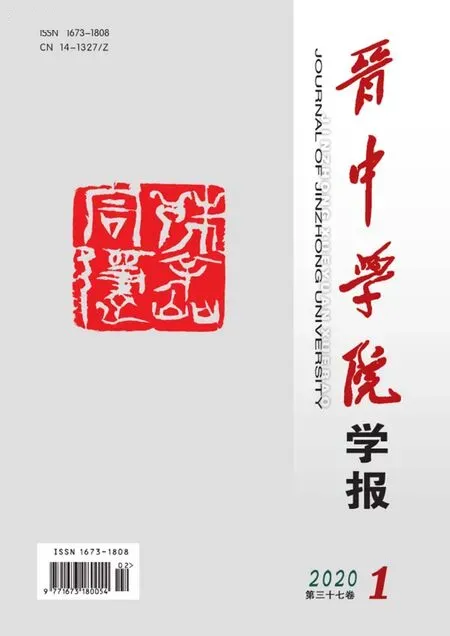以“戎”为“融”
——从京剧裘派的坚守与创新看戏曲的传承与发展
孔美艳,孙 雨
(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临汾041000)
每一种艺术的形成都会经历较长时间的打磨与沉淀,作为国粹的京剧,自徽班进京迄今已有300余年的历史,其间融合了多种姊妹艺术的精华,可谓是一门“海纳百川”的艺术形式。在快节奏、娱乐多元化的当代,传统戏曲发展受到严重冲击是不争的事实,京剧艺术同样难逃此命运。而今,京剧艺术甚至是戏曲艺术又该如何发展?或许,京剧“裘派”艺术的发展历程可以给京剧乃至其他传统戏曲艺术在当代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裘盛戎的艺术融合与裘继戎的“融合艺术”
京剧裘派艺术起于裘盛戎先生,至其孙裘继戎共历三代,其艺术成就可归功于“融”字。谈及裘盛戎先生,要提及其父裘桂仙。裘桂仙本净行演员,因倒嗓问题无奈转向幕后,曾先后为金少山等人弹琴,这为裘家以后探索京剧净行艺术提供了可能。
裘盛戎先生自幼随其父学习京剧,14岁进入富连成科班,凡是净行应工无所不学,自此他全面掌握了净行知识,为此后“裘派”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科后,他曾与杨小楼、尚小云、谭富英、高盛麟等多位大家合作。裘派艺术的形成是博采众家之长的过程,裘盛戎先生在唱腔方面,先后受到京剧净行金少山、郝寿臣、侯喜瑞及京剧老生谭富英、马连良的影响,其唱腔韵味悠长,“裘派”一时成为潮流;[1]在做工方面,裘盛戎先生不顾京派与海派的对立,毅然向“麒派”大师周信芳学习,在净角表演中加入表现人物情感的细腻情节,从而完成角色内心与外形的和谐统一,自此打破了铜锤花脸与架子花脸的界限,形成特有的艺术流派——裘派。[2]裘盛戎先生也曾因嗓音、身高等问题几乎断送自己的艺术生命,但他注重艺术的创新性,扬长避短,如在他的嗓音因倒嗓而变得苍老低沉时,他却能因地制宜地创造出一种不同于高亢与浑厚的、以鼻音为特色的韵味唱腔。[3]与此同时,他学习侯喜瑞、程砚秋的舞台处理手段,通过勾脸方式、服装道具及舞台走位来弥补自身身高的不足,将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条件,以此突出人物形象,成就了融合创新的裘派表演艺术。其代表作有《姚期》《包龙图》等。
其子裘少戎,无论是扮相、嗓音还是做派都酷似其父,受到国内外的一致好评。但其身患肺癌,享年仅39岁,故其对裘派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并无更突出的贡献,但他坚持带病参加中国京剧音配像的工作,为京剧裘派艺术的传承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其孙裘继戎,作为京剧裘派的嫡系传人,自幼颇具裘盛戎的风范。裘继戎自9岁便随其父学习花脸唱段,后进入北京戏曲职业艺术学院学习,在13岁时获得“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金奖”,可谓“英雄出少年”。对于戏曲演员来说,倒嗓意味着重生,而裘继戎作为“老天爷赏饭吃”的天赋型演员,倒嗓后的他声音越发透亮而浑厚。但是,年少的裘继戎却因叛逆而将更多的时间投身在现代舞中,从而走向另外一条道路。裘继戎迫于家族的压力与对自身要求的反思,于2013年推出京剧街舞音乐剧《融》。之后,开始尝试跨界做艺术融合,将自己喜爱的现代舞蹈与传统京剧融合在一起,辅之现代音乐、太极等其他因素,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京剧的韵味美。2015年,裘继戎加盟杨丽萍导演的舞剧《十面埋伏》,在剧中担任男主角萧何,油彩脸谱作为京剧因素贯穿其中。2016年,裘继戎参加中央电视台《叮咯咙咚呛第二季》的录制,在节目中他与戴荃合作《悟空》一曲,他仿佛就是悟空本尊,孤独但坚毅地走在一条不被认可的道路上。2017年,裘继戎参演张艺谋的观念演出《对话·寓言2047》,他在其中主演8分钟的舞蹈篇章,继续践行自己的融合道路。除舞蹈作品外,裘继戎还先后发表《皓月无眠》《遥远的路程》《奈若何》等单曲,其中音乐《皓月无眠》的创作灵感来自《贵妃醉酒》的“海岛冰轮”唱段,此曲亦是以新的方式表达对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尊重与敬畏。由此,裘继戎一步步走进人们的视野,并引发关注。
二、裘盛戎与裘继戎的坚守与创新
裘盛戎先生曾说,“艺术不会永远站着不动,他总像后浪催动前浪那样一个儿劲往前赶;但后人的改革与创新都应该首先吸取前辈留下来的成果,而不是依靠自己的一点小聪明而凭空臆造。”[4]所谓有继承才会让人感到熟悉,有发展才会让人感到新鲜,这也许就是“裘派”兴盛的真正原因。
在裘盛戎的时代,与自己构成竞争关系的是其他流派的艺术表演体系,而裘派艺术的形成与发展是基于其他流派艺术成就之上的采纳与融合,故更具有综合性与全面性。对于裘盛戎来说,他坚守的是老腔老调,是传统京剧的精华荟萃,是讲求唱念做打的基本功,是上百年来梨园弟子坚守的信念。
在京剧派别百家争鸣的背景下,裘盛戎毅然选择创新,不仅是基于对自身条件的磨合,更是对众多老腔老调的继承与发展。以“戎”为“融”的艺术追求要求裘盛戎先生能够结合多位大家的表演方法,博采众长,钻研适合自己的、满足大众要求的声腔系统。另外,他忽略了行当之间的差距,将主唱工的铜锤花脸与主做工的架子花脸进行融合,形成全新的、裘派特有的戏曲行当。
在裘继戎的时代,京剧裘派艺术已成定式,“十净九裘”已成格局,社会的快节奏已然影响了京剧艺术的发展与传播。而裘继戎的难处与困境在于,当今社会的观众群体不再关注京剧表演,讲究“情绪”“韵味”的京腔开始淡出大众视野。裘继戎认为,未来是属于青少年的,故京剧的传播应从青少年入手,有效传播是京剧艺术的当务之急。因此,他选择从自身素质和兴趣着手,探寻新的途径来“反哺”戏曲。裘继戎于2016年签约少城时代公司,之后在综艺节目中总以油彩脸谱视人,以此向观众宣传京剧文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裘继戎坚守的是京剧裘派的韵味,是以情入境的情绪,是京剧艺术的“神”。而他的创新表现在京剧与其他艺术形式的融合,即“形”,他以戏曲神韵为核心,融合吟唱、电子音乐、太极身段、街舞、现代舞等多元艺术风格,以情合境,以求探寻以“戎”为“融”的当代表达。
裘继戎认为,京剧艺术是“脑死亡的艺术”,而京剧的传承不应只是代表唱段的复制粘贴,而是京剧韵味的传达。所以,裘继戎力主分解京剧,提取京剧要素与其他艺术形式进行排列组合,从而形成新的艺术面貌。例如舞蹈作品《悟空》,裘继戎在其中担任舞者,借助戏曲要素翎毛,辅之太极、现代舞的代表性动作表现悟空的内心世界,流畅舒展的舞蹈令观众陶醉其中。但其全程无唱腔的表演形式也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如赵忠祥老师发问,“京腔韵味的表达是否算得上京剧艺术的传承?”再如音乐作品《皓月无眠》,裘继戎从“海岛冰轮”唱段中获得灵感,该音乐不同于京剧声腔,却又同京腔儿一般传递着感情,这样的艺术呈现是否是京剧艺术的传承?那么,京剧的传承应该是怎样的过程,当代的我们又该做出怎样的努力?
裘盛戎与裘继戎爷孙看似不同的做法,实则皆是为戏曲的传承做出的坚守与创新。裘盛戎的创新是从京剧艺术本身着手,通过自身与京剧艺术的磨合创造一种新的艺术流派;而裘继戎的创新是从艺术的表现形式着手,通过其他艺术与京剧艺术的融合,创造出一种新的艺术表演形式——融合艺术,以此博得大众的关注,从而赢得对京剧艺术的“反哺”效应。
我们认为,京剧艺术坚守与创新的道路应以坚守为主体,诚如裘盛戎先生所说,“后人的改革与创新都应该首先吸取前辈留下来的成果”,故坚守为第一位。只有真正地了解京剧艺术,才有资格谈及京剧艺术的创新。就裘继戎的创新来说,笔者认为他的做法大胆新颖,在短时间内赢得大批年轻观众的关注,有一定的合理性和价值所在,值得肯定。然而,长远来看,裘继戎的传承过程还应进行一定的战略性调整。即,裘继戎在已赢得大批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的注意之后,理应尽早回归京剧、反哺京剧。反之,确有可能误导大众对于京剧的认识,从而加速京剧的消亡。众所周知:何为戏曲?“以歌舞演故事也”。所以只有歌曲,或只有舞蹈的戏曲呈现,确实是戏曲艺术的倒退。
三、“方氏裘韵”的传承与裘继戎式的传播
正如裘继戎所说,京剧的危机在于缺少青少年的关注,故有效传播为当务之急。何为有效传播?在笔者看来,有效传播即传承与传播的集合体。传承,即尽量保持京剧的本来面貌。传播,指通过一定的措施与手段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并喜爱京剧艺术。事实上,京剧裘派艺术的传承还依赖于裘派其他弟子的努力,这方面,方荣翔先生的成就最为突出。方荣翔6岁开始练功,8岁入荣春社科班学习,10岁师从骆连翔习文武花脸,12岁登台演出。方荣翔于16岁时拜裘盛戎为师,专攻裘派花脸,成为裘氏的“手把徒弟”[5]。裘盛戎的表演艺术全面而精湛,方荣翔承其衣钵,结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将京剧裘派艺术的风格向媚婉方面拓展,他的唱腔遒媚舒畅,空灵剔透,被誉为“方氏裘韵”。方荣翔对裘派艺术的发展“传多于创”,其创新主要体现在唱腔上。由于师徒二者身体素质不同,二者发音部位亦不同,裘盛戎的发音浓郁,头腔、鼻腔、胸腔三腔共鸣,而方荣翔的发音位置更靠前,基本集中在鼻腔与面部;二者的发音方式亦有差异,裘盛戎多用炸音传达情感,而方荣翔却几乎完全避讳炸音,只在字眼上加强力度;二者的叙事节奏亦不相同,裘盛戎的节奏紧凑,张弛有度,而方荣翔节奏平稳,自然流畅。从舞台呈现来看,虽然二者的整体风格极为相似,但方荣翔更为纯净通透。总之,方荣翔在不违背京剧裘派艺术风格的前提下,以自身条件为依托,充分发挥自身能动性,以此发展京剧裘派艺术。其代表作有《姚期》《赤桑镇》等。至今,方荣翔的嫡孙方旭仍工花脸、宗裘派,长安大戏院曾举办“方氏裘韵·旭日龙图”专场演出,一连三天,为观众献上三出经典的“包公戏”——《铡美案》《包龙图》及《铡判官》。[6]“方氏裘韵”由方荣翔始创,方旭承之,皆是对京剧裘派艺术的传承。
京剧裘派艺术的传播倚仗于明星效应的带动,而裘继戎在娱乐圈中所发挥的“反哺”效应亦值得关注。裘继戎曾说,“观众之所以认识我,是因为舞蹈而不是京剧”,由此可见,裘继戎想要通过融合艺术来“反哺”京剧的想法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想要实现“反哺”效应的具体做法还有待商榷。裘继戎对于京剧裘派艺术的传承“创多于传”,他将戏曲艺术看作整体对其进行模件化解构,从中抽取“韵味”“勾脸”等艺术要素,与其他艺术相结合,从而形成新的艺术表达,这种做法具有一定的争议性。通过碎片化的方式来吸引观众,这无疑是在饮鸩止渴,这样的艺术形式虽会在短时间内引起较大轰动,但其对于京剧的反噬不可忽视。况且,该做法“反哺”的最大受益者是裘继戎本人而非京剧裘派艺术。相反,京剧裘派艺术会因模件化解构而变得面目全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误导大众对于“京剧”的定义。有人会问,“裘继戎是不是毁了京剧裘派艺术?”答案是否定的。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传承的定义亦是如此。裘继戎对京剧的传承以创新为主,他的艺术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他对京剧的贡献也是不可忽视的。就笔者而言,对于京剧裘派艺术的认知亦于裘继戎之后。虽然裘继戎的创新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作为传统艺术的传承者,切勿走得太远而忘记启程时的初衷,希望裘继戎在今后的创作中,能做到以京剧为主体、其他艺术形式辅之的创作模式,只有分清主体与客体,其“反哺”效果才会显著,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目前看来,京剧裘派艺术传承与传播的过程有分而处之之嫌。但事实上,该过程应相辅相成、合二为一。这方面,京剧余派女老生——王佩瑜的做法值得借鉴。王佩瑜,人称“不听京剧的人,最喜欢的京剧演员”。她曾说,“京剧来到了传承与传播同样重要的时代”,而她亦走在道路前沿,通过个人魅力感染更多的青少年感知京剧的魅力。人称“瑜老板”的她,亦有“小孟小冬”之誉,她将京剧的传承与传播视为己任,既不破坏京剧的完整性,亦不随波逐流地过度娱乐化京剧,这一做法值得大众的尊重与肯定。她曾说,“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听京剧的人,另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听京剧的人”。我十分认同瑜老板的此观点,现在的年轻人往往在没有了解京剧的情况下便对京剧妄下断言,此皆源于对传统文化的古老、刻板的印象。而瑜老板选择在此时走进大众视野,为的就是向更多的人普及京剧知识,传达京剧精神。王佩瑜走在娱乐化的道路上,却能做到始终保持京剧的传统性,懂得平衡坚守与创新的关系,是值得我们尊重的艺术大家。
“路漫漫其修远兮”,在新的历史时代下,以裘继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仍需上下求索,为京剧乃至戏曲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做出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