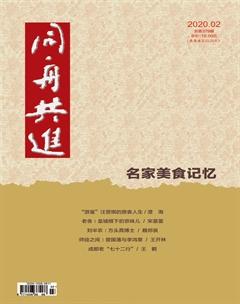江平先生印象
刘仁文
一
我虽然在1980年代读大学期间就听过江先生的讲座,但真正和他认识还是在1990年上研究生之后。研究生期间我曾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的研究生会主席,多次为研究生会的工作去他家里。他那时就住在校门外一个普通小区里,经常骑自行车在校园里经过。记得第一次去江先生家,他正在看足球,这多少有点让我失望,因为我是一个足球盲,而且当时他在学生眼中就是正义的化身,像他这样的人物应当日理万机才对呀,怎么会这么悠闲呢?后来我才知道,改革开放后先生确实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足球和音乐的热爱。其时,他不仅校内工作忙,社会活动也特别多,有时下课后在校外的面馆匆匆吃过就出差去了。
江先生有一个天生患有智障病的女儿。这也是法学界许多牵挂他的人总是小心翼翼避开的话题。他一直对这个孩子怀有内疚感。多年后,他的自传《沉浮与枯荣》面世,一时洛阳纸贵,在书里,身着古装戏服的江先生和师母、女儿的合影被放在扉页的显著位置,这时我已完全能读懂先生的慈父面孔了。以往还是学生时,每次去先生家,当他的女儿过来“干扰”我们谈工作时,我心里总想,先生为何不把她支走呢?
1993年我研究生快毕业时,有一天在校园里见到骑车的江先生,他主动下车问我的去向,我告诉他自己联系了中央政法委,他马上说,他和时任中政委秘书长熟悉,他愿意帮我写封推荐信。后来一切进展顺利,快要报到时,却因中政委当时暂时无法提供宿舍而作罢。后来我就到了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工作,没想到,这一去,就从此扎下根来。江先生的热心是出了名的,这些年来,他推荐过多少学生出国留学、推荐过多少学者出国做访问学者,又给多少人题过词、作过序、写过推荐语,恐怕他自己也未必记得清楚。
1998年我们同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较多,我和先生还一起参加过哈佛大学、纽约大学等校的学术活动。先生经常去中国城买鱼做饭吃(师母过一段时间才到),有时则跟我们去哥大附近一家中餐馆吃便宜的自助餐,还跟大家请教要不要自己放回盘子,外国人戴戒指在哪个手指表示哪种含义等小事。后来他和师母回国时,自己叫出租车去机场,我们几个为他送行,他双手作揖表示感谢。当时国内一个副厅级学者“郁郁寡欢”,跟我抱怨说美方竟不安排人送她,我说这是文化差别,江先生也没有人接送。
在美国期间,我跟江先生多次出游,他给我谈过一些观点,说实话,有的我当时接受不了,没想到后来都慢慢有了同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往一个能俯瞰大海的坡上走,江先生说自己有恐高症,就坐在路边的椅子上等我们。还有一次我们在海边散步,他说到几年前在夏威夷,看到那海水,想到自己来一次也不容易,就取下了假肢,下海游了几圈。
回国后我们时有往来。当时我们所的《环球法律评论》有一个名家访谈栏目,编辑部听说我和江先生熟,还派我去对他做过一次专访。这次访谈又得知了他的许多往事,对我也是一次人生洗礼。全文整理出来后,以“只向真理低头——江平先生访谈录”为题见刊,后来还被《永远的校长》等多本著作收入。
先生的《沉浮与枯荣》一书影响超出法学界,荣登过许多图书排行榜的前列乃至头名。我深感意外和荣幸的是,书中他长篇引用了我的《法学家为什么没有忏悔》一文。翻阅完这本书后,我给先生去了个电话,感慨他在前言中所说的:“我一生中真正能称得上是故友、至交的人几乎没有,这可能与我的人生信条‘君子之交淡如水有关吧……故友和至交逐渐离去,人情淡漠,我也不敢再奢求于故友和至交了。”我说看到这句话时,内心有种苍凉感,谁能想到,大名鼎鼎、前呼后拥的江先生竟几乎没有故友与至交?电话那边,没有声音,直到我岔开话题。先生是演讲家,但与他有过近交的人应当也能感受到,他私下里话并不多,除非你主动提到某个话题或问他某人某事,否则有时甚至会出现较为尴尬的沉默。
二
2018年,社科院法学所老所长王家福先生荣获改革开放先锋称号,江先生应邀参加座谈会,并祝贺家福老师。我身旁一个名校法学院的院长对我说,很多人认为,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深度参与立法和司法、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江先生也应当获得这一荣誉,难能可贵的是,江先生对此毫不介意,光凭这一点就值得敬佩。前不久,家福老师离世,遗体告别那天,江先生早早赶到八宝山。我当时排在长长的队伍后面,同事说,王师母看到江先生时十分激动,从轮椅上站起来抱着先生痛哭道:“您怎么也来了呀?您是兄,他是弟,您可以不来的。”
几天后,我在一个与江先生同桌的餐叙中提及此事,先生说起当年自己在延庆期间,家福老师先后数次去邀请他来社科院法学所工作,并帮他办理有关调动手续,就在办得差不多时,传来中国政法大学复校的消息,于是重回法大。江先生说,那时从城里去趟延庆可麻烦了,所以他特别感谢家福老师。这是我第三次听他讲起这段往事了,他虽然轻易不议论人的长短,但这次却主动问起家福老师到底因何病去世、某某为何没来参加遗体告别式等,使我深感这对上世纪50年代的留苏同学由于治学理念相通,在坎坷漫长的岁月中所建立起来的弥足珍贵的深厚友谊。
江先生在许多人眼中已是一个近乎传奇的人物。我曾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有崇拜他的年轻人在前往西藏求圣的途中,于青海高原路边的石头上刻上江先生的名言:“只向真理低头”,并表示完成了此生的一个心愿。然而在我眼中,江先生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巴金在《随想录》的代序中说: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以我对江先生的了解,他骨子里应当是不希望别人把他看成神的,所以他也从不伪装自己。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他“已经没什么可迷信的了,剩下的就是:只向真理低头”。然而到底什么叫真理?我曾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答案似乎并不明朗。
许多人感慨先生随和,没架子,对他的不卑不亢和宠辱不惊充满敬意。在回顾人生时,江先生并不把自己看作英雄,他说他也有沉默的时候,好在从未昧着良心说过假话。他从不主动提起自己的辉煌经历或头衔,相反,对一些在别人看来似乎有碍他高大形象的事,他却从不隐瞒、不回避。他曾在怀念谢怀栻先生的文章中表达出对谢老一流专业功底的景仰,“我也想到我自己,缺少像谢老那样过硬的基本功”。他和谢老一起担任仲裁员时,虚心得像个学生,“我在旁细心观察他的态度,他的风格,他的问语,他的处理意见,似乎能想象到这位经过严格司法考试、司法训练培养出来的法官当年断案时的风采,甚至我在默默地祷愿,如果我们的仲裁员和法官都能有这么高的水平,那就是国家的万幸”。看到谢老字斟句酌、反复修改仲裁裁决书,他自责道:“他那认真的态度,使我感到惭愧。”我曾问他,“呼格吉勒图的墓志铭写得真好,那是您自己写的么?”我多么希望他回答“是”,但他却说,“是我的学生王涌帮我草拟的”。先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后来不幸夫妻离散,现在的师母是他后来找的。在迎来人生高峰后,无论何时何地,他都大方地介绍師母:这是我老伴。在《沉浮与枯荣》里,他还专门说过,改革开放后自己之所以能在事业上有所收获,要多亏老伴和崔家人的支持(师母姓崔)。
先生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有一次,他所欣赏的学生张星水律师要我约江先生聚一下,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女儿在家没人照顾,后来我说,那要是让星水安排在他家楼下呢。他一听就动了心,开始犹豫起来。但最后还是说:你们聚吧,我出去还是不放心。几年前,他每到快过年,就因保姆要回家而犯愁,有段时间甚至与家人住进了养老院,他说养老院条件再好,也没有家的感觉。现在,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保姆,也不用为过年到哪去而犯愁了,谈起此事,先生喜形于色。
对人生有过深刻体验后,江先生把世间名利看得很淡,为人很真诚。他的教授、博導头衔在同龄人中解决得不算太早。当然,后来他当上校长和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也在意料之外。他曾说,改革开放后的20年,他该得到的得到了,不该得到的也得到了,自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没读过几本像样的法学名著,更没写出像样的法学专著。但他是一个法学教育家,培养出一批学生;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立法和司法……
三
江先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从不记恨人,也不纠结于过去。他在自己70岁时,就想如能活到80岁已经是幸运了;80岁时,心想如能活到90岁就更是幸运了。如今90岁已悄然而至,看先生的心态与形态,我对他的长寿充满乐观。大概十年前,他曾大病一场,自从那次病后,先生遵医嘱不再进行重度科研工作了,但作为终身教授,还带学生,也适度参加学校和社会活动。万幸的是,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迅速恢复,思维还是那么敏锐,对许多问题的见解仍入木三分。如今,他爱吃红烧肉的习惯已经改掉了,换成吃牛羊肉了,胃口很好,我见过他连喝三碗羊肉汤呢。由于腿不好,年纪又大了,所以在家里安装了健身器和按摩椅,每天坚持锻炼和按摩。从昔日那种充满激情的繁忙工作过渡到如今这种尽量减少外出的老年人生活,对于这一变化,他似乎已经习惯甚至享受。
先生把钱看得很淡。他是法学界第一个以个人名字设立基金会的人。在他70岁时,他把自己的积蓄几乎全部拿出来,设立“江平民商法奖学金”,台湾大学的王泽鉴教授等著名学者均捐款支持,可见江先生的人格魅力。如今,“江平民商法奖学金”已成为民商法学界含金量很高的奖项,每年颁奖,先生都会携师母与会,并寄语莘莘学子。与他对公益的追求相比,他的生活却简单而朴素。有一次与他同席,当他得知那晚的套餐人均消费近200元时,他露出惊讶的神色:这么贵啊!
2014年《新京报》出了一期特刊,每个领域约请两位学者对谈,我和江先生受邀成为法学领域的嘉宾。在“互评”环节,先生说:“现在我已接近完成使命,行将退出历史舞台,希望年轻人接过接力棒,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先生这话既是自谦,也是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勉励。当记者问到我俩的幸福指数时,先生的回答是9分,我的回答是8分。他说:“缺的一分,是人生不可能有满分。”事后我想,为何先生的经历跌宕起伏,却反而比我感到幸福呢?
江先生从不以权威自居,跟他交流不会感到压力。有一次我们讨论克里米亚问题,他认为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是对的,说那本来就是苏联送给乌克兰的。我反问他,那您今天送给我的礼物,明天您想要回就可以要回吗?这不符合民法原则吧。他呵呵一笑,就不做声了。
先生确实是一个充满故事的人。前不久见到他,我跟他核实,社会上传说他和屠呦呦是亲戚,可有此事?他说是的,两家现在还有往来,屠呦呦也到他家去过。按先生的说法,两家还是很亲的,江先生和屠呦呦的关系大概相当于表兄妹。江先生祖籍宁波,为何出生在大连呢?就是因为当时屠家在大连,屠呦呦父亲把江先生父亲也介绍到大连工作,于是江先生一家就搬到大连去了。
就在这次的饭桌上,主食久等不上,江先生似乎有点着急。我很少看到先生着急,心想都这么晚了,他又这么大年纪了,难道还有什么重要事情?过了一会,主食还没上,他终于忍不住了,跟大家说抱歉,自己要先走一步。我送他到门外,问他为何急着走,他说想赶回去看一场球赛。
这就是江平,一个可亲、可敬又可爱的人,一个纯净、善良又率真的人,一个严于解剖自己,善于学习,见贤思齐的人,一个“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人。待他百岁时,我期待能有更宁静的心情和更系统的时间来好好写写我眼中的江平先生,再细细品味那些本文没来得及诉说的故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刑法室主任、博导)
——写给我们亲爱的师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