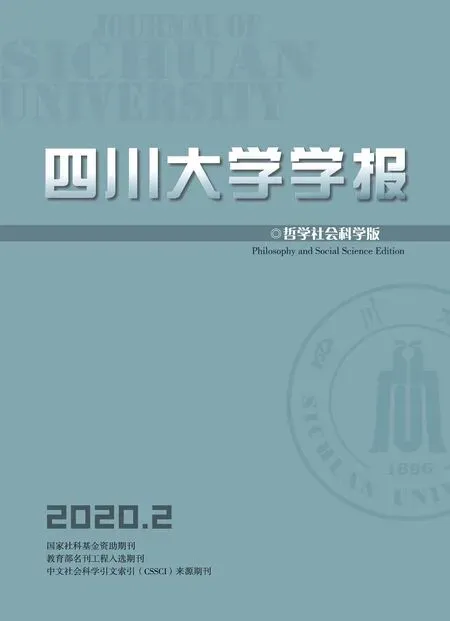游侠、党人与妖贼、隐逸
——汉末数类人群的相通性与汉魏禅代的知识背景
从“汉魏封建”说到“汉魏革命”说,(1)参见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第87-96页;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及其向中世社会的过渡》,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徐冲:《“汉魏革命”再研究:君臣关系与历史书写》,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08年。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由日本学者提出,到今天已广为学界识用的“古代”(“太古”)至“中古”(“中世”)的历史阶段划分,(2)这样的历史分期理论在内藤湖南所撰《支那上古史·绪言》(东京:弘文堂,1944年)中得到了系统论说。相关讨论参见气贺泽保规:《内藤湖南的历史分期论及其现实意义》,《唐史论丛》第23辑,西安:三秦出版社,2016年,第143-160页。还包括学术史上“经学时代”至“玄学时代”的概括,(3)此类概括在一般的学术史、思想史著作中多有所见,比如步近智、张安奇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等。这些基于不同背景、旨趣而提出的重大学术命题,无疑反映了海内外学界在有关汉魏之际历史嬗变及其时代独特性方面的某种共识。维持四百余年之久的统一帝国最后不得不以让渡天命的方式“禅位以贤”、落幕退出,传说中的理想的政治交接模式亦终于由此落实,此中变化之奇、之巨,以致即使悬隔两千年,我们依旧能够透过重重的价值之墙以及出于不同目的的叙事文本,感知、触及彼时历史演进背后剧烈的信仰危机与奔涌的时代热潮。基于这样的总体认识,笔者认为,以迄今尚未得到圆满解释的汉魏政权鼎革方式——汉魏禅代为研究指向,综合考察东汉中后期游侠与隐逸、经师与“妖贼”(术士)、儒生与道士的价值与行为相关性,以及思想与学术、数术与信仰、“正统”知识与“妖妄”知识的交涉与变迁,(4)宫川尚志较早指出了儒生颂经与道士、方士的相通处。参见宮川尚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京都:平乐寺书店,1964年,第80-83页。稍后石泰安(Rolf. A. Stein)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指出廉洁正直的儒者、方士和隐士的行动规律与黄巾、五斗米等道教运动之间存在着共通的基调和基础。参见石泰安:《公元2世纪政治的宗教的道教运动》,朱越利译,任继愈主编:《国际汉学》第8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第371-435页。此后,川胜义雄、吉川忠夫对该问题均有重要发挥,参见川勝義雄:「漢末のレジスタンス運動」,『東洋史研究』(京都)第25卷第4号,1967年,第386-413页;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王启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38页。陈启云、姜生亦曾讨论儒道的相通性及其相同文化背景问题,参见陈启云:《荀悦与中古儒学》,高专诚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45页;姜生:《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530-532页。更详细的学术史梳理参见冯渝杰:《大小传统理论的典范与失范:以汉末政治、宗教运动研究为中心》,《中国中古史研究》第6卷,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307-326页。当可管窥汉魏之际独特的时代性征与深刻的思想变化,以此进一步认识“古代”秩序的崩塌与“中古”要素的发端。
一、侠隐与仕处:汉末数类人群的相似风格与共通价值
东汉中后期,活跃于地方的游侠、经师,党祸后下潜至民间的党人,逐渐有影响、成势力的宗教信徒以及处于权力末端的隐逸、处士,在当时的朝、野舞台上均有引人注目的活动或表现。细绎史籍可以发现,从有关他们的成长、学术、性情、行为等方面的记述中(散见于《儒林》《独行》《隐逸》《五行》等处),能够透见他们在知识构成、行事风格、价值归趋等方面,均有不容忽视的相通处。
(一)游侠传统与党人婞直之风
“婞直之风”(袁宏称为“肆直之风”)乃汉末士人,尤其是“党人”所表现出的一种十分突出的行事方式与性格特点。典型事例如《后汉书·党锢列传》载:“时河内张成善说风角,推占当赦,遂教子杀人。李膺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获免,(李)膺愈怀愤疾,竟案杀之。”此即彻底引爆“党祸”的“风角杀人”事件。同传又载:“时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残无道,至乃杀孕妇,闻膺厉威严,惧罪逃还京师,因匿兄让弟舍,藏于合柱中。膺知其状,率将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阳狱。受辞毕,即杀之。”又载:“宛有富贾张汎者,桓帝美人之外亲,善巧雕镂玩好之物,颇以赂遗中官,以此并得显位,恃其伎巧,用埶纵横。(岑)晊与牧劝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晊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余人,后乃奏闻。”(5)《后汉书》卷67,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187、2194、2212页。另外,天下名士序列中的“八厨”,亦明显体现出刚直不阿、爱憎分明、不惧权势的风范,与游侠仗义疏财之行颇为接近。
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开篇即叙述了从汉初“任侠之风”至汉末“婞直之风”的士风演进过程。关于“婞直之风”的形成,他扼要论之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6)《后汉书》卷67,第2185页。可见在范晔看来,汉末“婞直之风”的形成,一方面受到此前“任侠”风俗的熏习,另一方面亦深受汉末政治局势及社会环境的影响。
当然,有此看法者并非范晔一人,葛洪在《抱朴子外篇·正郭》中亦曾以评判党人领袖郭泰的方式,明言汉末清议之士与党人群体形似隐逸,实乃游侠:
(郭泰)此人有机辩风姿,又巧自抗遇而善用;且好事者为之羽翼,延其声誉于四方。故能挟之见准慕于乱世,而为过听不核实者所推策。及其片言所褒,则重于千金;游涉所经,则贤愚波荡。谓龙凤之集,奇瑞之出也。吐声则余音见法,移足则遗迹见拟。可谓善击建鼓而当揭日月者耳,非真隐也。……无故沉浮于波涛之间,倒屣于埃尘之中,遨集京邑,交关贵游,轮刓弊,匪遑启处?遂使声誉翕熠,秦、胡景附。巷结朱轮之轨,堂列赤绂之客,轺车盈街,载奏连车。诚为游侠之徒,未合逸隐之科也。
又引“故太傅诸葛元逊”(诸葛恪)之语:
林宗隐不修遁,出不益时,实欲扬名养誉而已。街谈巷议以为辩,讪上谤政以为高。时俗贵之歙然,犹郭解、原涉见趋于曩时也。(7)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下,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53-464、472页。
郭解、原涉皆为西汉时期的著名游侠,而《正郭》篇的实际评议对象又是以郭泰为代表的汉末清议与党人群体,可见在去汉不久的诸葛恪、葛洪、范晔等人看来,汉末党人、清议之士与游侠的关系已不仅停留于表面,即党人并非只是表现出明显的游侠特征或与游侠群体存在某种程度的关联,他们之间的价值与风范如此接近,甚至可以说两者的关系已密切至界限模糊、难以分解的程度。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党人、清议之士与游侠群体的关系?牟发松在讨论总结可以称之为“侠儒”的党锢名士群体尚侠气质之渊源后指出:“从党锢事变形成、发展及其消灭的全过程中,可以看到汉末‘婞直’士风及其主体党锢名士与游侠风气的相似性。”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六点:(1)轻死重气、义重于生;(2)外于体制或反体制的舆论、声望;(3)外于体制或反体制的组织、群体;(4)疏财仗义;(5)复仇;(6)广泛交游。(8)牟发松:《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文史哲》2011年第4期,第74页。此可谓周全之论。下面拟就牟氏概括的第2、3、6点内容进一步展开,以此检讨汉末党人、游侠及所谓“妖贼”术士相互交流的一般面相,并说明这样的交流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成为可能。
实际上,牟氏总结的第2、3、6点特征,可统一归结为王朝秩序之外的言论、行为及价值取向。外在于体制的评价标准正是游侠群体最重要的特征,诸多研究者亦曾指出这一点。(9)参见吕思勉:《秦汉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61-462页;劳幹:《论汉代的游侠》,《劳幹学术论文集甲编》,台北:艺文印书馆,1976 年,第1021-1025页;刘修明、乔宗传:《秦汉游侠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71-80页;增渊龙夫:《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和任侠习俗》,孔繁敏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26-545页;彭卫:《古道侠风》,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卜宪群:《秦汉社会势力及其官僚化问题研究之一——以游侠为中心的探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编:《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73-83页。进而言之,游侠的价值与行为实具有在王朝法律之外另立“契约”(如与豪富交易)、重新定义社会价值和规范的属性。应当注意思考的是,游侠所结成的价值-秩序何以为社会所接受?其存在和被接受的基础是什么?虽然游侠经历了数阶段的演变,(10)大致包括尚武、犯禁的战国卿相之侠,以及秦汉之际开始大批出现的闾里布衣之侠。西汉中后期游侠逐渐儒化,至东汉已少有得见。相关讨论可参见增渊龙夫:《汉代民间秩序的构成和任侠习俗》,第526-545页;牟发松:《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文史哲》2011年第4期,第64-85页。亦有不同的类型构成,(11)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提出了“布衣之侠”“乡曲之侠”“匹夫之侠”“闾巷之侠”等概念,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则明确了“王公游侠”的概念。劳幹指出:“标准的侠者是闾里细民,……但最重要的游侠除去职业的游侠以外,似乎并无他种可能。”刘修民、乔宗传认为:“游侠往往分为上下两个阶层。上层的侠成为著名的侠魁,下层的侠就成为江湖流丐、游民无赖之类。”吉书时提出汉代游侠可以分为贵族游侠、布衣游侠(乡曲游侠、闾巷游侠、匹夫游侠)、侠官三种类型。详参卜宪群:《秦汉社会势力及其官僚化问题研究之一——以游侠为中心的探讨》,郑州大学历史学院编:《高敏先生八十华诞纪念文集》,第74页。相关讨论亦可参见彭卫:《中国风俗通史·秦汉卷》,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781页;牟发松:《侠儒论:党锢名士的渊源与流变》,《文史哲》2011年第4期,第64-85页。但就汉代游侠言行的整体情况而言,其较为稳定的特征大体包括:守信义、“已诺必诚”;仗义疏财以至于损己利人;重气节,任情适性,快意恩仇;“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又“羞伐其德”,接近个人英雄主义的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为坚持自己认为的“公”道可以“不轨于正义”(不遵从法规)。
仔细对照分析可以发现,游侠的性格特征、价值坚持不仅与士人的理念相匹(如重信、重气节、坚持“公义”以及“有道”与“无道”之辨等),因而也得到了士人的认可和接受,亦与民间社会中人们默默遵从的价值秩序若合符契(如讲信义、复仇合理、忠孝伦理等),这就是游侠群体之所以能够较长时期存在于汉代社会,并被人们理解、接受的主要原因。(12)不过应该注意,战国时期的游侠与秦汉之际以及西汉、东汉时期的游侠,其兴起、存在的社会原因,当各有不同。相关讨论请见宮崎市定:「漢末風俗」,『宮崎市定全集』第七卷,东京:岩波书店,1992年,第133-166页。这种潜沉于社会的共同价值既是汉末清议、党人群体与游侠群体的共同思想渊源,也是二者言行、价值如此接近而界线如此模糊的原因所在。据此,劳幹认为汉代游侠与黄老道家有“部分渊源”,二者在思想上兼容、相通,“彼此常常结合”,乃因二者“同属于社会较低阶级”,“游侠是汉代的民间行为而黄老是民间的信仰”,游侠之“任情适性”,“只有在道家之中可以适合”的观点,(13)参见劳幹:《论汉代的游侠》,《劳幹学术论文集甲编》,第1021-1025页;劳幹:《汉代的豪强及其政治上的关系》,《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83-304页。牟发松前揭文以为其论“颇难自圆其说”。尽管不无漏误(如简单认为黄老、游侠属于较低阶级),(14)史籍及汉碑记载显示黄老之学被汉代人广泛接受,其往往与图谶、京氏易等兼容,非仅术士用之,朝臣、帝王信从者亦不在少数。详参冯渝杰:《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文史哲》2017年第2期,第141-154页。但仍不乏洞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游侠价值亦植根于深厚的民间传统,并与黄老信仰土壤上的“妖贼”术士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游侠、党人、术士的思想与活动关联
在上引“风角杀人”事件中,河内术士张成推占风角,教子杀人而为李膺所案杀,刘昭瑞由此事引申论之:“想李膺对张成一类人早已视之为社会的反对力量而随时伺机予以镇压,看来早期道教的兴起与党锢之祸的形成是有一定关系的。黄巾事起,东汉王朝在政治上的主要应对措施就是废除党锢政策,似亦可看出二者应有一定的关系。”(15)刘昭瑞:《“老鬼”与南北朝时期老子的神化》,《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177页。认为汉末道教的兴起与党锢之祸之间存有一定联系,诚堪卓见,但以道教为党人对立面的看法却疏于表面、有失偏颇。(16)实际上,士人的清议运动与道教的宗教活动之间呈现出相互支援、前后而起的态势,由此连接为统一的汉末“抵抗运动”。详参川勝義雄:「漢末のレジスタンス運動」,第386-413页。翻检史书可知,党人与术士“接引”的事例不在少数,最典型的事例即陈蕃子陈逸与术士平原襄楷谋废灵帝之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
冀州刺史王芬、南阳许攸、沛国周旌等连结豪杰,谋废灵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败。
裴松之注引司马彪《九州春秋》曰:
于是陈蕃子逸与术士平原襄楷会于芬坐,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真族灭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愿驱除。”于是与攸等结谋。灵帝欲北巡河间旧宅,芬等谋因此作难,上书言黑山贼攻劫郡县,求得起兵。会北方有赤气,东西竟天,太史上言“当有阴谋,不宜北行”,帝乃止。敕芬罢兵,俄而征之。芬惧,自杀。《魏书》载太祖拒芬辞曰:“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17)《三国志》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5页。
另外,素有道术且极有可能与张道陵有关系的宦者栾巴,(18)详细讨论参见柳存仁:《汉张天师是不是历史人物?》,《道教史探源》,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9-136页。亦当与党人牵涉匪浅。《后汉书·栾巴传》载:“灵帝即位,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辅政,征拜议郎。蕃、武被诛,巴以其党,复谪为永昌太守。以功自劾,辞病不行,上书极谏,理陈、窦之冤。帝怒,下诏切责,收付廷尉。巴自杀。”(19)《后汉书》卷57,第1842页。
史料显示,“术士”(或方士)在汉代活跃范围广阔:他们不仅广泛活跃于平民之间,亦与公卿、将军、诸侯甚至皇帝多有接触。(20)陈槃:《战国秦汉间方士考论》,《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79-254页。“风角杀人”事件中,术士张成曾“以方伎交通宦官,(桓)帝亦颇谇其占”,而其弟子牢修亦曾借机上书告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由此引发了第一次党祸。可见张成攀附权势,当即“浊流”的一员,而“善说风角”的方技或不过是其巴结权势的工具罢了。不过也应注意张成的做法或许恰好反映了人们对方技的“迷信”,乃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情形,否则又何须借助该工具。在“迷信”方术的整体社会氛围中(如上引史料中陈逸、王芬、太史以及曹操皆莫能外),党人也并不例外,所以同样需要借助或利用术士的“占(天)命之技”,寻求或“制造”起事的“天命”依据。如李固在呈递顺帝的对策中言及:“《京房易传》曰:‘君将无道,害将及人,去之深山以全身,厥妖狼食人。’陛下觉寤,比求隐滞,故狼灾息。”(21)《后汉书》卷103,第3285-3286页。以著名阴阳数术家京房的灾异论为其重要的劝谏根据,适可印证数术、方技为不同阶层、不同立场人群所用的情形。
进一步考察则可发现,不仅党人与游侠、术士存在内在关联,两汉时期术士(道士)与游侠之间同样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22)增渊龙夫曾专门讨论两汉时期的巫(与术士颇有近者)与侠之关系。参见增淵龍夫:「漢代における巫と侠」,『新版 中國古代の社會と國家』,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第119-140页。这从南北朝佛道论争时佛教对道教早期历史的攻讦,以及道教内部出于自我“清整”之需而对其早期历史的公开批判中,即可看出。如释玄光《辨惑论》指责道教犯有“五逆”,其四便为“侠道作乱”。(23)一作“挟道作乱”,见《弘明集》卷8,《中华大藏经》第6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823页。为了与之区别并予对立,佛教则立诫“不得卖弓刀军器”,“一切凶器仗皆不得受”。(24)《佛说目连问戒律中五百轻重事经》卷1,《中华大藏经》第41册,第905、911页。相关讨论参见冯渝杰:《道教法剑信仰衰落原因考》,《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47-53页;冯渝杰:《神物的终结:法剑信仰兴衰变异的历史考察》,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02-203页。刘勰《灭惑论》则更直白地揭底、批判道教:“避灾苦病,民之恒患;故斩缚魑魅,以快愚情。凭威恃武,俗之旧风;故吏兵钩骑,以动浅心”,“是以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余波所被,寔(实)藩有徒。”(25)《中华大藏经》第62册,第827页。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也毫不避讳地提及早期道教的“逆乱”之行,且表示出强烈不满:
曩者有张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或称千岁,假托小术,坐在立亡,变形易貌,诳眩黎庶,纠合群愚,进不以延年益寿为务,退不以消灾治病为业,遂以招集奸党,称合逆乱,不纯自伏其辜,或至残灭良人,或欺诱百姓,以规财利,钱帛山积,富踰王公,纵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弦成列,刺客死士,为其致用,威倾邦君,势凌有司,亡命逋逃,因为窟薮。(26)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卷9,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73页。
可以说,正是在此压力下,道教开启了内部的“清整”步伐。(27)相关讨论参见葛兆光:《从张道陵“军将吏兵之法”说起:道教教团从二十四治到洞天福地》,《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12-28页;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41-374页。大略成书于3世纪的道书(28)Kristofer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130.《太上老君经律》之《老君说一八十戒》第17戒“不得妄与兵贼为亲第”,第62戒“不得带刀仗,若在军中不从此律”,第115戒“不得与兵人为侣第”等戒律条文;(29)《道藏》第1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19-220页。以及六朝道经《太上洞玄灵宝三元品戒功德轻重经》之《三元品戒目录》中,“不忠于上”“私蓄刀仗兵器”“合聚群众”“轻凌长官有司”等罪目,(30)《道藏》第6册,第880-882页。相关讨论参见冯渝杰:《道教法剑信仰衰落原因考》,《宗教学研究》2014年第1期,第47-53页。都可以看到道教清除“叛乱者”“遗毒”,拒绝与游侠、刺客等群体再度发生关联的努力。
综合以上讨论,党人、“妖贼”术士与游侠之士皆有一定的交接、联系,并呈现出或抵抗或反对政府之秩序与权威的属性。他们的连接,实缘于同样的民间(社会)基础以及某种程度的内在价值契合。如此,当“党锢之祸”发生后,在朝的士人下潜至民间之时,社会上才具有足够接纳他们的条件或基础。此即汉末隐逸群体得以生长的沃土。
(三)“党祸”后士人下移与汉末隐逸之风
两次“党祸”无疑使士人群体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第一次“党祸”,所染逮者,“皆天下名贤”,范晔所谓“党事起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第二次“党祸”,“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由此,“党锢之祸”中贤士大夫几乎被一网打尽,“凶竖得志,士大夫皆丧其气矣”。(31)以上分别见《后汉书》,第2189、330-331、2244页。司马光亦称:“党人生昏乱之世,……臧否人物,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跷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不亦悲乎!”(32)《资治通鉴》卷56,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823页。足见“党祸”牵连之众,对士人群体影响之巨。
这样的情形下,士人群体“激浊扬清”“澄清天下”的理想和志气受到严重挫伤,于是转而对“汉家”之昏聩、崩离,表现出近乎绝望的心态,更在行动上开启践行孔子“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劝诫。如党人领袖郭泰的同郡宋冲劝郭泰为官,郭泰断然拒绝道:“吾夜观乾象,昼察人事,天之所废,不可支也。方今卦在明夷,爻直勿用之象,潜居利贞之秋也。犹恐沧海横流,吾其鱼也。吾将岩栖归神,咀嚼元气,以修伯阳、彭祖之术,为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者。”(33)《后汉纪》卷23,《两汉纪》(下),张烈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453页。表明其已明确萌生退意。另一党人延笃看到衰世已至,亦不无感慨地说:“夫道之将废,所谓命也。”更有可论者,“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34)《后汉书》卷64,第2106页;卷79,第2589页。可知,在两次“党祸”后,士人群体对当时朝政走向与汉家天命兴废的整体判断,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精神状态、思想、心态等,的确发生了重要转折。显然,他们认可天命,并在这样的前提下对自身的仕、处做出安排,退隐即是其观天象、察人事的结果。
价值判断必定内在制约人们的行为趋向。汉末,基于历数、神学信仰的悲观情绪及其所抱持的近乎绝望的出世心态,在朝的士人群体逐渐下潜至民间,同时在野的多数士人亦选择隐逸于乡邑社会中,拒绝出仕。如党人张俭,“中平元年,党事解,乃还乡里。大将军、三公并辟,又举敦朴,公车特征,起家拜少府,皆不就”。(35)《后汉书》卷67,第2211页。如何夔,“汉末阉宦用事,夔从父衡为尚书,有直言,由是在党中,诸父兄皆禁锢。夔叹曰:‘天地闭,贤人隐。’故不应宰司之命”。(36)《三国志》卷12注引《魏书》,第379页。如夏馥,“诸府交辟,天子玄纁征,皆不就。尝奔丧经洛阳,历太学门。诸生曰:‘此太学门也。’馥曰:‘东野生希游帝王之庭。’径去不复顾。公卿闻而追之,不得而见也”。(37)《后汉纪》卷22,《两汉纪》下,第431页。如黄宪,“太守王龚在郡,礼进贤达,多所降致,卒不能屈宪。……宪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而还,竟无所就。年四十八终,天下号曰‘征君’”。如申屠蟠,对大将军何进的连续征辟皆“不诣”,“中平五年,复与(荀)爽、(郑)玄及颍川韩融、陈纪等十四人并博士征,不至”;中平六年,“蟠及爽、融、纪等复俱公车征,唯蟠不到。众人咸劝之,蟠笑而不应。……唯蟠处乱末,终全高志”。如襄楷,于“中平中,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不至,卒于家”。如名士徐穉之子徐胤,亦“隐居不仕”,“太守华歆礼请相见,固病不诣”。如陈寔,“及党禁始解,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谢使者曰:‘寔久绝人事,饰巾待终而已。’时三公每缺,议者归之,累见征命,遂不起,闭门悬车,栖迟养老”。(38)以上分别参见《后汉书》,第1744-1745、1754、1085、1748、2067页。此外,选择隐逸的党人还包括肱博、钟瑾、李昙、韦著、许嘉、周勰等。(39)金根发:《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4本下册,1963年,第544-546页。尽管这个数字远逊于当时的士人总数,(40)有关研究可参见祝总斌:《〈后汉书·党锢传〉太学生“三万余人”质疑》,《中华文史论丛》2010年第1期,第313-320页;祝总斌:《东汉士人人数考略》,《北大史学》第19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2-347页。但在明确载录姓名、事迹的党人总数中,这样规模的由朝而隐或隐而不朝者,亦着实壮观。
应当注意的是,汉末士人群体下移后,并未真正安于“隐”,而是身隐心不隐。笔者曾指出:“东汉的隐逸群体并非全然的社会受动者,他们以其特有的方式主动参与到汉末的社会运动中,与其他社会群体前后相继,共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抵抗运动’,并对汉末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学术与信仰的跨接者,汉末隐逸群体不仅拥有亦儒亦道的知识构成,并因之成为疏通不同知识的‘中转站’,而且凭借其远离政治的政治象征意义,发展成为朝野之间的中间知识阶层,他们以教授、卜筮、卖药等多种价值输出的方式广泛活跃于民间,在汉末地方伦理-价值秩序之坍塌与重建方面,发挥了潜在却不容忽视的作用。”(41)参见冯渝杰:《朝野之间:两汉的隐逸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8月17日,历史版;冯渝杰:《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文史哲》2017年第2期,第141-154页。川胜义雄亦曾尝试揭示隐逸在汉末的政治参与及其与党锢、黄巾的内在关联。他认为,拉开汉末统一抵抗运动序幕的是清流党人,但是党锢事件让知识阶层的抵抗战线遭受沉重打击,知识阶层的思潮于是朝“隐逸君子”方向倾斜,整个抵抗运动的核心随之向左翼集中。此时,左翼即是处于清流势力延长线上的逸民群体,他们正向民众接近,黄巾由此登上历史舞台。(42)川胜义雄:《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徐谷梵、李济沧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7-28、69页。陈启云将党锢事件后士大夫的反应分为:(1)逃往各地,深入民间;(2)发展秘密组织;(3)在学术著作中阐述革命思想等三种情况。(43)陈启云:《关于东汉史的几个问题:清议、党锢与黄巾》,《儒学与汉代历史文化——陈启云文集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2-206页;陈启云:《荀悦与中古儒学》,第3页。这些论点颇具启发意义。结合前此诸论可知,正是由于党人、游侠与“妖贼”(包括黄巾)、隐逸存在或明或暗、或显或隐的内在关联及价值相通性,所以才会出现汉末清议、党祸、黄巾相互支援、此起彼伏的抵抗形势,引发统治者的惶恐、担忧。史载“中常侍吕强言于帝曰:‘党锢久积,若与黄巾合谋,悔之无救。’帝惧,皆赦之”。(44)《后汉书》卷8,第348页。
那么,汉末诸类人群这种超越偶然的重要相似性,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到底是何因素导致了不同人群间,跨越庙堂与江湖、融汇“正统”与“妖妄”之相通思想、行为及价值的生成?(45)应予说明的是,儒生与方士以及后文所论经学与谶纬的融通,都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在由“辅汉”而“代汉”的汉末历史大背景下,各种思潮趋于汇流,不同人群之思想、行为与价值被进一步牵引至相同方向,由此表现出知识、信仰与政治、社会间的复杂互动,此即本文论述的焦点所在。有关他们在西汉中后期至两汉之际的历史呈现,可参见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冯渝杰:《从“汉家”神化看两汉之际的天命竞夺》,《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22-37页。
二、汉魏禅代的知识背景:经学、谶纬与道教的交互推进
“党锢之祸”和“黄巾之乱”作为东汉王朝崩解前夕渐次兴起的重大历史事件,始终无法摆脱与王朝覆亡的关系,所以相关研究从未停止。在此过程中,研究者逐渐发现“党祸”与“黄巾之乱”间若隐若现的关联,并就两者的起承关系进行了精彩的融通性解释。在石泰安、川胜义雄等先生坚实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党祸”至“黄巾之乱”间五十年的历史演进,吉川忠夫敏锐地提出:“‘太平’的理想才是贯流于东汉末的社会上下的东西,生活在这一困难时代的人们,是寄托于‘太平’一语的社会理想上来探索现实性课题的解决的,……尽管五斗米教团是宗教集团,私塾是学问集团,尽管有着这样的不同,但都是在这个困难的时代而目的在于各自理想的完成而聚集起来的人们的集团。”(46)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第438-439页。“太平”理想对汉末不同人群共同影响的提出,显示出吉川忠夫准确的学术直觉和判断力,然而这个问题仅出现在其著作的“后记”中,作为交代其研究缘起及学术旨趣的内容一笔带过,不免让人感到遗憾。下面笔者将分别从士人与术士的相似知识构成、经学与谶纬的价值相通性以及经学与原始道教的共通追求三个方面,具体论述汉末不同种类知识间的共同价值追求——“太平”,究竟是如何交织起来促成党人、游侠与妖贼、隐逸的共通价值与行事基调、行为趋向,(47)与“汉家”紧密相关的“太平”思想,对汉末党人、隐逸、原始道教的具体影响,主要表现在由这几类人群连接发起的汉末政治-宗教运动中。该问题所涉复杂,参见冯渝杰:《祈望“太平”:理想国家追求与汉末社会运动》,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年。并进一步构筑起汉魏禅代酝酿与实现的知识背景。
(一)“博通内外”:经生、术士、隐逸的相似知识构成
汉末游侠、党人、妖贼、隐逸之价值与行为的相通性,首先应直接导源于他们相似的知识构成。有关于此,我们先须理解东汉游学之风所带来的变化,包括:第一,学说的横向流动,即东汉游学之风致使区域壁障渐除。在刘太洋“汉代游学状况表”所举的106名游学者中,东汉即有51人,分别来自全国三十多个郡国,包括酒泉、会稽、吴郡、岭南等地。(48)刘太祥:《汉代游学之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第42-54页。方燕指出:“《后汉书》明确记载有游学经历者128人,而名师大儒门下从学者云集,及门弟子数百上千,著录弟子竟有达万六千人者。”(49)方燕:《东汉游学活动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第71-75页。相关讨论亦见张鹤泉:《东汉时代的游学风气及社会影响》,《求是学刊》1995年第2期,第104-109页;陈雁:《东汉魏晋时期颍汝、南阳地区的私学与游学》,《文史哲》2000年第1期,第71-75页;聂济冬:《游学与汉末政治》,《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第70-74页。可见东汉游学之盛。而游学最直接的结果,即促进不同地区及各种学说间的交流与融通,比如郑玄“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卢植,事扶风马融”,学成辞归,而马融乃喟然谓门人曰:“郑生今去,吾道东矣。”(50)《后汉书》卷35,第1207页。第二,纵向交流。典型表现即“党祸”后知识群体的民间下移带来一定程度的阶层突破,这在汉末隐逸之风中有明显反映。第三,不同“知识”间的融合。主要表现在由于谶纬的桥梁作用,带来儒学的儒术化倾向,同时道教也吸纳经学与谶纬中的有关内容,神学体系更趋完备。具言之,汉末经生、术士、隐逸的相似知识构成,可从以下两方面得到证明。
第一,出现了有关经生与经学的神秘化、术数化理解倾向及操作实践。如《后汉书·独行向栩传》载:
(向栩)少为书生,性卓诡不伦。恒读《老子》,状如学道。又似狂生,好被发,著绛绡头。……不好语言而喜长啸,……有弟子,名为“颜渊”、“子贡”、“季路”、“冉有”之辈。……或骑驴入市,乞匄于人,或悉要诸乞儿俱归止宿,为设酒食。时人莫能测之。郡礼请辟,举孝廉、贤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征拜侍中,每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惮之。会张角作乱,栩上便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51)《后汉书》卷81,第2693-2694页。
史载五斗米道即以《老子》五千言为恒常的教习之作,并专设“奸令祭酒”一职,“都习《老子》五千文”。(52)冯渝杰:《论五斗米道的“官僚性”特质》,《四川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26-134页。向栩“恒读《老子》,状如学道”“著绛绡头”“不好语言而喜长啸”等特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原始道教的某些做法与制度,然其弟子又纷纷诳称孔门之后,故实可谓亦儒亦道者也。更有意思的是,向栩竟当众认真提出北向读《孝经》以灭黄巾的建议,在这里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显然已被术数化,并被赋予咒杀妖贼的神秘力量。复按《风俗通义·怪神第九》曾记载郅伯夷诵经与以剑击魅之事,进一步折射出东汉《孝经》术数化的现象:“未冥楼镫,阶下复有火,(伯夷)敕:‘我思道,不可见火,灭去。’……既冥,整服坐诵《六甲》、《孝经》、《易本》讫,卧有顷,更转东首,絮巾结两足帻冠之,密拔剑解带,……再三,徐以剑带系魅脚,呼下火上,照视老狸正赤,略无衣毛,持下烧杀,明旦发楼屋,得所髡人结百余,因从此绝。”(53)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28页。有关此则材料的讨论亦见冯渝杰:《铸剑、剑解与道教身体观——“人剑合一”的知识考古》,《人文杂志》2019年第2期,第86-87页。或许正是因为《孝经》术数化程度的递进,六朝时方才多次出现《孝经》入葬之事。如吉川忠夫所论,六朝普遍存在着可以称之为“《孝经》信仰”的宗教性感情。(54)吉川忠夫:《六朝精神史研究》,第425页。相似的情况又见于逸民高凤,《后汉书》载其“少为书生,……专精诵读,昼夜不息”,“太守连召请,……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55)《后汉书》卷83,第2768-2769页。可见高凤或亦兼习巫道与儒术。
对经生、经学的神秘化理解,还尤其典型地体现在经学大师“驯服”、感化叛军的相关史实中。如笔者曾讨论指出,汉末的士人郑玄、孙期、袁闳、徐胤、荀恁等都曾因其学识、贤德等保全乡里,免受寇贼侵犯。进一步考察可以发现,这些“义感”类事例并非是徒有其形的“历史书写”,而是当时儒道共融之学术、信仰生态的自然写照;“妖贼”服膺经生,非感慕于名德,而确乎尊其学识也(实际上两者亦存在思想、知识的共通处)。(56)冯渝杰:《从黄巾拜郑玄看汉末隐逸与地方秩序的重建》,《文史哲》2017年第2期,第141-154页。依上所论,此说确然。
值得注意的是,对经书、经文的神秘化理解与操作,以及经生(儒生、官吏)与术士(妖贼、神灵)的“斗法”主题,在梁武帝时期的重要文士殷芸所著《殷芸小说》中,已被有效融合进东汉时期豫章太守顾邵与庐山君精辩复庙的“故事”中:
顾邵为豫章,崇学校,禁淫祀,风化大行。历毁诸庙,至庐山庙,一郡悉谏,不从。夜,忽闻有排大门声,怪之。忽有一人开阁径前,状若方相,自说是庐君。邵独对之,要进上床,鬼即入坐。邵善《左传》,鬼遂与邵谈《春秋》,弥夜不能相屈。邵叹其积辩,谓曰:“《传》载晋景公所梦大厉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则有之,厉则不然。”灯火尽,邵不命取,乃随烧《左传》以续之。鬼频请退,邵辄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气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逊,求复庙,言旨恳至。邵笑而不答。鬼发怒而退,顾谓邵曰:“今夕不能仇君,三年之内,君必衰矣,当因此时相报。”邵曰:“何事匆匆,且复留谈论。”鬼乃隐而不见,视门阁悉闭如故。如期,邵果笃疾,恒梦见此鬼来击之。并劝邵复庙。邵曰:“邪岂胜正!”终不听。后遂卒。(57)《太平广记》卷293,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332页。相关讨论可参乐维(Jean Levi):《官吏和神灵——六朝及唐代小说中官吏与神灵之争》,张立方译,《法国汉学》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32-59页。
顾邵禁毁庐山庙,庐山君至顾邵住所要求他复庙,庐山君以顾邵所擅长的《左传》与其彻谈“斗法”,弥夜不能相屈,当油枯灯尽之时,顾邵烧《左传》以续之,终于使得庐山君伏法请退。由此可见,经生与经书均被赋予了神性,而与术士、妖贼、神灵具有相似的知识构成以及与之直接对话、甚至“斗法”的力量。
第二,“博通内外”、亦儒亦道的知识群体——隐逸开始形成,并以术数俘获民心,如此他们手中的知识便逐渐发展成为类似宗教的权力。如法真“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为关西大儒”,“同郡田弱荐真曰:‘处士法真,体兼四业,学穷典奥,……将蹈老氏之高踪’”;郎顗“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昼研精义,夜占象度,勤心锐思,朝夕无倦”;张楷“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性好道术,能作五里雾”;申屠蟠“隐居精学,博贯《五经》,兼明图纬”;姜肱“博通《五经》,兼明星纬”等。(58)以上参见《后汉书》,第2774、1053、1242-1243、1751、1749页。
正因为学术与信仰的交融互渗,不少隐逸以此俘获民众,赢得士人、朝臣追从。比如王远“学通五经,尤明天文图谶、《河》《洛》之要,逆知天下盛衰之期,九州吉凶,如观之掌握”,由此,“举孝廉,除郎中,稍加中散大夫。……后弃官,入山修道。道成,汉孝桓帝闻之,连征不出。使郡国逼载,……不答诏”。值得注意的是,王远隐居乡里还得到了乡人供养:“乡里人累世相传供养之,……在陈家四十余年,陈家曾无疾病死丧,奴婢皆然。”(59)《太平广记》卷7,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5页。可见民众视其为神圣。又如“蓟子训者,不知所由来也,……有神异之道,……于是子训流名京师,士大夫皆承风向慕之”。(60)《后汉书》卷82下,第2745页。可见士大夫对学、术兼修的隐逸“高人”之追从。再如《博物志》载:“军祭酒弘农董芬学甘始鸱视狼顾,呼吸吐纳,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寺人严峻就左慈学补导之术,阉竖真无事于斯,而逐声若此。”(61)《博物志》卷5,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5页。说明神秘的道术知识对宣称以儒学修身治国的权贵仕宦而言,同样具有不可抵挡的魅力。
总之,游侠、党人、“妖贼”、隐逸存在价值与行为的相通处,其最直接的原因,乃在于他们具有相似的知识构成——一种学术与信仰交融互渗、博通内外、兼善经纬、亦儒亦道的知识构成。
(二)“为汉制法”:汉末经学与谶纬神学的共同主旨
作为经学的变种,谶纬神学具有明确的“为汉制法”之旨,这一点在学界几成共识,当无疑义。(62)相关讨论请参见徐兴无:《论谶纬文献中的天道圣统》,《谶纬文献与汉代文化构建》,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赵博:《谶纬中孔子为汉制法之说的研究与探讨》,《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284-287页;冯渝杰:《从“汉家”神化看两汉之际的天命竞夺》,《历史研究》2015年第1期,第22-37页等。如《春秋汉含孳》直言:“孔子曰:‘丘览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又言:“丘水精,治法为赤刺方。”《孝经援神契》亦载:“玄邱制命,帝卯行。”(63)以上参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编:《纬书集成》,吕宗力、栾保群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15、815、988页。然而问题在于,“为汉制法”究竟意味着什么?一向以理性精神和学术探讨著称的经学,在这个方面是否果真与神秘的“妖妄之言”判若两途、无有相似或相通处?实际上,长期以来理性至上的价值观在中古史研究领域的过深介入,的确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人们的相关认知,由此也影响到相关领域的史实建构。(64)参见冯渝杰:《天命史观与汉魏禅代的神学逻辑》,《人文杂志》2016年第8期,第85-92页。汉代经学理性而非神秘的面向、学术而非信仰的性格,正是这样一个亟待重新认识的认知层累建构的领域。下面笔者便从关涉《春秋》三传立意根本的“西狩获麟”出发,对汉末经学与谶纬神学的相通主旨——为汉制法,做一讨论。
“西狩获麟”可谓春秋学上的标志性事件,汉代今古文经学对此均有浓墨重彩的发挥,如华喆所总结:“围绕‘西狩获麟’的问题,汉代公羊家与左氏学者各有论述。公羊家侧重利用五德终始之说,把麒麟与汉朝德运联系在一起,以此为汉得天命的佐证。左氏学者本来并不像公羊这样攀附时政,但从陆逵开始改变态度,创造出‘修母致子’学说,希望获得皇帝支持。此后左氏学者如服虔等均主此说,并且不断附益新的内容,学说不断扩大。从公羊、左氏两派学说之中,我们可以注意到,至东汉中后期以后,两派主要学者都表现出了对汉朝政权的迎合与依赖,公羊固然传统如此,左氏学者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公羊也好,左氏也罢,‘西狩获麟’解释的重心都从孔子转移到了汉朝德运之上,成为郑玄所处时代春秋学的主流。”(65)华喆:《礼是郑学:汉唐间经典诠释变迁史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第168页。汉代经学史上,“西狩获麟”解释重心向汉朝德运的转移,整体上亦与西汉中后期以降不断深化、增强的“汉家”神学,以及日益凝聚、高涨的颂汉、归汉、辅汉思潮相吻合。对于这样的思潮发展过程,较为合理的态度或应为,不单方面归因于政治、权力的压迫、形塑,解之为“屈服史”,但也绝不能简单释之为士人与民众的自觉行为、主动意愿,而一定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选与被选的双向过程——一般而言,前期外力压迫的被动因素更显,后期则可能逐渐转化为一种无力检省的内部惯性,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方才呈现出如是整体性的社会思想样貌与历史现象。
具体到汉末经学领域,仔细研究可以发现,何休《公羊解诂》有关“西狩获麟”的相关解释,直可谓汉代经学“为汉制法”主旨的总结性表达。(66)陈澧指出:“《春秋繁露·符瑞篇》云:‘西狩获麟,受命之符。’是西汉时,《公羊》家已有此说。……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云:‘后制百王,获麟来吐。’史晨《祀孔子奏铭》云:‘西狩获麟,为汉制作。’又云:‘获麟趣作,端门见征,血书著纪,黄玉响应,主为汉制,道审可行。’汉人多以获麟颂扬汉代,何邵公囿于风气,遂以注经也。”参见陈澧:《东塾读书记》,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204页。《公羊传》“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何休注曰:

“图录”当然指谶纬图录。检诸谶纬文献,《尚书中候》有载:“夫子素案图录,知庶姓刘季当代周,见薪采者获麟,知为其出,何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将当周。”《春秋元命苞》亦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当兴也。”《孝经援神契》记述尤详。(68)以上参见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编:《纬书集成》,第451、580、992页。由此可见,《公羊解诂》当据《尚书中候》《春秋元命苞》等纬书所记,将《公羊》并未道明的“西狩获麟”瑞象,判断为孔子所预言的“庶姓刘季当代周”之瑞,此即前揭谶纬之“为汉制作”或“为汉制法”主旨。
复案《公羊》哀公十四年:“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解诂:“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子夏明日往视之,血书飞为赤乌,化为白书,署曰《演孔图》,中有作图制法之状。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又曰:“待圣汉之王以为法。”(69)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54页。此处何休之言,以更加神秘的叙事方式,将孔子作《春秋》解释为,由于其预知刘汉将继乱而兴,特制拨乱之法以授,达到为汉制法之目的。可以发现,强烈的谶纬之风弥漫于何休的叙述之中,尤其是后段有关“端门血书”的描写,从叙事方式到符瑞意象的使用,都与谶纬如出一辙。这再次表明,何休经注中的确贯穿着“为汉制法”的主旨,并且此般主旨的形成与图录、图谶的影响,不无关联。
时移世易,当原有的历史语境逐渐隐去、消失之后,何休援纬解经、为汉制法的做法遭到了后人的猛烈批评,如陈柱所言:“何休之《解诂》,最为诟病者,莫如谶纬之说。”他还在《恕何篇》中历数其过:“汉儒好说谶纬,谓孔子为汉制作。……班氏大儒,说尚如此,则当时学者风气,盖可知矣。故何休作《公羊解诂》亦不能不用其说。”此外,陈柱还引用清人江衡之说,叱何甚厉:“邵公之注公羊,支离附会,一意谄汉,不辞侮孔。汉儒多以治经起家,休直借《春秋》为干禄之计,可谓屈经从己。”(70)陈柱:《公羊家哲学(外一种)》,李静校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2-144 页。“谄汉”之说虽囿于经学藩篱,缺乏历史的同情理解,失于偏颇、独断,却从反向透露出何氏所代表的汉末经学之“为汉制法”主旨,确系至固至深。
何休之外,汉末经学之为汉制法主旨,在郑玄的学说体系中亦有相当程度的反映,为构建、圆融其理想的经学世界,郑玄援纬释经的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笃信谶纬甚至达到了“横造此言”、曲解史实的地步。(71)详参冯渝杰:《汉末经学通纬旨趣探微:以郑玄、何休为中心》,《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17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第59-75页。并且郑玄经注,尤其是《周礼》注中,还存有大量“比拟汉制”“以今况古”的手法及内容,其中缘由亦不脱谶纬之影响,适如马端临指出:“康成注二《礼》,……其病盖在于取谶纬之书解经,以秦汉之事为三代之事。”(72)《文献通考》卷68,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77页。鉴于谶纬“为汉制法”的明确主旨,及谶纬在郑玄经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可做如是判断:在郑玄的超现实的古制建构中,实当寄寓着他本人的信仰及现实慕求,即对汉家“太平”之想象与重构将通过“汉家法周”的途径达成。也是在此意义上,笔者以为,郑玄经注中“比拟汉制”的内容,不应仅仅被视为一种备受诟病的经解方法,而是深深地打上了“为汉制法”的烙印。当然,在“西狩获麟”的问题上,从留存下来的有限资料中,我们也可隐约察见郑玄的偏向及态度。《易纬辨终备》载:“一角期偶,水精得括考备,据谁授赤戴胜。”郑注:“一角谓麟也。文王得赤鸟书而演《易》,孔子获麟而作彖象及《系辞》以下十篇,故谓麟应期而来。偶,赤鸟也。水精者,孔子也。得获括考备者,易道也。赤为汉也,汉火精,高帝之表戴胜,自虙戏方宋记此,皆《斗冥图》言之也。得或将。”(73)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编:《纬书集成》,第193页。在这里,郑玄同样择取《公羊》之说,采信谶纬中的赤鸟神话,言孔圣为授命汉家之水精,终以麟至为赤汉受命之符者也。
(三)“想望太平”:经学、原始道教终极追求的相通性
经学与谶纬的共同主旨,透射出经学溢出于学术层面之外的信仰面相,而经学与道教的相通性,无疑将进一步揭示汉末学术(经学)与信仰(太平道)的交融互渗状态。上文论及“为汉制法”乃汉末经学的主旨及价值归宿。之所以说是价值归宿,正在于经学的“王汉”与“汉家法周”论说,及其以周、汉为“太平”理想社会及个人生命所属之信仰空间的终极追求。所以,“为汉制法”是途径,“想望太平”才是终极追求所在。下面笔者便以何休《公羊解诂》中有关“太平”的集中论述与原始道教经典《太平经》之主旨为主要论述点,由此揭示“太平”理想在汉末经学与道教中的相通属性。
《公羊解诂》的“太平”论述,主要蕴藉于“三世说”中。《公羊传》:“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解诂》曰:“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7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200页。从“衰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这显然构成一个逐层渐进的理想社会的序阶,“太平世”即是终极的理想社会,其显性标准或状态为:政治清明、至公至允,化外夷狄归夏、沐浴天威,天下远近大小若一、万里同风。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自然征象(瑞象)以为“太平”之符,如前揭之麒麟。这在《公羊解诂》中亦数次提及,如“麟者,大平之符,圣人之类,时得麟而死,此亦天告夫子将没之征,故云尔”,“人道浃,王道备,必止于麟者,欲见拨乱功成于麟,犹尧、舜之隆,凤皇来仪,故麟于周为异,《春秋》记以为瑞,明大平以瑞应为效也。绝笔于春,不书下三时者,起木绝火王,制作道备,当授汉也”,“尧舜当古,历象日月星辰,百兽率舞,凤凰来仪,《春秋》亦以王次春,上法天文,四时具然后为年,以敬授民时,崇德致麟,乃得称大平。道同者相称,德合者相友,故曰乐道尧舜之道”。(7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2353-2354页。在这里,谶纬便与“太平”论述联系起来了。而谶纬文献中大量近似于“三世说”的论说,表明何休“三世说”或仍渊源于此。(76)相关讨论可参见邱锋:《何休“公羊三世说”与谶纬之关系辨析》,《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4期,第130-134页;段熙仲:《公羊春秋“三世”说探源》,《中华文史论丛》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67-76页。果如此,那么谶纬神学便与“太平”理想再度关联到了一起。总之,根据《公羊解诂》“太平世”之脱溢现实的有关论说,尤其是谶纬神学与“太平”论说的个中关联,何休经学思想中,由“太平”所表征的终极理想社会,当已超越理性的学术层面讨论,成为被赋予一定信仰属性、类似于宗教构想的信仰空间;这个空间,在原始道教同样以“太平”命名的大型经典中,有着更为明确的设计和描述。
黄巾起事时即举“黄天泰(太)平”之旗号,《太平经》则可谓对包括黄巾在内的当时人们之“太平”“大吉”热望心态的系统表达。比如《太平经·三合相通诀》载:“天气悦下,地气悦上,二气相通,而为中和之气,相受共养万物,无复有害,故曰太平。”《太平经钞·癸部》释《太平经》之名曰:“太者,大也;大者,天也;天能覆育万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能养育万物。经者,常也;天以日月五星为经,地以岳渎山川为经。天地失常道,即万物悉受灾。帝王上法皇天,下法后地,中法经纬,星辰岳渎,育养万物。故曰大顺之道。”(77)王明:《太平经合校》,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49、718页。据此,“太平经”之意即“天地之常道”。“天地失常道”,“则万物悉受灾”,故《太平经》撰作之目的即辅佐帝王以“大顺之道”治国教民,“佐君致太平”。所以,在原始道教神学体系中,“太平”即意味着理想秩序和绝对意义,这与汉末经学之追求,似并无不同。正因如此,《太平经》所反映的黄巾的“太平”祈望与东汉正统儒术之间,亦颇有相通处。日本学者间嶋润一即曾考察太平道之“太平”与郑玄对周公招来太平过程之解释的若干相似点,可堪为证。(78)間嶋潤一:『鄭玄と『周礼』——周の太平国家の構想』,东京:明治书院,2010年,第451、462-463页。据此可进一步解明,经学与原始道教终极追求的相通性,当肇基于他们对于“太平”理想社会的相似理解与强烈渴慕。
三、结 语
综合以上讨论,从颇具游侠风范的党人婞直之风,游侠、党人与“妖贼”术士的隐秘关联乃至直接“接引”,以及党人下潜至民间而与隐逸群体的汇流等方面,可以发现游侠、党人、“妖贼”术士、隐逸这几类人群在汉末存在思想、行为、价值方面的相通性。导源于经学通纬风尚的时人对于经学、经师的神秘化理解,士人、隐逸“博通内外”的知识构成,以及流贯于经学、谶纬、原始道教经典中的“为汉制法”主旨和“想望太平”的终极追求,既是促使这几类人群的相通性生成的思想要因,亦是汉魏禅代酝酿与实现的知识背景。从今文经学至谶纬的神学性演变,再经谶纬至原始道教的神学跨接与过渡,复至经学与道教相通性追求的生成,“为汉制法”与“想望太平”堪谓不同种类知识间的共通基调,并明显构成这一知识与历史激荡演变过程的内在、连贯线索,由此促成汉末游侠、党人、“妖贼”、隐逸价值与行为方面的相通性,将错综复杂的汉末思潮最终导向不可逆转的汉魏禅代方向。进一步看,经学、谶纬、道教、数术等不同种类知识间的交融,乃深深植根于并从不同层面巩固了汉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信仰属性的国家神学。然而随着知识与社会的交迭奔进,不同人群从内部发生总体性思想转折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触发社会思潮转向,(79)有关汉末宗教、社会思潮转向的讨论请参见冯渝杰:《“致太平”思潮与黄巾初起动机考——兼及原始道教的辅汉情结与终末论说》,《学术月刊》2018年第5期,第138-153页。引起社会结构的微妙变化(比如持续的不同知识的交流活动促使东汉的地域与阶层区隔得到一定程度的突破),作为社会深层秩序的汉代国家神学随之走向解体。伴随汉魏禅代的完成,古代帝国秩序崩塌,历史进入绝对价值陨落、多重权威崛起的中古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