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局外人的反击
刘晗
面对着无以名状的时间,大多数人都选择在“局内”徘徊,每天被大小局面支配得有如牵线木偶般僵硬,在饭局、牌局、交际场上千篇一律伪装的面孔和讨巧的对白,沦为享受世俗生活的必备良方,仿佛只有如此,才能融入社会的洪流。年轻的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 以一篇《局外人》初闯文坛,这篇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让人看起来匪夷所思的故事,真实地还原了世界的本来面孔,不带任何修饰地还原了人最本真的状态。
在作品中揭开伪善,袒露身处异己现实之中的孤立无援,加缪不是第一个,但他思想的锋芒以及对真理的追求在他逝世60年后影响至今,成为无数读者的精神导师,正如他在题为《艺术家及其时代》的演讲中所说的,“面对时代,艺术家既不能弃之不顾也不能迷失其中。如果他弃之不顾,他就要说空话。但是,反过来说,在他把时代当作客体的情况下,他就作为主体肯定了自身的存在,并且不能完全服从它。换句话说,艺术家正是在选择分享普通人的命运的时候肯定了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艺术的目的不在立法和统治,而首先在于理解。”作为创作者,只有感同身受,才能在同理与共情之中倾听出世间微弱的呼声,坦承的自白。
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理解起来并不艰深,当人类投身于社会的准则,在利益与立场之间抉择,为了达成目的或者意愿而充斥谎言、萌生恶意、遍布奴性、邪恶丛生,甚至不择手段,在集体无意识的推动下,那些不假思索、自以为是的表达与行为便自然而然成了真相,身处异己的境况并不意味着自我谬误,越混沌愚昧,越要保持清醒,纵使独自忍受痛苦,也不同流合污;即便被大多数视为“局外人”,也要奋起对荒谬予以反击。
缄默者:在痛苦中隐忍
大多数反击依靠的是暴力,而加缪却是在痛苦之中保持隐忍,儿时丧父,生活拮据给他的童年蒙上一层阴霾,母亲做佣人供他完成学业。像大多数文艺青年那样,加缪热爱运动,投身戏剧,办报纸,做编辑,将所有的热情投入到了哲学与艺术中,从而也结识了如萨特、波伏瓦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友人,萨特一度是加缪最亲密的同盟,但后竟因立场观点的对立而争吵不休,最终分道扬镳。
如此艰难多于幸福的日子就像他后来在《西西弗神话》里的思索:“在他离开山顶的每个瞬息,在他渐渐潜入诸神巢穴的每分每秒,他超越了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推的石头更坚强。” 西西弗是古希腊神话之中的人物,身为科林斯的创始者,他神通广大、聪明绝顶,因触犯了诸神沦落到去山顶推巨石。终日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正是普通人一生的描摹,一复一日徒劳地抄袭每天的生活,永无出头之日,身在其中习以为常,在他者看来却是如此荒谬,要么奋起反抗、要么重获自由,拥抱激情。悲观重重包围,等不到翻盘的人无力在沉默之中爆发,只能苟且生存。

1957年,阿尔贝·加缪在巴黎一家出版社举行的诺贝尔奖招待会上。加缪成为第二年轻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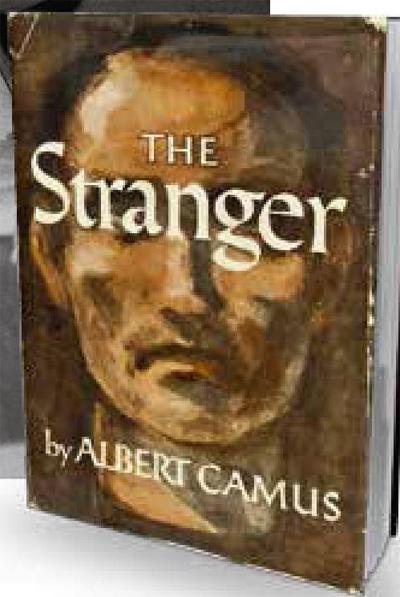
加缪因小说《局外人》成名,书中他形象地提出了存在主义关于“荒谬”的观念。
在《局外人》大获成功之后,加缪完成了长篇小说《鼠疫》。在他笔下,北非城市奥兰突发疫情,打乱了人们原本平静的生活,从大量死亡的老鼠,再到每日攀升的感染人数,数日之后封城,全民囚禁其中风声鹤唳……灾难之下的医生、记者、志愿者、政客、奸商,等等,有的舍身救人,有的为了一己私利的贪婪暴露了狰狞的面孔。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之中,瘟疫如影随形,早已是生活的一部分,“可鼠疫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是生活,如此而已。”面对这场浩劫,有些人挺身而出,在黑暗中投射了一缕光明。主人公医生里厄和志愿者塔鲁是故事的核心人物,也是整个事件的见证者,里厄從发现疫情到不顾个人安危冲在了抗疫一线,超负荷救治病患,却要独自面对染病妻子离世的噩耗;作为志愿者的塔鲁则始终为防疫而忙碌奔走,最终染病不幸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每当有瘟疫袭来都少不了焦虑恐慌、殉难牺牲,“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哪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鼠疫是一面镜子,照见了人性之恶,它存在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面对充满敌意的世界,凡人如何承受苦难,逃避、毁灭抑或迎难而上?灾难是现实,亦是寓言,加缪以瘟疫的蔓延来映射二战法西斯的肆虐,甚至暗指破坏人类平和与欢乐的一切不幸,加缪目睹了大屠杀之下的极度绝望,这样的情绪和瘟疫降临时民众的感受如出一辙。当瘟疫被驱散、阳光普照之时,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铭记这段至暗时刻。
局外人:在喧哗中逃亡
在《局外人》之中,主人公默尔索突闻长期居住在养老院的母亲离世的消息毫无一丝悲伤,面对生死离别时的淡定让人大感意外,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竟在母亲下葬的次日就沉沦于男女情爱之中,他不过问生命的去向和意义,正如他在送葬路上所说的:“走得慢,会中暑;走得太快,又要出汗,到了教堂就会着凉。”在他的世界中,感官的欲望才是其牵肠挂肚所在。
默尔索,目光专注、冷静,总是带着可有可无的笑容以沉思状倾听他人娓娓道来。他虽表面上对女友冷淡,内心深处却对她有着情感寄托,他也以诚相待身边的朋友,但由于不愿拒绝别人,他成了朋友的帮凶,命运的指针偏偏一步步让他走向不归路。对于默尔索自己来说,也许是一个陌生人,这种异己感的存在正是他的虚无所在。他从不掩饰真实的情感和事实,当法庭上的证人给出真实的供词之后,默尔索甚至有想拥抱他的冲动;他在法庭上说出的唯一一句辩护词竟然被法官和律师视为戏谑之言:阳光刺眼以至射杀他人。
这件不在计划范畴之内的杀人案是默尔索思想的走火,精神的偏轨。他完全可以为自己辩护,但是在法庭中的每一句轻声的否定,都一步步将他推向死亡的深渊。令人讶异的是,一场刑事案的庭审居然演变成一场关于道德是非的研讨,众多证人的出场像是维护默尔索母亲的后援团,纷纷声讨默尔索的不孝和无情。默尔索的律师在为其辩护时说道:“说到底,究竟是在控告他埋了母亲,还是在控告他杀了一个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作为道德矮子的默尔索终将被推上断头台,在他看来,这些司法程序就是一场游戏。
加缪的小说似乎离不开严肃的场景:医院、法庭和监狱,唯一令人感到阳光和煦的沙滩上却发生了令人心悬的惨剧,这使得小说全篇都陷入了异样冰冷的境地。在这接近零度的白色世界,在每一个丧失了自己名字的日子,穿梭在戴面具的人群中,默尔索对自己说,是该结束的时候了,看透了荒谬的世界,奉承无能,又无法改变现状,对一切无动于衷,幻化成尘埃般的白骨要比那些强颜欢笑的人真实得多。死刑执行那天,在一片仇恨的叫喊中,正是他脱离沉重的肉身上演的一场华丽的逃亡,这也是“默尔索们”共同的宿命。
加缪将局外人的处境与他者、与现实的对立推向了极端,无奈以荒谬抵御荒谬,他人眼里的诡异怪诞,在默尔索那里却是最实在的,一种深沉缄默的常态表达,不需要迎合揣摩,也无须逢场作戏。无论是面对生活,还是对待生死,低至冰点的情绪与其说是冷漠颓废,不如说是自我拯救,脱身于禁锢束缚以及难以入目的丑态。
天才的悲剧没有被小而舒适的名望所束缚,而是在绚烂而辉煌的时刻戛然而止。年仅四十七的加缪在车祸中遇难的消息令人扼腕叹息,如他所说过的,“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死在路上更蠢的事了。”作为一名存在主义哲学家,他的意外离世些许有些荒诞的意味,在《局外人》里,他写道,“当然,希望是在飞速奔跑之中,被一颗突如其来的子弹,击倒在街口。”这样的寓言更像是一则预言,一语成谶,惋惜的是,他离世前随身携带着一部未完成的手稿《第一个人》,留下了再也猜不透的小说结局,就像在鼠疫期间的度日如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