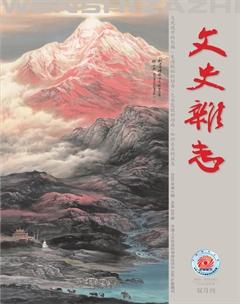苏洵与《太常因革礼》的修纂
谢桃坊



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由名臣名儒修纂的《太常因革礼》是今存中国古代仪制的一部重要的典籍。治平二年(1065年)“九月辛酉,提举修纂礼书、参知政事欧阳修奏,已编纂礼书成百卷,诏以《太常因革礼》为名”[1]。参加此著的编纂者有欧阳修、吕公著、宋敏求等名臣,以及太常寺礼院官员,而具体负责修纂者是礼院编纂姚辟和苏洵。欧阳修在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为苏洵作的墓志铭云:“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从食其禄,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而君以疾卒。”[2]在《太常因革礼》的修纂中苏洵起到什么作用?此著有什么新的意义?怎样贯彻了苏洵的史书之体的意图?凡此均很值得探讨。
一
自唐代以来中国朝廷的礼仪制度已经完备,今存《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成为仪制的典范。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宋王朝建立,建元建隆。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太常博士聂崇义上《重集三礼图》(祭祀天、地、祖宗之礼)。宋太祖诏令儒士讨论厘定,继于开宝(968—974)间命刘温叟、李昉等在《大唐开元礼》基础上修订为《开宝通礼》二百卷。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由王皞将礼院所藏宋开国以来仪制诏敕编集为《礼阁新编》六十二卷,景祐四年(1037年)贾昌朝撰成《太常新礼》四十卷。然而《礼阁新编》属于吏文汇集,无著述之体,《太常新礼》之载止于庆历三年(1043年)。嘉祐六年(1061年)欧阳修以尚书礼部侍郎参知政事同判太常寺,奏请仁宗皇帝差官修纂礼书。当时秘阁校理张洞奏请择用幕职州县官文学该赡者三两人置局修纂。此年七月朝廷任命姚辟与苏洵修纂宋开国以来礼书,以欧阳修提举修纂。治平二年(1065年)礼书修纂完成,欧阳修上奏朝廷,宋英宗赐名《太常因革礼》。此著一百卷,署为“臣欧阳修等奉敕编”。
当《太常因革礼》开始修纂之时,知制诰张瓌上奏仁宗皇帝云:“伏见差官编校开国以来礼书,窃恐事出一时 不合经制者,著之方册,无以示后。欲乞审择有学术方正大臣与礼官精议是非,厘正铎,然后成书,则垂之永久,无损圣德。”[3]此奏议当由朝廷转发与欧阳修处理,欧阳修又转于苏洵,由苏洵对此问题向朝廷答复。张瓌以为宋代开国以来的礼制仪式的施行中,有的出于临时的权宜或新制者,其中有许多事不合于传统礼仪经典的,即属于错误的,如果将它们都著之典册,岂不有损皇帝的圣德。因此为了掩饰朝廷之错误或过失,他建议对礼仪史料进行选择辨别是非,严加审核,然后才可著之于书。此即本着儒家为尊者隐恶扬善之意。关于修礼的原则,仁宗皇帝曾有敕文说明,特别强调“纂集故事而使后世无忘之耳”。苏洵针对张瓌的意见特上《议修礼书状》,请欧阳修备录奏闻。苏洵认为张氏之言与敕文之意完全背离,他说:
洵筹所编者是史书之类也,遇事而论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而善恶自白者,是史之体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则是制作之事,而非职之所及也,而议者以责洵等不已,过乎!而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礼,虽为详备,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处,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识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则其势不得不尽去,尽去则礼缺而不备,苟独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则实足以为抵牾龃龉而不可齐一。且议者之意不过欲以掩恶讳过,以全臣子之义,如是而已矣……今无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后世将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汉志》,凡汉之事悉载而无所择,今欲如之则先世之小有过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后世无疑之之意,且使洵等为得其所职,而不至于侵官者。[4]
苏洵阐释了“纂集故事”之主旨:一、修纂礼书是遵照史书之体,以客观的态度将发生的史事记载下来,不区别善恶,让后世的人们去判断,因此它不同于学者或文人的论著以表达己意为主;二、宋王朝开国以来的仪制及仪例可能存在不合礼制或错误者,但怎样去判断和去取,若去掉一二事则有矛盾之处,若全部去掉则使礼书残缺,故应以存一代之制而全部记载;三、本朝先世若有小过差并不足以损害其圣明,记载下来可使后世人们见到历史真相而不致怀疑。这样的修史原则正是史臣应当尽职坚持的。苏洵的意见为朝廷所采纳,因此保证了礼书修纂的历史价值。礼书修纂完成后,欧阳修上奏英宗皇帝论述历代仪制编订情况后,谈到新修纂之礼书体例云:
嘉祐中臣修以为言,而先帝属修与凡礼官,命臣姚辟、臣苏洵专领其局。始自建隆以来迄于嘉祐巨细必录,网罗殆尽。以《开宝通礼》为主而记其变,其不变者则有《通礼》存焉,凡变者皆有沿于《通礼》也。其无所沿者,谓之新礼。《通礼》之所有,而建隆以来不复举者,谓之废礼。凡始立庙,皆有议论,不可以不特见,谓之庙议。其余皆即用《通礼》条目,为一百卷。[5]
这在修纂礼书之始即确定了全书体例。彼书之修纂实为欧阳修任主编,姚辟与苏洵任修撰专职。欧阳修乃朝廷重臣,曾主持修纂有《新唐书》和《新五代史》,而且是大学者。苏洵是欧阳修向朝廷推荐的著名学者,其《权书》《衡论》所表达的政治见解使之名震京师。姚辟乃皇祐元年(1049年)进士,历官项城令,曾于皇祐五年(1053年)与欧阳修讨论过《礼记》问题,亦由欧阳修推荐为礼院编纂的。此著虽然署名为欧阳修编,但张方平为苏洵作的墓表却说:“俾就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使食其禄,集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奏未报而以疾卒”。[6]其以为礼书是苏洵修纂的。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蜀中学者李壁以为“《太常因革礼》老苏先生奉诏所修也”,继而叙述了苏洵与欧阳修、姚辟共同完成修纂,但又同意张方平之意见而言“张文定公所谓,其事业不得举而措之于天下,独新礼百篇今为太常施用者是也。”[7]我们纵观《太常因革礼》的修纂过程,可以肯定苏洵与欧阳修关于修纂的体例及原则是他们共同确定的,在具体的修纂过程中苏洵是起到重大作用的。
宋英宗为新修纂的礼书定名为《太常因革礼》是甚为确切的,表明了此书是朝廷所用的仪制并突出仪制在本朝的因袭和破旧创新的意义。中国古代的礼是关于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和仪式的规定,以区分社会人们的尊卑贵贱的地位。儒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主要职事便是制礼作乐,通过礼仪形式确定各阶层人们的社会地位。儒家的经典《仪礼》是为礼经。它是关于婚、冠、丧、祭、射、乡、朝、聘的种种礼仪形式的规定,适应于帝王及士大夫等统治阶级,其意义如朱熹所说:“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义……礼治则治,礼乱则乱,礼存则存,礼亡则亡。”[8]可见礼制是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关系着社会的治乱。秦代曾置奉常以掌管朝廷礼仪,西汉初年改为太常,乃九卿之一,至北齐改设太常寺。宋代的太常寺置卿、少卿、丞各一人,博士四人,主簿、协律郎、太祝各一人。卿掌管朝廷礼乐、宗庙、社稷、坛壝、陵寝之事。礼仪分为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五类,各类均有繁琐的制度仪式。宋初负责太常寺者由朝廷重臣监管,另置太常礼院以负责礼仪文献,讨论礼仪等事。因此欧阳修等修纂的礼书不是适应一般社会的礼仪,而是太常寺掌管的朝廷的礼仪。在朝廷的礼仪中的祀天、祭地、宗庙祭祀之礼为帝王的大祀。《中庸》第九章云:“祭祀之礼,所以祀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祭祀之礼,谛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帝王的祭祀天地,表示是受天之命而有至尊之位;祭祀宗庙,表示其所处之尊贵传统;这样可以昭显帝王的神圣威严,令臣民崇敬。儒者以为帝王如果懂得祭祀天地宗庙的意义,便可悟得治国的道理。我们从《太常因革礼》可见宋代帝王不仅非常重视各种大祀之礼仪,并对各种祭祀及各种仪式皆非常重视。儒臣们如果对某些礼仪细节提出意见,或以为不合礼制,皇帝则令礼院探讨,并由皇帝作出最后决定。在礼仪的制定、修改、废除、讨论的过程中实际隐含着统治集团内部微妙的政治斗爭,同时体现了儒家制礼的社会政治意义。
二
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年),李壁在《太常因革礼序》中云:“《新礼》(《太常因革礼》)百篇,今为太常施用者是也。钱侯太虚为吾州,尽刻苏氏之书于学官,所以加惠诸生甚厚,且属壁识其岁月,因备列之于末云。”[9]据此序,则《太常因革礼》曾在南宋为朝廷太常礼院所施用,淳熙时眉州太守钱太虚刊刻苏洵著作时附录此著。然而此刊本不甚流行,旋即失散,故《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皆未著录。清代中期阮元于《太常因革礼提要》云:“此书诸藏书家纥无著录者,兹从旧钞本影写,失去五十一至六十七凡十七卷,书中亦多阙文,无从访补。”[10]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及2003年《续修四库全书》收入之影印钞本应出自阮元从旧钞本影写者。晚清时藏书家莫友芝曾“依道光中钱塘罗以智本过录”,并言“罗氏一跋,考证甚详”[11]。罗以智字镜泉,乾嘉时藏书家,有《吉祥宝藏书目》传世。光绪二十年(1894年)廖廷相从藏书家方功惠碧琳琅馆借出一种钞本与阮元钞本相同。他发现钞本之讹误较多,特以宋代文献进行校勘,所校正者千余条,完成《太常因革礼校识》[12]两卷。从上述可见《太常因革礼》迄今仍以钞本流传,旧钞本有数种,但皆相同;若以廖廷相之校勘加以整理则可使此编得以完善。此编自南宋以来罕为流传,近世虽有影印本,但未受到学术界之关注,而其学术价值有待我们去认识,因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新的史料。
《太常因革礼》是按照最初确定的史家体例而修纂的,汇集了北宋王朝自开国以来讫于嘉祐六年(1061年)的朝廷百年的礼仪制度史料,贯彻了巨细必录,不加评议的原则,保存了原始资料。故从史料学的视角来看,此编是极为珍贵的。我们据此可以校补宋代有关的仪制文献。例如宋真宗时为赵氏六室追加谥号,《宋史》卷一百八失记加谥号的原因,而关于宋太宗之谥的“神”误为“仁”,又脱“文武”二字。《太常因革礼》关于天禧元年(1017年)正月九日加上六室尊谥,引《国朝会要》云:
初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闰十月,宰相以太祖尊谥有与圣祖名上字同者,请下有司改易。真宗曰:“朕亦熟虑,改易非便,况圣祖临降皇家,大庆六室,宜各加上尊谥,当令有司议定以闻,免改动玉册等。”即下诏:太庙六室,各奉上尊谥二字。宰相与礼官参详,加上僖祖曰文宪睿和,顺祖曰惠元睿明,翼祖曰简恭睿德,宣祖曰昭武睿圣,太祖曰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太宗曰至神应道神功圣德文武睿烈大明广孝。[13]
这说的是宋开国皇帝太祖之先四代及太祖、太宗在原有的谥号上再添加尊谥。宰相和礼官们使用大量的歌功颂德的最神圣美好的辞字予以美化。与此相应,则自然得给当今真宗皇帝加尊谥而美化了。《太常因革礼》保存了宋太祖于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六月关于享先代帝王陵庙之诏文:
历代帝王,国有常享,著于甲令,明白至今。自五代乱离,而司坠废,匮神乏祀,岂谓德馨;扞难御灾,或乖血食,永言祭法,阙孰甚焉。准《祠令》先代帝王,每三年一享,以仲春之月,牲用太牢,礼官以长官充,若有故,遣上佐行事。[14]
《宋史》卷一百五将此诏文摘要,比原文少16字,而文字亦有异。《太常因革礼》记载皇祐二年(1050年)宋仁宗关于明堂祭祀的手诏云:
今年九月,明堂正当三岁一亲郊之期,近见礼官所定,只祭昊天、五帝,而不及地祇,又配坐不及太祖、太宗,虽准旧典施行,未合三朝近制……其将来明堂行礼,宜特合祭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皇帝并配,朕躬亲行礼,五帝、神州,亦特享献,自余日月河海诸神从祀悉如圜丘之仪。庶协三朝旧规,以称朕躬事天地祖宗神灵之意。[15]
《宋史》卷一百一引用此手诏则据意改写,尽量简化,与原文大异,而且杂入仁宗皇帝与辅臣之语。以上枚举之三例,可说明《太常因革礼》所保存宋代仪制史料之真实性,可校正诸多文献之误。
《宋史》卷二百三《艺文志》著录有李沆等修《宋太祖实录》五十卷,钱若水修《太宗实录》八十卷,晏殊修《真宗实录》一百五十卷,又《宋史》二百四《艺文志》著录:
刘温叟《开宝通礼》二百卷
贾昌朝《太常新礼》四十卷
丁谓、李宗谔等《大中祥符封禅记》五十卷
文彦博、高若讷《大享明堂记》二十卷
贾昌朝《庆历祀仪》六十三卷
卢多逊《开宝通礼仪纂》一百卷
以上11种宋代文献均为《太常因革礼》大量引用,而原著早佚。故《太常因革礼》保存了宋代仪制之珍贵史料,可以从中辑出上述文献之佚文以及宋代太祖、太宗、真宗、仁宗之诏文和臣僚等之奏议,而其保存北宋的礼仪制度之原始史料尤为珍贵。
三
宋英宗为新修纂的礼书定名为《太常因革礼》是很确切的,表明朝廷现行之仪制是有传统的因袭与破旧创新的。唐代中期王泾修纂《大唐郊祀录》时谈到郊祀制度存在因革的关系说:“自五帝殊时,三王异礼,莫不因之沿革观损益焉。”[16]显然因社会的发展变化,各时代的礼仪制度也随之变易。王泾记述唐代现行之郊祀仪制时,注明它与古代礼制和唐代以来之礼制之沿革,并从儒家礼治的观念阐发其意义。《太常因革礼》则是仅记载本朝仪制之因革,不参核此前之礼仪制度,对仪制不作礼治意义的阐释,而是旨在保存真实之史料,自然地显示本朝仪制的因革,其意义当由人们去判断,体现了严格的史书的体例。在《太常因革礼》之前有唐代的《大唐开元礼》,在其后有宋代的《政和五禮新仪》(此两书今存),它们均为一朝现行之仪制规范。《太常因革礼》之学术意义如廖廷相说:“是书编 集故事,以备稽考,与开元、政和诸礼书垂为定制者不同,故纤曲并详,词繁不杀,其取名因革者以此。”[17]此著从整体结构到具体的条目均体现了宋王朝开国以来百年间的仪制的因革。
全书的结构由总制、五礼、新礼和庙议四部分组成。总制记载朝廷一般常用的仪制,例如神位、行事官、警戒、配帝、祝辞、祭品、祭器、宣赦书、音乐、舆服、仪仗等的规定。五礼包括以祭祀的事为吉礼,以冠婚的事为嘉礼,以宾客的事为宾礼,以军旅的事为军礼,以丧葬的事为丧礼。新礼为朝廷现行规定的仪制。庙议应是附录,记载关于本朝帝王及后妃定谥的议论。以上四部分仪制之各条目均引用本朝修撰的各种礼书,详细注明出处,严格记录原文,客观地表明其因革关系,兹举例如下:
关于祭礼天地的神位安排,总例引《开宝通礼》云:
冬至合礼天地于圜丘,第一等祀五方帝、大明、夜明七座;第二等祭祀天皇大地,北辰、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并差在前位余内宫及五星、十二辰、河汉都四十九座,齐列;第三等祀中宫、市垣、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摄提、太微、太子、明堂、轩辕、三台、五车诸天,月星、织女、建星、天纪等十七座及二十八宿并差在前列中宫,余一百四十一座齐列,祀外宫一百五座于壝之内,祀众星三百六十座于壝之外。[18]
在吉礼中则详记冬至祭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之仪式,并录北宋四朝之仪式;新礼中则记载天圣八年(1030年)祭天地而不设圜丘(祭天的圆形高坛),只设天地神位,并以太祖、太宗崇祀于大德殿。[19]帝王祭礼天地本属荒诞,但可表示其承受天地之命的合理与尊严。至仁宗皇帝时去掉杂多的天地河汉诸多神位,减少其荒诞的成分,而且不设高坛,这应是礼仪的改革。
关于皇帝在祭祀天地之后宣赦书,总例记述:
《通礼》:“皇帝亲祀毕还宫,无御楼宣赦之仪。凡宣赦书不著所因,自朝堂出宣于明德门外,皇帝不亲宣制。”《太祖实录》:“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南郊礼毕,上御明德门楼降制,左右金吾、诸军仗卫陈列填街如式。自后皇帝亲祀皆御楼肆赦,有司遂具仪。”
此两则史料说明在赵宋建国之初皇帝于南郊祭祀完毕亲自宣赦书,后来便不亲自宣制了。在此条下修纂者原注云:“国朝仪注皆同。今太常所存者乾德六年(公元968年)仪注最先,遂举以证《通礼》因革。”[20]修纂者继而于此条后引《开宝通礼》《礼院仪注》《国朝会要》等文献所载,详细表明仪制之变易沿革。
关于祭祀天地之仪式,新礼记述宋仁宗至和元年(1054年)九月十二日恭谢天地于天庆殿,修纂者原注:“国朝五行恭谢,其仪注散失不完,惟至和仪注具备,今全录以备因革云。”所谓“五行恭谢”即是皇帝祭拜天地及祖先——昊天上帝、皇地祇、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其仪式特别隆重和繁琐,例如拜谢昊天上帝:
皇帝升殿,乐止。礼仪使赞引皇帝诣昊天上帝尊坫所,执尊者举羃,侍中赞酌泛齐讫,僖安之乐作。礼仪使引皇帝进诣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俯伏,兴,赞称。皇帝少退,北向座,乐止。捧册官举册进于神座之右,中书侍郎东向跪,读册文讫。礼仪恭请皇帝再拜。中书侍郎进跪,奠册于神座,兴,还尊所。皇帝拜讫,乐作。[21]
此后继续拜谢皇地祇、太祖、太宗、真宗之神位,仪式相同。这样五次繁文缛礼,为时甚长,当使皇帝劳累不堪。我们似可怀疑制作礼仪的儒者们是否以此来愚弄帝王,展示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隆重。皇帝祭祀天地应于每年冬至之日于南郊设圜丘,仁宗皇帝改为九月十二日于天庆殿祭祀天地并祖先,于是南郊之礼得以改变。《太常因革礼》以翔实的史料记载了宋代百年礼仪制度的因革,在破旧创新的变易过程中,自然隐含着统治阶级及儒家礼仪观念的变化,也隐含着其深层的社会意义。
四
《太常因革礼》的主要修纂者苏洵(1009—1066)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兼学者。他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是采取批判态度的。他在《六经论·易论》里认为圣人作《易》是故弄玄虚的,因其道之神秘莫测,无法理解,遂使人们以为神圣,而儒家之道也为人们尊崇了。他在《义者利之和论》的专文里,认为儒家提倡的“义”实即统治者的价值观念。它之上尚有公平;若片面强调大义则必然违背天下之心,因而是戕害天下民众的工具。他在《礼论》中以为圣人提倡礼法乃是权术,“将欲以礼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22]。显然由欧阳修的推荐使苏洵修纂礼书,这仅是一种谋取禄位的职务工作,并非他自己愿意从事的著述事业。然而他在修纂之初所坚持的史书之体,坚持所记之事善恶并存的原则,却又反映了其真正的史家和学者的崇高品格。他对史料采取巨细必录,不加评论的态度,将朝廷仪制故实记录以让后世人们去评判,展示了历史的真相;仅此即显出这部礼书的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现在读这部礼书,可以从中发现诸多仪制的不善的恶的事例,由 此可见到北宋统治者的某些荒诞、虚伪与罪恶的事实。兹试举以下诸例:
关于皇帝祭祀宗庙的祝词的自我称谓问题。宋太宗在祝文里将朝臣给他上的尊号冠于“皇帝”之上,这是不合礼法的。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八月二日吏部侍郎兼秘书监李至奏言:
著作局称宗庙并诸祠祝文,皆以尊号冠“皇帝”上。伏寻此礼,自唐开元以来有之,议者不以为宜。王泾《郊祀录》弃而不载,至会昌中有司奏,宗庙祝文应称“嗣皇帝”,于时博士同考《礼经》遂为定制:是则祝文不著尊号,旧矣。窃惟尊号之称,兴于近世,盖下之归美于上,上不得已而受之。然则形容尊显示之臣庶可矣,非所以自谓于祖宗之前也。古者孤、寡、不穀,国君之谦称,得通于临下,则尊号不宜施于奉上。臣愚以为告享宗庙,当只称“嗣皇帝”,他祠称“皇帝”为得礼。[23]
祝文即祝辞,为祭礼时致祷之辞。宋太宗在祭祀祖先的祝文里冠上尊号,自称“神功圣德文武皇帝”,这是向祖先显示自己的尊贵,实即在祖先神位之前表现为狂妄自大,对祖先缺乏尊敬之意,尤其于情禮皆不合。李至的奏议中考查了《礼经》与唐代礼制,以为这样的称谓是很不恰当的,对祖先只能称“嗣皇帝”。宋太宗祭祀祖先的祝文加上尊号,可见当时皇帝和朝臣皆违背礼法,陷入狂妄无礼的境地。《宋史》卷二百六十六《李至列传》失载此奏议。
关于真宗皇帝册命贵妃收受礼物。杨淑妃年十二入皇子宫,真宗即位拜为才人,又拜婕妤,进封婉仪,升为从一品。真宗凡巡幸皆以之相丛。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六月制:“婉仪杨氏宜特封淑妃,其告身并用遍地涂金料花凤罗纸书之。”国朝后妃降制,皆学士院草词,宣于正衙,近臣、牧伯、皇亲,皆修贡礼为贺,至是真宗不欲令藩臣贡贺,故不降制外廷,止命学士草词付中书。翌日宰臣言:“掖廷加恩,朝廷庆事,臣下不可不备礼物,望令客省依例受贡贺。”诏可。[24]
宋代后妃受封,皇亲与大臣皆进贡礼物为贺,真宗皇帝封杨氏为淑妃,虽欲避免贡贺,但宰臣们仍坚持庆贺,而得到准许。这种类似的庆贺之事甚多,宫中妃嫔可以收受许多礼物,而臣僚们亦以此作为进取的机会。此类事正史不载。
关于祭祀火神。传说古代炎帝以火名官,春官为大火,后以大火为上天掌火之神。宋仁宗康定元年(1041年)南京(河南商丘)鸿庆宫神御殿发生火灾。太常博士集贤校理胡宿是通晓阴阳五行灾异之学的,他上书仁宗皇帝:
窃闻南京鸿庆宫灾,此上天示变以告人主。……臣谨按:《春秋》士弱对晋侯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陶唐之火正曰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大纪时焉。说曰:火正谓火官也,掌火星,行火正,后世以为火祖。相土契之曾孙,代阏伯,后主火星,宋其后也。按商丘在今南京,太祖皇帝受命之地,当房心之次,以宋建号,用火纪德,盖取于此。至真宗皇帝,始升建京邑,号为三都,则阏伯之神,上祀大火,国家之兴,实受其福,至于祀典,大宜超异。……比年国家数有火灾,宜遣使告谢,因饰祠宇,以申严奉之意。[25]
仁宗皇帝下诏由礼官讨论,礼官详细陈述了祭祀大火之礼及其意义,支持胡宿之议。关于朝廷祭祀火神 ,联系星变灾异,纯属妖妄迷信的荒诞行为。礼官们竟引经据典大谈祭祀礼仪,而帝王亦相信火灾与火神是有联系的,只要敬奉火神便不会有火灾发生了。《宋史》卷一百六于“大火之祀”仅言胡宿请修其祀,未录奏议。
关于宗庙祭祀差遣行事官。朝廷每当有宗庙祭祀活动,临时差遣朝臣担任行事官,负责整个祭祀活动的组织安排事务;但朝臣们不愿担任此职,总是借故推辞。宋太宗淳化元年(公元990年)正月水部员外郎直史馆同主判宗正寺赵昴奏言:
窃见宗庙祭祀奉敕差摄行事官,领命之后,多至受警戒日,辄称疾不赴,遂至享祭之时,员多通摄。况大国之事,祀典为先,苟循私心,恐不副朝廷之意。欲望今后差祠祭行事官,如实患者,以状上中书,乞具奏闻,遣使臣官验视,如涉虚诳,请行降黜,庶惩旷慢,用致斋恭。[26]
太宗皇帝接受此建议并付诸施行。此事表明朝廷虽然依照礼制规定非常重视宗庙祭祀,但朝臣们实际上不愿担任行事官之职,并不支持祭祀活动。帝王的宗庙祭祀实为一种礼仪形式,乃帝王及朝臣皆勉强从事的虚饰而已。
关于祭祀高禖。古代帝王相信存在一种媒神主管世间婚姻子嗣。当无子嗣时便可祭祀媒神而得到子嗣。为了使此神显得神秘,便改“媒”为“禖”,而且以之为“高禖”。景祐四年(1037年),因宋仁宗无子嗣,朝臣特请求祭祀高禖:
殿中侍卸史张奎言:“陛下春秋鼎盛,未有皇嗣,谨按《月令》仲春燕至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此先王求嗣之祭。愿有司准旧仪:天子恭行时祭,祈天赐美,承万世之业。”诏有司详定以闻。礼官以谓:“时《月令》虽可依据,然《周官》所载,独阙其文,则成康(西周)之时已废而不享。《月令》本秦呂不韦所集,疑此乃夏商所行。班固《郊祀志》(《汉书》)言汉宗祠祭最悉,不及禖祀。独《权皋传》曰“立皇太子禖祀”,则(汉)武帝乃一时之权,非经也。……陛下裕神训恭,稽古是式,垂采末议,图复旧章,然高禖之礼禋晦已久,今欲复之,则当筑坛于南郊,春分之日,以祀青帝,本诗人克禋以祓之义也。”[27]
礼官们对高禖之祀作了考察,以为古礼中并无此记载;汉武帝虽有此祀但乃权宜,并非常制。唐明皇也曾祭祀,但《大唐开元礼》不予记载。这已说明高禖之祀不合礼法的。如果仁宗皇帝要采用非根本的不重要的事例,也可以筑坛祭祀。仁宗皇帝求嗣心切,不顾礼法,仍然下诏在南薰门外筑坛祭祀。庆历二年(1042年),仁宗仍无子嗣,于是又祀高禖,《太常因革礼》引用《庆历仪注》详述了祭祀的过程。关于是否设弓韣和弓矢(象征受孕)的问题,博士余靖和礼官们又进行了一番议论,坚持尊循古典。《宋史》卷一百三记祀高禖事仅摘录庆历二年之祀一段,未载景祐四年礼官之议。《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之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这是祀高禖之始。姜嫄,传说为上古炎帝之后,高辛之妃。她祀天于郊求子,先媒配而有子嗣。朱熹对此解释说:“姜嫄出祀郊禖,见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于是即其所大所止之处而震动有娠,乃周人所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礼,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诗,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于天,固有以异于常人也。然履迹之说,先儒或颇疑之。”[28]周王朝编造了姜嫄于郊外履迹而受孕遂诞生了周之祖先的神话。后世帝王于郊外祀高禖则是相信神话发生的奇迹,实属荒诞愚昧,自来为真正的儒者所否定和批评。
关于郭皇后的庙议。天圣二年(1024年)九月,在章献太后的主持下,将中书令兼尚书令郭允恭之女立为仁宗皇帝的皇后。仁宗本不喜郭氏,而欲立张美人为后,故婚后对郭皇后甚为疏远。明道二年(1033年)某日宫中尚美人和杨美人因获得宠幸,与郭皇后忿争。尚美人语涉侵凌皇后,皇后去打尚氏耳光;仁宗前去救护,于是被批面颊。仁宗大怒,与入内都知阎文应谋划废后。此事得到宰相吕夷简的支持。十二月,郭皇后被废,封为净妃,以玉京冲妙仙师入道居长宁宫。景祐元年(1034年)八月,郭氏出居安和院,次年十月迁居于嘉庆院,暴卒,时24岁。当时传闻是由阎文应将郭氏毒死的。十二月仁宗诏以皇后之礼安葬。郭氏既然以皇后之礼安葬,但册文却仅书“故郭氏”,而且停止谥册,其神位不许进入祖庙。关于郭皇后神位是否应入祖庙,朝臣及礼官们多次讨论,是为庙议。《太常因革礼》关于郭皇后之庙议记载最详,近三千字。景祐三年(1036年)正月秘书丞余靖奏言:
伏睹废后郭氏诏令候葬日约用后礼者……而铭旌但书“大宋汾阳郭氏之柩”,诸般文书亦只称“故郭氏”,名轻礼重,臣窃惑之。……臣窃以郭氏作俪宸严,早经庙见,出宫之始,犹处次妃,今若特推天慈,追复位号,易名而葬,申之厚礼,则器服不虚,情理两得,俾营魄有托,天下知仁,不亦善乎![29]
余靖指出册文书“故郭氏”而以皇后之礼安葬,这是名轻礼重,名实矛盾,于礼仪不合,请为改正。仁宗皇帝对此奏议不予回答。正月二十三日,仁宗诏令“郭氏已降制命,追册为皇后,其谥册祔庙并停”。嘉祐三年(1058年)十月二十三日,朝廷依敕文准备于景灵宫为郭皇后设灵堂,翰林学士判礼院欧阳修表示反对。次年三月仁宗令礼院讨论,礼官以为郭皇后并无大过,义当祔庙,以正典礼。知制诰刘敞上书反对礼官之议,主张按照原诏书不许郭氏祔庙。八月,礼官张洞奏言:
伏睹刘敞札子,言郭后祔庙不当,令两制与礼官同共定夺。臣详考经传,以历代故事而言之。窃以郭氏正位中宫,母仪天下,逮事先后,亲奉寝园,按于礼法,无大过恶,不应出废,所以名臣感慨,抗论于朝,中外迄今韙之。陛下悯其偶失谦恭,旋亦昭洗,乃复号位。号位既复,则谥册祔庙,安得并停。[30]
张洞之言实为对郭后的公正评价,其间对仁宗表示批评指责,同时反映朝臣及中外人们对郭后的冤屈的同情。刘敞再次反对张洞的意见,特别指出“若不幸而此言传于后,且归过君父,亏损圣德”,意为张洞之言论倘传留后世,人们将见到仁宗的过失,则使圣德亏损。这正揭示了关于郭后庙议长期争论不休的实质。这时距郭后之死已25年了。
以上所举数例应是《太常因革礼》保存的宋代仪制之“不善者”或“不安者”,是苏洵坚持史家之体例,由此体现了其真正的历史与政治的观念。此编虽然为研究中国历史和礼仪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但显示的因革与统治阶级礼仪规范的议论所反映出的政治矛盾和斗争才使其具有丰富的历史意义。
注释: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六,中华书局,1985年。
[2]欧阳修:《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居士集》卷三十四,《欧阳修全集》,世界书局,1936年。
[4]苏洵:《议修礼书状》,《嘉祐集》卷十五,《四库全书》本。
[5]欧阳修:《太常因革礼序》《太常因革礼》,《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6]苏洵:《嘉祐集》附录卷下,《四库全书》本。
[7][9]李壁:《太常因革礼序》,《太常因革礼》卷末附录。
[8]朱熹:《礼序》,《朱熹外集》卷二,《朱熹集》第5758页,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
[10]阮元:《研经室外集》卷二,《太常因革礼》卷首,《续修四库全书》本。
[11]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卷十二,中华书局,1963年。
[12]廖廷相:《太常因革礼校识》,《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
[13]《太常因革礼》卷七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第541页。
[14]《太常因革礼》卷八十,《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第570页。
[15]《太常因革礼》卷三十四,《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冊,第481页。
[16]王泾:《大唐郊祀录》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第269页。
[17]廖廷相:《太常因革礼校识》后记,《丛书集成初编》本。
[18]《太常因革礼》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第363页。
[19]《太常因革礼》卷六十八,《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第526页。
[20]《太常因革礼》卷一十六,《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第411页。
[21]《太常因革礼》卷六十八,《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第530页。
[22]苏洵《嘉祐集》卷六,《四库全书》本。
[23]《太常因革礼》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第392页。
[24]《太常因革礼》卷八十八,《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第599页。
[25]《太常因革礼》卷八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第573页。
[26]《太常因革礼》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第381页。
[27]《太常因革礼》卷七十九,《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第564页。
[28]朱熹:《诗集传》卷十七,中华书局,1980年。
[29][30]《太常因革礼》卷一百,《续修四库全书》第821册,第638页,第640页。
作者: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资深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