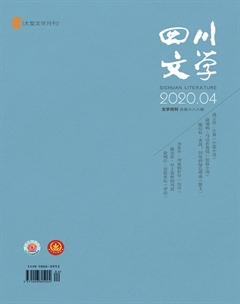村上春树的鸡蛋
陈培浩
1
2009年,村上春树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对于很多村上迷来说,或许是村上春树让他们知道了耶路撒冷文学奖。耶路撒冷文学奖给村上春树的是一个奖,而村上回赠以一个感人至深的获奖感言。这便是很多人所熟知的《站在鸡蛋那边》。无疑,这是一个特别政治正确的获奖感言。村上特别语调铿锵地说:“无论墙有多么的正确,鸡蛋有多么的错误,我会和鸡蛋站在一起。”那么什么是高墙,什么是鸡蛋呢?村上说“炸弹和坦克和飞弹和白磷弹就是那面高墙。而那些鸡蛋就是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他们被炮弹粉碎、烧毁、击中。这是这个比喻的其中一层含义”。当然,这不是全部,村上继续阐释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是一枚鸡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灵魂,而这灵魂覆盖着一个脆弱的外壳。这就是我自己的真相,而且这也是你们每一个人的真相。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程度或轻或重地,都在面对着一面高大的、坚固的墙。而这面墙有一个名字:它的名字叫作‘体制。这个体制本来应该保护我们,但有时它却残杀我们,或迫使我们冷酷、有效率、系统化地残杀别人。”正是在高墙所代表的体制和个人所代表的灵魂的对峙中,村上确认了他写作的意义:“我写小说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给予每个灵魂尊严,让它们得以沐浴在阳光之下。故事的目的在于提醒世人,在于检视体制,避免它驯化我们的灵魂、剥夺靈魂的意义。”很感人!唯一蹊跷的是,这个语调其实是非常不村上的。村上小说的语调是若有若无的性冷淡风。村上的语调不是“非此不可”,而是“或多或少”“可有可无”。村上很少这样说话。他的迷人处在于善于捕捉到生活那种幽微处,那种在放大镜下才纤毫毕现的身体茸毛。幽微处往往不是那么截然。斩钉截铁的东西是放在明面上的,但太截然的话语,很可能会伤害事物的复杂性。这是村上这个发言让我狐疑之处。
这样说吧,在高墙和鸡蛋这个对立极其清晰的情境中,高墙代表了令人憎恶的权力。站在鸡蛋那边就意味着站在正义那边,这几乎是人道主义伦理必然的文学选择。问题是,假如我们有一点现实感的话,就会发现,真正的伦理选择往往是两难选择,而不是高墙/鸡蛋这样的导向清晰的选择。换言之,我们知道要站在鸡蛋那边,可是在生活的层层迷雾中,什么是高墙,什么是鸡蛋?正义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在《正义》课程中提出了一个很折磨人的问题:一辆开着的列车面临着分岔的铁轨,一条轨道上有五个人,另一条有一个人,作为司机的你是将如何选择?你会选择轧死一人而保全五人吧?那你怎么可以确认那个单独的一个人就必须被轧死呢?假如你选择轧死五人而保全一人,那你同样要面临生命的拷问。牺牲一人保全五人,或牺牲五人保全一人,背后都有着各自的伦理立场。哪里会有高墙和鸡蛋那么明显的选择呢?
老实说,在村上春树的作品中,很多时候他也混淆了何为高墙,何为鸡蛋。
2
是的,我要说的正是《海边的卡夫卡》。
毫无疑问,村上春树是当代日本最有世界影响的作家,首先表现在畅销。《挪威的森林》在日本已经畅销超过千万册,2004年单这部作品在中国就已经畅销786万册。村上的作品在中国,没有一部不畅销。村上的每一部新作,都被各家出版社盯着抢着。可是,村上并不满足于成为一个畅销的小资作家。文青们都对村上诸如“我曾经以为人是慢慢变老的,现在我才知道人是一瞬间变老的”这样的小资语录耳熟能详。无疑,村上擅于掏出每个人内心不为人知的那种毛茸茸的触感。可是,村上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国民作家。《海边的卡夫卡》就鲜明地寄托了村上这种国民作家的理想,他由一个十五岁少年的成长出发,而触及了沉重的历史记忆。这是一部充满互文性的作品,互文就是为文本的孤立房间引入诸多可阐释的魔镜。从题目我们就邂逅了“卡夫卡”,这个创造了城堡般的文本迷宫的作家在这里或者意味着少年卡夫卡就像《城堡》里的那个k,何去何从,正是这部小说成长主题重要的提问。据日本文学专家孟庆枢的理解,“卡夫卡”在日文的发音中接近于“可不可”,所以,少年卡夫卡,就是那个在追问“可不可”的人?这个“卡夫卡”的发言中,显然又互文了一个哈姆雷特之问——to be or not to be?
当然不能忽略“俄狄浦斯”这个典型的互文。小说中,卡夫卡少年被母亲和姐姐抛弃,又受到了父亲发出的“俄狄浦斯式”的诅咒。雕塑家田村浩二诅咒儿子,你迟早要弑父娶母,甚至更严重,你连姐姐也要娶了。为逃避这命运,他独自启程前往四国,却在四国的甲村图书馆邂逅了优雅知性的中年女性佐伯(卡夫卡少年在内心把她认同为自己的母亲)、图书馆员大岛(一个跨性别的女性)和青年女性樱花(卡夫卡把她认同为自己的姐姐)。最终,卡夫卡少年邂逅了佐伯十五岁的生魂,并跟现实中的佐伯发生了关系,在梦的想象中强暴了樱花。他因此而完成了“俄狄浦斯式诅咒”。
当然还有更多的互文。比如邂逅佐伯生魂的描写就勾连着日本《源氏物语》代表的“生魂”叙事的传统;卡夫卡少年在甲村图书馆阅读的作品包括夏目漱石的《矿工》,包括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在各种各样的互文中,日本史、远东史和世界战争史被跟个人的成长史穿插拼贴到了一起。
村上春树当然是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这便是小说中的魔幻。理解《海边的卡夫卡》,必须理解村上的叙事虚线。作为一部魔幻色彩鲜明的作品,卡夫卡少年的“弑父娶母”不是在实线上完成的,而是在象征性的虚线上实现的。这就涉及作品中的“人物分身”功能。小说中,中田跟佐伯的一段对话很重要,中田说:
跟您说实话,中田我在中野区杀了一个人。中田我是不想杀人的,可是在琼尼·沃克的促导下,中田我替一个应该在那里的十五岁少年杀了一个人,而那是中田我不得不接受的。
这里涉及两个人物分身,琼尼·沃克作为田村浩二的分身,而中田作为卡夫卡少年的分身,因此,小说暗示了,中田杀死琼尼·沃克其实就是卡夫卡少年的“弑父”。小说正是在“分身”这道虚线上完成了“弑父”这一诅咒。事实上,所谓的“娶母”同样是在想象性的虚线中完成的。我们不禁要问,村上非常复杂的双线、分身、虚线构成的魔幻迷宫究竟要干什么?对于通俗文本而言,魔幻本身造成的悬疑性和可读性就是意义本身。但对于严肃文学来说,这是不够的。村上当然也知道,用魔幻的虚线来执行叙事,这不是他的发明,这是他对鬼怪小说的借鉴。问题在于,一般鬼怪小说的借尸还魂在村上这里获得了新的象征性表达,并完成了村上想要完成的精神叙事。
这就要说到这部小说中非常重要符号——“入口石”。入口石是魔幻无比的,从情节层面,中田老人冥冥中被引导向四国的森林,去把那块被打开的入口石关上,入口石是连接另一个世界的通道,卡夫卡少年也在星野的引导下游历了另一个世界。可是在作者所要进行的象征表达层面上,入口石还有更深的含意。这里需要注意到佐伯对中田所说的一段话:
佐伯闭起眼睛,又睁开来注视中田:“那样的事情是因为我在久远的过去打开了那块入口石才发生的吧?那件往事到现在还到处导致许多东西扭曲变形,是这样吗?
在中田自述杀死琼尼·沃克之后,佐伯把这一切的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佐伯的逻辑是什么?
我出生于离这里很近的地方,深深爱着在这座房子里生活的一个男孩儿,爱得无以复加。他也同样爱着我。我们活在一个完美无缺的圆圈中,一切在圈内自成一体。当然不可能长此以往。我们长大成人,时代即将变迁,圆圈到处破损,外面的东西闯进乐园内侧,内侧的东西想跑去外面。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未能那样认为。为了阻止那样的闯入和外出,我打开了入口的石头。而那是如何做到的,现在已记不确切了。总之我下定决心:为了不失去他,为了不让外面的东西破坏我们两人的天地,不管发生什么事物都要把石头打开。至于那意味着什么,当时的我是无法理解的。不用说,我遭受了报应。
对我来说,人生在二十岁时就已经终止了。后面的人生不过是绵延不断的后日谈而已,好比哪里也通不出去的弯弯曲曲若明若暗的长廊。然而我必须延续那样的人生。无非日复一日接受空虚的每一天又把它原封不动地送出去。在那样的日子里,我做过很多错事。有时候我把自己封闭在内心,就像活在深深的井底。我诅咒外面的一切,憎恶一切。有时也去外面苟且偷欢。我不加区别地接受一切,麻木不仁地穿行于世界。也曾和不少男人睡过,有时甚至谈婚论嫁。可是,一切都毫无意义,一切都稍纵即逝,什么也没留下,留下的唯有我所贬损的事物的几处伤痕。
联系到小说中的生魂,以下的猜想应该是成立的:入口石被打开之后,佐伯的生魂就被存到了另一个世界,只留下了行尸走肉的躯壳在世上行走。
佐伯在小说中其实是作为反面典型存在。少年卡夫卡在寻找成长,而将躯壳和生魂剥离出来的佐伯显然是反成长的。当她受到伤害之后,她的选择不是在生生不息的生命流程中消化痛苦,而是制作一个生命的琥珀——生魂。什么是生魂?生魂就是拒绝成长的灵魂,所以少年卡夫卡会邂逅佐伯十五岁的生魂。生魂就是以终止灵性成长为代价来使某一瞬间永恒化。自杀是制作生魂的最极端形式。当生命中止,灵魂就被永久地停留在那一刻。村上春树借用了一个形象化的表达——入口石,当入口石被打开,生魂被存放了进去,无疑,入口石的打开代表了一种反成长的生命姿态。这是何以五十岁的佐伯会用忏悔的语调来陈述入口石,也是何以中田被一种力量引导到四国,要找到那块打开的入口石,并把它关上的原因。它们都包含了村上春树对反成长姿态的批判性态度。
我们会发现,中田在某一刻成了少年卡夫卡的分身,但他却和佐伯构成了对位关系,他们对位于一种“半人”的生存。你会发现,中田的“失忆”和佐伯的“生魂”恰好是各自作为“半人”的生存方式。失忆其实就是生魂的丢失,中田和佐伯为何都跟入口石联系在一起,就因为他们的现世只剩下躯壳,他们的生魂都被存放在入口石打开的另一世界。剩下躯壳的问题就在于,他们的身体成了各种力量争夺的对象。中田被琼尼·沃克所代表的邪恶力量所操控,而佐伯則被图书馆所代表的文字世界所占据。他们冥冥中都在对抗这种力量。最终中田杀死了琼尼·沃克,标志着村上对于被操控的生命摆脱操控的期待。显然,在他看来,被暴力之魔操控的生命是不值得期待的,而沉溺于一种纯粹由书本构成的记忆世界也是值得怀疑的。小说中,少年卡夫卡是一个行走在边界的人物,他徘徊在入口石分割的现实世界和另一世界之间,他邂逅生魂,又留连于图书馆的世界中,他既可能陷于琼尼·沃克代表的邪恶世界,也可能陷于图书馆代表的生魂剥离之后的文字世界,这是两种行尸走肉的世界。小说作为成长小说的实质正在于对这两种危险的超越。
有意思的是,小说通过中田-佐伯、田村浩二-少年卡夫卡这三代人,并置了三代日本人在面对历史、时代和命运重负中的精神困境及各自脱困之路中迷雾。中田是被战争的历史记忆所伤害的一代人,代表了一种在历史中陷落,成了某种邪恶话语俘虏的道路;佐伯和田村浩二则是在196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日本人,伤害他们的是时代的凶险波澜,他们的灵魂都被封存于另一世界。而少年卡夫卡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处在佐伯当年生魂脱离的年龄,面对了命运的诅咒,在此他代表了最年轻的日本一代,他们将何去何从?将俄狄浦斯诅咒作为一个最古老的命运隐喻镶嵌进他的生命,暗示了村上春树对于生命的理解:每一代人都有着从历史中绵延过来的重负和困境,就像俄狄浦斯所面临的命运一样。我们该如何去面对?正是在这里,展示了小说典型的疗愈功能。
我们看《俄狄浦斯王》会发现,俄狄浦斯不断在逃避和对抗着这种命运,却最终成了被命运碾碎的齑粉,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命运的悲剧感。悲剧之美就在于人在捍卫自身的过程中最终的无能为力。可是,村上春树并不想复写一个古希腊悲剧。值得一提的是,中外文学史上俄狄浦斯式的悲剧比比皆是。比如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当然命运悲剧在《麦克白》中被转化为欲望和恐惧的悲剧,人无法抵抗欲望和恐惧的侵蚀而终为齑粉。又如金庸《天龙八部》中的乔峰,都是俄狄浦斯式的人物。可是,村上不想让少年卡夫卡成为俄狄浦斯的现代回声。不想让他陷落命运的罗网,他要让少年卡夫卡逃出生天,在凶险的命运面前获得生命的成长,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坚强的十五岁少年。当然,最后少年卡夫卡被想象性地疗愈了。村上的药方很有趣:迎着诅咒走上去,让它发生,让它过去。你不是有弑父娶母甚至娶姐的诅咒吗?那么,我不逃避,我甚至主动让它发生。我也绝不让生命被创伤剥离了生魂,从此行尸走肉。当我迎着诅咒走下去的时候,灵魂依然内在于我,恐惧被战胜了,我继续走下去!村上一再强调世界是作为一个隐喻存在的,而它对生命困境中的抉择也是以隐喻的方式完成的。
顺着上面的思路理解村上及其《海边的卡夫卡》,我们会发现村上建构的世界图景既魔幻又梦幻,它梦幻得简直是镜花水月。在村上的逻辑中,被诅咒的少年卡夫卡当然就是他文学价值观中的那个鸡蛋,他拯救了少年并提供了一张疗愈的药方,可是问题或许没有那么简单。鸡蛋或许没有那么容易被找到。
3
要说到小森阳一和他的《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了。这本书为什么有趣?它是当代最有名的日本文学教授对当代最有名的日本作家发出的最有耐心又严厉的批判。小森阳一最不能接受的是,村上在小说中对于历史记忆所做出的激发然后又割断的“疗愈”式处理。这部论著既有精彩的细读,又把写作引入到很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分析,相当令人信服。我想先说说“疗愈”作为一种文学观在村上文学中的出现。我们会发现,在此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朝向伟大的写作是以疗愈为诉求的。就说《俄狄浦斯王》吧,它是典型的悲剧,悲剧泄漏了命运的秘密又确认了人的尊严。它并不相信人可能得救,但相信人在不可能的命运之前的搏斗。搏斗越激烈,尊严越可敬,人被碾碎的刹那才越有悲剧感,这是悲剧迷人之处。但并非所有的作品都为了展示悲剧,像卡夫卡的《变形记》这样的作品,它的功能主要是发现或所谓预言。在绝大部分尚未意识到世界已经“变形”或者异化的时候,卡夫卡率先发现了这种变形并将其雕刻出来。对于现代主义作品来说,发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使被遮蔽于未明的东西被说出,给它一个鲜明可感的文学形象,这个东西可能是“第二十二条军规”,可能是精神的异乡感(《局外人》),“发现”对于文学的意义同样非同小可。事实上,提供一种精神价值也是文学重要的功能。鲁迅的《野草》就是这样的作品,《野草》不但有很强的发现能力,它为生命的诸多悖论赋形,“黑暗会吞噬我,而光明会使我消失”通过影子说出了生命的进退两难。但更重要的是,《野草》提供了一种在绝望中反抗绝望的精神价值。《悲惨世界》《约翰·克利斯朵夫》《老人与海》都是提供精神价值的作品,它们要么是悲悯成圣、要么是扼住命运的咽喉、要么是“可以被摧毁,但不能被打败”,这都是长久地激励着人类的精神价值。这一比较我们就发现,《海边的卡夫卡》并不提供悲剧美——它拒绝使少年卡夫卡被命运所压倒;不提供对生命困境的发现——所谓俄狄浦斯的诅咒本质上是抽象而非现实的,它很难跟我们实际的生存困境相关联;也不提供什么精神价值,虽然作者要把少年卡夫卡塑造成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可是由于他的生活基本上是在某种隐喻的逻辑上行进,他的顽强也显得十分抽象。与其说它提供了一种精神,不如说它提供了一张药方,一种在历史和命运的阴影中坚强活下去的方法。问题是,这张虚构的药方真的有效吗?
这里必须说到一个重要的区分,寓言型文本和现实型文本的差异。老实说,村上想赋予《海边的卡夫卡》的精神叙事如果在纯隐喻和寓言意义上,我们即使有质疑也是技术层面上的。但村上一面宣称身体是盛放隐喻的容器,但这部作品却充满着强烈的现实和历史动机,换言之,这是一部企图为历史和现实寻找隐喻的作品。从小说中引入的那么多具体翔实的历史事件及历史文本即可看出,其意不仅在讲述一个人生寓言。问题是,历史记忆可以被无条件地进行寓言化处理吗?
中田失忆事件被村上跟具体的历史背景关联起来,但最终这个背景又被模糊化,从而实现了他的“创伤与解离”的疗愈功能。此一点,小森阳一有非常精彩的分析,下面出自小森阳一的分析。小说中,中田的失憶被赋予了非常具体确凿的时间——1944年11月7日。这个时间节点毫无疑问地打开了通向历史的可能,但更具体的历史又是模糊的。叙事使中田的失忆跟冈持老师有了更直接的关联。小说以冈持在事件发生后的二十八年后写下的一封书信的形式交代出事情的细节:“去郊外采蘑菇的前一天晚上,冈持老师做了一个和已出征的丈夫发生性交合的梦。这一天进入森林后她突然来了月经,处理经血的手巾被‘中田君发现并拿在了手上,冈持老师便突然殴打了他。同班学生目睹了‘中田君失去意识的一幕,然后集体陷入昏睡状态。”(小森阳一《精读海边的卡夫卡》)没有任何医学证据证明中田的失忆跟冈持老师的殴打有直接关系,冈持老师在信中也提到了一年后在菲律宾参战的丈夫的阵亡:
我丈夫于战争即将结束时在菲律宾战死了。说实话,我未受到太大的精神打击。当时我感觉到的仅仅、仅仅是深切的无奈,不是绝望不是愤怒。我一滴眼泪也没流。这是因为,这样的结果——丈夫将在某个战场上丢掉年轻生命的结果——我早已预想到了。在那之前一年我梦见同丈夫剧烈性交,意外来了月经,上山,慌乱之中打了中田君,孩子们陷入莫名其妙的昏睡——事情从那时开始就已被决定下来了,我已提前作为事实加以接受了。得知丈夫的死讯,不过是确认事实罢了。我灵魂的一部分依然留在那座山林之中,因为那是超越我人生所有行为的东西。
这段话中冈持古怪的自罪逻辑跟佐伯的自罪如出一辙,冈持将非常具体历史事件的战争创伤作为自己“月经”“性梦”和“施暴”的报应,我们很难把这当作村上对战争扭曲人性的批判。根据大冈升平的《莱特战记》,1943年11月7日,冈持殴打中田的这一天,正是在这一天,身为大元帅的天皇为了顾及体面,做出了导致“众多将士无谓丧命”的战争决定。换言之,导致冈持丈夫战死的原因跟冈持毫无关系,小说却在毫无历史语境的前提下将它联结到冈持的性梦和月经布被发现而产生的施暴行为上。不难发现,《海边的卡夫卡》极大地强化了作家的虚构特权,对于很多问题,小说与其说不予解释,不如说根本就是由于缺乏逻辑而没有答案。假如说我们可以辨认出冈持老师丈夫死亡的真实原因,但我们却无法说出中田失忆的现实原因。如果强行解释的话,那只能是,他象征了被战争间接伤害的一代,战争伤害了冈持而间接伤害了他。如果由此出发不能生发出非常深刻的反战主题。偏偏村上其意并不仅在反战,而是为被种种创伤所禁锢者解离。因此,战争、失忆等等行为脱离历史语境地跟一个普通妇女的性梦联系在一起,使得历史分析失焦,反而呈现出非常陈腐的对女性性想象的嫌恶气息。
在我看来,《海边的卡夫卡》暴露了村上非常混乱的历史观、性别观和正义观,这种混乱跟他在耶路撒冷文学奖授奖词上庄严得有点斩钉截铁的回答实在不匹配。
不妨再说说上引那段佐伯跟中田的对话,它包含着小说叙事和精神叙事的诸多关节。正是佐伯的陈述和忏悔廓清了一条被否定的道路,它的价值就在于作为一个陷阱提醒少年卡夫卡此路不通。问题在于,佐伯为何要忏悔?当中田说到他替代一个十五岁少年杀死了琼尼·沃克的时候,佐伯匪夷所思地把一切的罪责揽于自身——正是因为我打开了那块入口石,世间的很多扭曲还在发生。从上下文看,村上强化而不是反对佐伯的自罪。假如我们强行给佐伯的自罪做一点解释的话,逻辑可能是这样的:由于佐伯年幼无知,打开了入口石,十五岁的生魂被存放另一世界,只留一个行尸走肉的躯壳在世上——用躯壳与田村浩二相遇的佐伯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丈夫,她带着女儿,抛下丈夫和儿子远走加剧了田村的创伤——田村浩二显然也是一个沉溺于创伤中的“半个人”,灵魂的丢失使他被琼尼·沃克所寄身,也使他成为杀猫来收集灵魂的人(请想一下,丧失了文字能力的中田获得了跟猫对话的能力,他在杀死了寄身于他的琼尼·沃克之后突然丧失了这种能力,猫在这里显然被赋予了跟入口石关联的另一世界莫大的关系)——田村把创伤加诸少年卡夫卡,对他发出俄狄浦斯式诅咒——为了逃避诅咒少年卡夫卡独自上路来到四国甲村图书馆,邂逅佐伯……按照这个逻辑来看,打开入口石的佐伯当然是今天这一切的“罪魁祸首”,问题是,佐伯真的该为当年的历史创伤负责吗?我们注意到佐伯说“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事,然而当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未能那样认为”,她幼稚就在于把“理所当然”的事情视为不可接受。可是,请回到事件那里。一群学生受到了围攻(村上在此进行了非常模糊的处理)佐伯的爱人前去为受围攻的同伴送食物,然后被围攻致死。不管具体的暴力事件如何被抽象化模糊化,但抹去制造暴力和创伤的现实源头,把创伤的女性承受者视为日后世界诸多扭曲的根源,这种“厌女症”的还魂,落在一向思想开通多元的村上君身上,还是颇让人意外的。一个女人被强暴,在男权主义的厌女症文化中,她的创伤成了她的罪责。这个简单粗暴的原则被村上移花接木乔装打扮之后,放在了佐伯的身上。村上很少显露出明显的性别歧视,即使是写到“雌雄同体”的大岛时,也貌似对这种不合常规的身体观毫无偏见。可是,《海边的卡夫卡》中代表整个民族去迎接自我成长、催生崭新主体的毕竟是男性。而女性,无论是樱花和大岛却都丧失了主体性,沦为一种功能性的存在。甚至于,她们就是用身体来启蒙卡夫卡少年。她们泅渡少年卡夫卡的孤独和性闷,这个时候,她们是所有十五岁男孩完美的欲望对象和精神向导,她们可以谈心,又随时可以和十五岁的少年共赴被窝,即使面对强暴的现实,说出的也是温柔的“你确定要这样做吗?”唯独无法察知她们精神的来龙去脉,她们的欢乐痛苦,她们的困境和难题。“我写小说就是要给每个人物尊严”,我不知道抽象无比的大岛樱花的精神尊严何在?她们作为一枚鸡蛋为何没有得到村上君的呵护呢?
樱花被少年卡夫卡强暴这个情节(即使它只发生于想象中)显得如此刺目,它既显示了村上将女性身体作为男性成长中介的逻辑,也显示了村上对于各种形式的暴力毫无条件地接受。小说的成长主题端赖于一个逻辑前提:对俄狄浦斯魔咒的超越。可是少年卡夫卡超越俄狄浦斯魔咒却是以将女性身体中介化和对暴力的无条件认同为前提。这就使得它的成长、疗愈和超越变得十分可疑。
现在重点说一说对暴力的无条件认同,这并非说村上主张暴力,而是村上倾向于将各种形式的暴力作为一个无法拒绝的结果接受下来。逻辑是这样的:既然弑父娶母娶姐必须发生,那么就主动让它发生,即使遭到樱花拒绝也不能止步,即使诉诸暴力也在所不惜。村上恰恰忘记了,他把少年卡夫卡当成了所有人的全称代表,却忽略了他在伸张主体性穿越自身魔咒的同时,恰恰是以践踏她人主体性为前提,因而代表的只能是他自己而不可能是所有人。作为旁证,不妨看看中田是如何描述他杀死琼尼·沃克的,“那是中田我不得不接受的”。这里典型地暴露了村上价值观的混乱,虽然这种无可无不可的被动姿态相当符合中田作为智力有所欠缺者的形象,但是它彻底消解了小说在面对暴力问题上所可能秉持的“正义”立场。(完全不要忘记,所谓高墙和鸡蛋的择边问题,正是一个正义的伦理问题)本来,以残忍的虐猫者形象出现的琼尼·沃克被杀死,邪恶者本身的形象有可能抵消暴力行为的不正义性。但是,村上选择了瓦解这种立场,中田并无能力做出选择,不管事情结果的正义与否,都不是他的主观意愿,换言之,作为少年卡夫卡的弑父行为乃是其强烈主导性的结果,他主动对暴力方式的接纳和中田被动对暴力的接纳事实上都在申明一种逻辑:暴力作为一种邪恶既然是不可抗拒的,要么主动接受它,要么被动接受它,反正它必然发生。假如说这是村上对世界的“发现”的话,这真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细思极恐的判断,因为它并非是对世界的客观描摹,而是包含了鲜明价值选择的现实判断。所以,我们再看一下琼尼·沃克这一形象,这个扭曲的邪恶者藏入中田体内,引导着中田把自己杀死,我们可以说琼尼·沃克是一个代表了他杀和自杀双重邪恶本能的符号。看到村上的这段话,就会发现邪恶是他一直思考的问题:
往下我想在小说中写的还是关于恶的,想从各个角度去思考恶的表现和形态,下回我想写既是象征性的又有细部现实感那样的恶,归根结底,恶这个东西并非独立存在的,而同卑鄙、怯懦、想象力匮乏等质素联系在一起的。
这段话发表于《海边的卡夫卡》出版之后,2003年,村上接受《文学界》采访时再次表示:“关于恶我始终都在思考,我认为,为了使我的小说具有纵深感和外延性,恶这个东西恐怕还不可缺少的,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描写恶。”可见,琼尼·沃克事实上是村上持久思考并用以表现恶的符号。我们再看一下琼尼·沃克与中田的对话,他对老实懵懂的中田说:要么你杀死我,如果你不杀死我,我就会继续虐杀猫。这句话典型地体现了他杀和自杀双重本能。令人不安的是,顺着琼尼·沃克的判断,不管采用哪种方式,最终胜利的都是暴力。换言之,即使琼尼·沃克被杀死了,也并不代表着邪恶被制止。中田不过是以琼尼·沃克所可预见的暴力方式终结了他的某种生命形式,这种终结反而使他代表的邪恶和暴力得到了再一次的重申。可见,对于人在邪恶和暴力面前的能动性,村上是非常悲观的。令人奇怪的是,他一方面把人的伦理能动性做了如此消极的处理,何以对佐伯的能动性又那样苛求呢?何以他居然会觉得作为暴力受害者的佐伯不能从创伤中痊愈而选择了剥离生魂的逃避形式,就必须为世界的扭曲承担罪责呢?这种自我矛盾和双重标准充分暴露了《海边的卡夫卡》疗愈的虚拟性和想象性。不断通过画虚线来强行画圆的叙事和精神叙事终究经不起推敲,在历史、暴力、性别问题上,村上一点不像他语调铿锵所宣称的那样永远站在鸡蛋一边。不是说他赞同体制选择高墙,而是说在这个迷雾重重的世界上,村上有时也会错把高墙当成了鸡蛋。
村上小说在叙事上有着可怕的迷人之处,即使是中田这样的憨傻老者都会写得妙趣横生。但这种迷人的叙事迷宫事实上掩盖了村上历史观、价值观上的混乱之处。一般读者并无兴趣和耐心去將其迷宫的来龙去脉条分缕析,只能顺着他架设的种种魔幻逻辑往下走,进而丧失了批判性的阅读,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植入历史又解离记忆的逻辑,确乎获得了某种想象性的疗愈效果。这样说,村上的作品其实是深度催眠的。若没有高度反催眠的阅读,很容易就找不着北而着了道。伟大的文学作品的精神力量来自对伟大价值的发现和捍卫,它跟村上这种将阅读主体导入迷宫绕晕,然后给出一个想象性的解脱有本质区别。前者是道,后者是幻术。
责任编辑 冉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