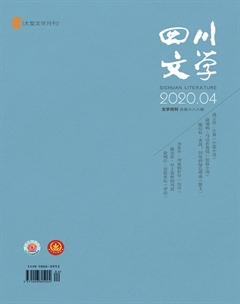短篇要短
徐则臣
1
《胡安·鲁尔福全集》(屠孟超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版)短篇小说部分《烈火平原》中,除了同名短篇《烈火平原》和《安纳克莱托·蒙罗纳斯》两篇字数过万,其他十五篇没一个超过八千字。《你没有听到狗叫吗?》还不是最短的,《你该记得吧》加标点满打满算也就2300字。短是我喜欢胡安·鲁尔福短篇小说的原因之一;短而精是我喜欢胡安·鲁尔福短篇小说的另一个原因;短而精且质朴和变化多端,于是在所有短篇小说作家中,我忠贞地喜欢了胡安·鲁尔福二十年,若无意外,还将继续忠贞地喜欢下去。在我看来,胡安·鲁尔福几乎具备了我理想中的短篇小说作家的所有指标,唯一的遗憾是作品数量太少,《全集》里也就17篇。
短篇要短,正如长篇要长。短和长既是它们作为一种文体的规定性,即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是其所是”,也是其作为一门艺术的限定性。它们需要在各自的尺度内完成只有自己才能完成的艺术探索。短篇之于长篇,正如匕首之于长矛,功能不同,活动半径不同,操作方法也有所区别;匕首不是截短了的长矛,短篇也非压缩了的长篇。我们习惯于礼赞某某短篇的容量巨大,美其名曰:这是个良心短篇,完成了一个长篇的任务。对此我一直存疑,若果真实现了这个任务,要么说明作为参照的长篇有问题,要么该短篇有问题。短篇是激流遭遇险滩,是靶心穿过了利箭,是大风起于青萍之末,是走索艺人高空中趔趄的那一下闪失,是寻常生活中的惊鸿一瞥、惊心动魄和面对一朵花盛开的会心微笑。而长篇是从容浩荡的生活本身。
唯有短,尽可能短,才能更加凸显一瞬间的激越和芳华,如同焰火喷薄而出,生死相依。唯有短,尽可能短,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创作者的艺术潜力。何为袖里乾坤?何为让更多的天使来针尖上跳舞?短篇应该是小说写作的一种极限运动。我常常想起中学物理课本中学到的压强。力不变,要让压强增大,怎么办?答案是:减少受力面积。一个作家的创造力很难在短时间内飞涨,要让创作产生更大的艺术冲击力,怎么办?缩短篇幅,删掉那些无效的、半有效的文字。节俭篇幅并非只带来整体瘦身的效果,它还强迫你改变创作方法、矫正你看待问题的角度乃至你的文学观。我相信一万字能讲清楚的故事,四千字应该没有理由一定讲不清楚;我也相信一旦你能用四千字把过去一万字的故事讲清楚了,那么这两个故事既是同一个故事,也一定不是同一个故事。对一个作家如此,对文学来说也如此。所以,短篇中其实必然包含了小说创作的炼金术,在可能的尺度内,它希望自己短、再短、继续短,它要求我们想办法节制、节制、再节制,节制的同时别致和及物。
2
《你没有听到狗叫吗?》加上标点也就2600字。故事很简单:父亲背着垂死的儿子翻山越岭去找医生,因为担心放下后再也背不起来,坚决不让儿子下来,父亲一直咬牙撑着。但他需要信心和希望,就不断问儿子,你看到那个村庄了没?你听到狗叫没?尽管月光明亮,夜幕下的村庄依然可能模糊不清,狗叫却是可以远远就能听见的。但儿子说,没看见那个村庄,也没听到狗叫声。父亲一路咒骂着不孝之子,在绝望中奋力前行。天可怜见,总算看见村庄就在眼前,月光下的屋顶闪闪发亮,狗吠声四起,而此刻,混蛋儿子还是一声不吭,甚至当他把儿子放下时,儿子的双手还紧紧地抱着他的脖子。这哪是亲生儿子,完全是个讨债鬼。所以小说结尾,父亲说:“你刚才没有听到狗叫吗?你连这点希望也不想给我。”
多像漫长电影中的一个片段。掐头去尾,就留着中间一段父子跋涉。如果是长篇,那父子和整个家庭的前生今世都会交代清楚;时代背景、社会现实、乡村景致、儿子混蛋到哪个地步、医生所在的村庄如何遥远,凡此种种,就连儿子跟人打的那场群架,可能都得一一道来。但短篇不需要,摄像机只要跟着父子俩,正打、反打,你一句我一句,在对话中必要的信息就全交代了。偶尔镜头一抖,照见了月光下的夜晚和漫长的道路,画外音都极少。但在对话中,我们足可以知道事情的原委:儿子的确不是个东西,拦路抢劫,以窃为生,杀人,关键是杀好人,连给自己洗礼的教父也不放过。好在他母亲死了,要不活着也会被气死。父亲坚持救儿子,不是因为父子连心,而是因为亡妻。“您已经不是我的儿子了。我已经诅咒过您从我身上继承的血液,属于从我那儿继承去的那部分血液已经被我诅咒过了”。当父亲对儿子称“您”时,父亲的愤怒和绝望就可想而知了。他对儿子说,真不是老子想救你,“是为了您死去的母亲,因为您是她的儿子”,如果不“送您去就医,那她定然会责怪我的”。可怜他的母亲,还“指望你长大后一定会使她有所依靠”。
儿子的回答全篇也没几句,且都惜字如金,不是直接绝了当爹的念想,就是提各种要求。你看到什么地方有灯光了?“我什么也没有看到。”“我还是一无所见。”“我累了。”你觉得怎么样?“不好。”你痛得很厉害吗?“有点儿痛。”“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口渴。”“给我点水喝。”好在中间有几次希望父亲放下自己,还算说了两句人话。
不过全天下的父母都一個样。这个墨西哥的父亲听上去嘴挺硬,一会儿“您”,一会儿看在亡妻的面子上,其实对不孝之子还是一肚子关爱。儿子不说话,他只好一个劲儿地说;儿子说得少,他只好多说。一则,他需要制造点动静给自己鼓劲,否则单调疲惫的负重前行很可能撑不到底;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通过说话这点他唯一能够制造出的动静,把儿子从死神那里拉回来。儿子受的是重伤,迷糊过去可能就回不来了。为了刺激儿子,他把死去的妻子都请出来了,负疚的儿子会因此保持更清醒的生命意识吗?他很可能已经预感到结局并不乐观,但作为父亲,出于本能,他也得尽一切努力。也许这一路上根本就不会听到狗叫、看到村庄,但他必须不停地挑起话头。不一遍遍问到了吗,他又能说什么呢?当然,他也在分散一下注意力,给自己壮壮胆,驱赶不祥的预感。如同走夜路要大声歌唱。
照这个思路反观儿子,也许年轻人并非人性全无。不给父亲希望,固然可能源于习惯性的冷漠与恶,也可能的确打算就此决绝地断其父的念想:反正命不久矣,何烦父亲再劳心劳力地跑这一遭。他虚弱地伏在父亲背上,唯一有力气做的阻止和反抗就是寡言少语,和不给乃父任何希望的冷漠。父亲说到亡妻时,愿她安息,“他觉得被他背着的人脑袋在晃动,像是在流泪”。当爹的此时肯定感到了一点安慰和温暖。当然,晃脑袋也可能不是在流泪,而是人死了。他“渴得很,也困得很”,这正是死亡的征兆。小说结尾,儿子抱着他脖子的手指僵硬得他要费劲才能分开,年轻人或许已经离开了人世。
依然是小说结尾,到达医生的村庄,放下儿子,父亲“感到如释重负”。卸掉的这个重负既是儿子的身体,也当是父亲在内心里对亡妻还了的那个愿:不管儿子是否活下来、能否得救,他尽力了,没有半途而废。只是,这重负卸得如此悲凉,而到处响起狗叫声。他必须给自己搭建个台阶,以免情感的落差过大,妻子死去多年,名义上的儿子也不在了,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孤独者。所以,小说最后一句话他也是对自己说的:
“你刚才没有听到狗叫吗?你连这点希望也不想给我。”
可能从来就无所谓希望。他只是给自己许了个空头的念想,长夜将尽,这念想终于也要见光死了。贫穷的、绝望的、彻底的孤独者,精疲力竭,只剩下了说一句话的平静。
3
对人物言行的解读可以从不同角度乃至完全相反的方向进入,并非刻意要找出其间的微言大义,而是因为该小说的确尽可能地过滤掉了单一的情感和价值判断。胡安·鲁尔福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能视角,但因为只通过细节的连缀呈现事实,客观至于具有了限制性视角的效果。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另一种“零度叙事”。这样的短篇小说如同电影的一个片段,只靠镜头自身言说,取消了一切画外音;但它又跟电影片段有所区别,在审美和意义上它必须自足,它必须通过有限的细节让自己成为一个充满张力、可以寻见来龙去脉、能够自圆其说的独立单位,它要在残缺中创造出完整来。“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此之谓也。所以,一个好的短篇小说,尤其是篇幅俭省的短篇,所有弹药都不能浪费,一颗子弹必须打死一个敌人。
短不是写不长,而是你有能力节制、隐忍、裁汰冗余,你有别致的角度看见简单中的丰富、复杂、暧昧和大有来。有时候这种丰富、复杂、暧昧和大有根本不需要条分缕析地总结和展示出来,我更愿意让它们停留在一个感觉上。这个感觉我以为就是“审美”。跟阅读长篇不同,看一个好的短篇,我喜欢感受小说中散发出来的那种介于明晰和清朗、含混和深沉、陡峭和开阔之间的意味。这意味游走在感性与理性之间。超越了两头的端点去面对一个短篇,要么只能得到一个囫囵的印象,要么庖丁解牛那般弄成了一个干巴巴的技术活儿,对短篇之美的获取都是一个伤害。好短篇要有迅疾、丰饶之美。评论家张莉论及理想的短篇,说她会想起“短而美的唐诗名句”“窗含西岭千秋雪”,“气质超拔,一骑绝尘”,我深表赞同。当然,我也喜欢另一种风貌的好短篇,“百年多病独登台”。只简单的几个汉字组合在一起,就已美不胜收、意味深长。
《你没有听见狗叫吗?》大抵属于后一种。事实上胡安·鲁尔福的短篇小说基本上都隶属此类,有种沉郁、粗粝、幽远和苍凉的调子。这种风格与贫困的墨西哥乡村天然地契合。2015年去墨西哥,去之前做了一些功课,旅游指南、政府报告和各种材料看了一大堆。真到了墨西哥,我发现管用的只有文学作品,尤其是胡安·鲁尔福的小说。尽管是几十年前的作品,时过境迁,那种把墨西哥写到了骨子里头的真切感觉,随时会被眼前的人文和风物唤醒。胡安·鲁尔福的风格,正是那片土地的风格。
短篇小说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征服读者,风格上的辨识度一定要高。二十年里我无数次阅读胡安·鲁尔福,每次随便打开一页都能迅速进入小说的艺术情境,跟鲁尔福的修辞风格有极大的关系,他能让你的心很快就沉静下来。好作品让人沉下来,烂作品让你浮上去。屡读不腻还因为胡安·鲁尔福浑然质朴。浑然是因为无限接近世界本身;質朴则是精准,寥寥几笔就直抵核心。所以,胡安·鲁尔福的短篇小说不需要长。就一个绝望的慈父救助生命垂危的不肖之子的故事,2600字足矣。
当然,单就《你没有听见狗叫吗?》,说它臻于完美也大可不必。但我敢肯定,把它放进鲁尔福短篇集《烈火平原》,或者再扩大一下范围,把它放在鲁尔福全集中来考量,这个短篇的力量会更大,我们对它的理解也会更加开阔和深入。在他的17个短篇小说中,没有任何两个是相同的,每一个都区别于另外一个。如此富于创新和变化,在以短篇名世的大作家里,也极少见。相互之间作互文式解读,对短篇小说这一文体的理解想必会别有洞天。的确,每个伟大作家都在努力构建属于他的完整的艺术世界,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这个完整世界的一部分,因此,单部作品在残缺和遗憾的同时,已然暗含了完整和圆满。也因此,我们经由《你没有听见狗叫吗?》理解胡安·鲁尔福之后,也需要再经由胡安·鲁尔福,重新回到《你没有听见狗叫吗?》。
责任编辑 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