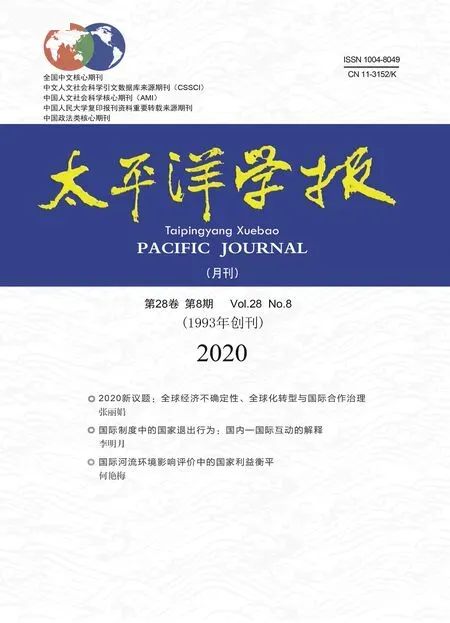国际制度中的国家退出行为:国内—国际互动的解释
李明月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社会日益结成一张制度网络,其中包括各种国际组织、双边和多边条约及其他制度安排。虽然大多数国家仍然处在当初加入的国际制度中,但也发生了一些国家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制度的现象。近年来,英国退出欧盟,部分非洲国家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美国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接连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朗核协议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使得国家的“退群”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作为诸多国际制度的创建者和主导者,美国的退出尤其成为新的话题和研究热点。那么,国家为什么会退出先前加入的国际制度?而这其中还隐含着一个深层问题,即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为何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并不是国际关系学者通常所关注的从游离到参与的改变,而是从参与到退出的改变。本文努力探索上述问题,并力求做出有价值的解释。
一、“退出”现象及既有解释的不足
国际制度是规定行为的职责、限制行动及影响行为者期望的持久且互为联系的一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1)Robert Keohane e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3, 转引自苏长和:“重新定义国际制度”,《欧洲》,1999年第6期,第24页。国际组织和国际条约是国际制度的基本组成要素,也是国际制度的承载平台和表现形式。1945年至2014年间,政府间国际组织中发生的成员国退出现象达200余次。(2)Inken von Borzyskowski and Felicity Vabulas, “Hello, Goodbye: When Do States Withdraw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4, No.1, 2019, p.339.如果将其他形式国际制度中发生的退出行为计算在内,或考虑国家的暂时退出与部分退出行为,那么将是更为庞大的数据。由于各类国际制度数量的日趋增长和国家参与国际合作的绝对数量优势,国际制度中的国家退出行为仍不是常态。本文之所以要研究国际制度中的国家退出行为,是因为“退出”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现象,然而有关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系统性研究仍然较少。
1.1 “退出”的概念界定
“退出”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根据条约(包括创建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基础条约)中规定的退出条件终止其成员资格的行为。(3)Laurence R. Helfer, “Exiting Treaties”,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91, No.7, 2005, pp. 1579-1648.若当事国单方行使退出权,而其他当事国在一定时间内不提出反对,那么该条约对退出国来说已经终止,但对其他当事国来说,仍继续有效。(4)《维也纳条约法公约(1969)》第56条用两种方式表达“退出”,即“单方解约(denunciation)”或“单方退出(withdrawal)”。其中,单方解约既适用于双边条约,也适用于多边条约;单方退出只适用于多边条约。参见United Nations,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y 1969”, May 23, 1969;银红武著:《条约退出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也就是说,“退出”是一种单边行动,并不需要其他成员国的同意和支持。但是,国家首先要向组织和组织内的其他成员国告知退出,然后再根据国际制度的退出程序和时间表完成退出的形式化要求。例如,《里斯本条约》第50条对成员国退出欧盟的主要程序作出了规定:退出国必须正式通知欧洲理事国其“脱欧”意向,之后欧盟必须与退出国就退出欧盟的具体细节进行磋商谈判并缔结一项协议,协议生效后(或如果协议不能生效,则自退出国发出通知之日起两年后),条约将不再适用于退出国。(5)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Journal, “Consolidated Versions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nion, C115, May 9, 2008.
一般意义上理解的“退出”,是相对弱势、被秩序主导国质疑合法性,以及处于边缘地位或具有离心力的国家迫于形势作出的选择,如本来就颇具离心力的英国作出退出欧盟的决定。(6)任琳:“‘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1期,第88页。从历史上看,主导大国频繁退出国际制度的现象较为少见。传统观点认为,主导国是现存国际秩序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且对现状满意,它们通常运用保持、吸收和驱逐战略维护其地位;新兴国家因在当前的国际秩序中缺少制定规则的权力,现存制度规范并不能很好契合自身的利益需求,而被视为既有秩序的挑战者,往往通过选择性或部分退出、呼吁和革新来改变现状。(7)See Lauchlan T. Munro, “Strategies to 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Exit, Voice and Innovation versus Expulsion, Maintenance and Absorp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9, No. 2, 2018, p. 310;汪海宝、贺凯:“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59页。然而,美国近年来接连退出或威胁退出的行为似乎为主导国退出国际制度提供了更多例证,而被视为崛起国的中国在国际制度中表现出的积极、开放和包容态度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可见,“退出”并不是弱势国、崛起国、主导国或其他某一类型国家所特有的国际制度行为,任何国家都有可能退出。
“退出”作为一种国际制度行为有时并不是真实和彻底的,国家有时会策略性地选择威胁退出,来改变自身的不利处境或获取额外收益,即国家威胁所参与的国际制度,如果不改变对本国的不利状况,就将退出该制度。如特朗普总统就曾公开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除非其改变对待美国的方式。(8)“Donald Trump Threatens to Pull United States Out of the WTO If It Does Not ‘Shape Up’” The National, August 31, 2018.无论威胁退出国最终是否退出国际制度,只要制度内的成员国接受了该国的利益诉求,该国的预期目标就实现了。威胁退出是一种策略性欺骗,有其特殊功效,但并不是真的退出,而是通过威胁退出达到重建国际秩序的目标。(9)任琳:“‘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1期,第85页。威胁退出和实际退出都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因而成为国家用来表达对条约体制或国际组织不满的重要方式。
1.2 退出行为为何重要
虽然“退出”并不是国际制度中的普遍现象,但会对国际合作、退出国家和存留国家的政策、某一领域内国际制度的未来发展、国际组织的经费和未来政策行动等产生重要影响。国际制度既有其加入条件的规制,又有退出的自由权利,这一方面体现出其开放性,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尊重国家自主权的特性。(10)马英杰、张红蕾、刘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及我国的考量”,《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5期,第26页。可见,国际制度中退出条款和退出机制的设计具有一定积极意义。首先,退出行为为国家在现有合作形式之外创造新的合作形式提供了可能,无论国家大小强弱,都能够通过退出策略表明自己对国际制度的态度并增加发言权。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美国相继退出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该行为导致对上述组织丧失支持和资金资助迟滞,迫使组织改变自身行为,随后美国又加入了上述组织。其次,退出行为还是国家对国际制度不合理和低效率的回应与质疑,国家从国际制度中退出的行为可推动国际制度的发展。例如,不少非洲国家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存在司法偏见,继布隆迪于2016年10月退出后,南非和冈比亚也宣布退出,纳米比亚和肯尼亚等非洲国家则表示正在考虑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可能性。(11)近年来,国际刑事法院多次受到司法偏见的指责。2016年10月18日,布隆迪因反对国际刑事法院关于布隆迪存在“大量侵犯人权的暴力行为”的指控,成为第一个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国家。10月21日,南非政府因无法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相关规定,正式启动退出程序。10月25日,冈比亚认为国际刑事法院在战争罪指控方面存在偏见,也宣布将退出国际刑事法院。“不满‘双重标准’冈比亚宣布退出国际刑事法院”,新华网,2016年10月27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0/27/c_129338759.htm。成员国怨声载道和集体退出的趋势可能会促使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一定的变革。最后,退出行为可使国家在国际制度约束与行使国家主权之间得到缓冲地带。英国退出欧盟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要换取对英国主权的“完全控制”,而不必再继续向欧盟“让渡”立法权等国家主权。(12)“英国‘退欧’风波后的国家中心主义”,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12月21日,http://mil.cssn.cn/dzyx/dzyx_llsj/201512/t20151221_2790493.shtml。
国际制度中的国家退出行为虽然有助于成员国寻求新的合作形式,创造新的利益格局,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但也可能对国际合作、全球治理和国家间关系造成不良影响。国家之间的复合相互依赖使很多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只能通过国际制度合作解决,国家退出国际制度可能会对某一问题领域的治理进程造成阻碍。在国际制度中,弱势国家退出的影响可能是有限的,但秩序主导国退出的影响则是系统性的,可能危及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秩序的稳定。例如,德国和日本先后从国际联盟中退出,造成了国际体系的混乱,并最终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制度退出行为已经对经济贸易、安全合作和全球治理诸多层面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13)汪海宝、贺凯:“国际秩序转型时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57页。因此,分析国家为何以及何时会退出国际制度,能为评估全球治理进程和国际秩序维护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1.3 既有解释的不足
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国际制度研究大多关注国际制度为何以及如何形成,为什么国际制度重要以及哪些国家在国际制度设计中最为重要,关于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一般性研究并不多见。要探寻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深层原因,必须对其镜像问题,即国家为什么参与国际制度进行分析。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国际制度能为其成员国带来高于不参与状态的合作收益。(14)新现实主义者虽然强调相对收益,但也没有否定绝对收益在国家选择参与国际制度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参见刘宏松:“对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另一种理性主义解释——国际制度中‘自为其事’权力理论书评”,《国际论坛》,2006年第5期,第13-18页。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国际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良好声誉的价值,增加决策和行为的透明度,减少不确定性等,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8-133页。按照这种逻辑,国家退出国际制度是因为国家参与的成本已经超过了其所获得的制度红利,不符合国家的利益。但是,对于这种收益变化导致退出的结果,新现实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
新现实主义认为,拥有更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国家可以更工具化地利用国际制度,国际体系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会导致相对收益的变化,从而导致国家退出国际制度。一战后,德国实力增长带来的欧洲权力结构变化的确是其退出国际联盟的重要原因,但是国际制度中的很多退出现象并不能用权力结构变化来解释,如英国退出欧洲联盟就很难说是欧盟内部权力结构变化的结果。而新自由主义认为,国际制度的高成本和低效率会使得国家参与的绝对收益不断下降,从而导致国家退出。虽然这往往也是政治家在宣布退出时的理由,但公开宣称的原因可能并不是真实原因。仅仅对国际制度不满并不一定导致成员国的退出,一方面,国家可能找到解决制度设计和有效性等问题的方式,另一方面,行动惯性和沉没成本也会使国家继续留在国际制度中,尤其是当退出成本更高的时候。(15)Inken von Borzyskowski and Felicity Vabulas, “Hello, Goodbye: When Do States Withdraw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14, No.1, 2019, p.337.
在回答国家为什么会参与国际制度时,建构主义认为国际制度规范可以改变国家对利益的认知,改变国家偏好,使国家对国际规范产生认同,在认同的基础上遵守国际规范,参与国际制度。(16)[美]玛莎·芬尼莫尔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也就是说,国家因认为符合国际制度规范的行为是合法的进而遵约。国家退出国际制度则是因为国际规范和国内规范的匹配程度发生了变化。(17)关于国内规范与国际规范的匹配与互动的研究可参见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2, 2004, pp. 239-275;潘忠岐:“国内规范、国际规范与中欧规范互动”,《欧洲研究》,2017年第1期,第18-36页等。然而,国际社会现实却表明,有些国家会拒绝与国内规范相一致的国际规范,退出相关的国际制度。美国作为诸多国际制度的创建者和主导者,退出了涉及多个问题领域的相关制度,并且曾反复退出和加入某些国际制度,很难说此类行为皆因国内规范与国际规范的匹配程度发生了变化。因此,国内规范和国际规范的匹配程度并不能有效解释国际制度中的国家退出行为。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领域较少关于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一般性且得到普遍认同的理论,主流理论学派也无法做出全面的解释。此外,国际法领域对国际条约退出机制的研究,以及对条约退出权的研究能提供良好的借鉴。(18)参见马英杰、张红蕾、刘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及我国的考量”,《太平洋学报》,2013年第5期,第24-32页;银红武著:《条约退出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但是,该领域往往回避和忽略对国家退出实践及其影响的研究,对国家何时和为何要退出也缺乏系统性研究。(19)韩逸畴:“退出,呼吁与国际法的演化和发展——基于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理论视角”,《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188页。
随着国际制度中的国家(尤其是主导国)退出行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外也涌现出一些具有洞察力的研究。在体系层面,除新现实主义关注的权力结构变化及新自由主义关注的国际制度本身的高成本低效率外,还有学者从地缘政治因素、国际制度内社会关系变化等角度进行了解释。(20)See Inken von Borzyskowski and Felicity Vabulas, “Hello, Goodbye: When Do States Withdraw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4, No. 1, 2019, pp.335-366; Mingtao Shi, “State Withdrawal from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hanging Social Relations within Divergent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5, No. 2, 2018, pp.221-241.不少学者转向国内政治层面寻找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内在逻辑,如国内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对国际制度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质疑,(21)Jack Snyder, “The Broken Bargain: How Nationalism Come Back”,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9, pp. 54-60.国内政治结构变化带来的国际制度行为变化等。(22)Helen V. Milner and Dustin H. Tingley, “Who Supports Global Economic Engagement? The Sources of Preferences in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5, No.1, 2011, pp. 37-68.
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国内—国际互动过程。(23)目前有关国家国际制度行为的研究大多是从国内和国际互动的角度进行解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运用双层博弈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及其变化是国际层次的谈判与国内层次批准博弈的结果。参见韦进深著:《决策偏好与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Harry Noone, “Two-Level Game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Assessing Domestic-Foreign Policy Linkage Thoery”, World Affairs, Vol. 182, No.2, 2019, pp. 165-186.仅从体系层面或国内政治层面对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行为进行分析都是不全面的,任何单一因素都不能导致结果,还有其他变量在发挥作用。然而,要区分出哪一种因素在国家的退出行为中扮演更重要的作用往往是困难的,“真正的挑战在于必须理解不同的因素如何互动,从而导致了特定社会事实”。(24)唐世平著:《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页。因此,本文将从国内—国际互动的角度对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行为进行解释。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收益变化、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偏好形成及最终决策,都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二、国内—国际互动中的收益变化与行为选择
收益变化是国家行为选择的动力。国家参与国际制度获得的制度红利是不断变化的,这主要涉及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互动过程中成本和收益的变化。虽然一般认为国家在国际制度中收益的衰减并不足以充分解释国家为何退出国际制度,但合作状态的巨大收益的确是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主要动力。国家不需要加入一个不符合其利益的国际制度,甚至有观点认为制度只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制度之所以有效,只是因为国家相信制度符合自己的利益。(25)Robert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p. 55-62.更重要的是,国际制度不只为国家提供一种简单的二元选择——加入或不加入、存在或退出,即使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收益减少,也并非只有退出这一种选择。
2.1 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收益变化
国际制度并不会保持其原始状态,持久存续的国际制度会随着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原来制定或参与国际制度的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导致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收益有所下降。一方面,由于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创造一定的剩余,从而使各类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具备承载低效运行的能力,因而绩效退减一定会发生。(26)[美]艾伯特· O. 赫希曼著,卢昌崇译:《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3页。无论国际制度设计得多么完善,都会有不断衰退的倾向,这种衰退既可能是持久的,也可能是间歇的。这种衰退必然会带来国际制度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增加国家参与的成本并降低收益。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参与国际制度收益的进一步增长就会变得愈发困难。经济盈余比付出的成本上升得快,国家才有参与制度的能力和动力。然而根据收益递减规律,当国际制度发展到某一阶段时,国家付出的成本会逐渐超过经济盈余,尤其对于主导国而言,维持国际现状的经济成本往往比用于支撑其地位和现状的财政能力上升得更快。因此,主导国参与和维持国际制度的成本终会超过收益,其他国家也会存在同样的发展趋势。
除上述绝对收益变化外,差异化收益的累积也会造成国家相对收益的变化。国际制度给所有参与者的行为设定了各种约束,这种设定往往决定了相关议题领域的利益分配结构。国际制度通常体现的是制度中权力最大的那部分成员的利益,至少该制度建立之初的情况如此。(27)[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经济、技术和其他领域的发展变化,国际制度中各国利益与权力平衡的状况也必然发生变化,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相对收益也会发生变化。相对收益受损会使国家产生危机感或不公正感,可能导致国家国际制度行为的改变。
更重要的是,国家对利益的认知也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国内利益集团的变动、经济和人口的长期变化及其他方面的发展,都会引入各种新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最终会在国家立场上得到反映。因此,国家在国际制度中收益的变化可能并不是绝对收益或相对收益下降,而是国家利益认知变化后对参与国际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做出的重新判断。例如,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以及特朗普政府宣布并正式启动退出《巴黎协定》程序,并不完全是美国在国际气候制度中的绝对收益或相对收益发生了变化,更多的是新政府上台之后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发生了变化,进而对参与国际制度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了重新衡量。
综上所述,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收益变化,既包括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的变化,也包括利益认知变化导致的收益变化。既有国际层面国际制度效能下降、制度内权力结构变化的原因,也涉及国内层面政治结构变化等因素。因此,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收益衰减实际也是国内—国际互动的结果。
2.2 国家的制度行为选择
无论绝对收益或相对收益的下降,还是利益认知变化导致的收益下降,都会对国家继续参与国际制度合作的动力和能力产生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意味国家必然会产生退出的偏好或决策,相反,国家有多种行为选择来应对其在国际制度中的收益损耗。
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在其《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一书中提出了“退出—呼吁”机制。根据其观点,当一国在其参与的国际制度中利益受损或遭遇不公时,国家会采取退出制度或在制度中呼吁改革这两种策略来表达利益诉求。(28)Scott Gehlbach, “A Formal Model of Exit and Voice”,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 18, No.4, 2006, pp.395-396.但事实上,国家并不是在退出和呼吁之间做单一选择,而是面临二分法的选择,即退出或不退出,若不退出的话,是选择呼吁改革,还是沉默忍受。(29)Brain Barry,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by Albert O. Hirschma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 1, 1974, pp. 91, 97.选择退出,意味着国家不接受不利变化,通过退出制度来改变不利处境。选择沉默,意味着国家接受不利变化,不改变其制度行为,但这并不是因为它们不希望以建设性的方式回应不满,而是它们根本无力采取其他行动。(30)William Roberts Clark, Matt Golder, and Sona N. Golder, “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Model of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7, No.1, 2017, p.721.选择呼吁改革,意味着国家不接受不利变化,而是通过各种方式在内部寻求改变,修正国际制度中的规则、政策或产出,以求恢复原本的有利环境。成员国威胁退出,即如果国际制度没有满足其要求便退出,实际上也是一种呼吁。
如图1所示,面对国际制度中收益受损的情况,国家有三种可能的行为选择:呼吁改革、退出和沉默。国际制度的参与国具有异质性,它们在制度内部呼吁或退出的成本和收益是不一样的。假设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预期收益是E1(E1>0),退出的成本是C1(C1>0);沉默实际意味着国家并没有改变其行为,假设其收益和成本皆为0(不考虑已经产生的利益受损);国家通过呼吁来改善自身处境的预期收益和成本分别为E2和C2(E2>0,C2>0)。国家是否选择呼吁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国家是否愿意承担这种不确定性;二是呼吁后国际制度发生改进的概率。(31)[美]艾伯特· O. 赫希曼著,卢昌崇译:《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31页。呼吁涉及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和讨价还价的能力,这种话语权通常在制度设计之初就已经确定,大部分国家往往无法通过在制度内部呼吁使其发生有利于自身的转变。若国际制度选择忽略呼吁国家的诉求,则呼吁国不能达到其预期收益。呼吁无效后,国家再选择退出的收益仍为E1,而退出的成本为C1+C2;沉默的收益仍为0,成本则为C2。

图1 利益受损时国家的制度行为选择资料来源:笔者结合艾伯特·赫希曼的“退出—呼吁”机制及其他相关文献自制
既然在面对收益受损时,国家有退出、呼吁和沉默三种选择,那么国家为何要选择退出?日常的外交政策制定主要以当前政治上的紧急事务为导向,集中于短期的成本和收益;与此相反,加入或退出国际制度这一更审慎的过程会考虑更长远的利益和价值观。(32)Abram Chayes and Antonia Handler Chayes, “On Compli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2, 1993, pp. 175-205.简言之,国家退出国际制度,除了短期的退出成本和收益的衡量,即当E1-C1>0时国家才会选择退出,还需要对退出的前景进行衡量。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希望通过有效的呼吁来改变国际制度,然而往往因为呼吁的成本过高或国家无力对制度和制度内的其他行为体施加影响而导致国家直接选择退出。即使是像美国这样的主导国也是如此,若美国能轻易通过呼吁改变对其不利的制度环境,也就无需承担退出成本。国家选择直接退出国际制度时的预期就是退出后的前景要优于留在制度中的前景,即E1-C1>E2-C2。
还有一种情况,在面对收益受损时,国家并不会直接选择退出,而是优先选择呼吁,也就是说,国家预期的呼吁前景要优于直接退出的前景(E2-C2>0且E2-C2>E1-C1)。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同样面对收益变化的情况,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选择威胁退出,而直接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制度。呼吁失效后,若退出的收益仍大于退出成本,并且退出的前景仍优于忠诚于组织的前景,即E1-(C1+C2)> 0-C2且E1-(C1+C2)>0时,退出仍可以作为呼吁的替代选择。事实上,呼吁是否有效也取决于行为体退出的前景。没有退出的可能性,呼吁也就毫无意义。
综上所述,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利益受损并不会直接产生退出的偏好和决策,并不是所有在国际制度中利益受损的国家都会选择退出。国家的退出选择是通过短期的成本收益计算与未来收益前景的衡量而得出的。影响成本与收益考虑的环境变化因素甚多,不可能一一列出,而且取决于国家如何理解退出国际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尽管人们把成本和利益作为客观的且可以做定量分析的要素来谈论,但实际上它们都具有很大的主观和心理成分。(33)[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毫无疑问,无论是客观的成本收益计算,还是主观的理解与认知,都是对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环境因素的综合考虑。
三、国内—国际互动与国家退出偏好的形成
简单来说,偏好就是存在多种行为选择的情况下,对其中一种选择的倾向性影响最终的决策与行为。国家在国际制度中出现利益受损时,并非只有“退出”一个选项,但为何产生对“退出”的倾向性呢?根据上文所述,当退出的收益预期大于呼吁和沉默时,国家就会倾向于退出。然而,由于不确定因素和决策者的有限理性,(34)在实践中,决策者既受到环境不确定的局限,也受到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后者即为“有限理性”。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信强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页。国家的退出偏好很可能并非基于完全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而是受到国内外因素互动的影响。国际制度中的权力分配会对国家是否退出及采用的退出策略产生影响,国内退出偏好是国内不同行为体利益和偏好复杂博弈的结果,国际制度的约束力作为一种外在激励效用也会强化或弱化国家的退出偏好。
3.1 国际制度中的权力分配
有不少学者将国家国际制度行为的变化归结于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的确,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行为在国际体系的转型期较为常见,如德国和日本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退出国际联盟。围绕国际制度的缔造、改革和退出所展开的博弈,本质上是大国权力、利益和声誉的竞争。(35)汪海宝、贺凯:“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第59页。由于当前国际体系处于深刻的变化过程中,制度变迁与权力转移相辅相成,由此也导致了一些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现象。尤其是当国家实力的增长或衰落引起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权力序位提高或降低,即国内—国际权力互动发生变化时,必然会导致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发生变化。然而,权力结构的变化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有些国家退出了,有些国家仍然忠诚于制度;为什么有些国际制度频繁出现退出甚至集体退出,而有些国际制度仍然保持着活力。
权力序位能为国家在面对收益受损时圈定不同的行为备选方案,因此,国家退出偏好的形成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际制度中权力分配的影响。这里的权力既指整体实力,包括经济实力、政治和军事实力、文化和价值观的影响力,也指在特定问题领域或制度领域内的实力。当利益受损时,实力地位会影响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选择,每个国家退出的成本和收益都是不同的。
在国际制度中面临收益降低的风险时,实力强大的国家通常有呼吁和退出两种选项。强大的实力可以赋予国家对国际制度一定程度的操控力,甚至一些实力强大的国家正是国际制度的最初创立者,在工具化利用国际制度时会更加积极主动。当国际制度不能满足其需求时,这些国家可以在内部呼吁进行变革或实行威胁退出策略。它们可以将其拥有的物质资源转化为具体制度中利害攸关问题的谈判筹码。(36)[美]奥兰·R. 扬:“政治领导与机制的形成:论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发展”,载[美]莉萨·马丁、贝思·西蒙斯著,黄仁伟、蔡鹏鸿等译:《国际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甚至,威胁退出策略会比在内部呼吁变革更加有效。因为其他成员国面对不满现状国的呼吁诉求时可以选择不作为而没有任何损失,但如果不满现状国威胁退出制度,选择不作为的其他成员国将可能承受不满现状国退出国际制度带来的损失。(37)刘宏松、刘玲玲:“威胁退出与国际制度改革:以英国寻求减少欧共体预算摊款为例”,《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1辑,第76-77页。例如,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多次声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给予墨西哥和加拿大太多让步,以致美国利益长期受损,要求重新谈判和修订相关条款,否则将退出。最终,墨西哥和加拿大同意重新谈判。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利用自身贸易优势地位率先与墨西哥达成协议,倒逼加拿大在谈判中妥协。2018年10月,三方完成新一轮谈判,并将该协定重新命名为《美墨加三国协议》(USMCA)。这个新协议在美国关注的汽车制造业、劳工和环境法规、药品定价等方面都发生了有利的改变,被特朗普称为“美国有史以来达成的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贸易协议”。(38)“美墨加三国领导人在阿根廷签署新版贸易协定”,新华网,2018年12月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2/02/c_1210006785.htm。
国家选择在内部进行呼吁,既取决于呼吁的成本和收益,也取决于该国相信国际制度未来发生更大变革的可能性。(39)Jonathan B. Slapin, “Exit, Voice, and Cooperation: Bargaining Powe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Federal System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21, No. 2, 2009, p.189.然而,呼吁并不一定会得到制度内其他成员国的积极回应。实力强大的国家也可能选择退出,除了呼吁的成本过高或无法进行可信和有效的威胁退出之外,该国对退出前景的预期可能要高于留在制度内的前景,但强势国家退出之后往往不会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一方面,退出国退出之后仍然在制度外呼吁,推动新的国际谈判,要求相关国际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如1984年,美国以管理不善和腐败等理由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重新加入,2019年1月又以教科文组织助长“反以色列偏见”为由再次退出。(40)“美国和以色列1月1日正式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华网,2019年1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1/03/c_1210028955.htm。另一方面,实力强大的国家往往会有替代性的选项,即退出后创立新的国际制度。它们不仅有能力和意愿主导国际制度和规则,还有能力废旧立新,退出已不符合本国利益的制度,设立符合本国利益的新制度。例如,美国退出旨在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照顾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并以此为基础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有利于美欧利益的义务性规定,进而推进了世界贸易组织及相应国际贸易规则的创立。(41)Richard H. Steinberg, “In the Shadow of Law or Power? Consensus-based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2, 2002, pp.339-374.
在国际制度中发生收益受损时,实力较为弱小的国家会有退出和沉默两种选项。只有当行为体有退出或威胁退出的能力时,它在制度内的呼吁才是强有力的。如果行为体的退出威胁不可信,或者它是否留在制度内并不被重视,那么它的呼吁将是无效的。相反,有能力进行有效呼吁的行为体通常不需要发声,因为制度会预测它的愿望并做出积极反映。(42)William Roberts Clark, Matt Golder, and Sona N. Golder, “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Model of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7, No.1, 2017, p.751.较为弱小的国家通常没有能力对国际制度和其他成员国施加影响,其成员资格可能对国际制度而言意义不大。因此,当制度谈判对其不利时,较为弱小的国家要么直接从国际制度中退出,要么沉默。一方面,弱小国家往往在国际制度中处于相对底层和边缘的位置,缺少必要的社会资本来面对制度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制度的非中性或其本身存在的某种倾向,不同成员国在国际制度中可能受到差别对待,弱小国家可能在制度内外的待遇相差无几。
3.2 国内利益与偏好
国内不同行为体具有不同的利益和偏好,国家的行为偏好并非某一行为体利益和偏好的体现,而是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的复杂博弈结果。但由于对外事务的特殊性和机密性,国家的外交政策往往由该国占统治地位的成员或统治联盟的利益决定。国家对外行为偏好最主要体现的是决策者的利益和偏好。例如,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中,保守主义主要强调实力,尤其是军事力量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强调维护美国的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同时,保守主义是共和党的主流意识形态,当共和党执政时,保守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往往占主导地位。(43)周琪著:《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页。此外,在外交事务的实际操作中,总统居于主导地位,是核心决策者,导致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践行都深受总统个人风格和偏好的影响。
首先,偏好具有主观性。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选择主要掌握在决策者手中,奉行“国际主义”的决策者可能会对国际制度采取更积极的态度,而奉行“孤立主义”的决策者可能对国际制度采取消极态度。国家在国际制度中持续出现利益损耗,会导致国家内部对国际制度的需求发生变化。当决策者或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和利益取向倾向于改变体系时,国家更有可能形成退出的偏好。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时曾针对外交政策发表演讲,他指出,“我们将不再让这个国家和人民屈服于全球主义的虚假之歌”。(44)Julian Hattem, “Trump Warns against ‘False Song of Globalism’” The Hill, April 27, 2016, https://thehill.com/policy/national-security/277879-trump-warns-against-false-song-of-globalism。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放弃”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选择放弃很多国际制度和框架”,不是因为任何军事或经济力量的丧失迫使美国削减其全球承诺,(45)David Wright,“Haass Says US Engaged in Abdication of Global Leadership”, CNN, January 3, 2018, http://www.cnn.com/2018/01/03/politics/richard-haass-trumpleadership-cnntv/index.html.而是因为奉行“美国优先”的策略。也有研究表明,美国在一系列国际制度中的退出行为正是特朗普的人格特质在国际关系上的表现。(46)参见尹继武、郑建君、李宏洲:“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质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7年第2期;王一鸣、时殷弘:“特朗普行为的根源: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98-127页。
其次,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国内利益和偏好,使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变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参与国际制度所产生的国内成本与收益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国内权力资源重新分配和利益集团分化,基于这种变化,国家外交政策中的利益或者目标的组合就有可能变更,(47)[美]罗伯特·吉尔平著,宋新宁、杜建平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页。国际制度行为偏好也会发生变化。这种国内—国际利益互动的变化,可能并不是通常所能观察到的绝对收益或相对收益的变化,而是由于国家内部权力分配变化之后导致的利益认知的变化。国内权力资源分配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府更迭。新总统上任等结构限制的松动为国家退出国际制度提供了良好的时机。(48)温尧:“退出的政治:美国制度收缩的逻辑”,《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第14页。国家对待国际制度的偏好发生颠覆性的转变通常与该国政府的交接同步进行,新一届政府往往倾向于否定前任的外交政策。例如,美国决定退出《京都议定书》发生在2001年3月28日小布什政府上台伊始,而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国际制度大多是奥巴马政府的政治遗产,如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关系(TPP)等,均在其上台半年之内宣告退出。再如,2016年10月,冈比亚向联合国发出了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退约通知,2017年2月,新总统上台仅一个月后,冈比亚就做出了撤回退约通知的决定。(49)Manisuli Ssenyonjo, “State Withdrawal Notifications from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outh Africa, Burundi and the Gambia”, Criminal Law Forum, Vol.29, No.1, 2017, pp. 63-119.
最后,偏好具有大众趋向性。国内偏好并不是固有的,也可能并不局限于物质状况,而是受到他者偏好选择的影响。不确定环境中的有限理性行为体经常从其他明显成功的行为体曾尝试过的解决办法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50)[美]玛莎·芬尼莫尔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当国家无法形成稳定的行为偏好时,模仿常常是一种理性的战略选择。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国际制度中退出行为(尤其是主导国退出)的外溢效应。例如,美国最早退出《京都议定书》后,加拿大也宣布退出,而日本和俄罗斯表示坚决不实施《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再如,南非、布隆迪和冈比亚向国际刑事法院递交退出通知后,肯尼亚、纳米比亚和乌干达等国也威胁退出。事实上,有些国家是在盟友或对手的压力下参与和退出国际组织的,如非洲联盟曾做出若干决定,呼吁非洲国家对国际刑事法院采取不合作态度,并支持成员国考虑退出国际刑事法院。(51)“国际刑事法院被质疑成西方干涉非洲国家内政工具”,《国际先驱导报》,2016年11月3日。
3.3 国际制度的约束力
国际制度对成员国的约束力作为一种外在激励效用也会强化或弱化国家的退出偏好。这种约束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成员国退出的机制约束力,即国际制度是否有退出机制或条款允许国家退出;二是,对成员国的道德约束力,这取决于国际制度自身的公正性、合法性等声誉影响因素。国际制度对退出行为的约束力越强,国家退出的预期成本就越高;反之,约束力越弱,国家退出的偏好就越容易形成。
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一个主要前提条件是该制度在设立之初是否有退出条款的设计,即成员国是否有退出制度的合法权利。为协调条约的刚性承诺与国家对灵活性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条约通常允许国家在某种情形下退出先前已经批准生效的条约,或在国际组织章程中规定国家退出的条件。(52)韩逸畴:“退出,呼吁与国际法的演化和发展——基于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理论视角”,《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188页。现今,大部分国际制度都有退出机制,能够以明确清晰的退出程序防止退出的不确定性,如果程序设计得当,还能防止其他成员国对退出国实施任意的惩罚性制裁。(53)Andrew Shorten, “Constitutional Secession Rights, Exit Threats and Multinational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62, No.1, 2014, p.102.若国际制度中有相应的退出机制,国家的退出就具有合法性依据,出现利益损耗的国家也就更容易产生退出的偏好。
然而,面对利益受损即退出国际制度的国家,仍可能被制度内的其他成员国视为非合作型行为体,对该国声誉产生影响,需要承担退出的声誉成本。事实上,国家从国际制度中退出是否会产生声誉成本与该制度本身的声誉挂钩。(54)Annika Jones, “Non-cooper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Olympia Bekou and Daley Birkett eds., Coope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erspectives from Theory and Practice, Brill Nijhoff, 2016, pp. 185-209.通常认为,合法性和公正性是国际制度得以遵守的前提条件。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往往取决于成员国的集体认同。(55)王玮:“国际制度与新进入国家的相互合法化”,《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第79页。而很多国际制度都带有隐蔽的非中性特点,完全公正的国际制度很难实现。尽管如此,具有明显歧视性和倾向性的国际制度的社会认同度仍会大大减弱。(56)李明月著:《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7页。
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越高,其国际声誉就越好,国家不合作或退出所带来的声誉成本就越高。(57)Stef Vandeginste, “The ICC Burexit: Free at Last? Burundi on Its Way Out of the Rome Statute”, Analysis and Policy Brief N°20, October 2016, p. 3.其他国家如果认为退出国的行为违背先前承诺、有损多边主义精神,则可能在未来的互动中采取相应措施,对这种行为实施报复和惩罚。(58)温尧:“退出的政治:美国制度收缩的逻辑”,《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第11页。对于声誉较差的国际制度,国家的退出不仅不会产生声誉成本,反而还会带来声誉收益。例如,自2009年初苏丹总统巴希尔被起诉以来,非洲国家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批评越来越强烈,普遍认为其指控丧失公信力,仅仅针对非洲国家,《罗马规约》也与国际法义务相冲突。(59)如《罗马规约》迫使包括南非在内的国际刑事法院缔约国“逮捕根据国际习惯法可能享有外交豁免权但被法院通缉的人”。Manisuli Ssenyonjo, “State Withdrawal Notifications from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outh Africa, Burundi and the Gambia”, Criminal Law Forum, Vol. 29, No. 2, 2017, pp.10-33.因此,布隆迪退出国际刑事法院在其他坚持自力更生和反对新殖民主义政治干预的非洲国家中具有良好声誉。它的退出可能会得到国际社会中那些将主权置于人权保护和刑事司法全球化之上国家的同情,最终甚至会带来经济收益。(60)同⑥。一般而言,在国际声誉较好的国际制度内,国家即使出现利益损耗也会谨慎选择退出;在国际声誉较差的国际制度中,国家则更容易形成退出偏好。
国际制度中的利益损耗并不必然使得国家形成退出的行为偏好,但会使国家内部出现调整国际制度行为的需求。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实力地位对国家的退出策略(实质性退出或威胁退出)产生影响。若国内利益主体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退出”的变化,如倾向于改变体系的领导人或执政党上台,而国际制度对于退出行为的约束力较弱,那么国家就可能形成退出偏好。
四、国内—国际互动与国家的退出决策
退出偏好并不必然形成退出决策,只能对国家行为进行趋势性解释,但无法判断特定国家在特定时间的具体行为。国家退出国际制度既是国际体系层面的问题,也是国内政治博弈的结果。作为一种对外决策,退出某一国际制度也并非简单地由国家决策者主观决定,而要受到国际体系压力和国内政治框架的共同束缚。国家与国际制度的相互依赖程度是判断国家退出在国际层面成本收益函数的重要指标,国内决策结构的集中与分散程度高低则是国家退出能否在国内获得“批准”的重要因素。退出偏好转化为外交政策实践也是国内—国际互动的结果。
4.1 国家与国际制度的相互依赖程度
国际制度中权力结构的变化会对国家的退出偏好产生影响,但并不是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决定因素,无论是强势国家还是弱势国家都有可能在利益受损时选择退出。但是,不同国家的退出成本和退出前景是不同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与国际制度的相互依赖程度。
一方面,国家对国际制度依赖程度越低,说明国际制度所涉议题领域同国内事务联系的紧密程度越低,国家退出的可能性就越高。国家之所以愿意参与国际制度并接受国际规则的约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家对国际制度及其主导国提供的市场、技术、资本、政治支持和安全保护等存在依赖性,不遵守相关规则的机会成本很高。(61)潘忠岐等著:《中国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页。国家对国际制度依赖程度较高,意味着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成本较高,当国际制度不能满足国家需求时,国家可能会通过呼吁变革或威胁退出策略来改变自身在国际制度中的不利处境,而不会贸然选择实质性退出。相反,若国家对国际制度的依赖程度较低,说明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获益有限或有其他替代选项,其退出国际制度的成本也较低。因此,当国际制度无法再满足国家需求时,国家极有可能直接退出。
国家对国际制度的依赖程度可以作如下衡量:一是,入会条件的高低。加入一个群体的条件越严格或费用越高,说明加入时投入的成本较高,人们就越发认为该群体具有较强的吸引力。(62)[美]艾伯特· O. 赫希曼著,卢昌崇译:《退出、呼吁与忠诚:对企业、组织和国家衰退的回应》,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122页。国家加入国际制度的成本不仅包括国家在国际层面的谈判努力,做出的国际承诺,还包括国家内部的政治博弈,相应的国内制度变革等。高成本说明国家对加入国际制度的预期收益较高,对国际制度的依赖性越强,退出的成本也越高。相反,加入国际制度时的成本越低,说明国家投入的成本越低,那么退出的成本也相对较低。二是,竞争性国际制度存在与否。竞争性国际制度的存在或多或少会降低国家对某一国际制度的依赖程度。(63)Scott Kasner, Margaret Pearson, and Chad Rector, “Invest, Hold Up, or Accept? China in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Security Studies, Vol. 25, No. 1, 2016, pp. 142-179.制度的非中性和非唯一性(即在同一个议题领域或同一个区域可能存在多个国际制度)为国家在国际制度之间的选择创造了空间,(64)李巍、罗仪馥:“从规则到秩序——国际制度竞争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4期,第38页。即国家在退出后不至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而是可以加入其他竞争性的国际制度。即使不存在竞争性国际制度,对现行国际制度不满的强势行为体,也可通过机制转换和创建竞争性机制的方式建立可信的外部选项。(65)See Julia C. Morse and Robert Keohane,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9, No.4, 2014, pp.385-412; [美]罗伯特·基欧汉:“竞争性的多边主义与中国崛起”,《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 年第6期,第20-27页。因此,无论是在同一领域或同一区域存在多个国际制度,还是强势国家在外部创建新国际制度的预期,都会降低退出国对当前国际制度的依赖程度,因为还有其他选择。
另一方面,国际制度以及制度内的其他成员国对退出国的依赖程度越高,退出国越有可能通过内部呼吁或威胁退出来达到目标,而不必实质性退出。这样的退出国往往是国际制度中的主导国或关键成员,其他成员国不愿意承受其退出带来的巨大损失,往往会选择尽力满足其需求。因此,国际制度中的主导国或关键成员在制度谈判中的议价权力较大,可以通过威胁退出来呼吁制度改革,这种呼吁的成本较低,且很容易得到制度内其他成员的回应,从而达到目标。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威胁要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之后,相关国家都同意开启重新谈判并达成了新的协定。制度内非关键成员的威胁退出却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因为制度内的其他成员国往往对其依赖程度较低。非关键成员在国际制度内部进行改革呼吁,不仅成本颇高,也很难得到积极的回应;更为弱势的国家甚至会在国际制度中被边缘化。
4.2 国内决策结构的集中与分散程度
决策者和执政党对国际制度的消极态度并不一定导致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行为,只会增强决策者在推动国家退出过程中的主动性。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同,利益分配方式也不同,决策者做出退出决策时面临的国内制约因素也不一样。国家并不是单一的理性行为体,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决策很少反应单一或一致的国家利益计算,国内不同政治和社会力量对国际制度的态度可能并不完全相同,最终做出退出国际制度的决策还取决于退出国的国内决策结构。决策结构越集中,意味着参与决策的人数和机构越少,决策者受到的国内限制就越少。例如,一个专制或独裁的政府,国内政治对对外政策的影响和限制总体上是有限的,领导人的决策余地很大。(66)张清敏著:《对外政策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62页。因此,当决策者偏好退出且国内决策结构更为集中而不是分散时,国家更有可能退出国际制度。
决策结构越是分散,意味着参与决策的人数和机构越多,考虑的要素也就越多,国家关于退出国际制度所受到的国内政治竞争影响就越大,甚至会出现制衡情况。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决策实际上就是国内不同政治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博弈的结果。例如,南非政府于2016年向联合国提交了决定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有关信件,并决定正式启动退出该机构的程序。然而,在野党向南非高等法院提起诉讼,即南非政府在未经议会批准和未向公众咨询的前提下发出了退出通知。(67)Manisuli Ssenyonjo,“State Withdrawal Notifications from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outh Africa, Burundi and the Gambia”, Criminal Law Forum, Vol. 29, No. 2, 2017, p. 3.2017年2月,南非高等法院作出判决,南非政府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违宪。(68)“南非高等法院判决南非政府退出ICC的决定违宪”,中国新闻网,2017年2月22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02-22/8156904.shtml。最终,南非政府正式撤回了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的申请信件,提前终止了退出该国际组织的程序。虽然南非政府终止退出程序是因为“程序不正确”,但也反映出南非国内对于国际刑事法院的不同态度。
国家在国际制度中成本上升和收益减少的变化,首先会反映在普通民众而非政治精英身上。在他们看来,退出国际制度的确会带来国内政治收益,并卸掉参与的负担。虽然民意和舆论并不会直接转化为政治家的行动或国家的退出实践,但民众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外交政策,如在民意测验中的表态、利益集团或社会组织的游说,以及对国会议员的影响等。民众对国家国际制度行为影响最直接的渠道是针对特定问题的公投,之后国家根据公投的结果做出决定。例如,英国的“脱欧”公投,支持“脱欧”的结果为英国国内长期以来具有争议的政策做出了最终决定。而美国民众在2016年选出了奉行“美国优先”的总统,关注国内改革和重建,在国际上表现为减少责任和退出国际制度。(69)Randall Schweller, “Opposite But Compatible Nationalism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Approach to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1, No.1, 2018, p. 15.
对于不同的国内行为体而言,退出国际制度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越低或收益越高,其支持退出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分散的决策结构下,国内反对退出和支持退出群体之间的力量对比,最终可能影响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决策。国际制度所涉议题领域的性质及其同国内事务联系的紧密程度,会对国内行为体退出国际制度的分歧程度产生影响。在涉及诸如国家领土、主权和安全等同质问题时,国内反对力量同政府总体上是一致的,这种情况下领导人往往具有更大的主动权;对于一些国内存在不同意见和主张的异质问题,如涉及众多国内利益攸关方的对外经济政策,受到国内政治影响的程度就更深。(70)张清敏著:《对外政策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3-144页。
国际制度与国内事务的联系越紧密,国际制度所涉的国内行为体就越多。不同的行为体会采取措施影响政策朝于己有利的方向发展,对于国家是否应该退出该国际制度的分歧就越大。即使决策者和执政党已经形成了退出的偏好,最终可能无法形成退出决策。反之,与国内事务联系松散的国际制度所涉的行为体较少,利益分歧也较少,对于国家是否应该退出国际制度更容易达成共识。
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决策实践不仅要考虑国际层面的成本和收益,还要考虑国内层面的成本和收益。其中,国际层面的主要变量是国家与国际制度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国家对国际制度的依赖程度越高,退出成本越高;依赖程度越低,退出的成本也就越低,退出的可能性更高。国际制度对国家的依赖程度越高,国家通过威胁退出来呼吁制度内改革的成本就越低,而无需实质性退出。同时,通过政府间会议达成的重大制度变化都必须得到国内批准。国内决策结构越集中,获得国内批准的成本就越低,国家的退出偏好越容易形成退出决策;国内决策结构越分散,国家的退出决策就越容易受到国内不同行为体利益分歧的影响,而这种国内分歧又受到国际制度所涉议题及其与国内事务联系紧密程度的影响。
五、结 语
国际制度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国家在国际制度中的收益也不断变化。理性主义者认为,当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成本大于收益,即出现利益损耗时,国家就会退出国际制度。实际上,即使出现利益损耗,无论是绝对或相对收益的损耗,还是利益认知的变化,国家在国际制度中面临的并非只有“退出”这一种选项。国家之所以选择退出,主要是出于对短期内退出成本和收益的衡量以及对退出前景的预期。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是一个复杂的国内—国际互动过程,退出的偏好和决策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形成的。国际制度中的权力分配、国内利益与偏好、国际制度约束力等因素都会对国家的退出偏好产生影响。然而,退出的偏好是否会产生退出的决策和行为,其关键在于成本与收益是否平衡及国内“批准”与否。
在国家主权原则下,各主权国家均享有退出国际制度的权利。国家选择退出某一国际制度框架,即对该领域的国际合作选择消极甚至背叛的态度,通常被认为是其对该体制表明不满的一种信号。如果赋予国家在必要时退出国际制度的权利,就能顾及国家行使主权的需要,并提高其参与国际合作的积极性,最终提升国际制度的运行效率。(71)韩逸畴:“退出,呼吁与国际法的演化和发展——基于阿尔伯特·赫希曼的理论视角”,《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192-193页。国际社会不同于市场和企业的制度环境,国家虽然可利用退出机制增强在世界舞台上的发言权,但不可能完全退出国际制度而单独存在。(72)Laurence R. Helfer, “Exiting Treaties”,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91, No.7, 2005, pp. 1579-1648.国家退出国际制度并不意味着国家彻底与该制度或相关问题领域割裂,而是对国际制度的反向参与。(73)“反向参与”的概念参见史明涛:“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一个国际—国内制度互动的解释”,《国际观察》,2009年第2期,第57-64页;韦进深著:《决策偏好与国家的国际制度行为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版。事实上,“退出”也是各国政治博弈的手段。特朗普政府在声明退出或威胁退出国际制度时仍然表示会推动新的国际谈判开展,或者要求相关国际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国际制度作为大国政治工具本身还没有被完全抛弃。(74)温尧:“退出的政治:美国制度收缩的逻辑”,《当代亚太》,2019年第1期,第30页。
国家加入国际制度是为了加强某一方面的合作,但是国际制度并不总能为国家带来制度红利,有时甚至是负担。因此,国家在必要时采用“退出”手段来维护国家利益。当前的国际体系处于深刻变化的过程之中,也涌现出一些国家退出国际制度的现象。尤其是主导国的退出,实际也为新兴国家提供了制度参与和构建空间,若能利用机会加大对国际制度的投入和参与,将大幅提高自身在国际制度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并进一步推动国际制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