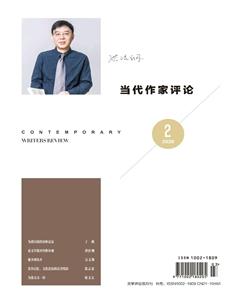“半开之美”与“越轨的笔致”
一
提及金仁顺,我们马上想到的或许就是“70后”女作家这样的文学史标签。“70后”是标记代际属性,女作家凸显的是性别意识。尽管这两个标签是金仁顺身上最为显著的文学史标志。但是随着“80后”、“90后”作家的涌现,“70后”集体出场时的代际轰动效应已然弱化了许多,或许当初这个标签也只是一群作家在文学批评或文学史中的出场方式而已,并不能真正代表那些作家的总体性特征。而由性别带来的身份意识,在随后的写作中也是不绝如缕,并非哪位女作家所独有。在今天看来,这两个文学史标签已经成为了一对空洞的能指与滑动的符号,显然无法准确地概括出金仁顺创作的独特之处和她的文学成就。
金仁顺写过一篇随笔叫《半开之美》。文章讲有个男人娶了一位美妻。两人每晚都到夜总会或酒吧坐坐,但两人从来都是分开而坐。丈夫从旁观看各色男人与妻子搭讪、调情。在金仁顺看来,这位丈夫是个聪明人。聪明之处有二:一个是他知道“满园春色”是关不住的;另一个是他对外宣称女子是他的未婚妻,“未婚,又妻,既亲近又隔着一层窗户纸。空间却就此产生了,还是一个弹性的空间”。这个弹性的空间持续了很多年,女人一直有令人瞩目的风韵,男人的风度更是耐人寻味。在金仁顺看来,这层“窗户纸”抑或“弹性的空间”就是“半开”的花朵,千回百转,时时动人。“绽放的花朵,美则美矣,但一览无余,终归少了些回味。微绽初放时,含着种种低回婉转,蕴藏着种种可能性,任是无情也动人。”
这种“半开之美”除了婉转含蓄低回之外,还代表着某种“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亦如金仁顺在随笔《暧昧》中谈男女情事的“暧昧”一般,“有关系必然有暧昧。一道残阳铺水中还半江瑟瑟半江红,没有残阳铺水中,也还有春来江水绿如蓝呢。暧昧关系,本来就有宽阔的空间,所有的暧昧关系都是灰色地带”。这种“暧昧”不仅仅是在感情上,在人生的其他方面也是如此,许多“神来之笔”都来自这“暧昧”带来的“宽阔空间”。这也很像张爱玲说的“参差对照”,“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极端的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存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张爱玲:《关于〈倾城之恋〉的老实话》,《倾城之恋》,第463页,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在我看来,这种“半开之美”是金仁顺创作的美学风格或总体性的特征。当然,这种“半开之美”并不一定是金仁顺所独有的,它承继着某种现代文学以来的文学传统,可能是某一些作家的“家族性相似”,但它却也实实在在出现于金仁顺的创作之中的。
二
金仁順是朝鲜族。这个少数民族身份是她与生俱来的一个标志。几乎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会在自己的创作中书写本民族的风物、记忆与历史。金仁顺自然也不例外。尽管金仁顺并不是以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在文坛上亮相的,但她的少数民族身份越来越被大家关注,在她自身的创作中也渐有这种少数民族身份的自觉,“是的,最近这几年越来越被强化。我个人觉得我确实也有这个责任和义务。 我毕竟是有民族身份的,大家都来介绍中国文学,那我来介绍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我觉得很好”。 ② 金仁顺、 邓如冰:《“高丽往事”是我灵魂的故乡——金仁顺访谈》,《西湖》2013年第5期。《高丽往事》《春香》《僧舞》等所谓的“高丽往事”,就是金仁顺对自己少数民族身份自觉创作的代表性作品。除此之外,我们在金仁顺的其他作品中,也会常见到她提及的故乡往事与民族记忆。朝鲜族身份对金仁顺的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她“灵魂的故乡”。这个“灵魂的故乡”不仅是金仁顺文学世界的重要根基,同时,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到金仁顺的“半开之美”,她文字中最柔软的那部分,我“一写朝鲜族题材,整个调子一下子就舒缓起来,仿佛画面一样徐徐展开……可见民族身份对我多重要,是我内心多么柔软的一部分。当我写朝鲜族题材的时候,我就觉得你们不了解我们,我有必要写一些闲笔。写一点衣食住行,写一点闲情逸致,让你们了解我这个民族的一些特质的东西,这样一来,节奏就完全不一样了”。②
无论是文化身份的认同,还是民族身份的认同,除了与生俱来的“基因属性”之外,作家往往都是以回溯民族历史的方式,来寻找、重构自己的民族记忆,并以此来确认自我的民族身份认同与自觉。只有经过了这样一个“自我指认”的过程,民族身份与民族记忆才能在一个人的身上被激活,成为一种“活”的、生气勃勃的标志。金仁顺在《高丽和我》中说过,“高丽”这两个字曾经让她十分痛恨,斗转星移,曾经被痛恨的“高丽”已然成为“山高水丽。如此浩阔,如此明媚”的两个字,“如同言情电影里男女主人公从看不顺眼到爱得不能自拔一样,我在长大成人之后,忽然爱上了这个民族的很多东西。我不知道这个过程是怎么完成的,忽然之间,我体味出原本被我厌弃的东西中间,埋藏着别致的美丽。这种美丽因为在意料之外,惊心动魄。少年时担心被独自抛弃的恐惧在我成年后变成了惊喜,我发现我拥有一个藏满宝藏的山洞,而开洞的咒语,只有我知道”。金仁顺:《高丽和我》,《广西文学》2019年第1期。
长篇小说《春香》就可看作金仁顺对自我民族身份的一次自我确认。《春香》取材于朝鲜族民间故事《春香传》,尽管金仁顺对这古老的民间故事进行了“故事新编”,甚至可以说“《春香》和《春香传》是没有关系的”,金仁顺是以一种“现代”的眼光来重新演绎了封建时代朝鲜半岛上的女性对自身命运的选择,当然春香的选择不是“古典”的,而是“现代”的。金仁顺一方面在这种对民族历史的书写中进行自我身份的确认,另一方面她也不甘于仅仅回到民族故事的“历史现场”,写出“原汁原味”的民族历史,而是从“民族秘史”的叙述中跳脱出来,以现代的个人主义视角和女性意识去审视民族历史中女性的命运。金仁顺的这种书写一方面是确认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另一方面这种现代性元素的介入,显然也是她对自我民族身份的一种超越。
金仁顺在一篇访谈中曾经说过:“少数民族题材,很容易写得狭窄,格局小,我很担心这个,所以,我觉得,真正有前途的写作,还是应该更多地关心普遍性,跟当下社会的关系应该保持亲近、紧密。”在我看来,《僧舞》就是将民族题材与“普遍性”和“当下社会的关系”融合得极好的一篇作品。《僧舞》最集中体现了金仁顺创作中的“民族性”和“超越性”。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2期 “僧舞”是朝鲜族的一个民间故事,讲述的是名妓黄真伊穿僧服跳舞,诱惑知足禅师破戒的故事。小说《僧舞》就源自这个民间故事。正常来说,明月(一个在浮世红尘中舞动的歌舞伎)与知足禅师(一个在清幽林间苦修的高僧)本是没有任何交集的两类人,但这两段没有交集的人生轨迹,却因为歌舞伎明月的“灵魂”追求与玄思冥想,产生了交集。
明月见了知足禅师直截了当地问:“请问大师,我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肉身?”
知足禅师道:“人生难得,理当自重。”
明月并未满足大师的解惑。人生的烦恼并不在“肉身”,而在于“肉身”之外还有“灵魂”,两者遵行的是不同原则,难以并行不悖。所以明月才接着发问:“虽然自重,但有时,灵魂似乎能自行从肉身中飞,蝴蝶般落在旁侧,观看肉身的喜怒爱恨,凡此种种。”大师道:“凡此种种,皆是空相,修行,能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不会为诸相苦恼了。”
明月痴念于肉体纵情的快乐,被男子迷恋的喜悦。而知足禅师觉得,这一切行色快乐,都是过眼云烟,稍纵即逝。人生苦短,悲苦无限,不可在这肉身的迷途中耗尽生命。正是看透了红尘的迷途与短暂,知足禅师才来到这清幽之地苦修,物我两忘,尤其是忘记那“沉重的肉身”,以期获得人生的“澄明之境”,精神的安宁。而明月却沉溺于这肉身带来的快乐,这快乐是青春的馈赠,人生苦短,韶华易逝,更不该辜负这稍纵的青春。与其说明月是来找知足禅师解惑的,不如说她是来与知足禅师辩难的。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两位的“三观”严重不一致,以知足禅师的“悲苦”“人身自重”怎能理解明月的“流光溢彩”与“肉身之乐”呢?
明月不仅美貌,还有舞蹈天赋,也有俗世间女子的痴念与凌厉。她的辩难紧逼知足禅师的答问,一度将知足禅师逼迫到了“解释学”的困境之中。困境之下,语言的辩难已经苍白无力,在语言两端的明月与知足禅师,均各执一词,难以说服彼此,犹如武林高手间“推手”一般,推来挡去,不见胜负。言辞的困境,终于被明月的舞姿打破了。明月为知足禅师跳了一支舞。舞动起来的明月,摇曳生姿,“在灯影中,她的手臂枝条般伸展、生长着,宛如春天新叶出萌,万物生发;她的腿,却是属于夏季森林和草地的,修长,优美,随时要跃动、腾飞,踢踏起野花的芬芳;她的僧衣果皮般从身体剥落……”舞动中的明月仍不忘辩难知足禅师,“肉身,难道不应该被亲近、被享受、被追忆吗?”最终,明月倒在了知足禅师的怀中呢喃道:“人身难得,理应自爱。”
小说《僧舞》的素材虽然是来源于朝鲜族的民间故事,但我想金仁顺写这篇小说的目的,不大会是或主要不是给我们讲述一个与自己民族有关的传说故事,她应该有更大的抱负或文学“野心”。我以为《僧舞》的价值,除了其作为“民俗志”的价值之外,更在于超越了少数民族故事的限制,直面我们当下每个人的一个大问题或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即我们每个人在这浮世红尘中如何安放肉身的问题。“沉重的肉身”是与生俱来的,是无法回避的。知足禅师的一句话讲得很好“人身难得,理当自重”。人生的苦与乐,或许就都来自这“沉重的肉身”。“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生命状态的两端。人生的悲苦大概属于“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当然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力量也是有“重”量,有质感的;贪恋于肉身的快感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荒芜与无质感,大体上属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明月的痛苦来自后者,她是要留住肉身的轻盈与美丽,享受俗世的繁华喧闹;知足禅师的悲苦来自前者,他要摆脱这肉身的庸常与烦难,逃离万丈红尘中的过眼云烟。痛苦既来自肉身,也来自于对肉身的思索。正如米兰·昆德拉有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是,正如肉身是与生俱来的一样,思想亦是人类的本性。因此,无论是肉身的悲苦,还是思想的烦恼,都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既然无法回避,或许就该顺着“本性”而为,肉身的悲苦与快乐,思索的烦恼与愉悦,都该欣然领受。无法寻求绝对的“享乐”与“超脱”,那就在“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间,找到适合自己的钟摆,在摇荡的生命韵律中,达到生命的中正平和,快乐安宁。
《桔梗谣》,仅从字面上看,就知道这肯定是一部与朝鲜族有关的小说,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金仁顺将一个有情人未能终成眷属的世界性文学悲剧,写进了她所熟悉的朝鲜族的生活中。一个男人忠赫听从母命,与自己不爱的女人春吉成家生子。不仅婚后对自己的意中人秀茶念念不忘,而且两人的情种还开花结果了。这意外的“收获”(万宇)自然给秀茶带来了不少痛苦,“她男人老打她,孩子被打流产过,还有一次打折了肋骨”。小说的高潮是忠赫带着春吉和两个孩子去参加万宇的婚礼。本是“情敌”的春吉与秀茶,见面后卻抱头痛哭,似乎要一哭泯恩仇;忠赫却“紧盯着大屏幕上的照片,这孩子小时候非常瘦弱,有些惊恐地瞪着镜头;五六岁以后,他好像不那么怕照相了,其中有一张照片活脱脱就是忠赫小时候的模样”,忠赫犹如在镜中与自己的童年重逢,体验这份岁月沉淀带来的“惊喜”:
忠赫去了一趟厕所,万宇在洗手,他们的目光在镜子里相遇,忠赫冲他点点头,走进厕所,解裤带时,他的手抖得很厉害,花了平时两倍的时间。他摸到了裤带里面的信封,除了春吉带着的三千块礼金,他把自己的两万块私房钱全提了出来,他知道万宇不缺钱,但他不知道,除了钱,他还能怎么表达自己的感情。
这重逢的一幕,尽管很尴尬,但对忠赫来说却很温暖。一个父亲第一次“正视”“自己”的儿子,却是在儿子的婚礼现场,这里既有愧疚,又有喜悦,有悲苦,也有欣慰。“半开”相对的情绪五味杂陈,这也是金仁顺写作中的另一副面孔,她一写朝鲜族题材,笔调就不那么冰冷坚硬,总是有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
在这些朝鲜族题材小说中,金仁顺自然也会写到朝鲜族的一些风俗人情:
秀茶结婚时,忠赫天不亮就起来,跟另外几个小伙子一起在院子里打打糕,刚蒸熟的糯米米粒晶莹剔透,像颗颗泪珠,他们用的木槌三斤半重,要几万槌才能把这些泪珠打成死心的一团。(《桔梗谣》)
黄励也是刀子嘴豆腐心。他们出发那天,她起早煮软软的白粥装进保温饭盒里面。饭盒上面的夹层里准备了苏启智以前爱吃的泡菜。怕他胃不行,用刀剁成了末,又另外拿了一个饭盒装了十几个茶蛋。(《仿佛依稀》)
朝鲜族一般在重要的日子里都会做打糕。秀茶结婚是大喜的日子,自然要有打糕这种带有强烈仪式感的食物;同时,这也是忠赫和秀茶的悲情之日,相思之泪在一次次锤打中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悲苦。如果说打糕是仪式性的,那么泡菜则是日常性的。制作泡菜是每一位朝鲜族女性的“必修课”,“每年秋天的泡菜季,白菜摞成山,一遍遍地清洗,盐渍去水汽,再清洗,腌菜的缸可以装下三个成年人,大蒜要成盆成盆地扒,还要捣成蒜泥;鲜红的干辣椒成堆地被石磨研细,还有生姜、苹果、白梨、盐、味精、白糖,一盆盆的调料最后融合在一起,艷丽夺目,像秘密或者诺言似的,层层抹入白菜菜帮之内,最后收拢封好,等待发酵”。金仁顺:《高丽和我》,《广西文学》2019年第1期。朝鲜族日常必吃的泡菜,在金仁顺笔下不仅是一道朝鲜族的风物,而且变成了一个温馨的记忆。苏启智是大学教授,黄励是他的前妻。黄励之所以成为“前妻”,是因为苏启智的“师生恋”,把学生变成了“师母”。黄励一个人带大了新容,她对苏启智恨之入骨,各种咒骂都用上了。但当得知苏启智胃癌晚期后,她还是给丈夫带上了爱吃的泡菜。“苏启智看到粥和泡菜,表情一顿。”这一顿,让苏启智诸多往事上心头啊!人生的晚景在回忆往事中也被拉长了一些。
三
鲁迅在给萧红的《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赞扬萧红作品中有“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生死场〉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4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金仁顺的一些小说就颇有这种所谓“越轨的笔致”,这种别样的笔致让这些小说充满了一种独特的质感和张力。小说《松树镇》讲的是“我”和几个朋友为了拍一部关于矿区中学生的“地下电影”——影片涉及中学生早恋、怀孕,还有绑架、坠井等方面的内容——而到松树镇看矿井,去学校选演员。松树镇有“我”的老朋友,一切事情都很顺利,任务完成我们准备打道回府:“我们去车站的时候,张今芳和孙甜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消息,跑来送我们。‘你们一定会回来吧?她们问了一遍又一遍,火车开起来时,张今芳一边跟着火车跑,一边还在问。‘一定我们跟张今芳挥手,跟孙甜挥手,跟赵红旗张景乾小莫挥手,跟松树镇挥手。我们确实以为我们会回来,在一个月后。”结果因为投资方的艺术热情消退,我们的电影没有拍成,我们再也没有回到松树镇。电影毕竟不是几个文艺青年靠热情就能拍成的,投资方的艺术热情飘忽不定,这都在情理之中。如果小说就这样结束了,倒也算是中规中矩的套路。可金仁顺并没有就此打住,加上了一个与小说前面内容非常“不相干”的结尾,我在铁北监狱里见到了孙甜。毕业后孙甜被招聘到电视台工作,为了有个编制,孙甜和台长有了暧昧的关系,结果被男朋友发现。男朋友要把事情捅出去,孙甜就开车撞死了他。孙甜见到我也没有多少意外:
“我们一直等你们来!”孙甜说。
“——对不起。”
“谁都知道我们要拍电影了,谁都问我们,在电影里面要演什么。”孙甜看着我,“我们不知道电影里要演什么。你现在告诉我,那个电影讲的是什么故事?”
我把剧本的内容告诉了孙甜:
是矿里的几个初中生,白云飞扮演的男生跟你还有张今芳扮演的女生是同学,白云飞喜欢你,但你却跟体育老师好上了,还怀孕了,他为了帮你忙,去找张今芳借钱。在电影里,张今芳的爸爸是小煤窑主,很有钱。张今芳不肯借钱给白云飞,说话还很刻薄,把白云飞给惹火了,他就绑架了张今芳,跟她爸爸要钱,张今芳逃跑时,掉到一口废弃的矿井里。白云飞勒索张今芳的爸爸,被警察抓住了,他到底也没能帮上你——你演的那个女生。
孙甜对剧本大失所望。但现实中孙甜的人生与剧本中的白云飞何其相似。剧本与现实构成了某种“互文”关系。现实中的人生命运,早已在剧本中被摹写了。我们也很难分清倒底是剧本中的情节“残忍”,还是现实中的命运悲惨。只有这越轨的笔触才能写出这戏如人生与人生如戏的精彩“互文”。
在金仁顺的小说中,《芬芳》也算是比较特别的一篇。金仁顺的小说一般与社会上的一些事件、现象都没有太大的关联,即便是在她的文字中出现一些,也都是浮光掠影,一带而过罢了。但是《芬芳》不同,它是以90年代流行的“传销”为核心来叙述的。芬芳从“雅芳”开始,一路干到“仙妮蕾德”“丝昂”。芬芳的事业越做“越大”,但也未见她“飞黄腾达”。90年代“传销”的影响很大,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多数人的结局是被“套牢”了,不仅没有发财,反而是“血本无归”。芬芳的命运自然不在此列,要不这小说也无什么特别之处了。金仁顺没有让芬芳套牢在传销的窘境中,而是让一次意外之祸结束了芬芳鲜活的生命,芬芳“蓬勃发展”的事业也随着一起烟消云散。芬芳酒后从三米高的地方坠下,当时便失去了知觉,送到医院抢救,一度出现“奇迹”,但最后还是走了——这恐怕就是小说和新闻的区别,或者说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与一部庸常的小说的不同。这也是金仁顺小说的“越轨”之处,这种“越轨的笔致”常常让小说呈现“跨越式发展”。因为是“跨越式”的,自然也就是惊人的,出乎意料的。
四
金仁顺早期的小说如《名叫马和》《听音辨位》《一篇来稿和四封信》等都是极具“先锋性”的作品,这可能是“70后”作家出场时的普遍姿态。除此之外,金仁顺还写了不少都市情感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写得也都精致细腻,直面当代人的情感困境,但也不算金仁顺的独特之处。本文就不做详细讨论了。
金仁顺生活的城市是长春或广而言之生活在东北。但我们在金仁顺的文字中会发现,她与长春或东北有着明显的“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与上文所言的“半开之美”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一起构成了金仁顺的文学“炼金术”。虽然在金仁顺的创作中也会时常出现长春或朝鲜族的一些风物,如重庆路、医大二院、日式建筑等,但她的创作并不依赖这个“地域性”资源,这是她与许多出身东北或身在东北的作家的不同之处。对她来说,“地域性”不应该,至少不是全部“题材性”的内容,而是一种观看世界的方式。金仁顺在这方面的分寸拿捏得特别好,让她显得与众不同。
〔本文系吉林大学校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世纪小说研究”(2018XXJD0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涛,吉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