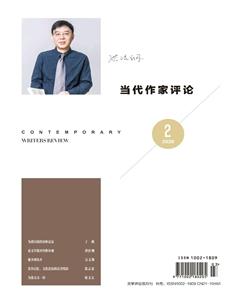极端境遇中人性面向的反思
汪曾祺新时期小说研究多围绕展现其“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一面的高邮故里小说而进行的。而从艺术渊源的角度强调汪曾祺对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抒情小说”传统、西南联大传统的继承,甚至指认为他为“京派”后人的观点影响很大。如黄子平从“现代抒情小说”传统与当代寻根文学论及汪曾祺小说的“回忆”和“遗忘”的中介机制,见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234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谢泳则强调西南联大作为五四新文学新文化传统的精神家园,奠定了其自由主义文人的身份地位,见谢泳:《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穆旦的文学道路》,《文艺争鸣》1997年第4期;严家炎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则把汪曾祺视为京派传统的最后传人。然而其前提都是对于他50—70年代经历有意无意地“忽视”。这造成的印象便是汪曾祺似乎“遗忘”了政治,尽管从作家个人经历来看与政治有密切关系:他解放初在江西参加过“土改”,也有被错划成“右派”下放劳动的经历,甚至一度悲观。
事实上,“遗忘”政治的或许是某些研究者。其实也有论者注意到汪曾祺50—70年代的经历及创作,但其中涉及的小说并未正面表现50—70年代的现实政治经历。如王彬彬对《羊舍一夕》的文本细读,从文本修辞和文体意义上谈鲁迅对于汪曾祺的影响,见王彬彬:《“十七年文学”中的汪曾祺》,《文学评论》2010年第1期;罗岗则将40—80年代空白期视为其创作的重要影响时期来考察,见罗岗:《“1940”是如何通向“1980”的?——再论汪曾祺的意义》,《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有论者就指出:“其实汪曾祺的看透和规避政治并非遗忘政治……他的不少小说,包括去世前一年的《当代野人系列》,都是写‘文革的。”郜元宝:《汪曾祺的两个年代及其他》,《岂敢折断你想象力的翅膀》,第7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从创作的数量和占比来看,新时期以来发表的超过五分之一的20篇小说都属于这类以50—70年代重大政治事件为背景或故事线索的政治题材小说,分量不小。根据2016年版《汪曾祺小说全编》目录统计,汪曾祺:《汪曾祺小说全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且贯穿新时期创作始终,而他此前从未创作过这类小说。
汪曾祺绝大多数小说都以生活经历中熟悉的人事为基础,具有明显的地域特点。因而笔者按照地域对这20篇政治题材小说进行分类,由此进行文本细读式的整体考察。在考察中试图对其艺术特征进行总体的把握,从而展现汪曾祺创作的“另一面”,由此个案反观文学史中的作家定位问题,再思政治与文学的关系。
一、北京:人与兽的世界
以北京为背景的作品多发生在“文革”时
期的剧团内。共计14篇,包括:《天鹅之死》(1981)、《尾巴》(1983)、《云致秋行状》(1983)、《郝有才趣事》(1985)、《虐猫》(1986)、《八月骄阳》(1986)、《子孙万代》(1993)、《非往事》(1994)、《唐门三杰》(1996)、《当代野人》(1996)、《不朽》(1996)、《当代野人系列三篇》(1997)、《八宝辣酱》(未编年)、《焦满堂》(未编年)。在那种极端的政治境遇里,扭曲的文化心理和人性得到了最充分的暴露,这些小说堪称创造了“人与兽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人”多为在舞台上的演员以及幕后的工作人员两类“小人物”。无论台上风光还是幕后无名,都有自知之明:工作上兢兢业业,并不希望扬名显身。他们在剧团里虽说不是可有可无,但也容易被遗忘。然而也正是他们在此上演了一幕幕令人印象深刻的悲劇或喜剧。
《云致秋行状》里的云致秋是前者的代表。他有本事:嗓子好,“很聪明,模仿能力很强”,“又有文化,能抄本子”。但他不贪功求多,只当好“二旦”。更重要的是他有自己的一套为人处世的哲学,即戏班里流传的处世格言:“小心干活,大胆拿钱”,“不多说,不少道”。平日虽然聊得热乎,“但都是海聊穷逗,从不钩心斗角,播弄是非”。这样一个好人却在“文革”的冲击下崩溃了——“他不但不知道怎么说话,怎么待人,甚至也不知道怎么思想”,组织、领导和同志都无法依靠,而老伴被吓得犯心脏病,“他发现他是孤孤仃仃一个人活在这个乱糟糟的世界上,这可真是难哪!”
“文革”对人们最重要的冲击是心理的。云致秋原有的那套哲学崩溃后,心理的扭曲难以避免,这又导致其日常行为的“异化”,他做了三件“在平时绝不会做的事”:“揭发批判剧团的党委书记”,“把有关治安保卫工作的材料,就是他到公安局开会时记了本团有关人事的蓝皮笔记本,交出去了”,“写了不少揭发材料,关于局领导的,团领导的”。 ②③④ 汪曾祺:《云致秋行状》,《汪曾祺小说全编》(中),第662-663、667、668、6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虽非出自本性,只是在极端境遇下为求生存的无奈之举,却使他苦心经营的人际关系破裂。“四人帮”倒台后,他没有被安排工作,又遭丧偶,更感寂寞痛苦。在“我”探访他的时候,他半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这也是一辈子。我算个什么人呢?”②他死后葬礼清冷,“一个小礼堂,稀稀落落地站了不满半堂人。”③尽管补写了光明的尾巴,汪曾祺以不无称赞的语气写道:“一个人死了,还会有人想起他,就算不错。”④但好人在极端境遇下心理扭曲,误入歧途的遭遇带来的悲凉氛围终难消去。归根到底,人承受了本不该承受的历史沉重。
在这里,即便幕后籍籍无名者也不得不“粉墨登场”。《郝有才趣事》里在舞台工作队工作的郝有才,是个不起眼儿的人,“没有什么露脸的事”,却有点小毛病,“过日子特别仔细,爱打个小算盘”。 ⑥ 汪曾祺:《郝有才趣事》,《汪曾祺小说全编》(中),第734、7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但遇上“文革”,居然得到“露脸”的机会。郝有才自掏腰包换掉打碎的暖水壶胆这样一件小事是在追求“思想进步”,抓典型的时候也被团里的军、工宣队当成“他们的思想工作的结果”。目不识丁的他被安排在全团大会上做了一次“讲用”,一上台就引起哄笑:“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卒 瓦了就卒 瓦了!”⑥这里的“卒 瓦”是北京土话“打碎了”的意思,而毛主席语录里居然会有北京土话——意在展示思想工作成果的大会成了闹剧和笑话。《不朽》里老实本分的梳头师傅赵福山同样被抓成典型——会议组长甚至要讨论他的“艺术思想和美学思想”。于是工作上的本分负责和纠正同志背语录时的北京土话被视为政治思想先进突出,把样板团的好饭菜带回家给孙子吃,喜欢天天吃炸酱面被当作生活作风朴素。故事结尾的献花圈和“赵福山同志永垂不朽”的呼声,以及所有人给赵福山三鞠躬的滑稽场面把故事推向了高潮。若说《郝有才趣事》只是让普通人变成大会先进代表,人物还有些自鸣得意,更近于有讽刺意味的闹剧的话,那么《不朽》则从标题到表彰过程都解构了极左时期整套关于“革命英雄”的神话,讽刺力度和深度更甚。
而在失序的世界里,还有“兽”们的叫唤。这里的“兽”主要是指剧团里的“假兽”,即《非往事》《唐门三杰》《当代野人》《当代野人系列三篇》等小说中徒具人形的“当代野人”们。其“兽”性首先表现在其心理扭曲——与“小人物”们因“文革”而心理扭曲尚值得同情不同,他们本性如此,只是被“文革”放大了。如《非往事·打叉》中庹家老三从小是恶作剧的主儿,遇上“文革”更如鱼得水。调查黑帮事迹,给黑帮剃头,抓黑帮游街,当“糨子手”贴大字报的事情统统有他。“哎呀,‘文化大革命,太来劲了!”汪曾祺:《非往事》,《汪曾祺小说全编》(下),第9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其次,野人们的“兽”性还形象表现于动物性欲望——这突出表现在“吃饭”上。在《当代野人》其一中的庹世荣就执着于“吃”到“痴”的程度:“爱吃猪下水、肠子、肚子、猪心、肺头,吃起来没个够”,置大夫告知的高胆固醇危险于不顾,而没有活儿的时候就出门遛弯,“到南横街‘小肠陈来两个卤煮火烧,垫补垫补”。汪曾祺:《当代野人》,《汪曾祺小说全编》(下),第100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吃饭”,即食欲,本为人之基本欲求,并无可褒贬之处。关键在于“野人”本身。正如论者在分析汪曾祺小说里的“恶食”现象时所指出的:“‘恶食之‘恶不在‘食,乃在‘人。写‘恶食,重点写‘恶食者的粗蠢、恶俗、恶劣、恶毒、恶搞。”郜元宝:《与“恶食者”游——汪曾祺小说怎样写“吃”》,《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5期。显然,上述对旺盛食欲的描写已经失去了节制和平衡——个人健康或闯荡奋斗都让位于“吃饭”,理性让位于贪婪的欲望,“吃饭”已然变成兽性残留的象征。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2期 “野人”们甚至在外形上也具有兽的特征。在《当代野人系列三篇》中负责抄功的耿四喜的脚就是如此:“这双脚宽,厚,筋骨突出,看起来不大像人脚,像一种什么兽物的蹄子。”“火葬场把蒙着他的白布单盖横了,露出他的两只像某种兽物的蹄子的脚,颜色发黄。”汪曾祺:《当代野人系列三篇》,《汪曾祺小说全编》(下),第1024、10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在此,外在的生理特征恰恰是其本质的形象暴露。
有论者曾以汪曾祺的小说《鸡毛》说明他也“很善于写人之恶,也具有很高超的讽刺才能”。王彬彬:《其实汪曾祺也善写恶人》,《一嘘三叹论文学》,第103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但这是与被视为和谐优美的故里小说相较而言的。若以政治题材小说而论,可以看到汪曾祺岂止擅长写恶人,还擅长把恶人写成“兽”。这种讽刺其实也是延续五四以来对于“进化”的人应当发展向上的人性的“进化”的要求:“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该排斥改正。”周作人:《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6号。
相较之下,剧团之外的“真兽”反而是美好的象征——《天鹅之死》里被盗猎者射杀的天鹅象征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残的白蕤,《虐猫》以被孩子们虐待致死的猫象征“文革”中被批斗迫害自杀的“走资派”李小斌的父亲。非常吊诡的是:假兽是丑陋扭曲的人,真兽反而是美好的化身,更具人的意味。由此,“人与兽的世界”的荒诞被推到了极致,让我们看到种种文化心理和人性在极端政治环境中如何呈现,这就超越了一般的政治讽刺小说。
二、张家口:“有情”如何“事功”
有关张家口的三篇小说,即《黄油烙饼》(1980)、《寂寞和温暖》(1981)、《荷兰奶牛肉》(1989),对应的是汪曾祺从1958年底到1961年底作为“右派”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劳动下放的经历。小说反映了“大跃进”运动时期的困难生活和“反右”运动中对人的迫害,但并非“伤痕文学”那样借抒发伤痛来控诉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方式。
在此借用对汪曾祺影响深远的沈从文关于“有情”与“事功”的说法或许能为理解这三篇小说打开路径。1951年末,沈从文赴四川内江参加“土改”,意在进行“自我”的改造和探索新文学方式。偶得《史记》重读的他忽有新感,在家信中认为《史记》的“诸书诸表”分属事功,而“诸传诸记”则近于“有情”,进而感叹“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对此研究者在论及现代抒情传统时多有提及,但大多将其视为二元对立的关系评述。有论者就提醒其中存在着的沈从文个人思考中的曲折反复,“他当时的用心,更在二者‘综合之难度与可能性”。姜涛:《“有情”的位置:再读沈从文的“土改书信”》,《文艺争鸣》2018年第10期。在他看来,将一切“有情”转为“事功”的工作理想的关键是“对于文学艺术‘作用以外‘作者的认识”——实际上强调主体的位置和作用。在谈到《史记》的“特别”和“奇迹”的原因时,他强调“还是作者对于人,对于事,对于问题,对于社会,所抱有态度,对于史所具态度”,沈从文:《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33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而这“却本于这个人一生从各方面得来的教育总量有关。换言之,作者生命是有分量的,是成熟的。这分量或成熟,又都是和痛苦忧患相关,不仅仅是积学而来的!”沈从文:《致张兆和、沈龙朱、沈虎雏》,《沈从文全集》第19卷,第318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简而言之,“有情”与“事功”的综合之可能与难度,根本上在于“有情”的主體位置是否可能。而这种综合有赖于诗书学养和痛苦忧患的现实经历。
由此回顾汪曾祺的小说,亦可见“有情”与“事功”综合的努力。在以文学形式书写作为个人苦难经验的政治经历时,他始终坚持从“抒情的人道主义者”这一主体位置出发,人道主义仍是其关心的核心问题。而其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的尊重和欣赏。”汪曾祺:《我是一个中国人》,《汪曾祺全集》第3卷,第30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他始终立足于对人性善恶的挖掘,特别是人性善的一面。从人性的光辉到人的基本欲望的层面,他的小说充分展现了其朴素动人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本身就是一种“抒情”。
具体而言,《黄油烙饼》虽笼罩于“大跃进”时期普遍饥荒的忧虑中,却又着力于表现萧胜对奶奶的深厚感情。在小说中,他四次回忆起奶奶而痛哭:第一次是在奶奶葬后第一次有了“死”的经验,躺在还有奶奶头发气味的枕头上哭了;第二次是夜里梦见奶奶为自己做鞋的场景,醒来后试鞋而哭泣;第三次是在用线穿起蘑菇时意识到奶奶是饿死的惨痛事实而流泪;第四次是吃着黄油烙饼时想起奶奶始终没有动过一勺爸爸带去的贵重黄油而痛哭。四次哭泣,不仅描绘了一个儿童如何认识人世的惨痛,也以真挚动人的亲情描写展现了人性美好的一面。《寂寞与温暖》则描述了被错划为右派后心理沉重而陷入绝望和寂寞的女技术员沈沅如何借助于外在的人性温暖重拾生活的信心:所里的老工人王栓不但为她默默打水,还主动来看望精神近乎崩溃的她,“俺们心里有秤杆。他们不要你,俺们要你!你要好好的,一定要好好的!”汪曾祺:《寂寞和温暖》,《汪曾祺小说全编》(中),第451、45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科学家“早稻田”和熟人褚大姐也都主动关心其身体健康和生活所需,更不用说后来上任的帮助沈沅摘帽、又给她批丧假的堪称伯乐的赵所长。至于《荷兰奶牛肉》则围绕“吃”这一基本欲望,虽讽刺了以季书记食堂讲话为代表的压抑和否定人的合理欲望的形式化的干部,但更根本的还是肯定在大饥荒中包括季书记在内的人们吃的欲望的合理性,这突出在小说结尾的点睛之笔:
荷兰奶牛肉好吃吗?非常好吃。细,嫩,鲜,香。
时1960年初春,元旦已过,春节将临。汪曾祺:《荷兰奶牛肉》,《汪曾祺小说全编》(下),第8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此外,作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的“抒情”还体现在对诗意和美的发现上,因而下述几点也值得注意:
首先是儿童视角的使用,作者借助这一视角带来的陌生化效果在熟悉的生活中发现诗意的存在。《黄油烙饼》中以萧胜的视角为“口外”的大山和汽车上山的过程赋予了天真的想象色彩,既舒缓了悲痛的情绪,也展现了生活中的诗意和对未来的希望。
其次,风景的描写也舒缓了人物紧张痛苦的情绪,在非诗意的现实生活中不经意间展现了诗意,体现了作为“抒情”主体的作者意识。这在《黄油烙饼》里对“口外”景物和《寂寞和温暖》中令沈沅感到舒畅的劳动风景的描写中都有所体现。
再有,抒不平之气亦是一种“抒情”的表现,“抒情”也有对现实不合理的批评和讽刺。除前文提及的《荷兰奶牛肉》外,《黄油烙饼》中儿童视角也被用于对于“大跃进”中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的批评——在萧胜父子关于三级干部会和黄油烙饼的两次问答中,天真的萧胜的好奇询问逼得父亲无从回答。
换言之,在此汪曾祺绝非谱写田园牧歌,在文学与政治之间划清界限。只是作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在描写个人生活经验时,落脚点仍在人性和未来的希望之上。汪曾祺谈到自己作品的感情色彩时曾总结说:“总起来说,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的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自序》,《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9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沉重的现实作为一种背景性经验而存在,未必深刻。但作家主体的气质和作用却得以凸显,确实将个人的“有情”与“事功”综合起来了。他在书写中将亲历的痛苦积聚转换为“人道主义者”的“情”而抒发,最终达到一种总体“和谐”的效果。
三、高邮:传统文学与现实政治的“偶遇”
以高邮为背景的小说中,《钓鱼巷》(1995)只是在表达人事无常的意味时捎带提到“反右”运动,正面触及当时现实政治的还是《皮凤三楦房子》(1982)。这一小说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它是叙写高邮的小说中唯一反映当时现实的:小说以汪曾祺首次返回高邮所见所闻的修鞋匠高天威为原型;另一方面小说借用民间评书的传统文学形式,开头先引清代评书《清风闸》中皮凤三的故事,结尾处有“究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的字样,中间提到楦房子时也有“此是后话”的表达,结果造成了传统文学与现实政治的一次“偶遇”。
小说讲的是见多识广的修鞋艺人“高大头”与“文革”中的造反派斗智斗勇的故事。“高大头”因帮助“文革”中同被迫害的邻居朱雪桥夺回房子,因此得罪了造反派头头——财政局长谭凌霄,反而要不回自己的房子。“高大头”被告知只能拥有九平方米的地。结果他不但“硬是把九平方米楦成了三十六平方米”,还举报谭凌霄修建私人住宅。最終,谭凌霄及另一参与审查他的造反派领导都被撤职。
由此可见,“高大头”这一人物身上很有些传统评书里的侠义之气。汪曾祺将之与同样“楦房子”的皮凤三类比,或许也与此有关。而且评书这种形式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直接迅速地反映现实的教育作用。谭达先就曾指出:“评书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它轻便灵活,可长可短,善于集中刻画典型人物……便于迅速、直接而又细致地反映现实社会的生活,种种英雄人物乃至新鲜事物,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谭达先:《中国评书评话研究》,第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但细读起来,这又绝非一个简单的“文革”背景的现实批判小说:
首先,这种带有传统意味的行侠仗义本应被历史淘汰。这种行为无法消灭扭曲的文化心理,最多是一种个人式的惩罚,而且需要考量双方的力量差距。深知两者地位实力差距的“高大头”并非主动对抗造反派。“文革”期间他虽然吃了点儿皮肉苦,但毕竟没有吃大亏,因此“他没有什么抱怨,对谁也不记仇”。而因自己的仗义举动得罪谭凌霄后,要房子时的他面对嘲讽还赔笑说自己是“酒后狂言”,他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举报的。这其实也是对在“文革”中出现的类似于皮凤三的有侠义之气者的认识。
其次,小说带有通俗文学常有的巧合情节的特点。“高大头”能够成功揭发谭凌霄依靠的是四个“巧合”:省报记者正好来本县了解秋收分配情况;“高大头”先前的举报信引起了谭凌霄一伙儿的忧惧,他们主动来找记者澄清,并中伤“高大头”,反而有“掩耳盗铃”之嫌,引来记者的调查;记者写了报道后,又正好赶上大抓不正之风,报社决定采用这篇报道;报社征求县委意见,犹豫的县委书记在正派的奚县长的劝说下权衡利弊同意刊发。而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高大头”都将无功而返。
最后,用评书这种传统文学的形式来讲述政治题材的现实批判故事在文本层面就成为一种特点。借由此,小说摆脱了特定时空的限制,具有一种历史延续性的视野。叩问和批判的深度,不言而喻。
四、内蒙古和江西:失败和补充的“意义”
如前所述,汪曾祺政治题材小说可以追溯到1979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1期上涉及“文革”中干部被迫害故事的《骑兵列传》,小说艺术上乏善可陈,反响平平。但这一作品仍有其意義。首先,作为“复出”后的第一篇小说,具有表明作家姿态的意味,它证明作为文坛边缘者的汪曾祺一直关心着现实政治,虽有所远离,但绝非规避;其次,即便失败,也仍有价值。这一小说的成败与是否符合当时的主旋律没有必然关系。当时“伤痕文学”已成大势,符合主旋律的《班主任》在两年前就在同一期刊上发表而大获成功。80年代初汪曾祺几篇并不符合主旋律的故里小说也博得大名。问题关键在于小说写的是他所不熟悉的、仅仅靠调查走访了解的传奇“大人物”。比如小说中年近60的黄司令员,即使在吃的方面也依旧有“传奇”色彩:吃起难消化的年糕“不放筷子,一口气吃了十四个”。汪曾祺:《骑兵列传》,《汪曾祺小说全编》(中),第3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而经历政治动荡后,读者希望看到的是能引起共鸣的普通人的伤痛记忆,这才是他们所期待的现实主义。人物既“大”,又都是“不熟悉的人和事”,汪朗、汪明、汪朝:《老头儿汪曾褀》,第182、148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失败当然不可避免。这提醒了汪曾祺转变“方向”:不久发表的仍未引起太多注意的《黄油烙饼》在政治题材小说类别里已实现了向熟悉的“小人物”的转向,更不必说另一类大受欢迎的故里小说。不再过分关心主旋律的问题,反而成就了其创作。
以江西进贤的“土改”经历为背景的小说《迷路》(1983)、《仁慧》(1993)、《历史》(未编年)三篇中,《迷路》讲的是迷路遇虎的惊险过程,而《仁慧》也只以寥寥数语交代“土改”没收观音庵之事,只有表达对于政治的思考的《历史》可以归入政治题材小说中。故事讲述了在“土改”期间工作队启发农民诉说地主的阶级剥削这样非常普遍的事情。可笑的是这个被启发的妇女的控诉对象居然是吃了她种的豆子的“兔子”。“种一次,吃一次!害得我颗粒无收!”汪曾祺:《历史》,《汪曾祺小说全编》(下),第104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而这一小说和其他政治题材小说也共同证明了汪曾祺对于亲身经历的种种现实政治一直在关注和叙写。
五、结语:再思“小我”与“大我”
总的来说,汪曾祺的这类政治题材小说,从地域而言涵盖了他在50年代以后所生活的所有地方,从创作时间来看则涵盖了整个新时期的创作,应当予以重视。他的这种努力放在80年代中期以后文学“向内转”,“去政治化”逐渐成为时代潮流的现实中尤其可贵。而落实到这类题材中,依然是与故里小说相同的主题,即人性和文明的问题。如果说故里小说主要关注旧社会中非政治的“自然”状态下人性种种面向的展现,并着力于寻找某种自然和谐的人性的话,那么政治题材小说更关注极端境遇中人性的种种面向如何被放大展露,让我们在记住历史的同时保持警惕和反思,努力使我们的民族文明起来。汪曾祺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政治题材小说《当代野人系列三篇》题记中就强调了其之以“文革”为背景创作,正是出于保存这一渐被忽视的扭曲文化心理的大暴露的历史和记忆,“应该使我们这个民族文明起来”。①
更重要的是,他将人性放在那种极端的政治境遇中考察,同时也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的呈现方式,超出了过往“京派”那种朴素的人性考察。借助于境遇的呈现、“有情”与“事功”的综合和传统形式与现实政治的结合等文学方式,这类小说往往能够避免政治的束缚,而最终仍能“回落”到对于历史的真切认识:“写‘文革要回答一个问题,‘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儿?”②
由此个案反观文学史,也可以重新思考“小我”与“大我”的关系,即作家与社团流派的关系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从前者来看,如前所述,过往论者往往将汪曾祺放置于“京派”“现代抒情小说”等传统中。而“京派最后一个作家”的说法也得到汪曾祺本人认可,问题的关键在于其作品能否支持这种判断。如果我们考虑到其政治题材小说创作的话,那么《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着力赞扬淳朴、原始人性美和人情美”,“总体风格上的平和淡远隽永”③这两点关于京派小说风貌和特征的归纳就不能说准确概括了汪曾祺的创作事实。
其实鲁迅早已提醒:“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④作为文学史概念的文学社团流派与作家的关系虽是“小我”与“大我”的关系,但“小我”并不都融于“大我”。文学社团流派内的作家自有其创作个性。除了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确实存在诸多社团流派的崛起,之后的大多是文学史家建构的,其艺术上的共同特征往往是文学史家们总结归纳出来而非作家们的自觉意识,因而对于这类概念本身的限度意识应当成为分析具体作家作品的前提。
从后者来讲,即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来说,汪曾祺亦不失为具有一定意义的个案。百年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作家们始终不可能真正回避政治,关键是如何面对。汪曾祺的书写方式始终在自己亲历的熟悉的人事经验范围内选择,借助于“复合和延伸”的方式,背后是一以贯之的对于人性和文明的思考。格局未必多么大,思想也未必多么深刻,但自有其价值:即文学必须要面对和认识作为现实的政治的同时,终究要能以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从而“溢出”这一题材本身。
若从文学史研究层面来看,这再次说明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有论者谈到汪曾祺如何置入“京派”脉络时就指出:“汪曾祺向八十年代文学所显现的正是一种当时所急需的对抗性资源——四十年代成熟的新文学经验,乃至八十年代刚刚被几个青年人发现,并引以为先锋形式的现代派技巧。”⑤若以政治题材小说纳入考察范围,那么这些经验和技巧与其说是汪曾祺自身显现的“对抗性资源”,不如说是研究者们的选择性发掘。更重要的是,这种思维模式存在着明显的等级制。减少其影响的途径是回到作品本身,从其直接呈现的现象回溯考察其在历史语境中的生成,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地恢复文学史中文学与政治缠绕的复杂面向。
【作者简介】王泽鹏,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 王 宁)
① 汪曾祺:《当代野人系列三篇》,《汪曾祺小说全编》(下),第1030-10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② 汪曾祺:《责任应该由我们担起》,《汪曾祺全集》第4卷,第7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③ 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第22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④ 鲁迅:《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2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⑤ 屠毅力:《1980年代以来“京派”研究的几种模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