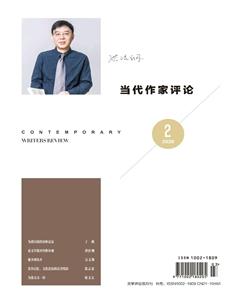远行精神与家园意识
方卫平 赵霞
一、“林子”“地平线”与童年之谜
薛涛的少年故事里有一种渺远的气韵,这气韵使它们以独特的表情和姿势,静立于当代儿童文学的艺术城池。当大多数儿童故事里的孩子在“家—校园—街区”构成的日常空间里探寻、建构其童年体验的时候,薛涛笔下的少年们却将这种日常性远远地抛在身后。这是一些显然难以被普通生活的缰绳收编和驯服的孩子,他们或是只身踏上穿越边境的危险之旅,或是凭借一己之力在都市一角落自谋生路,有时则仅仅为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便闯入一场未知的远行和冒险。即便是在那些以日常生活为基本背景和素材的故事里,作家也要让他的少年主角摇摇晃晃地撞开边界,跃出规束。
你不知道这些小孩究竟在想些什么,他们的摇晃的姿态和斜睨的目光,好像刻意与众人熟知的那个孩子的形象保持着距离。这大概也是为什么薛涛的故事读来总带着些许不轻松感的原因之一。在这个快读流行的年代,这样的阅读体验颇有些特别:当我们的目光和理解力试图像快马那样踏着纸页疾驰而去、征服文字,文字却反过来牢牢地扼住它的笼头,迫使我们不得不在疾驰中慢下节奏,按辔缓行,细细琢磨这个故事和故事里的这个孩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又要做些什么。
薛涛的少年小说似乎是要向我们证明,童年的经验是配得上这样仔细的咂摸和切磋的。惟有在这样认真细致的对待中,我们才能像懂得《小王子》里那条吞下大象的蟒蛇、那个装着小羊的盒子一样,理解童年简单、稚气,一目了然的外表之下蕴含的丰富、奇异,却也往往无人在意的内容。或如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所说,这一个“童年”,实在是一口“深不可测”的“存在的深井”。〔法〕加斯东·巴什拉:《梦想的诗学》,第144页,刘自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童年的这种如谜般的生命感觉和文化质地,可能就是薛涛小说着意想要表现的一个重要方面。少年小满谋划着一场不可能的行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向边境线发起秘密的“突击”,谁能说清这番“疯狂”之举究竟是为了寻回黑狗九月,还是出于某种辨不清、道不明的精神的骚动?事实上,这种骚动在故事起始、九月仍然陪伴着小满的时候,就已经酝酿成形,蓄势待发。在这里,真正带给少年困扰的问题不是“五乘九”等于几,而是那片被人们引为禁忌的神秘对岸,“草木茂盛,炊烟升起,对岸的人永远也看不到它的清晰面目”。薛涛:《九月的冰河》,第4页,天津,新蕾出版社,2014。这近在眼前又远不可及的“对岸”,对少年构成了莫名的诱惑和强烈的召唤。说到底,九月的出逃其实是为这份冲动提供了一个切实的爆发点。还有少女小菊,为了保留拥有一只青蛙宠物的权利而干脆地休学回家,又为了电视节目上一瞬而过的若干镜头而决定离家出走。这样的行为举止除了向我们昭示一个孩子过分的率性和任性,是不是还带着那么一点儿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才有的天真的胆量和雄心呢?像故事里的“风镇”所寓言的那样,成人们拖着生活的思虑滞重而行,孩子们则带着轻扬的灵魂高高地飞翔起来。
因此,薛涛小说中不时出现“林子”和“地平线”的意象,并非偶然。甚至,这两个意象不但透露了薛涛本人生活理解和审美经验中的某些重要内容,也透露了他的少年小说和这些小说中少年精神的某个基本面向。林子是阔大、深茂和窅无边际,也是鲜活、美好和生机勃勃,它还是与大地、天空和太阳有关的那个远方,因为林子往往伫立于地平线上,仿佛伫立于天和地的尽头。薛涛的林子里总有一棵或一片白桦树,那种刷白细长的优雅树体,令人想到某种同样优雅的存在的姿态。它们是流浪少女网小鱼在都市楼墙的包围下坚持温习的关于家的记忆。
“林子”和“地平线”的存在,更准确地说,意识到“林子”和“地平线”的存在这件事情,令人怅然若失而又兴奋莫名,“既幸福又忧心忡忡”。 ② 薛涛:《小城池》,第81、54、67页,昆明,晨光出版社,2013。他像一个豁然开蒙者,从此知道世界不仅仅是低矮的屋顶和围墙,生活也不仅仅是吃饱穿暖的卑微生存;但他的身心从此也开始了不安分的游荡。薛涛笔下的少年主角们,无不是被“林子”和“地平线”的远大风景诱惑着的孩子。他们对待大人们看重的日常生活的某种心不在焉,底下掩藏着的是对那片广阔的“林子”和那道遥远的“弧线”的全心倾慕。少女沙漏站在高高的领操台上向她的仰慕者宣布:“我看见地平线了,那边有一排白桦树。”她也倚着废墟小屋的门这样劝告拆迁者:“要是到处都盖上楼房,就看不见地平线了。”②网名鼠辈的少年一跃而起,去拥抱“太阳在林子后面落下去”的地方,那里,“一条地平线闪现出来。大地和灰蓝的天空逐渐接近、融合,在那个细微的地方形成鲜明的界限,把大地和天空分割”。 ⑤ 薛涛:《大富翁》,第5、205页,天津,新蕾出版社,2015对于少年小满和少女小菊来说,一片林子意味着一段刻骨铭心的旅程,一次书写生命的成长。
我们大概明白了,为什么日常生活的篱墙圈不住这些孩子的世界,因为他们的目光远远地越过篱墙,投向了视域尽头的阔大世界,就像“木排的目标是绚烂的河流尽头,听说那里的水域无比开阔,能容纳落日,也能容纳所有的江河”。薛涛:《形影不离》,第147页,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從站立的这头到遥望的那头,“一半是活着,一半是梦想”,⑤少年的脚步试图征服这段“无法逾越”的距离。你会觉得,这些孩子的思想和作为方式大为超出了我们对于一般童年的理解。但仔细想来,你或许也会承认,这样的“不切实际”和“野心勃勃”,可能才是童年时代方有的精神财富和气魄。
二、传奇、现实与童年之力
所以,薛涛笔下的少年主角们总在远行,或是身体的历险,或是灵魂的出游,他们忍受不了望见远方却顿步不前的状态。
而远行注定与传奇有关。废墟中央的孤岛小屋,冰河对岸的异域森林,烂尾楼里的“富翁”岁月,雪山脚下的凶险逐猎,无不激起我们关于传奇生活的各种遐想。这些跳脱平淡和寻常的传奇经历,是对少年敢于远望和远行的胆气的丰饶回馈。在《形影不离》中,作家将他擅长的另一支幻想的墨笔也施用到生活传奇的书写中。小菊的风镇旅程,分明由寻常风景的巷口转入,却在不知不觉中深陷奇境的包围。这段历险带着某种荒诞暗黑、充满隐喻的幻想气质,或许教我们想起了德国作家奥得弗雷德·普鲁士勒的名作《鬼磨坊》。“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古怪小镇,将各式旅人困于其中。神秘的乌鸦驻守入口,掌控着风镇的秩序。人们茫然无奈地穿行其间,等待一场无望的大风的降临——使你的灵魂轻到足以被风带走,这是离开这个荒诞小镇的唯一可能。困境中的少年如何解开神秘的禁制,寻找脱身的出口?如此激发童年冒险本能的悬念,足以对少年读者构成难以抗拒的魅力。李利安·史密斯认为,这样的历险故事迎合了儿童天性中对于“浪漫和刺激”的追求,由此“给儿童带来了某种感同身受的体验,扩展了他们的兴趣,提升了他们的视野,满足了他们对想象的需求”。〔加拿大〕李利安·H.史密斯:《欢欣岁月》,第185页,梅思繁译,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
然而,薛涛的传奇,其要旨却并不在“奇”字。它虽由一个逃离日常生活的姿态开始,却有别于斯蒂文森《金银岛》里那种远离普通生活语境的历险。后者看似在现实生活的情境里展开故事的叙说,实则更多是在远离现实的想象里编织惊心动魄的奇遇。一张指点宝藏的地图,一座满藏财富的孤岛,在这些意象跟前,现实生活按下了暂停键,另一段奇异的旋律悠然响起。那是一个与日常烟火生活隔岸相望的英雄故事空间。但在薛涛的传奇里,英雄的遭际奇则奇矣,其超然的身份特权却并未在故事逻辑层面得到积极的回应,生活的那种不无黑色幽默感的偶然性,始终在不断打破英雄行为及事件的“奇”和“巧”,为的是把我们的目光重新带回现实的地面。《九月的冰河》里,小满想方设法要偷渡边境河,现实世界却并未向这孩子气的轻率闯荡做出廉价的、欺哄性的低头。借船,偷船,造木筏子,每一项尝试都遭遇了现实生活逻辑下可想而知的失败。他居然敢趁着冬天的夜色从结冰的河面上匍匐过境,但这番在许多英雄故事里足以赢得奖赏的“壮举”,很快也被冰面中央支开的一个野兔夹子无情地阻断。生活就是如此,它很少依照少年的雄心展开它的逻辑。就像《大富翁》里的城市流浪少年们,在废弃的都市一角开掘自己的“财富”王国,日常生计却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凭小聪明规划的“生意”很快泡汤,彩票的梦想始终遥不可及,好不容易挣得的“地盘”被大人侵夺……比之浪漫虚幻的谎言,作家似乎更愿意向孩子透露生活的不无冷峻的本来面目。真实的世界,何曾会为一个孩子心中的“林子”和“地平线”作轻易的俯就?
当代作家评论 2020年第2期 于是,生活对孩子而言,不再是屋檐下大人俯身给予的糖果,而是他们需要充分调动自己的体魄和心智去丛林里摘取的果实。这片丛林里穿行着各种目的和企图的大人,并不会为一个孩子的愿望做太多让步,而且可能充满危险。如果说现实中的孩子难免为生活所迫闯入这片丛林,那么让人更为印象深刻、也更意味深长的,或许是薛涛的少年们主动拒绝成人世界收编的姿态。《大富翁》里,对三个流浪少年留意许久的瘸龙再三表达了“招安”的愿望和善意,却遭谷哥一再拒绝。这拒绝里有叛逆的意气,也有对成人世界的不信任和深深失望。透过这个姿态,一种比表述清楚的规则、观念和伦理道德复杂得多的现实世界的“儿童—成人”关系以及童年对生活的理解,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从规则、观念和社会伦理的角度,儿童救助站站长的话道出了与童年有关的一种公理:“赚钱跟战争一样,让小孩儿走开。你们是小孩儿,赚钱是大人的事情。保护好你们也是大人的事情。”薛涛:《大富翁》,第115页,天津,新蕾出版社,2015。但这只是对于“儿童—成人”关系中后者理应如何的理想要求和期望,它像天空中太阳的光芒,璨然至极,投到现实的地面上,却也迎来了各各不同的阴影。这才有了谷哥的诘问:“大人在哪儿啊?”这真是一个充满隐喻的质问。当大人们肆意破坏他们在孩子面前“理应如何”的规则,却要孩子站在原地,深陷谎言,这是对童年的二度不公。因此,谷哥拒绝瘸龙,拒绝儿童救助站,正如沙漏拒绝老师沙宣递来的橄榄枝,拒绝父亲和继母边角料式的关心,因为它们更像是大人想把孩子乖乖揽在旁边的糖果,而不是目光平视、彼此尊重、并肩而行的握手。
正是在与这样的现实相搏的过程中,童年的力量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也因此得到了有尊严的确认。当一群孩子努力破开成人世界和现实法则的重重包围,向着心中的“林子”和“地平线”突进,这本身就是一种传奇的冒险。面对困境和绝境,这些少年往往表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沉稳和淡定,但它却非成年人的老辣与世故,而是来自童年时代看待世界的独特视角和化解压力的独特方式。这视角和方式里闪烁着童年天性里的乐观气质和幽默精神,那是由孩提时代有限的经验和无限的想象力交织而成的奇妙本能——有限的经验使孩子不必忧心忡忡、深思熟虑地关切太过遥远的生活算计,因而比成人更能看见近在咫尺的平凡事物的乐趣、意义并将它们放大;无限的想象力则使他在最清贫艰难的生活中,仍能凭借一点想象的支撑,为自己造起一个完满的王国。饥饿中的三个红薯,足以让三个孩子满足地坐在太阳底下,正儿八经地探讨“两元钱让三个人吃饱”究竟是“能力”还是“运气”的哲学。“太阳温暖,热气腾腾地照耀着谷哥的富翁居”,而所谓的“富翁居”,其实是一幢无主的烂尾楼,钢筋裸露,四面漏风,但看在孩子眼里,“这幢楼足足十层,够高,也很大。住上一个富翁,外加他的第一号保镖、表妹以及她的宠物猫,这都很匹配。”薛涛:《大富翁》,第11页,天津,新蕾出版社,2015。此番话语中的“富翁”“保镖”“表妹”“宠物猫”,无不充满了复义的幽默与反讽。同样,少年小满口中的“船长”“大副”“出国”“旅游”,少女沙漏眼中的“城池”“领主”“公主”“光明”,也无不包含了现实对象与童年目光相碰撞、现实所指与童年解释相交叠而造成的复义内涵,前者的凡常低微与后者的精彩宏大之间,构成了幽默有趣而富于意味的张力。
薛涛对童年语词的这种复义性无疑有着特殊的钟爱。在他的少年小说的文本之內,充满了童年视角下世界和生活的这种复义感觉。一面是童年生存现实的真切困境,一面是童年眼中世界的迷人面貌,后者既构成对前者的批判和讽喻,也构成了对它的重构与抵抗。有如“小城池”“大富翁”的题名所喻,大人们眼中毫无价值的废墟,落到孩子眼里却是弥足珍贵的城池,坐拥它,足可以富翁自居。这背后有某种与现实有关的深刻的悲伤,也有童年借以应对这悲伤的了不起的审美天性与精神。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少年身上,这种天性并不止步于精神上的自我抚慰,而是化为了努力重建自我生活的单纯而不懈的行动。
这样乐观无畏的进取理想与单纯明亮的欢乐精神,是我们许多人在成年之后已然失去的力量。
三、成人、家园与童年关怀
不难理解为什么,薛涛小说的童年镜子里,总有一个大人(往往是父亲)的身影。这个形象站立在少年的对面,既构成他的烘托和背衬,又仿佛是其未来的某种预言。有时候,少年的目光有多远大,成人的视界就有多狭小;少年的生命力有多鼓荡,成人的存在感就有多萎缩。沙漏的父母是在平庸生活的数字算计中彻底忘掉“林子”和“地平线”的大人。对小满的父亲而言,那个眺望对岸悸动不安继而做出越境的荒唐之举的儿子,同样十足地衬出做父亲的毫无光彩的“老老实实”和“循规蹈矩”。这种激越与庸常、冲撞与规束的相碰,注定要挑起少年与成人之间的文化战事。《九月的冰河》开场,小满与父亲之间那段弥漫着火药味的对话,犹如双方“出战”的宣言。而对沙漏来说,这场“战争”的铺开面要广得多,它最后造成的后果也严重得多。沙漏在父母的漠视中渐行渐远,终于没有冲破那张等待着她的不幸之网。从生活的逻辑来辨,她的死亡是可以避免的,但从小说的逻辑来说,少女的意外之死完成了对那个不可靠的成人身影的终极判决。
然而,站在童年视角向成人提出生活的批判,只是上述“少年—成人”对位关系的表层蕴含。在薛涛手里,这一对位法的安排还别有深意。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时候,成人不仅作为少年的对手立于其形象的对面,也构成了与少年身影之间的某种暗自呼应甚至彼此诠释。小满的父亲一面为儿子的荒唐行径头疼不已,一面又对他怀着难言的歆羡。他“常常对儿子冷嘲热讽一番”,心里却“还藏着那么一点儿欣赏,甚至是钦佩。他从儿子身上能看见自己的小时候,他是长大以后才变成现在这么老实的”。 ②④ 薛涛:《九月的冰河》,第64-65、65、193页,天津,新蕾出版社,2014。实际上,某种近似于儿子的精神骚动正折磨着他。身为护林员的他“一方面迷恋现在的工作,隔三岔五去林子里转转,心里便敞亮;另一方面,他又想走出林子,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一番……”②《白银河》里,这种精神上的“不自在”几乎同时发生在父亲段老倌和儿子龙雀的身上,进而将他们一道推入远行的旅程。小菊的父亲则更像一个从未长大的少年,着迷于“沿着地平线走,找最宽敞的地方,天空做屋顶,天边做墙壁” ⑤⑥⑦ 薛涛:《形影不离》,第14、15、200-201、189页,青岛,青岛出版社,2017。的远行生活。女儿小菊从潇洒退学到离家出走的种种“任性”,无疑正是继承自这位同样“任性”的父亲。谷哥与瘸龙在城市里抢生活的交手中分享着共同的“逃亡”命运。这对并无血缘关系的成人和少年,不知为何更令人联想到父与子,那种狼狈落魄中的坚强,精明狡猾里的深情,在彼此的过招中交相映衬。小说里,这些大人与少年一道历经传奇,他们的形象也常常与少年叠合在一起。我们从成人身上看见了那个不安分的少年身影,也从这个身影里看到了从少年到成人的某种不变内质。
更重要的是,透过这一成人镜幕的反观,我们对于“林子”和“地平线”所代表的少年精神,以及它们所标示的现实出路,有了更为完整的认识与理解。这个成人的身影促使我们回过头去重新审视和思考:“远行”对于小说中的少年和成人远行者们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通过“远行”,他们所追寻的又是什么?同样是被不满于现状的躁动和焦虑刺激着,父亲与小满一样,选择了“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一番”。他的传奇闯荡原本注定失败,但意外救回儿子,却使这场远行有了最了不起的收获。最终,躁动和焦虑不再困扰着父亲,他坦然决定,“留在林场,陪伴着这片杂交林”。④这个回归的结局或许令我们有些豁然开朗:“林子”原来不一定在外面,“远行”的终点也不一定在远方,它的目标,毋宁说是为了寻找身心的真正归宿,或者说,一种“远行”之前未能得到确认的存在的家园感。在小菊父亲身上,这一回归的深意表现得更隐晦,却更能说明问题。这位父亲着迷于远行的自由,“像一只鸟,怕笼子,喜欢四处飞”。⑤乍看之下,这是一个从未失去少年时代自由冲动的成年人形象。然而,这种洒脱无羁的远行,并未能解决他灵魂里“毫无目标”的不安。直至陪伴小菊走完那段奇异的旅程,通过那些严峻的考验,他才在蓦然回首的顿悟中,明白了使远行变得有意义的内容究竟何在。“现在,他躺在一张木床上感到惬意。这间屋子不大也不小,恰好容纳他的身体和灵魂。……他可以回家了。”⑥
事实是,追寻这种“恰好容纳”的妥帖和“可以回家”的踏实,才是小说中的少年和成人们踏上旅途的最终动因。正是在这一目标的照亮下,原本处于对抗或疏离状态的“儿童—成人”关系,获得了其意义重大的重构契机。旅途中,一方面,孩子是使成人的追寻最终有所着落的重要动力和标的。《形影不离》中乌鸦的独白蕴含深意:“没有女儿,就没有爸爸。”⑦成人是因孩子而学习、晓悟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大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孩子面前,大人们一样面临着自我成长和身份重构的课题。沙漏的父母实际上没有迈过这道成年的门槛。小菊的父亲在任性的远行中一度茫然若失,对女儿的牵念使他的行走有了目标,在与女儿形影不离的飞翔中,他实现了父亲身份的圆满完成,也因之获得灵魂的安定与充实。对小满的父亲来说,他在自我迷失的远行中与儿子意外相逢,这个过程让他最终理解了儿子,也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显然,在这些成人“回家”的旅途中,孩子扮演了某个不无救赎性的角色。
而另一方面,对孩子的闯荡和行走来说,成人的身影也是他们最终实现自我、有所归栖的根本仰仗与支撑。某种程度上,薛涛的小说常常既诠释着“孩子在哪儿”的话题,也在回答“大人在哪儿”的质问。从《小城池》里的父母角色缺位,到《大富翁》里的父亲角色补替,再到《九月的冰河》《形影不离》中的成人拯救性角色,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作家对于“大人”的某种角色理解和期望。《形影不離》几乎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种期望的理想。小菊的父亲怀着“爸爸要陪着你”的强烈愿望,在与离家出走的女儿通话的瞬间被雷电击中,身体昏迷,灵魂出游,从此寄身飞鸟,陪伴着女儿的行程,在迷途给她点拨,在困境给她勇气。薛涛的小说里,很少出现如此明白无误的主题表达,也很少有如此完备的成人守护者形象。让我们把它看作深埋于薛涛少年小说文本底部的某种迫切冲动的表征——不论小说里的少年们如何努力摆脱那个在他们眼里常常不值得托付的成人身影的压制,挥动权杖另建自己的世界,成人在孩子面前,仍然承担着一种无可回避的生活和文化的责任。
这样,薛涛的少年小说从一个激进的远行姿态出发,最终回到了一种传统的家园意识,其“儿童—成人”关系也从一个激烈的对抗姿态起始,最后回到了一种温情的守护理想。这或许是一个对童年怀有真诚关怀和殷切期望的儿童文学作家最终必然会选择的向标。但这种回归并非后者对前者的简单替代或否定。相反,薛涛对少年时代的那种远大妄想和自由意志,始终怀有莫可名状的深切迷恋。他有一篇题为《铁桥那边的林子》的散文,回忆童年时代“远行”的乐趣,颇可视作作家骨子里莫可名状的远行冲动的纪念。读者或许会觉得,薛涛小说里这些始终不服膺于日常现实的圈养、甚至与这一现实有意保持疏离的少年,并不代表童年现实生活的普遍状态。大多数时候,一群孩子中的绝大多数成员无疑更习惯于“家庭—学校—社区”构成的稳定空间以及其中稳定的生活方式,在这个群体里,小满、沙漏、谷哥们永远是异数。但在这些异类个体的身上,恰恰流动和闪耀着属于童年的某种普遍精神。那样的不安分和不安定,有若牛虻,刺激起我们身体里永不能被驯服的对自由和阔大的向往。救助站里的网小鱼说:“在这里不开心,这里也没有地平线,还是外面自在。”这段话表达的“还是外面自在”的情绪,与谷哥向瘸龙开出的“不上学”的条件一样,更应当作象征来读。这里面当然有对现实的不满——之所以“不开心”,并非孩子不愿受到照顾和教养,而是这个庇护所不够温暖和理想。但另一方面,即便生活优渥,一切满足,精神的骚动难道就会因此停止?因此,“还是外面自在”,非是对流浪生活的虚幻美化,而更多是对难以忘却“林子”和“地平线”的精神本能的表达。这样的表达是薛涛少年小说永恒的主题,也构成了其独特的魅力。
但作家显然并不满足于书写童年自我的精神呓语,而是进一步把它推到儿童生活的现实关切和成长语境里,审视其现状,想象其未来:对童年来说,向着“林子”和“地平线”的瞭望与追逐,它的终点究竟是“远方”本身,还是经由“远方”想要寻找的某个地标?同样,在“远行”的过程中,少年与成人的对抗、与现实的博弈,是以对抗为最终的姿态,还是向往和追寻着一种新的和解?
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薛涛笔下,少年的远行和反抗或许永无止歇,但家园与和解的希望也在彼处熠熠闪耀。“找到地平线,就找到了家。”①某种意义上,薛涛的少年小说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寻找“地平线”的努力,在那里,或许是遥不可及的远方,一座属于童年,也属于成人的完美家园,向作家和读者闪耀着永远的诱惑。
【作者简介】方卫平,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霞,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王 宁)
① 薛涛:《大富翁》,第205页,天津,新蕾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