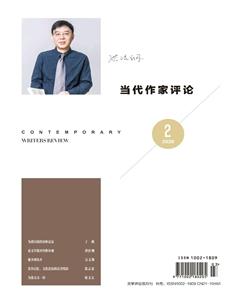新诗、文体问题与网络文学
易彬 贺麦晓
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间,易彬教授在荷兰莱顿大学从事访问学者工作,其间制订了“中国文学在荷兰”的研究计划,主要工作包括:荷兰汉学家系列访谈;中国文学在荷兰接受、传播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荷兰汉学由来已久,中文版、英文版的研究专著均有出版,荷兰汉学的历史脉络已经得到了比较清晰的梳理,但近二三十年来,荷兰汉学家在中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尚未得到很好的梳理,不为国内学界所知晓。本次访谈是2017年7月7日贺麦晓教授从美国返回荷兰之际,在莱顿大学汉学系进行的。访谈全程使用汉语,访谈稿由易彬教授整理,经过了贺麦晓教授本人审定。
《雪朝》,早期新诗史
易彬:从2016年9月开始,我在莱顿大学做访问学者。“荷兰汉学家系列访谈”是我着手进行的研究计划。我注意到,您最近这些年的研究工作,比如文体问题研究、网络文学研究,在中国国内得到了很多的关注,著作也被翻译出版,但您当年在莱顿大学时期所做的很多工作,中国国内的相关材料不多。所以,今天首先想请您从莱顿大学时期谈起。
贺麦晓:我是1982年进入莱顿大学中国语言与文化系,1987年毕业,其间去中国辽宁大学留学了一年。一开始的时候,我对汉语比较感兴趣,主要是想学语言;后来觉得我们系里面教文学的老师,包括伊维德老师(Wilt Lukas Idema,1944— )、汉乐逸老师(Lloyd Haft,1946— ),他们的课都特别有意思,就决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从1989年开始,导师就是伊维德、汉乐逸两位老师,1994年毕业。博士论文就是这本《雪朝:通往现代之路上的八位中国诗人》(A Snowy Morning:Eight Chinese Poets on the Road to Modernity,Research School CNWS,Leiden,1994)。访谈当天,采访者带去贺麦晓教授不同时期的著作、论文多种,相关信息穿插在谈话之中。
易彬:当时莱顿大学中文系的中国文学教授为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伊维德先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比较薄弱,新诗方面也只有汉乐逸先生关于现代诗的研究,您为什么会选择早期新诗作为研究对象呢,有什么特别的契机吗?
贺麦晓:当时本科的时候,我上了汉乐逸老师的“中国现代诗歌”课,课程论文就是写早期新诗人徐玉诺。那时候徐玉诺在西方还没有多少人知道。
易彬:就是这篇《艺术为了什么?:徐玉诺的诗歌和叶圣陶的美学原则》(Art for whose sake?:The poetry of Xu Yunuo and the esthetic principles of Ye Shengtao)吗?Lloyd Haft ed.Words from the West:Western Texts in Chinese Literary Context.Leiden:Centre of Non-Western Studies, 1993. p.5-25.
贺麦晓:这是最后的定稿,当时念本科的时候当然还没有写得这么仔细,但是从那时开始,我就已经比较喜欢查原始文献资料了。我找到了徐玉诺20年代的一些诗,翻译并且做了一些解读,交给了汉樂逸老师。我觉得早期民国的东西特别有意思,又比较喜欢诗歌,就决定将徐玉诺和他周围的那几个诗人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我知道他们有一个诗歌合集,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雪朝》。不过,莱顿大学的图书馆里并没有那本书,后来通过汉老师找到瑞典的马悦然老师(Goran Malmqvist, 1924—2019),他从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 University)图书馆给我复印了一本。我第一次看到原书,已是毕业以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有些人知道我研究早期新诗,也曾怀疑它们的研究价值。我的观点是:从纯粹的美学价值来说,它们可能不是很好的诗歌,但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讲,还是会涉及很多诗人,关于他们的讨论还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不研究文本,我研究文人。这些早期诗人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们肯定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当然,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太清楚到底要做什么。单纯的翻译、解读好像并没有很大的价值,但我沉下来去看跟这些人相关的杂志、资料,了解到他们都是文学研究会会员,然后又去找文学研究会的资料,就这样慢慢地了解了那一段历史,最终决定写1917年到1922年《雪朝》出版的那一段新诗的历史。全书分为五章,详细讨论了朱自清、周作人、俞平伯、徐玉诺、郭绍虞、叶绍钧、刘延陵、郑振铎这八位早期新诗人的诗歌、诗学理念以及他们的作品被接受的情况,对早期新诗的现代性提出了新的观点。当时用的理论,即接受美学理论,也算是比较新的,至少在中国文学研究界还没有很多人用过。
易彬:我注意到您有一次谈到文学研究会,通过找资料后发现“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呈现出来了”。见刘涛、〔荷兰〕贺麦晓:《文学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关于文学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对话》,《西湖》2009年第6期。
贺麦晓:我当时搜集了很多中国国内的学术文章,也到北大图书馆、其他图书馆去查过资料,发现当时很少有人用比较独特的看法去研究早期新诗的历史。所以,当时我们做的研究,它的价值在于看到了一些别人没有看到的资料,提供了一些中国学者无法提供的观点。当时西方学界没有人知道这些资料,早期新诗历史在西方大概还是第一次被写得这么仔细。现在的研究局面当然很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各种各样的方法和角度都有,资料也很容易找,这么短的、窄的博士论文选题大概也是不会通过的,但当时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找资料上了。
吴兴华,新诗“通还是不通”
易彬:我个人比较早注意到您的名字,其实是因为您的那篇吴兴华研究,《吴兴华:新诗诗学与50年代台湾诗坛》。〔荷兰〕贺麦晓:《吴兴华:新诗诗学与50年代台湾诗坛》,谢冕等主编:《诗探索》2002年第3-4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当时吴兴华在国内诗坛还少为人知,能否谈谈您是如何“发现”吴兴华的?
贺麦晓:我一直对诗歌有兴趣。博士论文就是写早期新诗人。之后的每一本书里面都有一些跟诗歌有关系的内容,比如这本《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杂志(1911—1937)》(Questions of Style:Literary Societies and Literary Journal in Modern China,1911—1937,Brill,2003),也有刘半农翻译散文诗之类的内容。关注吴兴华是因为我去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后,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博士生,叫作吴吕南(Stephen Ng)。他的博士论文是写香港诗歌,以戴天为中心,把整个香港新诗史都研究得很仔细。是他给我介绍了吴兴华的故事:吴兴华的诗最初在中国内地发表,1949年以后,用笔名“梁文星”先是在香港发表,然后又在台湾发表。虽然吴兴华自己生活在北京,但是他的诗在香港和台湾有了一定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而且也很喜欢吴兴华的诗,就翻译了一些,并且写了那篇文章。实际上,当时香港、台湾诗歌界的很多人都知道吴兴华的名字,梁秉钧老师比较早就写过关于吴兴华的文章。
易彬:不知您后来有没有注意到吴兴华作品的出版情况,先后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的两卷本《吴兴华诗文集》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的五卷本《吴兴华全集》,您后来还有相关研究吗?
贺麦晓:我也注意到了这些出版情况,它们对于吴兴华研究都很重要。解志熙、张松建等人关于吴兴华的研究工作做得比我仔细得多。不过我后来也另外写过一篇关于吴兴华的文章,通过论述吴兴华作品的传播、接受及研究,来展现吴兴华作为现代诗人是如何生成的。〔荷兰〕贺麦晓:《吴兴华作为现代诗人的生成》,李春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2期。
易彬:吴兴华全集的出版,可能会引起一些新的话题。
贺麦晓:当时我在北京的时候,曾去看望过吴兴华的妻子,她也给过我一些资料。当然,不光是我一个人有,别人也会有这些资料。当时除了吴兴华的诗和故事之外,最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诗歌在台湾发表的时候,同时也发表了一篇诗论。关于那篇诗论当时有过一个小的论争。已经到了50年代,但是那个论争中还是有人在说:诗歌用白话写不知道会不会成功,用白話写也要能够吸引工农兵之类的。当时我特别惊讶:新诗已经40年了,完全知道好诗是什么、现代主义是什么,怎么还会觉得形式那么重要,怎么还会觉得诗歌是为了跟老百姓交流,这让我想到,中国的新诗跟西方的现代诗确实有不同的地方。后来我就写了《通还是不通: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些问题》。〔荷兰〕贺麦晓:《通还是不通:中国现代诗歌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些问题》,曾昭程译,《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2期。实际上,现代主义诗歌不是为了读者而写的,它是一种艺术的东西。比如汉乐逸老师,他一直写诗,出版过10本诗集。他获得荷兰最重要文学奖的那年,其诗集只卖出10本。
易彬:我做汉乐逸老师访问的时候,也聊过这方面的话题。您文中对于“顿”和形式的关注,也会让我想到汉乐逸老师对于卞之琳诗歌形式的研究。
贺麦晓:当时吴兴华给了我很多启发,但是他的保守也给了我很多烦恼。吴兴华诗歌的形式本身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新诗并不一定要有形式,一定要押韵,或者语法一定要通。
易彬:《通还是不通》一文是十多年前在中国国内刊物上发表的,现在来看,您目前所遭遇的读者或者学生方面的情况,还是这种状况吗?您觉得有改变吗?
贺麦晓:我现在的思路大致还是如此。诗歌在中国文化里面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在荷兰,我很少会碰到一个知识分子告诉我现代诗歌都不行,都不如古诗;但是在中国,我经常会听到这种声音。有些人会有一种无意识形态,会受到一种关于诗歌的价值体系的影响,会认为新诗不行,古诗比新诗更好。我想,可能每一个文化大概都会有这样的情形。荷兰诗歌可能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但艺术会有,有人会觉得伦勃朗的画是最好的,最晚也是梵高,梵高以后的画大概都不行。在英国,就是莎士比亚最好,谁都不如莎士比亚。
鲁迅,多多,民国诗选
易彬:我注意到,1988年的一本荷兰文版的书里,有您翻译的鲁迅的《雪》,Lloyd Haft,ed. China:verhalen van een land,Amsterdam:J.M.Meulenhoff,1988.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贺麦晓:这可能是我最早发表的译文。当时汉乐逸老师编一本书,我就翻译了鲁迅《野草》中的这篇作品。任何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人都要面对鲁迅,我写《文体问题》的时候,因为用的是文学社会学的方法,非常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注意到鲁迅人际关系的一些情况。我有时候觉得鲁迅的影响是被后来的制度扩大了,不过实际情形也不一定如此,比如1998年我采访施蛰存老先生的时候,访问时间为1998年10月24日,当时陪同前往的陈子善先生后有简略的记载,见陈子善:《施蛰存先生侧记》,《素描》,第30页,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7。主要问的是当年的一些人物和关于他的一些论争,其中也提到:“30年代鲁迅的地位是不是像现在这么高?”他的回答是:“现在低了。”
易彬:鲁迅作品在荷兰的反响如何呢?
贺麦晓:汉学家鲁克思(Klaas Ruitenbeek,1951— )做了很多鲁迅作品的翻译工作,包括几乎所有的小说和其他一些作品。我觉得他所翻译的鲁迅还是有一点影响的。喜欢文学、知道鲁迅的读者,会去找来一看。当然,我想西方的读者,包括我自己的学生,他们也会接受、会喜欢鲁迅的作品,但是也不一定会认为这是他们读过的最好的作品。我个人觉得,《野草》中的一些篇章写得很不错,从中也可以看出鲁迅对于文学的理解,包括文学文本应该是多元化的,应该有不同的阐释,文学不是宣传,这些东西他都很清楚。我之所以喜欢《野草》里的一些诗,主要是因为有一些非常美的意象,有很多解读的可能性,而且它的形式也比较独特。要说中国新诗里的现代主义,鲁迅的因素是很重要的。
易彬:有观点认为,新诗的现代主义是从《野草》开始的。
贺麦晓:对。我也很难想到比《野草》更早的作品。
易彬:但是西方读者可能很难凭一部《野草》来认定鲁迅的重要性。
贺麦晓:我给西方学生教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一般会给他们看《狂人日记》。《狂人日记》是中国比较早的一个新小说,它和当时整个的历史、文化语境相关联,有很多值得讨论的地方。鲁迅写他故乡的那些怀旧类小说,也很有诗意。
易彬:我注意到您翻译了不少多多的作品。
贺麦晓:我翻译过多多的散文和小说。他当时给荷兰报纸的文化副刊写专栏,都是新写的稿子,我们当时把它叫作随笔。开始是每个星期一篇,后来变成每个月一篇。当时还没有电脑写作,也没有邮件,多多是提前一天将手写稿传真到莱顿大学汉学院,每篇大概800字。专栏文章后来合成了两本小册子出版,另外还有一本短篇小说集。第一本专栏册(1991)由我翻译,第二本专栏册(1996)和小说集(1994),是我和柯雷(M.van Crevel,1963— )一起翻译的。
易彬:多多的专栏写作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贺麦晓:后来频率就越来越低了,持续了可能有五六年吧。多多刚到荷兰的一段时间内,是在媒体里面很有名的人,在电视上露面,在报刊开专栏,大家也都喜欢看他的随笔。他经常写他对荷兰的一些观察,当然,也会写北京的、中国的一些情况。很多人都很关心他。多多本来就是很有才华的一个诗人,他当时来荷兰是接受鹿特丹国际诗歌节的邀请,纯粹是因为他的诗歌。他当时在诗歌节朗诵的诗感动了很多人,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诗人。
易彬:多多之外,当时其他来荷兰的中国诗人,您有关注和接触吗?
贺麦晓:和中国诗人的接触主要还是通过柯雷,因为他跟中国当代诗人比较熟悉。虽然我当时不研究当代文学,但通过柯雷的介绍,跟那些诗人也都挺友好的,他们也都变成了我的朋友。有一些能在荷兰见到,每次去北京也会见到一些。北岛也在荷兰待过一年。
易彬:2016年出版的《民国时期中国诗选》(The Flowering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 of Verse from the Republican Period,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也請您介绍下相关情况。
贺麦晓:这是一本整个民国时期的诗选。译者本来有两位美国学者,Herbert J.Batt和Sheldon Zitner,但后者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主要是和Herbert J.Batt合作。他原来是教英国文学的,在中国也教了很多年的书,他的中文挺好,翻译过几本中国现代小说集。我们前后合作了十多年。他让我给书的每一部分写一个序,然后再写一个总序。这些工作花了不少时间,加上解决版权问题、寻找出版社,到2016年,诗选终于出版。当时,我刚刚从伦敦大学到美国圣母大学(University of Notre Dame),而H.J.Batt正好是1960年代的圣母大学毕业生,所以我就请他到学校做了一个讲座,同时邀请了一些民国诗人的后代到我们的校园,朗诵他们父母的诗,搞了一个小活动。郑敏的儿子和女儿、穆旦的儿子、纪弦的儿子都去了。我觉得这本书挺有价值的,读民国诗歌的人可能也不一定很多,但是有了这样一个英文选集,感兴趣的学生可以找来看看。
易彬:和其他中国新诗的英文选本相比,这个选本有什么新的特点呢?
贺麦晓:奚密的选本《中国现代诗选集》(Anthology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1992年出版,是整个20世纪的诗选,不光是民国时期的。她的选本比较偏向于现代主义,我们一直都还在用。之前是许芥昱的《二十世纪的中国诗》(Twentieth Century Chinese Poetry:An Anthology),1963年出版的,出版时间很早了,选的诗人和作品也比较有限。所以,有这么一个新的选本还是挺好的,选的诗人比较多,有50位诗人,超过250首诗歌,其中选了比较多女性诗人的作品,这也是好事情。
布迪厄,文学场,现代文学文体问题
易彬:请您介绍下这本《现代中国:文学场》(Modern China:Literary Field,1996)的情况。
贺麦晓:1994年我博士毕业以后,在莱顿的国际亚洲研究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做博士后。这是1996年1月,由我组织的国际亚洲研究院工作坊(Workshop)的论文集。部分情况见〔荷兰〕贺麦晓:《“现代中国文学场”国际研讨会》,《世界汉学》1998年第1期。当时,我已经开始使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文学场(literary field)理论。工作坊的每一个与会者都提交一篇运用“文学场”的概念来讨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论文。会后,我留了一本论文集给莱顿大学图书馆。1999年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场》(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 Century China,Curzon Press)就是这个工作坊的部分论文的选集,共收论文9篇,作者包括王宏志、陈平原、冯铁(Raoul David Findeisen)、文棣(Wendy Larson)、胡可丽(Claire Huot)等人,也有我的论文和长篇导论。当时介绍最新的西方理论到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面的还不是很多,所以它虽然只是一本论文集,但是因为用的是一个比较清楚的方法,出版之后还真有一定的影响。很多人看了这本书,很多图书馆都买了,被引用的次数也比较多。它可能是我的书中读者最多的一本,对我作为学者事业的发展来说,起了不小的作用。
易彬:“文学场”的理论,在您随后的《文体问题:现代中国的文学社团与文学杂志,1911—1937》一书中,有非常充分的运用。当时的主要研究动机是什么呢?
贺麦晓:1994年我在IIAS做博士后的时候就开始研究文学社团。1996年去了伦敦,大概是2001年写完,2003年出版。主要是因为我在博士论文里用的很多杂志资料涉及到文学研究会,后来找到了文学研究会的更多资料,包括会员名单之类的,因为我一直对那些人感兴趣,就决定要研究文学社团。当时,伊维德教授建议我去学习文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literature)的理论方法,把我介绍给荷兰南部的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他们那边当时有一个团队,不光是用历史的方法,也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书,包括出版、书店、文学奖等,研究整个作为社会机构的文学,现在可能会叫作Book History或者Sociology of the Book。他们在理论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给我介绍了布迪厄,说如果要做文学社会学,非得看布迪厄的书不可。当时,布迪厄的《艺术的规则》(The Rules of Art)一书刚刚出版。这本书改变了文学社会学的方法理论。在此之前,文学社会学大部分的方法都有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背景,就是把文学当作社会现象的反映。布迪厄是第一个比较清楚地走到另外一个方向,从反映变成反射,讲到习性、资本、文学场,把整个事情变得复杂多了。听起来有些好笑,布迪厄的作品真的是改变了我的生活。以前没有意识到的问题,突然一下子意识到了,不光是跟文学有关的,也是跟学术、社会有关的,跟我自己的背景、我在学术界遭到的一些困难有关的。从此以后,我基本上就一直用同样的角度来展开研究。布迪厄讲的是差异(distinction),人和人之间怎么样造成差异,我一直到现在都还在追问这个问题。我看文学作品的时候,不一定是看作品是什么意思,我在看作者和他的出版商、他的编辑,他们怎么样去构造和其他的文学产品的差异。
易彬:1996年,您在中国思想类杂志《读书》第11期发表了《布狄厄的文学社会学思想》,那对中国学者而言,也是非常早的介绍了。
贺麦晓:当时我在北大做访问学者,导师是乐黛云老师。她和她的研究生每个星期都有一个讨论会。大家都在看理论,每个星期都会有人介绍一篇理论文章。我当时刚看完布迪厄的一本书,那时布迪厄的书还没有被翻译为中文,我就做了一篇关于他的介绍。当时花了很多时间把布迪厄的一些概念用中文词汇表达出来,手写了大概20页左右,拿到乐黛云老师的讨论会上念出来。大家都觉得非常有意思,乐黛云老师就介绍给《读书》杂志发表了。据说当时北大一些年轻的学人像姜涛、胡续东,好像都受了一定的影响。
易彬:姜涛的著作《“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广受好评。
贺麦晓:姜涛关于早期新诗的这本书非常不错。他用布迪厄的方法,把整个新诗,包括文本,包括它的环境,包括所有的东西,都写了出来。我是一直很佩服他。他很客气,说是之前看了我的那篇文章,受到了启发。
易彬:我注意到您也谈到了对王晓明老师关于五四社团研究的不同观点。
贺麦晓:王晓明老师之前发表了《一个杂志和一个“社团”——论五四文学传统》,讲《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因为当时读了很多五四时期的资料,我不同意他的看法。后来在一个讨论会上,我把我的不同观点都说了出来。当时北岛正好也在场,因为王晓明老师的论文是在《今天》(1991年第3—4期合刊)发表的,所以,我的反驳文章《文学研究会与“五四”文学传统》随后也在《今天》(1994年第2期)上发表了。胡志德教授(Theodore Huters)和我后来把王晓明的文章翻译为英文,发表在《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第11卷第2期(1999年10月1日),同时也发表了我的反驳文章的英文版本。后来在上海,我跟王晓明老师认识了。他也读了我的那篇文章,他说我还是不同意你说的,我说我也不同意你说的,但我们还是变成了很好的朋友。最有意思的是,我们约好第一次坐下来吃个饭、谈个话的那一天,正好就是5月4日。他送我一本书,我也送他一本书。我们两个人都写了赠词,但没有写具体日期,就写“五四”。很长时间内,每次到上海,我都会跟王晓明老师见面。1998年研究《文体问题》的时候,我还在他的学校做过访问学者。当时他还在华东师大。我在华东师大图书馆查了不少的资料。王晓明老师、陈子善老师,还有当时在上海社科院的袁進老师,都给过我很多帮助。
易彬:我很期待《文体问题》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在国内的反响。我个人是觉得,这本书如果能够早10年被翻译成中文,影响可能会更大。我之前请译者陈太胜教授跟您联系,将《1930年代审查制度和文学价值的建立》那一章,放到我主持的学报栏目上发表了。〔荷兰〕贺麦晓:《1930年代审查制度和文学价值的建立》,陈太胜译,《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2期。这一章真是非常精彩,涉及审查的诸多方面因素。
贺麦晓:那一章我很早就已经在中国做过一些讲座,很早自己也做了译文。因为其中的故事还真的是很有意味的。我觉得那本书有一些内容现在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有数据库,但是关于图书审查那一章我自己还是最满意的。我觉得用布迪厄的方法,比较重要的一个启发就是:在中国,不管是现代还是当代,审查官也是文学场里的一个活动者,不能把审查官放到文学场外面去。在文学场内部,审查官、作者、出版商,各种各样的互动都是可以研究的。这种工作不容易做,但还是可以研究的。布迪厄自己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自己写到审查的时候,只是把它看作一种外在的力量。我研究审查,是把它看作一种内在的、文学场内部的力量。
易彬:关于现代文学研究著作的翻译,我注意到一个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翻译为英文的情况,那就是您翻译的陈平原老师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Touches of History:An Entry into“May Fourth” China,Brill,2011)。相关情况,也请您介绍下。
贺麦晓:那是我和我的学生一起翻译的。当时,北大出版社跟Brill出版社签了翻译合同,好像国内也有一点经费支持,然后就找译者。我在北大上过陈平原老师的课,受过他的影响,当时我知道Brill要找人翻译他的书,就觉得应该是我来做。陈平原老师本来希望可以在五四90周年(2009)的时候出版,但很遗憾未能如愿。
易彬:中国学界对于陈平原老师这本书的评价很高,不知它翻译为英文之后,反响如何?
贺麦晓:问题可能在于,对五四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外国人,一般都懂中文,不一定需要看英文。但我还是很希望有一些人来看,因为这本书确实是很好,特别是开头那一章用新历史主义的方法,尤其精彩。其中讲到五四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后来在各种各样的回顾里面又被寫成什么样的。有一个细节是写,五四那一天是什么天气,先是找当时的资料去查证是什么天气,然后看50年代的回忆材料,其描写的天气完全不一样,把它描写得非常戏剧性。现在,陈老师的另外一本著作也要被翻译出版了,写武侠小说的《千古文人侠客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另外一个人翻译的,我写的序。
网络文学,管理制度和它的意识形态
易彬:从早期的研究,到后来的文体问题研究,再到现在的网络文学研究,文学社会学的理论方法始终贯穿于您的研究之中。下面,想请您谈谈网络文学研究的情况。
贺麦晓:我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杂志和文学,写《文体问题》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做文学社会学研究的时候,媒体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东西。每一个社团都有他自己的Style,叫作“体”或者“风格”。我们看一个杂志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的Style,不光是从小说、诗歌,也从整个杂志的格致,看得出来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团体。而且,文学场里面的其他人也都有这个能力,都能看得出不同的杂志之间、不同的团体之间的差异,都是“体”。当时的杂志也是一个很新的媒体,所以给“文学场”带来了变化。21世纪前后,相对于传统媒体来讲,网络就是一种更新的媒体。我意识到中国有人开始讨论网络文学,把它当作一种和一般的文学不同的东西。有时候一模一样的线性文本,比如说诗歌,完全可以在纸质版里面发表、出版,但是一发表在网络上就被认为是网络文学。这种差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像布迪厄有一篇文章写摄影变成艺术的过程:以前的艺术当然是绘画之类的,摄影怎么就变成了艺术,变成了艺术以后它是怎么适应博物馆的惯例,怎么把它放在一个框里面挂在墙上。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一个新的媒体怎么样被旧的制度采纳。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机遇,没准是一个新的“文学场”正在定型。先就是想看看,后来就写成了一本书,《中国的网络文学》(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在2015年出版。
易彬:那您的网络文学研究,是从什么时候真正开始的呢?
贺麦晓:我第一次在课堂上讲到中国的网络文学是在2000年。当时中国有一个争论,有人在讨论什么是网络文学,网络文学和文学有没有区别。之后,我先是在上课的时候讲,后来在亚非学院校内做了一个讲座,再后来,美国有人请我去参加一个会,就开始慢慢地介绍中国的网络文学现象。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找到一个方法或者角度,大部分的工作都只是介绍性的。因为西方基本上没有人知道网络上有文学,西方讲电子文学(Electronic Literature),主要是指实验性特别强的、在纸上没办法做的、电子的、多媒体的、超文本之类的东西。他们觉得在网上发表线性文本跟纸质文本没有什么区别,根本不算新的文学。但我慢慢发现中国的网络文学真的很独特,里面还是有一些新的东西,作者和读者的互动就是一种新的现象,虽然它的文本本身没有什么实用性,但是网络文学的整体语境是很新的,我关于中国网络文学研究的最早思路基本上就是这样来的:反对西方电子文学的定论,试图证明中国网络文学的独创性在于它的社会功能,不在于它的美学功能。后来写《中国的网络文学》一书时决定做三件事情:一个是介绍中国的网络文学,因为很多西方读者不知道;一个是讲中国网络文学在文学上有哪些新的东西,对于传统文学观念提出一些什么样的挑战;第三是网上发表作品,给中国文学的出版管理制度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挑战。那本书写得很简单,但是我自己很喜欢。看了那么多年的网络文学,搜集了那么多资料,最后觉得很自由,因为网络文学的线索实在是太多了,很难找到一个固定的线索,那么,就不用太多考虑什么东西有没有代表性,就写了自己喜欢写的。但是,《中国的网络文学》出版之后,第一个出来的书评就说,书里面讨论的作者都是男性,一个女性作者都没有。这完全是对的,我自己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以为我那么自由,其实一点都不自由。不是说书里面没有提到女性作者,而是比较深入研究的那些实例确实都是男性。
易彬:关于网络文学,您的最新研究进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贺麦晓:与早期相比,现在中国的网络文学已经变成一种产业了。但我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之前参加一个关于中国数字文化的小型讨论会的缘故,我翻看了十几年以前搜集的一些网络文学资料。我发现当年那些资料到底有多少还能在网上找得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易彬:中国学者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很多网络文学的原始文献都找不到了。
贺麦晓:这本来也不一定是个问题,问题是,国内一些网络文学教材、网络文学史,已经认定了网络文学的经典作品,会说网络文学第一代经典、第二代经典之类的,这样的归纳也很好,便于教学,问题是,那些经典作品可能找不到了。这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我们在教其他文学课程的时候,如果跟学生讲哪些是早期的重要作品,一般来说,学生都是可以找得到那些作品,但是目前来看,网络文学的教学可能做不到。西方网络文学很早就已经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们有一些网站保存了很多原始文献,作者自己也可以上传。我有很多早期中国网络文学的资料。因为当时我知道怎么保存,当时我就意识到如果我不存它,将来可能就没有了。我不清楚中国网络文学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人这么做过,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档案。所以,现在我觉得我可能有责任把搜集的那些资料拿出来,至少拿一部分在什么地方发表,或者放在某一个网上档案里面。既然已经有了历史记载,而且学者们已经认定哪些早期作品是经典,那么,在教学生的时候,我们至少应该有这些资料。
易彬:除了网络文学之外,您目前还有其他的研究计划吗?
贺麦晓:准备研究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面所用的那些美学概念,它们的背景是什么,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使用的。说到底,也还是对文学和政府、文学和法律、文学的管理制度等方面感兴趣,只是扩大到国家领导人借用的那些美学观点、概念。比如,习近平说:“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真善美”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中国自从1978年以来,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些话题,为什么选择“真善美”这三个概念,是有很多内容可以讲的。这三个概念在历史上往往被用来建立一个价值体系,不光是在中国,在别的国家也是如此。习近平关于文艺的讲话确实是在建立一个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强调中国自己的传统,认为是很有中国特色的,但是像“真善美”这些概念源自西方。所以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说,这可能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这些话题有很大的可比性。实际上,《中国的网络文学》那本书虽然是2015年出版的,但是资料都是到2012年为止的,之后中国网络文学的管理制度也有一些变化。我想了解到底是哪些方面发生了变化。我相信西方媒体肯定是把它过分简单化了,里边有一些细节是可以展开比较研究的;但是同时我又想把研究范围再扩大一点,不光写网络文学,还想写整个的文学和艺术,写管理制度和它的意识形态。这个是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我很感兴趣。我在《中国的网络文学》绪论里说道:一方面,我反对西方媒体的偏见,不满西方媒体关于中国网络的报道,他们老是强调政治性、翻墙之类的,但是往往就不知道所谓的伟大的防火墙里面在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中国的网络文化其实很丰富;另一方面,我也想比较客观地描写中国的实际情况。如果我认为有什么问题,我也不会讳言。因为我学的是布迪厄的方法理念,不会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信仰来批评中国的某些情况,我会比较客观地去观察,也会试着比较客观地说出我自己的一些看法。我想,像我这样身份的学者去研究习近平的文艺思想也是有可能的。
【作者简介】易彬,博士,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教授,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荷兰〕贺麦晓(Michel Hockx),美国圣母大学东亚系教授兼刘氏亚洲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 李桂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