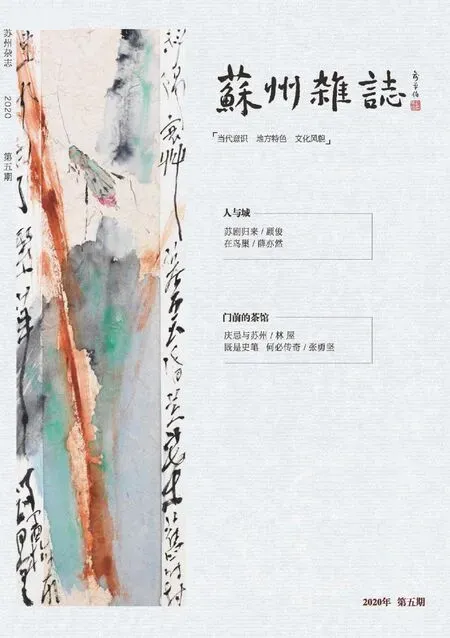以梦为马
吕一禾
一
我问刘潇,做戏剧这么多年,最难的是什么?
孤单吧,他说。
这回答让人意外,我料想中的答案,应该是现实而确切的,一是一二是二的。
后来听说他喜欢俄国文学,喜欢契诃夫,于是我有点明白了。
还记得契诃夫小说《苦恼》里那个老车夫约纳吗?成千上万的人中,没有谁愿意听他的倾诉,在乎他的悲痛,他只好跟自己的马诉说衷肠。偌大世界里,只有这匹马是他的唯一慰藉。作为文艺青年,刘潇应该很能体会这种无处倾诉、无法消解的寂寞感吧:面对一个沸腾、喧哗的世界,无论是呐喊或哭泣,都像泥牛入海;每个人都活在套子里,活成了一座孤岛。

☉ 话剧《小城之春》剧照
我猜想,戏剧应该是他对抗孤单的方式:没有戏剧,他的孤单是浮游抽象的;通过戏剧,他将其冷凝或蒸发,可以赏玩,也可以一笔勾销。
选择《小城之春》,正是因为他喜欢契诃夫。作为剧作家的契诃夫认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地流逝,悲喜交集都从乏善可陈里孕育和诞生。而在刘潇看来,《小城之春》正是一个十分“契诃夫”的作品,它用散文化的叙事,讲述了一个非常“中国”的故事。全剧所有的矛盾冲突都是暗藏于视线以下,暗藏于内心的,丝毫没有刺刀见红的凌厉之气。
“《小城之春》的本子是我2015年写的,从那时开始,每年都演几场。虽然本子是一个,但每年演出都不一样。最初是舞台剧,后来我们把演出搬到了平江路的茶馆里,也在一个破旧的水塔里演出过。今年,我们想在一个废弃的园子里来演,利用老宅后花园作为实景舞美,通过‘环境戏剧’的表现手法,让观众与故事人物互动。舞台表现方面,我们每年都会去找一个点切入,再加以放大……”这部脱胎于经典影片的改编之作,也是刘潇的心血之作,提起来就放不下:
“像今年,就把费穆这个角色搬上了舞台。也是很巧,那本来是我写的另外一个本子,名字就叫《费穆》。我有时候写得很快,一个本子一两个星期就写好了,写好就放在那里。这次觉得,放着也浪费,就把两个本子揉到一起去了。舞台表现上也增加了一些元素,将当年电影《小城之春》上映后的评论在剧中呈现了出来。”
说起来,《小城之春》确实是一部与苏州有渊源的戏。电影导演费穆原籍苏州,据说,影片的内景和外景均取自陆巷古村。半个多世纪后,导演田壮壮重拍《小城之春》,选外景时又相中了陆巷的王鏊故居惠和堂,里面的庭院搭建和家具摆设,都由身为编剧的作家阿城亲自设计。费穆的《小城之春》如今已被时间过滤成经典之作,最初上映时却遭受冷遇与批评。批评界有人指责其为“在革命和反革命斗争特别尖锐时期的懦弱动摇”。所以现在看来,中国电影史上有“两个费穆”:一个是创作了“国防电影”《狼山喋血记》、抗战纪录片《北战场精忠录》的费穆,一个是留下了《人生》《小城之春》的费穆。这两个面目迥异的费穆,究竟哪一个更有生命力,更具有永恒的艺术价值,已毋庸赘述。
而在当初那个战乱纷扰的时代,费穆苦恼的心绪只好借助文字抒发出来,“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寂寞。”
二
2014年,刘潇从苏州大学文学院戏剧专业毕业,成立了自己的文化策划公司,取名“普罗公园”。
“我在上海的一个公园里,看见各色各样的人,他们的诉求是迥异的,然而都在那里各自呼喊……我觉得这就是‘普罗’的意思。”而“普罗公园戏剧计划”,正是他对于戏剧市场化道路的个人尝试,“我们‘普罗公园’团队四个人,我是专门负责戏剧这一块的;另一个是瞿子竣,从事当代艺术、舞台美学的;还有一个是古典文学专业的,人人都有一个艺术梦。”
当然,这条“梦之路”并不好走。
“就我来说,现在特别辛苦,因为还处在文化产业比较初级、原始的阶段,还没有一个很成熟的管理制度,我现在很多的时间花在管理上。上海现在实行制作人制度,以制作人为中心,导演、剧本都由制作人去找,然后根据导演要求去找演员……”这种运作模式区别于以前的导演中心制,那时的制作都听导演的,不需要考虑成本,甚至是不惜成本来做。市场化以后就完全是两回事了,需要找到经费,控制成本,然后再安排演出场次,演员工资,宣传媒体等等。
“前两年房地产发展不错的时候,还是能找到一些投资的,这两年明显少了。我们挺缺人的,特别是制作人。制作人缺就说明市场不好,找不到钱。现在我们团队的制作人主要就是我,太累了。因为人基本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晚上要写剧本,白天要忙另一摊事,不是同一种思维方式。”
望着坐在对面的年轻人,一副叫苦却决不言弃的架势,让我忍不住好奇,戏剧到底给了他什么,让他如此执迷?
“对于做戏剧,其实我们都有一个心理预期。就是做这个,不赚钱。但我们又希望能够赚到钱。特别希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尤其是家庭的认可。最近我怂恿我太太辞了职,因为我希望她能和我一样,做点让自己开心的事。想清楚自己想做什么,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去努力。”看样子,刘潇坚信,让自己开心,比追求更多的收入和更舒适的物质生活,都要来得重要。而戏剧,恰恰就是这个让他痛并快乐着的事业。
“将来我们老了之后,起码可以跟后辈们说,自己年轻时候曾经做过这么牛的事情:不计得失,不论成功与否,我们为了理想,都去尝试过,努力过了!”
以梦为马,他简单直白的话语中透着一种孩子气式的骄傲和诗意。

☉ 实景版喜剧《金榜题名时》剧照

☉ 话剧《玩偶日志》剧照
当然,“普罗公园”的其他业务可以挣钱,家庭生活不会受影响。可是演职人员收入低是个现实问题。“我们甚至有些演员,一边排戏,一边在卖脚气药。”刘潇说。所以,可以将戏剧当成理想中的事业,但显然,这不是个理想的谋生手段。关于演员收入,在我的刨根问底下,刘潇也“幽了一默”,“我们是按照北京人艺的标准来执行,排练一场100块,一场大约四五个小时。以今年新排的《小城之春》为例,按项目制运作,从建组开始到首演为止,一个人到手的收入也就两三千块吧。”
然而,演出经费拮据还不是刘潇最头疼的事。在他看来,剧本才是灵魂。
“今年新写的一个剧本,涉及的是一个我完全不懂的领域——暗网,所以要做很多的知识准备,还要跟相关的专业人员,甚至黑客打交道。采风结束,前后写了两三稿,当时是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心绪起伏,也影响了作品的进度。本子最初叫Hamlet.exe,取了个病毒程序的名字,后来是全盘推翻,一遍遍改写,写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本子。”这就是在今年第二届中国苏州江南文化艺术·国际旅游节上首次亮相的舞台剧《玩偶日志》。
将自己的原创剧本顺利搬上舞台,就像一个母亲亲历子宫里的胚胎成长为呱呱坠地的婴儿,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与期待,也不无妥协与煎熬的过程。刘潇一直行走在戏剧理想和现实环境之间的跷跷板上,寻找着微妙的平衡。
他深深明白,戏剧是一门特别综合的艺术,是单个人无法独立完成的。从文本、舞美、音效,到演员、观众及空间剧场,缺一不可。既需要诗歌一般的情感冲击力,又要能让观众感受到这种冲击,一个好的剧作者要具备从象牙塔到世俗社会之间来回穿梭的能力。
三
“我是白羊座,闲不下来。”刘潇带着少许的腼腆,笑着说。就在不久前,他辞掉了苏州文旅集团的工作。
“我还在文旅的时候,知道要做‘江南小剧场’,很是开心,然后就单枪匹马地开始张罗起来。开始就想做个喜剧,考察了很多剧目,出了很多方案;当时我们正在排一部戏,就组织了集团的中层干部去看,想让他们知道,还有这样一群年轻人,在不计回报地做这样的事。钮家巷3号潘世恩故居东部,就在状元博物馆隔壁,很早的时候我们就计划把这里的老宅子打造成小剧场。经过修缮的潘家老宅,后来终于摇身一变成了‘江南小剧场·太傅第’。”
作为苏州首部室外沉浸式喜剧,实景版《金榜题名时》5月上旬在状元故居正式首演。当时的项目负责人刘潇有着更为长远的设想:凭借“江南小剧场”的东风,搭建一个苏州本土青年戏剧人才的孵化器,扶持更多的青年戏剧创作团队,孕育出更多植根于苏州的优秀原创剧目。在这个新鲜出炉的“江南小剧场·太傅第”,既可以上演传统的地方戏曲剧目,也可以推出非常现代的先锋话剧和实验戏剧。
随着刘潇的辞职,这些设想大概都成了愿景。他就像那个始终追逐着理想之光的人,身后投下那些长长短短的暗影,喻示着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一直都在。
我有个疑问,“你毕业后一直是个体创业,为什么会在去年选择进文旅集团工作呢?”
“首先是因为有了孩子,觉得生活似乎应该有所变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我想知道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想体验一下那种相对稳定的上班状态。”刘潇说。
在他身上,有种豁达、年轻态的特质,沉闷而乏味的日常生活,也可以是一场充满先锋意味的实验。实验可以结束,但头脑风暴一刻未停,他写剧排剧的日子还将继续:“田汉有个独幕剧《苏州夜话》,我觉得主题很好,就计划着写一个《苏州夜话》的本子,与‘江南’非常契合,目前只写了个梗概。”
“我还想给东吴剧社写个本子,就叫《东吴剧社》……”在读研究生期间,刘潇曾担任东吴剧社版《哈姆雷特》的艺术指导,在这里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人,剧社亦可视作他的戏剧之路起步的地方。
“东吴剧社”和“普罗公园”,一个是老大哥,一个是小字辈,如今都是苏州具有代表性的青年戏剧社团。而近年来本土民间戏剧社团的发展,与“苏州青年戏剧节”这类平台的搭建不无关系。
“青年戏剧节最早是在2016年,由苏州文化艺术中心发起。时间在春末夏初,五六月份的演出淡季,参与的多是本土学生剧团。一开始很原生态,台上台下很多人都认识,演得虽然有点青涩,氛围很好,10块钱一张票。大部分是学生自己花钱去看,主要是培养了青年观众。”
从首届青年戏剧节到今年的“燃”第三届江南青年戏剧节,“普罗公园”从最初参与“竞演单元”的“青苗”,长成了如今树的姿态。年轻的戏剧人刘潇,则完成了自己戏剧生涯的10个剧本,其中包括《小城之春》《渡僧桥》《悉达多》《人间》《天堂》《诗人刘浪的一生》《玩偶日志》等。
一提起《渡僧桥》,刘潇兴冲冲地将剧情梗概发给我,说本子已经有了,只等今年戏剧节上的《小城之春》演完,就开始做这个剧。“我希望可以将一些好剧扎扎实实地做出来,市场需要时间来沉淀,观众也需要培养。急不得!”
是不急,因为对他来说,“戏剧是我一辈子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