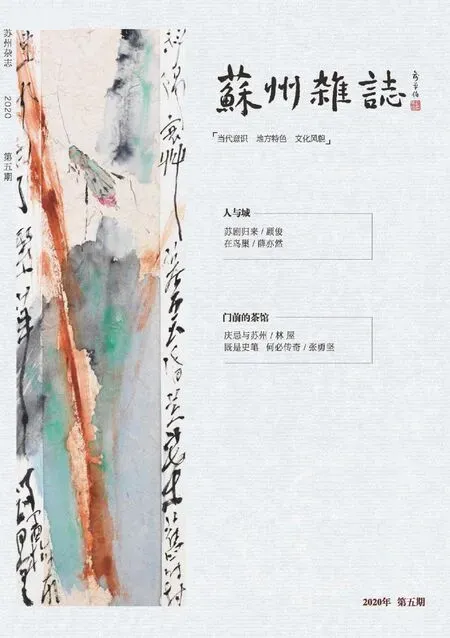闻琴疑有仙
金曾豪
游历四川。有一晚宿在一个什么矿的招待所,离峨眉山不远。地处偏僻,夜深时静如深渊,唯闻秋虫吟咏,听久了便迷离以为在梦中。
这时听到了琴声——呀,是古琴!
峨眉月下遇古琴,何等的古典呢。
琴音断续,往往一个孤单的音响起,缥缥缈缈逝去了,第二个音还迟迟不至。是在调弦么?
听觉有些饥荒,觉得耳廓在动呢。是错觉,人早就丢失了转动耳廓的能力,但捕捉声音的欲望还在。
古人有时把奏琴称作“弄”。这时的情状便是“弄”吧?
猜想弄琴的是位清矍老者,长发披肩,微眯着眼,脸上是那种孩童式的俏皮。他的手指在弦上动作得随意,随意到近似于玩了。不是“玩耍”,而是“玩味”。那“味”不只是一个一个的音,还有音与音之间的那种若有若无的粘连。
到底出现了一个连绵的乐句,而且重复了几遍。之前的那些断续的音,原来就是这个乐句的松散化。珍珠还是那些,现在是串起来了。
琴不是在表演,而是在独语,古远,淡逸,和润,静美……
峨眉冷月,一琴如诉,千古寥落,清虚旷远,就缺一炉檀香了。
琴声却戛然而止,竟杳渺不归。这才发觉,秋虫们是一直在吟诵着的,这散逸的琴声居然没有打扰到它们。真正的天籁是不会惊扰生灵的。
琴声再没响起。翌晨,旅行团匆匆起程,我没有机会寻找那位猜想中的老者。之后回想,自己也拿不准那夜半的琴声是真实还是梦幻。想起一句诗:鹤鸣疑有仙。
开始留意古琴。
而家乡常熟,正是古琴之乡,历史上出过闻名遐迩的“虞山琴派”,接触古琴是日常的事。我所在的文化馆,就有一位画家兼能古琴。我和他说起古琴。不记得他说了什么,只记得他过几天就送了我一幅水墨荷花。一片高茎的荷叶,一朵淡墨勾成的、半开的白荷花,题一个字:清。把这幅画裱了,挂在我的单身宿舍里。不久,他借我一把古琴,说,你拿回去玩几天吧。因为我当时还迷恋着小提琴,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和古琴缘只浅浅,过一些日子,新鲜劲过去,就把古琴还了。
当我快把古琴淡忘时,又在西泾岸居委会的俱乐部里听到了翁瘦苍老先生的古琴。
那天,翁先生在古琴旁一坐定,我的脑子里立刻跳出来峨眉山的弯月。
翁先生面无表情,端坐,迟迟不动,似乎在等待场子里安静下来。那儿是居委会的活动室,难免噪吵。
琴声响起来,镇定自若,旁若无人。刚才,他并不是在等待别人的安静,而是在等待自己的安静。
不知道他弹的什么曲子,我直觉得这琴声是在养着一朵云。那朵淡灰色的云,在缓缓地舒展,在悠悠地变幻……又觉得这琴声放牧着一条林中的小溪。那一脉瘦瘦的水,在秀秀地流动,在轻轻地亲吻水中的云影……
在地为水,在天为云。水和云是一样的品性。有一首古琴曲叫《潇湘水云》,让人想到竹林,又无端让人觉得那是个秋天。曲名是一种引领,其实大多时候是不必有的。许多古琴曲皆可以“清静”为题。操琴是一种使自己安静下来的艺术,与茶道、围棋相类似,传递的大多是色彩不一的静思意味。
一如此时,场子里还是有孩童的吵噪,但琴人却如坐无人之境,一脸沉醉,而琴声穆如清风。这习习的轻风在安抚着琴者,安抚着听者,安抚着天地之间的一切生灵。“千古寥落独琴在,犹如老仙不死阅兴亡。”这是苏东坡说的。
在不知不觉间,我已被感动。犹如这微微的风,琴声不想惊动我,却又整个地浸透了我。人总有几处人手够不到的旧伤痕,是古琴替人抚摸到了。
我不时听到细微的指腹压迫琴面的声音,觉得琴人是在和古琴交换对世事的感想。那古琴因感慨的积累而渐渐兴奋,而琴人提醒和压抑着琴,让它保持平静,让它以歌当哭,让它把苍凉和忧伤化作凉爽的咏叹。琴人在说:不管你走过多少沧海桑田,你还得从容前往;不管你的心有百孔千疮,你的情感还得保持干净和芬芳……
这么想象着,人直想流泪呢,是那种莫名的泪。此时的人,就像一只怀珠的蚌——欢欣中有一点点隐约的疼痛。古琴就这样,不动声色,却容易引起人的悠远之思和归真之想。
翁先生还是一位书法家。事后,我向翁先生求字。这位饱经磨难的老者,提笔在手,略作沉吟,然后一挥而就,竟是一联赞美家乡的诗:七溪流水皆通海,十里青山半入城。字里行间透出来一种灿烂的欢愉,透出来一种汪洋般的博大和平。
几年以后,心血来潮,我为陶玉霖的《昭明太子读书台》谱曲。文化馆做伴唱带时,我提出要用古琴为主伴乐器。文化馆请来了年轻的朱晞。朱晞提出只用一支箫来协助他的琴。古琴这种乐器太过清高,其他乐器大多与之难于相处,唯有孤傲的箫和苍幽的埙较易协调。“箫”和“埙”是两个怎么也读不响亮的汉字。
听过古琴和钢琴的协奏,说是“中西文化的对话”云云。我却不以为然,不知妙处何在,倒是觉得这两件乐器不是在对话,而是在话不投机地争执。
琴箫伴唱的效果不错,把昭明太子那种带一点贵族品质的书卷气营造了出来。书卷气是天地间最典雅的气质,是在蕉窗前端砚旁,经过经史子集、诗书画印的长年浸染方能养出来的气质,而古琴中蕴涵的正是中国文化儒道诗书的理想。
朱晞说:发现了没有?有几个音我是故意作了处理的——稍稍离一点儿谱,着意撞在箫声的“腰”上呢。
作曲不过是客串,我是此道的门外汉,哪能考究出来朱晞的变通,就是觉得有几处琴箫人声的相和煞是曼妙有趣。其实,古琴从来就是在追求大自在的境界,即使离谱,亦属常态,机械的节拍又何能约束了它呢。古琴总似宽袖飘逸的名士,归去来兮,自由自在,离谱之时,往往离人倒是近了。
首届中国古琴艺术节在常熟举办,常熟人有幸聆听许多古琴大家的演奏,如龚一、李祥霆、朱晞、戴晓莲、王菲等。那几天的常熟城满城风雅,遍地云水,妙处难与君说。
古琴有伏羲式、神农式、仲尼式、灵机式、联珠式、响泉式……这些名式皆与古时圣贤或造化相关,闻之先就使人肃然起敬。琴家们流派不一,性格不一,但临琴时的神态却是一样的,皆一脸高古,旁若无人。大琴家面前的古琴,显得浑厚而精致,古朴而玄妙,似乎在内心里蕴藏着无数的命运和玄机。人和琴在此时一纵一横,一动一静,“泱泱乎高山,澹澹兮流水”,听琴者赶紧肃然危坐,不敢妄思。
琴之为“君子四事”(琴棋书画)之首,就是因为弹琴不为谄媚,不为炫耀,只为秉持一种清澈的心情,只为营造一片清明平和的天地。

☉ 朱晞演出照
第一个琴音响起,常常很轻,你却觉得这声音是那样的坚定,宛若峻岭之石。第一个琴音响起,常常很钝,你却觉得这声音旷逸沉郁,径直抵达了你身体的最深。你不由得安静下来。
琴在诉说,在凭吊历史,在景仰前贤,在怀想亲情,在挥别故人……
现代人发现,这样的倾诉和聆听竟是难得一回了。因为忙碌,人们努力把交通和通讯弄得越来越便捷,但人们的忙碌并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更加马不停蹄,心如火燎。原来,我们大家是一起坐在了现代化的流水线上,一切活动再由不得自己了。迷惘、孤寂和无奈就这样产生,这样漫漶,发自内心的欢愉和美感就这样一点点地离我们而去。原来,欢愉不全是用金钱买来的,常常得自于无价的清风明月和行云流水。原来,美不全是实用的,但心灵需要,需要美的慰藉和滋养。
安静是生命的艺术,也是生命的力量。只有安静下来,内心的力量才会一点点集聚和滋生出来,犹如沙坑滋水,悄然充盈。
听龚一的《流水》,听李祥霆的《流水》,听朱晞的《流水》,那水是一样的清澈,而水流的状态却有细微的不同。有的有粼粼的波光,有的有浅浅的旋涡,有的有小鸟的点水和小鱼的唼喋,有的摇动着岸边的藻荇……
想:似乎每一个音符都是有独立的生命的,而音符之间的静默暗示含容万物的虚空。那人称旋律的东西,好像并不重要,不过是众音符相聚的一个话题。
想:最纯真的音乐,可能是不承担治国平天下的责任的,它们只是随着情感的流淌,即兴地感叹一下人间的沧桑,陶醉一下大自然的曼妙。得了心领神会的快意,那音微微波动,稍稍上行,很快又平缓下来,平淡起来。
又想:音乐既是从语言的尽头起步,就有可能摆脱俗世的纠缠,直达人心。为了直达人心,难道就要那么多的和声和复调么?有了那么多高难的技巧,那么多繁琐苛刻的计较,音乐还怎么顺畅地呼吸呢?
又想:一首曲子,最好像山野里的一棵树,自由自在地生长。唯其自由自在,它才会那样的健康,那样的潇洒,那样的曼妙。
又想:五代时董源曾说,“不为奇峭之笔,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论的是画,用来论音乐又何尝不可。如果西乐是油画,中乐是国画,那么,古琴曲就是中国画中的大写意水墨了。
再想:许多人说虞山琴派的艺术风格是“清微淡远,博大和平”。这样说对么?对的,但还说得不准。“清微淡远”不只是艺术风格,实是中国古琴的精髓所在。如果失了正宗,忘了雅俗,弹奏的风格是不足道的吧?
听过关于古琴是乐器还是道器的争论,觉得有点深奥,有点神秘。我以为古琴本身不是神秘的器物,但它的关于文化和心灵的神秘性却是需要我们一辈子珍爱与玩味的。
古琴在端庄而自由地诉说。
在这样朴实无华的大音之中,人可以默坐,可以起舞,可以吟诵。在这样朴实无华的大音之中,人不敢妄动,不敢谩骂,不敢斗殴,否则就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