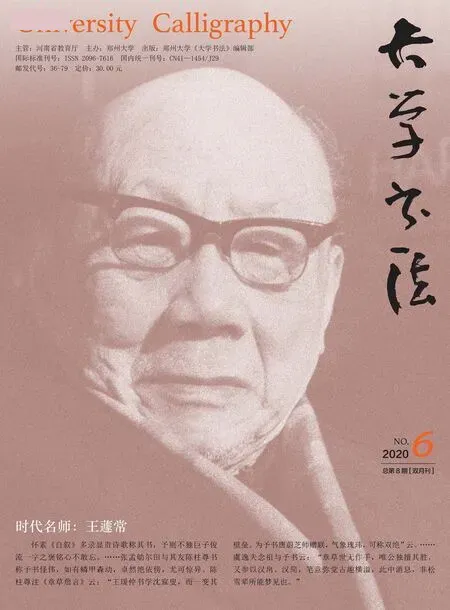余绍宋论书法“自颜柳辈出而始大变”的理论生成
——兼谈其“颜柳”书法情结
刘耀桢
一
浙儒余绍宋字越园,号寒柯,浙人皆尊称其越老,光绪九年十月初六(1883 年11 月5 日),余绍宋诞生于浙江省衢州化龙巷一个书香门第,1949 年6 月30日下午病逝于杭州,享年67 岁。先生为近代著名的学者、诗人、书画家,编著有《书画书录解题》《画法要录》《寒柯堂诗》等书。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余绍宋的著作、文稿等流传下来的并不多,后人对其了解的也不多,研究者亦不多。2003 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现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了余绍宋之孙余子安所编的《余绍宋书画论丛》一书,该编收录了余绍宋1926 年5 月6 日在燕京华文学校讲演的《中国画学源流之概观》一文,此文也见于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余绍宋集》。
余绍宋在《中国画学源流之概观·唐及五代》中说:“至中唐,开元天宝以后,则诗文及书法,均大形进步,盖初唐之诗,虽渐趋于雄浑,而仍存六朝艳冶之余风,直至李杜出而始一变;文则多属骈俪,至韩柳出而始一变;书法若虞褚,虽稍改六朝恶态,亦自颜柳辈出而始大变。”[1]本文就余绍宋对书法“自颜柳辈出而始大变”这一结论性的观点进行理论上的溯本探源,并借助“书法若虞褚,虽稍改六朝恶态”的褒贬,试图窥析出余绍宋对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情结。
二
余绍宋论书法“自颜柳辈出而始大变”,主要是建立在对颜真卿、柳公权楷书认识的基础上的,因此本文讨论的二家书法仅从楷书的视角谈起。谈论书法“自颜柳辈出而始大变”并非余绍宋首创,北宋即有之,苏东坡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2]可见余绍宋论“颜柳”书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坡翁的影响。颜、柳楷书在唐时并未被世所重,宋初才逐渐为世所宝,此后围绕着二家楷书的品评从未断过,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自颜柳辈出而始大变”。那么这一“变”究竟指的是什么?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杜子美《李潮八分小篆歌》曰:“书贵瘦硬方通神。”[3]此论虽是针对“篆书”而发,然亦能代表魏晋至唐的书法审美传统,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中说:“自魏晋以来,书贵瘦硬,以筋骨笔力相标榜。”[4]张怀瓘《书议》曾云:“风神骨气者居上,艳美功用者居下。”[5]在唐以前书法的主流审美是以“瘦硬”为“贵”,追求“风神骨气”,极力反对“艳美功用”,而颜真卿的楷书早期受初唐欧、褚等人影响,中年以后则志力于继承北派家学,类属民间书风,与今见北朝碑刻及唐时民间碑刻颇有相通之处,主要以“肥润”为美,以“华饰”为巧,以“干禄”为用,因此在唐时其书未被重视,以至于同时期的张怀瓘论书竟鲜无颜名,南唐后主李煜甚至说:“真卿之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耳。”[6]又说:“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7]可知颜、柳楷书至少在晚唐以至李煜的时代,也仍未受世所重。
米芾《书史》曾云:“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8]欧阳修《唐颜鲁公书残碑》中记:“余谓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见而长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9]又说:“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类其笔画。”[10]“韩忠献公琦”为北宋名相韩琦,欧阳修(1007—1072)与韩琦(1008—1075)为同时期人,长韩琦一岁,由目前掌握的北宋士人,可知文献较早对颜楷进行学习和推崇肇于此二公。不过欧阳修对颜楷的推崇是基于对颜真卿忠烈人品的敬服,并未过多谈论颜楷的书法美,甚至连他自己也说过“颜公书虽不佳”的话,如他在《笔说· 世人作肥字说》中说:“古之人皆能书,独其人之贤者传遂远……使颜公书虽不佳,后世见者必宝也。”[11]甘中流曾说:“颜真卿之所以在北宋以后书名日隆,其首肯者非欧阳修莫属。”[12]在欧阳修之后推颜楷的大有人在,尤其是苏东坡、黄山谷等人,东坡《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云:“颜公变法出新意,细筋入骨如秋鹰。”[13]在《评杨氏所藏欧蔡书》中记:“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磨灭,五代文采风流扫地尽矣。”[14]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云:“予尝论书,以谓锺、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锺、王之法益微。”[15]坡翁认为“颜柳”书“集古今笔法而尽发”“萧散简远”之妙,对颜书“变法出新意”推崇有加是基于宋初“尚意”的时代背景,然坡翁也意识到颜书导致“锺、王之法益微”,这里的“益微”主要是指颜书“细筋入骨”,打破了锺、王以来书法的“瘦硬”传统。坡翁论书云:“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评。”[16]可见其更倾心于“细筋入骨”的书法,如王镇远所说:“东坡最重颜真卿、徐浩、杨凝式等体貌宽裕阔大一路的书风,而蔑视那些以瘦硬故作矫健的书法。”[17]涪翁《跋法帖》中记:“鲁公书,今人随俗多尊尚之。”[18]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东坡又为永叔门生,此三人可谓颜真卿书法接受史上的功臣,甘中流亦称:“颜真卿历史地位的确立有赖于北宋诸贤,从欧阳修到苏轼、黄庭坚等,都在不遗余力地宣扬颜真卿书法的价值。”[19]
米南宫与苏、黄同时代,对颜书具有一定的理性认识,他说:“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20]米芾对颜、柳楷书批之甚重,他在《跋颜平原帖》中说:“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21]在《寄薛绍彭诗》中写道:“欧怪禇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22]他甚至在《海岳名言》中说:“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23]黄惇《颜、柳的障碍》曾说:“可见米芾已看到传世颜真卿碑刻与初唐楷书的这一差异(“华饰”现象),和唐代楷书自颜为一大变这一事实。”[24]米芾认为“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这里的“古法”主要指锺、王以来书法追求的“瘦硬”传统,而颜真卿“变法出新意”导致“古法荡无遗”,柳公权又继而学欧、颜,导致“世始有俗书”。姜夔《续书谱·真书》亦云:“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25]南宫、白石之论与余绍宋所说的“书法若虞褚,虽稍改六朝恶态”,可谓是大相径庭。由此,我们可知自颜真卿楷书为世推崇之时,便伴随着一种反对的声音,这主要是因为颜书“细筋入骨”,打破了锺、王以来书法的“瘦硬”传统。
欧阳修以后,颜书已经成为论书者绕不开的经典,朱长文《续书断》中说:“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弋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以来,未有如此公(颜真卿)者也。”[26]一度把颜真卿与王羲之、王献之放到同一历史地位上来评价。潜溪隐夫在评颜书时说:“惟公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也。”[27]评柳书时说:“盖其法出于颜,而加以遒劲丰润,自名一家,而不及颜之体局宽裕也。”[28]可知朱长文推颜是出于其书“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此在颜书中体现得很是明显。潜溪隐夫之论可以称得上是真正发掘了颜楷之美,而不是假借颜真卿“忠义之节”来引发后世“肃然起敬”从而“必宝”颜书。晚于朱长文的姜夔在《续书谱·用笔》中说:“颜、柳结体既异古人,用笔复溺一偏。予评二家为书法之一变,数百年间,人争效之,字画刚劲高明,固不为无助,而晋、魏之风轨,则扫地矣……故之与其太肥,不若瘦硬也。”[29]姜白石说“二家(颜真卿、柳公权)为书法之一变”,与苏东坡所说的“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都看到了“二家”之“变”,只是各自对“变”的褒贬不同。姜白石乃是继承杜子美、米海岳等人的观念而来,旨在贬颜,余绍宋所说的书法“亦自颜柳辈出而始大变”,乃是继承苏东坡、朱长文等人的观念而来,旨在推颜。
元代郝经亦继承了朱长文的观点,他在《叙书》中说:“锺、王变篆隶者也,颜变锺、王用篆也,苏变颜、柳用隶也。”[30]在《移诸生论书法书》中说:“颜鲁公以忠义大节,极古今之正,援篆入楷。”[31]稍晚于郝经的袁桷却主张守魏晋旧法,他在《跋柳诚悬陇西李夫人志》中说:“颜鲁公锥沙、印泥法,仅传于藏真,诚悬真得其遒劲。魏晋隶书以扁古为工,至唐虞永兴、褚河南犹守旧法,唐世碑刻作字逾广,遂以长劲为能,而晋法悉变矣。”[32]与袁桷同时代的虞集也主张守魏晋旧法,他在《题朱侯所临智永千字文》中说:“锺、张之法,至右军而极,右军之法至永禅师、永兴公而后,难为继矣。盛唐作者变又极焉,宋人远不相逮,……而晚宋谓之无书可也。”[33]其又有“坡谷出,风靡从之,而魏晋之法尽矣”[34]之论,此中之意乃是云智永、虞世南后楷书便在走下坡路,一直到盛唐“变又极焉”,此“变”的代表人物即是颜真卿,宋人“坡谷”等又多受颜书影响,因而弊端多出“谓之无书”。朱关田有“颜书在宋最为显赫,一代书家无不受其影响”[35]之论,此“影响”可谓是两宋之楷书成也颜公,坏也颜公。
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别开“颜字”一门,足以说明颜书影响之大,他说:“写颜字的人,向来不曾绝迹的。宋元之时,无所谓碑学,要写大字,非用颜法不可,那时书家,没有一个不从颜字转出来的。”[36]不过在明时,杨慎、王世贞等人对颜书的反思也很多,杨升庵《墨池琐录》曾云:“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37]升庵批颜书之重与米海岳类同,王世贞说:“平原、诚悬有书力而无书度。”[38]何良俊说:“柳公权则规模颜鲁公,而去晋法渐远矣。”[39]项穆也说:“颜、柳得其庄毅之操,而失之鲁犷。”[40]直到晚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也称:“欧、虞、褚、薛,笔法虽未尽亡,然浇淳散朴,古意已漓;而颜、柳迭奏,澌灭尽矣。”[41]对颜、柳书继续推崇的也大有人在,李日华说:“其不贱迹而天成者,颜平原、杨景度二人耳。”[42]在清代碑学未兴起之前,可谓是颜书之天下,王铎、傅山、何绍基等大书家几乎都有学颜之经历,清蒋骥《续书法论·用笔》谓:“学书当从颜、柳以立其体。”[43]清杨翰《息柯杂著》云:“贞老(何绍基)专从颜清臣问津,积数十年功力,探源篆隶,入神化境。”[44]
三
推颜书者无外乎得篆隶古法,贬颜书者无外乎守魏晋旧法,无论推贬,书法“自颜柳辈出而始大变”,这一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何蜷叟《跋道因碑旧拓本》中说:“有唐一带,书家林立,然意兼篆分,涵抱万有,则前唯渤海,后唯鲁国,非虞、褚诸公所能颉颃也。”[45]刘伯简《书概》中说:“颜鲁公书,自魏晋及唐初诸家皆归櫽括。东坡诗有‘颜公变法出新意’之句,其实变法得古意也。”[46]余绍宋论书法“若虞褚,虽稍改六朝恶态,亦自颜柳辈出而始大变”,乃是站在“得篆隶古法”的角度旨在推“颜柳”书法。余绍宋《题赵松雪书〈道德经〉真迹四首》其三写道:“从来书法关人品,刚健婀娜信尽妍。可惜终篇稍纵恣,岂真晚节未能全?”[47]在余绍宋看来,书法与人品休戚相关,这正是醉翁推颜书的核心所在。余绍宋1922年在陈宝琛家中观颜真卿《告祭侄帖》原稿真迹时叹服之至,他说:“观此可知钱南园、何子贞诸人学颜无一是处。唯明王觉斯尚能得其用笔之法。”[48]清代翁方纲在《跋王觉斯书》中说:“王觉斯于书法亦专骋己意,而不知古法也。”[49]王铎好为连绵大草,藏篆隶古法于毫端,挥洒自如“而不知古法”,离魏晋旧法远矣,亦可知先生推颜书除却人品因素以外,关键点还是在于“得篆隶古法”,此又是继承了宋元以来朱长文等人推颜的内因。此外,余绍宋在1940年10 月的日记中说“临颜平原《宋璟碑》:此碑极变化纵恣之妙,非深知颜书之妙者不能解,亦不能临也”[50]。“临颜书《宋广平碑》:临此碑极不易,非习颜书有得者,不能得其意趣精神。”[51]我们通过这两则日记中所表现出来的对颜书的敬意,足以想见先生是十分推崇颜真卿书法的。
余绍宋向来重学理,他在《书画书录解题·序例》中说:“欲明斯学著作渊源,以求学理进展之迹,舍以学理分类之外,其道末由。”[52]先生推颜、柳书亦可察其“学理进展之迹”,先生谓“书法若虞褚,虽稍改六朝恶态”,可知先生不喜“魏晋飘逸之气”,不愿守“魏晋旧法”,通过与前文对比分析“自颜柳辈出而始大变”,可知先生推崇颜真卿、柳公权的书法,在于他们的书法中有与“篆隶古法”相契合之处。此正是继承了自朱长文评颜书“合篆籀之义理,得分隶之谨严”以来的学理传统,如此观之,余绍宋对颜真卿、柳公权书法的情结便逐渐显明。
注释:
[1]余绍宋.中国画学源流概观[G]//余绍宋书画论丛.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6.
[2]苏轼.书吴道子画后[G]//东坡题跋.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69.
[3]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 [G]//朱长文.墨池编.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372.
[4][17]王镇远.中国书法理论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05,151.
[5]张怀瓘.书议[G]//张彦远.法书要录.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125.
[6]刘有定.衍极·注[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438.
[7]李煜.书评[G]//张玖青编.李煜全集.武汉:崇文书局出版社,2015:107.
[8]米芾.书史[M].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2014:193.
[9]欧阳修.唐颜鲁公书残碑[G]//朱长文.墨池编.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531.
[10]欧阳修.唐颜真卿麻姑坛记[G]//朱长文.墨池编.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504.
[11]欧阳修.笔说·世人作肥字说[G]//欧阳修集编年笺注(7).成都:巴蜀书社,2007:159.
[12]甘中流.中国书法批评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208.
[13][16]苏轼.孙莘老求墨妙亭诗[G]//孔凡礼,刘尚荣.苏轼诗词选.北京:中华书局,2015:34.
[14]苏轼.评杨氏所藏欧蔡书[G]//东坡题跋.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44.
[15]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G]//东坡题跋.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178.
[18]黄庭坚.跋法帖[G]//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61.
[19]甘中流.中国书法批评史[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256.
[20][23]米芾.海岳名言[M].北京:中国书店,2014:247,241—242.
[21]米芾.跋颜平原帖[G]//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955.
[22]米芾.寄薛绍彭诗[G]//张毅,于广杰.宋元论书诗全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67.
[24]黄惇.颜、柳的障碍[J].大学书法,2019(1):63.
[25]姜夔.续书谱[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100.
[26][27][28]朱长文.续书断[G]//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室,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324,324,332.
[29]姜夔.续书谱[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113—114.
[30]郝经.叙书[G]//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171.
[31]郝经.移诸生论书法书[G]//崔尔平.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175.
[32]袁桷.跋柳诚悬陇西李夫人志[G]//清容居士集(4).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1085.
[33]虞集.跋朱侯所临智永千文[G]//虞集全集(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406.
[34]虞集.题吴傅朋书并李唐山水[G]//虞集全集(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421.
[35]朱关田.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170.
[36]沙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G]//沙孟海论书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7:68.
[37]杨慎.墨池琐录[G]//明清书论集.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64.
[38]王世贞.艺苑卮言[G]//华人德.历代笔记书论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169.
[39]何良俊.四友斋丛说[G]//华人德.历代笔记书论汇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193.
[40]项穆.书法雅言[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167.
[41]康有为.广艺舟双楫[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3.
[42]李日华.竹懒书论[G]//明清书论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368.
[43]蒋骥.续书法论·用笔[G]//明清书论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866—867.
[44]杨翰.息柯杂著.皇清书史[G]//丛书集成续编(38)史部.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111.
[45]何绍基.跋道因碑旧拓片[G]//明清书论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1138.
[46]刘熙载.艺概[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7:163.
[47]余绍宋.题赵松雪书《道德经》真迹四首[G]//余绍宋书画论丛.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96.
[48]余绍宋.古书画经眼录[G]//余绍宋书画论丛.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145.
[49]翁方纲.跋王觉斯书[G]//明清书论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955.
[50][51]余绍宋.1940 年10 月日记[G]//余绍宋书画论丛.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254.
[52]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叙例[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