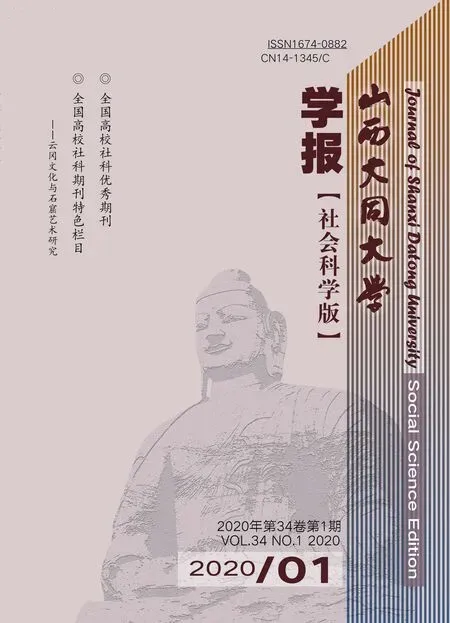北魏内河航运的南朝化
岳 东
(华清池文管所文史室,陕西 临潼 710600)
陈寅恪先生认为隋唐制度有三个源头:北魏、北齐(系南朝宋、齐制度北输后与河西文化的融汇成果),梁、陈,西魏、北周,前二源最重要,[1](P3-4)其中南朝制度文化北输的趋势很有分量。唐长孺先生认为魏晋南北朝无论南北地域,总发展趋势是向先进的南方靠拢。[2](P486、P491)牟发松先生试图将陈、唐二说糅合,并铸成其唐代的南朝化倾向说。[3]无论如何,南北朝隋唐时期,在宏观的历史发展趋势中,南朝化倾向都是十分明显的,因而,北魏内河航运领域的变化也可以见到这一影响。如果从南朝相关经验技术、专业人员的北输入手分析,可以见到清晰的地域化演变轨迹,与前辈们的宏观论断相符,下面就详细展开具体研讨的过程。
一、北魏发展内河航运的环境
在论证之前,笔者首先要交待,南朝航运技术、经验虽对北朝有重要影响,但受特殊的社会背景条件限制,北魏内河航运在其交通运输方式中并不占主要地位,因而南朝化的影响也有限。中国古代时期,全国运河体系的兴修,汇入都城漕运的繁盛,都象征着王朝传承的正统性,也展示着对全国统治的稳定性。如西汉定都关中,漕运经渭水而连通黄河、鸿沟、济水与荷水。东汉定都洛阳,漕运仍通往黄河、淮河与长江各大水系。[4]东吴、东晋与南朝时,长江上浮航成队,元兴三年(404)二月,建康“是时贡使商旅,方舟万计,……”[5](P956)北魏运输景象则截然不同,至其末年,“鸿沟之引宋卫,史牒具存;讨虏之通幽冀,古迹备在。……请诸通水运之处,……纵复五百、三百里,车运水次,校计利饶,犹为不少。……东路诸州皆先通水运,今年租调,悉用舟楫。”[6](P2860)说明北魏沿用战国、魏晋兴修的华北、黄淮水运,但当时在华北、黄淮罕见水利工程的兴修,[7]致使各地运输不得不水陆接驳。在航运相对前代严重衰落的背景下,北魏兴建起了发达的陆运网络,保障由都城通过各大经济腹地,腹里陆运的旺盛持续到北魏末不变,所谓“计京西水次汾华二州、恒农、河北、河东、正平、平阳五郡年常绵绢及赀麻皆折公物,雇车牛送京。道险人弊,费公损私。”[6](P2858)洛阳辐射到华北平原经济腹地的陆运也是畅通无阻的,如太和十九年(495),“时宫极初基,庙库未构,车驾将水路幸邺,……道悦表谏曰:‘……又欲御泛龙舟,经由石济,其沿河挽道,久已荒芜,舟楫之人,素不便习。……且邺洛相望,陆路平直,时乘沃若,往来匪难,……’”[6](P1400)在这种陆运为主的运输背景下,北魏要重新恢复与发展水运是较困难的。北魏虽距离汉晋并不遥远,但历经五胡十六国时期之破坏,航运技术人才、经验、设施、运渠已残剩无几,要发展航运事业,不得不向毗邻的南朝学习现成经验技术。因而,航程的开发,水运设施的兴筑,跨河桥梁的修建,都受到了南朝的影响。
二、黄河上游运输的开发
北魏虽未疏浚全国河渠,但其前期曾在黄河上游利用天然航道开发过中短程航运。即在太武帝拓跋焘时,在薄骨律镇(治今宁夏灵武南)与沃野镇(治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间开发的黄河漕运。[6](P868-869)时为太平真君七年(446),薄骨律镇镇将刁雍上表:“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今求于牵屯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6](P868)先前,以黄土高原(高平镇,治今宁夏固原;安定镇,治今甘肃泾川)、宁夏平原(薄骨律镇)与无定河谷地(统万镇,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产粮供给河套戍兵,用牛车运送是惯例。当时,北边六镇乃北魏北方门户、国脉所系,军粮的供给关系着边地安危。常年形成的供给模式与运输方式,一经推广就已成定律,一般镇将不敢轻易打破此惯例。身为镇将的刁雍虽此时身份显赫,但毕竟非鲜卑权贵血统出身,而他到任伊始,就敢于改变现状,不惧同仁怀疑及上级非难,必深悉航运运作模式,并坚信其能成功施用于西北边地。虽然刁雍有决心变陆运为水运,但支撑这场变革的经验技术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协助其具体实施航运的专业队伍又是一支怎样的组织呢?
实际上,刁雍的身世来历、航运技能均与沿海生涯环境有关。据《北史·刁雍传》载:“刁雍,字淑和,渤海饶安人也。高祖攸,晋御史中丞。曾祖协,从司马睿渡江,居于京口,位至尚书令。父畅,司马德宗右卫将军。……及裕诛桓玄,以嫌故先诛刁氏。雍为畅故吏所匿,奔姚兴豫州牧姚绍于洛阳,后至长安。……泰常二年,姚兴灭,与司马休之等归国。”[8](P947)渤海饶安,今河北盐山西南,东临渤海,乃冀鲁枢纽。民国《盐山新志》载:“居民以海为田,……境沿岸海口凡三,……关东杂粮、巨木,连樯西来,……”[9](P28)又载“由海而西皆上古逆河之公境也。枯渠废河弥望皆是,……”[9](P29)这里处于以孟村县(与盐山县毗邻)为顶点的古黄河三角洲,河流改道叠成复杂的沉积格架,[10]口岸并列,河道交织。刁氏乃渤海世家,后迁京口(今江苏镇江),其家世长期生活于沿海或沿江水运枢纽,家族人员的习性、技能深受地域环境的熏陶,而多少熟悉造船、航运的组织实施与配套的水文环境要求。东晋末,刁雍由江南投后秦。泰常二年(417),后秦为东晋所灭,刁雍转投北魏,被明元帝拓跋嗣(太武帝拓跋焘之父)任为建义将军,守南境,“雍遂于河济之间招集流散,得五千余人,……于是众至二万,……”[6](P865)未久,其军被南朝宋所灭。泰常八年(423),明元帝巡邺(今河北临漳西南)伐宋,封雍镇东将军,辅叔孙建南讨,并“给五万骑,使别立义军。建先攻东阳,雍至,召集义众,得五千人。……建乃引还。……又诏令南入,……雍于是招集谯、梁、彭、沛民五千余家,置二十七营,迁镇济阴。”[6](P866)这段史料有误,北魏精骑向来由鲜卑贵族自领,岂能以五万众划归降人?司马光对此已发怀疑,所以《资治通鉴》处理为:明元帝遣刁雍助叔孙建南征,“乃以雍为青州刺史,给雍骑,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济河向青州者凡六万骑,刁雍募兵得五千人,……”[11](P3753)五万或是五百之误。由于河济新兵被叔孙建扣留,雍再次南进,重招沿淮百姓入伍,这些兵生长水边,习于造船业、水运业,成为刁雍以后组织实施河运的人力依靠。
河运实施的具体时机与边镇设立有关。明元帝南征时,柔然乘机寇边,为北魏所忧。太武帝继位后,神二年(429),大破柔然,于边地置军镇。太平真君五年(444),刁雍以本将军为薄骨律镇将,[6](P867)率淮兵北上,充为镇兵,因而“镇内之兵,率皆习水”。[6](P868)七年(446),他调查今宁夏平原、河套平原上黄河水文特征、运输条件,知其水流平缓而适宜航运后,上报朝廷,在牵屯山(今宁夏固原西北六盘山脉北段山区[12)]造船,组织实施薄骨律镇与沃野镇间的漕运。从河运开发的组织者、实施队伍的地域来源,可知北魏黄河上游航运的开发系其南朝化一例。
三、其它水运设施的建设
(一)中原邸阁的兴修 北魏陆运发达,运输网络覆盖全国,而它要发展漕运,即使中短程的,也必须发动版图内的两淮人户移民充役,依靠他们的专业技能与经验,才能组织船只的生产,安排船队的航行。非仅西北地域如斯,就是内地也同样,如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四月,于彭城(今江苏徐州)曲赦徐、豫二州(徐州治今江苏徐州;豫州治今安徽寿县)运漕之士复租赋三年,[6](P177)说明供给淮东前线的水运例由淮河流域本地居民充役,因为他们熟悉当地水文、水运的缘故。徐、豫所以有专门的运输组织,与邸阁大规模设立于彼地域有关,史载“自徐扬内附之后,仍世经略江淮,于是转运中州,以实边镇,百姓疲于道路。……有司又请于水运之次,随便置仓,乃于小平、石门、白马津、漳涯、黑水、济州、陈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阁,每军国有须,应机漕引。”[6](P2858)邸阁是储存粮食等物资的巨仓。[13]泰常八年(422)到神三年(430),经明元帝、太武帝两代征伐,夺取宋黄河以南司、兖、豫大部(在今河南、山东境)。宋泰始二年即北魏天安元年(466),宋将薛安都等内附,北魏又获淮北、淮西地,[11](P4124-4125)“徐扬内附”指此事(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扬州原宋豫州,北魏改名扬州,治今安徽寿县),设邸阁即在此年以后。八处津渡散布于黄河、漳水、济水、鸿沟与泗水等河渠枢纽处,其中黄河之上多为津渡,其余邸阁也系水陆接驳联运的所在,陆运成分占了很大比重。尽管如此,置八邸阁仍是北魏全国范围内唯一实施的大规模运输方案,成功的协调河、漳、济、颍、蔡与泗等河渠运输、津渡为一体,辅以陆运,供给了两淮前线。
邸阁的设立虽源自东汉末、三国,但普遍的设置却在西晋末到南朝前期,分布于淮河流域的泗沂沭水系沿岸水陆枢纽位置。而同时期的北魏本是缺乏此类仓库设施的。民国《临沂县志》载:“邸阁:兰陵西南十二里村名,故宋盐河南岸,储粟之所也。……东泇故道西岸,又有晒米城。”[14](P104)兰陵(今山东兰陵)本属东晋、南朝宋边地,于沂水支流盐河岸边置仓储粮以备战,查今地图,兰陵县西南仍有兰陵镇、底阁镇沿省道依次由北往南分布,说明当地古今俱为交通要道。又如《水经注·泗水》载:“泗水又迳宿预城之西,又迳其城南,……晋元皇之为安东也,督运军储,而为邸阁也。”[15](P341)晋元帝即司马睿,东晋开国皇帝。西晋晚期,晋怀帝在位,司马睿被任为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镇下邳(今江苏邳州)。宿预城在今江苏宿迁郑楼镇古城山南麓,现今周围仍是河湖沼泊众多,泗水邸阁设于此,有交通地利之便。时八王之乱刚刚平息,卷入战乱的匈奴刘渊、羯族石勒势力这时已入中原,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国家破裂在即。在这种形势下,司马睿于其根据地内设置邸阁,即为防战乱及割据作准备。邸阁虽由来已久,但北魏得两淮后始置,明显因淮东前线本来就有西晋、南朝宋的粮仓,便于保障粮食需求。北魏军队即亲历此等地域,与敌对之南朝作战中,知晓邸阁储粮备战之效益,所以着力模仿,于中原、华北到两淮前线间的水陆枢纽,大规模的设置邸阁,此举系南朝化又一例。
(二)洛阳浮航的搭建 北魏洛阳布局系凉州、平城、江南文化因子的集大成之作,[1](P71)其中江南因子就有水运交通设施北输之一例。原来,在南北朝对峙中,江淮地带的运输偏重于水运,长江、淮河、珠江流域都有水路抵达建康。[16]建康城的淮水(今秦淮河)上架有朱雀航等二十四座浮航,城东青溪架有七桥,城西运渎架有五桥,沟通了城内外水陆交通网络。[17]大市、小市、草市、苑市与专业集市等多沿秦淮河岸分布,[18]跨河的桥梁沟通了两岸的城区,延伸了建康城发展的空间轴,促进了城市的繁荣与居民生活的便利,这自然为同时期的北魏所羡慕与模仿。史载北魏太和十九年(495),成淹在洛阳跨洛水架起浮航,“于时宫殿初构,运材日有万计,伊、洛流澌,苦于厉涉。淹遂启求敕都水造浮航。帝赏纳之……”[8](P1700)成淹祖籍上谷居庸(今北京延庆区),祖父时迁北海青州(今山东青州)。[6](P1751)青州本属南朝宋,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皇兴二年至三年(468-469),夺取青、冀(治历城,今山东济南)二州,改冀州为齐州,掠二地居民北归平城(今山西大同)。成氏属青州降人即“平齐户”。成氏本来世代居于海隅,受地域环境熏陶,或多或少的熟悉造船架桥技术经验与组织施工之法。成淹在此家世中成长,耳濡目染中,就奉南朝水陆交通模式为楷模了,因而奉命造浮航时,自然模仿建康城中轴线上的朱雀航,修造了洛阳城中轴线上的洛河永桥,以南朝上国名都大航修造技术移植于中原,促进壮丽的洛阳布局更加辉煌,此为北魏内河航运南朝化又一例。
四、小结
北魏交通运输网以陆运为主,内河航运断断续续,因而只能在局部河段、个别地点的仓储设施、桥梁设施上有所兴建,而且这些工程的相关主持人物、具体实施专业组织均系原南朝地域居民。晋、南朝以来,南方水系上航运发达,又在有军事意义的水陆枢纽处置有邸阁,在都城城区则广架桥梁以延伸城市空间,这些运输、存储与基建活动或设施先进而普及。世代生长于江淮或沿海地域的居民们熟悉水运技术,掌握着一些水上交通设施的制造、施工经验。他们因缘成为北朝子民后,带来南朝先进的航运技术、经验,推动了北魏内河航运事业、水运存储、交通设施的发展。虽然航运南朝化的影响并不普及于北魏版图内,但毕竟在一定时间内、局部场合中,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轨迹,对北魏社会变化带来或多或少的积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北魏内河航运的发展方向是南朝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