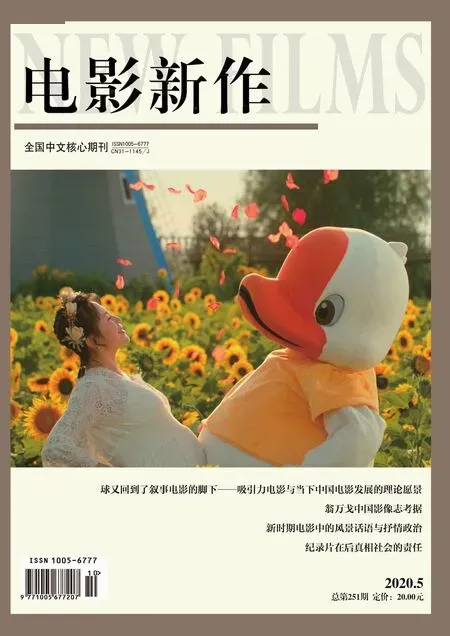发现翁万戈
——上海音像资料馆龚伟强先生访谈
龚伟强 何国威 李 骞
一、发现翁万戈
何国威(以下简称何):龚老师,您好。您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翁万戈的?
龚伟强(以下简称龚):您好。这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2018年,我们在一个文物商那里发现了两部海外回流的彩色影片拷贝,时长都在8分钟左右。一部是关于叶浅予的画中国人物,另一部是关于戴爱莲的两段舞蹈。这两个人物,我们都比较熟悉。于是,我请我们馆里(上海音像资料馆)采集部同事将它购买了回来。买下来后,我们立即作了数字化处理。在看片的时候,我们发现片中出现了Wango Weng的英文字样。我想这肯定是个中国人的名字,但对他的情况我是一无所知的。中国电影史书上没有出现过这个人,学界、电影圈和民间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随后,我就开始追查,从两部影片拍摄的主人公的传记和日记中查找到了线索,顺藤摸瓜,一直查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东亚图书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步掌握了一些关于他的信息。
何:Wango Weng是谁?
龚:这个Wango Weng就是翁万戈,他是翁同龢的五世孙(嗣)。1918年,翁万戈出生于上海,在天津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2岁时,翁万戈成为翁同龢家藏的继承人。1936年他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工程系。1938年,翁万戈赴美国留学,就读于普渡大学,获得机电工程硕士学位。出于对艺术的热爱,他还进入威斯康辛大学的美术系学习过油画……
何:作为一名画家,翁万戈先生是如何与电影结缘的?
龚:翁万戈从事电影事业与华美协进社的第二任社长孟治有关。工科出身的翁万戈对自己的专业并不感兴趣,他更喜欢艺术、电影。孟社长就把他推荐到好莱坞学习电影。“二战”期间,翁万戈被美国政府征召,主要从事电影翻译和中国电影推介工作。
何:翁万戈先生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拍摄电影的?我看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说,翁万戈先生最早摄制影片在1944年。
龚:关于翁万戈先生电影摄制活动开始的具体时间,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比较确定的信息是,我们知道1946年,他与郑用之、司徒慧敏一起在美国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国电影企业美国公司。郑用之、司徒慧敏去美国的事,当年有新闻电影拍摄。这一事件,在《电影与播音》杂志上也介绍过。
何:翁万戈先生也亲自撰文阐述了做这个公司的目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以教育片的方式,拍摄中国的文化。同时,我们也发现了他所倡导的“平民电影计划”。
龚:是的。我们馆藏还有一段影像资料,拍摄的是在上海码头,人们欢送郑用之、司徒慧敏他们几个人的场面。他们几个人的影像,还有欢送他们的标语都出现在画面中。我们现在还了解到翁万戈是在1940年末,组建了“中国电影照相器材供应公司”。这家公司在中美两地之间开展电影、照相、影院放映所需用品和器材的销售与服务业务,同时也兼营影片版权交易和私人、机构的制片业务。翁万戈从事电影事业的主要目是为了在中美之间搭建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他的作品是非盈利性质的,几乎不做商业性的放映。改革开放后,翁万戈成为华美协进社社长,再次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开展文化、文物交流工作。他可能是第一个获准进入故宫拍摄文物的人。
李骞(以下简称李):翁万戈电影的发现,究竟有什么价值?
龚:翁万戈可以说是近期电影“考古学”的一个重大的发现,可以跟前几年史学家发现孙明经相媲美。但是,与孙明经研究相比,翁万戈的研究要困难得多。关于孙明经的很多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在当时的杂志、报刊上找到,尤其是在《电影与播音》杂志上面看到。翁万戈的文献资料在国内基本上没有多少被人们所发现。目前,我们对他的了解主要还是通过他的作品。翁万戈电影作品线索的突破点是我们查到了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存有大量的翁万戈电影拷贝。通过朋友介绍,我跟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程健馆长建立了联系。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知道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收藏了600多个翁万戈电影的拷贝。随后,我们又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也发现了一批,加上去就有900多个电影拷贝。
何: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还藏有一批未被标明内容的影像,如果把这些也算进去的话,“翁万戈电影拷贝”有1204本了。其中,也发现了有一些影像是由印第安纳大学制作、完成的。
龚:1204本电影拷贝,可能不全是翁万戈先生的作品。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还馆藏有其他电影人的拷贝。我们估计翁万戈实际上完整的片子可能有30到40部。哥伦比亚大学方面已经将影像中的近20部完成了数字化处理,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十多部。国内的人对翁万戈不了解,美国人也不十分关注他。他的很多电影作品,按我的推测,很多都没有正式公开放映过。就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来看,“翁万戈电影拷贝”的构成比较复杂,最大的一部分是翁万戈摄制或主持制作的影像拷贝。在这里面有的是完成片,有的是未完成片,有的是原始素材拷贝,有的是工作素材拷贝。比如说我们最近在整理的《北京,马可波罗的奇迹》这部片子,已经进行了数字化,但拷贝的声带还没有找到,具体的解说词内容现在还不能确定。我们还在请让“哥大”图书馆寻找声带。
何:我查到的《北京,马可波罗的奇迹》的拷贝是有6本,哥伦比亚大学那边的资料反馈也是6本。这6本拷贝中,哥伦比亚大学对其中的4本作了大致的拍摄内容描述,剩下的2本只有基本的物理信息,没有内容信息。另一个问题就是说,成片的时长问题。一本胶片的时长按照10分钟或者15分钟来算,6本的话,时长能达到60分钟或者90分钟,它的时长还是很长的,内容应该很丰富。

图1.翁万戈(左:1921年、右:2018年)
龚:但这6本胶片中的拍摄内容可能是重复的,比如说其中的某一本,可能是翁万戈复制的一版工作拷贝。再一个就是说,其中有些还可能是同样的素材剪辑出来的不同成片版本。我们今天做电影、电视剧经常会制作几个版本,这是很常见的。所以说,现在关于《北京,马可波罗的奇迹》的这6个拷贝的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确定,必须逐个看过之后才能最终确定。从现有翁先生的影片来看,一般不会有60分钟那么长的。
二、“翁万戈电影”项目启动
何;发现这些影片后,上海音像资料馆、哥伦比亚大学和翁氏后人是如何开展合作的?
龚:目前,我们正在开展的这个“翁万戈电影”项目,它由上海音像资料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翁万戈家人三方一起来推进的。在对人物的考据过程中,我们发现翁万戈的电影蕴含着巨大的“中国文化传播学”价值,于是我们决定发起一个翁万戈电影学术研究和文化推广项目。在与美国方面的接洽中,我们得知这个项目的开展必须突破两个障碍,一个是要争取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支持,另一个是取得翁氏家族的授权。哥伦比亚大学方面的态度比较积极,不过他们只是翁万戈影像及文献资料的馆藏单位,这些拷贝的所有权仍归属翁氏家族,只有在获得翁氏家族的授权之后,他们才可以与我们一起开展工作。随后,我们联系了翁万戈先生的家属,得到了翁氏家人的授权。翁万戈先生的女儿翁以思女士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几乎是有求必应。
李:合作三方是如何分工的?

图2.翁万戈于美国波士顿美术馆(1951)
龚:“翁万戈电影”项目是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翁万戈家人、上海音像资料馆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展开。得到翁氏家族的授权后,哥伦比亚大学方面将这个项目纳入他们的一个“华人影像研究”工程中,这个工程专门筹集了一个有200万美元的数字化项目基金支持。首先,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可以提供关于翁万戈的一些片目信息。然后,我们依据片目信息作出判断和选择。最后,美国方面根据我们的要求对胶片介质予以数字化处理后,再将数字化版本的影片移交给我们。同时,我们的采集、研究部门工作人员还需要对影片做整理和翻译工作,最后完成的影片我们会在国内推广,巡回放映。
李:关于翁万戈电影的这个合作研究项目现阶段开展状况是怎样的?
龚:现阶段工作的重点是用三到五年的时间,把翁万戈先生的创作情况核实清楚。关于他的馆藏文献和影片脚本,关于翁万戈的文献资料,在美国还是有一批的。这些文献,包括与电影相关的文字资料在内有几大箱子。前几年,这些资料都随着胶片一起转存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了。但哥伦比亚大学还没有时间打开过,里面具体有什么东西,我们还都不清楚,亟待整理。
李:在当前研究工作中,我们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龚:主要是甄别和完善影片的版本,他的很多影片在版本方面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今年(2020年)我们放映的《杭州,中国的园林城市》就是未完成的残缺片。哥伦比亚大学把拷贝完成数字化后,直接传给了我们。我们发现影片缺失了结尾部分,声音部分的解说词还很长,但是画面却没有了。为了保证一定的放映效果,我们就尽量地把一些影片素材尝试着加上去,制作成一个有头有尾的完整影片。在巡回展映中,这部影片给观众们观看是可以的,但从专业研究的角度来看,它还是有缺陷的。这个片子的原版是什么样的,我们没有看到。它是否还有其它的版本,我们暂时也不清楚。还有,我们获得的刚刚完成数字化制作的《中国木偶:永恒之歌》,这部影片时长有10来分钟,画面是完整的,但声音的部分缺失了。我们掌握的情况是这部影片是有声音的,譬如唐明皇的配音者是著名电影演员程之。如果这部影片的声带部分能够找回来的话,与画面配在一起,将会是一部非常精彩的影片。现在美国方面正在找,我们希望能找得到它。
三、翁万戈电影活动及其评价
李:从电影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创作者艺术活动主要的时间区间及其分期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维度,目前上海音像资料馆就这个方面是如何开展考证工作的?
龚:他的很多影片的拍摄日期,我们现在都没法判断。我们会去梳理哥伦比亚大学那边提供的馆藏文献归档信息,不过它的一些信息的完整度都是很有限的。比如说,一方面他们认为翁万戈的电影摄制活动开始于1944年,另一方面他们“哥大”图书馆的片目列表中并没有出现这一年度的记录来支持这个说法。现在看来,要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还需要结合我们国内能够利用的线索去作一些历史还原。比如《中国木偶:永恒之歌》,这部影片之前大家都以为是摄制于1947年。这部影片拍摄的主人公是中国木偶艺术大师虞哲光。虞先生的外孙告诉我,老先生于1947年,在上海拍过一个电影,拍摄者是一个从美国来的华人,叫翁兴庆(翁万戈)。我们掌握的资料显示,翁万戈先生是1948年的时候回的国。回来后,他在上海拍摄了中国的第一部木偶戏影片,当时还出了一本专刊。由此看来,这部影片应该是拍摄于1948年。
何:据说在1948年的时候,翁万戈先生还拍摄过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的电影。
龚:是的,在调查《中国木偶》这部影片时,虞哲光先生的外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息,说是在上海拍摄他外公的木偶戏的同时,翁姓导演还在愚园路幼稚师范学校礼堂为梅兰芳先生拍摄了一部《生死恨》。关于这部影片,美国方面目前还没有发现,我们也在找它的拷贝。也许,它只是一些素材片段,也有可能拍摄完后并没有剪辑成成片。如果翁万戈真的拍摄了梅兰芳的影片,那就有意思了。所以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里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待发现。
李:翁万戈先生与当时中国的电影界是否有着广泛的社会交往?
龚:他跟电影界的关系应该还是很熟的,他当年开办过电影贸易公司。我们现在知道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回国时第一个找的人就是司徒慧敏。他还拜访了民国时期的著名影星黎莉莉。
何:从上海音像资料馆举办的翁万戈电影放映活动的展映的几部作品来看,翁万戈作品的生产空间似乎与他的私人生活经验有着很大的关系,您是如何看待他的作品样式的?
龚:我的观点是可以把他的作品创作形态视作一种私家电影,就是一种私人拍摄的纪录电影。民国时期,影像文化已经开始浸入一部分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了,比如说某个大户人家去宁波祭祖扫墓、踏青,去苏杭旅游、逛公园,或者参加一些生活中的仪式化活动,年轻人的婚礼,小孩子的洗礼等,他们会用影像的方式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就像八九十年代,我们用手持摄像机去拍摄一些家庭活动那样。翁万戈的电影摄制活动明显带有这种私家影像文化的影子,他从美国回来,去自己的故乡常熟,第二故乡天津,就拍摄了《扬子江畔一小城》(拍摄地为常熟)和《天津,华北的门户》这两部片子;他去杭州拜访亲族故人,就拍摄了《杭州,中国的园林城市》;他与家人一起去旅游,就拍摄了莫干山、灵隐寺等自然人文景观,而且他的家人也出现在了他的电影中。我们能够在画面里看到他的母亲强夫人、他的女儿等。他所熟识的社会名流,像张伯苓、齐白石、张书旂、叶浅予,都出现在他的电影里。当然,翁先生的电影作品,和一般的私家电影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他的电影作品不是单纯的供自己或家人欣赏,他拍摄这些影片有使命感,是要向西方传播中国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只是,他的影片,充满了个性化。
李:翁万戈电影的主要艺术特点是什么?
龚:翁万戈很注重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影像呈现效果。在拍摄《中国皮影》时,他要求表演者用比较慢的速度操控皮影,以便更好的呈现出皮影艺术的细节和魅力。在拍摄叶浅予的《画中国人物》时,他希望画家能够将人物画得大一点,以便更好的与摄影镜头所呈现的效果相匹配。在拍摄《两种中国舞蹈》时,他与戴爱莲商议后,选择了拍摄更适合电影观众接受习惯的《瑶鼓》和《哑子背疯》。他对影片的音乐性、动作性、喜剧性,还有服饰特点等方面都是有所考虑的。翁万戈自身的中国文化素养很高,他是懂中国绘画的,很擅长画山水花鸟。他拍中国山水画,手绘的部分就是他亲自上手画的。在影片中,你可以看到他的笔锋,他的运笔是很有神韵的。你看在《扬子江畔一小城》中所写的解说词绝对是一篇散文,是可以纳入乡土教材里边的。
何:您是如何看待翁万戈先生的艺术品格的?
龚:我认为翁万戈还是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一个路子。他的影片跟孙明经的风格是不一样的。孙明经的风格是很客观的,像科教片一样告诉你科学道理,而他的每一部影片都很主观的。比如,在他的《画中国山水画》中的解说词写作里,一上来就是中国山水画是什么,中国人物画是什么。或者说,在“我”心目中、在中国的文化系统里,中国画是什么,他都很主观的。他有着自己的一个判断在里面,这种判断建立在他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之上。因为他出生于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里,读了很多中国古典的书籍,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化教育,他骨子里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气质。按现在的观点来说,他的主观是对的,这是一种中国文化自信感的表现。翁万戈的作品中还流露出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中悲天悯人的人文关怀意识。在《天津,华北的门户》一片中,他除了拍摄天津的工厂、港口、学校之外,还拍摄了很多平民、穷人的生活场景。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选择去拍这座城市最美的、最漂亮、最繁华或者最代表性的东西,而是跑到大杂院去拍摄那些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拍得很“细”。他还关注了平民学校,平民教育问题,用今天的话说,他的片子是追求有“正能量”的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