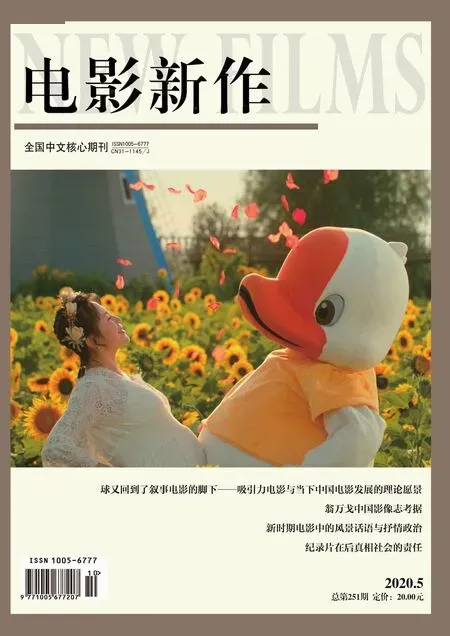意境一种:诗化小说的影像习得1
李铭韬 田雨萌
1980年,中国电影界面临了三重任务:电影艺术语言的觉醒、意识形态的重新修复及国门打开后“走向世界”的传播渴望。“诗电影”便是在此过程中被强调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且具有一定“类型化”特征的电影。它发轫于中国早期电影,兴起于“第四代”导演的纪实尝试,在“第五代”导演的整体爆发中得到关注并确认其美学传承。伴随着电影技术、市场、观众的发展与成熟,两代电影人在对诗化小说的改编过程中,成功地将“意境”以影像语言来营造和展示,为中国电影开辟了一片富有抒情传统的诗意视野。
“意境”,作为中国古典美学核心范畴之一,通常指在诗词、书画、戏曲、园林诸艺术门类中,运用虚实相生的手法创造,以自然景物为媒介,抒发主观情思与生命感悟的,意象契合、情景交融,令人回味无穷的艺术境界。小说中的意境萦绕在文本的字里行间,经读者的神思想往,在头脑中浮现一个属于个体独特审美创造的抽象画面。电影中的意境以空间为载体,在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信息通道中进行塑造,以具象的符号作用在观众的多重生理感知间。意境分“景、情、意”三个层次,鉴于以往中国电影意境理论探讨与电影本体联系较少,本文对应着电影本体构成中的“画、声、剪”三个部分,认为在画面和声音的创作对于景的生成和情的抒发虽各有其突出表现,但经剪辑呈现出的蒙太奇空间及剪辑间的镜头间隙才是意境与电影有机结合的真正所在。这符合电影艺术的制作规律,以此作为影像习得诗化意境的思路统筹。
一、虚实相生的镜头景语
虚与实是中国美学传统的核心论说,遵循着“天人合一”的中国人文精神,认为艺术和审美活动只有达到虚与实的统一才能达到圆满的境界。宗白华先生在“虚实”的美学范畴中提到了绘画、戏剧、书法、舞蹈和建筑等艺术样式;蒲震元先生在谈到意境的生成机制时提到了实境与虚境——实境即是诗、画中“直接呈现的蕴涵情景、形神的特定艺术形象或符号”,而虚境则是“由特定形象在幻想、联想、想象中生成的形象”。虚与实的审美原则贯穿在中国传统艺术中,作为电影的艺术参照标准。
(一)长镜头与景深镜头打造实境
“影戏”传统是我国电影的特色之一,它不仅意味着以戏剧冲突来架构叙事,而且在影像中也呈现出较多戏剧性特征。1980年初,在现实主义为创作导向的大背景下,巴赞的纪实美学被着重提出,并成为当时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表征。这种理论界的新一轮“西学东渐”很快就在创作中显现了效应,一批中国电影在视听语言方面做出一系列的突破,如在片中使用大量长镜头和景深镜头来拓深叙事的诗意性。

图1.电影《城南旧事》剧照
吴贻弓导演的《城南旧事》由三个相对独立的段落组成,段落以长镜头开篇,缓缓地摇过北京城南的胡同,随着人物的运动进入故事的环境中去;段落结尾处以人物主观视点为起始,慢慢地拉开,镜头内可容纳的景物越来越多,而人物则越变越小,以示与伙伴们渐行渐远,告别的伤感情绪在其中蔓延;在景深镜头中,“由远及近的被摄景物在画面中表现为全部清晰的影像”。跨院中的秀贞讲到缘分时,前景是青灰色院墙,中景的拱门隔出一个圆,英子没有搭话,微微出神。镜头在此刻做了静止的延长,人物仿佛被定格在此刻的画框中,共享此刻超越年龄的默契神会。前中后景在画面内清晰的位置关系不仅表明人物的内心境遇及人物间关系的距离,也让观影者拥有选择观看内容的权利,并在强化了真实感和唯美感的空间内产生对人物心灵的领会。
景深镜头与长镜头在影片中结合使用,通过人物与摄影机的横向与纵向调度,来展示层次丰富的景及与人物的关系。张艺谋导演的《我的父亲母亲》中,母亲多次故意经过父亲学校,均使用纵向运动的景深长镜头。身着艳丽棉服的母亲穿梭在被黄色覆盖麦地,少女和乡村的结合呈现出一种纯天然的画面景致。而当母亲听到父亲回来的消息,在白雪覆盖的村路中奔跑时,则以横拍的升格镜头来展示,使人物跳脱了环境;奔跑的动势中蕴藏着情感的积蓄,加之长镜头的辅助,在连续的镜头画面中被完整释放。霍建起导演的《那山那人那狗》中,父子清晨踏上行程,镜头先纵拍二人从雾尽头走来的小巷石路,接着横拍跟随人物跨过河流小桥,将人与景物空间的位置关系形成嵌入。以纪实性为特征的巴赞电影理论经过实践的演练,使中国被教育的观影模式产生了改变。观影视点在清晰的纵深和平面空间内富有变化地自由游移,带来一种自觉的沉浸观感。人物与空间的位置真实与观众的视觉真实由此而被牢固树立。
(二)空镜头和留白构图营造虚境
诗化小说的抒情特质使得意境营造成为电影表现的重要手段,由此而来的诗化影像类型演绎成独特的写意风格,以其对主流叙事和视听手法的反叛与突围,拓展了此时现实主义电影的阵营。具体表现为运用空镜头和留白的技术构图来营造虚境,与实境相伴相生。其中,空并不代表内容的简单,空的形式内蕴着充沛的情感,蕴藏着无限的生机与灵韵。空镜头排除了人的在场,给空间以无尽的遐想。观众在此得以长久地凝视驻足,体悟时间的停顿和感情的延宕。
《城南旧事》中秀贞讲述与思康第一次见面的场景,伴随着梦幻般的耳语,跨院中的画面慢慢游移般地流连,延伸向院外,再回到院子中来,定格至窗户。此时的空境是摄影机以英子的主观视角介入,让观众通过人物的眼睛来看和感受,得到画面物质之外的个体独有的心灵感悟,深入影像背后抽象的哲理思考与生命存在。《我的父亲母亲》在母亲殷切盼望父亲回归的一场戏中,加入了许多叠化空镜头来展示被太阳照射的乡村树林雪景、大路和学校,为父亲的归来和母亲的等待增添了一层心理的期待。它将人物在景物中排除而产生的距离感,使得物象得以孤立绝缘,自成境界。而空灵虚化的空间则由观众对其投入的情感观察与深度领悟所填补完成。
《那山那人那狗》中运用了构图留白的手法,运用自然界的天气雕刻空间。如开场戏中的山、乡间小路和房子均隐藏在飘着的白雾和云层之中,以半透明的云雾覆盖住主体的部分,使其有保留地不展示全貌,营造出静谧氛围。运用光线和物件,如父子俩坐在门前歇脚,背光的人物和门框形成黑色的部分将画面分隔成正方形置于画幕中间,形成老电影的观感。在简单的灰阶对比中,旧木屋场景与旧电影荧屏诞生出怀旧的质朴意境。虚实相生的镜头景语打造出技术化处理后的纪实美学风格,在发展现实主义的电影语言现代化过程中,融合了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意境到其中,为之增色,并树立属于东方抒情特征的电影美学风格。
二、抒情手段的声音探索
观众的审美体验建设需要多重心理活动的共同作用,其中包括感知、想象、理解和同情,从而达到直觉、神思和灵感几个不同的层面,因而需要多种渠道和方式搭建起叙述者—人物—观众之间的心灵通路。苏珊朗格认为音乐是情感生活的音调摹写。《礼记·乐记》中,提到音乐乃感情之产物:“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笨崽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在电影这门视听艺术中,声音是独立于画面之外的并行维度,对于叙事传达和审美接受有着关键性的参与。声音按其自身性质分为语言、音响和音乐,与画面结合形成声画关系,分同步和对位来展示和反衬情感。
(一)声音与画面同步
独白参与叙事,经营时空穿梭。独白是语言的一种,在诗化小说中,独白是人物直抒胸臆的一种方式。在电影中,人物独白伴随着画面,起到时空与情感自然过渡的结构性作用。《那人那山那狗》《我的父亲母亲》《暖》均采用复线叙事,选择人物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进入其内心世界并以独白的方式,在回忆往事的过程中将当前时空与过去时空相勾连。现实世界以人物所见画面呈现,内心世界以独白声音传达。在电影的改编中,独白作为声音的一种增添了多重叙事表意的可能性。
音响映照内心,丰富情感细节。音响分为有声源与无声源。在诗化小说的电影改编中,音响多为无现实来源的内心声音。《红衣少女》中安然在街上走着,街上嘈杂的环境音被无限放大,而林荫路上的安静又与重重的脚步声形成鲜明对比。安然茫然地看着前方,镜头画面快速地切过树上的“眼睛”,韦老师数选票的声音响起,这样强烈的音响将人物不平静的内心对照出。《我的父亲母亲》中,母亲在家织布听到读书声,奔跑向学校的途中所听到的孩子们朗读的声音越来越大。此时的读书声是母亲心中对于父亲归来的幻想,这幻想被化外成可感知的声音来表现。《城南旧事》中,英子看着小鸡吃米、秋千空空地荡着,和妞儿的笑声和聊天声出现在画面,这是英子脑海中声音的回响。观众在当下立刻领会到这是两个孩子经常玩耍的地方。
音乐组接镜头,构建抒情段落。《那人那山那狗》中,儿子背着父亲,轻音乐再一次响起,父亲回忆当年儿子骑在自己脖上的画面,恍如昨日。父亲在儿子的长大中理解到自己的衰老,一瞬间伤感与欣慰一起涌上心头,五味杂陈。《青春万岁》中,杨蔷云和张书群湖上滑冰的潇洒动作与激昂音乐结合,成为整部影片最为抒情的青春段落。
(二)声音与画面“不同步”
对位的声画关系产生引人深思的艺术效果。巴拉兹认为,对位的声音更有电影艺术的形式美感,也是有声电影有力的一种表现手法。非同步的声音独立于形象而存在,效果是象征性的,观众能感觉到它跟他场面之间的联系。这并非是观众感到它的真实,而是由于它引起了观众的联想。
《红衣少女》中,米晓玲退学去商店接替妈妈的班,安然得知后从球场穿过树荫斑驳的校园,途经一群女生合唱《闪光的珍珠》,这首歌成为这场戏的背景音乐,洋溢着青春气息。而米小玲的视线依依不舍地环绕过教室的每一处,要与朋友和校园生活的告别之时,这样富有生机的音乐反而衬托出离别的伤感。《湘女萧萧》中,三人乘船时,春官转交花狗送给萧萧的头花,船桨发出细细的划水声响,小船悄然驶过泛着波光的水面、错落的梯田和的村庄,一切看似都是那么宁静、祥和,却反衬出此时萧萧的内心已不再平静,因此波澜不惊的水面下实则蕴含着情窦初开的激情与懵懂;当萧萧生下花狗的孩子后,水满舂米的声音伴着悠长隽永的音乐,在山村风光的叠化展示中响起,实则暗喻着女性命运在蒙昧不自知中轮回。《暖》中最唯美的一场戏是暖和井河在谷场中荡秋千,浪漫的轻音乐配合秋千架吱吱呀呀地在空旷中回响,淡蓝色的薄雾中两个年轻人在空中浪漫地飞翔着。而当音乐突然静止,所有的声音消失,人物命运悄无声息的突变,瞬间进入永久的静默,曾经的唯美成为悲凉的愁绪萦绕在观众心头。
隐喻是诗化小说中的一种常见修辞,将环境与人物命运或情感症结相关联以达到隽永洗练的深长意味。电影中的隐喻通常将一种视觉内容同一种音响元素并列,音响通过它所包含的形象与象征价值而去突出画面的意义。当音响作用于人物的内心世界,画面的表意符号潜移默化地变为情感符号进行抒发。音乐以声音在运动中的组合来表现主体心部情感的艺术在所有的艺术类型中,它是最接近于主体情感与精神的艺术。当音乐的流转与画面运动的本质一致时,辅助着画面进行情感宣泄。与画面内容相悖时,也并非简单的视听分离,而是遵循着艺术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原则,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真正的和谐是对立中的统一”。因此,对位的声画可以制造出反差感和新奇感,吸引观众的注意和思考,从而凸显被反衬的深层情绪表达,增强艺术表现的张力。
三、蒙太奇间的情景空间
意境是一个由诸多意象构成的、情感往返其中的特殊审美空间。谭德晶强调:“完整连续的空间性是意境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意境形成的基础。”电影的独特性在于,作为时空兼备的艺术,一方面在时间中展开叙事,另一方面以画面占据空间。这两方面经蒙太奇的交织构成电影整体。因此,普多夫金说:“电影艺术的基础是蒙太奇。”马尔丹也谈到,蒙太奇是电影美学中最独特的元素,是创立电影美学所必需的条件。自苏联蒙太奇学派以来,电影的表现手段被不断发展,场景被切割为一个个拼接而成的镜头,蒙太奇从理性工具变为思维方式,为研究空间运动的拆解与合并提供本体论依据。“意境”寄托的空间首先在镜头中营造,在场景中展开,与人物发生互动,按照蒙太奇的节奏规律被铺排至整部影片。

图2.电影《红衣少女》剧照
(一)以景别铺垫情绪基调
宗白华认为中国传统艺术的意境偏向远景,从世外的高度鸟瞰律动的大自然;“高远、深远、平远”构成中国透视法的“三远”。诗化小说在电影改编时承袭了此美学原则,放置了大量能容纳更多景物的全景和远景镜头叠加,在一场戏的开始时营造环境氛围。平远的构成以摄影机机位与城墙、屋顶为水平线,加以俯视的角度来拍摄。如《暖》中的晒谷场是平远的运用。“山随平视远”意欲传达出天地浩渺的无我之境在此表现为黄与绿的大色块土地铺排,因其中孕育着生命与收获而成为平淡的生存向往意境;深远指走廊等传统建筑的空间表达。不同于景深镜头压缩纵深关系,深远的全景有助于现实空间和人物内心空间丰富又含蓄的展示。《湘女萧萧》中沉潭一场戏,通过光线明暗与构图纵深的层次安排呈现出萧萧心中对命运未知的恐惧;《红衣少女》的家中和走廊以及《青春万岁》的学校宿舍走廊也成为深远空间呈现的代表,反映少女青春的烦恼与心事繁密;高远即由摄影机仰拍而产生的由下向上的大全景。《我的父亲母亲》中仰拍母亲等待的路,《那山那人那狗》中仰拍父子二人的邮路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高远全景体现。几个不同机位角度的远景相接,全方位展示出环境空间与意境氛围。
(二)将景物缝合在人物的视线之中
“缝合”来源于拉康的儿童精神分析学说,意味着想象界与象征界自我统一。剪辑中的缝合指客观景物与人物行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人的内在经验发挥审美作用,将自然界化为认识对象来评价与取舍,达到《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境界。《红衣少女》中,安然泛舟一场戏使用了对切镜头,一个人物近景接一个景物空境,如此往复几个回合,示意人物正在对所见之物发生反应,而镜头充当人物的眼睛展示给观众。当镜头定格在闪着波光的平静水面时,观众已体会到她平静脸庞下的内心暗涌。《青春万岁》,随着杨蔷云的讲述,大量的雪景空境与人物的近景以降格跳接镜头相拼接,镜头中的景象成为人物内心的客观反射,由景物来传达出内心情感,形成内心情感的写意外化。
(三)在镜头的省略与重复中生成意境
电影是充满间隙的连续性画面,其本质在于看不见的抽象空间。在镜头中碰撞出产生想象性的空间,也是体现运动趋势的运动——影像。在前苏联蒙太奇学派的电影实践与理论中,“剪辑就是思想”。镜头之间的抽象空间往往强调的是一种观念。观念是一种现代价值观的经验判断,不属于古典美学的审美范畴,也就是刘勰强调的情感,“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要产生意境的审美效果,镜头剪辑的抽象空间应当是人物情感的隐喻,而不是理性观念的阐述。需要激发观众的想象,使镜头间的省略生发出无限的意义。
镜头间的省略生发出跳跃的节奏,而间隙就成为情绪蔓延的缓冲地带。《暖》的时空随着人物的思绪穿梭,当暖回到屋子放鞋回忆到蚕时,屋外井河与哑巴二人抽烟。随之又回到井河考上大学之时的场面,那宏大的远景紧接着窄窄屋檐下暖的家。这场戏中省略了一系列的动作的对白,没有事件的发展、物件的过渡和人物动势的连接,影像似乎成了意识流的再现,只任凭人物内心的情绪游荡回放。《红衣少女》中,安然发现三好称号的猫腻后破门而出,家中留下沉默的三口人。黑暗的楼梯间内小军告知父母离婚要搬家,家里姐姐看信后收拾东西要奔赴外地,镜头在一扇门内外切换,两场离别跟在一个真相后悄然来临。安然在夜幕中一路跟着姐姐到河边,看姐姐发呆出神,她似乎也跟着忧愁起来,忘记了该为哪件事而难过,体贴理解他人的心情又占据了心头。《城南旧事》的搬家途中,当爸妈说到过去和未来的事,镜头中英子的近景展示茫然的表情,幕幕往事在英子的脸上叠化着翻滚出现,碾压着英子的记忆。观众看到了她在想,也看到了她想的内容,但却无法确切地得知人物想起这些时的心情。事实上发生的事情对小小的英子来说实在是太难以捉摸了,但却留下了想象与体悟的空间。

图3.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剧照
另一种情况则是重复。《城南旧事》中,从院墙上俯拍学堂下课、胡同井口小推车打水、英子和妞儿玩耍与分享秘密的鸡窝子,在不同阶段出现,伴随着和玩伴的分离和英子的成长,暗示着时间的流动和人物的变化。《湘女萧萧》中,水满舂米、磨坊场景都出现了三次以上,暗示着女性的命运在蒙昧的不自知中轮回。《那山那人那狗》片头启程时出门的幽深小巷,父子二人和阿黄,三个主体在构图上呈现出三角形的稳定形态,而结尾当儿子踏上邮路时,父亲在家门口驻足,黄狗像一只箭射向充满雾的清晨田野,虽是同样的景象,但此刻的人物心境却截然不同了。《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父亲任教的学校、《暖》中的秋千架、《青春万岁》中的响起铃声后的鸽群飞翔,校园安静的镜头等,都是场景复现的实例。
结语
随着对诗化小说的改编和对电影语言的深入实践,一批富有诗化特征的电影形成了一种富有民族风格的电影类型,意境由此进入了体系阶段,经技术与艺术的融合演化,逐渐成为最具中国独特电影风格的标志性元素。考察诗化小说改编中的意境生成方式,从影像的本体规律入手,为中国传统的抒情文学指明了向现代性影像转化的沿袭之路。与西方电影理论推崇的符号论相比,东方电影以意境论为代表,承袭了民族性中诗意和抒情的文化传统,形成更为完整直观的诗电影类型创作规范,为中国电影学派的理论建构提供丰富的案例研究和规律总结。
【注释】
1本文来自第27届大学生电影节国际青年学者论坛。
2刘书亮.中国电影意境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3同2.
4罗艺军.致力电影民族化研究建立中国电影理论体系[J].当代电影,2008(8):85-87.
5宗白华.艺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86-290.
6蒲震元.中国艺术意境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许南明、富澜、崔君衍.电影艺术词典[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
8申燕.巴赞电影理论对中国电影的影响[J].文艺争鸣,2010(12):27-30.
9余月秋.虚实相生与中国电影的诗意生成[J].当代电影,2020(2):65-70.
10宗白华.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宗白华全集 (第二卷)[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346 .
11钟惦棐.电影美学.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5.
12[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84-107.
13胡安仁.电影美学[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84-107
14谭德晶.意境新论[J].文艺研究,1993(6):44-50.
15爱森斯坦论文选集[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2:348.
16宗白华.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宗白华全集(第二卷)[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10.
17[法]德勒兹.电影1:运动-影像[M].谢强、马月译.湖南: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