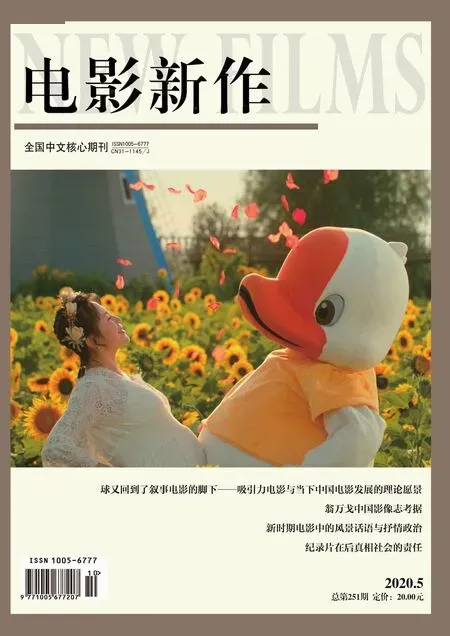《桃李劫》:“悲剧”美学与“吸引力”法则
陆佳佳
电通电影制片公司(以下简称电通公司)转型甫就,在起先给数部左翼电影配音之后,便立即开始了左翼电影的摄制工作。颇具戏剧编剧和舞台表演经验的袁牧之被委以编写剧本之重任,于是《桃李劫》就这样诞生了。《桃李劫》作为电通公司摄制的第一部左翼电影,其成功与否实际上直接关系到了电通公司的存亡。而电通公司作为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左翼电影机构,《桃李劫》也间接地影响着左翼电影运动的全局。因此,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桃李劫》也一直都得到了以夏衍为领导的党的左翼电影小组的倾情关注和密切指导,从而促使其成为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影响力的左翼电影之一。同时,《桃李劫》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也“标志了这一时期左翼电影‘围剿’的重大胜利”。作为一部左翼电影,《桃李劫》不仅大胆、直接地向观众们展现了一段在黑暗统治历史下发生的社会悲剧。同时,《桃李劫》通过“吸引力”的叙事策略,在进行左翼叙事表达的时,也注重其影像上的现代话语和体感经验,并试图在影像层面上积极地建构现代性和都市文化的反身话语。

图1.电影《桃李劫》剧照
一、“悲剧”美学:知识分子的理想破灭与希望
根据左翼影评人舒湮的说法,《桃李劫》是由斯迭芬列浦的舞台剧《未完成的杰作》改编而成,“但是其在内容上又是优于前者的,它摒弃了原舞台剧中善恶的唯心观念,并科学地把握到现象所产生的社会根据”。在这里,舒湮所提到的“现象”其实就是影片中所展示的“悲剧”。《桃李劫》讲述了一个有关知识分子的家国理想在现实的黑暗社会/世界中逐渐幻灭,并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剧道路。《桃李劫》中,袁牧之将知识分子推向深渊/悲剧的最直接原因归为“失业”。袁牧之将笔墨触及社会问题,是因为当时的电影“已不仅是娱乐,就因为这个缘故,使电影制作者将更慎重于其题材之选择。所谓题材,即便故事的中心,在故事本身的发展,使之服从于这题材的蓄意。电影制作者在取用题材的时候,已经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了,他们该认清所取用的题材,是不是更广泛的于一般人发生较大的意义”。

图2.电影《桃李劫》海报
《桃李劫》的主人公是一名叫陶建平(袁牧之饰)的建筑工业学校青年毕业生。在老校长的教导下,陶建平和他同毕业于建筑学院的妻子黎丽琳(陈波儿饰)都满怀一腔正义,充满了抱负社会和国家的激情。因此,走上工作岗位的陶建平时刻怀揣着这种信念,踏实奋进,对社会中各种不公、不正、不义之事保持着强烈的不满,从不屈服于各种恶势力。但是,也正因如此,陶建平常会触及资本家的利益,在工作与生活中被排挤、被压迫,后来不得不陷入失业的窘境,以至穷困潦倒。陶建平的妻子黎丽琳更是被困顿的生活折磨到几乎生命垂危。影片最后,走投无路的陶建平也因向工厂预支工资不成,万般无奈后偷了包工头办公桌上的银元而被警察逮捕,最终因暴力反抗被判死刑。怀着孕的黎丽琳也因无药医治而不幸玉殒。袁牧之特意安排了“老校长”这个角色,在叙事中承担了很大的作用,即“老校长”承担了叙事的推动力和视角的作用。作为“叙事推动力”,“老校长”帮助观众提出了疑问:在校时,各方面表现得如此优秀的年轻人走上社会后竟会落得如此境地?陶建平究竟经历了什么?是陶建平自甘堕落,还是他被迫而为,或者有其他难言之隐?另外,“老校长”作为一种叙事视角,呈现出了造成陶建平悲剧的关键原因。与此同时,作为老师,“老校长”教陶建平要为人正直、心怀家国。但是,“老校长”却目睹了陶建平的悲剧史。在影片中,“老校长”对于陶建平和黎丽琳遭遇的惋惜感和悲痛感时时刻刻溢于银幕内外,并在《毕业歌》的营造下呈现了最痛人心的“悲剧”。可以说,“老校长”的存在,不仅见证了陶建平的悲剧发生的过程,还将对陶建平的惋惜以及无力感无限地放大,更是将“悲剧”传递给观众。通过这种叙事手法,袁牧之得以成功地将战后的社会形态与人际关系赤裸裸地、不加修饰地放置于每一个观众面前,以影像与观影装置的魔力“强制性”地让大众去目睹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善良人,是如何一步步地被乱世的深渊所吞噬的,这种方式可以让人们在观看和体验悲剧的过程中产生同情感,并最终在这种情感体验的督促中去展开对社会、战争和人性的诸多思考。
毋庸说,在《桃李劫》中,陶建平和黎丽琳的个人悲剧是彻底的、深刻的,而这种悲剧也能够在叙事上更加明显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统治之下的社会黑暗现实。影片一经上映便获得了不少左翼影人的好评。但是,《桃李劫》的这种悲剧叙事也曾一度被当时不少的观众所批评。他们认为,这种纯悲剧式的、不给观众提供出路的影片是无益于社会的正向发展的。例如,克真在《<桃李劫>评——银壇新人的处女作》一文中指出,“看完了这部《桃李劫》影片,我们只留着一串的社会的黑暗面于观众的脑海里,虽然我们已是身受过这种社会痛楚的过来人,但毕竟这是令人过于失望的悲剧啊。老实说,这种一轨的揭发社会黑暗的影片,一方面似乎是负起了透视社会剖析社会的责任,但另一方面是只给观众们取得了对现社会黑暗面的认识,不但不能鼓励观众对社会‘正面的’‘向上的’努力,而只使观众们受到了‘颓废’‘苟取’‘腐化’的社会观,否则好似只有被摒弃于现社会的资格了。唉,这是多么可怕的影响,如果负有社会教育责任的影片制作者再不顾到向上的鼓吹,怕只有留下了一个万念俱灰的恶印象在观众的脑海里……”
实际上,《桃李劫》的此类批评,并非个例。对于持此类观点的观影者所产生的情绪也并非是不可理解的,因为生活于困顿的现实社会中,他们更希望通过电影这种造梦机制来为他们提供一种走出现实、解决问题的方法,抑或是提供一种心灵上慰藉。对于“电影”这种新兴艺术的期冀,他们还未能完全跳出20世纪20年代的“娱乐性”。所以,在面对左翼电影所展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时,他们无法快速地适应。很显然,袁牧之的《桃李劫》并无意于去迎合观影者的“娱乐性”。相反,袁牧之是以“对社会极端的现实认知和激进的理念表达”,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直面悲剧、正视现实的机会。《桃李劫》中,陶建平和黎丽琳的悲剧也必然将是“现实社会的人类生活里面的一个赤裸裸的生活断面”表征。事实上,袁牧之借由主人公陶建平的口直接地揭示出悲剧和“不公正社会关系”的阶级源头——资本主义。
《桃李劫》“是一部现实的作品,在题材上,是没有什么空幻的结构,生硬的穿插。他把握住这转型期中的知识分子一般的生活,从开始到结局叙述下去。”“通过让人物生活在产生他们的正值意识中,编剧可以创造一种‘社会曝光’的形式。这种社会曝光可以激发‘进步的观众感受到社会不公正和其现实内部冲突的痛苦’,而非进步观众则亦能觉察到迄今为止掩盖了的不公正社会关系的意识。”“《桃李劫》中暴露的正是一般社会的现象,每个曾经看过的智识大众也许会勾起满腔哀感的创伤,承认电影是种文化运动宣传工具的,更不会驳斥我们这是无聊的说谎。”
此外,在影片中,袁牧之在文本叙事当中提供了一种“变化”的概念,这种“变化”既是空间的——从学校生活空间到社会生活空间的变化,又是正义、善良的知识分子陶建平和黎丽琳的个体命运的“变”。陶建平和黎丽琳从一个青春洋溢、怀揣抱负的奋进青年,最终变成了形容枯槁的阶下囚和丧命者。要知道,他们原本是坚守知识分子心怀天下、谋福社会的信仰,是具有一定崇高属性的“道德化了的自我”,是社会精英阶层。然而,他们却在个人主义式的狭隘自利的乱世中“毁灭”了。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典型,他们在个人命运和生活中产生的这种“变化”,实际上折射出的是知识分子群体所面临的命运困境,承载了知识分子理想悲剧的现实内涵。

图3.电影《桃李劫》人物海报
《桃李劫》中所展现的这种“变”,所表征和承载的“悲剧”美学与当时寻求新出路的“救亡话语”相契合。因为,这种“救亡话语”所蕴含的不仅仅是希望拯救以陶建平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更是希望拯救这个正被战争、压迫所侵蚀、迫害着的中国社会,它是包含着美好的、光明的、正义的且属于中华民族的人性话语、文化话语、社会话语和民族话语的多元综合体。只有整个社会免于被“黑暗”吞噬,人才能各得其所,各得所幸。这是袁牧之《桃李劫》“悲剧”的真正意图。袁牧之的《桃李劫》“以知识分子身份投入时代洪流中,同时继承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所秉承的批评精神”,是对黑暗社会直接的揭露和个人命运的“悲剧”拷问,并且它“逆向度”地表达了人们对美好未来地期许和追求。
二、从体验到认同:“吸引力”元素的运用
1986年,汤姆·冈宁(Tom Gunning)提出“吸引力电影”(The Cinema of Attractions),认为它“是直接诉诸观众的注意力,通过令人兴奋的奇观——一个独特的事件,无论虚构还是实录,本身就很有趣——激起视觉上的好奇心,提供快感。”事实上,制造“快感”是需要“吸引力”法则/元素的,它“具有具有不断地吸引/诱惑人们的功效……它是一种主动追逐观众的方式,而不只是简单满足观众喜好的过程”。如此,影片才能够获得观众的喜欢,从而在市场上获益。基于此,深入考察袁牧之的《桃李劫》,我们可以发现,它在声音、人物和都市景观等方面都遵循了“吸引力”的法则。
(一)现代性:都市景观的想象
现代化的都市风光,总能让人产生惊讶感受。而这种“惊讶”实际上就是汤姆·冈宁所说的“吸引力”。事实上,对于早期中国电影来说,上海的都市风光就是一种“吸引力”的具体表现。在《桃李劫》中,上海的繁华街道、霓虹夜灯、歌舞厅、饭店等场景,除了吸引观众之外,也时刻刺激着“观众对电影的热情”的作用。
《桃李劫》中,有两个段落呈现了繁华的都市空间。第一,黎丽琳受男老板之约到泰山饭店与客户洽谈业务(实际上是老板想要设计占有她)。下班后,黎丽琳与男老板一同乘坐轿车前往泰山饭店。一路上,沿途风光尽是华灯闪烁的霓虹灯以及时不时发出的汽笛声。到了泰山酒店后,他们乘坐着电梯来到就餐地点,路过了歌舞厅,并与无数个都市摩登男女擦肩而过。音乐、摩登女郎、霓虹灯闪烁的建筑等混杂在一起,造成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令人沉浸其中;第二,陶建平到泰山饭店去寻找黎丽琳。黎丽琳仓惶地从色魔老板的魔爪中逃脱而出,又恰好与等在饭店自动门前的陶建平相遇。他们二人互相对视,一言不发,各自心中千头万绪。此时,二人的尴尬和局促与周围充满资本主义气息的都市景观格格不入。不可否认,这种格格不入的都市景观又反衬出了陶建平、黎丽琳的失落感。可以说,袁牧之是借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摩登景观来吸引观众的同时,也强有力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虚伪,更巧妙地为观众提供了一个宣泄和抒发现代性感受和情感压迫的有效窗口。
此外,《桃李劫》还通过都市景观的内部进行了直观地呈现。影片开头部分,新婚后,黎丽琳、陶建平居住的洋房的装饰是以当时流行的欧式风格为主,配以宽大柔软的沙发、纯白的拖地帘蔓、带镜的衣橱、玫瑰花、天使骑马造型的西洋雕塑,以及墙上挂着的结婚照片——西式婚纱照。这些奢华的景观,都被袁牧之直观地呈现了出来,并产生了一种汤姆·冈宁所谓的“与现代性的遭遇”的观影效果。
(二)摩登性:反身话语的都市“代言人”表达
摩登男女同样吸引着众多人的目光。当她们穿着时髦的衣服,打扮得帅气或妖娆,身体的魅惑性便凸显了出来。因此,相对于现代化的都市景观的“吸引力”来说,都市“代言人”的审美更多的是一种视觉与精神触觉的交织,能够使观众迷恋其身体。在《桃李劫》中,都市“代言人”是具有反身话语性的,即通过都市中的陶建平、黎丽琳来呈现。
毕业后,陶建平梳着光滑的油头,身着笔挺的西装,脚穿锃亮的皮鞋,仿佛一个有头有脸的都市成功者,是阔绰少爷。同样,黎丽琳也是身穿时下最流行的紧身开叉旗袍,烫着微卷的短发,略施粉黛,画着柳叶眉,好似一个摩登女郎。她们这种打扮,还是吸引力不少观众的注意。不容忽视的是,陶建平与黎丽琳是进步的知识青年,有着造福社会的伟大理想。从而,从他们身上,观众看到了时尚、活泼、青春的个人形象。与此同时,陶建平与黎丽琳的浪漫爱情,也为观众提供了一个现代性的情感体验。

图4.电影《桃李劫》剧照
但是,“摩登性”极强的黎丽琳,在应聘工作时,吸引了公司的男老板。他常常窥视工作时的黎丽琳,甚至还设计把黎丽琳约到舞厅、宾馆里,并企图强行占有她。在此,黎丽琳承担了一种被男性偷窥、想象和觊觎的女性喻体,不仅吸引着银幕内的男老板,还吸引着银幕外的男性观众。此时的黎丽琳实际上沦为了一种“现代性产物”,凝聚在她身上的各种性格和外在特征都将象征着一种“城市文化,以及速度、商品文化、异域情调和色情的魅惑”。进一步说,男老板把对摩登女性的欲望和幻想不加掩饰地投射到黎丽琳的身上,并试图以中产阶级的“成功者”去占有这个处在身份、性别和阶层劣势的摩登女性。换言之,“男人作为认知的主体,他把女人的身体放置在认知的客体位置上,通过视觉观看行为来声称揭示真实——或者就把客体推入了终极谜面。”由此,“她在男性身上激起的情感,是极端令人迷糊又极端具有判性的。”黎丽琳在性别和阶级上的双重弱势也恰如其分地凸显了这个现代都市对她的冷漠和不善。这一设计丝毫未削弱影片的批判性。与此同时,声音作为一种新技术被导演们所应用,既能改变影片的整体结构,又能赋予角色多层次的情感,还能给观众带来新鲜感,成为“吸引力”的元素之一。尤其是,1930年,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的诞生,引发了国内影人对电影声音的讨论。同年,在担任《艺术》月刊主编时,夏衍便敏锐地意识到“声音”元素/技术之于未来民族电影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他以《艺术》月刊为研讨平台,广邀冯乃超、郭沫若、王一榴、郑伯奇、洪灵菲等进步文艺工作者集议有声电影的前途问题,并发表《有声电影的前途》专辑。在这次讨论中,大多数的文艺家通过观看以音乐为主的欧美有声电影后,一致认为,“有声电影现在自然还在开始试习的期间,故一面给予人以一种新奇的趣味,但另一面却使人感到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并且,他们指出,“要使用有声电影去辅助在某对于观影大众而言,它也具备足够的吸引力。
(三)“大众语”:“声音吸引力”
20世纪30年代,有声电影的技术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迎来了电影声音美学的一次新革命。种表情和境地更使观者感到加强的印象与感触,这才是有声电影的重大任务,否则纵使歌女的喉音如何魅婉,跳舞的肢体,如何活泼,也还不过是到音乐会,到跳舞厅里去一样而言。”可以看出,当时的上海电影界同仁大多已经关注了有声电影的技术问题,并对本土有声电影的发展充满了期待。这次对有声电影的集体讨论从侧面反映了时人对“声音”这种新技术与电影相结合的现代想象。

图5.电影《桃李劫》剧照
1934年,袁牧之的《桃李劫》率先采用了“影乘音”有声电影技术,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使用有声电影的声画技巧进行创作的影片。《桃李劫》中,声音元素不再是那种与叙事不耦合的、简单的电影配乐,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到叙事中且能产生情感效果。进一步说,《桃李劫》中的声音元素不仅是对各种“新的生成条件(机器、工厂、都市化)、流通(新的运输工具、交通)与消费(大众市场、广告和大众时尚的崛起)的一种反应”,也是参与表达现代性的“工具”。例如,主题曲《毕业青年的内心,是“突起于悲剧中的雄壮的呼声”,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反抗压迫、奋起抗争的热情和斗志。与此同时,它也如一首温柔的抚慰曲,治愈着每一个受伤的、破碎的、胆怯的心,同时,也让观众沉浸在歌曲中,感受到它的精神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毕业歌》外,其他声音/音响元素也跳出了原来国产影片蜡盘配音,机械配合画面的窠臼,形成了“新”的声音奇观。例如,影片开头展现街市的一场戏,音响的运用便很独特。报纸叫卖声、自行车铃声,以及行人嘈杂的喧闹声等都“充溢”于街道之中,为观众展现出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摩登都市景观。再如,老校长坐在办公室翻看报纸,其身后是一扇面对街道的窗户。在处理这一场景时,袁牧之并没有将前一个街道场景中的各种喧闹声消除,歌》的运用。《毕业歌》由著名左翼文艺家田汉作词、作曲,歌曲旋律铿锵有力且不失雅致、悠扬,尤其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兴亡……”唱进了每一个爱国而是通过“窗户”这个中间介质,合理地将窗外街道上的声音保留了下来。因此,我们看到的效果就是老校长在屋内翻看报纸,找寻学生陶建平档案的过程中,画外音也表现出了街道上的嘈杂声和叫卖声。此时,这些声音元素的存在,不仅有效地扩大了影像上原来略显狭窄、固定的室内空间,还扩大了影像表述的空间张力,增强了影像给予观众的真实感受力,从而能够在银幕上调动起人们对日常的生活经验的总结和思考。更为重要的是,这段街道声的画外音也将老校长看到其昔日爱徒陶建平将要被执行死刑时的内心活动进行了“外化”,一如那喧闹、嘈杂、无序的街道之声暗示了老校长的慌乱、震惊、无措与懊恼。在这里,影像声音/音响元素不仅仅作为现代技术的表征,为观众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的、现代性的观影体验,同时也有效地参与和推动了电影的叙事。
再如,毕业后,陶建平和黎莉丽来到湖边幽会。他们在林荫小道上奔跑、嬉闹、拥抱,一起坐在垂柳下互诉衷肠,而此时的画外音是浪漫、活泼的西洋钢琴乐,以及鸟儿雀跃的啼叫声,这表现了他们相互间甜蜜的爱意。但是,在表现陶建平于工厂做工时,声音就发生了变化,即由动人的音乐变成了嘈杂的声音。笨重的机器声、杂乱的工作声,以及各种车轮声、工人的喘息声等环境音混杂在一起,有效地将苦闷的陶建平勾勒了出来。同时,在陶建平将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婴儿送到育婴堂的过程中,狂风暴雨的呼啸声与婴儿凄惨的啼哭声混杂在一起,将陶建平内心的痛楚、压抑、苦闷和绝望的情绪展现地淋漓尽致。尤其是,陶建平被执行枪决时,影片配以“砰”的枪声和《毕业歌》,“雄壮的毕业歌声就隐藏在耳,不觉老泪横流,悲恸欲绝”,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震撼着每一位观众。可以说,《桃李劫》中“声音”成为叙事和艺术表达的重要表现手法,大大超出了声音单纯图解影像的作用,为影片的现代体验表达提供了一个技术层面的阐释维度和一种特定的现代性历史体验,并成功将这种体验带了观影的领域。
结语
《桃李劫》将镜头对准了当时“失业”这个社会性的问题,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资产阶级,“他的个人反抗必然将和他的小资产阶级幻想一起破灭”。毋庸说,《桃李劫》一方面以知识分子理想幻灭和自我“毁灭”的悲剧来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当局的腐败统治。另一方面,《桃李劫》巧妙地采用了“吸引力”法则,通过声音、都市风景、人物等增加了影片的戏剧性与可看性。
【注释】
1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378.
2舒湮.《桃李劫》(评一)[N].晨报,1934.12.7.
3同2.
4华光.从《桃李劫》的题材说起[J].青春电影,1934(10).
5克真.《桃李劫》评——银壇新人的处女作[J].新人周刊,1935(1):19.
6袁庆丰.电影《桃李劫》散论——批判性、阶级性、暴力性与艺术朴素性之共存[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2).
7金光洲.《桃李劫》(评二)[N].晨报“每日电影”,1934.12.17.
8周青如、苔立、梁天华.“桃李劫”[N].民报,1934.12.17.
9同8.
10[英]Victor Fan:Cinema Approaching Reality:Locating Chinese Film Theory Minneapolia,Unive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5,P63.
11秋蛹.《桃李劫》杂东北[N].金刚钻,1936.3.1.
12戴海光.知识分子悲剧精神消解的图式——以阎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为个案[M.广西:.广西社会科学,2014(4).
13周文姬.40年代知识分子自我主体的剥离与建构——以《一江春水向东流》和《哀乐中年》为例[J].当代电影,2017(12).
14[美]汤姆·冈宁.吸引力电影:早期电影及其观众与先锋派[J].范倍译.电影艺术,2009,(2):62.
15刘宇清.吸引力电影:翻译、旅行与生命力[J].文艺研究,2012(6):121.
16张真.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M].沙丹、赵晓兰、高丹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19.
17[美]彼得·布洛克斯.身体作品[M].麻省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33:97.
18[美]史书美.性别,种族和半殖民主义:刘呐欧的上海都会景观[J].亚洲研究,1996(4).
19《艺术》月刊于1930年3月16日创刊于上海,上海艺术剧社出版,红叶书店代理发行,沈端先(夏衍)主编。内容以戏剧、电影为主,主要配合艺术剧社的演出,积极从事戏剧理论建设。文章主要有《普罗文艺的大众化》(麦克昂,即郭沫若)、《中国戏剧运动的进路》(郑伯奇)、《有声电影的前途》专辑文章等。此外还刊载了《艺术剧社第一次座谈会速记》《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等重要文章,为现代文艺运动的珍贵文献。由于该刊积极倡导左翼进步文艺运动,提倡“普罗戏剧”,仅出版了一期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查禁。后更名为《沙仑》月刊。
20专辑文章载《艺术》月刊,1930年3月16日。沈端先(夏衍)为此次讨论撰写了“编者小引”以及《Sound picture的时代》一文。其他文章还有冯乃超的《有声电影》、郑伯奇的《Movie Radio Talkie》、洪灵菲的《关于有声电影》、侯鲁史的《看了有声电影之后》、李一氓的《我与Talkie》、超孟的《有声电影到那里去》、祝秀侠的《对于有声电影的意见》、陶晶荪的《有声电影写几句》等。
21祝秀侠.对于有声电影的意见[J].艺术,1930(1):1.
22[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状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4.
23探曲.《桃李劫》里的毕业歌[N].民报,1934.9.22.
24舟叶.《桃李劫》.时代日报[N].1934.10.9.
25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2:3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