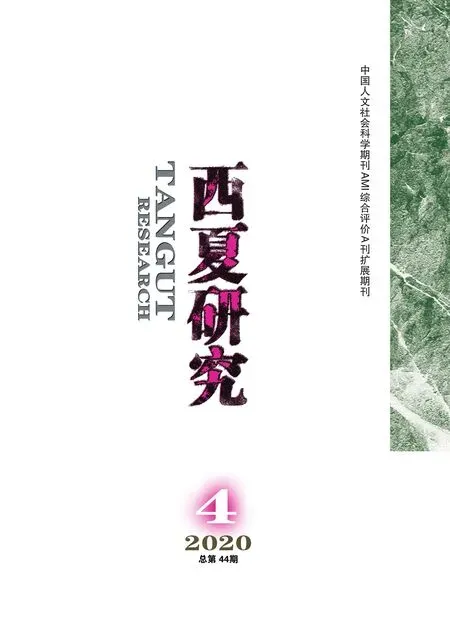西夏的北邻①
□[英]高奕睿著 吴宇译
自11世纪始,西夏逐渐发展成中国宋朝西北边境的主要势力,被强大的邻国全面包围,其首要任务之一是建立民族认同。初期的准备涉及雄心壮志的文化工程,比如发明自己的文字,翻译中原的宗教、哲学和文学作品。现存的西夏文献②大部分是佛经,反映了佛教在西夏的重要性,同时也翻译了许多世俗作品,包括一些儒家经典和一些历史著作、文学作品。虽然佛经几乎逐字地被译成西夏文,但其他著作的翻译往往并没有那么严格地遵循原文的语序和语法结构,从而能为西夏本土读者提供更易读的文本。
在这方面有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保存在英国国家图书馆的一个写本,最初由斯坦因(1862—1943)在1914年发现于故城哈拉浩特遗址。这是一本名为《将苑》的军事专著,表面上托名于3世纪著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诸葛亮(181—234)。现代学者认为这个作品是后来伪造的,托名诸葛亮只是用来使其内容具有权威性③。《将苑》现存最早的版本可追溯到明代(1368—1644),所以其西夏译本代表了现知最早的版本,而且早得令人惊讶。遗憾的是这个写本不完整,丢失了前半部分。但如同汉文本中的情况,其章节有编号,我们可以看到(二者)章节顺序是非常不同的。然而除了章节编排的不同,该写本现存的大部分与存世的汉文本的内容十分一致。西夏文本唯一明显不同于汉文本的部分就是最后四章,描述的是中央王朝周围的外族,即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汉文本清晰地反映了边境族群的中国中心观,这种模式是否已被尽力调整以符合西夏的世界观,是值得研究的问题。通过比较西夏文本和汉文本可以发现:译文中确实省略了对这些部族的描述,只保留了被称为“草原主”的北狄。其中描绘了骑马好战的族群,在正面作战中优于汉人。考虑到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的地缘政治情况,蒙古人在西夏和女真的北部草原上迅速积聚力量,对西夏读者来说,“草原主”可能指的是蒙古人。今天我们知道译者在当时不可能知道的事情,就是这个北方邻国将在几十年里通过格外残酷的军事行动,消灭整个西夏,征服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译文对其他三个——东夷、南蛮和西戎的省略,表明了有意识地脱离汉文原本,创造一个在西夏人看来既相关、地理又准确的文本。
一、西 夏
西夏,或称唐古特(1038—1227)的史料很缺乏。 元朝(1271—1368)时修了金朝(女真)(1115—1234)、辽朝(907—1125)和宋朝(960—1279)的正史,西夏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所以未修其历史。我们所了解的西夏历史,主要来自其他三个朝代的史书和少数其他的史学著作④。毋庸置疑,在汉语材料的单方面主导下,作为敌人的西夏,其历史自然会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和其他类型材料相似的情况,然而本土西夏文文献更贫乏,大部分文献在蒙古征战中遗失。虽然书面上这种文字很好地延用至了明代,但日常环境中不再使用,最终被人们遗忘。只有随着20世纪初大量西夏文文献的发现和后来的破译,研究人员才逐渐获得西夏文写成的第一手资料。
12世纪下半叶,西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势力之一。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它从一个河曲北面的小政权,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实体,占据了青海湖以北的大片地区,是其原来领土的20倍左右。到1036年,李元昊继承王位四年,西夏已经管辖夏州、银州、胜州、凉州、甘州、肃州和瓜州[1]58[2]179-180(参见《宋史》卷四八五)。此时的西夏年轻且不断扩张,西夏是个多民族政权,其核心居民是党项人,还住着汉人、吐蕃人、回鹘人、契丹人和其他民族的居民⑤。随着西夏的扩张,这些外族中大多数人居住的地区被吞并,他们便成为西夏的一部分。从而,同一种族的人最终居住在西夏边境内外,内外人口的划分模糊,是很常见的军事扩张的结果。我们必须设想,“外(foreign)”通常不太被视为民族的问题,而被视为专指某个特定国家或政权。依据西夏的法律,居住在境内的非党项民族享有相对的平等。从族群义务的层面来看,族群内的社会地位比民族和部族关系更重要,且仅在同等级的情况下,党项人才享有特权[3]147[4]200。
从元昊的统治到被蒙古征服,在这近两个世纪里西夏有许多邻国,大多数邻国都曾和西夏发生过或长或短的战争。其西南有吐蕃,西有回鹘。在东北,1115年以前夏与契丹接壤,之后与女真接壤。在东面、东南面和南面,11世纪时与宋接壤,12世纪时与金接壤。最后,北方被突厥蒙古部族占领[1]61。13世纪早期之前,突厥蒙古部族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已凝聚成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西夏是蒙古扩张之路上第一个重要的阻碍。第一次袭击始于1205年,从那时起,西夏境内每天都充斥着来自北方的威胁⑥。最初他们还有能力抵抗甚至赢得一些争战,但同时他们也在东部与女真作战,这种双重战争耗尽了他们的资源。为了建立一个能够抵抗蒙古的统一战线,夏曾试图与金结盟,但最终都未实现。当然,这样的联盟没有达成,夏—金冲突得以维持,最大获益者是蒙古。经过20年断断续续的争战,1225年底成吉思汗亲自指挥了一场征伐西夏的决定性战役,其结果是1227年西夏灭亡。
至少从我们现代的角度来看,西夏对人类文明史的主要贡献之一是他们的文字和著作。西夏文字创制于1036年,这是李元昊建立西夏准备的一部分,目的是建立其身份,可以将西夏与强大的邻国宋朝区分开来。这种文字被采用后,几乎立马用于一个宏大的翻译工程,这个工程的目的是造出一个西夏文的《大藏经》。除了佛经外,中国世俗著作也普遍地被翻译,包括一些儒家经典和一些历史、军事和文学作品。大部分的翻译似乎是在12世纪完成的,当时的西夏经历了长期与邻国激烈的战争,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
考虑到与汉文原本相比译文的保真度,科洛科洛夫和克恰诺夫[5]11针对儒家经典注释道:“西夏译文做得异常准确,几乎逐字逐句对应,西夏译文通常只在词序上不同于同时代的汉文本,附加了一系列西夏语法要求的额外的虚词。”另一方面,非经书作品倾向于不那么严格地遵循原文的语序和语法结构,试图为西夏本土读者提供更易读的文本。有时不仅语法,而且内容本身也可以修改,以使文本符合西夏的世界观。日本学者西田龙雄称这种方法的结果为“非字面和自由翻译”,并注意到西夏译文有时比汉文更容易理解⑦[6]233-234。在西夏文《孙子》的研究中,克平[7]20-21更进一步认为,有时译者为了本土读者更容易理解,对文本进行意译⑧。特别是文学隐喻、寓言和文学典故被灵活处理:或者完全省略,或者用日常语言重述[8]19-20。
二、汉文本《将苑》
这个名为《将苑》的文本,传统上托名3世纪的战略家和政治家诸葛亮,对于普通大众来说,诸葛亮之名在14世纪的小说《三国演义》中得以不朽⑨。诸葛亮尤以非凡的智慧和军事才能著名,他利用出色的计谋击败敌人,取得胜利。他已成为一个象征着军事智慧的标志性人物⑩,哪怕历史上他并不总能赢得战争。作为一个在用笔和用剑上有着同样天赋的人,其文学能力亦拓展了人们对他的浪漫主义想象。虽然3世纪的正史《三国志》收入了诸葛亮所著的一系列作品,但其中并没有《将苑》。
这些情况导致学者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将苑》是一本相对晚出的伪书。表面上,这部作品中出现的大量军事战略借自其他文本,这也被看作指示了该作品辑录自其他的书,意图创造一个可托名诸葛亮的文本。伪作的标签本身足以降低这本书的价值,并把它排除在严肃的学术研究之外。一定程度上由于对这个文本的不重视,学界并没有严肃的研究来确定它真正的时代和作者。这本书只存在于流行的军事战略知识中,通常被认为是战争方面的权威著作,基本上不涉及真实性或批判性的学术问题。
《将苑》现存最早的版本可追溯至明代。我们所知的明本有正德十三年(1517)、嘉靖四十三年(1564)、万历年间、崇祯十一年(1637)的印本。1564年的复本有一篇序,写于弘治三年,1637年的复本可追溯到成化乙巳年,即1485年。这些年代使我们能够在时间上大大地往前追溯这些版本。此外,该文本也被收入陶宗仪的大型丛书《说郛》(fl.1360),据其序言可追溯到1370年⑪。在汉文材料中,该文本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名称。除了《将苑》,有些版本还以《心书》或《新书》为题。这是我们根据汉文资料所能追溯的《将苑》的历史。西夏文献的发现帮我们把这段历史又延长了两个世纪,这两个世纪在汉文传统中完全丢失了。
就其结构而言,该文本由50个短小的章节组成,每章开头有两个字的标题⑫。在大多数版本中,标题都有章号,但不是全部都有。每章谈论一个具体的战略原则,比如要正确地用人、要考虑地形特征、要奖惩合理等等。总的来说,《将苑》是从将军的立场来写的,针对领导的不同方面提出建议。最后四章(C47—C50)讨论了四夷,描述了他们的特征和与他们作战的方法。本文提出的是文本的最后一部分及其西夏译文。汉文本的完整译文如下⑬:
东夷第四十七
东夷之性,薄礼少义,捍急能斗,依山堑海,凭险自固。上下和睦,百姓安乐,未可图也。若上乱下离,则可以行间,间起则隙生,隙生则修德以来之,固甲兵而击之,其势必克也。
南蛮第四十八
南蛮多种,性不能教,连合朋党,失意则相攻。居洞依山,或聚或散,西至昆仑,东至洋海,海产奇货,故人贪而勇战。春夏多疾疫,利在疾战,不可久师也。
西戎第四十九
西戎之性,勇悍好利,或城居,或野处,米粮少,金贝多,故人勇战斗,难败。自碛石以西,诸戎种繁,地广形险,俗负强很,故人多不臣。当候之以外衅,伺之以内乱,则可破矣。
北狄第五十
北狄居无城郭,随逐水草,势利则南侵,势失则北遁,长山广碛,足以自卫,饥则捕兽饮乳,寒则寝皮服裘,奔走射猎,以杀为务,未可以道德怀之,未可以兵戎服之。汉不与战,其略有三。汉卒且耕且战,故疲而怯;虏但牧猎,故逸而勇。以疲敌逸,以怯敌勇,不相当也,此不可战一也。汉长于步,日驰百里;虏长于骑,日乃倍之,汉逐虏则赍粮负甲而随之,虏逐汉则驱疾骑而运之,运负之势已殊,走逐之形不等,此不可战二也。汉战多步,虏战多骑,争地形之势,则骑疾于步,迟疾势悬,此不可战三也。不得已,则莫若守边。守边之道,拣良将而任之,训锐士而御之,广营田而实之,设烽堠而待之,候其虚而乘之,因其衰而取之,所谓资不费而寇自除矣,人不疲而虏自宽矣。
这里我们看到了著名的对中原邻国的传统分类,通常翻译成英语就是东方的、南方的、西方的和北方的蛮夷(Eastern,Southern,Western and Northern Barbarians)。这些称谓可追溯到先秦时期,但后来它们失去了其特殊性,根据地域分布成为不同的非汉族的通称。其他资料中也有对四个主方位上居民的相似描述,且这些描述通常出现在五行四时的宇宙框架中⑭。在措辞方面,《将苑》描述外族的个别元素似乎在7世纪中期(例如《南史》、《北史》)的编纂历史中能找到根源,其只言片语早在《史记》时就出现。但作为一个系统来看,《将苑》似乎与《通典》的关系最密切,《通典》是8世纪末期杜佑(735—812)编纂的一部大型百科全书⑮。在《边防》一章中,《通典》用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四类来划分唐朝边境以外的领域,和《将苑》结尾的描述相符。在描述诸民族时,只有《通典》将这些通用术语作为一个更为详细精确的框架。从而,西戎被分为四类,包括至少76个民族和国家,从龟兹和楼兰到波斯和印度。西夏的祖先党项也被归为这类。另一方面,北狄的分类较少,但对一些群体(比如匈奴和突厥)有更详细的分析。
《将苑》不同于其来源的是,它是一个关于军事战略的文本,明确地将这些外族视为威胁,并针对如何与他们作战提出了可行的方案。而不久我们就认识到,12世纪末期中国领域周围的四夷和西夏并不直接相关⑯。他们有不同的邻居:南边和西南边是吐蕃,东边和东南边是女真,西边是哈喇契丹⑰,北边是蒙古。到12世纪末,西夏已不再与南宋接壤,那时的南方边境被女真所控制。事实上,从原本《将苑》的角度来看,西夏应该属于西戎的类别,如同党项在《通典》中的情形。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西夏译文中省略了四邻中的三个而只包含了北狄。毕竟对西夏读者来说,像今天云南、贵州地区的南方人这样的“邻居”与他们完全不相关。
在我们开始阅读西夏译文之前,值得指出的是:《将苑》的最后一部分脱离了文本的其余部分,没有讨论战争和将领的理论战略问题,而是解释了四方民族,虽然理想化,但具有描写性。我们所论述的这个部分不仅脱离了文本的主体,而且处于作品的结尾,这增加了其作为附录的可能性,而非文本的一部分。然而元朝末年编纂的《说郛》收入有这四章,并且这是我们所知最早的汉文本。虽然我们没有《说郛》的原本,但存世的明代写本证明了这一点⑱。同时,《说郛》清代早期的印本从顺治三年(1646)就完全省略了这四章⑲。这明显可以解释为:将生活在境外的蛮夷描述为国家的敌人会让满族人感到被侮辱,此时的满族人已成为了中国的统治者。如格林斯蒂德所说:“清王朝的统治者是满族人,也就是北方的非汉人,很可能觉得自己被包括在了通称中。”[8]36景培元[9]1在其对《说郛》的研究中提到,因为有众多冒犯满族祖先的片段,从乾隆(1735—1796)和嘉庆(1796—1821)统治时期开始作品的原型就被禁止⑳。
由于政治的民族敏感性,满族时期也有类似的文本省略情况。叶翰[10]有篇文章专门讨论这个主题,里面举例说明了清代编纂者如何改变和省略了宋本或明本中涉及的蛮夷,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与他们自己的身份有太多共通处。有个例子是《四库全书》版的胡安国《春秋传》,里面所有涉及西戎和北狄蛮夷的都被剔除了[10]。为支撑叶翰的发现,我们还注意到,《四库全书》版的《说郛》也没有四夷的部分㉑。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苑》的最后一部分没有流传于清代。上海图书馆藏有一个稍晚的写本,18世纪的学者沈可培(1737—1799)作的注,其中将这四章合为一章,称为“四夷”㉒。因此,《将苑》其余部分的编排在各版本中相当一致,但这一部分体现了较小的稳定性。尽管肯定没有完全被省略,但西夏文《将苑》提供了这种解释的另一个版本。
清代处理蛮夷敏感问题的另一个例子,见于张鹏翮(1649—1705)的《忠武志》1705年版中保存的《将苑》(题为《心书》)。这里的术语“东夷”写作“东彝”,第二个字被同音的民族名称代替,失去了任何的贬义㉓。而西戎和南蛮的名称在文中保持不变,北狄出现于“北敌”之下。此外,这个版本省略了原文最后一章的大部分内容,这证实了我们对其相对不稳定性的怀疑。
我们还应认识到,对蛮夷的叙述并不一定要理解成字面意思,而是外国人的具体类型的名称。事实并非如此,在另一写本中得到了证明,这个写本年代不明,很可能写于19世纪下半叶㉔。这个小册子的末尾有不同手迹加的注释,用红点作为标点符号,对四夷的描述作了注解:
行间则隙生·衅之以内乱·候其虚而乘之·因其衰而敢之·此审势御外国之最要著也。
其中每个策略都是从四夷的描述中选取的,加进了读者自己的总结。作为针对如何与外国人作战的意见,这个注释极大地反映了清代最后几十年的情形,当时中国逐渐地被迫对抗欧洲列强。显然,西方殖民者不能等同于西戎和东夷,但《将苑》最后一部分的建议如此通用,以至于晚清有爱国情怀的读者可从中找到灵感,想出办法阻止外国侵略。
三、《将苑》的西夏译本
1914年,斯坦因在故城哈拉浩特发现了《将苑》西夏译本的写本,1908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1863—1935)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西夏书籍和写本。
1962年,那时英国国家博物馆斯坦因藏品的管理者格林斯蒂德[11]35首次确认了这个写本为《将苑》的译文。这个写本目前保存在英国国家图书馆(Or.12380/1840),是斯坦因藏品的一部分。当这个写本第一次被带到伦敦时,用格林斯蒂德[11]36的话来说,它仅仅是“一张揉皱的纸”,英国国家博物馆的管理员用一张更厚的纸来托裱。目前它以卷轴的形式保存。遗憾的是,这个写本的下半部分丢失了。出于这个原因,所有的行都是不完整的,底部都缺少几个字符。卷轴的开头也被撕掉了。从写本的章号判断,我们仅有约一半的原文。由卷轴末尾的最后一行可认定前面的内容是《窲疽苾臎臷》(将军森林本)。很可能同一行中最初添加了编者或抄写者的名字,但现在佚失了。题中的汉语词“苑”也有“树林”的意义,这里通常译为英语的garden,西夏文题署证实了文本的标题为《将苑》。西夏文标题并不意味着在同一时期该文本没以其他名字流传,但它提供了证据表明,西夏亡国前汉文本使用的标题是《将苑》。
这个写本年代不明,也没有关于年代的直接线索。克平指出:世俗著作,包括军事文本,通常在12世纪被翻译成西夏文[8]22。她还表示,翻译《将苑》的时间“不早于12世纪下半叶,而是还要晚得多”(出处同上)。此推测一定程度上基于这样的假设:《将苑》结尾描述的骑马的北狄指涉的是蒙古人,他们1205年开始袭击西夏领土[2]206。那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汉文本,因为其中也已出现关于北狄的描述。汉文本也写于蒙古征战前夕吗?乍一看,汉文本《将苑》似乎不可能在几年内写成并被译为西夏文。该文本托名诸葛亮,那它就是专门为了让人们相信这是诸葛亮的作品而写的。一个新伪造的文本似乎不太可能在编成后十年左右,就足够流行以保证翻译成西夏文,还有如此权威的兵法著作《孙子兵法》、《六韬》或《黄石公三略》。此外,虽然蒙古人完美地符合北方骑马好战民族的形象,但大部分北方草原被各种游牧部落占据,他们的生活方式非常相似。当然,这不一定与西夏译文可追溯到13世纪早期的假设相矛盾,但需要更多的证据才能得出明确的结论㉕。
与大多数汉文本一样,西夏译文也由有序的章节组成。同时,他们的顺序与汉文本不一致。而且,汉文本有50章,而西夏文本只有37章,因此有些部分在译文中没有出现。由于译文写本的前半部分缺失,我们只有T20—T37章。除了顺序和编号不同外,西夏文本非常紧密地遵循了汉文本,没有重大偏差㉖。
唯一有明显差异的是汉文本描述四夷的最后四章。更确切地说,西夏译文中省略了汉文本原文中提到的三个族群,所以西夏文本只含有对北狄的描述。西夏译文中这部分出现在T37章。这一章内也包含了汉文本的C46章。也就是说,西夏译文的最后一章(T37)结合了汉原文的C46和C50章,省去了汉文原本的C47、C48和C49章中对三类蛮夷的描述。为了以稍微易懂的方式展示这种相关性,以下是汉文本的最后五章:
C46.威令第四十六
C47.东夷第四十七
C48.南蛮第四十八
C49.西戎第四十九
C50.北狄第五十
其中,只有C46和C50在西夏译文中出现,且合并到T37,标题是“娇築戊灯蒤吨”(威仪三十七第)㉗。这个标题无疑对应汉文本C46的标题,仅第二个字符西夏文用同义的“仪”代替“令”。在这个写本中,前三行半覆盖了C46的内容,其余是C50的译文。
下面,我将过录对应汉文本C50章的西夏本原文,并为每个西夏词语提供汉文对译和汉译㉘。上文关于四夷的最后四章中已呈现了汉文本㉙。这里的汉文对译不是翻译,而是用汉字书写所对应的词。因为我们有两种语言写成的平行文本,所以对于比较两个版本而言,这些对译非常有用㉚。
讨论的这段话是对北狄的描述。它始于西夏文本T37章的第三行半,所以我抄写的第一行是缩进的。文本的前三行大致对应汉文本的C46章,讲述的是一个人如何(即将军或统治者)给他的下级树立榜样,不然他就无异于桀纣等暴君。虽然C46中西夏文本遵循汉文本原文(至少可以根据残缺的行断定),但汉文本的最后三分之一明显被遗漏,反而西夏文本继续紧接着翻译描述北狄蛮族的C50。这一主题的突然转变特别有趣,因为西夏文本忠实地遵循了汉文原文(C1—C46),直到这个地方。然而西夏译文的最后一部分,将被省略的四章(C47—C50)连接在一起,呈现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本。总的来说,汉文本和西夏文本都是高度分段的结构,每章只有几行字的内容。因此有趣的是,整部作品中最明显的断句位于西夏译本的一行中间,且没有标记过渡。
1960年左右,格林斯蒂德[11]开始用聂历山新出版的字典㉛研究西夏写本,他在早期尝试过抄写这个西夏文本的最后一部分,但没有进行翻译。幸运的是,在那之后的五十年里,我们对西夏语言文字的知识不断拓展,让我们不仅对这些文字有了更好的理解,还能做出连贯的翻译。由于带译文的这个卷轴下半部分缺失,所以没有一行是完整的,每一行的末尾都有一些方框,表示该行中缺的字㉜。


这个西夏文本最明显的一个特征,是汉文本原文中的北狄蛮族出现在“草原主”的标记下,西夏文写作“螪 箷”(gjiwˑo),对译汉语的“广主”。英译由克平[8]21提出。格林斯蒂德是第一个描述这个写本的学者,使用了“草原主”这个术语[11]36。虽然这两个术语基本上表达了相同的意思,但我使用了克平的翻译,因为它在这个框架中更符合语境。西夏的术语“螪 箷”(gjiwˑo)中的“螪”(gjiw)可以理解为宽或广,通常用汉字的广或宽来对译。这个词在西夏文字典《文海》54.161中的解释为:“螪落聋綼螪蒜蓒睫八谍端”(宽者地势广也,广也,地利之谓)。这在我们所讨论的文本中,显然指没有树木和山脉的广袤开阔的地形。
克平还依据西夏仪式歌,确定了其他主方位上的族群的三个民族称谓,即“西主”(吐蕃)、“东主”(汉族)和“山主”,“山主”是居住在西夏南部一个族群㊴[8]20。而克平认为,我们所讨论的写本中的“草原主”是“失踪的本语词”,指居住在西夏北方的族群,更可能的是,这些词不是具体的民族称谓,而只是单纯指西夏人眼里的在他们居住地上的族群。我怀疑这些术语的使用,类似于我们在英语中使用“西方人”或“东方人”、“高地人”或“低地人”等词,不需要或不要求在特定的文本中具体到一个实际的种族㊵。其实西夏在向北迁移并开始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其邻族发生好几次改变,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一点,那可能性就很大了。
西夏文《新集金碎掌置文》中出现了类似的术语,对西夏邻族的描述如下㊶:
弥药勇健行,契丹步履缓,羌多敬佛僧,汉皆爱俗文,回鹘饮乳浆,山主嗜荞饼。㊷
最后一行的民族称谓“山主”与术语“草原主” 的形式相符,和克平在仪式歌中确定的其他术语也相符。克恰诺夫[12]158提出了这种可能:这两个字用于表音,来书写一个国家的名字㊸。考虑到上述例子是完全相同的结构,及其在仪式歌中出现的情况,这似乎更可能是具有描述性的西夏本土民族称谓,阅读时应该使用它们的语义值。然而它们指的是什么人仍然是个谜。
上文的《将苑》篇章中,草原主与汉族形成对比,“汉”这个词写作“锡”(),中文通常译成“汉”。这意味着翻译保持了其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与草原主作战的仍是汉人,而不是西夏人。为了让文本真正与本土读者有关,没有试图用西夏去替代汉,表明这个文本不被认为是具体指导如何保卫西夏的手册,而是一部中国军事专著,仅作为一个特定类型的态度和逻辑的例子时,才与西夏有关㊹。
评价该译文质量和目的时,基本问题是考察它有多接近汉文原本。该写本的每一行缺失超过了三分之一(即其下部),这于我们不利,尽管如此,西夏文本显然大体上忠实于原文。虽然不是逐字逐句地严格翻译,但原始材料的内容和目标语言很容易相互校准。在某些情况下,同样的意思可以用相近字数的不同词来表达,但基本上没有太多偏差。唯一例外的是汉文本的最后部分的一章(C50),这一章提出了如何对付北狄的具体解决方案(即“选用一个好将军”等)。译文(T37)省略了其大部分内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该写本的结尾是完整的,表明文本在这里就结束了。就内容来看,似乎没有明显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对西夏读者来说丢失的文本没有必要,但这部分在所有现存汉文本中都有,所以它很可能也是译者使用的版本的一部分㊹5。至于为什么最后一部分在西夏译文中被删,虽然我们怀疑是技术原因而不是意识形态原因,但目前还不能解释。
四、结 论
尽管在中国文献学传统的主流中相对被忽视,但诸葛亮的《将苑》仍是夏译汉籍之一。夏译本是《将苑》现已知最早的版本,比其他版本早了近两个世纪。译文中有趣的是《将苑》最后描述四夷的四章。我们已经看出,尽管译者保留了原文的中国中心观,但排除了四夷中的三个,仅留下了北狄。他称这个骑马的族群为“草原主”,这个名称可能是指蒙古人,13世纪初他们在西夏北部建立了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这种身份认定对翻译的年代判定有重要影响。没有明确的线索来确定该写本的年代,但在北方边境可能被蒙古威胁,意味着西夏文本的年代是13世纪早期,这在某种程度上有悖于我们所知的大多数世俗著作翻译于12世纪。但是“草原主”同样可以指契丹或女真,这样的身份认定表明年代更早。此外,对北狄的描述来自汉原文,这显然早于蒙古时期,更不用说这些人的刻板特征,这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代。虽然蒙古的确也是一个好战的北方骑马民族,但纵观中国历史,一直占据着北方大草原的游牧族群过着类似的生活方式。“草原主”一词的描述性质也表明,西夏人用这个词并不涉及一个特定的种族,而是当作北方游牧族群的总称。
至于为何翻译中省略了描述其他三类蛮夷的章节,似乎是因为在原来的四夷分类中,这是唯一符合西夏人世界观的族群。辽国和后来的金国地理位置相符,但也不会被称为东夷,因为西夏本身曾一度处于从属地位,充当它们的附属。但最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占领了领土,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领土一直是中国文化领域的中心,实际上继承了这个传统。同样地,宋在被女真逼到更南边之前,与西夏相邻,既不属于东夷也不属于南蛮。再者,从夏的角度来看,南部和西南部的吐蕃不是“蛮夷”,而是一个与西夏共享文化遗产重要部分的文明。西夏对其邻国的文化依赖和亏欠还表现在,除了西夏语,藏语和汉语都被广泛使用,也被官方承认。这不仅说明西夏是多民族融合,而且说明其最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联系。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这些国家之间具有共同的佛教背景,碍于此它们也不应被称为“蛮夷”。
因此,汉文本《将苑》四类典型的蛮夷中,只有“草原主”不能与一些庙堂文化形式和共同的宗教传统联系起来。这是四类中唯一符合西夏地理的群体,西夏地理中心本身就从原来的中心移到了西北,形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地理布局。相应地很容易将蒙古视为西夏最大的威胁,只有回顾历史时才明显,然而当时女真也和西夏交战,可能将女真视为了一个更强大的军事挑战。
(译自Imre GALAMBOS,The northern neighbors of the Tangut,Cahiers de Linguistique-Asie Orientale40(1)(2011):73-108.)
注释:
①感谢萨姆?范?谢克(Sam van Schaik,国际敦煌项目,英国国家图书馆),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s,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东亚语言学报》的编辑齐卡佳(Katia C hirkova)和柯理思(C hristine Lamarre),以及两位匿名评论者提供有帮助的评论和建议。特别感谢李孟涛(Matthias Richter,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对初稿的细致阅读。同时感谢英国国家图书馆国际敦煌项目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雷切尔?罗伯茨(Rachel Roberts),为研究这个写本提供了高分辨率的图像。感谢黄君榑对译稿提供建议。
②本文的西夏音标根据李范文的字典(《夏汉字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收录。除了语音,大多数情况下用汉字注释西夏词语,虽然这些字既不是翻译也不是转写,但在平行文本中对应,因此,省略了汉语注释的发音和意义。使用的缩写和凡例如下:C=文本的汉原文,T=文本的西夏译文。转写中方括号内的文字表示这些字不见于写本,但能根据上下文可靠地重建。方框表示字符缺失。在西夏文本的汉译中,三角形(△)用来标示没有直接可对应的汉文的语法词。由一个字以上组成的复合词,西夏文和汉文都有下画线,表示它们属于一个整体。
③仅列出其中一些例子,姚际恒(1647-1715)在他的《古今伪书考》里简要声明这本书“诸葛亮撰,伪也”[13]4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〇〇《子部》一〇:“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而明代之后伪造的,归于14世纪的军事战略家刘基(1311-1375)。清代学者谭献(1832-1901)称它是一个抄袭其他文献言论的集子[14]809。
④有关西夏史料文献的概述,参见克恰诺夫[1]5-10。
⑤此外,西夏自身的种族并不一致,而是由多个可能说着不同西夏方言的部族组成。参见西田[6]246,n.2。
⑥关于西夏灭亡的历史,参见克恰诺夫[1]298-330和邓如萍[2]205-214。
⑦为阐述这个概念附带说一下,西田引用了两部汉文兵书的译文:《六韬》和《黄石公三略》,都是来自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的藏品。
⑧克平[8]19-20对本文所讨论的《将苑》提出了更有力的观点,认为它是为西夏读者的“改编”。
⑨与《将苑》类似,小说《三国演义》流传至今的最重要的早期版本之一也是译本。这是小说印于1650年的满语本,早于四书五经的满语译本[15]87-90。小说和其他文学文本的满语译文,也参见杜润特(Durrant)[16]和吉姆(Gimm)[17]。
⑩关于他人生的详情,参见张磊夫(C respigny)[18]1172-1173。
⑪遗憾的是,序的年代不容我们把《将苑》追溯到这一时期,因为流传下来的各本《说郛》都来自16世纪。由于其庞大的规模和复杂的文本历史,我们根本不能确定《将苑》是否在其中。
⑫唯一的例外是C3这一章,在多数版本中其标题由三个字组成:“知人性”。
⑬汉文本来自《诸葛亮集》(1960),是《诸葛忠武侯文集》张澍(1781-1847)版的句读版。因为该版本没有段落编号,为了方便,我在中英文版中添加了它们在明代本中出现的方式(例如:东夷→东夷第四十七)。
⑭例如:我们在汉代医学著作《黄帝内经素问》第十二篇中,看到了类似的对世界主要方位和其居民的描述:“中央者,其地平以湿,天地所以生万物也,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
⑮ 801年《通典》正式呈现给君主,虽然在此之前杜佑已为之工作了30年以上,并在812年去世前做了细微调整(参见崔瑞德(T w it ch ett)[19]106-107)。虽然我们知道《通典》的很多内容有更早的出处,包括现已佚失的8世纪学者刘秩所撰的《政典》,但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中国邻国章节的主要来源。
⑯可以说,这种对相邻蛮夷部族威胁中央统一领域的描述,也没反映公元3世纪诸葛亮生活时中国的政治状况。
⑰哈喇契丹人是契丹人的后代,契丹人在女真征服辽后逃离家园,在中亚建立了西辽王朝(1124-1218)。
⑱关于《说郛》最早版本的比较,参见陶[20]。
⑲这是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份复本,文本在第46章之后直接结束。
⑳关于用西方语言对《说郛》复杂系统的大量著录研究,参见伯希和[21]。
㉑同时,《将苑》对蛮夷的描述,在明代百科全书《图书编》(1613)中被大段引用。百科全书引用了南蛮、西戎和北狄章节的全文,相互分开并插入到他们自己对中国邻国的分类中;然而它省略了《东夷》的一章,毫无疑问,因为它不适合对这些人更详细地阐述。然而《四库全书》中出现了其他三章的全文,表明对涉及戎狄内容的审查要么不够全面,要么不够彻底。
㉒《心书校注一卷》,上海图书馆,善本部,索书号:802672-79。这是一个简洁的版本,文本不到一半并且没有章节号。难以知道是沈可培仅想对这些部分发表评论而省略了文本的其余部分,还是他着手的已经是一个同样编排的较早版本。
㉓文本中这种文字的替换,强烈地让人想到君主名字的避讳。
㉔《新书不分卷》,上海图书馆,善本部,索书号:863710。该写本年代不明,但在第20页的顶部空白处用满语写了注释。此外,印有所有者的印章“三将军后人”。图书馆的目录说这是晚清的复本,这可能是基于获得它的情况,虽然目录本身没有提及任何这方面的信息。这样一个事实也支撑19世纪的年代认定,那就是这个版本在措辞和行文特征上比起更早的版本,更接近于张澍的版本。
㉕当然,除非这是译者的复本,不然原稿的日期要晚于译文的日期。
㉖克平和龚煌城[8]23还认为,该文本是一种改编,而不是逐字的翻译。然而,我自己对这两个版本的比较并没有证实这个假设(参见高奕睿[22])。
㉗西夏文标题的最后一个字(即“吨”tsəu[第])在写本中佚失,但有信心重构出来。它产生序数词的后缀,其他标题中经常出现。
㉘译者注:原文为英译,本译文转换成汉译。
㉙译者注:本译文省略汉文本的英译。
㉚一些学者(如克平[7])倾向于避免使用这样的汉文对译,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远离原文的额外步骤,而另一些研究人员(如向柏霖[23])使用对译,因为它们有助于理解西夏译文和汉原文的关系。
㉛这本词典是聂历山(1892-1937)不朽的两卷著作的一部分,该著作在他去世后出版,彻底改变了西夏语的研究(聂历山[24])。
㉜据本人估计,最初的一行有20个字的长度(参见高奕睿[22])。
㉝这里汉文本和西夏文本有所不同。汉文本只是说,当草原主强大时,他们就会入侵南方。西夏文本说,他们来破坏中国领土。
㉞这一行中,“切穋”(dzǐʥë,粮食)的第一个字在写本中写为“钦”(lıe,香),产生了这个尴尬的、未经证实的组合“钦穋”(lıeʥë,香粮)。因此这很可能是讹误,本意为更常见的词“切穋”(dzǐʥë,粮食)。感谢本文的一位匿名审稿人注意到这一点。
㉟译者按:形,当对译作“顺”,西夏文“槽”有“顺”义,《掌中珠》(20.B.02)“孝顺父母”的“顺”即用该字对译,“糣槽”,与汉文本“顺风”正对应。
㊱这里的短语“糣槽”lɕiε(~风形)翻译成“环境优势”是有疑问的。汉文本此处所对应的是地形,意为地形特征或优势。西夏文用“风”代替“地形”,大概是指自然环境的特征。
㊲写本中“婚蔰”(khiu wu,保守)的字符顺序相反,但编者或抄写者自己在两个字符间加有校改符号,是现代对钩的形状,表明这两个字应该颠倒。在这里我以校改符号所示的正确顺序抄录它们。
㊳由于在始于新一行的末页之前,这是文本的最后一行,所以不确定原文有多少字。因此,我只放了一个方框来表示写本上部分可见的字符。
㊴遗憾的是,克平并没有详细说明她指的是什么仪式歌,我也无法亲自考察它们的内容。因此,我只能依据克平的讨论。总的来说,正如一位外部审稿人所指出的,圣彼得堡语料库中唯一的仪式文本是法庭颂歌(见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1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㊵可以说,此时的汉语词中的四夷(西戎、北狄等)也失去了其特殊性,因而不再被用作民族称谓。同时,在汉语中这些术语不是描述性的,仅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此外,正如在汉文本《将苑》中出现的那样,这些术语每个也有其特定内涵或与之相关的刻板印象。
㊶有关本文的描述和翻译,参见克恰诺夫[25]。
㊷我主要采用了克恰诺夫的俄译[12]157。克恰诺夫的翻译前四行依次取自聂历山[24]81,1。
㊸更准确地说,克恰诺夫认为这可能是罗布泊地区的古王国鄯善,但这可能纯粹基于语音理由。
㊹关于战略作品(《素书》、《黄石公三略》和《六韬》)翻译为满语,杜润特[16]654-655指出,这些几乎没提供明确的具体战争策略知识。相反,他认为这是出于这些文本的表面作者的利益,正如他们都“与一个崛起的势力征服的前夕有关,奉天统治者可能在他们那获得了特有的利益,那时希望类比早期征服前的势力和他们自己。”
㊺例外的是清代本的《说郛》,其中关于四夷的整个部分都被省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