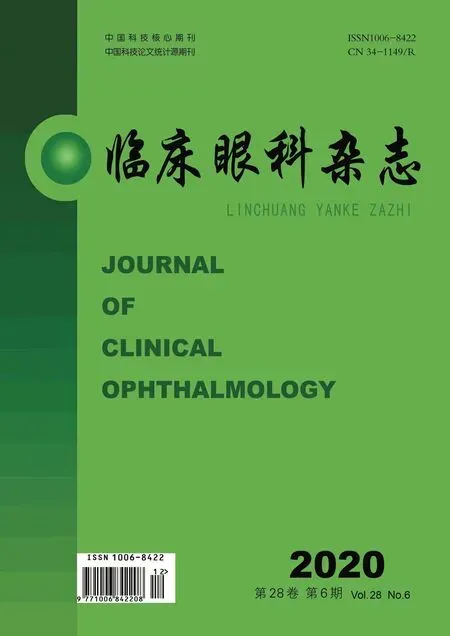早期2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患者周围神经传导速度与内层视网膜厚度的相关性研究
赵芹 张昊志 代艳
糖尿病是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最常见的慢性疾病,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iabetic retinopathy,DR)是其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在全球范围内,至2030年预计患有DR的人数将从2010年的1.266亿增长至1.91亿[1]。在糖尿病患者中,有研究报道视网膜神经胶质功能障碍发生于DR之前[2],并发现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是最早受影响的细胞,凋亡率最高[3,4],在1型[5]和2型[6]糖尿病患者[无糖尿病视网膜病变(non-diabetic retinopathy,NDR)或非增生型糖尿病视网膜病变(non-prolifertive diabetic retinopathy,NPDR)]中,由于视网膜神经纤维层(retinal nerve fiber layer,RNFL)、神经节层(ganglion cell layer,GCL)及内核层(inner nuclear layer,IPL)的选择性丢失致内层视网膜变薄已得到证实,现可通过相干光层析成像术(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OCT)对视网膜内各层厚度进行评估。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diabetic peripheral neuropathy,DPN)是糖尿病最常见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也是导致足溃疡、感染及坏疽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是一组以感觉神经及自主神经损害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周围神经病变,与糖尿病肾病和DR共同构成糖尿病三联征。研究报道早在糖尿病糖耐量受损时期,便可发生DPN[7,8],而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神经元死亡之前可出现突触丢失、轴突串珠样等神经变性改变[9],故认为两者具有相似的病理改变,临床上糖尿病周围神经损伤可通过周围神经传导速度测定进行客观评估。故本研究旨在通过HD-OCT测定早期2型DR患者内层视网膜厚度改变,探讨早期2型糖尿病DR患者周围神经传导速度与内层视网膜厚度的相关性,从而为DR的早期识别提供新的临床诊疗思路。
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选择2019年4~10月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就诊的糖尿病患者81例(81只眼),所有患者均明确诊断为2型糖尿病,接受药物或胰岛素治疗。所有患者排除相关禁忌证后于眼科门诊行眼底荧光造影检查,按照2002年国际分期标准,将无DR和轻度NPDR患者(轻度或中度非增生型DR)纳入研究,所有人员等效球镜度数均在+3.00 D~-6.00 D内。排除标准:(1)屈光介质严重混浊者(角膜瘢痕、严重白内障等);(2)既往患有青光眼、高眼压症、葡萄膜炎、玻璃体积血、视网膜血管疾病、视神经疾病、视网膜脱离等;(3)曾行视网膜激光治疗、玻璃体内药物注射或其他眼部手术;(4)除糖尿病相关神经病变外的其他周围神经病变(患有严重脊椎病、脊髓创伤、神经肌肉疾病及遗传代谢疾病等)。所有患者在接受周围神经传导速度测定前未接受过任何影响神经传导速度药物治疗(如异烟肼、呋喃唑酮)。所有患者在了解本研究的目的后,均同意行相关检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本研究获得绵阳市中心医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符合赫尔辛基宣言伦理标准。
二、一般检查
记录所有患者糖尿病病程、糖化血红蛋白(HbA1c)、胆固醇(TG)、甘油三酯(TC)、低密度脂蛋白(LDL-C)、肾小球滤过率(GFR)、肌酐、尿素、同型半胱氨酸(Hcy)、尿微量白蛋白及颈动脉内-中膜厚度(intimal medial thickness,IMT)。
三、眼科检查
所有患者均进行最佳矫正视力(best corrected visual acuity,BCVA)、眼压、裂隙灯检查,在满足排除标准前提下选择视力较低眼进行分析。 使用Cirrus HD-OCT (Carl Zeiss,Meditec, Inc, Dublin, OH, USA)行视网膜厚度测定:所有患者均由一名经验丰富眼科医师进行检查和最终图像获得。在散瞳下被要求直视检查探头中的固视点,选择Cirrus macular cube 512×128模式对黄斑中心凹进行高密度扫描,自动识别黄斑RNFL边界,以及IPL内界,RNFL边界及IPL内界为GCL-IPL,内置算法自动测量平均GCL-IPL厚度、最小GCL-IPL及6个部位(鼻侧、鼻上、鼻下、颞侧、颞上、颞下)GCL-IPL厚度,最终取平均GCL-IPL厚度。采用Optic Disc cube 200×200模式对视乳头进行高密度扫描,自动测量视乳头RNFL厚度(包括鼻侧、鼻上、鼻下、颞侧、颞上、颞下),最终取平均视乳头RNFL厚度。
四、周围神经传导速度测定
使用美国Viking Quest肌电图仪行周围神经传导速度(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NCV)检测。每位受试者均行正中神经、腓总神经、胫神经及腓肠神经检测。检查者在清醒状态下,于无干扰、安静的室内平卧,室温保持在22~24 ℃之间,表皮温度维持在32 ℃以上,使用表面电极记录感觉及运动神经传导速度。
五、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根据 K-S 检验,对符合正态分布的参数使用均数±标准差表示,NDR和轻度NPDR组间差异使用成组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对不符合正态分布的参数用中位数(四分位间距)表示,组间差异采用Mann-WhitneyU检验进行比较。采用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周围神经传导速度与内层视网膜厚度的关系,Logistic 回归分析进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危险因素评估。P<0.05为差异具有显著性。
结 果
一、一般情况及两组基线资料比较
本研究共纳入81例2型糖尿病患者(男性46例,女性35例)。根据t检验分析结果,年龄、病程、HbA1c、尿素、肌酐、TG、TC、LDI-C、尿微量白蛋白及IMT两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然而与NDR组相比,轻度NPDR组收缩压且肾小球率过滤更低(P=0.002;P=0.048),轻度NPDR组与NDR组相比,正中感觉神经传导速度(sensory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SCV)、腓总运动神经传导速度(motor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MCV)、腓肠SCV及黄斑区平均GCL-IPL厚度均明显降低,差异有显著意义(P<0.001)。此外,与NDR组相比,轻度NPDR组胫MCV、视乳头平均RNFL厚度均降低(P=0,012;P=0.012)。见表1。

表1 NDR组与轻度NPDR组基线临床资料
二、Pearson相关性分析结果
正中SCV、腓总MCV、腓肠SCV与黄斑平均GCL-IPL厚度呈正相关(r=0.428,r=0.386,r=0.434;均P<0.001)。DR危险因素分析,纳入本研究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并结合临床有意义的危险因素为候选变量,所有候选变量先进行单因素分析(见表2),为保证重要因素不被漏掉,对单因素分析P值较小者(P<0.2)的候选因素采用向前逐步回归法开展多因素分析。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腓肠SCV(OR=1.03,95%CI:0.78~3.13,P=0.011,B=-0.143,Walds=6.54)及黄斑区平均GCL-IPL厚度(OR=1.05,95%CI0.76~0.91,P=0.003,B=-0.176,Walds=14.41)是2型糖尿病患者DR的独立危险因素。

表2 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轻度NPDR独立相关危险因素
讨 论
DR是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严重影响糖尿病患者的生活质量。既往对DR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血管功能障碍方面,如内皮细胞受损、周细胞凋亡、视网膜毛细血管基底膜增厚和紧密连接等改变,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在眼底出现微血管病变之前,体内多元醇、己酰胺及蛋白激酶C(protein kinase C,PKC)等多条代谢途径被激活致氧自由基等高活性分子产生增多,诱导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紊乱及神经营养因子减少等改变致神经细胞损害,表现为神经元凋亡、轴突变性、胶质细胞激活及反应性增生等变化[10],而神经元细胞的存活情况可通过OCT技术表现为相应视网膜厚度变薄或增厚。另一方面,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主要由氧化应激、代谢紊乱及神经营养因子减少等共同因素作用而成,致周围神经纤维发生脱髓鞘及变性改变,通过电生理检查表现为神经传导速度减慢。了解到糖尿病视网膜神经变性与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可能存在相似的病理改变,本文欲通过OCT测定内层视网膜厚度及电生理检查测定周围神经传导速度,探讨两者是否有相关性,以推测通过周围神经传导速度变化是否能对早期DR的识别起一定的临床辅助作用。
本研究发现,正中SCV、腓总MCV及腓肠SCV与黄斑平均GCL-IPL厚度均呈显著正相关,这一结果与Kim等[11]研究相似。研究表明早在糖尿病糖耐量受损时期便可出现周围神经轴突变性及脱髓鞘等改变[7,8],此外研究证明糖尿病患者在眼底出现微血管病变之前就已发生视网膜内神经退行性改变[12],这从分子机制上可理解早期DR患者周围神经传导速降低的同时可发生黄斑平均GCL-IPL厚度变薄。Azusa等[13]研究发现早期DR患者周围神经传导速度与脉络膜厚度相关,认为可能的原因是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受损时往往伴随着自主神经功能受损,而脉络膜内平滑肌受自主神经系统支配故可受到一定的影响。此外研究表明自主神经系统还可直接影响眼部视神经、睫状体及虹膜的血流,且视网膜微循环也可间接受到影响[14]。由此我们可推测GCL-IPL厚度降低的原因除氧化应激、线粒体功能紊乱等改变直接致神经细胞损害之外,还可能是由于糖尿病患者自主神经系统受损影响视网膜微循环,表层微血管灌注降低从而使神经节细胞缺血变性,由此可进一步增加本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HbA1c及糖尿病病程等因素常被认为是DR发生的危险因素,但本研究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分析未得出以上结论,而黄斑GCL-IPL厚度及腓肠SCV是DR发生的危险因素。研究表明糖尿病患者在未发生DR时,已出现视网膜内神经退行性改变[12],且糖尿病视网膜神经元凋亡机制与神经节细胞特征性丧失有关[15],此外大量研究报道在无或者轻度NPDR糖尿病患者中,普遍已发生神经节细胞层变薄[16-19],这表明神经节细胞层厚度可在一定程度反映DR的发生及进展。Sasaki等[20]对糖尿病患者周围神经功能分析发现,周围神经传导速度降低与DR的发生相关,且Morimoto等[21]进一步证明了正中MCV及SCV与DR的进展相关,且正中MCV随着DR的进展显著降低。与既往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本研究分析显示腓肠SCV与2型糖尿病患者DR的发生相关。可能是因为DPN存在“长度依赖机制”,即病变呈逆向性改变,表现为远端轴突变性较重而近端相对较轻,下肢周围神经因行程更长故更易受到损害,并且临床上DPN患者最常见且最早的临床症状为感觉异常,尤其是下肢感觉异常,故可更好的解释为何在周围神经中腓肠感觉神经纤维传导速度最先出现异常。
本研究还发现与NDR组相比,轻度NPDR组收缩压显著篇偏高,这与既往研究结果[22]较一致,血压增高可使视网膜高灌注致毛细血管内皮受到损害,从而促进DR的发生及进展;同时我们还发现轻度NPDR组肾小球滤过率(GFR)较NDR组普遍偏低,但微量白蛋白尿浓度无明显差异,可能与24 h尿液采用标本易受存储温度或时间影响有关,且研究表明4%DR患者同时合并糖尿病肾病[23],而超过30%的糖尿病肾病患者合并有DR[24],这提示我们2型糖尿病患者若已出现GFR值下降,应早期行眼底检查,同时应严格控制血压。
考虑到年龄因素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干扰,故本研究将纳入患者的年龄控制于55~75岁之间,这可减少因年龄因素对黄斑区GCL-IPL厚度产生影响[25];此外Li等[26]和Karti等[27]研究表明血糖控制较差所致的长期慢性高血糖是影响黄斑区GCL-IPL厚度的危险因素,但年龄及HbA1c与黄斑区GCL-IPL厚度关联程度不明确。本研究NDR组及轻度NPDR组HbA1c相比无显著差异,可排除HbA1c可能对黄斑区GCL-IPL厚度造成的影响。考虑疾病变化可能对神经电生理检查指标有所影响,故本研究仅搜集6个月内符合纳入标准的糖尿病患者相关数据,因此存在样本量较小的缺点。
DR作为一种潜在的致盲性疾病,合格的临床眼科医生不仅需要对糖尿病眼部疾病做出及时识别及有效干预,更需注重全身其他临床改变。在本研究中,正中SCV、腓总MCV、腓肠SCV与黄斑区平均GCL-IPL厚度均呈显著正相关,且腓肠SCV及黄斑区平均GCL-IPL厚度是DR发生的危险因素,因此结合周围神经传导速度特别是腓肠SCV的变化及临床改变,可能作为DR早期诊断及病情监测的有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