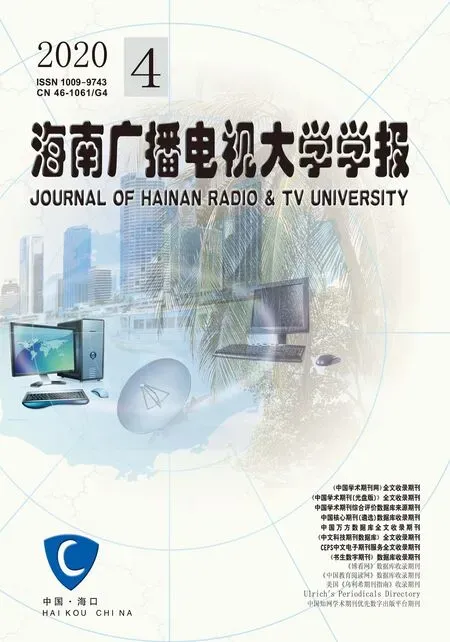龙绡潜织碧月下 珠泪遗泣青冥中
——唐诗鲛人意象探微
程润峰
(华中师范大学 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鲛人,亦作蛟人,又名人鱼、泉客和渊客等,是一种半鱼半人的神话生物。其普遍存在于各民族神话系统和文学叙事之中。目前对鲛人/人鱼的研究共有三种取向:一是原型考论,如陶思炎(2009)认为人鱼的诸多特征是对孟姜女形象的想象性映射[1];二是中西比较,如黄雪敏(2009)指出中西人鱼的共性是作为“爱欲—死亡”主题的载体,差异则是中国鲛人多以喜剧表现,浓重的伦理色彩柔化了矛盾,而西方人鱼却多以悲剧表现,爱欲和死亡的冲突更为纯粹[2];三是本土文学的系统阐释,如倪浓水(2008)揭示出人鱼叙事在中国古代海洋小说中的变形以及人鱼形象的文化蕴涵[3]。
本文即属于第三种取向。一方面,前人已对中国古代小说中的鲛人叙事进行了详细探讨,但古诗中的鲛人意象尚未有人予以系统梳理;另一方面,相较于宋诗,唐诗素以“丰腴华美”著称。大唐王朝的繁荣造就了诗歌意象表达的成熟,使其呈现出兴象玲珑、汪洋恣肆的总体风貌。唐诗的浪漫性也与鲛人的神秘性遥相呼应,形成某种互文性的对照和映衬。而这正是本文选择唐诗作为研究底本的题中之义。
藉由唐诗中“鲛人”意象及其表述,我们得以领略唐诗的艺术魅力和唐人的生活面貌,进而管窥中国古代诗人对海洋神话的接受、继承和创造,以及由此衍绎出的富有浪漫想象的情怀和哲思。
一、“鲛人”形象的滥觞与嬗变
源究鲛人早期形态的叙写,应是先秦神话《山海经·海内北经》中关于人鱼原型的建构:“陵鱼人面,手足,鱼身,在海中(1)(东晋)郭璞注:《山海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09页。。”此处的“陵鱼”,以及《海内南经》的“鲛人”、《大荒西经》的“鱼妇”,还有《山经》中多次提及的“人鱼”,都可以看作原始先民对鲵鱼的某种纪实性描述,并且带有一定生殖崇拜色彩,这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文学式反映,也在后世的鲛人形象不断风情化的文学事实里得到显影。另外,先民对人和鱼的夸张性联想与组合,以及鲛人身上日益加重的人伦色彩,亦为“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海洋生物书写的缩影式体现。
《楚辞·天问》中有一句“鲮鱼何所?鬿堆焉处?(2)(战国)屈原等:《楚辞》,太原: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学界曾对此处的“鲮鱼”争论不休,实际上柳河东早在《天对》中给出了答案:“鲮鱼人貌,迩列姑射(3)侯外庐等编:《柳宗元哲学选集》,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33页。。”鲮鱼就是人面鱼身的陵鱼,屈原沿袭了《山海经》中关于鲛人的称谓。
曹植《七启》云:“然后采菱华,擢水蘋,弄珠蚌,戏鲛人(4)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页。。”这是人鱼形象继《山海经》后,首次以“鲛人”之名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而这也是其替代“陵鱼”和“人鱼”,逐渐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意象的开始。
“鲛人”叙事构建的真正的启动则要追溯于两晋的时期。西晋张华《博物志》曰:“鲛人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绢。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5)(北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第3567页。”东晋干宝《搜神记》卷12亦云:“南海之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泣则能出珠。(6)(东晋)干宝:《搜神记》,长沙:岳麓书社2015年版,第115页。”此两则将“鲛人”从一种冰冷的对某种怪鱼的模糊性的指称成功塑型成一种有血有肉的生命形象,既交待其来龙去脉,“从水出”“南海之外有鲛人”;又勾勒其形容轮廓和生活习性,“水居如鱼”“不废织绩”“眼泣则能出珠”;还赋予其生动灵现的故事背景和某种人格化的行为举止,“寓人家,积日卖绢”“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则进一步丰富了“鲛人”的背景和形象:“南海出鲛绡纱,泉先(即鲛人)潜织。一名龙纱,其价百余金。以为服,入水不濡(7)温广义:《唐宋词常用词辞典》,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2页。。”唐诗宋词里常见的“鲛绡”意象也就诞生于此处,并逐渐演化为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蕴的话语符号[1]。由此,“鲛人”与“南海”“龙纱”“潜织鲛绡”和“泣泪成珠”等文学符号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典故系统,成为后世鲛人书写的题材来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述三书中的“鲛人”才是唐诗中鲛人意象的真正前身。这一时期,随着鲛人神话的真正定型,“鲛人”不仅正式遨游于文学的“海洋”,比如西晋左思《吴都赋》中的“泉室潜织而卷绡,渊客慷慨而泣珠(8)(清)严可均辑:《全晋文(中)》,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81页。”“想萍实之复形,访灵夔于鲛人(9)(清)严可均辑:《全晋文(中)》,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84页。”。也开始以意象形式出现在诗歌的创作之中,并逐渐在诗人的笔端流光溢彩、熠熠生辉。比如,南朝诗人刘孝威的《小临海》中,就有“蜃气远生楼,鲛人近潜织”一句。这首几乎囊括了先秦以降、隋唐以前所有的与海洋相关的神话传说的诗作中,也自然不能缺席鲛人的丽影[4]。
而要论及中国古代文学中人鱼叙述最为成功之作,则要首推清代戏曲作家沈起凤《谐铎》卷7中的一则故事《鲛奴》,它以相对完整的叙事架构,以及相对丰富的情节书写,在继承性叙事基础上将人鱼进一步人格化,成功塑造和刻画了一个知恩图报、善解人意的“鲛奴”形象。故事开始于穷书生景生航归故里的途中,他在岸边遇见一位因被龙宫驱逐而漂泊无依的鲛人,将其收留并带回家中。后来景生向心仪的陶万珠求亲时,却被其母索要“万颗明珠”的聘礼。鲛奴不忍目睹景生相思成疾,于是“抚床大哭,泪流满地。俯视之,晶光跳掷,粒粒盘中如意珠也(10)薛洪勣:《明清文言小说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95页。”,成功帮助景生集齐万珠,随后便纵身赴海,返乡南冥。
由此观之,先秦时期是鲛人雏形的孕育期,它建立在先民对鲵鱼等生物的朴素认识和对生殖崇拜的原始情愫之上,缺乏相应的叙事逻辑和连贯的结构原型。汉魏六朝则是鲛人形象的确立期,一方面开始拥有生动完整的故事背景和某种人格化的内在属性,另一方面也开始从文化形象到诗歌意象的转化。之后鲛人形象不断丰满,并于清代臻至人鱼叙事高峰。
二、唐诗中的“鲛人”意象
意象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审美范畴,是“象中之意”和“表意之象”的水乳交融[5]。其进入文学创作领域,始于南朝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11)(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页。”。由此,以意象经营为主的诗歌艺术开始在中国古典文学里大放异彩,并呈现出独特的东方美学。
本文以《全唐诗》为底本,辅以北京大学中文系研制的全唐诗分析系统的工具检索,对相关诗作进行筛选与甄别,一方面剔除自成一体的“鲛绡”意象,例如李节度姬《书红绡帕》中的“囊裹真香谁见窃,鲛绡滴泪染成红”;另一方面把有些借“鲛人”来代指海滨居民的诗歌也不纳入意象讨论的研究范围,例如刘禹锡《莫猺歌》中的“市易杂鲛人,婚姻通木客”。最终选择38首含有鲛人意象的唐诗作为样本,相关作品统计结果如表所示:

序号诗人关键词篇名1李峤鲛人《太平公主山亭侍宴应制》2李显泉客《石淙·太子时作》3孟浩然鲛人《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4李颀鲛人《鲛人歌》5储光羲鲛人《采莲词》6杜甫鲛馆《雨》

7杜甫泉客《客从》8杜甫鲛人《雨四首》9杜甫鲛人《渼陂西南台》10杜甫鲛人《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11岑参鲛人《送杨瑗尉南海》12顾况鲛人《龙宫操》13顾况鲛人《送从兄使新罗》14卢纶鲛人《慈恩寺石磬歌》15刘商蛟人《姑苏怀古送秀才下第归江南》16李绅鲛鱼《涉沅潇》17李绅鲛人《登禹庙回降雪五言二十韵》18刘禹锡鲛人《伤秦姝行》19刘禹锡泉客《武陵书怀五十韵》20刘禹锡鲛人《韩十八侍御见示岳阳楼别窦司直诗因令属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韵》21施肩吾泉客《贫客吟》22施肩吾蛟人《酬周秀才》23长孙佐辅鲛室《楚州盐壒古墙望海》24张署鲛人《赠韩退之》25鲍溶鲛人《采葛行》26李群玉泉客《病起别主人》27方干鲛人《题故人废宅二首》28李商隐珠有泪《锦瑟》29李商隐泉客《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30李商隐河鲛《奉同诸公题河中任中丞新创河亭四韵之作》31顾云鲛人《苔歌》32吴融鲛人《赠李长史歌》33齐己鲛人《还人卷》34殷文圭鲛客《边将别》35康翊仁灵鲛《鲛人潜织》36成彦雄鲛人《露》37无名氏蛟人《斑竹簟》38无名氏鲛人《天竺国胡僧水晶念珠》
诗人方面,有不少作者都创作过不止一首的涉鲛诗歌,其中杜甫以5首的数量居最,其次是刘禹锡和李商隐都以3首的数量紧随其后。关键词分布方面,“鲛人”得到最为广泛的运用,而“泉客”也受到部分诗人喜爱。内容题材方面,大致可以分为4类,有以南海鲛人及其相关奇闻为直接书写对象的诗作,例如李颀的《鲛人歌》和康翊仁的《鲛人潜织》;有借茕居南海的典故来烘托人物、抒怀言志的诗作,例如李绅的《涉沅潇》;也有借泣泪成珠的典故来抒发情感、表达思想的诗作,例如吴融的《赠李长史歌》;还有借鲛人织绡的典故来营设意境、映现情思的诗作,例如刘禹锡的《伤秦姝行》。从初唐到晚唐,鲛人就像一缕忽远忽近的魅影,无时无刻不在拨弄诗人的心弦,哀感顽艳之际,挥笔写下一篇篇诗作,仿若溟濛飘渺的海雾里,鸣奏出美妙绝伦的乐歌。
三、“鲛人”意象的文化意蕴解读
(一)方外想象和幻魅猎奇
如果粗略地把古人眼中的世界一分为二,大致可以划为方内和方外两地,前者对应凡尘俗世,后者则代指世外玄境或者修行之人居住的洞天福地。《楚辞·远游》曰:“览方外之荒忽兮,沛罔象而自浮。(12)(战国)屈原:《楚辞》,长春:吉林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5页。”古人经常把“方外之地”想象为浩瀚幽茫的汪洋深海。因此,往来于海洋和人世之间的鲛人,也就自然地被寄寓了某种对“方外”的遐思。李颀的《鲛人歌》就将这种遐思书写得淋漓尽致,全诗为:
鲛人潜织水底居,侧身上下随游鱼。轻绡文彩不可识,夜夜澄波连月色。有时寄宿来城市,海岛青冥无极已。泣珠报恩君莫辞,今年相见明年期。始知万族无不有,百尺深泉架户牖。鸟没空山谁复望,一望云涛堪白首。
前四联诗人在继承《博物志》中的鲛人叙事基础上,用如画的语言对原典进行了创造性解读,并生动地描绘出鲛人所居的境域:游鱼穿梭在南冥水底,一轮明月挂在青苍悠茫的天空,洒落下皎洁清亮的月光,映照在澄碧荡漾的波浪。后两联则是诗人读罢故事后的有感而发:世界之大,族类繁多,无奇不有,鲛人也许本就真实地存在,在泓澈的深泉和浩淼的波涛之中建造屋舍,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但转念一想,鲛人就如同隐没于一片深山里的飞鸟,谁又能真正地看见呢?不过是徒然望着滚滚涛浪,等到白发苍苍也不能一睹她们的芳容。李颀在字里行间既蕴含了对“海岛青冥”的向往和好奇,也表达出对寻访鲛人的不切实际的无奈和失望。与其笔下凄冷的月海相异,另一位诗人顾况则摹画出一个幻妙奇瑰的龙宫仙境:“精卫衔石东飞时,鲛人织绡采藕丝。”(《龙宫操》)。
除了对方外玄境的想象,诗人也多利用鲛人的神秘诡幻来衬托物象的奇特。例如,顾云目中的青苔“即是仙宫欲制六铢衣,染丝未倩鲛人织”(《苔歌》)。杜甫亦将雨落空江叮咚作响的自然现象联想到鲛人正在泉室里织绡鸣杼,发出高亢激越的声响,“鲛馆如鸣杼,樵舟岂伐枚”(《雨》)。而在《送杨瑗尉南海》这首诗里,岑参则把鲛人与南海的荒蛮险恶联系在了一起,“楼台重蜃气,邑里杂鲛人”,与中原大地不同,边远的南蛮处处充斥着恢恑憰怪的景象:海市蜃楼的幻相里悬叠着亭台楼榭,人来人往的城邑里也会混杂着诡奇的鲛人。诗人虽然表露出对中原以南地带的误解和偏见,以及固化的负面印象,但他主要是欲借“蜃气”和“鲛人”来说明南海的奇异风情并不适合从北方而来的杨瑗,对朋友的劝慰之意和关切之情溢于言表。
(二)清风峻节和隐逸情结
一面是远离红尘喧嚣的南冥玄境的背景置设,一面是广义的“水文化”意象群的语义互动与感染,“鲛人”作为一种文学意象,亦被赋予了不趋媚俗、坚守情操或者渴慕隐逸的文化意蕴。例如孟浩然的《登江中孤屿赠白云先生王迥》,全诗曰: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屿出。回潭石下深,绿筱岸傍密。鲛人潜不见,渔父歌自逸。忆与君别时,泛舟如昨日。夕阳开返照,中坐兴非一。南望鹿门山,归来恨如失。
清澈幽深的江水露出一方沙屿,繁密茂盛的碧竹亦将江畔绕出一片绿意。悠然自在、怡然自得的渔夫唱着欢快的乐调,传说中的鲛人也潜匿在悠悠江水下。前三联极言汉江及其两岸的神奇美丽,既是诗人登岛的所望所想,也为后文回忆曾与友人王迥泛舟作下铺垫。夕阳西下,诗人独坐遥望南方的鹿门山,游水荡船的快意与乐趣已经不再,只余下思念的苦楚和不能相见的遗憾。通览全诗,大可视为诗人独游汉江的水程心志,不仅表达出对友人的深厚情谊,也潜寓着作者精神的向往依归——那种身世两弃、山水相依的清旷与逍遥。
储光羲的《采莲词》也流露出向往恬淡的情感倾向,“浪中海童语,流下鲛人居”是采莲的环境,同孟诗中的汉江一样,奇丽灵性的水土方能孕育出富有灵气的人,采莲女们“采采乘日暮,不思贤与愚”,栖息于江南水乡的她们,没有是非的困扰,也没有贤愚的分别,处于安静祥和的美好状态之中。而反观诗人,仕途失意、沉沦下僚,又饱经宦海官场上的雨雪风霜,世俗的名利早已让诗人内心疲惫不堪。眼前的菡萏随风摇曳、莲香四溢,诗人抖尽倦客的一袭风尘,与采莲女一起,陷入和谐宁谧的精神领域,并从中获得莫大慰藉。而李绅则用与俗世隔绝的鲛人来衬托屈原的遗世独立、超逸脱俗,“潇湘岛浦无人居,风惊水暗惟鲛鱼”(《涉沅潇》),来到潇水和湘江的岛屿与洲浦,屈子曾经浪迹此处,而如今却已无人居住。身陷于中唐政治漩涡而屡受贬谪的诗人,不禁与遭历放逐的屈原产生了共鸣,希冀能够坚守住自己高尚的情操。
《全唐诗》中张署之诗仅存一首《赠韩退之》,顾名思义,此为诗人同韩愈酬唱应和之作。读罢全诗,似为作者怀旧伤时之感,实则暗含悲愤。贞元十九年冬天,张署与同为监察御史的韩愈一同上书诤谏、力争国是,却遭人弹劾陷害,两人双双被贬南方,此诗即为谪守临武时所作。且看退之的《答张十一》中的最后一联:“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13)孟二冬:《韩孟诗传》,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116页。。”韩愈读过张署的来诗,陡然发觉自己的鬓发已经白了一半,这背后既有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惺惺相惜,更多的则是壮志难酬的悲愁激愤以及对污浊世俗的厌恶。带着这样的“共鸣”去理解张诗中的“鲛人远泛渔舟水,鵩鸟闲飞露里天”,则能更加贴切诗人的本意。作者自喻为随浪漂泊的鲛人,以此表明自己清高的气节。而鵩鸟则是喻指那些刁滑卑鄙、妒贤嫉能的势利小人。古人常道,“鵩似鸮,不祥鸟也(14)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第一册上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288页。”,诗人对那些诬蔑自己的奸臣小人的忿怨之情便潜藏其中。
(三)离情别绪和暌违之痛
正如前文所述,有别于西方诡戾的海妖塞壬,中国古代的鲛人形象被倾注了浓重的人伦色彩,更富有亲和性和人情味。其中最为明显的特征便是鲛人的眼泪,诗人多用其来表达惜别之情。例如,“又似鲛人为客罢,迸泪成珠玉盘泻”(吴融《赠李长史歌》)这一句中,诗人就自比为泣泪成珠的鲛人,落泪不止乃至玉盘倾泻,足见作者对友人的情意是何等真挚深切。又如,“朱门泣别同鲛客,紫塞旅游随雁臣”(殷文圭《边将别》)亦言诗人离别的伤感与悲痛。李商隐《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中的“江生魂黯黯,泉客泪涔涔”则将这种情愫写得凄怆惨恻、肝肠寸断,渲染出一种清寥黯寂的氛围。还有的诗作也把鲛人受飨于人家并以泪相报的典故融汇其中,借此来表达对他人帮助的感激以及即将分别的哀思。李群玉的《病起别主人》便是如此,全诗云:
益愧千金少,情将一饭殊。恨无泉客泪,尽泣感恩珠。
诗人病愈初起,对寓所主人的悉心照顾感激不已,即使是千两黄金也难以为报,只恨自己不是传闻中的鲛人,不能把泪水尽数化作晶莹圆润的玉珠。涕泗横流之际,千言万语道不足,却又不得不挥手作别,悲戚之意便瞬间跃然纸上。方干的《题故人废宅二首》则并不直抒胸臆,而是把对故人的感怀寓托于时过境迁的慨叹之中,“举目凄凉入破门,鲛人一饭尚知恩”。
(四)伤时忧事和愤懑之感
杜诗以前,鲛人意象的运用多是关切个体的生命体验,并不直接牵涉到复杂的社会现实。然而杜甫却把包括鲛人在内的众多意象都纳入到缘事而发、书写民生疾苦的成诗模式之中,使之染上一层沉郁顿挫的悲怆色彩。其诗《客从》全文如下:
客从南溟来,遗我泉客珠。珠中有隐字,欲辨不成书。缄之箧笥久,以俟公家须。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
这是一首典型的寓言式的政治讽刺诗。杜甫假借鲛人泣珠的传说,用落泪的“泉客”来喻指备受剥削的劳苦大众,用泪水凝结而成的“珠”来象征百姓用血汗创作出来的劳动果实,珠上的“隐字”则喻示着人民心中有苦难言的隐痛。尾联卒章显志,昔日的“泉客珠”已经化为一摊殷红的血迹,“哀今征敛无”,如今已没有任何财物能够应付官家的横征暴敛。另一首杜诗《奉同郭给事汤东灵湫作》中的讽切之意则表现得较为隐晦,此作写于唐玄宗天宝十四载秋,当年11月安禄山起兵叛唐,安史之乱就此爆发。逆乱前夕,帝妃前往华清宫沐浴温汤,此时暗流涌动、端倪已显,为君者却依然在纵欲享乐。“箫鼓荡四溟,异香泱漭浮。鲛人献微绡,曾祝沈豪牛”,诗人表面上是在描绘祭祀灵湫的盛大典礼,其场面之恢弘,“古先莫能俦”,实际上正是在反讽这所谓的清明盛世已然岌岌可危——唐玄宗荒淫无道、姑息养奸,安禄山一众势力已经“化作长黄虬”,成了大气候了。与杜诗相似,施肩吾的《贫客吟》也以鲛人落泪来讽喻朝廷对百姓的欺压,“今朝欲泣泉客珠,及到盘中却成血”,泪至盘中,却是触目惊心的淋漓鲜血,诗人对贫民的怜悯同情和对虎官狼吏的愤懑怨怼尽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