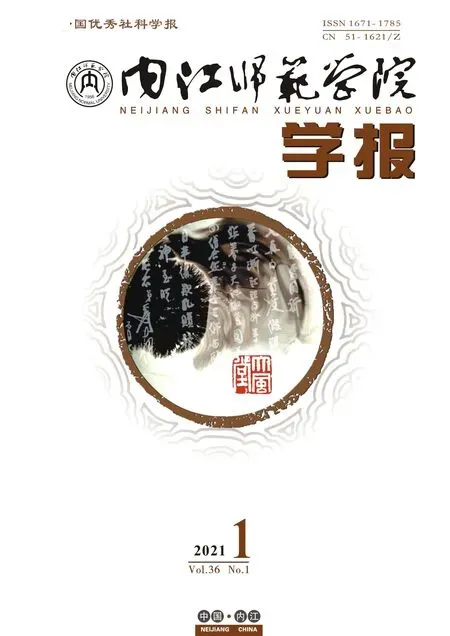金代进士张庭玉碑文辑校暨民间建桥活动略考
马 振 君
(内江师范学院 文学院, 四川 内江 641100)
金人文献传世甚少,《金史》所载又多语焉未详,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一代历史、文化与文学研究的深入。因此,只有开辟新的途径,下功夫将那些现存“未知”文献挖掘出来,并加以悉心整理,才有可能缓解这种窘困状况。但是,挖掘在先,整理在后,两者同等重要。以张庭玉《五里河义桥记》为例,拓本原藏于国家图书馆,曾以影印形式收入《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公开出版发行,迄今三十年余,却未见学界关注,原因在于碑版长久经受风雨侵蚀,文字漫漶残缺,难以利用。再如,其《朝散大夫前德州安德县令郭公碑铭并序》,较早为《(光绪)定兴县志·金石志》辑录,由于原碑残泐,以及“官差”恶习,抄录者漫不经心,“碑版残泐”加“识录讹误”,致使碑文几不可读。有感于斯,兹以年代类次,逐字校订。所补文字,均加括号“[]”注明,以供学界同仁参考。晚学不敏,两碑二千余字,竟费时四载方考定一二,稍有感悟:石刻文献之整理,何其艰也!
张庭玉字子荣,易县人①[1]。幼敏慧,善吟咏,为时彦推服。大定中擢进士第②[2],然未求出仕③[3]622。其友邢进之以题百种授之,曰:“能一日为之乎?”庭玉挥翰不停,日中已就。承安中召试,俄顷成七十篇,为章宗皇帝叹赏。泰和七年,隐居磐溪,以诗酒自娱,足不入城市,号曰磐溪居士[4]。尝著《磐溪居士诗集》行世④[2]。元好问辑纂《中州集》,于这位前辈似不甚了解,小传寥寥数语,仅录其《即事》诗一首:“乌鸢绕树山梨熟,蝴蝶穿花木槿开。赤脚城中借书去,苍头原上负薪来。”实际上,这位磐溪居士才华卓著,亦擅书法。其明昌四年为蔡珪《易州玉溪善兴禅寺记》书丹墨迹尚存[2]。
一、五里河义桥记⑤[5]
易州宋村五里河新建义桥[之记]⑥
[前]进士张庭玉[撰记]并书丹题额⑦
予尝读《方舆记》,知易县本汉故安县也。隋初置昌黎郡,后兼置易州。按《图经》云,隋初移南/营州,居燕之候台,仍改名为易州,取州南易水为名。境内之水著其名者,别有数种,曰鱼/丘水,出鱼山;曰濡水,出穷独山;曰雹水,出石兽岗;其余不可历数。惟郡东[五]里许⑧[6],一水自/北来,源流甚近,《水经》不载其名,俗谓之五里河,正当行旅东西之路。粤自畴昔,尝构木为桥/,桥积[有]岁时⑨,亦[日渐]朽甚,不为轮驺之便。
有七里村梁彬、李仲信暨本村王群可辈,皆乡/里义人也。一日聚会,喟然发叹,而相谓曰:“大丈夫见义不为,无勇也。临难不济,非义也。况/修造桥梁,为造物之大者,我辈盍为之?”既倡且和,[众]谓之可。复议之曰:“纲维是者,[亦]在得/人。”乃共推梁村刘惠、涞水县司徒村崔运[造][为]之,既[请],皆听命。于是各出金帛之外,至鬻/土地院舍,尚未能办,乃乞诸他人以给之。采北山之石余五百载,工作之徒,常不啻百数/。以日继日,以月继月,志不可夺,事期有成。自大定廿四年至廿六年,始告功毕。是桥也,成/艰难,成乎易,致险峻为之平。[呈]虹霓之[形],取坚固也;无彩绘之饰,尚质素也。落成之日,观/者如堵,罔不叹美。
前所谓刘惠、崔运,惠然过予,备言其事,曰:“吾二人者,少失恃怙,各无昆/弟姊妹之亲,茕独自立,至于今日,皆寿逾七十,财产且丰,岂非平日为善之所致耶?今义/桥既成,以报父母罔极之恩,以捄往来不通之患,能无文叙纪之?因[兹]而请记。”予感其至/诚□,□摭实成文,刻之于石,以告来者云。时丙午夏十三日/。
刘惠、崔运立石。赵奉先镌/。
在数学发达、建筑技术精湛的金代,人们建造了大量桥梁,比如举世闻名的建成于明昌三年(1192)的“泸沟桥”(《金史·章宗纪》,现在名“卢沟桥”),可谓科学技术与雕刻艺术的结晶。除此之外,现存的一些金代石桥也有不少,如黄河新闻网晋城频道《景德桥:山西现存年代最久远的金代石拱桥》一文报道:“(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乡村古桥调查成果:金代乡村古桥有5座,分布于长治、临汾、晋城、忻州4个市,有屯留县仙济桥、襄汾县洪济桥、原平市普济桥、晋城市景德桥、襄垣县永惠桥。”[7]这仅是山西一省的调查结果,其他原为金代辖地的省份也有石桥留存的报道。当然,这些桥梁肯定是金代所建桥梁的极少部分,绝大部分都已经消亡在时光的长河中了。幸运的是,还有少量的桥梁通过碑记等文献载入历史的记忆,五里河义桥即是其中之一。张庭玉此碑纯字数不足800,记述了桥的地理位置、修建缘起、资金筹集、建造经过等,其中最有价值者有两点,一是桥的建造技术,二是资金来源。
上文已略及金代建筑技术高超,有像卢沟桥那样堪称建筑技术与雕刻艺术结晶的杰作。卢沟桥是官方所造,而五里河义桥则纯为民间自建。与卢沟桥一样,五里河义桥也是一座石桥,“呈虹霓之形”表明它还是一座拱桥,而且颇具造型艺术之美。现在留下来的金代石桥,绝大多数都是石拱桥,可见这种形制在当时的普遍性,同时也说明这种形制的桥梁具有坚固耐久的优点,所以才留传最多,保存最好。如果将存世的桥和文献中记载的桥汇总考察研究,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一部金代桥梁史。
据现有的文献记载,金代建桥的资金来源有两个途径,一是官方投资。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卢沟桥的修建,《金史·章宗纪》:“(大定二十九年,1189)六月己丑朔……丁酉,幸庆寿寺。作泸沟石桥。”[8]210“(明昌三年,1192)癸未,泸沟石桥成。”[8]220这是君王亲自下旨修造,其费用自然来自国库。由此也可推知,各地方政府也会有相应的修桥经费。这些都是官方投资。
二是民间醵资。这又有两途,一是庙观善款,二是乡民集资。
金代佛教发达,佛寺禅院,遍及全国,高僧大德,所在多有,信众檀越,广布天下,因此就催生了聚集大量财富的寺院经济。这一经济门类既使边事军需有了一定保障,也为国事用度提供了大量资金。除了购买度牒上缴国库之外,寺观僧道也将修桥补路作为修行的一种方式,募化善款,醵资集事:
众善信士而谓长户曰:近有所闻,前副录僧判净范大德琛公弟子,王俗姓氏,法讳文超,本登州人也。性惟持善,志爱修崇,三事之衣称体,六和之德于身。王石峰畔,增修广化莲宫;瑞马城中,助建慧光宝塔。今则于栾武郡东冶水河创盖石桥一所,计日万功,稳铺山骨,高叠云根,霄虹弯于头尾,海月现于半轮。既然无滞,将以毕功。若从虔诚,一心礼请,善意慈心,必无阻也。[10]695上
高僧文超,不仅募修宫殿宝塔,还创建石桥,大行善举。正因这些高僧大德募化善款,零抷碎集,终于成事。很显然,寺观经济特有的号召力使社会零散资金汇集起来,之后再用于民生,这是当时非常常见的一种集资形式,是国家经济主体的重要补充。
需要补充的是,因为高僧大德德高望重,他们还常常被聘请担任第三方工程监理人,例如“有渤海吴氏者,率乡闾之众,共资所费,创缉是桥。仍请振公上人兴其事,董其役。不日告成,众人皆欢跃而观之。”[11]
修造乡间桥梁,乡民醵资的情形则最为常见。五里河义桥之所以名“义桥”,即指公益之桥。此桥是由梁彬、李仲信等乐于公益事业的人士倡导,乡民集资兴建。上面所举“吴氏”即“率乡闾之众,共资所费,创缉是桥”。再如《龙安山兴国道院修完记》:
海陵天德初,社长李全、李文成、刘约,同试共贯,护嫪林峦山麓,以给诸方举炬之用。及为东临拒马水,跋涉行遇路,必由之桥栈可通。每岁经葺,以济不通[12]。
这是由里社社长牵头,联合社民,醵资完成的公益事业。再如《鸡泽县文宣王庙碑阴题名》载“兴建庙学社宇人姓名”,其中有一人名刘浩,其下小字注云“怀义桥”[13]633上,说明他投资兴建了文庙建筑群中的一座小桥。还有多篇金代文献涉及了乡民集资建桥的情况,都证实乡民出于公益,自发醵资建桥,这在金代是非常普遍的一种集资方式。同样,这种集资方式也是金代国家用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五里河义桥记》的价值就在于,它非常详尽地记载了乡民集资的过程,反映了那时的民生经济现实,打开了我们认识金代经济历史的一扇窗口。
二、朝散大夫前德州安德县令郭公碑铭并序[14]425-426
磐谿张庭玉撰并书丹题额
公讳济忠,字子正,其先易县河内里人也。大定六年,黄甫村南置定兴县,拨而隶焉,今为涿州定兴人。曾暹、祖成,皆高尚不仕,以农为业。成三子,长璘,公之父也。长于□□□□法度,习进士业,不中第。后为□官,至□品,追赠朝散大夫骑都尉汾阳县开国男。母李氏,封汾阳乡太君。次□,□□丰姿,业[律科],以贞元三年登[第],官承事郎,终[于]三部[检]法。璘二子:长济道,亦以正隆二年律科登第,终承直郎兴中县令;次即公也。
公生则异常,不好儿嬉。稍长,有[节]操。以兄先第,慨然叹曰:“兄且贵矣,我岂不愧于心乎?”遂昼夜诵习,寝食俱废,律令精通,寻升五年第,授将仕郎。时年二十五,乡人荣之。调睢州知法,后改遂、□、保等州及河□□路转运司[知法],□□公□,无一毫私曲。十一年,改潞州壶关主簿,累迁征仕郎。既下车,循法而治,部民安之。十四年八月秩满,□□□□安肃州[知法],[超]迁文林郎。十八年,丁父忧,[哀]毁过[度],几至灭性。已而制终,二十一[年],改汾州介休主簿,迁儒林郎,守职□三□□□□北引领。[以]垂白之亲有阙侍[养],□□□□□,有司许之,还家奉甘旨。三岁余,亲戚勉谕,俾复求仕,再调安肃州知法。二十七年,丁母忧,号泣哀慕,诵经食素,誓守松[楸],以毕余生。
明昌初,设提刑司,纠察严明,知公尚康健,督之使起[复]承直郎,授云内州云川县令。再迁安肃、闻喜、安[德]三县令,所至皆以廉能称。迁承德郎,复覃奉直大夫,循至奉议、奉政大夫。
公以荐治名县,寿几七十,致仕之期,正合典礼,乃引年求退。既遂其请,超朝散大夫食半俸于家。乃安居里闬,与故旧往来,登山临水,把酒啸歌,兴尽而返。如此率以为常。以[泰和四]年□月□□日[终]于其家,享寿[六十九]。长男旭以□□月□□日,卜[葬]于先茔之原,礼也。将立隧首之碑,以彰厥美,求铭于庭玉。自惟拙恶无才,然而忝预门下侄女之婿,备知行事之始末,故得言之而不敢坚拒。
谨按《姓纂》:周王季弟虢叔,受封于虢,或曰虢公,因以为氏。《公羊传》云:“虢谓之郭,声之转也。”燕[南]郭隗子孙[徙]居燕鄙,公其后也。一家同时入仕者几十人,门风之昌茂,当世少比。娶魏氏,封汾阳乡君。子二人:[长]□□□□□□,次□□□将军。女子二人:长适登仕佐郎张翥,次适承奉班祗候任锐。孙男六人;长承奉班祗候汝梅,次汝霖、汝嘉、汝楫、汝□、汝翼。孙女四人,重孙女二人。
公体貌充伟,长六尺,美须髯。人望而畏之,即之也温。每历任,当时无□□其恩使及□□□多思之。及还家,□□兄弟,抚育儿女,皆尽其意。承安二年间,北边用兵,行六部官知公有才干,□□□□□□□□□□□□□勾当。其间,凡麾下所委,事无不济。岁周还任,优蒙旌赏。呜呼能哉!累官自将仕郎至[朝散大夫],[勋自]武骑尉至[上骑]都尉,职自[知]法曾四任县令。策名入官,则无过犯;居家临财,则无私偏。行身至此,可不铭诸?铭曰:
燕南之陲,氏惟汾阳。世有[郭隗],子孙其昌。叔侄弟兄,相继而第。风动闾阎,闻者自励。专掌条宪,数任荐更。意尽于□,□委□生。壶关[主簿],簿籍再主。暨宰四县,善乎绥抚。年几七十,厌名利场。退休告老,□□□□。鱼既县金,袍复赐紫。上荣父母,下庇妻子。堂堂郭公,有礼而仁。始终如一,□何□□。生荣[死]哀,□□曰寿。立[碑]刻铭,以传不朽。
注释:
① 《中州集》卷九《张庭玉》。
② 金蔡珪《玉溪善兴禅寺记》,撰于大定十四年,并署“范阳李嗣周篆,进士张庭玉书”,见清陆继辉《八琼室金石补正续编》卷六四。
③ 《中州集》小传及张庭玉撰碑自署,俱未言仕宦。另,清杨晨《定兴金石志》著录《十方院记》亦可证:“前题《大金涿州定兴县金台乡百楼北十方道院之碑》,巨川进士张委撰,易水磐溪老人进士张子荣门人南溪田宾书丹并篆额。末题泰和六年岁次丙寅三月十六日”刊。
④ 《中州集》小传谓“有集行于世”,此从《(光绪)畿辅通志》卷一三六《艺文》著录。
⑤ 此碑高一百零八、寛六十三厘米。额高三十二、寛三十厘米。额题“五里河义桥记”竖行二行,隶书。首题“易州宋村五里河新建义桥之记”。文十八行,满行三十五字,正书。撰于大定二十六年。在易县。
⑥ 之记:原泐,据残存笔迹及文意补。按碑题“之记”为常例,当时石刻文献屡见。
⑦ 前进士张庭玉撰记:“前”字泐,据残存笔迹及文意补。今按,凡前朝擢第者,当时称“前进士”。金蔡珪《玉溪善兴禅寺记》撰于大定十四年,署“范阳李嗣周篆,进士张庭玉书”。“撰”字残泐,“记”稍可辨识,据文意补足。
⑧ 五:原泐,据《(乾隆)易州志》卷二《山川》补:“五里河,在州东五里。发源梁村,经范村南,流入易水。”
⑨ 有:漫漶,据残存笔画及文意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