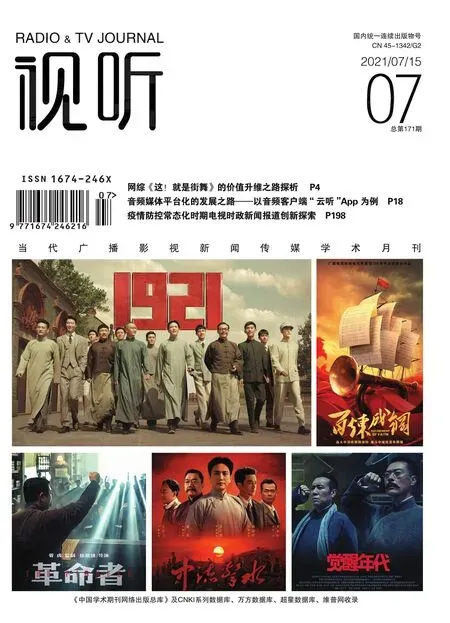中国水墨山水画在动画电影中的运用
——以《山水情》和《牧笛》为例
石殊韬
水墨山水画早在六朝时期便有迹可循,随着历史的发展,水墨渐渐受到禅宗和诗歌的影响,山水画渐渐脱离民间,开始从“无我之境”向“有我之境”转变,由对山水的客观描绘走向对创作者本人情感的抒发,书法、诗歌和绘画也在这个过程中紧密结合起来。观者在观看山水画时,跟随着画者的思绪感受着画者心中的无穷世界。这种审美体验在动画之中得到了更为直观的表达。
传统的动画制作方式不同于普通胶片电影的制作方式。胶片电影通过摄影机以复制现实的方式将现实景物摄入胶片,并通过连续快速播放的图像,依靠完形心理学在人的大脑中形成一系列的动态影像。也因此,电影图像完全遵守着现实的运动规律,具有写实的特点。而动画本身在早期则是通过绘图的方式将运动的分解图一一画下,再通过快速播放使得原本静止的图像彼此联结,获得运动感。非复制的创作方式加之非真实的景物使得动画本身并不是对现实简单的复制。非真实的场景使得故事发生的场景和设定可以进行更为天马行空的想象,允许人物做出不符合物理定律与时间规则的运动。随着媒介的不断融合,动画与电影彼此影响,数字化的创作使得电影得以借助于动画特效来完成现实所无法表现的奇观,而动画则在保留其特殊运动与时间特点的同时具有了更为电影化的叙事与表达,形成了动画电影。
在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之中,水墨画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被创作者反复使用。上世纪60至80年代,先后出现了《小蝌蚪找妈妈》(1960)、《牧笛》(1963)、《鹿铃》(1982)、《山水情》(1988)等一系列优秀的水墨动画电影。它们以水墨作为影像的呈现方式,以动态影像赋予静态水墨画新的生命。水墨的“有我之境”作为内心的投射,通过动画电影的镜头语言以及摆脱现实束缚的运动,将画中的意蕴以动画电影的形式直观呈现在观众面前,并通过观影机制带来的沉浸之感将观众带入水墨山水所营造的意境之中,体悟其中的无穷意蕴。这种特点在《山水情》和《牧笛》中得到鲜明的体现。
一、人文地理景观:“游”的审美与东方文人的自由
林年同在传统艺术的启发下,基于东方艺术的核心理念,提出了“镜游”美学理论,指出中国传统电影以中景镜头作为取景理论,单个镜头和移动镜头发展了中景的电影语言形式①。移动镜头流畅自在的游移很好地契合了“镜游”中的“游”,在动画中以手卷式镜头移动、移步换景的方式展开镜头的运动。长镜头与绵延起伏的山水结合,将流动、飘逸之感以动态的方式直观呈现于影片中,同时结合音乐与镜头移动的快慢节奏拓展延伸了山水画的绵延之感。《山水情》中老琴师弹奏古筝的段落,镜头随着音乐缓缓在竹林间平移,随后,又缓缓移至荷塘。琴声的悠扬通过在淡墨色的植物间缓慢移动的镜头得到具象化显现,舒缓的镜头移动、悠扬的音乐与竹子、荷塘的宁静意象相契合,增强了影像的幽静之感。《牧笛》中,牧童在山中吹奏竹笛,镜头则伴随着清脆的笛声有节奏地跃动。不同于《山水情》中的横向缓慢移动,《牧笛》中的镜头移动更为迅速、更具节奏感,且出现了不规则晃动,以对应笛声的音阶高低变化和鸟儿欢快的舞动,更突出了人与自然的融洽以及笛声的欢快清脆。影像所营造的清幽、灵动的意境通过镜头的缓急交替得到具象化的表现。同时,镜头运动的多样性赋予了影像独特的节奏感,也为水墨意蕴的表达提供了更为多样的表现方式和情感维度。
单个镜头同样是“镜游”美学强调的重点。不同于苏联蒙太奇镜头忽略单个镜头中内涵的丰富性,强调影像彼此之间的碰撞产生的新意义,也不同于新浪潮的长镜头强调对于现实的复制,中国创作者们巧妙地将二者结合,更加注重单个镜头内部的意义承载,单个镜头内的景与物的运动凸显着“游”的特质。在单个镜头之中,中国的山水诗歌创作中,强调“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的审美方式。由于“以物观物”旨在通过物我两忘的方式,达到在自然状态中理解万物精髓的境界,因此在创作中表现为主体让位于客体,以客体视角切入并进行观察和领悟②。《山水情》中的送别段落,伴随徒弟送别的琴声,镜头依次展现了密布的乌云、飞翔的孤鹰、飞泻的瀑布、翻滚的江水、飘动的云雾。这些景物在单个镜头内均有着自己的内涵,乌云象征着离愁的浓厚,孤鹰则是萧瑟凄冷,瀑布和江水表示离别之情的汹涌,飘动的云雾则象征离愁渐渐复归平静。单个镜头中的意象都是主人公内心的投射,通过蒙太奇的组接,离愁的丰富情感层次得以彼此交融,增加了离别的愁苦凄美之感。同时,意象的叠加将“物”置于主体之前,通过意象来表现人的情绪,“物”与“我”的界线被模糊、跨越,形成物我合一之感。镜头内部元素、符号的组合增强了内容、意蕴的阐释,而不同镜头的组接打破了山水画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将更多的意象进行了整合,进一步增强了表意与意境营造的能力。
二、在水墨山水影像中的永恒时间:从传统的纯一空间到现代的绵延
由于受到理性思维的影响,在传统的认知当中,人们将时间进行了严格的区分,过去、现在与未来彼此分离,且可以通过科学的计算予以准确的预测与计量。在这种思维之下,时间以数字的形式呈现且具有空间的性质,可进行测量与简单的叠加。这样的时间观极大地影响到电影的创作。德勒兹指出,传统电影中存在“运动感知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为了在其所处环境中有所动作,主体必须将自身隔绝于那些未经区分的流动,并预计只有基于那些对其有特别兴趣的影像,才可以动作。由此,客体与影像之间的复杂关联被简化为因果或空间联系③。但正如伯格森所说,时间并非一种纯一的空间,而应是一种浑然一体的倒锥模型,过去、现在与未来彼此交织。这种时间的混合在影片中以“天人合一”“物我两相忘”的方式得到呈现。《山水情》中的时间不停地在线性叙事之外游离,更多地呈现为自然环境中动植物的运动以及悠扬的琴声。在脱离线性叙事的影像之中,过去、未来与现在不再依次呈现,时间不再表现为师徒情感的变化或人物的行动,而是伴随着琴声带领观众感受着夜色的寂静、湖水的清澈以及动物与人的和谐共生。人物与环境相融合,形成天人合一之境,观众沉浸于物我合一所带来的流动着的时间,借以体验自己同世界的联结。
“时间—影像”立足于对流动着的绵延时间的把握,与“运动—影像”的空间化的时间相对。“运动—影像”对应着好莱坞电影的经典叙事,在影片中剧情紧密联结,环环相扣,因果关系的承接通过蒙太奇的组接得以实现。这种叙事方式表面上让观众跟随着主角的视线依照叙事的发展而感受着时间的流逝,但实际上,这里的时间是经过逻辑串联之后被空间化了的时间。“时间-影像”概念则打破了单一的英雄主义的文化叙事,倡导一种体验生命的多样性或尝试多种可能性生存方式的多元主义的文化叙事④。在这里,“感知—运动”回路出现断裂,脱节的随意空间得以游离于叙事,绵延的时间在影片中通过纯视听情境得以展现。在水墨动画中,大量的山水景观打断了连贯叙事,形成了纯视听情境。《山水情》摆脱了复杂、严密的叙事,通过松散的叙事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老琴师昏倒后住在撑船的孩童家中修养,并收孩子为徒传授琴艺,随后二人离别。影片打破了情节的连贯性和逻辑性,以大量的纯视听情境来表现琴师与徒弟练琴的场景。影像不再紧密围绕“相聚与别离”展开,而是在其中逐渐游离,走入对自然与琴声的展现。远景、大远景镜头将人物同景物相融合,人物不再进行功能性的活动,而是静坐于自然之中,同琴声和万物融合。在这些脱离叙事的纯视听情境中,叙事出现断裂,观众于其中不再感受到线性时间的流逝,而是沉浸于人与自然相交融的和谐宁静的意境,达到“游心”的境界,通过主观情感的投入来感知人们内心的时间之绵延。
德勒兹认为“过去”与“未来”是潜在的,“现在”是实在的,只有在时间晶体里,实在与潜在无法区辨。晶体是一个最小的循环,当潜在发挥作用的时候,纯粹的真实伴随而来,形成不可区辨的结晶⑤。时间晶体在现实与潜在中循环、混合,而梦幻影像是其中的较大循环,它向未来敞开,与世界时间和“全体”相连接。梦的形式恰好实现了这种现实与潜在的循环与混合。《牧笛》的叙事同样极其精简,并没有清晰的因果联结,有的只是一个牧童奇幻的梦境。整个影片并无严密的叙事线,而是围绕着一个梦境展开。梦境与现实、潜意识同意识相交织,形成混合的时间晶体影像。牧童的笛声将梦境与现实相连接,将梦幻中的万物有灵同现实的清幽相连接,以水墨的形式呈现于银幕。观众沉醉于水墨动画之中,跟随镜头的游动与静止,逐渐脱离叙事线进入天人合一的空灵之境,进而把握延伸至过去与未来的永恒时间。
三、社会空间与自然空间:入世与逸世的此在
栖身于人类社会,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来自社会法律制度、道德以及他人的规训,也不可避免地在制度与道德的循唤与他人的凝视中渐渐遮蔽了本真的自我。海德格尔将这种生存状态称作“沉沦”。在现实中,自我不可避免地需要同他人产生联系、沟通,与他人“共在”,而他人则对自我产生种种影响与限制,使得自我无法实现自由,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沉沦”之中。伯格森则指出,联想学派的学者把自我还原为一堆意识状态:种种感觉,种种情感,种种观念。而如果人们在其中看到的不超过它们的名字所表示的,如果他所保留的只是它们那不属于私人的方面,那么,尽管他永远把它们并排置列,他所得的仍不失旁的而只是一个虚幻的自我,只是那把自己投入空间的自我之阴影⑥。若想获得自由,就应当摆脱他人对自我的建构,摆脱标签式的情感与观念,从内在出发,找寻属于自己的独特性。这在影片中表现为脱离线性叙事的人物在流动时间之中的复杂情感。在《山水情》师徒告别的段落中,情感的抒发不再通过人物的对话予以呈现,而是依靠意象的叠加和琴声的变化进行隐晦的表达。意象的彼此组接和琴声的绵延变化将这种复杂的情绪进行了影像化的呈现。
由于现实对人的自我感知的蒙蔽,出于对自由的探索使得海德格尔和伯格森纷纷将目光转向了艺术。在海德格尔看来,艺术品摆脱了科学技术的思维方式,是艺术家主观思维、情感的具象化呈现,这使得真理得以摆脱外在的束缚,自行置入作品之中。它将事物的本真展现于自己的形式与内容之中,在带领观众沉浸其中时,使得观众得以摆脱现实的枷锁,而走入自己的内在,于无穷意蕴中感受自己的真实情感以及同世界万物的连接,进而感知到自己的真实存在。《山水情》中徒弟弹奏古筝的段落,伴随着悠扬的琴声,鱼儿摇动钓鱼线,跟随鱼饵在水中游动,随着琴声的突然转疾又快速散去,在邻近徒弟身边的河水里游荡。没有了垂钓的捕杀,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只有人与自然于静默中的和谐共生,和隐于琴声之中的情感流露。人此刻并非独立于其他生命体的特殊存在,而是与自然万物相交融。《牧笛》则以“梦”为主题,借助梦所特有的迷幻之感来进行“游”的体验。在牧童睡去后,梦中出现两只黄色的蝴蝶飘然飞去,暗合着“庄生梦蝶”的典故。在梦境之中,自然万物在牧童笛声的感召下纷纷做出回应,本无运动与思维能力的植物开始了规律的律动,看似野蛮、不具有思考能力的动物也纷纷驻足,各种飞禽纷纷抬头,呈现出一个万物有灵的世界。
在感受自己的内在以及同万物的联系方面,对于自然之物的表现尤为重要。斯奈德将“野”(wild)作为荒野的本性,视之为人在“地方”存在的必需,从而将人们对荒野的“地方意识”升华到中国佛与道的“空”“无我”和“道”的境界。荒野是自由主体、随性滋长、自然而然的本真存在,能让人们在忘我境界中化身为与自然宇宙万物具有相同性质的物,使人拥抱他者、跨越物种界限⑦。水墨画经历长久的发展,摆脱了对于现实的精确复制,而追求通过心灵来映射万象。通过对于自然的体察,把握事物生生不息的规律,感知永恒时间中的奥妙,感知无形的“道”,以求心灵摆脱现实的束缚,实现逍遥游。在电影之中,“游”的审美体验包括了“目游”与“心游”,“目游”通过动态镜语的艺术来表现,而“心游”则通过时空一体的美学观得以呈现。在水墨动画之中,这种对“心游”的追求通过水墨形式的虚实相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镜头悠然自在的运动和远景大远景的构图得以充分表现。《山水情》全片以黑白水墨为主要表现形式,影片的片头通过一段缓慢横移的长镜头开始了故事的讲述。在山水的缓慢呈现中,老琴师以白色的身影缓缓出现在其中,极静的场景只有风在呼呼作响,衬托了场景的空旷,与淡墨色的背景一同营造出仙风道骨的独行隐士形象。影片将师徒二人的居所立于山间,地理环境的特点使得这里成为人迹罕至的“世外桃源”般的存在。二人在此得以摆脱社会属性,醉心于琴声之中,于宁静闲适之中进入“禅”的境界,在静穆的观照和飞跃之中抵达生命的本真。
四、结语
水墨山水画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文化的积淀,形成了属于自己独特的表现方式与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随着技术的日益进步与媒介的相互融合,水墨山水画通过动画电影的形式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使人们得以在浮躁的现实中暂时地抽身,于飘逸的形式与绵延的时间之中,感知自己的存在。随着技术的日益进步,如何在保留水墨动画原有独特意蕴的基础之上将新的技术同水墨动画相结合,成为创作者需要面对的新的挑战。希冀创作者能够根植于本土文化,借助新的创作手法赋予水墨动画电影新的生命力。
注释:
①洪楚钿.论林年同的“镜游美学”理论[D].南宁:广西大学,2016.
②华海婷.从“以物观物”看斯奈德与王维山水诗的相似性[J].海外英语,2020(07):182-184.
③于东兴.德勒兹的影像之谜[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0(02):15-24.
④王秀芬.德勒兹的影像论及其文化叙事分析[J].电影文学,2019(05):116-118.
⑤马腾.从感官机能到时间晶体:德勒兹影像理论初探[J].江西社会科学,2016(08):107-111.
⑥[法]伯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M].吴士栋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23.
⑦蔡霞.“地方”:生态批评研究的新范畴——段义孚和斯奈德“地方”思想比较研究[J].外语研究,2016(02):102-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