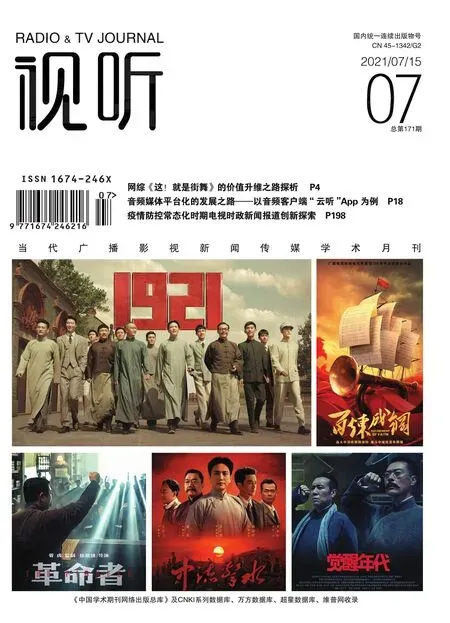自我的建构与解构
——青年群体在微博中的自我呈现研究
王小芳
伦敦大学的米勒教授指出,当下的媒介环境中,媒介平台和传播渠道不仅数量激增,而且相互交织,呈现出一种综合性的结构,即“复媒体”。在复媒体时代下,大量的媒介充斥着我们的生活,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媒介和“观众”进行差异化定位、多面体的自我呈现,甚至根据不同的社交媒体匹配不同的人际关系网络,社交媒介已不仅仅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个人选择。
用户会根据人际传播的需要进行媒介选择,Broadbent(2011)指出“隐私性、社交性、严谨性、反馈及时性、交流频率、时间便利性、交流质量”等因素是用户进行媒介选择的关键因素。用户在进行社交媒体的选择时,会结合平台特性、用户经验和感知选择合适的平台,同时媒介背后的社会规范和人际网络也会影响用户的媒介选择,比如正式场合选择企业微信或者邮箱,跟家人朋友聊天则选择微信。
微博是一个典型的陌生人社区,来自不同城市甚至不同国家的人都可以在该平台上发表观点和展示生活,用户可以在微博上进行“自我狂欢”。对于青年群体来说,他们是“网络原住民”,虽然微博现在也有分组可见、朋友关注,但是相比于微信的熟人关系网络,微博的匿名性、弱关系链等特征更加吸引青年群体在该平台进行自我呈现。
一、积极的自我建构
(一)多面体的自我呈现
根据研究调查,不少青年群体都会开通微博小号,即使没有微博小号,也会在平常发微博的过程中注意分组,针对不同的“观众”进行差异化展示。对于明星和达人,微博小号成为他们释放自己的舞台。在微博大号上,出于社会监督和规范,他们不得不进行自我规范,而在微博小号上,他们不用担心既定“人设”,可以自由地释放自己的情绪。
用户之所以进行多面体的自我呈现,是基于对“自我”和“他我”的想象。微博平台本身就是一款信息分享、获取、传播的即时通讯软件,在该平台上,用户之间的贴近性较弱,即使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也会因为用户的某一条微博内容或者微博的风格而进行长期关注。用户还可以在搜索栏搜索时装、美妆、摄影等关键词,关注某一领域的KOL(关键意见领袖)。这与微信和QQ的熟人好友不同,在微博中,用户可以构建一个完全远离现实的“自我”,想象在别人眼中的“完美人设”,来自陌生人的关注和点赞,可以让用户获得自我满足,同时通过议程设置,进行多面的自我呈现,也能满足自我关于他者的想象。
正是由于这种“他者”的想象,激发了用户在微博的创作欲。在微博大号上,他们关注“镜中我”的形象,然后根据点赞和评论的反馈,适时调整自我呈现的策略;在微博小号上,不用担心社交关系的压力,用户可以大胆地发表一些负面情绪,进行“自我狂欢”。
(二)前台的自我操控
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提出拟剧理论,将人们的人际交往场景划分为“前台”和“后台”,认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就是担任不同角色的自我呈现。在微博中,前台是基于社会监督和约束呈现的自我形象,而后台则是真实的自我或者与标准规定相反的真实自我。
戈夫曼还提出“给予”和“流露”的概念。“给予”是用户根据需求决定展示给观众的部分,而“流露”则是用户不经意间或者无意识流露出来的内容,用户在发布微博内容时,会事先进行一个形象的预设,设定好要在前台展示的内容,同时对“给予”部分进行把关。比如用户喜欢追星,那么她可能随时在微博中发布明星的动态,在明星最新微博内容上进行评论留言,还可能会加入有关的粉丝群和圈子,而追星之外的生活常态,则取决于个人的选择性表达,她的微博主页也可能会展现追剧、爱看书等内容,用户自己对“给予”(展示部分)进行筛选。此外,根据其他网友的反馈(点赞、评论等),用户还会实时调整呈现的策略,对于前台化的自我进行积极操控。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观念的变化和Vlog的兴起,“前台”和“后台”的界限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正如梅罗维茨在《消失的地域》中指出:介于“前台”和“后台”中间存在着一个“中台”,即话剧表演时演员在侧幕等待的地方,而在电子媒体时代,原来的具体情景和空间地域已经消失。广播和电视的出现让表演前台的时候很难不流露出某些后台,或者说其前台在不断后撤,于是电视观众就像进入到了侧台。将这些概念放置在社交媒体的情景中,就可以连接到分享与过度分享的概念。当人们在前台或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内容越来越多,以至于这种分享可能是一种过度分享,而人们因为过度分享会产生一种后台前台化的趋势,分享很多在前社交媒体时代的东西。不少用户选择用Vlog的形式,展示真实的后台情景,进行一种传播的展演或者沉浸的传播,就是后台的前台化。
虽然微博的匿名性等特征激发用户进行积极的自我呈现,但是复媒体的蜂窝式传播、数字痕迹等特征也使用户开始思考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二、消极的自我解构
(一)社交媒体倦怠
微博作为青年群体常用的社交媒体,当前已经多次进行产品更迭,算法推荐让通讯录的好友也成为微博粉丝,即使开通微博小号,由于账号绑定也会有实时暴露的风险。微博中的“熟人”越来越多,在用户的工作和生活中,会添加越来越多来自身边的朋友,用户开始疲于分组和表演,产生倦怠情绪,而且出于对隐私的担忧,害怕来自他人的“视奸”和“考古”,用户开始减少在微博发布的频率和内容,进行一种消极的自我表达,产生潜水、隐退甚至回避的行为。离开微博本身的特性,当前有越来越多的其他媒介分散着用户的注意力,微博不是用户自我呈现和线上交友的唯一渠道,在微博中,用户的社交媒体倦怠已经越来越明显。
(二)自我规范与逃避
当下,互联网已经渗透进现代人的生活肌理,用户在享受技术带来的便利时,也进入了福柯所说的圆形监狱中,用户信息一览无余。由于网络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匿名性,隐私已经从原来的号码、身高等显性信息变成兴趣偏好、习惯这类更加深层隐蔽的方面,这些个人信息被或多或少地“袒露”着。在社交网络时代,公开或不公开已不再是判断隐私的标准,信息主体对已公开信息依然具有合理的隐私期待,这是一种以信息的自我控制为核心的隐私定义。
在微博中,用户注册需要填写个人信息,而微博主页表露着用户的个人喜好和倾向。基于来自圆形监狱的审视和隐私泄露的风险,用户需要不断地规范自己,让自己的微博内容不仅符合自我期待,还要符合社会秩序的规范。正如一些明星的微博内容中,必须传递符合正能量的价值观,不能出现违背规范的言语和行为。另外一些用户疲于进行自我规范,则直接选择逃避,只观看他人的微博内容或者干脆不打开微博主页。
(三)语境崩塌与瓦解
用户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截然不同的展演,对于展演的对象(观众)会进行一个区隔,然而复媒体时代,用户很难清晰地将观众区隔开来。在社交媒体中,观众隔离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观众可被识别,第二个是观众可被隔离。观众可被识别,意思是观众是可控的,但是在社交媒体中很多时候观众是不可识别;观众可被隔离,生活中很多物理隔离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互联网中这种物理隔离其实是很难实现的。
微博一开始吸引用户进行自我呈现就是出于其匿名性,这意味着观众的画像是模糊的,用户很难将不可识别的陌生人按照某种特性进行分类,然后针对不同的观众分发信息。即使是垂直类的博主,其观众也很可能是多样化的,这种语境的坍塌和瓦解,加大了用户分组展演的难度,降低了用户在微博更新信息的欲望,使用户进行一种消极的自我解构。
三、总结与反思
一般来说,自我包含着三重自我,第一种是真实的自我,第二种是理想的自我,第三种是规范的自我。在微博中,不管用户是进行积极的自我把关还是消极的自我逃避,三重自我都呈现在微博主页,用户可以开通小号释放完全真实的自己,也可以通过关于他者的想象,构建一个虚拟完美的“镜中我”。
这种关于自我的建构满足了用户的自我期待,来自陌生人的认同促进了用户积极的自我建构,但圆形监狱的审视、社会秩序的规范也让用户进行自我解构。用户不再360度全景地展示自我,而是有选择性地进行自我表露,当遇到与“既定倾向”相反的情况时,甚至会出现逃避和隐退行为,产生社交媒体倦怠。
微博作为用户进行社交的重要平台之一,其特性一方面吸引着用户留存,另一方面也在“遣散”用户。青年群体是微博的重要用户画像,在一开始他们扎根于QQ和微博,后来微信的出现分离了部分用户,但当用户发现微信的强关系链和严格的自我归训多有不便时,他们又开始将目标转移到微博上。而以后用户是会沉淀在微博,进行积极的自我建构,还是会产生社交媒体倦怠,逃离微博这块土地,很难下定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