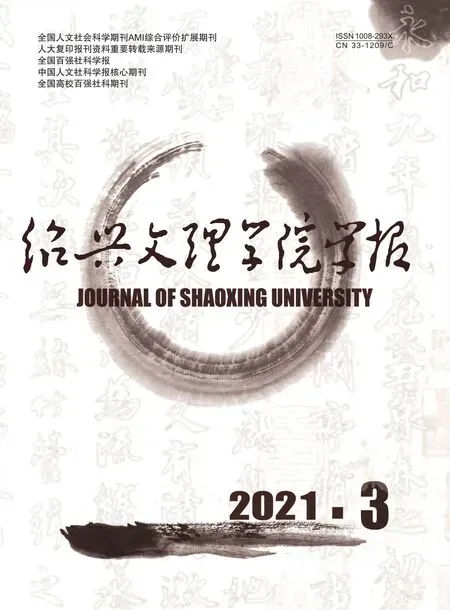陆游“沈园系列诗歌”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张 艳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上海 201209)
陆游一生忠君爱国,堪称“亘古一男儿”,唯有与前妻唐氏的婚姻悲剧让其抱憾终生,诗人无处寄托的悲哀似乎只有在诗歌的世界里才能寻回一点安慰,至情则文,也因此陆游“沈园系列诗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堪称宋代佳作,具有鲜明的文学意义。
所谓“沈园系列诗作”,从狭义上来说,是指陆游那些在“沈园”等处所作的,内容是抒发与唐氏的情感的十几首诗的总称。主要有《沈园》二首、《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园亭》、《禹寺》、《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山行见三十年前题名怅然有感》以及《城南》等作,由作者明确点出是在山阴城南的沈园、禹寺凭吊之作。从广义上来说,那些并未言明但内容显然与唐琬有关的诗作也可归入这一范畴,如《幽怀》及《凄然有感二首》等作(1)黄世中先生考证“沈园本事诗”有12首,又考证有“沈园本事疑似诗”20首,见黄世中《钗头凤与沈园本事考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
“沈园系列诗作”在陆游的总创作中所占比例并不大,但将其放在文学史的背景上来看却有着多重的意义。
一、宋人绝句中罕见的情诗系列
钱钟书《宋诗选注》曾言:“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除掉陆游的几首,宋代数目不多的爱情诗都淡薄、笨拙、套板。”[1]的确如此,宋代诗人写给妻室的作品中较为出色的几乎都是词作,如苏轼《江城子》、贺铸《鹧鸪天》等,这固然与文学的发展趋势有关,宋代诗歌公认以表现理性思考见长。毕竟诗歌发展至宋代,诗人们有难以为继的感慨,同时,由于词体在早期被认为是“小道”,因此宋人从主观上也倾向于以诗文来表达社会性、政治性的内容,而将那些私人化的,甚至是难以言明的情感放在词体中传达。当然,词这一体裁,本身也适宜表达缠绵深窈的情愫。
宋代诗作名篇并不多,绝句佳作更不多,宋代绝句创作较为出色的有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他们的绝句各具特色,但整体而言多以写景和议论为主,只有陆游选择绝句(也包括少数“古体诗”)来表达私人隐秘情感,这无疑值得我们重视。
绝句向来被认为是较难的一种文体, 因为篇幅较短, 可以发挥的空间有限。要在极为有限的篇幅内表达既丰富又深刻的内容, 那就必须比长篇诗歌更严格地选择要表达的内容, 这就决定了这种诗体的表达特征是 “摄取其中具有典型意义, 能够从个别中体现一般的片段加以表现因而它所写的往往是生活中精彩的场景、 强烈的感受、 灵魂的悸动、 事物矛盾的高潮, 或者一个风景优美的角落, 一个人物突出的镜头”[2]。
陆游的这一系列诗作避开了宋人长于理性的习惯,真正做到了情韵悠长,如“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强烈的感受”,而“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就是这样一个“动人的场景”。夕阳影中,画角声里,垂垂老者面对庭院池台,追想那年杨柳依依中的美人倩影,这样的画面和黄土垄中、美人薄命的事件联想互为生发,画面越美丽,情感就越动人,不必多作陈述和议论,就有“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更难得的是陆游的表达虽沉痛哀婉,却并不伤于绮靡,即使是“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的表达,也只有沉痛之意,并无消沉之感。也因此,有学者指出陆游沈园诗“大多采用绝句的抒情体式固然与放翁晚年豪华落尽归于平淡真淳的风格有关”[3]。然而如上述两首这类表达,于尺幅之间能浓缩千言万语,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情感纯度极高。
陆游的这类绝句,就形式而言,完美地实践了绝句这一文体的特征,但同时又有自己的特色。如在题目上列出时间和地点,有时甚至点出写作背景,如《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这首,题目之长几乎可与诗序相比,又或者是以诗序的形式点出背景,作者以铺叙之笔明确表达自己的创作意图,这些平铺直叙结合诗行中情景交融的文字,共同创造了一个凄婉的文学情境。同时,又使得诗情与本事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见诗又见事,特别真切感人。
陆游这一系列的诗歌又常表现为二首绝句并行,二首各有侧重却又互相映照,如《沈园》其一云“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4]2478,此诗侧重以今昔空间感的对比来表达对于旧日旧人的怀念,前二句写当下实景,于景中寓情。画角声哀,夕阳惨淡,沈园已然易主数次,池塘楼阁不复可认,作者在时空变化中叹息流年暗换,无力回天。后两句追忆往事,春波绿水照见“惊鸿照影”,这是多年前的倩影,也是历久而更为鲜明的印象,昔日的明亮和今日的暗淡形成鲜明的对比。《沈园》其二云“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这首侧重表现时间感,景物的提炼在上一首中已经恰到好处,此处便索性用上数字来概括,直白而惊心,然而岁月漫长而无情,而人脆弱而深情,“犹吊遗踪一泫然”,永诀之悲化为永恒之美。两首诗结合起来看,可谓是互相生发,各有妙处。
从陆游重视诗歌的时间编年来看,作者的初衷不过是为自己的人生一结,但却无意间为宋代的绝句创作作出了贡献,是宋人绝句中难得一见的一组情歌。
二、“沈园”意象定格为文化符号
中国古典诗歌长于抒情,但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和意志却需要借助客观物象来传达。所谓客观物象即所写之景、所咏之物,借景所抒之情和借物所咏之志便是创作主体之“意”了。意与象的完美结合就是“意象”。古典诗词中的意象包括有人事意象,也包括环境意象。“环境意象的创造是一个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之间双向作用的过程。观察者的所见来源于环境的外在形态,但是他表达和组织的方式,以及引导自身注意力的方法,都会反过来影响观察者的所见。”[5]环境意象又包括城市意象,如洛阳城、金谷园和北邙等。而在这些公共场所之外,宅园作为私人生活空间,也成为文人内心世界的折射,如杜甫的草堂,王羲之的兰亭,池台楼阁花木泉滩等各有其趣,构建出宁静、悠远、远离尘嚣的诗意世界。
我国的古典园林艺术,讲究小中见大,即“以有限面积,造无限空间”[6],缩千里于尺幅之中。而要做到这点,便常常需借助假山、叠石、曲径、回廊、雕栏、花墙、小桥、漏窗这些实物来增加景色的层次,使园林风光更加深远多变。创作与造园,其理一也。特别是宋代,尤其崇尚含蓄蕴藉、婉曲层深之美,也因此园林的意象频繁地被运用于诗词中。尤其是“宋时池台极盛”,有关园林的诗词在宋代文学作品中俨然成为一大类别,“它们或即景生情,或托物言志,用对叠石为山、引水为池以及花木草虫的细腻描写而寄托作者的情怀”[7]。园林,尤其是那些名园,“可以说处处蕴蓄着诗意,时时荡漾着诗情,事事体现着诗心,是地道的‘诗世界’”[8]。
《绍兴府志》言沈园在府城禹迹市南,作为宋代私人园林,至绍熙壬子年(1192),沈园“已三易主”,但陆游晚年仍以“沈园”为题写作了大量诗歌,表达的是同一主题,即伤悼自己和唐琬的情事。
沈园对于陆游来说,是伤心地,也是爱情圣地,唐氏的影像和沈园的景象,已经混为一体,定格在陆游的诗中。
值得注意的是:陆游沈园系列诗歌中常用的是自然意象,如杨柳、池塘等,而并非画堂、罗幕、锦屏、珠帘诸意象。相较而言,反而是后者有助于构筑深幽意境,如宋词中频繁出现“罗幕”和“珠帘”的意象,但陆游所要表达的伤悼之情尤为深重,至晚年更是浓烈不可化开,因此反而是自然情景更加合适表达这种喷薄而出的情感。对陆游而言,沈园并不仅仅是游历的场所,而是心灵深处的家园。陆游的痴情如陈年老酒,历久弥香,并与诗人的生命相始终。
陆游之后,“沈园”仍旧牵动诗人的思绪,如姚莹《镜湖棹歌》云“沈园零落凤箫空,谁把黄滕酹放翁?一自钗头歌错莫,至今波影不惊鸿”[9],诗中对情事的感慨可谓深得陆游诗意。此外又如范珍《过放翁沈园》、邵纬《过沈氏园怀陆放翁旧事》等诗更是直接称呼沈园为“放翁沈园”,又如邬鹤征《春波桥》也直接以“春波桥”命题,有的诗人更是将春波桥称为“第一无情是此桥”。可见“沈园”在陆游之后已承载起特定的含义,成为诗歌的固定意象。
陆唐的沈园相遇也一直是戏曲关注的题材,如蒋士铨《沈氏园吊放翁》(《忠雅堂诗集》卷十六),清人桂馥将陆唐悲剧搬上了戏曲舞台,创作了《题园壁》(《后四声猿》)。近人吴梅有《陆务观寄怨钗凤词》(《霜厓三剧》),戏曲作者陈梅香又将其改编为京剧《钗头凤》,由著名花旦荀慧生主演。吴琛、魏于潜又将此剧改编成话剧,赢得众多年轻人的观看。陈明锵曾将此剧改编成闽剧。在越剧界,陆唐题材是这个剧种最感人的传统题材之一。1989年,由著名越剧编剧顾锡东创作的《陆游与唐琬》诞生,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排演,此部越剧还被摄制成同名电影,在更大范围内为人们所熟知。20世纪80年代,陆游与唐琬的故事还被改编成电影,拍摄了故事片《千古风流》,在全国放映。至今,在绍兴沈园仍有固定的夜游节目,其开场就是用越剧形式演出《钗头凤》,将游客带进800多年前发生的那首刻骨铭心的爱情悲剧。
因此,沈园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私人园林,沈园情结已经被烙上爱情的符号,成为文化园林。
提到园林意象,值得一提的是园林题壁诗歌:在诸多题壁作品中,写男女之情的题材并不占据大多数,这自然也与国人的审美倾向有关。毕竟题壁文字面对的是向公众展示,国人涉及私人情感尤其是情感悲剧往往是讳莫如深,语焉不详。流传广泛的《钗头凤》一词却挂名在陆游名下,并为多家采信,大约皆以为正如传说所言,是陆游偶遇前妻,出于抑制不住的情感迸发,才有了这篇有较强即兴色彩的创作。但参考陆游的多篇有关沈园的诗歌创作,情感的指向一直很鲜明,即以悼念和伤感为主,对人事的态度却有所收敛,而《钗头凤》一词,却直露胸臆,表示“错错错”,窃以为,出于自身及家族和舆论的考虑,陆游应该不会如此直白。但无论如何,由于《钗头凤》一词抒情深挚,且又与陆游的沈园情事相连,也早已成为题壁诗中的名篇,客观上也强化了沈园这一文化意象。
三、对悼亡主题的继承和发展
由于唐琬早逝,因此陆游怀念前妻之作实际上也是悼亡之作,但陆游的悼亡诗不独体现为对传统悼亡诗的继承,更多的是突破。
悼亡诗的主题源远流长,最早的当是《诗经·绿衣》一首,此诗表达丈夫悼念亡妻的感情是由衣物开始,由衣而联想到治丝,赞美亡妻的能干,由此想到亡妻的贤德,最后落实到家有贤妻,“俾无訧兮”“实获我心”[10]的情感上来。这里体现出在儒家传统家庭观和婚姻观的影响下,古人对婚姻的本质和意义的理解与认识,即夫妇之爱从属于家庭伦理,是一种融合了亲情、恩情、责任等各种因素的情感体验。而那种属于男女性别上或是心灵上的天然吸引,也就是我们现代意义上所谓的“爱情”,则不甚受到重视。相反,当“爱情”过于浓烈时反而会受到来自外界的限制,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古代笔记中常有记载,父母会以科举为由限制小夫妻的日常接触,史书中也曾记载过三国荀粲因爱重妻子而最终殉情的故事,然而世俗舆论对此行为的定性则是“惑溺”,即认为这是一种失去分寸的沉迷,是不合乎大众的期望的。在这种文化环境下,中国古代悼亡诗的内容范畴也就此奠定。以潘岳、元稹、贺铸等人的作品为例,无论是诗还是词,都体现出对传统思想的继承。如潘岳的悼亡诗云“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沉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11]1090,叹息自己中年丧偶是有乖人伦,失落得几乎生出远离俗世的念头,幸而还可寻求道家思想的安慰。元稹的“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12],则是写妻子为家庭牺牲的贤惠举动,叹息贫贱夫妻的同甘共苦以及自己丧偶之后痛失内助之感。又如贺铸,在妻子亡后叹息“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13],究其情感实质而言都是相似的,即以日常生活之细节来表达夫妇相濡以沫的亲情。而陆游的悼亡诗,以《凄然有感二首》一诗为例,写于陆游的暮年,诗中写到菊花枕,回忆当时尚是新婚的唐氏亲手为他缝制了菊花枕,陆游为之“作《菊枕》诗”,诗作“颇传于人”,“采得黄花作枕囊”“少日曾题菊枕诗”[4]1473,这些日常细事中体现出的固然是文人雅趣,但更多的是年少夫妻情投意合、相知相得的幸福。严格说来,爱情的成分远远高于亲情。也因此,当作者失去至爱时,“灯暗无人说断肠”,那深埋于心的痛苦,在43年后仍然无法释怀。“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分明是痛失知己的幽恨。毕竟,从陆游的人生来看,陆游和唐琬的婚姻时间较短,因此他对唐琬的情感更多的是知己之爱,而非伦理亲情。所以陆游写给唐琬的悼诗,其中心在于伤悼爱情。对陆游而言,复合无望,阴阳永隔是他一生的遗憾。
陆游的悼亡诗不仅伤悼爱情,且是自伤之作。
陆游的自伤,首先包括了对自身老去的伤感,这点突出地表现为:陆游沈园系列诗歌不仅重视时间,且多作于诗人的晚年,如《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一首:“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4]1809,此诗作于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此时的陆游年已67岁,诗人自觉黄泉路近,念及40年前沈园之事,不禁怅然。此后的《禹寺》写于作者76岁,《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作于80岁,81岁作《城南》,82岁作《禹祠》,最晚的是南宋宁宗嘉定二年(1210),即诗人85岁,也是陆游临终的前一年,诗人也不忘来到沈园对唐琬作最后的凭吊。诗人追忆往事,哀叹故人零落已久,自己也是垂垂迟暮,然而经过时间的长河不仅没有冲淡他的情感,反而让伤痕更加凸显。“空吊颓垣墨数行”,作者只能对着遗迹默默凭吊、深深叹息。
其次,这“自伤”中也包含了对往事的诸多遗恨和对自身的愧悔,如《夜闻姑恶》一诗言“孤愁忽起不可耐,风雨溪头姑恶声”[4]3727,这里写夜闻姑恶鸟的叫声,“姑恶鸟”所蕴含的意义自不待言,而作者所由此而起的愁绪竟致“不可耐”,联系陆游另外一首《夏夜舟中闻水鸟声甚哀若曰姑恶感而作诗》,诗云:“君听姑恶声,无乃遣妇魂?”[4]1161这里提到被遣走的妇人,其情不言可知。陆游另有一首《文君井》乃淳熙四年(1177)作于成都,诗云“青鞋自笑无羁束,又向文君井畔来”[4]678,陆游感慨卓文君临事决断,排除众难,终于成就自身的爱情传奇,而凭吊文君,实则也是对自己的婚姻的反思和哀悼,其中的自悔与憾恨,是不言自明的。
最后,陆游的感慨从爱情扩散到生命,不仅感慨当日两情相悦的美景不长,同时也抒发人生无常和内心的沧桑,诸多滋味混杂以至殊难分解。陆游与后妻王氏生活近50年,王氏死后,陆游作《自伤》诗句,有“白头老鳏哭空堂,不独悼死亦自伤”[4]2328之句,虽云“自伤”,但其情似乎只因“白头鳏夫”,连他给王氏所作的《令人王氏圹记》中也并无追怀之语。然观其写给唐琬的诗作中悼死的情感却十分浓烈,如《城南》诗云“城南亭榭锁闲坊,孤鹤归飞只自伤”[4]2792,这里“孤鹤”的意象, 既是表达自身的孤寂,又流露出失去知音的哀伤;又如《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云:“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怯新霜。”这里所用“河阳愁鬓”的典故来自潘岳《秋兴赋》“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11]585一句,潘岳曾任河阳县令,故以“河阳”代称。潘岳感慨人到中年,鬓发斑白,兴起岁晚之叹,此处诗人用典既是表达对伊人久逝的无限怀念,同样用以自指,表达自身的孤独哀伤。又如《沈园》诗中“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4]2478一句,用的是王安石《题永庆壁有雱遗墨数行》诗中“遗骸岂久人间世,故有情钟未可忘”[14]之意,既是“哭人”,也是触景伤情“哭己”。陆游在八旬高龄时,更是写下“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4]3677之句,俨然是触目皆是伤情,此情不禁令人深思,何以事过境迁很多年后陆游的思念非但不减,却更加不可收拾?陆游自言“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一炷香”(《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所谓“年来妄念”应该是指“收复故土”等理想。因此,综观陆游诗作,不难看出,在其前半生,虽痛失爱妻,但却将痛苦深藏心底,毕竟陆游的前半生多是戎马倥偬,无暇顾及儿女情长。但人到晚年,历经世事沧桑,家愁国恨交织一体,乃至于这所伤之“情”凝结了包括爱情在内的很多情绪在内,又借爱情这一憾事而生发开来,故而格外哀婉动人。
小结
对于陆游沈园系列诗歌,近人陈衍曾有评论:“无此绝等伤心之事,亦无此绝等伤心之诗。就百年论,谁愿有此事?就千秋论,不可无此诗。”[15]陆游这组沈园诗意蕴丰厚,律绝古体兼具,是作者真情真性、艺术才能与深厚学养的综合体现,不独是宋诗中弥足珍贵之作,更是诗歌史上光耀古今之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