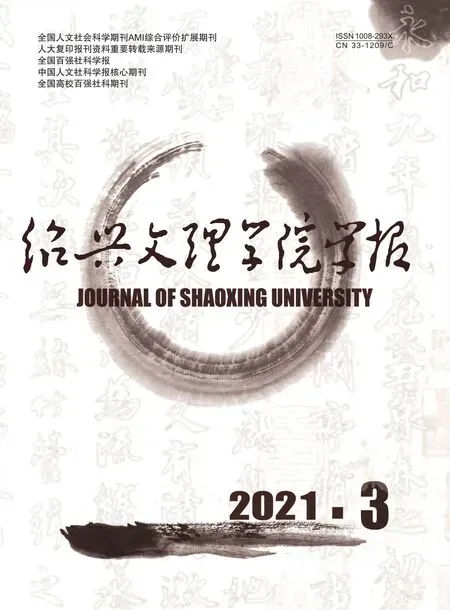《燕丹子》士子群像论
叶 岗 徐丹丹
(绍兴文理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燕丹子》是成书甚早的优秀小说,作品人物总计14个,可按五个层次来归纳:第一层,太子丹、荆轲,作品对这两个主要人物形象,作了重点描绘;第二层,田光、麹武、樊於期,他们是构成全篇三部分的次要人物;第三层,秦王,作为暴虐者的反面形象出现;第四层,夏扶、宋意、武阳、高渐离,他们的身份为太子客或荆轲友,其群像在篇中也有适当表现;第五层,中庶子蒙、美人能琴者、鼓琴之姬人、屠者,他(她)们近乎背景式人物,只起穿针引线的作用。除此之外,真正背景式人物还有秦廷之上的“百官”或“群臣”,可以不计算在内。《燕丹子》涉及人物虽多,但主要以太子丹和荆轲为主,核心情节是为燕国复仇而行刺秦王。在筹划行刺阶段,人物关系集中在太子丹之与麹武、田光、荆轲三人之间的递接上,即由麹武引出田光,由田光引出荆轲。
上述五个层次的人物,除太子丹和秦王之外,若纯以人物职业身份而论,则大多为“士”,他们是荆轲、田光、麹武、夏扶、宋意、武阳这6人;若衡之以人物在篇中所展现出来的精神品格而论,则秦之叛将樊於期、易水击筑的高渐离,亦可以“士”待之。如此,则文中所谓“士之群像”,包括了以上8人。下面针对群像中的重点人物,就其士节和士行作些讨论。
一、士节卓绝,人物具备道德感
战国公子王孙如“四君子”有招养门客的传统,门客汇集帐下,品类不一,既有鸡鸣狗盗等一技之长的食客,也有择主而事、致位将相的客卿。一般来说,在“主二客一”的历史环境下,除极少数之外,门客的人生目标大多从利益出发,求富贵、取尊荣、建不朽之功业,他们往往依附某个主子,将自身工具化,达成豢养与被豢养的关系。
但是,在《燕丹子》中,我们却看到了卓然不同的门客群体,他们中的殊绝者,所展现出来的人格情操,达到了孔子所谓“士志于道”(《论语·里仁》)的精神高度,有担当道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在《燕丹子》的士子群像中,无论是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他们身上大多表现出原始儒学所倡导的崇高道德感。尽管由于作品特定题材的原因,人物的类型可以归结为出仕之士,即他们都先后聚集于太子丹营垒中,为其奋斗目标而驰力。这就不像后世那些专意反映士子生活的大部头作品如《儒林外史》,有着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更为复杂多样的题材,能够充分刻画各类士子尤其是出仕者和归隐者的复杂面貌。但是,即便如此,《燕丹子》在类型单一的士子群像中,还是将这些人物的性格特殊性尤其是道德个性,较为出色地反映了出来。其中,个别的形象,可位居文学史一流人物形象的画廊里。作品中,田光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若按常人的标准,在《燕丹子》的士林里,道德感最强的是田光,而且作品对此的刻画也很集中凝练,富于力度,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是由太傅麹武引荐给太子丹的,介绍语是“深中有谋”[1]5,即心意深沉且谋略出众。此语出自太傅之口,评价不可谓不高。但是,作品之后的形象刻画,在展现这两方面特征之外,给人以莫大惊喜的,便是深刻地描写了他道德出众的一面。
作为谋士,在太子丹向他介绍情况、表达抗秦之志、先行否决合纵之计以后,田光沉稳地以“此国事也,请得思之”作为回应。之后,在太子东宫之“上馆”滞留三月,竭尽全力,替太子设法。他经过观察和判断,认为要完成太子丹计划中事,不仅自己难以胜任,而且现有太子丹帐下门客也不能挑起重任。作品记载了他与太子丹的对话:
田光曰:“微太子言,固将竭之。臣闻骐骥之少,力轻千里,及其罢朽,不能取道。太子闻臣时已老矣。欲为太子良谋,则太子不能;欲奋筋力,则臣不能。然窃观太子客,无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阳,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为人博闻强记,体烈骨壮,不拘小节,欲立大功。尝家于卫,脱贤士大夫之急十有余人,其余庸庸不可称。太子欲图事,非此人莫可。”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灵,得交于荆君,则燕国社稷长为不灭,唯先生成之。”[1]7-8
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田光对自己和“太子客”的评价,由于这些评价与太子丹之行刺拟议有着很深的牵连,故选人尤其是选对人,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太子丹否决合纵之计在先,故而田光在说到自己之时,才有“欲为太子良谋,则太子不能”;因为自己“已老”而难以出任刺客,故有“欲奋筋力,则臣不能”。至于评价他人,后人包括历代类书所交口称誉和引录的“血勇之人”“脉勇之人”“骨勇之人”“神勇之人”之词,就出于田光之口。真实的田光,其能力如何,我们已无从得知,但由这些语词所显示出来的鉴识人才的观察和判断能力,让我们对田光作为一介智略之士的出众才能,刮目相看。
再看田光向荆轲介绍太子丹之语:
遂见荆轲,曰:“光不自度不肖,达足下于太子。夫燕太子,真天下之士也,倾心于足下,愿足下勿疑焉。”[1]8
这里须重点关注的是“天下之士”的评语。此词亦甚为精炼,蕴意也很出色,但并非首次出现于《燕丹子》,如《战国策》就出现过多次。词语意思有两个方面,一是字面意思,即来自天下各处的士子,这较为多用,包括汉初贾谊也在这个层面使用此词;二是指胸怀天下之志的士子,类似于后代范仲淹所曰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思,《战国策·赵策三》即在这个意蕴上运用此词评价鲁仲连的品格。田光以“天下之士”许之于太子丹,编作者的用意应该有三:一是太子丹的世俗身份实际是君而不是士,但田光称其为士而非为君,意在视太子丹为同道人,这说明田光的价值倾向是重人品而不重阶层门第;二是对太子丹精神品格和抗秦行为的褒扬,将其拟议之事评价为有功于天下;三是赞人为有天下之志者,自己亦应是有天下之志者,田光真是这样一个人。
如此,作为艺术形象的田光,作为谋士或策士,其才能主要体现在目光如炬,善于观察人、分析人、评判人上。还有,从麹武引荐田光到田光引荐荆轲,我们发现,在编作者的心目中,古代被称为“士”者,大概是一个广交天下朋友的人。然而,作品对田光所浓墨重彩予以表现之处,则是其高度的道德感:
田光遂行,太子自送,执光手曰:“此国事,愿勿泄之!”光笑曰:“诺。”[1]8
田光谓荆轲曰:“盖闻士不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时,言:‘此国事,愿勿泄!’此疑光也。是疑而生于世,光所羞也。”向轲吞舌而死[1]8。
太子曰:“田先生今无恙乎?”轲曰:“光临送轲之时,言太子戒以国事,耻以丈夫而不见信,向轲吞舌而死矣!”太子惊愕失色,歔欷饮泪曰:“丹所以戒先生,岂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杀,亦令丹自弃于世矣!”[1]10
以上三段,将田光自杀的前因后果叙述得很清楚。从写法上看,后两段略显重复,显示出在小说发生之初编作者于描写人物对话方面的不成熟。但是,第一段极为精彩,于简短的叙事中,深埋伏笔,且人物情态毕现。下面,我们针对性地来分析田光的士节表现。
第一,田光自杀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他评判自己谓“太子闻臣时已老矣”“欲奋筋力,则臣不能”,清楚地写出了他主观上竭力想为太子丹所用、投身于抗秦大业的心情;何况,他承受过太子丹之礼遇,“侧阶而迎,迎而再拜”“三时进食,存问不绝,如是三月”,对田光这样一个有着高度道德自觉心的人来说,这些礼遇当然会促发其“忠”义,并内化成压力。压力越重,效忠的心态就格外强烈。“忠”的要义在于一个“尽”字,办事尽力,死而后已,如先儒所说的那样,“尽己之谓忠”[2]72。他向太子丹举荐荆轲,这固然是一桩尽忠之举和一项贡献,但自己若因“老矣”难“奋筋力”而置身事外,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遗憾和不道德的事。故而,以死明志,以死表忠,显示其欲为天下图存而献身于抗秦之壮烈事业,倒是一种最好的选择。要补充的是,田光在此尽忠的对象,非为太子丹个人,而是由其发起组织并将要实施的抗秦大业;其次,对田光来说,荆轲既已是执行太子丹行刺计划之不二人选,但他到底能否成行、抗秦意志如何、中间是否会发生意外和变故等等,这些都不是田光所能决定的,故而,他只能以自杀行为来推动荆轲去完成刺杀任务。至于他的自杀对荆轲的灵魂会产生怎样的震撼和触动,田光基于对荆轲的了解,是能够把握得了的。因此,以自杀来坚定荆轲之心,这也是一种忠于抗秦大业的选择。田光“吞舌而死”这一幕,其价值意义和壮烈之态,犹胜于“北乡自刭,以送公子”[3]的大梁夷门监者侯嬴;最后,太子丹送别之际的戒言“此国事,愿勿泄之”,成为导致田光“吞舌而死”的直接原因。在《燕丹子》中,这是最令人唏嘘不已的情节。尤其令人过目难忘的是,田光回应太子丹叮嘱的表现为“笑曰‘诺’”,此一“笑”字,真是神来之笔,不知埋藏着多少无尽之言、难尽之语。
第二,田光之“疑”与“信”及其道德选择。在前引之后两段中,田光口中出现了两个“疑”字,即“闻士不为人所疑”“是疑而生于世,光所羞也”;太子丹口中出现了一个“疑”字,即“丹所以戒先生,岂疑先生哉”。对于“疑”字之反面,荆轲则理解为“信”义,即上引之“言太子戒以国事,耻以丈夫而不见信”,所谓“不见信”即为“疑”义。如此看来,田光是将“被疑”视为人生的耻辱,而将“见信”作为比生命更为神圣的对象来看待的。是“被疑”和“不见信”直接导致了田光“吞舌而死”的悲壮之举,此举将士节的道德高度推升到了一个极致。汉初邹阳在《狱中上梁王书》中有“臣闻忠无不报,信不见疑”和“士有伏死堀穴岩薮之中耳,安有尽忠信而趋阙下者哉”之语,头尾两处很好地概括了这篇上书的主题,亦与田光之士节所体现出来的“忠”“信”观念若合符节。
在原始儒学所倡导的君子之德中,“忠”“信”是基本的义则。关于“信”,《论语》和《孟子》都有不少语录: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2]59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2]336
孟子曰:“君子不亮,恶乎执?”[2]346
上面所言之“信”有二义,即信任、信用。最后一条的“亮”,同“谅”,诚信义。在此,先儒将“信”,作为“人”“天爵”(即人类精神世界)、“君子”的基本品格。田光所言之“闻士不为人所疑”“是疑而生于世,光所羞也”与孔孟之道相通,即视“信”为立人之道从而视“被疑”作为斫丧生命的依据。
由于“信”往往与言论有关,而且太子丹戒以“愿勿泄”,故而田光所采取的自杀方式是“吞舌而死”,以保全“不为人所疑”之节操。田光此举,最主要的因素,是缘于极其强烈的道德内驱力,他将不被太子丹完全信任视为自己的道德污点,故以自杀这种最为极端的方式来打消太子丹之“国事”或被泄的疑虑,以此清除投射在自己身上的污点,证明自己清洁无瑕的士节。
在《燕丹子》中,有着不少古风盎然的人物,田光即为其一。他的重信死节,犹如伯夷、叔齐避周而饿死首阳山,弃生以立其意;又如介子推却晋文公之赏而远遁深山,匿迹以彰其志。编作者以深沉委婉之笔描述了田光之死,从而将其定位于道德志士的历史坐标上,清除了蒙在战国游士身上的部分污垢;同时,通过将田光之死组合在抗秦活动之中,彰显其生命的价值,从而将其嵌刻于抗秦义士的行列。
第三,田光的遗生行义与“大信”有关。先儒所谓的“信”,有“大信”与“小信”之别。前引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与此相应的是,孟子也有类似议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燕丹子》中“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于乡曲;马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于服舆”,也同于此义。这些与孔孟推崇“信”的其他言论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等表面上形成了矛盾,其实,解开矛盾的要义乃在于孟子的“惟义所在”之语,即以是否合乎道义来对“信”进行区分。如此,则“信”既是儒学的核心观念之一,亦是士子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又不能拘泥固执于“信”而不知变通,要依据是否合乎道义来通权达变。也就是说,要大信,而不要小信;要在原则问题上讲信用,而不要拘泥固守于小节上的一成不变。
田光自杀的原因我们前面已有分析,其直接原因是为打消太子丹的疑虑,间接原因是彰显其抗秦之志和借此激励荆轲。这些都与抗秦大业有着内在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以田光行义而死为标志,行刺之事便正式拉开帷幕。试想,如果太子丹疑虑未消,时刻提防着“国事”被泄,则整个计划将无法贯彻和实施;如果荆轲未曾入燕或中间出现犹豫不前等变故,则行刺计划也将陷于停顿;如果田光不以生命为代价而表其效忠于抗秦伟业,则无法真正激励太子丹所团聚起来的众士,以杜绝他们置身事外的任何念头。如此,则可以说田光立信而合于时务,因“大信”而一死重于泰山,其意义,远远大于齐桓公以四百里地而见信于天下。
正因为田光的艺术形象,闪耀着光辉而厚重的色彩,充满着独特的魅力,故而后世还有类似以《田光传》为题的作品出现(1)“李远有《读田光传》诗,可见唐代还有《田光传》其书。”参见中华书局1985年程毅中点校本《燕丹子》“点校说明”(第5页)。,或许是裁割《燕丹子》之田光部分而以《田光传》命之。作品中的其他人物,在士节表现上,也精彩夺目,令人沉吟不已,如荆轲之临大利而不忘其义、樊於期之为复仇而不避其难、夏扶之忠于国事而舍生取义。在这些战国末期的群士身上,体现出人类精神所可能达到的历史高度。
二、士行毅然,人物赴难不辞
行刺秦王,其实质,是为天下主持公道以反抗暴政的正义行为。不同于《战国策》和《史记》所书那些遍谒列国诸侯而求取富贵的游士们,《燕丹子》中的群士则争先恐后投身于这一极其惨烈的正义之举。这其中,表现出他们决烈的心志和迥异于常人的生命观念。
原始儒学的士文化具有实践性品格,强调士子要为天下百姓承担起更多的义务,济世救人、扶倾持危,当是有德之士应尽的现实化责任。在这方面,孔子寻周道于列国,孟子游说诸侯王,都给天下士人树立了榜样。
在士行方面的表现,《燕丹子》中最出色的人物,当是荆轲。也正是因为荆轲的存在,作品才具有了激荡后人灵魂的强劲生命力。
有关荆轲身世和经历,作品为集中表现主题而不横生枝蔓,只在人物对话中给了我们简单隐约的提示:
尝家于卫,脱贤士大夫之急十有余人,其余庸庸不可称[1]8。
轲出卫都,望燕路,历险不以为勤,望远不以为遐[1]10。
前一句,出现在田光的推荐语中,而后者,则出于荆轲自道。它们告诉我们三方面情况:一是荆轲来自卫国,卫国在战国时期先后被魏、秦所掠,尤其是秦国在始皇帝六年(前241年)侵占卫之东郡、废卫元君之后再杀之。《史记》载公元前241年“秦拔我朝歌。卫从濮阳徙野王”[4],这种小国被大国辗转侵占的辱国之痛,当是荆轲投身刺秦大业的思想基础;二是荆轲出发地。卫国屡次迁都,句中荆轲自谓“出卫都”,当指卫之西周古都朝歌(今鹤壁),而非指迁徙后的首邑帝丘(今濮阳)或野王县(今沁阳)。古代朝歌之地,还存有荆轲冢;三是荆轲颇有君子之风,能救急扶难。田光夸其“脱贤士大夫之急十有余人,其余庸庸不可称”,是说荆轲多有仗义之事,其中数得上的是十多起帮助士大夫的事,可见荆轲日后的赴秦行刺绝非偶然,而是出于其品格和习性。值得一说的是,卫地自古多君子,如许穆夫人(约前690年—?)、子路(前542年—前480年)、李悝(前455年—前395年)、聂政(?—前397年)、吴起(前440年—前381年)、商鞅(约前395年—前338年)、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等,史不绝书。荆轲远程入燕,既出于田光的邀约和对太子的褒扬,也缘于荆轲自身的行为选择。
战国时期主客之间多有以势利交结者,然荆轲与太子丹结交的基础在于互为知己的关系,这就给荆轲所展现出来的赴难不辞之行为,奠定了士行道义的性质。关于两人的知己关系,篇中曰:
荆轲曰:“有鄙志,常谓心向意投,身不顾;情有异,一毛不拔。今先生令交于太子,敬诺不违。”[1]8
轲言曰:“田光褒扬太子仁爱之风,说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厉天,美声盈耳……今太子礼之以旧故之恩,接之以新人之敬。所以不复让者,士信于知己也。”[1]10
今轲常侍君子之侧……太子幸教之[1]12。
今荆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国。今丹以社稷干长者,不知所谓[1]12。
这一关系的开始,得自于田光分别在两人面前,所作的相互介绍:
光所知荆轲,神勇之人,怒而色不变。为人博闻强记,体烈骨壮,不拘小节,欲立大功。尝家于卫,脱贤士大夫之急十有余人,其余庸庸不可称。太子欲图事,非此人莫可[1]8。
夫燕太子,真天下之士也,倾心于足下,愿足下勿疑焉[1]8。
荆轲与太子丹的知己关系体现在:(1)由“士君子”田光所介绍和促成,义胜金石,非比寻常;(2)荆轲素有“心向意投,身不顾”的想法和作风,这当是两人建立起知己关系的基础,也是他大义凛然、不顾安危而行刺秦王的心理原因;(3)荆轲借田光之言称太子有“仁爱之风”和“不世之器”,甚至后来以“君子”许太子,说明两人合作的基础已从知己关系发展到为着天下大义而共同奋斗的关系;(4)太子丹亦以“荆君”“长者”许荆轲,并将“社稷”命运委以荆轲,说明在太子丹这里,也不仅仅将荆轲视为简单的知己和朋友之关系,而是共赴国难的一体关系。
为了展现两人间关系的进展与深化,作品多采用场面描写的方法,铺叙了迎候、酒宴、“黄金投龟,千里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槃”等事例,一方面表现太子丹对荆轲的态度和心意,另一方面用以描述荆轲对太子丹的考察和证验。当然,它们的作用还远不及此。
《燕丹子》在构筑起荆轲与太子丹合作基础的同时,重点则在表现荆轲的杰出行为,这方面也存在着一个变化过程:
将令燕继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1]11。
闻烈士之节,死有重于太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1]12。
今天下强国,莫强于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诸侯,诸侯未肯为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国之众而当之,犹使羊将狼,使狼追虎耳……樊於期得罪于秦,秦求之急。又督亢之地,秦所贪也。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图,则事可成也[1]12-13。
所谓“继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是指施仁政于国内,以期达到“甚得兆民和”[4]的效果。按荆轲初入燕的本意,是想辅助太子丹治理好内部国政,推动燕国的发展和强大,“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霸”,在这过程中,扮演类似管仲之于齐桓公、郭隗之于燕昭王那样的策士角色。然而,随着对太子丹心意、燕国国势和天下情况的深入了解,荆轲对自己在燕国使命之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事实上,秦统一天下、扫荡关东六国的进程,在太子丹归燕后的次年(前231年),便已加速。
作品中荆轲入燕的时间,在前231年或稍后,即太子丹逃归的次年。秦于前230年虏韩王安并灭韩,其他五国上空也战云密布,燕国料亦难以幸免。这种战争环境已容不得荆轲再在燕国从容地设计和实施他的仁政之策,故而,在入燕的第三年,荆轲便将自己的使命定位于“烈士”之职,即重义轻生而愿杀身成仁以挽燕国覆灭危险的人,故有“闻烈士之节,死有重于太山,有轻于鸿毛者,但问用之所在耳”之句。通过与太子丹的对谈分析,荆轲既排除了太子领袖群伦、合纵抗秦的可能性,也摒弃了太子率军队正面抗击秦军的可能性,最后定位到行刺秦王以抗秦的行动上来,“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图,则事可成也”,而完成此事的人选,荆轲则慨然自任,最终怀抱“将海内报仇”的天下公义,出使秦廷,行刺秦王,奏起历史绝响。
所以,荆轲之为刺士抑或“烈士”“壮士”,既非平生之愿,亦非入燕之初衷,而是在与太子丹建立起知己关系以后,出于固有的抗暴之志以及主动为燕国分忧的心理而作出的大义选择。在这主动选择的过程中,荆轲丝毫没有顾及自身的利益和安危,表现出足以令后人敬仰不已的悲剧英雄的风姿。胡应麟评荆轲曰:“轲也,裹匕首入虎狼,万戟九关,声色亡动,至肢体分裂,嬉笑自如,非盖世之勇孰与斯乎?”[6]荆轲大义凛然的英勇士行,比孔子所言之“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上士”之举,还要高出一截;至于多数战国群士的作为,则难以望其项背。作品“易水送别”一节,于重彩浓墨中荡漾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无尽哀思,寄托着壮烈而哀婉的深重情愫。
荆轲之士行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实质,若以先儒之词,可名之谓“士君子”。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超迈于古今士人的高节死义之上的精神力量、为信义和公理而把生命置之度外的精神气概。
在《燕丹子》中,十一次出现“士”字,所谓“勇士”“天下之士”“烈士”“壮士”等等,均非一般的士,而是那种具有士节、士行的特殊的士。这些特殊的士,除了太子丹、田光、荆轲之外,还应包括“当车前刎颈以送”的夏扶、为除“积忿之怒”而自刭的樊於期。若以“士志于道”来衡定,概之以“志士”可也。这些“志士”所共同体现出来的精神力量,在与强秦以欺诈和暴虐吞并列国的行为对比中,在“势”与“道”之争中,建起了另一座价值丰碑。远隔两千多年的历史烟尘,遥想这些品节自高的志士,《燕丹子》为天下公义而刺秦的重要价值,就自然凸显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