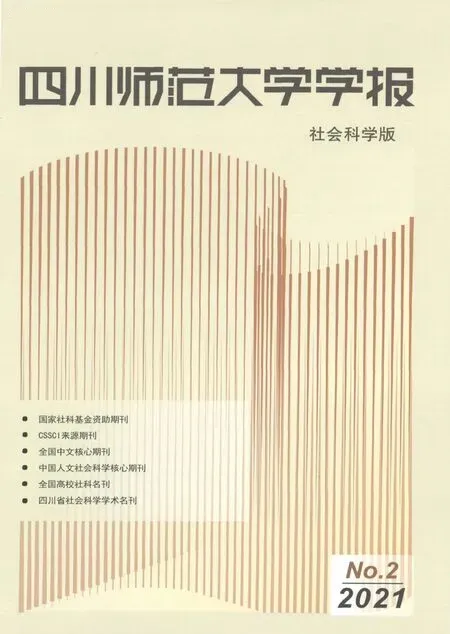清末铁路建设与多方势力的路事博弈
——基于锡良筹办川汉铁路的讨论
潘 崇
近代以来,掠夺铁路修筑权和控制权,是列强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而由此衍生的铁路问题,从来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关涉中外关系以及国家主权的重大政治问题。《泰晤士报》即言,铁路“是一个通商的工具,也是一个征服的工具”(1)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2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424页。。清末铁路问题向为中国近代史学界所重视,属于“传统型”的研究论题。总体上看,既往研究侧重从中外对抗、官民对立的视角,讨论列强对中国路权的侵掠以及官民在路事上的冲突。随着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尤其是新史料的发掘和更多史实的重建,已有认知面临着进一步的学术追问,远非中外对抗和官民冲突所能涵盖。新政时期四川总督锡良主导下的川汉铁路筹办过程,由于涉及多方势力的博弈而呈现出丰富驳杂的历史面相,较大程度地突破了我们对清末铁路问题的既有认知。因此,揭示清政府内部的矛盾纠葛以及官民之间形成的既有冲突又不乏协作的多面关系,无疑是川汉铁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由于四川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且对全国革命形势高涨起到直接推动作用,因而川汉铁路筹办过程以及四川保路运动研究历来受到学界重视,其中最具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当首推隗瀛涛著《四川保路运动史》一书(2)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其它相关成果,可参看苏全有、邹宝刚《近三十年来四川保路运动研究综述——纪念四川保路运动100周年》(《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74-78页)一文的综述。。该书重点讨论了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及演进、四川保路运动始末等内容,同时着力展现清末四川社会整体面貌,对四川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四川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等内容也作了系统梳理,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川汉铁路史打下了坚实基础。此外,还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就川汉铁路筹办情况开展研究(3)杨永指出,川汉铁路改商办后,存在资金来源单一且管理混乱、企业官本位现象严重等问题;黄权生、罗美洁则对宣统元年十月由宜昌开工的川汉铁路建设过程做了梗概式描述;经盛鸿、开云则梳理了詹天佑主持修建川汉铁路及其支持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过程。详参:杨永《从近代企业制度的角度观清末铁路“商办”政策的失利——以商办川汉铁路公司为例》,《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第76-80页;黄权生、罗美洁《清末宜昌川汉铁路建设小考》,《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7页;经盛鸿、开云《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第40-46页。。总体来看,与学界研究清末铁路问题惯从中外对抗、官民对立角度着眼的整体状况相一致,加上史料发掘利用不够,既有研究在视角和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局限。就清政府内部而言,外务部、商部在铁路资本筹集策略上存在歧异,川、鄂两督亦就先修路段及其路权归属问题展开过长时间的讨论和争斗,而上述内容学界几无着墨。就官民关系而言,川籍留日学生与京官关于路事的评骘与献策及其对四川当局的影响,学界梳理也尚不全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锡良档案,详细记录了锡良筹办川汉铁路的始末,系统审读之,可以发现前人对此问题的讨论尚多有未尽之处。故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锡良档案为基本史料,辅以张之洞档案和相关史料集,对锡良主持筹办川汉铁路的诸多细节予以揭示,以期对深入认识清末铁路交通建设的复杂艰巨性以及清末政治与社会状况有所裨益。
一 外务部、商部对川汉路事的策略歧异以及列强对川汉路事的干预
19世纪末,地处内陆的四川开始遭到列强觊觎和入侵,他们妄图攫掠四川铁路修筑权,从而控制中国广袤的西南地区(4)如英国试图攫掠自缅甸、西藏至四川的铁路并进行实地线路踏勘,法国则策划攫掠自越南至四川的铁路。详见: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23),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205-224页。。处此背景,光绪二十九年(1903)闰五月十四日,新简任四川总督锡良在赴任旅次正定之际,即具折提出修建川汉铁路之议,并着重阐发此路对于保固西南边防以及畅通四川物产的重要意义(5)锡良《奏设川汉铁路公司折(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四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第1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9页。。锡良未及到任即有此奏,固然反映出希冀通过铁路建设破解当时四川内忧外患困局的急迫心情,但贸然提请显然失之轻率。以至有论者言:“从现代工程技术的角度来看,锡良没有经过任何可行性论证,就提出了一个工程难度相当高、所需经费非常巨大的工程,已经近于荒唐。”(6)鲜于浩、张雪永《保路风潮——辛亥革命在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更值得注意的是,川汉铁路涉川、鄂两省,其修建理应由川督锡良与鄂督张之洞联衔奏请。锡良起家州县,政治经验丰富,断不会虑不及此。笔者以为,其单衔具奏大致出于以下原因。首先,锡良秉性清刚,“治事以锋厉著”(7)陈灨一《睇向斋秘录(附二种)》,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40页。,此亦可解释缘何未及到任即有修路之奏。其次,锡良曾为张之洞抚晋时属吏,两人“气谊本极契合”(8)周询《蜀海丛谈》,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正编》第1辑第7册,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505页。,张之洞亦颇赏识锡良,“目为循吏第一”(9)翁同龢著、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4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724页。。在锡良看来,单衔独奏,无伤大雅。其三,此际张之洞恰赴京陛见,锡良曾与之协商路事,然张氏忙于议定商约及修订学堂、矿务章程诸事,实无暇细商(10)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抵京、十二月二十二日出京(参见:吴剑杰《张之洞年谱长编(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84、814页)。锡良档案中有一封致张之洞电,言及“川汉铁路自办宗旨,上年在都仰蒙指示”之事。参见:《致湖北张香帅电(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发)》,《锡良督川时外省来往电报》第8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以下简称“所藏”):甲374-5。。尽管锡良单衔独奏有其理由,然无论如何不啻为冒失之举,不仅招致张之洞的不满,更埋下两省合作不畅的隐患。四川机器局总办章世恩曾致电锡良转述鄂抚端方之言:“午帅谈及川汉铁路,奏准自办极好。惟似须两省会衔,通力合作,且免意见。因与午帅至好,饬恩密陈。”(11)《章道世恩自汉口来电(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四日收)》,《锡良督川时本省来往电报》第3册,“所藏”:甲374-20。锡良僚属周询也记述道,张之洞对锡良是举“深致不满”,但凡涉及路事,“鄂方每多为难”,对此锡良“亦悔而无及”(12)周询《蜀海丛谈》,第504-505页。周询曾在锡良督署办理文案前后凡三年,所记应当可信。。
闰五月十七日,外务部在议覆折中肯定了川汉铁路对于盘活四川物产流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也指出该路绵亘数千里,需费数千万,“外人度中国目前财力未逮,蓄意觊觎,终难以空言为久拒之计”,由此主张“俟设立商部后,由商部大臣切实招商,专集华股,力除影射蒙混之弊,以资抵制而保利权”(13)《外务部议覆川督奏设川汉铁路公司折》,邮传部编纂《轨政纪要初次编》,王有立主编《中华文史丛书》第89册,台北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版,第189页。。显然,外务部担心自办该路不仅难成,反给列强插手提供借口,力主由商部主持专集华股。七月十六日,商部成立,并于十月十四日奏定《铁路简明章程》24条。该章程原则上允许中国铁路建设引入洋股,但须由商部批示,并经外务部查核,且“集股总以华股获占多数为主,不得已而附搭洋股,则以不逾华股之数为限”(14)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3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926页。。显然,此办法和外务部“专集华股”的主张形成矛盾。时人已注意及此,如陶湘密报盛宣怀:“川督请示,振公云:‘何外部如此矛盾?’人告以爷之主意。振云:‘且回家再说。’后亦寂然。”(15)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页。振公,即商部尚书载振;爷,即载振之父庆亲王奕劻,时任外务部总理大臣。
七月十六日,锡良行抵成都。经数月考察,锡良“深讶川省百物蕃昌,而民间生计之艰,公家榷厘之绌,皆因商货不畅所致”,遂又于十二月初六日上《开办川汉铁路公司折》。在该折中,锡良强调,尽管川汉铁路工艰款巨,然其修建刻不容缓,必先设官办铁路公司,“然后人人知事之必成,无虑旁扰豪夺,俾集款助路次第可以措手”,并在资本筹集上提出了“先集华商股本,将来推广,或附搭洋股,或添借洋款”的主张(16)《开办川汉铁路公司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六日)》,《锡良遗稿·奏稿》第1册,第389-390页。。在公司人事方面,锡良遴委署理布政使冯煦为督办,成绵龙茂道沈秉堃、候补主事罗度、奏调河南候补道陆钟岱、即补道蔡乃煌为会办(17)《咨两湖督部堂文》,《锡良存川汉铁路奏咨录要》第1册,“所藏”:甲374-27。。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初四日,新任四川布政使许涵度到省,遂任许为督办。由藩司兼任督办,意在统一财权。正如锡良所言:“公司造端宏大,必资群策而后成,财政隶于藩司,尤应兼综并理。”(18)《委许藩司督办川汉铁路公司片(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四日)》,《锡良遗稿·奏稿》第1册,第400页。显然,锡良面对外务部、商部指令不一状况,未待清廷允准即先设公司,实属先斩后奏。需注意的是,锡良所言“附搭洋股”之语,仅为不拂部意而已,揆其本心则坚持自筹资本。一个例证是,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间,锡良曾致电外、商二部说:“铁路章程内开,无论华洋官商均可按照新章办理,系为推广路轨,裕国便民起见,至为钦佩。川汉一路局外争先恐后,互相猜忌,设非自办,恐中立不易调停。且拳乱甫平,川民浮动,借端便发,保护为难。”(19)《为遵章筹办川汉路事(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案卷号2-04-12-029-0996。
列强本就对四川路权觊觎已久,在探得中国欲自办川汉铁路消息后,英、美、法等国随即群起干预。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照会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要求川汉铁路若借用洋款或允许外人修筑,当先向美国公司磋商。对此,力主专集华股的外务部,“深恐外人揽办,自失利权”,“均经竭力驳阻,议归自办”(20)《外务部议覆(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十七日收)》,《锡良存川汉铁路奏咨录要》第1册,“所藏”:甲374-27。。英国提出贷款要求,并准备遣派工程师至川、鄂测量地段。对此,锡良专门电请外务部,迅速照会英国驻华公使焘讷理予以制止(21)《四川总督锡良致外务部请速照会英使焘讷理制止英人在川测量地段电(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初一日)》,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册,第240页。。随着《简明铁路章程》的颁布,列强投资川路的欲望愈被激发。十二月间,外务部致电锡良,通告“此路屡经英、美两国请办,法国亦有此意,均告以中国现拟自造”,指示“尊处招商承办,切勿掺入洋股,以免纠缠”(22)《北京外务部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收)》,《锡良督川时外省来往电报》第3册,“所藏”:甲374-5。。可见,外务部为维护铁路利权、避免外交纠纷,坚决反对洋股掺入。但是,商部则致电锡良,虽仍强调可招洋股,却规定不得另借洋款,“原奏内称‘照商部先集华股,将来或附搭洋股,或添借洋款’等语,查本部奏定铁路章程第六款载:‘不准于附搭洋股外另借洋款。’诚以洋股可分招各国散商,事权由我操纵;洋款则或需抵押,流弊滋多……改正为要。”(23)《商部来电(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收)》,《锡良存川汉铁路奏咨录要》第1册,“所藏”:甲374-27。
迨至川汉铁路公司成立,列强掀起了新一轮干预。光绪三十年正月,英国驻成都总领事谢立山致函锡良,再提由英国负责查勘线路的要求:“筑路先须查勘,而查勘一事又非外国工程师不能尽职。川汉铁路如有需延本国工程师查勘之处,本总领事亦无不可代为筹划。”(24)《谢领事来函(光绪三十年正月初五日收)》,《锡良存川汉铁路奏咨录要》第1册,“所藏”:甲374-27。同时,各列强重点就资本一项提出要求。四月间,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照会外务部,声称上年奕劻曾承诺中国若不能筹集全股开办川汉铁路,“所需之外国资本,皆在英、美二国借用”,同时要求成都至叙州、泸州、万县三支路归其承办(25)《英使致外务部预定川汉铁路借款照会(光绪三十年四月)》,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4页。;法国更是“强横无状,威逼不一端”,在资金、工师两方面提出要求(26)《四川留日学生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书(光绪三十年十月二十一日)》,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8页。。六月间,法国驻成都总领事安迪照会锡良,声言法国华利公司“刻在贵国外务部商定‘招股勘路代办合同’,将次就绪”,该公司已集款38亿法郎,由其参与修建川汉铁路最为适合(27)《法领事致锡良包揽川汉铁路款、工照会(光绪三十年六月)》,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5页。;德国驻华公使穆默亦向外务部提出无理要求,强调川汉铁路“各国人民均应一律同沾利益”,自办办法“应不准行”(28)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3册,第1072页。。
对于各国干预,外务部在议驳的同时,指示锡良“坚持勿允”(29)《外务部来电(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二日收)》,《锡良督川时外省来往电报》第4册,“所藏”:甲374-5。。事实上,锡良料及列强必将群起干预,在筹办路事之初即树立“不肯甘心退让”(30)锡良曾致函山西巡抚俞廉三说:“川省铁路外省久已垂涎,昨始奏准自办,以杜觊觎。现正创设公司,分途招股,明知智小谋大、力小任重,然处此竞争世界,力求进步,日寸则寸,不肯甘心退让也。”见:《拟致俞廙帅》,《锡良督川时函稿》乙册,“所藏”:甲374-113。之志。在这一点上,中央部门和四川当局保持了高度一致。光绪三十年正月初六日,锡良覆函英驻成都总领事谢立山,指出招股、勘路、筹款等一切事宜,“均札饬公司妥慎经理,以专责成”(31)《覆谢领事函(光绪三十年正月初六日发)》,《锡良存川汉铁路奏咨录要》第1册,“所藏”:甲374-27。。四月间,锡良又照会各国,声明川汉铁路“系奏定川省自办之路”,且公司已派员实地测量(32)《法领事致锡良诘问川汉铁路何人主政照会(光绪三十年七月)》,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6页。。七月,川汉铁路公司声明:“本公司此次经营川汉铁路,一切均系自办,尚无须借助于人;即将来万一改议,彼时亦当体察情形,斟酌办理。”进而义正辞严地批驳了法国驻成都总领事安迪的无理要求:“贵领事于本公司创办伊始,动以笔墨相诘辨,不特有碍交谊,将来虽有应商之件,亦不便奉商矣。”(33)《川汉铁路公司覆法领事声明铁路自办照会(光绪三十年七月)》,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7页。后者则辩称中国政府强调自办的同时“忽云‘将来万一改议’”,此实为“欺藐敝国”,而“动以笔墨相诘辨”一语更是铁路公司与法国政府“绝交之明证”,进而施其恫吓狡谋:“不论贵督办升迁何省,本领事亦电知敝国钦使,惟贵督办是问!”(34)《法领事覆川汉铁路公司路政结局惟督办是问照会(光绪三十年七月)》,戴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8页。
毫无疑问,外交交涉仅能对列强干预川汉路事做出有限抵制,欲图杜绝外人觊觎之心,并使自办路事落到实处,归根结底还是需要解决资本的难题。
二 川籍留学生和川籍京官建言路事以及川鄂协商集股办法和先修路段
光绪三十年正月间,铁路公司督办、会办诸人致函锡良,提出“百两为一股,凡三十万股”的集股计划,并汇报官商绅庶“咸知此项路工实自保全蜀利权,刻不容缓”,对集股自办颇表认同(35)《督、会办川汉铁路司道为详请事(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七日收)》,《锡良存川汉铁路奏咨录要》第1册,“所藏”:甲374-27。。然而,川汉铁路长达4000余里,需费至5000万两以上,川省民众虽态度积极,但并不能消解资金筹措之困难。实际上,即便是锡良本人,对于四川自筹铁路资本亦信心不足。早在光绪二十九年十月间,锡良就致电商部,陈请派员至新加坡等地商埠招集华股(36)《锡良致商部请派员赴新加坡等地募集华股电(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二十日)》,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册,第266页。。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四日,他又致电外务部坦承:“招集华股即不获,而借洋款亦必权自我操。”(37)《致外务部电(光绪三十年四月初四日发)》,《锡良督川时外省来往电报》第4册,“所藏”:甲374-5。显露出对自筹资金修路并无十足把握之心理。
这一时期,川籍留日学生怀抱“中国失一省之路,即失一省之权”的忧患意识,感戴锡良筹建川汉铁路实属“事制机先”,但又对“资本久未鸠集,工程久未兴行”深为不满,直言“有公司而无资本,则等于无公司而已”。因而,光绪三十年九月十四日,川籍留日学生300余人专就川汉铁路事集会,先就力量所及认筹4万余两,并愿承担募劝30万两之责。会后,川籍留日学生致书锡良,提出如下建言:首先,铁路公司改官办为官商合办:“举此大业,必非徒藉商股之所能成,亦非徒仰官款之所可集,故必出于官商合办”;其二,先修宜昌至重庆段,主张将川汉铁路分为汉口至宜昌、宜昌至重庆、重庆至成都三段,并建议先修宜重段,原因在于此段“水道艰阻,不便交通,较汉宜一段为尤急。且路成之后,运转货物较多,获利更速”(38)《留学东京四川学生为川汉铁路事上川督锡制军书》,《新民丛报》1904年第9期,第95-97页。。从路事发展进程来看,上述建议基本被官方采纳。
与此同时,时人亦要求川汉铁路早日开工。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三日,军机大臣字寄锡良:“有人奏四川铁路关系大局,宜及早开工,以工代赈等语,着锡良体察情形。”(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0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79页。两个多月后,川、鄂方就招股办法及路线勘测等问题展开磋商。十二月初五日,锡良致电张之洞,指出四川路款筹集途径拟分集股、按租抽谷两种:“现拟集股章程,以五十两为一股,周年四厘给息,路成分红,劝令各省官绅商民出资入股;并仿湖南绅议按租抽谷,百中抽三,填给股票。”同时,征询张氏对川、鄂交界路线设置的意见:“窃拟从大宁经巴东至宜昌,不知尚有捷径否,并求示遵。”(40)《致湖北张香帅电(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发)》,《锡良督川时外省来往电报》第8册,“所藏”:甲374-5。初七日,张之洞覆电,认同集股自办“最为上策”,但同时接连抛出数问:“惟路太长、工太巨,此路在川境内取道何处,入楚境后取道何处,已筹定否?全路共长若干里,每里需费若干,已略加估计否?川省谷捐每年能筹款若干,已有约数否?”在路线设置上,张氏则与留日学生一致,主张先修万县至宜昌段,认为如此一方面可收经济之利,“从来铁路办法,皆先从有贸易货物处办起,修成一段即可收一段运费。川汉之路必宜先从万县至宜昌一段下手,以避三峡众滩之险,商货人客皆多,获利较易……方有养路之资,以后集股亦易”;另一方面亦可有效避免外人干预,“自万至宜,此中间一段我已兴工,则长江上下外人即无从插手,余路可听我从容布置矣”(41)《致成都锡制台(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七日发)》,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23册,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638-640页。。
经与张之洞协商,锡良于十二月十三日具折,再次强调自办原则,即“不招外股不借外债”,“非中国人之股,公司概不承认”;在路线规划上,先修宜昌至万县段,如此“可避峡江覆溺之患”,亦可使“商货顿易流通,轨料均便输运”(42)锡良《川汉铁路集股章程折(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锡良遗稿·奏稿》第1册,第455页。。折后附《川汉铁路集股章程》6章55条,规定铁路股本的四个来源:一是认购之股,“凡官绅商民自愿入股冀获铁路利益者”,五十两为一股;二是抽租之股,“凡按租抽谷入股者,即作为抽租之股”,业田之家无论祖遗、自买、当受、大写、自耕、招佃,收租在十石以上者百分抽三;三是官本之股,即由国家库款拨作股份者;四是公利之股,即铁路公司开办“别项利源”而“收取余利,作为本公司股本者”(43)《川汉铁路总公司集股章程(光绪三十年十二月)》,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4、35、35、38页。。上述主张获得清廷认可。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月间,军机处将锡良原折及集股章程交商部、户部、外务部议覆,三部在议覆折中认同其议,仅就章程条文提出若干意见:“原章有抗违不完,提案追究之条,若使办理稍有未善,抑勒强派,在所不免”,同时提请锡良充分行使督饬之责,以免各州县发生需索情事(44)《商、户、外务等三部会奏议覆〈川汉铁路集股章程〉折(光绪三十一年正月)》,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1页。。同时,集股办法也颇得四川绅民认同,且不乏个别人持乐观态度。如溥利煤矿公司总办杨朝杰即认为,“四川地大物博,筹款招工皆非所难,煤铁木石亦取之裕如”,就筹款而言,以川省之力当能计日程功:“全省百六十二府厅州县,七千九百万丁口,除去妇女一半,余四千万,又除老弱一半,余二千万,又除贫苦一半,实余一千余万。每人年捐一钱,亦可获银百万余。”(45)《溥利煤矿公司总办候选知县杨朝杰谨禀(光绪三十年)》,《锡良存川汉铁路奏咨录要》第6册,“所藏”:甲374-27。为发挥上行下效的示范作用,锡良带头认筹20股,并呼吁各府厅州县按年认股,“以资集腋,而为民倡”(46)《四川总督部堂锡行知公司通饬各府厅州县派认铁路官股札稿(光绪三十一年正月)》,谢青等主编、王嘉陵审订《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四川保路运动史料书影汇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然而,事实上,川民认购股票并不积极,“民自行承买之股票殆寥寥焉”(47)《四川留日学生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光绪三十二年)》,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47页。。此时,锡良对于筹款愈加缺乏信心。锡良档案中有两封写于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二月间的电文,颇能显露其心境。十月十三日,在《致川籍京官电》中,锡良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自筹资本的不确定性疑虑:“绅耆妥议,多以分年按租筹款、不借外力为词,果能办到,富强基础,蜀开其先,岂非大幸?”(48)《致川省京员电(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三日发)》,《锡良督川时外省来往电报》第7册,“所藏”:甲374-5。十二月初八日,在《覆湖北张香帅电》中,他也直言:“川省筹款之法,惟集股、抽谷两层,抽谷岁约可得三百万,集股尚无把握。”(49)《覆湖北张香帅电(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八日发)》,《锡良督川时外省来往电报》第8册,“所藏”:甲374-5。这就为之后川汉铁路公司的改制埋下了伏笔。
更为棘手的是,尽管川、鄂两省对于先修宜昌至万县路段并无分歧,然在此路段如何修建的问题上则颇起争执。起初,张之洞鉴于川汉铁路“全路之艰巨”而“力主两省合修”(50)《度支部主事杜德舆为川汉铁路事呈都察院代奏折(三续)》,《申报》1907年10月14日,第3张第10版。,先修之宜万段亦按此办法规建。进入光绪三十一年后,张之洞“屡接锡电称及川绅面称”,力主由川代修宜昌以上鄂境铁路(51)《湖广四川总督部堂张、锡会奏为筹办湖北境内川汉铁路折稿(光绪三十二年正月)》,谢青等主编、王嘉陵审订《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四川保路运动史料书影汇编》,第47页。。锡良致电张之洞解释,“以川款代修鄂路”,乃意在避免两省分修“易致参差”之弊(52)《致湖北张香帅电(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发)》,《锡良督川时外省来往电报》第12册,“所藏”:甲374-6。。其时,四川绅商虽不乏主张川鄂“各修各境”者(53)如胡峻即主此议,据锡良致电张之洞说:“昨经公司绅董集议,据称前因胡雨岚来电各修各境,遂拟先修万渝、成资两段,取其成功稍易,获利较速,人情歆动,集款再修。”见:《致湖北张香帅电(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发)》,《锡良督川时外省来往电报》第12册,“所藏”:甲374-6。,但绝大多数四川绅商却力主代修,甚至“未经商明,即拟由重庆修至宜昌,以便商贾”,从而形成四川绅商内部对“以川款代修鄂路”的意见分歧。
之所以上自川督、下至绅商普遍力持“代修”之议,主要出于以下原因:一是“非从宜昌修起,则川民疑惧”,所谓“鄂境不修,则川路无用,必致认捐者中悔,招股者裹足”;二是川路运机运料必由宜昌入手,否则“转输不便,川路亦将无可施工”;三是宜昌至万县约一千里的路段皆系连山大岭,“工作极艰,费用极钜”,而湖北近年财力“已忧枯竭”,且方议修粤汉铁路,“鄂省所应分任续路造路之款已属不资,则接川之路一时断难并举”。对于四川代修鄂境路段之议,“鄂省闻之,众情甚为不惬”,特别是鄂籍留日学生,“龂龂以省界所在即权利所关,尤力主画境分修之说”。(54)以上引文皆引自:《湖广四川总督部堂张、锡会奏为筹办湖北境内川汉铁路折稿(光绪三十二年正月)》,谢青等主编、王嘉陵审订《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四川保路运动史料书影汇编》,第46-47页。
由于四川集股成效不佳以及川鄂两省在宜昌以上鄂境路段如何修建问题上迟迟未决,致使路事陷入停滞。自光绪三十一年始,四川民众普遍起而要求川汉铁路改归商办。长寿县举人张罗澄等呈请督察院代奏,指出川汉铁路“议办至今已一年有余,其路线所经并未绘图入奏,至工程款项及一切详细章程均未核定”,同时在管理上也存在重大缺失,进而提出川汉铁路以川中商民之款修建,理应正名为民办铁路,如此“既可杜各国之觊觎,亦可享自有权之利”,若仍为官办,“局面万一有事,如赔款磅亏之类,外人指索抵押,其将何以谢之”,进而重提锡良单衔独奏事,将之视为川、鄂两督“情势既属暌隔,意见尤多龃龉”之证明(55)《照录四川举人张罗澄等呈》,《锡良存川汉铁路奏咨录要》第12册,“所藏”:甲374-28。。川籍京官工部主事王荃善也提出商办要求,其理由有二:一是四川民众意愿所在,川民“恐以频年节省之膏血,一旦委诸虚縻,匪惟将来之股息难期,即现在之捐资无着”,二是可有效抵制外国干预,所谓“民款官办,外人可以藉词干涉;民款民办,则不独抵制于将来,兼可收绅商交劝之益”;同时指出川汉路事,川、鄂两督兼顾为难,应援芦汉铁路例,由清政府简派专员督办(56)《照录王荃善呈》,《锡良存川汉铁路奏咨录要》第13册,“所藏”:甲374-28。。另外,还有人以“川省官权尊重,谷捐激变,官幕盘踞,虚耗巨款”为由弹劾锡良(57)张之洞、锡良《川汉铁路毋庸请派督办折(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锡良遗稿·奏稿》第1册,第559页。。上述陈请和要求,构成锡良将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官商合办的重要动力。
三 川汉铁路改为商办以及川鄂争夺由川代修鄂境路段之路权
光绪三十一年六月间,商务部将张、王诸人呈文转至张之洞、锡良,并督责两人“力祛官民隔膜滞碍之弊”(58)《商务部来函(光绪三十一年六月收)》,《锡良存川汉铁路奏咨录要》第12册,“所藏”:甲374-28。。七月二十一日,外务部因外交交涉带来的严重压力而函促张、锡赶速筹办川汉路事:“此路关系綦重,英美法三使争相借款,虽经本部严词驳阻,而此路一日不成,一日不能杜三使之觊觎。”(59)《外务部来函(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收)》,《锡良存川汉铁路奏咨录要》第13册,“所藏”:甲374-28。八月初六日,上谕张、锡就川汉铁路如何“画一事权”妥议具奏(6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页。。处在清政府与社会舆论两方面催促赶办川汉路事的压力下,张、锡做出了如下回应。
首先,将川汉铁路公司由官办改为官绅合办。“为调和官绅意见计”(61)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1863-1911)》第3册,第1072页。,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五日,锡良具折指出川汉铁路因官民合股,“即应官绅合办”,铁路公司理应“尽除官习”并“多用士绅”,官、绅各派总办一人,官以沈秉堃代理,绅则为刑部河南司郎中乔树楠(62)锡良《奏调京员办理铁路折(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五日)》,《锡良遗稿·奏稿》,第497-498页。后改派在籍翰林院编修胡峻为绅总办,乔树楠任川汉铁路驻京总办。见:锡良《改派川汉铁路公司官绅总办片(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锡良遗稿·奏稿》第1册,第546页。。其次,回应相关指责言论。七月十日,锡良覆函商务部,指出川鄂矛盾之说实属“茫无风影”,并解释道:“川、汉道里适均,而建轨则在鄂为缓、在川为急,亦在鄂为易、在蜀为难,故必川省疏陈。”(63)《覆商务部函(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初十日发)》,《锡良存川汉铁路奏咨录要》第13册,“所藏”:甲374-28。针对指责铁路公司“官权尊重”之论,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张、锡指出:“公司用官,不过数员,绅则倍之。复设研究所,每事集绅讨论。……盖官以董率牧令,绅以导喻商民,川省所设局所,莫不官绅并重。”(64)张之洞、锡良《川汉铁路毋庸请派督办折(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锡良遗稿·奏稿》第1册,第560页。对于由政府简派专员督办的提议,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张之洞指其“议论模糊,事理不清”,若果如其议,“势必事权纷歧,动多掣肘”,并且指出“筹款、办事两省办法判然不同,即在一省亦有因时变通之处,一派京员便多窒碍,不过徒滋无穷糜费而已”(65)《致成都锡制台(光绪三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发)》,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24册,第381-382页。。在联衔奏折中,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张、锡声称,芦汉铁路为借款而修,“故以一人总其全工于事始便”;而川汉铁路则为自办,“无论官款必须官集,即民款亦须疆吏督察董劝”,若另派专员,“恐民情未悉,众信未孚,措置立形扞格”(66)张之洞、锡良《川汉铁路毋庸请派督办折(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锡良遗稿·奏稿》第1册,第559页。。
回应各种指斥言论尚属易事,更为严峻的问题则是锡、张二督在代修路段的路权归属问题上再起争执。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张之洞致电锡良,指出宜昌以上铁路让归川省修造“自当照办”,但同时提出“宜昌应设车栈、货栈,仍当由鄂修造”的主张,声明此举“并非争利”,意在“完全本省管辖之权”,“庶各管各境,路权界限得以画清”(67)《致成都锡制台(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三日发)》,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24册,第328-329页。。之所以湖北认同四川代修宜昌以上鄂境路段,实由于此时粤汉铁路权之争回。这正如张之洞致电锡良所言:“粤汉铁路现既向美国争回,三省分境自修势不能缓。然鄂省财力较薄,既修接湘之路,又修接川之路,款分两用,工即不能速成。”然而,四川坚持路由谁修、权归谁有,要求代修鄂境路段的路权归川所有。在这点上,川、鄂争执不下。十月间,锡良派胡竣往鄂商谈路事,核心问题即是代修路段的路权问题。其时,“管路之权鄂中绅士学生坚不允让”,“因定各修各境之议”,进而张之洞致电锡良,提出了湖北自修宜昌以上鄂境路段的两种策略:一是完全依靠湖北之力,但效果不容乐观,“宜昌以上至巫山交界处约五百余里,尽系大山,工艰费巨,只能尽力筹办,造成一里是一里,势不能刻期竣工”;二是提出湖北“以借洋款之法改借川款”的建议,“宜昌以上路工,鄂若不能刻期告竣,则川无出路。川虽集有巨资,于万、宜之间修成车路一段,亦无所用。川路欲早见利,非鄂路及早接通不可。今为川鄂两省计,莫若鄂省即借川款,以修接川之路”,如此,“川自万县修起,鄂自宜昌修起,两端相接,约六年可成”(68)《致成都锡制台(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三日发)》,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24册,第539-542页。。很显然,宜昌以上鄂境路段,若由湖北自修,四川所谓代修路段之路权归川所有的要求则无从谈起,再加上此时四川筹集资本亦困难重重,张氏所提“借川款”修鄂境路段之策几无实行可能。张之洞明知其事不可为而言之,不可谓无故作“刁难”之意,其心中芥蒂亦昭然若揭。
正当川鄂协商之际,十一月间,鄂、湘、粤三省签订《鄂、湘、粤三省会议公共条款》,议将粤汉铁路之湘省边界自宜章以下至永兴县路段让归粤省代修,一切权利暂归粤省收管,以路成后二十五年为限,照粤省原用工本由湘备价赎回。这为川鄂解决代修路段路权问题提供了借鉴。十二月三十日,张之洞致电锡良声称:“鄂绅见湘路粤修有例可援,遂亦愿将宜昌以上路工让归川修,一切照湘粤成案办理。”(69)《致成都锡制台(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发)》,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24册,第606页。此电似乎昭示双方争执已然消解,但不意风波又起。恰在这一时期,锡良在未与湖北协商情况下派胡竣出国选聘勘路工师,而此时张之洞已不惜重金聘请日本工师勘测鄂境路段。对此,张氏难掩心中怒气。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初六日,他在写给锡良的一封长电中言辞激烈地说道:“揆川省之意,必谓宜昌以上鄂路既让归川修,全路即可统归川勘,不愿鄂省与闻。不知代修之权为期甚短,赎回之后鄂路仍为鄂管,利害之关于鄂者实为久长,鄂岂能竟不过问。”“川既不愿与鄂共聘工师,则鄂所聘者鄂不妨独任其费,但川楚全路必须统勘,将来定线、估费、兴工必须与鄂省商定方可开办。否则,川修鄂路之议仍待熟筹,不能遽作为定论。川省如愿事事与鄂会商,此次覆奏折内,务须将鄂境宜昌以上一段暂归川省代修,订期二十五年,由鄂省照原用工费,备价赎回。及川楚路工大纲,皆系两省公同商榷,折衷至当,并非由一省专主各节,切实陈明,庶免鄂绅又有违言。”(70)《致成都锡制台(光绪三十二年正月初六日发)》,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24册,第623、625-626页。最终,张、锡“电商数四”,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联衔具折确定干路分两部分:一是宜昌至成都段,分宜昌至万县、万县至重庆、重庆至成都三段;一是宜昌以下干路,取道荆门、襄阳以达应山县属之广水,接通京汉铁路。更重要的是,双方就四川代修鄂境路段的路权问题达成协议:“宜昌以上,鄂境之路,让归川省代修,订期二十五年,由鄂省照章备价取回;未赎以前,一切权利暂归川省收管。”(71)张之洞、锡良《川汉铁路毋庸请派督办折(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锡良遗稿·奏稿》第1册,第560页。
尽管川鄂两督最终达成协议,然两省路事纷争远未销声匿迹,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集中表现为四川民众对此一协议普遍不满,当中尤以川籍留日学生表现最为激进。他们指出,湖北赎回川修鄂境路段不啻“坐而收其成”,此路段理应由四川“永有其路权”,原因在于鄂境路段工险费巨,“将必耗全路资本之大半”,“此段竣工,总须七八年之岁月,即开车犹虞赔本,大利可获,又当在开车十年以后,届时而赎路之期迫矣。且路而无利,鄂可以迟一日赎路,路而有利,则川不能使之迟一日赎路,是始终皆鄂处于利益之地位,而川处于损失之地位”,进而指出,“赎路之说,乃外国攘我路权,而当外交之冲者,无以拒之,姑为经若干年由中国赎回之约”,在他们看来,本为中外之间的协议,此时由两省达成,实为“自欺而欺人”之举(72)《四川留日学生代表向川督岑春煊所提改良川路公司五点建议(光绪三十三年)》,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册,第445页。。
除此之外,由于省界观念造成铁路资本本省化,就地筹款以及派捐成为常态,对民众生计造成极大侵害。度支部主事杜德舆揭批:“州县敢以所纳之正粮硬派为铁路捐,而严科以抗粮之罪,鞭笞棰楚,监禁锁押。……卖妻鬻子、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故民之视铁路也,不以为利己之商业,而以为害人之苛政。”(73)《度支部主事杜德舆为川汉铁路事呈都察院代奏折》,《申报》1907年10月11日,第3张第11版。铁路公司原定租股不超过股本总额2/5,但实际上远超这一比例,“为筹款大宗”(74)《商、户、外务等三部会奏议覆“川汉铁路集股章程”折(光绪三十一年正月)》,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31页。隗瀛涛先生爬梳地方志史料,详细梳理了川汉铁路公司在四川抽收租股的情况,认为租股实际征收对象不仅包括大中小地主,且及于广大自耕农和佃农,极大地加重了群众负担,对四川大小地主也产生了巨大冲击。见: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第165-169页。。光绪三十二年间,川籍绅民要求改为商办的呼声迭起。如川籍留日学生蒲殿俊、吴虞等44人联署发文,提出“公司股本全出商民”,应遵照《公司律》将公司正名为“商办”(75)《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光绪三十二年)》,谢青等主编、王嘉陵审订《四川省图书馆馆藏四川保路运动史料书影汇编》,第72页。。四川民众在一份公呈中,痛陈铁路公司存在资本滥用、任人不当两大弊端,进而断言“股本永无集足之日”,川汉铁路建设进入死胡同,“铁道我不自修,则外人将进步,外人进步,我川必亡;我自修,则同类复自残,同类自残,我川亦必亡”,因此呼吁川人“宜急求救亡之道”,办法则是“破坏野蛮官立之旧公司,建设文明商办之新公司”(76)《四川人民呼吁将川汉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公启(光绪三十二年)》,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汇纂》上册,第315-316页。。
由于四川民众的强烈要求和全国范围内收回利权运动的开展,川汉铁路改制已势在必行。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间,《申报》披露“鄂督张宫保拟借洋债建造川汉铁路”,对此“川省官绅大为反对”(77)《川省官绅反对鄂督借债筑路》,《申报》1907年1月4日,第1张第4版。,此亦助推锡良改制川汉铁路公司之决心。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二十日,锡良具折上奏,拟将铁路公司改为“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并仿浙江等省通例,设总理、副理各一人,乔树楠为总理,胡峻为副理,裁撤原设官总办,同时颁定续订章程,规定“本公司专集华股自办”,并接纳留学生意见,预算铁路需款总额约计银5000万两以上,募股办法分为股份之股和抽租之股两部分(78)锡良《四川铁路举定总副理并续订章程折(单一件)(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锡良遗稿·奏稿》第1册,第653-654页。。对于此一举措,川籍留学生颇为欢欣,并将其视为锡良“爱民如子,爱国如家”(79)《四川留日学生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书(光绪三十年一〇月二一日)》,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3页。的表征。具折次日,上谕锡良调补云贵总督,此举也成为他经营川汉铁路之尾声。
四 余论
锡良督川时期筹办川汉铁路的过程,自始至终交织着中外对抗、枢部歧异、省际矛盾、时人评骘等多方势力的博弈,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列强对中国路事的干预和阻挠,亦可观察到外务部与商部之间的策略差异、川督锡良与鄂督张之洞之间的态度异势,以及官民之间既有矛盾冲突又不乏协同合作等多重历史面相。上述内容,凸显出清末铁路建设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展现出清末政治和社会的某些时代特色。
中外对抗固为影响清末铁路事业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全国范围亦具有普遍性。就川汉铁路而言,外务部、商部、川督以及四川绅民在抵拒列强方面并无二致。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列强要求参与川汉路事尤其是注入资本的压力,外、商二部因立场不同而在应对策略上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主要从政治角度出发,出于避免外交交涉的目的而要求“专集华股”;后者主要从经济角度出发,考虑到华资不足,而在原则上允许“附搭洋股”,但反对另借洋款。锡良意图通过自办川汉铁路而实现“靖边陲而消衅隙”(80)锡良《开办川汉铁路公司折(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六日)》,《锡良遗稿·奏稿》第1册,第390页。的目的,因而始终坚持自筹自办。上述清政府内部存在的矛盾歧异,典型地凸显出清末时期中国应对列强侵扰的内部差异和自我内耗。
更严重的阻滞因素则是以地域情结为基础的省界观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各省经济结构变化和新政事业开展,立足于一定地域经济文化认同和自身利益的“省”意识开始形成,“本省”成为知识分子和一部分封疆大吏乃至部分群众的流行语(81)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第59页。。无论是在地方政权体系、私营经济领域,还是在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群体、革命派当中,省界观念都广泛存在着并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正负面影响(82)苏全有《论清末的省界观念》,《安徽史学》2009年第1期,第17页。。铁路建设则是受省界观念负面影响的重灾区,表现为“各省所定之路线,往往省界分明,各存畛域”(83)《准军机处片交商部奏各省筹筑铁路亟应统筹全局预定路线折(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锡良存各省铁路奏咨录要》第2册,“所藏”:甲374-19。。就川汉铁路而言,上自川督锡良,下至四川绅民,皆主张由川代修宜昌以上工艰费巨的鄂境路段,固因湖北财力难以同时支撑川汉、粤汉两路之修建,但亦是考虑到本省利益的抉择,诸如消除川民疑惧、便于四川运机运料等。锡良曾向张之洞表白,川省代修鄂境路段,表面助鄂,而“实亦利川”(84)《致湖北张香帅电(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八日发)》,《锡良督川时外省来往电报》第12册,“所藏”:甲374-6。。因此,四川代修之议,与其说是对省界观念的消解,毋宁说是省界观念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同样,由于省界观念使然,宜昌以上鄂境路段由川代修之议一度遭到湖北民众强烈抵制,而四川民众则对川、鄂两督经过长时间争论达成的代修路段在路成二十五年之后由鄂赎回的协议极为不满。在资本筹集方面,省界观念促使川汉铁路资本筹集本省化,川鄂之间不能形成有效合作,进而实现有限资金的合理分配和使用,直接导致四川强捐、派捐成为常态,远远超出民众承受能力。上述现象,不仅从个案角度展示出新政时期省域合作之实态,也暴露出新政改革对省际之间利权矛盾的激化。
就官民关系来看,锡良对来自于朝野的建言献策乃至指斥言论并非全然反驳,而是在斟酌局势前提下作出了有选择性的采纳和让步,诸如调整租股起征点、改变川汉铁路公司经营模式等。尤其是后者,当筹集股本遭遇困境并演化为扰民之举时,锡良两次改变川汉铁路公司经营模式,最终实现从官办到商办的重大转折。此一转折过程,是列强侵凌背景下朝野间讨论乃至争执的产物,这当中尤以川籍留日学生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展现了以保国保省为主要内容和基本指向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清末留日学生中间的发展实态和实际效力。对此,日本舆论慨叹:“中国人最有血性而能任事者莫如蜀。”(85)《四川留日学生为川汉铁路事敬告全蜀父老书(光绪三十年一〇月二一日)》,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8页。留日学生的建言献策,对当政者决策产生了直接影响,终使朝野在川汉铁路问题上形成一定程度的趋同性,不可不谓为清末朝野互动之典型一例。这也反映了清末官民间不仅有冲突对立的一面,亦有协同合作的一面。
进一步言,作为影响省域新政成效和方向的关键因素,督抚行政作为理应受到重点关注。锡良提议修建川汉铁路,展现出他对区域发展的思考和对国家路权的捍卫,也展现出列强威逼态势下督抚作为的具体指向。总体来看,锡良在筹办川汉铁路过程中颇有可圈可点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超乎阶级桎梏的开通性。究其原因,则在于锡良强烈意识到铁路建设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多重功效,将其视为“守土之命脉”(86)此语出自锡良离任川督前至四川铁道学堂的演说辞。锡良在演说辞中说道:“吾未到川,首以自办川汉铁路为请。既在川,又主川滇铁路分任川办之议。夫岂不知山川之险巇、经费之困绌,有百难无一易哉?诚以守土之命脉全在于斯,通汉所以兴利,通滇所以固圉,兹事体大,上为国家,下为疆场,尽吾职耳!谁毁谁誉,固在所不计也,求济事耳,官办、商办亦在所不拘也。”是言鲜明地展示出锡良契合时代诉求的国家主权观念和督抚担当意识。参见:《云贵总督部堂锡留别四川铁道学堂训辞》,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3辑第135册,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200页。,这构成了他亟亟于铁路建设事业的动力源泉。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锡良在川汉路事上存在着浓厚的“理想化”倾向,集中体现在由川代修宜昌以上鄂境路段、铁路资本筹集本省化等方面,此则皆可从省界观念上找到根源(87)时人指出代修之议致路事蹉跎:“设当时从鄂督合修、分修两议,兼两省人力财力,彼此通融办理,则合谋三年谅早有开工之望,而两头并举亦可决成功之期。”参见:《度支部主事杜德舆为川汉铁路事呈都察院代奏折(三续)》,《申报》1907年10月14日,第3张第10版。。另外,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亦是问题纠纷不断,诸如思想不统一、所用非人、财务混乱、贪污浪费严重等,以致路工进展迟缓。从宣统二年(1910)十月二十八日川汉铁路举行开工典礼,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时,宜万段仅修成三十余里(88)隗瀛涛《四川保路运动史》,第185页。。理想最终难敌现实,锡良初衷徒成泡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