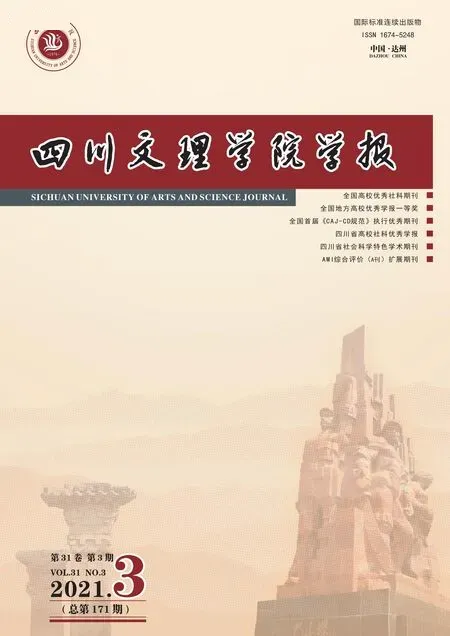张爱玲与托尼·莫里森文中女性身体的异化
李雪梅
(四川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0)
张爱玲与托尼·莫里森在世界文坛上的影响差异较大,因而在国内少有人将她俩放在一起比较和研究,前者生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她避免涉及政治话题,读者却还能隐隐听见作品中战争的枪炮声,而托尼·莫里森心系本族人民,积极剖析社会、种族和性别压迫等问题。然而,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却是两位作家共同的主题。张爱玲生活在20世纪的中国香港,过世于香港回归祖国前夕的1995年。作品故事地点多集中在20世纪早期的香港和上海,文章以秀美的文笔、凄婉的故事著名。在《倾城之恋》小说集里,《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出生在上海的中产阶级家庭,想留在香港南英中学完成学习,暂住姑妈家,最后沦为交际花。小说中的社会环境是英国殖民统治时期的香港,社会充满了阴霾、糜烂的空气,上流社会里男盗女娼,清纯靓丽的年轻女子是成年男人追逐的对象,最后薇龙通过身体的异化劳动维系她卑微的爱情和婚姻。在美国黑人女性文学和中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女性身体被商品化和被奴役具有共性特征。托尼·莫里森的小说中,女性身体异化现象非常普遍,《宠儿》《天堂》《苏拉》等作品中,女性被社会异化,身体被摧残,被工具化,被商品化。作品中美国黑人是第一世界中的三等公民,同20世纪早期的半殖民地中国人一样都是被压迫对象,女性的命运则更为凄惨,女性在异化的社会里痛苦挣扎,具有相似的命运,性别压迫渗透到了社会的骨子深处。本文拟就中美两位女作家张爱玲和托尼·莫里森的作品中的女性身体异化现象进行对比分析,梳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异化的逻辑过程,寻找东方女性和西方社会黑人女性的相似命运。
女性身体的异化是指男权社会束缚、支配甚至压抑女性,而女性不能呈现出自己的行动和意向,主要表现在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对女性的任何摧残和控制都是通过对身体的摧残和控制来实现的,张爱玲的小说揭露了封建族权、夫权政治对女性的压迫,对于女性个体来说是通过对女性的情和欲的压制和管理来达到对女性身体的管制。小说中的女主角不能主宰自己的身体,但是,她们渴望守护身体、解放身体来呼吁女性的人性。托尼·莫里森等美国黑人女性作家在多部作品中讲述了黑人女性以身体作为自己反对社会压制的故事,在美国社会里,黑人女性面临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张爱玲和莫里森等中美女作家虽处于不同的国度,遭遇不同的社会境遇,在菲利斯·逻格斯中心主义框架下,她们都从女性身体出发,寻求女性在社会的自我和自由。然而,这一路径显然充满曲折、辛酸和悲壮,来自男权社会强大的控制力和物化力,使女性不得不面对来自家的囚禁、身的物化和性的紊乱。
一、家——囚禁女性身体的牢笼
“家”原本是一个让人得到安宁,受到保护的港湾,在人们的心目中,“家”代表了温馨和安全。在中国人的心中,家文化更是悠久而且浓厚,深入到社会,提倡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用家的理念治理国家。然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男女在家中的地位都是不平等的,“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庇护的地方,男女是主仆关系,男人是家的主人,而女人只能是家里的仆人。中美现代女作家们在小说中,纷纷讲述了女性成员无法忍受家庭男性成员的压迫,反抗和逃离家庭的主题,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托尼·莫里森的《天堂》都没有把家描绘成可以保护女性成员的“天堂”而是折磨、压迫和监控女性的“牢笼”。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女人必须遵循“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通过它的教化来维护社会的伦理道德、政治制度。出嫁前,父亲是家的主人,决定女性成员的生与死,爱与恨,父亲做主把女儿嫁给谁。出嫁以后由丈夫做主,夫死以后由儿子做主,女人永远处于低贱、被动和服从的地位。白流苏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里的主人公,花一样的年龄嫁到一家大户人家,丈夫在外吃喝嫖赌,在家长期殴打妻子,后来又三妻四妾,流苏忍受不了丈夫,回到娘家。在娘家,哥哥主宰她的生活,花光了她的积蓄,嫂子嫌弃她,就连亲生的母亲也不能庇护她,她成了家里的拖累,娘家成为一个不能久居的冰库。婆家和娘家都没有为她提供安静的生活,反而成为囚禁身体、摧毁精神的牢笼。
在美国南部小镇——鲁比,黑人建立了一个纯黑人自治的社区,远离种族压迫,被命名为黑人的“天堂”。作者莫里森虚构这样一个场所,其目的在于讨论,在美国,当人们没有深刻的种族矛盾时,人们是否能够像在“天堂”一样幸福地生活呢?事实证明,即使没有种族矛盾,仍然存在着性别压迫。鲁比镇里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男人同女人之间的、镇子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矛盾使小镇不可能宁静像天堂。小说里的康瑟蕾塔、玛维斯、吉姬、西尼卡、帕拉斯五个女人的故事告诉了我们,在 “天堂”里,黑人男性组建的社会保证了自己的权威和地位,女性只是依附于他们的附属品。她们在生活中饱受创伤和耻辱,纷纷逃到相隔17 英里的修道院,“女修道院的每个女人几乎都是在外界的各类暴力的驱赶下来到此地的。”[1]远离尘嚣的女修道院里没有男性,成为一帮黑人妇女的寄居地。她们在这里互相帮助,分工合作,靠勤劳的双手制造食物和生产农产品,不再是没有经济地位的男性附属。这些受伤的女人通过对伤痛集体记忆的方式,在康瑟蕾塔的带领下,赤裸着身体,以自己最为舒服的形式躺在地板上,诉说尘封多年心底里的伤痛和羞于启齿的过往遭遇,彼此悉心照料,耐心倾听,心中的苦痛逐渐驱除了出去。修道院的这五位受伤的妇女终于发现了自己鲜活的生命和自我,找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她们自食其力、自由随性地生活、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身体、爱灵魂,逐渐建立起自立、自尊、自爱,彰显了女性自我疗伤的能力,然而她们却成为鲁比男人心中异己,最终女修道院被捣毁了。这个纯女性乌托邦群体的构建以失败结束。“家”在《天堂》中是黑人女性备受摧残、羞辱和努力逃离的象征。玛维斯是一位家庭妇女,作为家庭建造者,在丈夫的眼中,“她是地球上最蠢的女人。”[2]40最终变成了家庭的逃离者。西尼卡的家是一个被哥哥性侵,被养母嫌弃的场所。帕拉斯的家却见证了亲人和爱人的背叛,社会的羞辱。“家”同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一样,没有成为庇护女性的港湾,而女修道院才是她们言说痛苦,治疗创伤,远离性别压迫的像天堂一般舒心的“家”。这一基于男性尊严而建立的家,具有压迫女性的全部特征,家没有成为女性的庇护地,反而成为伤害女性的地方。女性伴随着身体的丧失丢失了自己的主体性,不断被物化,她们的身体成为男权社会的生产和交易的工具。
二、身——男权社会中的生产和交易工具
“在传统哲学和父权制的身心二元对立法则中,身体是阻碍精神圆满的危险敌人,它与自我相分离,由女性所承载。由此,自我与身体的关系被假定为某种占有和控制的伦理学,女性被视为男性的他者,男性的自我认同凌驾于他者的关系之上。这种身心分离的哲学和文化渗透在性别压迫和不平等的规范权力中,由女性身体对其的内化而成就。”[3]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是一个畸形社会,英殖民主义凌驾于全社会之上,西方霸权随着殖民者占据社会主流,而原传统中国的遗风又深深影响当地,东方西方各种政治、经济势力杂糅在一起,渗透着肮脏的交换勾当,女性在那种社会的生活状态更加痛苦,身体成为交易的工具。“政治必须通过亿万个身体来发挥其操控世界的作用是显然的,政治从来没有离开过身体消灭、再生和改造,政治(宗教家、政治家、革命家他们对身体的关心是一致的)从来没有离开过对身体的关心。”[2]49
张爱玲的小说中,香港社会的组织形式和政治权力对于处在社会中下层的原住民来说都是一种高压态势,而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女性更是无望。香港社会的等级化、各个阶层之间的对立和妥协都是通过对人的身体进行了“训诫”,“规制”或者“蹂躏”来实现的。社会正常运作和欲望表达是对女性身体的奴役实现的,女性作为男性之间的交易工具或符号,在这个社会性别分层中处于被压制的位置。葛薇龙原本清纯,有理想,在上海沦陷后,希望寄居香港的姑妈家完成学业,靠自己的知识独立于社会中。“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拍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4]3然而,在半殖民时期的香港,社会没有给女性自强自立的基本条件。大学即使毕业了,要想靠自己的知识谋生都太难,结婚或依附男性是女性最容易的出路。薇龙清纯漂亮的脸蛋,充满活力的身体是无数香港政商权贵和封建遗老欲望和交换的工具。姑母是粤东富商梁季腾的第四房姨太太,她善于利用男性,周旋于香港许多权贵之间,“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满清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当姑母人渐老,色渐衰,盘算着把小侄女培养成她勾结和攀附权贵的棋子,支撑她骄奢淫逸生活的财富来源。而薇龙倾心所爱的乔琪乔在显赫的乔家地位极其低下,想利用薇龙的身体获得父亲的财产。薇龙的身体是男人之间钱、权的交易,父子相互妥协的工具,当薇龙失去了身体的主体性,她的身体被权利锻造和揉捏,在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利关系中变成一种受害物,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经济和政治交易的媒介。
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天堂》里,鲁比镇由15个父系家族构成,其模式也是以女性为媒介,由男人控制的社会,鲁比的社会结构展示了黑人女性只是镇上15个家族相互联系的礼物,从一个父系宗族交付到另一个父系宗族,有效地巩固男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摩根兄弟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地位,完成两个大家庭经济合并,弗拉德家族的小女儿阿涅特只能嫁给摩根的侄子K.D.,这与爱情和人品无关。鲁比的女人身份 “落在了她们所嫁的男人身上——如果婚姻有效,就会成为一个摩根,一个弗拉德,一个布莱克霍斯,一个普尔,一个弗利特伍德。”[2]210女人就是确保男性家族的再生产,是联系男人群体的一种条件。“把女性客体化、肉体化是男性中心主义与逻格斯中心主义合谋的结果…性及性别是男权文化建构的虚假幻象。”[5]
托尼·莫里森在另一本小说《宠儿》里,黑人女奴隶身体被异化的情况更为严重。黑人女性的身体被侵犯、被殴打、被标记在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中很普遍,女奴既要从事繁重的生产劳动又要承受奴隶主对她们的各种身体折磨,殴打、性侵以及当动物一样的标记都有。在早期,奴隶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女奴更是生育机器,贝比·萨克斯一生与6位黑人男奴生了8个孩子,当孩子快长大时,就被卖掉,丈夫也被卖掉或死亡。塞丝的母亲屡遭侵犯,在贩卖到美国的路上,她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奴隶制的愤恨,把所有被白人性侵所生下的孩子扔了,只留下一个与黑人所生的塞丝。塞丝的身体上有一颗枝繁叶茂的“树”,是奴隶主及其侄子所制造的伤疤,“在《宠儿》的文本中,身体上的伤口、身体的残疾、身体上的记号以及对于身体的虐待等场景构成了身体书写的基本图景。”[6]所以,在这生不如死的奴隶制社会里,身体极度的异化,只能导致极度的暴力,即使是充满慈爱的母亲为了女儿免遭相同的奴役,残杀女儿这样无人道的故事,也变得让人同情。
三、性——女性身体的异化根源
“性是权力为了控制身体及其力量、能量、感觉和快感而组织的性经验机制中最思辨,最理想和最内在的要素。”[7]男权社会通过制定了性的道德规范来实施对身体的权力管控。“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男性对女性身体的统治,这是父权制的基础,由身体统治延伸到意识形态上的统治。”[8]104张爱玲和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塑造了一些身不由己,渴望掌握身体自主权的女性。由于深受不同的文明影响,两位作者对于女性身体的异化劳动持不同的态度。
中国传统社会风气讲究安分守纪,含蓄自律,具有强烈的荣辱观,因而社会中女性的性表现得隐晦、低贱、矛盾和痛苦,一方面,社会允许男性娶三妻四妾,寻花问柳,另一方面,明媒正娶的第一个女人才是正经的婚姻。在这种憋屈的婚姻制度里,男人可以妄为,而女人必须承受社会的非难,无数女人的身体被物化、异化。张爱玲的作品中,女性人物羞愧难当,隐隐痛苦。《第一炉香》中的姑母嫁给了香港富豪做四姨太,娘家人觉得蒙羞,拒绝与她来往,婚姻使她失去了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乔家更是反映了香港殖民时期的社会生活,乔家的老爷在政治上拉拢殖民者,用金钱购买了一个皇家的爵士爵位,在生活中却过着中国清朝遗老那种腐败的生活,娶了20位太太,平时还保持着与香港各种社会交际花交往,小说中的姑母和后来的侄女葛薇龙都成为他手中的玩物。身体的自主权是一个真切的悖论,作为物质,它总是被转与他人。“身体既属于我,又不属于我。身体从一开始就被交给了他人的世界,打上了他们的印记,在社会熔炉里得到历练。”[9]因而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性让女人羞愧、痛苦,许多女人被异化为不洁,生活在社会的灰色地带。“这种静默无声的含蓄力与它背后那沉重不堪的羞辱感,两相纠葛,互为加固,并最终催生一个致人死地的无意识杀人凶手。”[10]香港社会没有给女人留下独立自主生存的空间,身体的自主和性的自主是一种奢望。葛薇龙指望通过自身努力进入职场,实现独立的梦想被粉碎,最后沦落为周旋在社会遗老、商业肱骨等男人之间的肉体交易,她的性是不为人齿的。“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和乔琪乔,整天忙着,不是替乔琪乔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4]50那低贱的、不为人齿的性压在心底深深地伤害着她,“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惧。”异化的社会异化了薇龙的身体,囚禁了薇龙的性,内心隐隐痛苦和担忧充斥了像她这类女人的一生。
什么是女性身体的异化?什么是身心合一,生命和灵魂的相遇?怎样才能拥有身体的自主性,自由的行为活动能力?以及怎样才能成为自己身体的主体?“无法拥有和控制自己身体的女人,不能说自己是自由人;直到女人可以有意识地选择是否成为母亲。因此,对生育的自主权应该是妇女的基本权利,是妇女人权中的一个重要内容。”[8]104女性身体自由来自于性的自主权。托尼·莫里森在小说《秀拉》中阐释了女主人公秀拉追求身体的自主,性的自主思想。
《秀拉》祖孙三代女性特立独行,祖母伊娃以自残身体的方式解决男人留下的难题,身体缺失却捍卫了家的存在和精神的独立,当丈夫鲍依鲍依耻笑伊娃丢失的一条腿时,她对那个男人就放弃任何的幻想,黑人女性的身心只能靠自己独立起来。母亲汉娜生活观念有别于其他黑人女性,不热衷繁衍和养育子嗣等传统女性责任,她热爱自己的身体,享受着同男人平等的性爱关系,她不断更换性伙伴,“性事是愉悦而频繁的,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称道之处。”[11]44秀拉的性爱观更加不同于其他黑人女性,她的身体鲜活丰满并充满了野性,她认同了性的愉悦性,也认同了男人是靠不住的,她追求性的快乐却不依赖男人,学会了同男人性爱但决不对他们动情。从祖母和母亲的经历中,秀拉认识到如果女人想真正拥有自己,就必须消解强加在女人身上的生育义务,因此,她不愿结婚,也不愿生育孩子,“不愿变成另外一个人,我要创造我自己。”[11]92“秀拉的性行为是用来确立她自己的性主体性,颠覆男权社会中男人的主导地位,是她确立自我的手段,是一种种族政治和性别政治。”[12]
结 语
中美两国属于东、西方不同的文明体系,在文化传统、历史路径和治理方式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然而两国女性追求平等权利的历史却相似,女性受到压迫的家-身-性的三者逻辑关系和过程表明:身体的存在必须依赖某种社会规范,然而,公正合理的社会规范取决于人类文明程度高低和两性间的平等和谐思想,检验一个社会的公正合理性在于人与人之间是否存在着难以忍受的压制。性自由是在遵行或接受社会规范的前提之下而存在的。黑人女性的命运与半殖民时期的中国女性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家成了囚禁身体的牢笼,身体是男性之间交换的工具,性是最终规定和压迫的根源。规范了女人的性,就控制了女性的身体,最终又以家的形式束缚了女人的身。女性的主体建立应该从热爱身体开始,进而使身体和精神得到统一。把女性从性别规制的压抑和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这是女性主义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