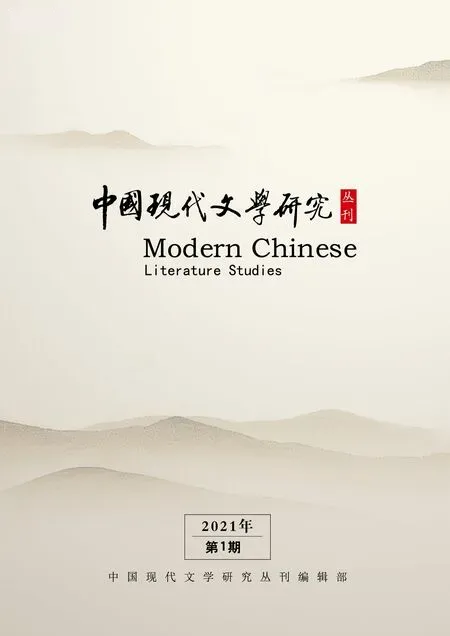“子见南子”案中鲁迅与林语堂的思想分歧
郑浩月
内容提要:1929年鲁迅与林语堂关系的破裂,并非仅仅一场意外的私人纠纷,而是已经有着内在的思想分歧。这种分歧在二人对《子见南子》演剧案的不同认识中已经隐约可见:林语堂的剧作有意识地重塑了一个受到新文化感动的孔子形象,在演剧引起纷争后也着力于捍卫新思想革命的既有成果;而鲁迅则在这场反孔斗争中看到了斗争对象的“孔子”已经从思想象征物转变为肉身化的封建大家族的宗祖,斗争的重心也从思想斗争落到法律、土地等政治经济方面。此后,鲁迅和林语堂的思想分歧逐渐明朗化了,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青年组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而林语堂则成为胡适牵头的“平社”一员,并在后期平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27年年底,从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广东黯然退居上海的鲁迅,本拟“关起门来,专事译著”①,但是却意外地遭遇了“感情似乎很好”的创造社小伙计们的围攻。这一次,鲁迅成了“落伍者”,而对手所使用的概念武器新鲜又模糊不清,使他难以辨明其中就里。出于切实地介绍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理论和作品的目的,他迅速着手与郁达夫合办《奔流》杂志。据郁达夫日记,1928年3月6日,鲁迅与郁达夫相约出版一本杂志,②6月20日,创刊号即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实际上,“关于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③
此时,与鲁迅在女师大学潮中相交、曾经在厦门大学国学院短暂共事的林语堂,也经历了武汉分共的政治动荡,来到了上海。此一时期周、林二人往来密切,不仅一同受聘于蔡元培主持成立的中央研究院,而且,因被奉系军阀查禁而南迁上海的《语丝》杂志由鲁迅接编后,以及鲁迅与郁达夫合办的《奔流》杂志,林语堂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自1927年10月起,林语堂在《鲁迅日记》中频频出现,至1928年七八月间,二人会面交往达四十余次。10月底,林语堂写出独幕悲喜剧《子见南子》,发表于《奔流》1928年第1卷第6期。然而,就在次年8月的“南云楼风波”中,鲁迅和林语堂却突然因为一次“误会”而“绝交”了,直到1933年因共同参与自由大同盟事才再度恢复联络。这顿在南云楼的聚餐,本来是鲁迅与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版税纠纷经郁达夫调停之后的“和解”宴,却意外地成为鲁迅和林语堂的绝交宴。绝交事件的过程,据《鲁迅日记》1929年8月28日载:“……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其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④而林语堂同日日记则记录:“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⑤四十年后,林语堂再次提到此事时称:“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名张友松……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两句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渡过了。”⑥
综上来看,事情的经过是比较清楚的。而且看起来,不管是当事人还是旁观者都将周与林的绝交看作一次因误会而偶然导致的意外。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称这是“因误解而起了正面的冲突”。⑦1936年鲁迅逝世时,林语堂写作《悼鲁迅》一文,也称“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⑧然而,鲁迅与林语堂果真并无轩轾吗?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此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子见南子》演剧案上,就会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林语堂的《子见南子》正是发表在鲁迅与郁达夫所编的《奔流》杂志上,并且,原本流布不广的《奔流》杂志,刊载《子见南子》的这一期还因此大卖,这恐怕也和此剧引发的案件争端脱不了干系。这也是林语堂唯一一部戏剧作品,此剧刊出后曾在南京、上海等地的剧院演出。不过,这些地方的演出并未引发什么问题。只是到1929年6月,此剧被搬上位于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舞台时,却激起轩然大波,以至于当地孔氏族人越级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控告二师校长宋还吾。8月1日,在案件的尾声,山东省教育厅发《训令》宣布“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此案前前后后历时两月,激起的舆论沸沸扬扬,关涉的力量也多元复杂,从中透露出时代核心问题转移的讯息。在此风波中,鲁迅辑录了案件的材料并且加上了自己的注解,而林语堂则将此文易名为《关于〈子见南子〉的文件》,收入了自己的文集《大荒集》,因此人们习惯于认为,在此案中鲁迅和林语堂是相互配合的关系。这未始不可以说是对的,然而这种笼统的说法却忽略了二人在理解演剧案时的差异。这种差异看似微小,但却已经显示出二人的思想分歧,这才是同一时期二人因为一场小小的误会而从密切的交往状态,突然断绝往来达二三年之久的真正原因。
一 两种剧本:林语堂的《子见南子》和山东省立二师的演出
“子见南子”本就是儒学史上关于孔子生平的一个难解公案。此事见于《论语·雍也》《史记·孔子世家》等处,时孔子在卫,卫国实际的掌权者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召见孔子,而孔子见之。因其人名声不佳,“子路不说”,以至于孔子不得不赌咒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史记·孔子世家》说,当南子召见时,“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此后朱熹、崔东壁等人也为子见南子的不合礼法大伤脑筋,寻找不同的办法解释之,例如,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杜撰了“盖古者仕于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来为孔子辩护。林语堂认为孔子的真面目乃是“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老练官僚”⑨,他将孔子晚年周游七十二国理解为“游说乞贷碰官运”⑩。这种理解也不是没有其渊源,《吕氏春秋·贵因篇》云:“孔子道弥尔瑕,见釐夫人,因也”,即“因欲以说灵公也”;新文化运动中,吴虞尖锐地称:“其以干禄之心,汲汲于从政,三月无君,栖栖皇皇,自比匏瓜,贻讥丧家之狗,下拜南子,思赴佛肸,所干至七十二君之多,急于求沽。”⑪在林语堂的《子见南子》一剧中,孔子一面口是心非地表示对于奉粟多寡、做不做官“全不在乎”,“无可无不可”,“有礼则就,礼衰则去”,一面却积极主动地要在卫国谋求职位,且深谙谋官之道,明白“妇人之口,可以出走,妇人之谒,可以死败”的道理,因此面见卫夫人时“态度谨肃庄严,如临大敌”。可以说,在林语堂的剧作中,孔子会见南子的动机正是为了谋得一官半职,孔子的形象正是一个“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老练官僚”。
但是,在与南子的会面中,剧作中却奇特地冒出一个转折。南子出人意料地请孔子创立“六艺研究社”,要求男女同学,由孔子领导指教,讲解三代的诗画礼乐。实际上,南子与其说是要以孔子为师,不如说是要以自己的一套理论来与孔子争夺话语权,因为她不断地大发议论:
人伦之间以男女关系为始,莫重乎男女之间的交际,如果共同研究,借此也可以实习一点,比单看书上白纸带黑字好,我有时看见你书生男子在妇女之前,只会发呆,一句话不会说,极讨人厌,这都是不懂男女交降之礼,缺少实习所致。
我想饮食男女,就是人生的真义,就是生命之河的活源。得着河滚滚不绝的灌溉,然后人生能畅茂向荣。男女关系是人之至情,至情动,然后发为诗歌,有诗歌然后有文学。⑫
在林语堂的剧作的后半部分,与南子的会见对孔子造成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以至于他开始自我怀疑,虽仍坚持说,“男女有别,这是三代相传,周公制定的”,但也感佩南子关于“饮食男女”的人生真义这一深刻觉悟和高超思想,并认为事实上“南子有南子的礼”,即“一切解放,自然”,“如果我不相信周公,我就要相信南子”。不过,孔子仍然选择离开卫国,并非因为南子不知礼,而是因为他必须首先“救出自己”,即从这种思想的震荡中重新掌握自己的方向。林语堂甚至在剧本的末尾加注,“按‘史记孔子世家’,过月余孔子去卫。过三年反卫一次。既去卫,始晋,不果,又反卫一次”,此注基本信息尽管来自《史记》,但在新的语境下显然已经改换本意,暗示着孔子对“南子的礼”始终无法忘怀。因此,通过重写“子见南子”这一历史公案,林语堂将南子从一个“美而淫”的女人塑造成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女性,并且杜撰出孔子晚年的一个思想转折。
不过实际上,剧本发表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半年后,1929年6月8日,曲阜的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举行游艺大会,演出此戏,才引发轩然大波。当时,二师的学生在设计孔子与南子的舞台装扮时,故意使孔子出场时“抹着满脸锅灰,畏畏缩缩”,“样子和大成殿里孔子塑像截然不同”,⑬与南子会见时,孔子为南子的美色所动,魂不守舍,丑态毕露。⑭《子见南子》原剧本最初发表时,杂志的目录和正文中都注明此剧的体裁为“独幕悲喜剧”,即英文的“A One-act Tragicomedy”。所谓悲喜剧,是“介乎英雄悲剧和轻快喜剧之间”的严肃戏剧,结合了悲剧与喜剧的特点,既具有道德意义,又能直接而深刻地打动观众的感情。⑮应该说,林语堂的原作对孔子的确有讥讽,不过只是针对孔子的口是心非地汲汲于“碰官运”的一面,而对他与南子会面情况的表现是严肃的,孔子在此时是严肃的思想者,而非虚伪滑稽的好色之徒。林语堂这样写的目的,是将他杜撰出的二人的思想冲突放到戏剧的前景,并肯定孔子的通达的一面。在“子见南子”演剧引起风波后,林语堂仍只说孔子是“一副患得患失,寒士想过官瘾的丑相,儒林外史人物的老祖宗”,子路所“不悦”的正在于此(《关于〈子见南子〉的话—答赵誉船先生》,《语丝》1929年第五卷第28期)。至于山东二师演剧中着力表现的孔子与南子之间的暧昧关系,林语堂在剧本中并无暗示;仅仅表现了歌女在吟唱称颂齐庄公的女儿,即卫庄公的夫人庄姜的美貌的卫国民歌《硕人》时,孔子的自然人情之流露,以至于失言。然而,山东二师舞台上的《子见南子》,却将孔子演成彻头彻尾的丑角,突出的就是南子的“美而淫”,以及孔子的好色、猥琐与虚伪,因而《子见南子》一剧本身,也从“悲喜剧”变成了讽刺性的“喜剧”,戏剧表现的重心也发生很大的偏移,甚至可以说改头换面成为另一部全新的剧作也不为过。
不仅如此,山东二师的师生们很显然是有意地向孔府挑衅。他们的舞台道具中有不少直接借自孔府内宅,这种实与虚、历史与现在、严肃与戏谑的拼接组合与反差,更构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而且,在演剧前师生们“大肆散票,招人参观”,孔府也很早就得到了山东二师的演剧消息,当时孔府的女主人、已故衍圣公孔令贻的寡妻孔陶氏也带着继子女前往看戏,看戏后气得“浑身发抖”“脸色铁青”,同时又得到孔府总管去世的消息,立即瘫在床上,从此瘫痪不起。⑯
二 林庙改革声中的“子见南子”案
不久,孔氏族长孔传堉,孔庙首领执事官、孔教会会长孔繁璞以孔氏六十户族人名义,向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状告二师校长宋还吾,信中称:“竟有《子见南子》一出,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国风·豳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⑰孔祥熙将此信转呈至蒋介石,蒋介石令教育部“严办”。6月26日,教育部向山东省教育厅发出了第855号训令,责令其查办此事,并专派参事朱葆勤同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委派省督学张郁光)赴曲阜查办。朱、张二人经调查后认为,孔氏控告各项并无实据,据此,教育部发出第952号训令,指出宋还吾“尚无侮辱孔子情事,自应免予置议”,但日后必须“对学生严加训诰,并对孔子极端尊崇”。⑱但孔府对这个结论很不满意,再次向教育部上告,连带指责朱、张二人偏袒一面,被二师师生“同化”,同时向曲阜县政府状告二师学生,在法庭上上演了一场闹剧后败诉。⑲不过,为了平衡各方力量,息事宁人,8月1日,山东省教育厅最终发布《一二〇四号训令》,将校长宋还吾“调厅,另有任用”。⑳
很显然,在如何处理这一案件的问题上,南京国民政府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所以才会导致案件处理结果的一波三折。1928年4月,国民党驱逐奉系“安国军”和直鲁联军,势力逐渐深入山东境内。此时,如何处理山东孔氏就成为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迫切问题,同时也是全国瞩目的问题。《子见南子》的演出之一石激起千层浪,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讽刺剧引发的争端。刘姗的《政治与文化的离合:新文化运动背景下1929年的“子见南子”案》一文,以国民党政府在处理“子见南子”案时的进退失据,说明其在政治转型的激进迅速与文化转型无法“齐步走”的矛盾,即国民党随着分共与建立全国性政权,试图以保守的孔子及其儒学在文化上争夺领导权,走向了它曾予以支持的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李先明、孟晓霞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反孔”与“拥孔”之争——以1929年〈子见南子〉案为中心》一文,和杨政的硕士论文《政治变迁和文化重建——以1929年“〈子见南子〉案”为中心的研究》也将其放在南京国民政府过渡时期文化政策的转变和内部斗争的视域内加以理解。㉑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子见南子”案也并非仅仅是一个文化案件,而是以曲阜的林庙改革这一政治经济变革风向为背景的。
孔氏家族历来被尊为“天下第一家”,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优待。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十二年),孔子的第8世孙孔腾获封为“奉祀君”,自此孔子嫡系长孙便世袭爵位。宋代起兴建“衍圣公府”,孔府的土地是皇帝赐予的“祀田”,在清代最盛时,每年约有五万到十万两的地租收入。此外,衍圣公个人还有近百顷私田,每年还得到皇帝的俸禄和赏赐,并通过卖官制度每年获得几十万两的收入。㉒孔府里的主要职掌是祭孔,每年大大小小的祭孔活动达五十余次。㉓但帝制崩溃后,来自皇室的收入断绝,经济逐渐拮据;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之后,孔家的地位因反孔运动的发展日渐式微。伴随着文化、经济地位的降低,孔府在曲阜地方的政治影响力也被削弱。“清朝时,县长要由衍圣公任命,县长审案要按衍圣公送来的帖子所写的意见办事”,但民国以后早已不复从前,而且孔庙砖石遭政府拆用,祀田被官员侵吞等事时有发生。㉔不过,与赐祀田同时赐的“钦拨佃户”“钦拨庙户”等也采取世袭制,“世世代代为孔府从事屠宰、养猪、养羊、养牛、绑笔帚、挑祭品、供应鸭蛋、菱角、香米、择豆芽等单一的劳动”,㉕这些人至此依旧负担着孔府的各种劳役。
国民党北伐军进入山东之前,孔府与张宗昌往来密切,衍圣公孔令贻本人与张是换帖兄弟,孔死后张宗昌曾在经济上多次给予孔家援助,继任的衍圣公孔德成则与张宗昌之子结为兄弟。㉖国民革命军的到来,使得孔府深感恐慌。不过,蒋介石却于5月到曲阜谒拜孔子,后发出尊奉遗教、保护圣迹的布告,以达到“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㉗6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对山东省政府代主席石敬亭关于保护孔林庙宇问题的咨询作了肯定的答复。㉘继任衍圣公的孔德成则于1928年8月呈请取消衍圣公的名号,以“俾符体制”,“同游平等之世宙”,但实际目的却是保留林庙和祭田的归属权。㉙8月28日,国民政府会议通过了孔祥熙的保护孔子林庙的提案,称“当次革新之际,人心浮动,异说纷呈,一班青年,知识薄弱,难保不为共产党徒打倒礼教之邪说所惑”,应当保护孔子林庙“以正人心,而息邪说”。㉚此消息立刻于8月30日见于《申报》《时事新报》《京报》《时报》等各大报刊。林语堂于见报当日即致信孔祥熙反驳,以《给孔祥熙部长的一封公开信》为题公开发表。10月30日,林语堂写出《子见南子》,正是直接受到此事的刺激。
然而,国民党内另一种声音也同样无法忽视。1928年7月,国民党党员于心澄等呈称,“曲阜之衍圣公系封建余孽、应即取消、孔林孔庙为公欵所建筑、应收归国有”。㉛1928年12月,内政部长赵戴文综合各方意见,拟具《曲阜林庙改革意见》及办法条例。㉜1929年3月5日召开的国民政府行政院第十七次会议,形成整理林庙委员会的条例草案,其中关于祀田处理办法的第九条是,“孔庙祀田,隶属山东、左求、江苏等省,占遗迷失,历久无征,由委员会调查明确清厘升科,归国家征收”。㉝10月,经内政部共同讨论后,蔡元培等人拟订了《审查改革曲阜林庙办法报告》,计划“撤销衍圣公名号”“以原有祀田充作办理纪念孔子各项事业之基金”㉞。面对田产充公的危险,孔府立即以孔德成的名义上书国民政府,说祀田等产业“系由宗祖孔子暨历代先祖父子相继所遗留,已二千余年”,私有财产继承权属于合法权利。㉟11月3日,孔氏六十户首孔昭声以《敬告全国同胞书》电告全国,措辞严厉地攻击蔡元培的提议是“蹂躏人权”,属于“非法处分”,孔府主人“寡妇孤儿,任人鱼肉”,族人又“慑于学阀余威,莫之敢撄”。㊱与此同时,孔府又以孔德成的名义电请孔祥熙、蒋介石、冯玉祥、梁漱溟等人,支持反对蔡元培提议。㊲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商讨《曲阜林庙改革办法》和《国民政府整理林庙委员会条例(草案)》时,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反对没收祀田,认为孔府祭田很多是由私田拨入,“属公属私不可分辨”,因而提出折中办法,“以十分之四为孔子嫡后子孙升科纳税,自行管理。其余以十分之三为孔林孔庙保管岁修之资,再以十分之三为设立图书馆、古物陈列所、护卫林庙公安队、附设国学研究馆等基金”。㊳后经过孔祥熙的多方斡旋,这个方案被“暂缓执行”,后又因战事而不了了之。
三 鲁迅与林语堂的“分手”
显而易见,《子见南子》演剧案正是发生在这个林庙改革提案闹得沸沸扬扬,引起社会各方力量广泛关注的时间段里。二师的师生演出此剧,目的正是有意识地向孔府主人示威,他们在改编剧本和设计舞美服装时,有意识地造成讽刺效果,使剧本重心发生偏移;当演剧发生纠纷后,他们积极斗争,并组织了许多孔府的庙户、佃户到孔府门口游行示威,提出了“打倒孔家店”“打倒孔陶氏”“打倒土豪劣绅”“解放百户”的口号,㊴矛头直指曲阜孔氏享有的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的特权。校长宋还吾在答辩书中则历数孔氏六十户户首们包揽诉讼、勒捐功名、杀人免责等种种劣迹,称其为“特殊之封建组织”。㊵这表明此时的反孔运动已经超越了“五四”时代的思想文化抗争。
在此案中,作为原告的一方是山东曲阜的孔氏族人。可以看到,孔子作为中国儒家正统思想的象征物的意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孔子的重要性已经被狭窄化、具体化为一个地方家族的远祖。孔氏族人在教育部呈文中即称,“孔子在今日,应如何处治,系属全国重大问题,钧部自有权衡,传堉等不敢过问”,孔家上诉的理由是“公然侮辱宗祖孔子”,这个孔子已经不再是儒家思想的抽象象征物,而是具体的孔氏祖先的肉身,“凡有血气、孰无祖先、敝族南北宗六十户、居曲阜者、人尚繁多、目见耳闻、难再忍受”。㊶而且,之所以《子见南子》一剧在南京、上海的演出没有发生什么问题,而在孔门圣裔所在地的曲阜上演却引起了这场官司,并不仅仅是“曲阜是封建思想的大本营”的缘故,根本上是因为这一戏剧的演出已经成为与以孔府为代表的特权阶级、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经济斗争之一部分了。而山东二师在对峙中最终败下阵来,也与孔子林庙改革法案受阻密切相关。
鲁迅在《关于〈子见南子〉》一文中认为,孔府的呈文中可见“‘圣裔’告状的手段和他们在圣地的威严”,而国民政府对“子案”的最后处置结果,表面看是“息事宁人”之举,而从校长被“撤差”、学生被开除来看,依然是“强宗大姓的完全胜利”。㊷鲁迅字里行间的批评显而易见,但更重要的是,鲁迅看到了案件背后的政治经济斗争的信息,曲阜孔氏实质意义上的胜利被理解为“地方大族”的胜利。1934年后,在新一轮的尊孔的复古潮之下,鲁迅又想起了几年前林语堂创作的这部独幕剧。他的《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最初用日语写成,发表于1936年六月号日本(改造)月刊,从此文中也可以看到鲁迅理解孔子的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孔子生时命途多舛,死后落入被种种的权势者用作“敲门砖”的命运,但这与孔子思想本身即远离民众,为权势者设想治理民众的办法是脱不了干系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再次提及五六年前发生的“子见南子”演剧案,比此前的《关于〈子见南子〉》一文的结论更加明确地指出,孔门圣裔在孔子故乡已经成为“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而这“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㊸这就是更明确地将《子见南子》的演剧斗争放到与孔氏家族作为特权阶级之一分子进行的政治经济斗争范畴来理解了。可见,同样是反孔,却因为有了新的理论认知坐标系而具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
然而,林语堂对“子见南子”案的理解与鲁迅却并不一致。如前所述,演出所参照的他的原剧本是将杜撰出的“子见南子”之后的思想转变为重心的“悲喜剧”,与这一古今糅合、亦庄亦谐的剧本相比,实际的演出状况已经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个被具有新思想的南子打动的孔子,并不是山东二师舞台上那个“抹着满脸锅灰”的、被南子美色迷得神魂颠倒的丑角孔子。实际上,触发林语堂写作《子见南子》的直接刺激,也是国民政府会议通过孔祥熙的保护孔子林庙的提案,但他的着眼点在于维护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成果,即抵制保护孔子林庙的象征意义,他在给孔祥熙的公开信中反驳以卫道为反共的办法:“是否打倒礼教即共产党徒之言论?打倒礼教者是否即共产党徒?此是否孔门世传‘古已有之’而似很面熟的思想耶?民国七年新文化运动似乎确系共产党徒陈独秀先生所提倡,新文化运动是否亦即共产党的玩意,应否明令禁止取缔?”㊹而当《子见南子》的演剧引起诉讼纠纷后,他更表示难以理解,仍以为只是“卫道先生”太多、“卫道之心”太切的缘故,因此,对于案件纠纷本身他显然以为不值一哂。在整个事件过程中,他对案件的细节不置一词,唯一引起他关注的是一位名为赵誉船的作者对他的剧作几处史实错误的指摘,他唯一的回应文章《关于〈子见南子〉的话》全文基本上在这方面为自己辩护,而“子见南子”演剧本身激起的法律案件中的政治经济斗争并未进入他关注的视野。
鲁迅曾多次表示过,他一生多次与人论战,但没有私怨,只有公仇。同样,1929年鲁迅与林语堂的“分手”,尽管只是起因于一次偶然的冲突,但如果只是简简单单的个人之间的误会,那么想要解开矛盾尽释前嫌也并不是什么难事。然而,二人从此之后却断绝往来近三年之久,直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才复有往来。事实上,尽管此时看起来二人往来密切,但在认识上已经渐行渐远:鲁迅筹办《奔流》杂志本意在于切实地介绍苏俄文艺理论与作品,而林语堂在《奔流》上发表的几篇译作,如美国批评家勃卢克斯(今译布鲁克斯)的《批评家与少年美国》,斯宾加恩的《新的文评》等,则都与美国方兴未艾的新批评理论相关。在《子见南子》剧本演出引起的诉讼案中,人们一直认为鲁迅与林语堂是互为声援的,也没有注意到《子见南子》的剧本和演出在同一个能指,即“打倒孔家店”之下,其具体内涵的所指已经发生了转移。实际上,鲁迅对“子见南子”演剧案的认识与判断和林语堂并不一致。“南云楼”事件只不过是一个二人矛盾的爆发口而已,他们的“分手”已经成为必然,这一点在“子见南子”案他们的反应差异中已见出端倪。
在“南云楼”风波之后不久,鲁迅和林语堂的思想分歧逐渐明朗化了。1930年2 月,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的青年不计前嫌,放下争议,共同组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而林语堂则成为胡适牵头的“平社”一员,并在后期平社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㊺
注释:
①1927年10月14日鲁迅致台静农、李霁野信,见《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②吴秀明主编:《郁达夫全集》第5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页。
③⑦郁达夫:《回忆鲁迅(续二)》,《宇宙风:乙刊》1939年第11期。
④《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9页。
⑤林语堂日记曾在厦门展出,现存于私人藏家手中。见厦门网2014年4月26日:http://news.xmnn.cn/a/xmxw/201404/t20140426_3816754.htm。
⑥⑧林语堂:《悼鲁迅》,见《鲁迅回忆录散篇·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64~565、663页。
⑨1925年4月7日写的《给玄同的信》,见《剪拂集》。此信中这句话的原文是“孔子乃一活泼泼的人,由活泼泼的人变为考古家”,在1928年9月林语堂编入《剪拂集》中时改为“孔子由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老练官僚变为考古家”。
⑩㊹林语堂:《给孔祥熙部长的一封公开信》,《语丝》第4卷第38期,1928年9月17日。
⑪吴虞:《礼论》,《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⑫语堂:《子见南子》,《奔流》第1卷第6期,1928年11月30日。
⑬⑯㉒㉓㉔㉕㉖㊴孔德懋:《孔府内宅轶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9、119、5~7、34、115、6、65、117页。
⑭高文浩:《山东二师〈子见南子〉案始末》,收入中共曲阜县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曲阜党史资料选编》第1辑(1983年版)。
⑮廖可兑:《西欧戏剧史》上,中国戏剧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
⑰⑱⑳㊵㊶㊷鲁迅:《关于〈子见南子〉》,《语丝》第5卷第24期,1929年8月19日。
⑲李毅夫、骆承烈:《一九二九年曲阜的“子见南子”反封建斗争》,《山东省志资料》1959年第3期。
㉑李先明、孟晓霞:《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反孔”与“拥孔”之争——以1929年〈子见南子〉案为中心》,《民国研究》2015年第2期;杨政:《政治变迁和文化重建——以1929年“〈子见南子〉案”为中心的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布告》,见中国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研究室、山东省曲阜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孔府档案选编》上,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0页。
㉘《国民政府内政部咨二七六号》,《内政公报》1928年第1卷第3期。
㉙《一九二八年末代衍圣公孔德成被迫呈请取消封号要求保留祀田》,见《孔府档案选编》下,第721页。
㉚《时报》1928年8月30日。
㉛《申报》1928年7月26日。
㉜赵戴文:《内政部呈:呈国民政府、行政院:拟具典阜孔林改革意见并附办法条例请鉴和施行由(中华民国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内政公报》1929年第2卷第2期。
㉝《国民政府整理曲阜林庙委员会条例革案》,见《孔府档案选编》下,第718页。
㉞《申报》1929年10月6日。
㉟《孔子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反对蔡元培之处分孔林案》,《益世报》1929年11月1日。
㊱《处分孔林案:孔昭声再电攻击蔡元培》,《益世报》1929年11月2日。
㊲见《孔府档案选编》下,第722~723页。
㊳《一九二八年孔祥熙反对没收祀田,拟出祀田收入分配办法》,见《孔府档案选编》下,第721页。编选者所拟标题中年份有误,应为一九二九年。
㊸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329页。
㊺陈子善:《林语堂与胡适日记中的平社》,《新文学史料》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