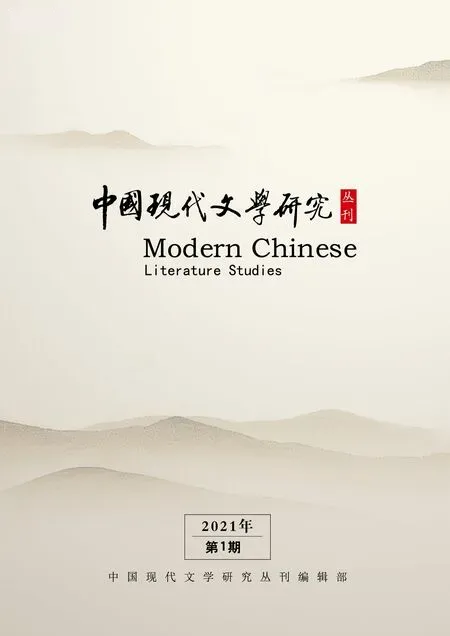论赵树理小说叙事形式的传承与创造※
袁盛勇 刘 飞
内容提要:赵树理小说在表现农村革命的同时,也从叙事角度为人们动态呈现了较为独特的现代性维度。赵树理在其小说中不断进行着文学叙事形式的变革,从古典和民间角度而言,既有传承,更有创造,并且是一种富有民族—现代意味的文学叙事形式创造,具有文学现代性的全新内涵。
1947年8月15日,赵树理在《人民日报》“文艺通讯”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艺术与农村》的文章,具体分析了当时农村艺术活动的现实状况,明确指出发展农村文艺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他说,“只要承认艺术是精神食粮的话,那末它也和物质食粮一样,是任何人都不能少的”,“至于说农村的艺术活动低级一点,那也是事实,买不来肉自然也只好吃小米”。①又说,要“到农村对各种艺术活动加以调查研究,尽可能分时期按地区作出局部的总结,再根据所得之成绩及自己之素养,大量制成作品,来弥补农村艺术活动的缺陷和空白”②。赵树理在20世纪40年代的人生实践,无论是个人生活、革命工作还是文学创作,都与农村密不可分。他在小说创作中比较真实地叙写了不同时期共产党与农村如何结合的革命状况,在表现农村革命的同时,也从叙事角度为人们动态呈现了较为独特的现代性维度和内涵。在赵树理小说创作中,文学的民族性、现代性和革命性不断融合,显示出赵树理具有较为独特的文学理念。其中既有革命工作的需求,也有艺术方面的考量,既有民族性的承续,也有现代性的发展,并且它们与党领导的农村革命事业达到了水乳交融、辩证相生的程度。
1955年,赵树理在谈论《三里湾》时提到,他在创作中有受到“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③。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1947年的采访中,也记录了赵树理在师范学校上学时就曾接触过屠格涅夫、易卜生的作品。④这些进步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及其传统对赵树理的小说叙事产生了深刻影响。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小说宏大叙事的追求上。贝尔登曾经记录道:“他不喜欢在作品里只写一个中心人物,他喜欢描写整个村子、整个时代。”⑤赵树理后来也曾指出,“农村是个广大而具体的社会面,所包涵的和所联系的方面甚广”⑥。从《小二黑结婚》到《李有才板话》再到《李家庄的变迁》等,赵树理小说所涵盖的农村生活范围越来越大,小说规模也愈益宏伟。这表明,赵树理在创作小说时不是对农村中的人与事进行简单摹写,或只注意琐碎生活细节的描摹,而是试图反映较为广阔的农村世界,叙写农村生活较为真实的状态,艺术呈现共产党领导下农村变革的艰难。其次还体现他在小说创作时的革命功利性追求。赵树理以“问题小说”来定义自己的创作,其目的之一就是想“发挥实用性功能,帮助政治解决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⑦他写作《邪不压正》,就是想“写出当时当地土改全部过程中的各种经验教训,使土改中的干部和群众读了知所趋避”。⑧这就道出了小说写作的目的,希望作品发表后,能够帮助干部和群众在实际工作中有所改变和完善,以利革命工作和农村生活的进步与发展,这就是一个小说的革命功利性观念。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赵树理的问题小说,既是社会小说、乡土小说,更是教育小说、成长小说。这在当时,显然也是符合党的文学、工农文学和人民文学等主流文学观念的。
更为值得称道的是,赵树理在自觉作为一个党的文艺工作者之外,始终具有一个地道农民的立场,这一立场使得赵树理始终能够秉持一种较为坚实而朴素的现实主义创作姿态,它在很大程度上只忠实于作者对于乡村与农民生活的观察和感受,具有一种鲜活而生动的感性特征。但也正是对于此种现实主义观念的执着,带来了赵树理小说及其文学观念的悲剧宿命:有限的现实主义和党的文学观往往具有难以调适的特征,其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状态,往往取决于不断变化着的党的政策,而非现实主义和作家本身。本来,赵树理采取的便是一种二者兼顾的态度,他既要立足农村和农民,忠实于农民的感受和体验,又要服从党的政策和利益的要求,使自己的小说发挥较大程度的政治性作用。赵树理自觉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又说自己的创作宗旨为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此种写作姿态无疑是较为理想的。但是,党的具体政策跟赵树理所观察和体验到的农村生活往往既相一致又不一致,当两者一致时,赵树理的作品就符合党的文学观念的要求,而当两者不相一致时,就会产生矛盾,就会不太符合甚至背离党的文学观念的要求。果真如此,赵树理就会受到批评和奚落。⑨赵树理后来创作的小说《三里湾》《“锻炼锻炼”》等大都受到愈来愈严厉的批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在农民立场和党的立场之间,赵树理更为基本的农民立场和忠于生活的写作姿态,使他不仅注意到了农村问题的实际存在,而且执意要在文学创作中反映这些问题的存在,但是,这已经超越了不断变化着的党的政策和意识形态所许可的边界与限度。赵树理的小说是写给农民的,但以一个真正党员作家的诚挚立场来考察,又是向党反映和倾诉问题的。这样一种表达,自延安时期开始,他在文学实践中可说是一以贯之。因此,不是赵树理变化了,而是时代变化了,主流的审美规范和期待变化了,更是党的意识形态要求和政策变化了。比起社会和政策的变化来,赵树理不会与时俱进,不会像当时一些作家那样机智而稳妥地应对现实语境的变化,自然就有些落伍了,不伦不类了。但也恰恰于此彰显了他作为一个质朴的农民式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良知和正气。套用一句现成的话来说,也是体现了现实主义(哪怕是有限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胜利吧。在这意义上,赵树理并非仅仅是一个农民作家,而是一个有着真正知识分子情怀和革命道义的作家。这样一些情怀和道义的综合,其实在我们看来体现了赵树理文学在党的文学观和现实主义文学观之间的复合性特征,赵树理在小说创作中坚守了一个真正革命者和党员作家对于艺术和土地的忠诚,这份忠诚的内核其实就是信仰。在这意义上,赵树理是一个具有真实信仰的作家,作家及其作品所表征的乃是一种基于信仰的文学和基于文学的信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赵树理尽管不是第一个这样的作家,却把如许值得称道的信仰文学推向了一个历史高度,也把延安文学现代性所具有的信仰维度带向了一个更为真实的境地。
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密不可分,它既来源于艺术实践,也深刻影响着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在赵树理的文学批评、经验论述、艺术总结等相关文字中,大部分着重于文学的人民性、功能性、通俗性等方面的阐述,却也并没有忽略艺术方面的追求。延安时期,赵树理总结太行根据地秧歌剧本评选时就强调:“所选择的主题是对了,但不会用艺术的手段去处理它,也是不能取得服务于群众的效果”,优秀的作品“不仅在于内容好,而表现这内容的艺术性也是好的。这里所谓艺术性,也并不是一个超然不可捉摸的东西,既是服务于群众的意志坚定了,艺术上的努力如何,也是求之于群众,群众所喜好的东西,也就是艺术上所应致力的东西,面向群众来研究,也就自能提高艺术的效用”。⑩不难看出,在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认知上,赵树理具有清醒的认识:内容当然是作品的核心,但是没有相应富有审美性的艺术形式,也不会产生更好的社会效应。而艺术上的追求和运用,首要的还是要考虑群众的喜好和接受程度。赵树理并非没有艺术上的自我追求,而是在小说叙事形式的传承与创造上,有着自己明确的追求。
延安时期的赵树理在创作方面横跨雅俗、纵贯古今,不断突破现有文艺体裁和形式的限制,在小说、杂感、诗歌、戏曲、鼓词、快板书等不同创作领域均有建树,走上了一条不断自我发展、自我超越的艺术道路。回顾赵树理在延安时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我们不难看出他在其文学实践中不断进行着文学形式的变革,从古典和民间的角度而言,既有传承,更有创造,并且是一种富有民族—现代意味的文学叙事形式创造。
在论及创作时,赵树理多次提出:“最好的办法,是多读古今中外的好作品。”⑪面对古典的、民间的、外国的三份艺术遗产⑫,赵树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秉持开放的态度,但从其内心而言,他受到影响最深,且最愿意谈的,还是以中国古典的、民间的文化遗产为主。严文井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和他对门而居,两人几乎天天辩论中外文学的优劣。严文井一方面惊愕于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断定他不是个通俗作家;另一方面则感到他不仅不想改造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且想说服别人也不必去钻研外国文学名著。⑬谈及民间曲艺时,赵树理如数家珍:“我认为曲艺的韵文是接受了中国诗的传统的,评话是接受了中国小说的传统的。我觉得把它作为中国文学正宗也可以。”⑭论及对传统文艺的继承时,赵树理显得忧心忡忡:“以前我们有些理论工作者对中国传统的东西接受就不是太够。”⑮
赵树理曾对新中国成立后文艺中存在的崇洋媚外现象痛心疾首:“小说咱们有,诗歌咱们有,为什么要丢掉自己的,去学人家的?学人家的长处可以,但学了以后最好把它化为自己的,化不了也不过使它作为另一种形式,不能因此把咱自己的传统丢掉。有些人误以为中国传统只是在普及方面有用,想要提高就得加上点洋味,我以为那是从外来艺术环境中养成的一种门户之见。即使文化普及之后,也不应该辛辛苦苦去消灭我们这并不低级的传统。”⑯而谈起民间的传统曲艺,赵树理是那样的爱不释手:“如果从直接为工农群众服务来看,曲艺还是比较直接一点,它的读和说差别不大,听了叫人懂,不但懂,还使你感兴趣。中国几部重要的小说,如《红楼梦》《水浒》等,基本上都是评话体,流传了好几百年。”⑰“我们的东西满可以像评话那样,写在纸上和口头上都是统一的。这并不低级,拿到外国去决不丢人。评话硬是我们传统的小说,如果把它作为正统来发展,也一点不吃亏。”⑱正如詹姆逊在研究文化的变革时指出:“每种艺术形式都负载着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意义。当过去时代的形式因素被后起的文化体系重新构入新的本文时,它们的初始信息并没有被消灭,而是与后继的各种其他信息形成新的搭配关系,与它们构成全新的意义整体。”⑲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绝不意味着与原有文学形式的割裂,而应该是如何进行有效的传承与创新,即致力于一种传承转化中的创造与创造转化中的传承,然后达到一种新的文学创造。在这方面,赵树理展现出极高的热情,他对多种文艺形式都有过实践,并尝试将其融入文学创作中。从延安时期的作品来看,赵树理明显表现出对民族叙事传统的认同,在创作中也意识到自己在这一传统中的位置,表现出对赓续叙事传统的强烈责任感,主动参与到对传统叙事形式的吸收、改进、激活、绵延之中。赵树理正是在这种传承与创造中开创了一片新的文学天地,在叙事语言、叙事结构、叙事视角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叙事特色。
首先来谈其小说叙事语言的传承与创造。1946年,郭沫若阅读《李家庄的变迁》后,热情地称赞赵树理小说“最成功的是语言……全体的叙述文都是平明简洁的口头话,脱尽了五四以来欧化体的新文言臭味。然而文法确实谨严的,不象旧式的通俗文字,不成章节,而且不容易断句”⑳。相比于当时部分新文学作品过分欧化的现象,赵树理小说的通俗性无疑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冲击与推动。赵树理在1964年撰写的《语言小谈》中曾说,他在语言的使用中特别关注读者能否“听得懂”和是否“愿意听”两个方面。㉑而他在延安时期的叙事语言探索也可从这两点展开考察。前者强调文本的表意功能,要求“说的通”,强调叙述事实的顺畅通达、表情达意的清晰易懂;而后者是语言的应用技巧,要求“说得好”,强调使用语言的具体技巧,即口语化的特点。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赵树理的叙事语言特征。
1946年5月,赵树理与记者李普交谈时,曾经将新文学语言过分欧化的缺陷比喻为“拦路羊”:“那种复杂的甚至古怪的欧化句子,即使由比较习见的字眼组成,却像羊一样,一群一群的来,比拦路虎更可怕。”㉒繁重的劳务使群众无暇去咀嚼文辞的华丽,落后的教育与文化让农民无力去品味篇章的精妙。早期的赵树理曾尝试用“翻译”㉓来解决这个问题,在创作中也能窥得一二。㉔但随着创作的深入,赵树理意识到要想让群众“听得懂”,作品的叙事就必须使用“选择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他采用常见的文字,重视表意功能,遣词造句使用通俗易懂的口语,减少方言土语和地方语汇的使用,形成了叙述功能丰富、语言逻辑清晰的叙事语言。1947年,赵树理在采访中自豪宣称:现在的自己“用农民的语言写作”,并热情解释道,“我用词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我写一行字,就念给父母听,他们是农民,没有读过什么书。他们要是听不懂,我就修改”。㉕这种修改并非单纯将“然而”改成“可是”,将“所以”变为“因此”的文字调整,而是真正从农村的艺术沃土中生长创造出来的语言,并以叙事为重心,着重将事情交代完整、表达清楚。叙事语言选择的背后蕴藏着思想与价值观的立场,赵树理摒弃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对农民的启蒙态度,自觉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将地道的农民口语登堂入室,折射出他与劳动人民同甘苦、共进退的决心。正如茅盾评价:“他是人民中的一员,而不是旁观者,而他之所以能如此,无非因为他是不但生活在人民中而且是和人民一同工作、一同斗争。”㉖延安时期的赵树理形成了朴实简洁、情感丰富、通俗易懂的叙事语言风格,客观上达到了《讲话》提出的简单浅显、容易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的要求。但要真正形成劳动人民的语言,达到群众愿意听的程度,还必须从应用技巧入手,形成叙事语言的口语化特色。
在赵树理看来,叙事语言的运用绝不能全盘照搬理论,因为“光从那里边学不到语言”;㉗也不可以机械地“记录”生活,那是“语言还没有学到足够应用的程度”㉘的表现。而是应该从真实生活中采集语言,提炼出群众口语表达的特点,对其进行艺术化的加工和改造,将其运用在叙事中。不妨读一段赵树理延安时期的作品来领略其中奥妙吧:
一天,孟祥英给丈夫补衣服,向婆婆要布,婆婆叫她向公公要。就按“老规矩”,补衣服的布也不应向公公要。孟祥英和她讲道理,说得她无言答对,她便骂起来。孟祥英理由充足,当然要和她争辩,她看这情势不能取胜,就跑到地里叫她的孩子去:
“梅妮(孟祥英丈夫的名字)!你快回来呀!我管不了你那个小奶奶,你那小奶奶要把我活吃了呀!”
娘既然管不了小奶奶,梅妮就得回来摆一摆小爷爷的威风。他一回来,就按“老规矩”自然不用问什么理由,拉了一根棍子便向孟祥英打来。不过梅妮的威风却也有限——十六七岁个小孩子,比孟祥英还小一岁——孟祥英便把棍子夺过来。这一下可闯出祸来了:按“老规矩”,丈夫打老婆,老婆只能挨几下躲开,再经别人一拉,作为了事。孟祥英不止不挨,不躲,又缴了他的械,他认为这是天大一件丢人事。他气极了,拿了一把镰刀,劈头一下,把孟祥英的眉上打了个血窟窿,经人拉开以后还是血流不止。㉙
赵树理强调叙事语言的简洁。在文字使用上他宛若晋商,节俭和精密均达极致,语言极尽简单之能事,将每个汉字表意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言简意赅,直击要害。“一番话从哪里说起,说到哪里为止,应该以说的最少又说的最周全为标准。”㉚在具体叙事中,摒弃传统叙事语言中拖沓刻板的描述性语言,采用简单经济的白描手法陈述事实,内容清晰,节奏明快。上述引文仅用三百余字,寥寥几笔勾勒,就将混乱的家庭闹剧交代明白,且清晰展示出背后复杂的婆媳矛盾、夫妻隔阂和家庭压迫等多重矛盾。长期扎根农村的赵树理了解劳动人民普遍文化水平偏低、理解能力较差,对复杂的长句缺乏足够整合能力的问题。“句子长了人家听起来捏不到一块儿,何妨简短些多说几句。”㉛因此,赵树理的叙事语言多用短句,一方面方便读者理解;另一方面加快了叙事节奏,加速了情节发展,更容易形成画面感,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形成独特的艺术效果。追求叙事功能极致的同时,赵树理注重对语言的锤炼:叙事语言应该注意使用“劳动人民的口气”㉜,采用生活化的语言展开叙述,将类似引文中“小爷爷”“小奶奶”等闲话俚语引入叙事当中,塑造真实的生活气氛;叙事过程中时常加入“那个”“这”等口语中常见的语气助词还原日常交流的情境。口语化的叙事语言,带来一种特殊的语言张力,对农村读者而言,具有天然的亲切感,更容易产生呼应与共鸣。还原生活语言的同时,赵树理还注重对语言文字的创造性使用,主动发掘日常口语中的精华,采撷群众“话海”中最美的浪花。引文中最细腻也最直接展现生活真实感的就是对“老规矩”一词的使用,放在不同的语境中形成迥异的叙事效果:用在婆婆处代表家长的权威,用在丈夫处代表夫权的蛮横,放在孟祥英身上则是封建婚姻的枷锁。无形中“老规矩”具有了“意象”的功能,用来指代农村落后思想、包办婚姻对妇女的荼毒,体现旧俗的可恨,凸显“翻身”的可贵。类似的语言细节如《小二黑结婚》中的“恩典恩典”、《邪不压正》中的“看看再说”等在赵树理延安时期的创作中比比皆是。正是对语言的千锤百炼,才使得赵树理的叙事丰富多彩,字里行间氤氲着迷人的泥土芬芳,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语言艺术风格。
“听得懂”和“愿意听”从文法、修辞学、叙事等多方面入手,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形成了表意清晰、语言凝练、真实可信的口语化叙事风格。在实际的阅读体验中,读者并不单是从语言或故事的层面来认识作品,文字背后蕴含的感情同样能够被读者所感知。正如赵树理建国后指出,“锻炼语言”的目标是“要说什么就能恰如其分地把什么说清楚,也就是能把自己要传达的思想感情百分之百地传达给读者”。㉝口语化的表达、贴近生活的语言,不仅完成了叙事任务,更从形式上为读者带来吐露心声、自我表达的快感,产生强烈的感染力,激发文学故事与现实生活、情感体验与俗世经验的良性互动,使群众在阅读中获得参与感。这种叙事语言不仅唤醒了群众在情感上的认同,方便作品传播,又为他们从作品中接受革命教育提供了平台,有利于革命思想的宣传。可以说,赵树理在叙事语言方面的探索,符合他一贯持有的文艺为群众服务的立场,也是延安文学在文学叙事形式方面的重要实践成果。
其次来看赵树理小说在叙事结构方面的传承与创造。杨义在研究中国叙事传统时指出:“(‘年—月—日’)的时间意识和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叙事作品的时间操作方式和结构形态。”㉞传统文学受史传传统的影响,多采用“顺叙”结构,以时间流转来引导叙事进行,强调情节间的连贯。赵树理在延安时期的创作基本是以时间的线性流动展开情节,较少以倒装、交错等打乱时间。例如在《李家庄的变迁》中可以看到“到了晌午”“晚上”“第二天早上”“第三天”“一月之后”“到了民国十九年夏天”等大量标示时间的名词。在小说第一节,用“正做早饭”“把饭做成”“吃过了饼”等具体的人物动作表现时间的线性流动,推进情节发展。在情节衔接处强调首尾连贯,形成完整的叙事链条,使整体结构清晰完整。这种叙事结构迎合了农村读者长期形成的阅读习惯,也兼顾了农村地区群众文化水平较低的现实。正如赵树理所言,“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强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㉟。
袁枚《随园诗话》云“文似看山不喜平”,这提示人们传统文学叙事形式的审美不仅希望叙事如山脉般连绵不绝,更强调叙事之中如山峰般的危峰兀立。的确,单纯依靠时间来推动故事发展的“顺叙”结构,常常会使作品陷入“流水账”式的叙事陷阱,使小说枯燥乏味。如前文所述,赵树理在叙事过程中,重视故事性,强调情节曲折动人,无疑是从传统文学中汲取的经验:“(他)读过许许多多旧式的章回小说,弹词唱本之类,凡是找得到的,他都看过,都有这个优点。”㊱在这方面,他主要依靠叙事节奏的变化和悬念的设置来实现自己的意图。叙事时间流动的缓急会赋予叙事不同的节奏,产生情节的起伏,并影响读者阅读心理的变化。以小说《邪不压正》为例,在小说的第一节的“订婚”部分,赵树理不厌其烦地用“十五这天”“就要开饭了”“天已经晌午了”等时间单位以及“起得晚一点儿”“睡了一小会”“送礼的来了”等表现具体进程的词汇,而在情节发展的重要的关节处更是屡屡强调时间的存在,从感觉上使读者意识到叙事时间的加速,使读者在阅读中产生紧迫感。而在叙事的串联方面,赵树理则借鉴传统曲艺表演中设悬念、“留扣子”等手法,在正常的连贯叙事中故意切断线索,设置悬念,如在《小二黑结婚》中提到“三仙姑”吸引青年的本领时故意设问,形成一种悬而未决的阅读感受,吸引读者继续阅读。
而在中国传统叙事形式中,叙事结构完整最重要的标志是故事的完整收束,赵树理通常使用“大团圆”结局作为叙事的终点。深谙中国传统文艺的赵树理曾在新中国成立后明确指出“大团圆”的意义:“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懂团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他们也应该懂得团圆。”㊲从叙事结构上看,赵树理的问题小说是依据革命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展开,情节也沿着处理问题的过程发展,最后在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或政权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下,圆满解决问题,皆大欢喜,最终团圆。在古典文学和民间文艺视域中,大团圆式结局不仅体现着对叙事结构完整的追求,更内含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希冀,形成了一种审美上的民族无意识心理结构。赵树理将其放在现代革命语境中,肯定在共产党领导下,群众团圆、事件圆满不再只是一种想象,而是“实际和可能的事情了,它是生活中的矛盾的合理圆满的解决”。㊳所以,赵树理小说的大团圆式结尾并非只是一种古典的传承,更是一种革命叙事观照下的农村生活与人事的现代表征,具有其新的现代内涵,不可予以简单批评甚或否定。
再次,赵树理小说在叙事视角方面的传承与创造。延安时期赵树理创造的小说,文学史家称其为新评书体小说,这是比较准确的。韩南曾将古典小说中那种源于评书表演的叙事方式称为“虚拟的说书情境”㊴。传统评话体小说多模仿说书人的口吻叙述,在叙事中使用评书表演的固定套语,从形式上还原勾栏瓦舍听故事的情境。赵树理的小说在形式上完全摒弃了古典小说“书接上回”“且听下回分解”等僵化套语,而将重点集中于叙事视角的创造性运用。赵树理小说基本上采用第三人称叙事,即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在全知视角下,叙事者是作者在文本中的心灵投影,是无所不知的上帝,负责完成具体的叙述任务。在讲述故事、串联情节的过程中,叙事者可以随时出现,补充说明、评点内容,从而加强叙事的完整性和表现力,满足读者对故事完整性的期待。而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叙事者又可以在故事内部穿梭自如,随时进入故事内部,将笔触集中在某一具体人物上,成为小二黑、李有才、张铁锁等,以角色为依托观察世界,形成叙事的局部限知视角。小说通过具体表现人物语言、动作、心理等细节,在事件的发展中塑造人物,拉近读者与人物的距离,使呆板的第三人称叙事更加细腻丰富,使叙事更富有活力。整体上看,限知视角是对全知视角的补充,它让情节的推动变成一个自然发生过程。如《李家庄的变迁》中,读者正是通过限知视角观察张铁锁在太原流浪的悲惨经历,对贫苦农民饱受欺凌的无奈和悲凉感同身受,认识到反动军阀统治的腐朽和荒谬。而全知视角则为限知视角提供了逻辑方面的补充和必要说明,保证叙事的完整和故事主线的顺利进行。赵树理正是在全知视角与限知视角的流动贯通中,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叙事效果,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中华民族的审美认知心理结构。㊵而视角转换的频率则又从侧面带动叙事节奏:紧张处,视角转换较为频繁;舒缓时,视角转换只是偶尔出现,较为稀少。
除了形成叙述视角的作用,叙事者还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同时它也是读者进入这个语言叙事世界,打开作者心灵窗扉的钥匙”㊶。古典小说中叙述者一般应该完美地诠释作者观察世界的眼光和角度,表达作品的思想内涵,更方便地实现小说的社会功能。文以载道的传统在赵树理心中具有重要地位,他认为“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说评书就是讲小说),都是劝人的”㊷。 只不过,他是从革命功利角度出发,将传统的“道”替换成革命道理,“给自己的作品提出了崇高的教育使命,处处用中国农村及其变革中发生的真实而常常又很复杂的问题,来努力教育读者”。㊸利用传统文学形式赋予的创作自由,尽情地释放革命激情,宣传革命思想,将审美的社会效益发挥到极致。
此外,赵树理小说在叙事技巧上也有所传承与创造。传统话本小说在引入故事、介绍背景时常常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以人或物作为向导,用人物的行动、语言等展开叙述,避免静止地介绍人物、风景和社会结构,赵树理形象地将其称为“领路人”,“让读者跟随着人物的行动去熟悉环境”,“把环境、人物和故事情节结合起来”。㊹比如刘家峧的二诸葛和三仙姑,阎家山的李有才等均出色完成了引导叙事的任务。还有,赵树理在《李有才板话》中创造性地将诗词韵文与快板书置换,摒弃了传统的“定场诗”等呆板套路,而用富有节奏感的快板代替严肃的诗文,用快板来形成“有诗赞曰”“有诗为证”的叙事形式,以利突出重点、标识人物、增强渲染、启蒙民众、调控叙述,能够生动呈现农民的智慧和民间的率真。
赵树理曾经指出,“农村艺术活动,都有它的旧传统。翻身群众,一方面在这传统上接收了一些东西,一方面又加上自己的创造,才构成现阶段的新的艺术活动”㊺。在文学的传统与现代之间,赵树理小说在叙事形式上做出了贡献。赵树理将革命道理融入小说叙事,利用传统形式满足群众的阅读习惯和欣赏水平,但又摒弃了跟现实生活不相适应的某些旧的形式,在这基础上,终于产生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创造性的叙事形式。于是,赵树理小说为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政治或政策的结合提供了新的可能,既可以有效地宣传党的政策、理念,有利于革命工作的开展,又可以提升与激活农村的艺术活力,有利于现代文学在农村的广泛传播。
综上所述,赵树理不仅有着自己对于文学较为独特的认知,而且在小说叙事形式的传承与创造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在文学叙事形式的不断探索中,赵树理不仅充分释放着对农村、土地和农民长期积累的情感,而且在对于传统和民间文学叙事形式方面的传承与创造上,表现了可贵的才华。在赵树理努力下,从“五四”时期就开始孕育的大众化思想,终于在延安时期产生了较为符合时代需求的文学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以往新文学过分欧化导致的形式缺陷,不仅为古典文学、民间文艺传统融入现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更是提供了标本和范例。诚如周扬所言,赵树理“所创造出来的决不是旧形式,而是真正的新形式,民族新形式”㊻。这是说,赵树理小说在文学形式上不仅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更是具有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亦即在文学形式创造上达到了一种富有民族—现代意味的统一,具有文学现代性的全新内涵。
注释:
①②㊺赵树理:《艺术与农村》,《赵树理全集》第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232、229页。
③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赵树理全集》第3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页。
④⑤㉕杰克·贝尔登:《赵树理》,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4、34页。
⑥赵树理:《谈“久”——下乡的一点体会》,《赵树理全集》第5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00页。
⑦李松睿:《吞噬一切的怪兽或劳动者——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之一》,《小说评论》2020年第1期。
⑧赵树理:《关于〈邪不压正〉》,《赵树理全集》第3卷,第370页。
⑨参阅钱理群《1948:天地玄黄》,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6~239页。
⑩赵树理、靳典谟:《秧歌剧本评选小结》,《赵树理全集》第2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23~424页。
⑪⑭⑮⑯⑰㉚赵树理:《和工人习作者谈写作》,《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89、259、89、263~264、259、91页。
⑫参阅赵树理《我对戏曲艺术改革的看法》,《赵树理全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158页。
⑬参阅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
⑱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264页。
⑲伍晓明、孟悦:《历史—本文—解释:杰姆逊的文艺理论》,《文学评论》1987年第1期。
⑳郭沫若:《读了〈李家庄的变迁〉》,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68页。
㉑㉗㉘㉝参阅赵树理《语言小谈》,《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371、371、372、373、373页。
㉒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5页。
㉓赵树理在《也算经验》中写道:“有时候从学校回到家乡,向乡间父老兄弟们谈起话来……也要设法把知识分子的话翻译成他们的话来说,时间久了就变成了习惯。”《赵树理全集》第3卷,第350页。
㉔如在《白马的故事》中,“暴涨了的山谷,转动着石头轰轰作响,从断断续续的电光中,隐隐看见(几乎看不见)褐色的波涛,正在涌沸”。括号中的内容具有“翻译”的意味《赵树理全集》第1卷,第29页。
㉖茅盾:《关于〈李有才板话〉》,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70页。
㉙赵树理:《孟祥英翻身》,《赵树理全集》第2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页。
㉛㉟赵树理:《也算经验》,《赵树理全集》第3卷,第350、350页。
㉜赵树理:《和工人习作者谈写作》,《赵树理全集》第5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㉞杨义:《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
㊱李普:《赵树理印象记》,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5页。
㊲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赵树理全集》第5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67页。
㊳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
㊴[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㊵㊶杨义在著作中对“视角的流动性”进行了专题讨论,并以鲁迅谈中国农民绘画欣赏为例做出了详尽的解释,见《中国叙事学》,《杨义文存》第1卷,第221、191页。
㊷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赵树理全集》第6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64页。
㊸[捷]雅罗斯拉夫·普实克:《写在赵树理〈李有才板话〉后面》(节录),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458页。
㊹赵树理:《谈花好月圆》,《赵树理全集》第5卷,第20页。
㊻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第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