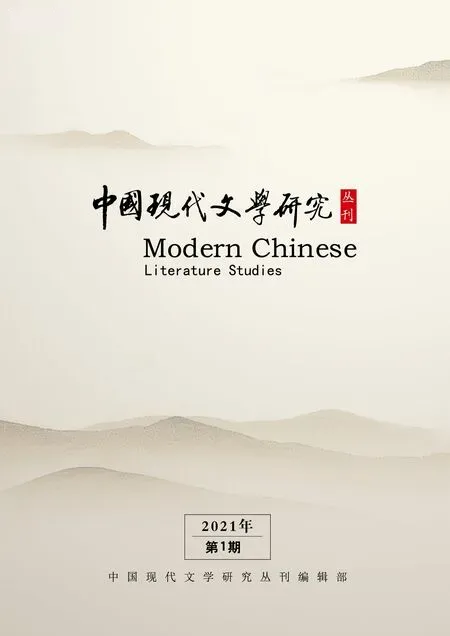时代故事、他人与痛苦
——李晓桦小说《世纪病人》中的历史追忆
胡红英
内容提要:近十年对二战后历史的书写受到了世界范围文学界的重视,《世纪病人》同样激发于战后一代记忆历史之重负。小说塑造了一位在当下自居于“他者”位置的“世纪病人”,以感性经验再现了其人半生遭际的三段迥异的生活历程,讲述了一个关于时代的故事,由展示过往时代在人物心灵划下的深刻烙印,质询了当下对于不久前历史的健忘。这一历史追忆也显露了作者/叙述者携带着“一体化”时期的精神基因,其自命为“病人”的痛苦,则因于“一体化”时期理想的失落,而其精神结构又使其拒绝融入新的生活。如何面对这样一个为共同体理想受挫的他人及其痛苦,为这部小说提出的尖锐问题。
随着时间流逝,记录“短促二十世纪”历史,日益构成历史见证者的压力。新世纪后,中国回忆录、口述史的出版颇成一股热潮,诺贝尔文学奖对书写二十世纪历史的作家也越发青睐。而近十年,二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其记录历史的压力,突出表现于,诺贝尔文学奖2012—2017年的颁奖中,除爱丽丝·门罗,其余五位获奖者的写作都与战后历史密切相关;而其中,莫迪亚诺、阿列克谢耶维奇和石黑一雄,都致力于探索历史在个体心灵深处留下的印记,似诉求于在读者内心辐射动荡历史带来的冲击,从而延续见证者对历史的认识。
李晓桦的长篇小说《世纪病人》出版于2014年,其正好诞生在世界范围文学界对二十世纪后半叶历史的看重之时,显在地同样激发于战后一代怀有的记忆历史之重负。这部出自20世纪80年代最受瞩目的青年军旅诗人①对自身过去半生展开追忆的小说,因作者/主人公过往的人生历程恰跟中国当代历史的阶段性发展一致,而作者/主人公的生活也始终处在时代旋涡的中心,加之作者身为大院子弟具有大历史的情怀和眼光,小说对自我个人经历的叙述,便是一种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叙述——因而,自我书写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可转换性,才是推动作者进行创作的内在动力,对历史的追忆实是其激情所在。
李晓桦书写骤变的历史对个体带来的命运性影响,也侧重于讲述历史在个体心灵深处留下的印记。他尽数一个孤独穿行在当下的人物自闭而又无聊的生活状态,同时伴随对骤然失去的过去兼及深情与反思的回忆——它使人迷恋的时代气氛、精神状态和价值观念,它所提供的不同的行动样式和理想承诺,以及终究被时间证明的虚妄与残酷,企图再现已被遗忘的时代侧影。相对于石黑一雄等对小说人物心灵伤痕展开的理性探究,李晓桦感性地展示了自身所携带的“一体化”时代的精神烙印。
一 “世纪病人”:自居于“他者”位置的人
尽管对历史的叙述是作者创作的内在动力,由小说书名可知,它的落脚点仍是指向由世纪之交导向的现在时。小说对当下生活的叙述,也占了较多的篇幅。因而,小说出版当年举办的研讨会,发言者多关注于人物新世纪后移居加拿大的生活。②
确然,全球最宜居城市的风光移民和“世纪病人”之间具有的反讽张力,率先展现了这部小说独特的叙述视角。若非“病人”,也许便没有讲述过去、追忆历史的必要了。这“病人”又不是一个用于探讨抽象人性的角色——如伯格曼、基耶斯诺夫斯基电影中仿佛天生罹患忧郁症的人物,他由特定的历史时间——一个为全球化、市场经济、消费主义主导的世纪之交所框定。在这种情形下,对当下移民生活的讲述,便表现为对“我”当下病症的讲述;其叙述的心理动机,则是建构创伤氛围,以道出尘封于历史深处的隐情。
作为过去的对照,小说对“病人”——亦即当下之“我”病态生活的讲述,概言之,突出了两种状态:一是自我禁闭;二是无聊。前者既指向抑郁般的精神境况,又是一种将自己与外界区隔开来的行动;后者则属于“我”对当下生活的强烈感受。这两者共同写照了一种自居于“他者”位置的心理状态与生活状态。
首先,与一般讲述移民故事的小说常迫不及待、兴高采烈地展示异域风情不同,这部小说开篇便带出一股幽禁的气氛。本来是新鲜事——温哥华的“学校没有大门,也没有围墙,看上去不像是个学校”,却令“我”想起“在北京,学校都是有围墙的……无关者禁入”。接着,“我”更是认为,这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像一座古老的监狱”。同样在第一章,小说写“我”中午独自在家吃饭——“蹲靠在卫生间的浴缸旁边”:“蹲靠”是个把身体包裹起来的局促动作,“卫生间”是一个幽闭空间——如果读者记得小说《私人生活》中罹患“幽闭症”的人物对浴缸的“情有独钟”③,更能直接意会这个场景的幽禁意味。
不难发现,小说开篇的幽禁气氛,便是“我”内在心境的投影。这一着力渲染的情绪基调,在故事的讲述中,通过人物对自我心理不事掩藏的自陈,实亦贯穿了整部小说。在小说种种幽禁场景的提示下,“我”自我禁闭的心理状态,亦便逐一在其对应物中得以显形,写照“我”在惯性的对外界的警惕/拒绝行动中,将自己幽禁在抑郁的精神状况里面。其本质在于,目及的事物都成了“我”心理的投影之物——这些由“我”之内在情绪着色的事物,在“我”对它们的警惕/拒绝之下,如同一堵堵密不透风的墙,又把“我”禁锢起来。
从症候性的行动而言,“我”对外界的警惕/拒绝,显著体现于“我”对温哥华自然风光之美的无感。中国文学素有寄情于景的传统,如赵园先生说——“享受山水”是“中国式文人的一种传统态度”④。李晓桦20世纪80年代诗歌对风景也有细腻的描写,《蓝色高地》尤其表达了他对自然的倾心,但《世纪病人》中风景之美全然是缺席的。“我”移民到以风景著称的城市,却仿佛蛰居于窒息的空间,连风景都使之压抑。小说对温哥华的介绍只有寥寥几句:“这里是温哥华,美洲大陆的西部,太平洋的东岸,一座依山傍海的城市。”小说对风景稍细致的刻画,止于描述窗外环境,以示家里过分安静。柄谷行人认为:“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连接在一起的……风景乃是被无视‘外部’的人发现的。”⑤这位自我禁闭的“病人”,则将风景也视为“外部”——他在其中投射了对外界的警惕/拒绝。
“我”的警惕/拒绝,还体现于“我”对外部世界中的人和事十分排斥。“我”在温哥华没有生活中往来的朋友,日常谋面都是仅有几句交谈,不产生真正对话的人物。同样陪孩子读书的“女人帮”,她们的爱好不外养狗和看电视,是“我不想搭理的人”。仅一次与多人相处——受托送几位国内来购物的客人到机场,“我”讽喻他们为“黑衣大军”。“我”对与华人相处不耐烦,对于外国人则尽可能隔绝交流。身处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加拿大,“我”却拒说英语——致使常去的咖啡馆服务员以为“我”是哑巴。“我”还把白人情侣握一起的手形容为“耗子”,强调白人女警有个“巨型的屁股”,排他心理格外昭然。
其次,自我禁闭使“我”对风景之美视而不见、排斥与人交往,但“我”精神又非自足的,离开人群的孤独感和失落感“我”也有,因而又深感生活之“无聊”。“我”对于自己被称为“一爹”——“全温哥华第一惯儿子的爹”的解释,颇能说明其生活与内心处境:
这是我目前唯一的事情。我无所事事,无事可做,也没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去做。世界不需要我做任何事情了,属于我的世界不要我了,属于别人的世界更不要我。
小说中,唯一跟“我”达成对话的是一个来路不明的人物——“我靠”,通过与之讲电话,“我”得以听说各种温哥华故事打发无聊。这人物虚实不定,如美国电影《美丽心灵》中纳什教授的朋友查理一样,给“我”带来虚幻的陪伴和对话关系。这样的交集在“我”看来竟——“几乎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最重要一部分,是我赖以活着的支撑”。
因此,虽自觉承担了追忆历史之重负,《世纪病人》在讲述当下生活中展示的这一生活于世纪之交的“病人”形象,却极其具有当下性。这一人物的存在,使笔者颇认同于韩炳哲对全球化社会中“他者”之缺席的理解:“他者的时代已然逝去。那神秘的、诱惑的、爱欲的、渴望的、地狱般的、痛苦的他者就此消失。如今,他者的否定性让位于同者的肯定性。同质化的扩散形成病理变化,对社会体造成侵害。……如今的病态时代标志不是压制,而是抑郁。具有毁灭性的压力并非来自他人,而是来自内心。”⑥自我禁闭,实是一件格外费力的事,其根本上是在一个“他者”消失的时代,自居于“他者”的位置:“病人”既要用力拒绝外部世界,又要用力承担拒绝的后果;而他的主动拒绝,使当下社会暴露其无聊,⑦也使他自己成为从众人中区隔开来的持否定性的“他者”。“病人”与外部世界的格格不入,隐含了一股对“同质化”的对抗激情——对抗跟外界融为一体,对抗外界取消他的独特性,以捍卫他与眼前时代格格不入的主体精神。
二 “时代”才是故事的主角:对历史失忆症的质询
小说以“世纪病人”为题、立足于“病人”当下生活,但若认为小说只是讲述了一个活动于世纪之交人物的故事,可能无法把握小说的主旨和精彩之处。程光炜先生也表示:“这部长篇有一个基本的叙述特点,这就是作者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絮絮叨叨。……这种叙述有一个好处,就是你非常清楚作者和主人公的精神状态是什么,他们对时代所引起的个人精神问题,在小说中有十分精彩有力的展示。但这种写法抛开了总体框架,以及一些必不可少的主要人物,包括这些人物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历史矛盾等东西,它把主人公以这种方式隔离了出来。”⑧如果将小说看作对人物故事的讲述,这部小说是多有不足的。它带有意识流的倾向,却又未据此对人的精神展开深度的探索,失之“絮絮叨叨”。小说对人物不同时期生活的讲述,也主要是对个人经历的讲述,创作只像是过分自恋的自我表达。
程光炜先生实指出了小说创作的诉求——“对时代所引起的个人精神问题”的“十分精彩有力的展示”。在笔者看来,这一小说的精彩之处,正是作者的写作动机和小说的主旨所在。如前所述,《世纪病人》通过对人物不同时期生活的叙述,来表达作者对过去半个世纪历史的体会和认识——自我书写与历史叙述之间的可转换性,才是推动作者进行自我叙述的内在动力。因此,“时代”事实上才是这部小说最重要的书写对象,小说通过人物故事,讲述的实质上是一个关于“时代”的故事。
孟繁华先生亦言:“‘世纪病人’是‘多余人’谱系中的人物。不同的是,他还在追问关于归属、尊严、孤独、价值等终极问题。”⑨“世纪病人”之为“多余人”就在于其当下进行的病态生活,而其与“多余人”的不同,则在于其对病之根源的自觉追问。小说的主题实为:在对人物不同时期生活的讲述中,围绕种种“终极问题”展开对历史的追忆,从而对时代迅疾更替下社会亦迅速遗忘不久前历史——罹患严重失忆症——构成质询。
从“时代”划分,这部小说正好可分三部分理解。按照叙述先后、“我”的身份和经历,第一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下海经商结束后在温哥华做儿子的全职陪读;第二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我”身为青年军官和诗人的阶段;第三部分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身为大院子弟初入部队的青少年阶段。小说对第一部分内容的叙述,如上文所述,最令读者印象深刻的是在对“病人”无聊生活的讲述中展示其自居于“他者”位置的处境:小说对其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商生活基本忽略,对温哥华移民生活的叙述,重在展现其此时自我禁闭的精神与行动状态。小说对第二部分内容的叙述,也没全面交代“我”20世纪80年代生活状况,只挑了几件彼此之间无直接关联的事件,讲述“我”充满干劲的行动状态及对诗人身份的认同。最肃穆的场面,来自对1983年去30高地采访的回忆,它是“我”离战争最近的一次。也着重回忆了“我”如何投入地写诗和与文坛众人会面,极力强调人物的光彩和与之相处时愉快、尽兴的心情。小说对第三部分内容的叙述,亦挑了几个彼此独立的事件,强调其时度日的清苦、人怀有的崇高感和“我”对军人身份的认同——“我”自14岁展开的军旅生涯作为美好往事得到着重回忆。
一般而言,小说如要讲述人物不同时期的故事,会借助于某些彼此联系的事件。如石黑一雄的《远山淡影》,叙事通过讲述过去发生了什么、今天又发生了什么,借助相关事件突出今昔生活之间的延续性,来探究战争在人内心留下的创痕,从而传达作家对战争与人性、人生的理性思考。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实也有相近的诉求。对比之下很明显,《世纪病人》致力于把人物不同时期对生活的直觉感受传达给读者。它不断强调的是今天心情怎样、过去心情怎样。它也依赖于情节,但情节只是为了展示心情,因此片段化。它更倾向于建构不同时期有血有肉的心理现实。在小说建构的这些直觉般的生活感受中,读者便也从感性的角度体认了三个时代的巨大差异。短短五十余年间,“我”的自我身份认同由军人到诗人再到“一爹”,因此,很好地写照了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这三个时代在“我”内在精神及其所支撑的行动力的反差中,便也暴露出巨大裂缝,突显历史断裂的本质。
“短促二十世纪”似乎过去很久了,好长一段时间人们都朝向未来生活,但当下出现的种种问题却不断地说明,未来未必意味着一切都比从前、现在更好。《世纪病人》对时代的书写绝非一种个人情绪,它是一次回首、一种怀旧,但它并非沉溺于过去,它同时也在反思当下与过去的关系。“最好的时光”原本是唐诺的文章题目,他说:“所谓最好的时光,指着一种不再回返的幸福之感,不是因为它美好无匹从而我们眷恋不已,而是倒过来,正因为它永恒失落了,我们于是只能用怀念来召唤它,它也因此才成为美好无匹。”编剧朱天文则说:“每个创作者都有一个他自己的最好时光,唐诺说侯孝贤比较特殊之处在于,他同时也记忆了台湾这不会回头如单行道的最好时光。”⑩因而,对过去/历史的追忆,其本质是为了抵抗全然的遗忘。相较于唐诺、侯孝贤、朱天文态度的温和与冷静,李晓桦情绪化的对当下生活的“絮絮叨叨”,对时代变化中的丧失有着更多的深省。
赵园先生曾说:“‘学’是可以在时间中积蓄的,‘性情’却难免于时间中的磨损。”⑪《世纪病人》在叙事上似乎顽固地抵抗小说的结构模式,采用了一种片段化、跳跃性的以情绪带动情节的呈现方式,这自然源于诗人的写作习惯,却恰好提供了一种另类的时代记忆。
三 他人之痛:“一体化”时期精神的遗民
洪子诚先生在界定“当代文学”含义时指出:“‘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⑫这个“一体化”的实现到解体的过程,大致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其除了指向左翼文学“一体化”,也包含文学生产、组织方式的“一体化”。因之,20世纪80年代虽不强调左翼文学规范,文学生产仍具有较高的组织性、覆盖面广的文学思潮此起彼伏,亦有着较显著的“一体化”特征。相对而言,学界似普遍意识到20世纪80年代面对问题的思路延续了20世纪50—70年代的二分法,却较少探讨知识分子20世纪50—80年代精神结构相近的一面,其都受“一体化”模式形塑。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视野延伸的理解中,《世纪病人》三个时代内容,“我”对自身充满认同感的生活都算处在“一体化”时期。尽管新时期初社会转型幅度不小于20世纪90年代初,“我”却没感到内心经受太大冲击。而20世纪90年代初揭幕的多元生活模式、价值观念、精神状态,却使“我”深感不适。究而言之,李晓桦在追忆往事/历史中对其三段生活内在精神的自我叙述,所体现的对应于文学史分期人的精神的阶段性变化,正反映了其有着形成于“一体化”时期的精神底色。“我”在当下以“病人”自居,痛苦之如影随形、无处排解,而姿态又颇高来高去,已迹近于朝代变换中对旧日不忘、无意于新生活的遗民。
切实而论,虽有自觉的反思与自嘲,“世纪病人”仍可命之为“一体化”时期精神的“遗民”,其自居于“他者”位置而有的深切痛苦体会,莫不可囊括于这一独特的身份能指之中。尽管程光炜、陈晓明等先生都直言小说叙述手法之不足⑬,小说在其敏感而又细腻的对不同时代生活的再现性书写中,确也呈现出不同时代的精神特征和人物风貌。
小说对“我”青少年生活的叙述,主要聚焦于军人身份之上,而贯穿其间被高举的是与之紧密相关的——英雄主义,其痛点则在于对英雄主义的洞穿和无法弃绝。
追忆20世纪70年代生活时,小说选取的角度和讲述的语气,与其时公开发表小说有着颇为相近的一面。小说重点讲述了步兵“我”如何练习“走路”:“我的眼睛要看地下的白线,一条又一条白线排列整齐,延伸开来,每条白线之间的距离是七十五公分,一共有一百二十条白线……”此般事无巨细的描述,正体现该时期小说的显著特点。⑭这反映了生活方式的单一,也表明其时人们分享了激昂的建国热情和顽强的吃苦毅力。虽小说没直接道出支撑其热情和毅力者为何,在“我”对当下生活的自陈中却有深切表现——“我”对儿子强烈的保护欲,“我”无比懊悔没能救下无辜的波兰人,此类事迹莫不显露刻骨的英雄主义情结。
在“我”当下对战争的反思中,小说则直接表达了对军人英雄主义的反思。小说花许多笔墨讲述了“我”在加拿大街边遇见的美国老兵的故事,辨明为英雄主义所遮蔽的军人进退两难的处境。小说也花了很多笔墨谈论军人墓地:那些因援助别国战争而葬在异国他乡的中、美义军,那些曾交战的双方却安葬在同一墓园,那些为新的建设用地而不复存在的军人墓地,——强调历史之诡谲多变、军人的英勇捐躯终究沦为一时一地之争。
20世纪50—70年代文学中,描写战争中的英雄是一个规范性要求,在这样的气氛下,英雄主义成为14岁便参军的军人子弟最突出的精神取向,乃是合情合理的。但作者/叙述者或只意识到其身为军人有着英雄主义倾向,而没有意识到英雄主义业已渗透其思想与生活,因此当下“我”仍不自觉地将英雄主义寄托于对他人的强烈保护欲,却未有反思。
英雄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理想主义,从过来人的各种讲述中能知道,20世纪80年代也是一个充溢着理想主义的时代。只是这一时期理想主义不是把人导向英雄主义,而是导向知识分子所张扬的精英主义。20世纪80年代的李晓桦,由军人向军队文学刊物编辑和军旅诗人转型,恰好顺应了历史重写中主体经由“工农兵”向知识分子的转变。他20世纪80年代最著名的诗歌很好地说明,其成功地将英雄主义灌注于诗歌创作中——“在此/我谨向世界提醒一句/从我们这一代起/中国将不再给任何国度的军人/提供创造荣誉建立功勋的机会”⑮。
小说“外一章”叙述的那个夏天,作为历史断裂的标记及“我”之病症的隐情所在,则是其步出“一体化”时代的起点。“我”被动进入20世纪90年代,成了引发其时“人文精神”讨论中心话题的文人下海经商热参与者之一。“我”这一次身份变化,实也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不同的是,成功创立几间上市公司、作为经商成功者的“我”,却不再能在这个以资本运作和消费主义为主导的时代完成自我认同的转变,小说对经商生活仿佛不屑提及。
“一体化”时期有相近的精神结构,却也不仅指其都恣肆着理想情怀,还指向独特的人物风貌和对人的审美取向,其亦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极不同,这在小说中也得以反映。
在20世纪50—80年代,一方面人们因理想主义而凝聚了强大的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理想主义激发的英雄主义或精英主义都有助于形成关于“高大全”人物——那种完美主体形象的想象。这显得很吊诡,正是那样一个对共同体具有清晰感知的时代,产生了韩炳哲眼中魅力非凡的对“同质化”持否定性的“他者”。小说对20世纪50—80年代生活的回忆中,不断跃现使“我”怀想的人物:同为军人子弟的赵建军强化了“我”之身份认同,交谈甚欢的美国女诗人、驯服军犬的将军女儿让人惊艳,30高地牺牲的排长使人沉痛,王朔等作家各有风采,领导们亦是那样的有人情味。反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却无一人物唤起“我”的认同——连“我”都是病了的。这一迥异的时代境遇,同样印证了韩炳哲对当下的批判和对“他者”的致敬:“抑郁的人是栖居于一个……不可能产生他者经验的空间内”“在拉斯·冯·提尔的电影《忧郁症》中,当贾斯汀对他者的渴望觉醒之时,她的抑郁症瞬间得到了治愈。”⑯
站在当下的对面,以“他者”立场叙述生活的无聊,以直觉般的感受再现过往时代风貌,意图重振的与今天格格不入的主体精神,其来处正是“一体化”时期,这大概是一种作者自身亦百感交集的处境。时代骤变间,人物的社会角色亦几经转换。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由对英雄和精英的呼吁走向对中产阶级个体的创造,“我”则从理想主义共同体的一分子,变为一个独自疗伤的个体——有如海子自杀被看作20世纪80年代终结的标志,而今天诗人自杀只会归因于个人抑郁。因而,在罹患历史失忆症的视野,作者借助小说意图重构“一体化”时期主体形象追问“终极问题”,却不免确认为精神抑郁的他人,其所讲述的时代故事亦不免确认为他人的故事。如何面对这样一个他人及其痛苦,也许是这部小说提出的最尖锐的问题。
结语
“短促二十世纪”的提出者霍布斯鲍姆认为:“过去的一切,或者说那个将一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代人经验承传相连的社会机制,如今已经完全毁灭不存。……历史学者的地位遂愈发比以前重要;因为他们的任务,便是记住已经为他人所忘怀的历史经验。”⑰这一看法解释了当代记录历史的焦虑背后深层的现实因素。文学界对于记忆历史的自觉实亦不晚于历史学界,前述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此番高论发表前亦已展开他们对历史的回顾。
较之历史研究对于宏观经验的重视,文学创作在历史再现中主要着力于重构个体生命轨迹,以表达作为旁观或亲历者的作家自身的生命体验。尽管同样受个体生命时间激发,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已结束经济腾飞的“黄金时代”,而更早于反思二十世纪历史“遗产”,对于书写战后历史在人类心灵的留痕,有着较多可资借鉴的经验;近十年方谓之崛起的中国,其文学的类似探索似至今仍在较为初步的阶段,李晓桦的创作因而有其意义。
《世纪病人》显示,在长时段历史切割为若干不同时代的境遇中,时代在个体心灵划下的深刻烙印不会随时代更替而被覆盖,它虽淡化成不易察觉的精神底色,却又如个体当下生活中的巨大投影。于此,时代经验对个体人生的影响,似已超过弗洛伊德眼中的童年经验——两者有时存在某种重合。李晓桦对历史失忆症的质询,也是对由时间连续性所遮蔽的历史断裂的暴露,“一体化”时期感性经验作为裂痕的黏合剂在他的书写中得以激活;对历史的追忆,成为自命“病人”的创伤性言说,因而又带有一种寻求交代的心理动机。至于如何阅读这样的文本,或也将始终赖于具体的时代生气。
注释:
①李晓桦曾在1988年凭借《白鸽子,蓝星星》获其时全国最重要的诗歌奖项——“全国优秀新诗(诗集)奖”(第三届),同届得奖者有郑敏、绿原、北岛等。
②⑧⑨⑬见《“断根之痛”,或全球化迁徙中不可屈服的失落——李晓桦长篇小说〈世纪病人〉研讨会纪要》,出席者为陈晓明、程光炜、格非、贺绍俊、何向阳、胡红英、李敬泽、李洱、李晓桦、刘伟、孟繁华、乔良、孙郁、宋琳、唐晓渡、阎晶明、殷实(以姓氏拼音为序),《作家》2014年第21期。
③陈染:《私人生活》,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页。
④赵园:《郁达夫:在历史矛盾与文化冲突之间》,见《论小说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页。
⑤[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15页。
⑥⑯[德]韩炳哲:《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70页。
⑦韩炳哲认为:“同质化的滋长是一个‘充盈着空虚的膨胀体’。他者的消失营造出充盈的空虚。”见《他者的消失》,吴琼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第11页。在笔者看来,“病人”自陈之“无聊”感,也是内心空虚的体现。
⑩朱天文:《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326、328页。
⑪赵园:《后记》,收入《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15页。
⑫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3页。
⑭笔者曾在《七十年代的话语“围城”——读〈沸腾的群山〉和〈中国行日记〉》(《文艺争鸣》2013年第2期)中指出,《沸腾的群山》对矿工们进山伐林过程的描述,其细致程度大概能让读者从中学会砍树。
⑮李晓桦:《我希望你以军人的身份再生——致额尔金勋爵》,《金石:李晓桦诗文录》,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129~131页。
⑰[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郑明萱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第2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