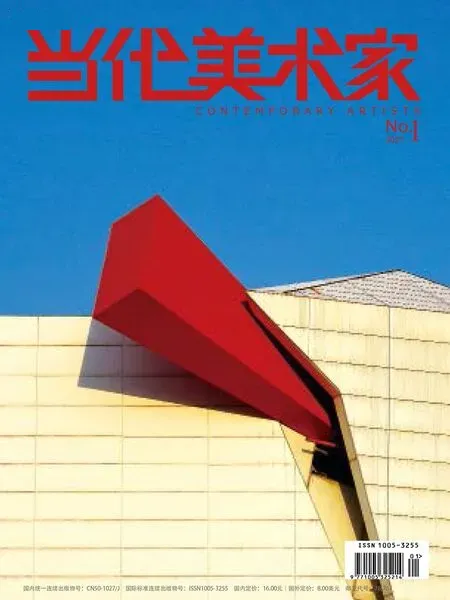从美的艺术到一般艺术部分历史
蒂埃里·德·迪弗 译者:陈小光 诸葛沂 Thierry De Duve Translated by:Chen Xiaoguang Zhuge Yi
艺术圈感受到了杜尚的在场和缺席。他改变了在这里的存在条件。
——贾斯珀·琼斯(Jasper Johns)1
不是每一个艺术理论都是美学理论,也不是每一个美学理论都是艺术理论。对于创造了现代意义上的美学这个词的亚历山大·鲍姆嘉通(Alexander Baumgarten)来说,美学的对象是感官认知,其最高形式是尽善尽美(perfection),其寓于对自然美或艺术美的之中。他在1750年出版的《美学》(Aesthetica)一书中并没有将艺术孤立为一种特殊的、自律的审美实践领域。黑格尔关于美学的演讲稿由他的学生们在他去世后整理成书,他的观点与鲍姆嘉登正好相反:艺术是准专门性的(quasi-exclusive)美学领域,品味和欣赏相较于阐释和历史命运来说,处于次要地位。康德按年代顺序居于中间位置,他认为审美判断是美学研究的合适对象,从本质上讲,它的实践领域是自然(nature);对艺术的审美判断永远不可能是纯粹的,因为艺术创作的规则和惯例可以被置于概念之下,而自然美是无法被概念化的。
因为“杜尚之后的康德”这个思考路径要求我们在阅读康德的《判断力批判》(Critique of Judgment)时,在心里用“艺术”一词替代“美”这一词的出现,所以它保留了康德对审美判断的强调,同时又把判断的对象从美的自然转移到艺术品上。这种转变既不是无端的,也不是“杜尚之后的康德”这一思路的人工产物;它假定,在康德和杜尚相隔的这段逝去时间里,美学的“责任”发生了从自然到艺术的历史性的转移。这个转换非常重要,我将在本书《一般的美学》(Aesthetics at Large)第二卷中,用两章来讲述它。目前而言,重要的是,《杜尚之后的康德》的路径试图构建的美学理论与一种艺术理论是毗连的。它与对自然的审美欣赏无关。 既然这个理论的核心是艺术“作为艺术”的判断受到了挑战——由于艺术取代了美、崇高和善等——这个理论就不能成为任何教条义上的理论;更确切地说,这是一种基本忠实于康德的艺术的审美批判(critique)。这一批判的唯一原理是,宣称“这是艺术”就是一种审美判断,现成品艺术和其他准艺术都是通过这句话而得到洗礼。这一不言自明的宣称意味着,艺术的领域会随着每一次这样的洗礼而重新划定,因而永远不会被预先限定。《杜尚之后的康德》的方法并没有持有,也没有寻求持有一个先验的艺术观念,尽管在某些时候它的“推论”问题将不得不被提出。艺术的概念是经验主义的,并以历史惯例为依据。
但我们必须从某个点入手,问题“一个名称中有什么?”便是个不错的切入点。通常情况下,这是由新名称的来临而激发的一个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谈论艺术的跨学科趋势,使用术语如混合媒介(mixed media)、跨媒介(intermedia),以及多媒体(multimedia),首要重点是为全新和非常多样化的实践定位归类,因为它们不能被划为绘画和雕塑的传统类别。在那十年间获得艺术意义的那些新名称以及术语集合(assemblage)、偶发(happening)、事件(event)、行为(performance)或装置(installation),仅仅是描述性的。 对“艺术”这个词的定义的严肃理论性争论,则围绕着激浪派、极少主义和观念艺术而同时形成;在这场争论中,马塞尔·杜尚对20世纪60年代的一代的艺术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以及他对现成品艺术及艺术理论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争论蔓延到了学院里。那些基本不踏足美术馆的哲学家们开始质疑艺术的概念,这体现在不少临界的艺术案例中,如现成品和捡拾物(found object)这样的真实制品,或者是虚构作品,如阿瑟·丹托(Authur Danto)(他确实定期去画廊)在其著作《寻常物的嬗变》的开篇俏皮地提到的,那8幅标题不同的红色单色画。2在20世纪80年代,我对现成品艺术系谱的研究,使我开始研究绘画尤其是与一般艺术(art in general)之间的关系,并发展出一种艺术作为专名(proper name)的美学理论,这是杜尚与康德意外相遇的结果。3当时激发我的是艺术(art)(单数形式)一词的彻底开放性所产生的兴奋和焦虑的混合,而这种开放是由艺术(arts)(复数形式)之间模糊的或全然被否定的界限所导致的。正如我在《艺术之名》(Au nom de l’art)一书的背面所写:
“人们一直惊奇或担忧的事实是,如今人们认为任何人成为艺术家都是完全合法的,而不是成为画家、作家、音乐家、雕刻家、电影制作人等。现代性会创造一般的艺术吗?”4
有关(一般)“艺术”的问题
当我使用它的时候,一般艺术这个词,或一般词义上的艺术,是模糊的。它似乎指的是一种新的艺术实践门类,既不是绘画,也不是雕塑、音乐、文学、电影等,而且也摆脱了新的名称集合,偶发、事件、行为、或装置——产生的东西要么是艺术,要么什么都不是。现成品艺术曾经是这样的物品,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现在依然是,但文化已经通过把它们作为一种艺术物品来对待并同化了(assimilated)它们。在我意识到“一般艺术”这个词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心中没有一个对象门类,和生产艺术概念的“情境”(situation)的需求一样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似乎能够同化所有的可想对象和技术。我太沉浸在那种情境中了,太过于成为艺术界的一份子,太过于执迷于“内幕”,想要看到那个框定了我自己的问题的更大的图景。
“艺术”这个词在特定时代的意义,就像它真实地被人们所使用的那样,是一个表达一种非常特定的历史意识的词语。“艺术”在单数时,是与那些艺术(the arts),即复数时是不同的,它是一个来自于视觉或造型艺术史的结果。今天所谓的艺术世界,或者更确切地说,“艺术界”(artworld),是一个由视觉艺术家、画廊老板、艺术评论家、收藏家、博物馆常客等组成的松散的社会环境。这不是作家、文学评论家或文学教授的世界;也不是音乐表演者、作曲家或歌剧爱好者的世界。它甚至不仅仅是一个由画家、雕塑家和其他视觉艺术家及其狂热爱好者组成的世界。 这是一个使用“艺术”(art)这个词的世界,这个词在单数和没有修饰词的情况下,是指一系列创造性活动,当然这其中包括了绘画和雕塑,但少数情况下也包括诗歌朗诵(在画廊里或艺术家的阁楼上)、一段舞台表演(但不是在百老汇),或一个声音片段(例如,时代广场5)。然而,上述后面这些活动的艺术身份,以及以它们的实践者作为艺术家的状态,实际上与文学、戏剧以及音乐的历史无关,而几乎这些门类的发展都囊括在绘画史的发展中。事实上,恰恰相反,这些发展经常作为对绘画的批判和远离,并不能掩盖它们的根源是寄于绘画的具体历史中的。举几个例子:行为艺术并不是源于戏剧;它受到现代舞蹈和极简主义艺术的影响;装置艺术并非源于雕塑,它也是脱胎于极简主义艺术;极简主义艺术是作为一种雕塑和绘画的杂糅而出现,在此之中绘画占据了主导地位,是因为它的身份更备受争议。6虽然他们放弃了绘画,但大多数极简艺术家都是从画家起步的,这一点也适用于一些观念艺术家。有人可能会说,所有的后极简和后观念艺术家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个人的和传记的,而是历史的和理论的——前绘画者(ex-painters)。20世纪六七十年代见证了无数画家转变成“艺术家”。当一些摄影师也成为艺术家时不是“艺术摄影师”,而是“从事摄影的艺术家”,他们是搭上了画家的顺风车。
虽然这种向艺术的过渡在一般意义上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现象,重要的历史先例使画家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画家,而不是雕塑家,发明了抽象艺术;20世纪头十年后期的构成主义和拼贴艺术是从纸贴法(papiers collés)中发展而来的,是立体派绘画的衍生品;从他们的雕塑的纯粹质量来看,画家马蒂斯和德加对现代雕塑的出现所作的贡献显然超过了许多同时代的雕塑家;正如大卫·史密斯(David Smith)和安东尼·卡罗(Anthony Caro)后来回忆的那样,罗丹最伟大的创新之一是他的作品表面有画家一样的对明暗光线的敏感性。[看看卡罗(Caro)的青铜裸体,而不仅仅是他的钢棍和梁架结构。]在现代艺术史上,绘画的首要地位是被超定的(overdetermined),其意识形态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和雕塑优劣的争论(Paragone),如果不追及拜占庭时期的圣像之争(Bilderstreit)的话。但我相信,意识形态上的超定最终与眼下的问题无关。首要的不是至高无上。如果所有的后极简和后观念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前绘画者,那是因为,在所有的媒介和艺术形式中,绘画是唯一我在《杜尚之后的康德》(Kant after Duchamp)中所说的那段从特殊(绘画)到一般(艺术)的过渡的中心。7
从特殊到一般的过渡
我的第一本书《绘画唯名论》 (Pictorial Nominalism)的副标题是“论马歇尔·杜尚的从绘画到现成品的通路”(On Marcel Duchamp’s Passage from Painting to the Readymade),我认为这一过渡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范例。 我试图明晰杜尚在被我称为“一般艺术”(art in general)的时代来临时的代表身份。我觉得他是一个(也许是失败的)立体派画家这一点这很重要,杜尚在1912年秋天放弃绘画,几个月后组装了他的第一个现成品《自行车轮》(Bicycle Wheel)。
与传统观念相反,在现成品中看到的是一种彻底的决裂,我把它们解释[特别是1916年的《梳子》(法语为Peigne),它有双关语的虚拟语气动词peindre,画]为表明杜尚矛盾、忧郁,但也是非常清楚地从特殊绘画艺术到一般的过渡,“观念”艺术实践后来被认定是他开拓的。无论杜尚个人的转变如何,他的转变设立了一个过渡仪式,从长远来看,这个过渡仪式被证明事关所有视觉艺术家,这是因为其传达了这样一则消息: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从美术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为了成为艺术,任何给定对象作为先验必须属于既定的艺术形式和题材)转移到一个新体系,我们依然生活在这个体系中,在这个体系中艺术可以用任何东西制成,甚至不管是什么的体系。我可能偶尔会像在20世纪那样使用“一般艺术”(art in general)这个术语,来划分那些抵制特定分类的实践和作品,并因此倾向于说明这种“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情况。但是考虑到这个情况的限定条件,我将使用“一般艺术”[ Art-in-General(大写和连字符)]这个术语。在杜尚个人从绘画的特殊艺术到现成品的一般艺术的转变背后和之外,存在着一种一般化(generalization)(请注意,我不称其为解放),我现在确信,杜尚只是一个杰出的信使。
从理论上讲,这种一般化可以从诗歌、音乐或任何其他既定的艺术形式内部产生。只是事情不是这样发生的。路易吉·卢梭罗(Luigi Russolo)的《噪音艺术》(Art of Noise)可以实现(operate)从音乐到一种新的艺术形式的转变,特别地说,这种艺术形式叫做“噪音”(Noise),或者“广义声音”(Sound at Large),或者简单点叫“艺术”(Art)。它并没有成功——我们仍然认为音乐是一种艺术,而不是广义艺术,我们把《噪音艺术》限制在一个特殊的领域,叫做“噪音艺术”(The Art of Noise)。此外,卢梭罗是一个画家,这是另一个迹象表明相关的过渡是从绘画到艺术,即使它必须通过噪音艺术。约翰·凯奇(John Cage)比卢梭罗更成功,但那可能是身不由己[我怀疑他是否寻求从音乐到艺术的一般化(generalization)]。《4分33秒》是艺术还是音乐?那些称之为音乐的人也称之为艺术;那些拒绝称其为音乐的人[我当面听过伊安尼斯·希纳基斯(Iannis Xenakis)这么说]并不一定拒称其为艺术。因此,他们无意中展开了一个新的类别:声音和无声虽不是音乐,但仍然是艺术;一场不符合演奏定义的钢琴独奏会,却借用了它的程式礼仪;一场音乐演奏的操演性,由于钢琴家没有演奏任何音乐的行为而被加剧;虽然这一段无声短音是向古典音乐的传统致敬(《4分33秒》借鉴了奏鸣曲形式的三乐章结构),但它在音乐创作史上的地位不如它在艺术殿堂中的地位稳固。8
如果约翰·凯奇没有和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或者马塞尔·杜尚交好的话,很难说他能否创作出《4分33秒》。9不论当代艺术家是否有资格成为我们艺术界成员的从业者,我们中知情的人,并且日益壮大的公众,所称的“艺术”,并不需要取得什么资格,所谓“广义艺术”或“一般艺术”是一个取决于那些艺术家是否意识到他们生活在“后杜尚环境”中的问题。正如贾斯珀·琼斯(Jasper Johns)在杜尚的讣告中所写的那样(引用在本章的题词中):“艺术圈受到了杜尚的在场和缺席。他改变了在这里的存在条件。” 不奇怪琼斯这么认为。而且毫无疑问,杜尚确实改变了在20世纪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成为艺术圈中一员的条件:通过他的作品,或者人们对它的了解;通过他在艺术圈中谨慎的出现,以及神秘和超然的光环,他获得了推进的诀窍;或者更多地通过他的崇拜者们的皈依,以及他们投入其中的那种传播围绕他的每一个流言蜚语的类似宗教般的狂热。这个“影响”是否导致了所有这种多半附带的神话建构,是值得怀疑的。当然,真正的“后杜尚”状态不能基于一个模糊的概念来解释。在我看来,“影响力”虚构了后杜尚的一种循环状态,它形成于杜尚的声望中,以一种回声的形式回到他身上,并被放大从而创造了一种错觉,即一个艺术家改变了这个游戏的所有规则。除非我们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否则我们就无法对“后杜尚”状态的有疑问的和荒谬的概念有一个正确的理解。然而我相信确有这样一种理解,这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从美的艺术到一般艺术的体系的变化。
从美的艺术到一般艺术体系的过渡
关于这种我们称之为从前杜尚到后杜尚的变化以及它的意义,我应该说两句。10我们所应对的是各种机构及其各自的美学体制。19世纪的法国美术体系——一个包括部长、学院和美术学院在内的强大的国家机制——在19世纪80年代崩溃了,此后美术体系在欧洲各地迅速消亡。法国美术体系的基石一直是它的年度沙龙,更确切地说,是由沙龙评审团任意裁决的“是”或“否”来决定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在其他活动中,1884年独立艺术家协会(Société des Artistes Indépendants)的成立标志着美术体系的结束和一般艺术体系的出现——尽管所有有关的主角都完全不知情。这一变化是政治性的,最初并没有影响到美术的审美体制,这种传统体制继续规范艺术家的行为,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是这样。新颖之处在于,艺术家们现在可以独立于官方体系之外,过他们的职业生活,因此官方不再能保卫和掌控画家或雕塑家的职业通道入口。任何人都可以宣称自己是艺术家。法国艺术家独立协会的章程对会员资格没有其他标准,只要每年支付适度的费用即可;而法国社团沙龙没有经过审核,因此会员提交的任何东西(“提交”这个词已经不合适了)都会自动被接受并被展示出来。自17世纪末以来,在沙龙的阴影下,商业画廊一直在缓慢发展,但在美术体系的废墟上,它们突然繁荣起来了。在那里,任何人都可以碰碰自己有没有作为艺术家的运气,不管有没有得过罗马奖或国家颁发的奖章,有没有接受过学院教育都无关紧要。
迟早会有人会观察到这种巨大变化已经悄悄地改变了视觉艺术机构体制,并得出关于新体系的审美体制的合理总结;如果自称艺术家的人能在艺术市场上碰碰运气,如果任何人都能成为独立协会的一员,并展示他们想要展示的任何东西,那么他们实际展示的绘画或雕塑是否合格,就成了后验评判认可的先验假设。任何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具有貌似合理的艺术身份的候选者。所有艺术传统事实上都被消解了,审美界限的破碎不是因为创新的艺术家侵犯了他们,而是因为国家机器以前能够决定谁是谁不是合法画家或雕塑家,它在失去了面对艺术家的权力时,也失去了传统和界限的管辖权。
杜尚的消息
杜尚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通过如此理性的推理而获得的。作为一个年轻人,他有过一段痛苦的经历,目睹了独立艺术家协会如何背叛了他们的“无陪审团”原则:一个成员“提交”的任何东西都应该被展示出来,而他从1911年起就是该协会成员了。然而,在第二年的独立沙龙(Salon des indépendants)上,他看到了自己对立体主义的第一次大胆尝试——一幅名为《下楼梯的裸女2号》(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No.2)的画作被立体主义展厅的悬挂委员会审查了,尽管他的同事们做居间调解。深受伤害的他,五年后在纽约以一群渴望摆脱国家设计学院监护的美国艺术家为代价进行了秘密报复。他建议他们以法国独立艺术家协会为蓝本创建一个艺术社团,随后他接着测试他们是否也会违背自己的原则。1917年4月,在新成立的独立艺术家协会(Society of Independent Artists)的首次展览上,他以假名向他们赠送了一个名为《泉》(Fountain)的男用小便池,并附有穆特先生的签名。当然,他们确实违背了自己的原则:《泉》被迅速带走,也从未被展示出来。杜尚礼貌地认识到,等展览结束再发布这则新闻,就没有丑闻会损害这个年轻社团的名声——并且十分隐秘地,在一个他和几个朋友作为编辑的《盲人》小杂志上——发表了名为《理查德 · 穆特的案例》,对边放了一个小便池并附加了三个标题,“穆特先生的泉”“阿尔弗雷德 · 施蒂格利茨所摄”和“独立艺术家协会拒绝的展览品”。和这张照片一起,杜尚把这这则消息放在邮件里,然后等待时机成熟发出去。
直到20世纪40年代,当杜尚又一次秘密地发行了《手提箱里的盒子》(Boîteen-Valise),一个盒子里面装着他大部分作品的微型复制品,其中包括《泉》,此时杜尚等于公开承认自己是穆特先生小便池的创作者。1963年,他在帕萨迪纳艺术博物馆[Pasadena Art,现诺顿·西蒙(Norton Simon)博物馆]举办了第一次大型回顾展,在此之前,《泉》在艺术界的观众只比为数不多的几个当代评论家、艺术家和收藏家朋友多一点,这些人都是他的忠实拥护者。但一两年后,《泉》的复制品出现在市场上,其中一件甚至被送进了博物馆;这个可恶的小便池受到了一些人的欢迎,也有人认为它是前卫艺术的缩影;它已经成为一种艺术创作的范例,激发了当时许多最前卫的年轻艺术家。杜尚在1917年的来信已经抵达。无数艺术家和评论家立即在“收信确认”(acknowledging receipt)中对它的意义进行了解读,用激浪艺术家乔治·布莱希特(George Brecht)的话来说就是:“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任何人都可以做。”11
作为一个过渡和孵化期的高度现代主义
如果聚焦于标志性日期,并用一个艺术家特有的名字大致标明整个时代,我会说,后杜尚时代紧随着帕萨迪纳回顾展(Pasadena retrospective) 开始于1964年,伴随着第一个独立团体沙龙的出现,“前杜尚”时代在1884年结束。这日期之间的80年的间隔可以被形容为,在美术系统崩溃和“一般艺术”系统全面开始生效之间的潜伏期。这个时期的艺术史家很清楚,这80年的高度现代主义处于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从塞尚到修拉(独立艺术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到毕加索和马蒂斯,到抽象画的创始人蒙德里安、马列维奇、库普卡、德劳内等,再到沃尔斯、波洛克、凯利、哈通、约翰以及很多人把现代主义建设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流典型风格(idiom),再到纽曼、罗斯科、斯蒂尔还有莱茵哈德——在他们之后,雄心勃勃的抽象绘画开始不得不在“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的波普和激浪一代面前证明自己。在这80年的潜伏期里,人们对正在进行的变革有了直观的、未理论化的意识,这给那些对他们那个时代最为敏感的艺术家们以一种极大的自由感,激励他们尝试前所未有的形式、媒介、风格和技术。他们不太确定他们的自由得自于谁或来自于哪里(实际上,是美的艺术体系的消亡),所以他们自由地幻想,他们是自我解放的唯一的作者,并通过追求抽象艺术,他们迎来了一个新的审美体制,从内部来颠覆美的艺术体系来宣告它的破产。
杜尚消息的“回执”
紧随抽象表现主义者和色域画家之后的一代艺术家——比如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皮耶罗·曼佐尼(Piero Manzoni)或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这一代——他们看待事物的方式非常不同。人们常说,他们反抗前辈们的英雄化的主体地位。这可能在主观上是真的,但这种俄狄浦斯式的解释并不能完全说服我。我更愿意看到,在他们莽撞自信的艺术背后,有种不一样的机制在起作用。他们的第一个举动不是抛弃前辈艺术家,而是通过杜尚的消息的“收信确认”(acknowledging receipt)对自己进行授权: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艺术,无论是单色绘画或单音调的交响乐(克莱因),还是镀铬绘画(achrome painting)或活体雕塑(曼佐尼),抑或是融合绘画(combine painting)或一个3D集合(劳森伯格)。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位艺术家都建立了一种类似于杜尚从绘画转向现成品艺术时的过渡仪式。对他们和杜尚来说,一般艺术都是绘画的非正统的产物,必然要归功于所谓的绘画消亡。对他们和他们那一代人来说,美术体系的崩溃是一个既定的事实[(etant donne),这是杜尚派(Duchampian)的一种恰如其分的说法,他们把作品置于它的庇护之下],而一般艺术体系的毫无疑问的存在是另一个既定的事实,一个他们全心全意地投入其中的事实。劳森伯格公然地宣扬杜尚的遗产且恶意地提及曼佐尼,而克莱因否认自己受惠于任何他之前的艺术家,这三个人都欢欣鼓舞地赞美着所有界限都被打破的解放意识。杜尚消息的“收信确认”也是——我现在意识到——1989年我在《艺术之名》(Au nom de l’art)封底上的宣传。《杜尚之后的康德》对美学和艺术理论的探讨路径,就是基于这种接受的承认。对于我当时的问题,“现代性会创造‘一般艺术’(art in general)吗?”现在我给出以下答案:现代性,在“高度现代主义的鼎盛时期”的限定意义上的“现代性”,是从艺术到一般艺术的过渡时期的艺术,以及新审美体制的孵化期,我称之为“一般艺术”(art-ingeneral),用连字符和小写区分它与作为制度的“一般艺术”(Art-in-General)体系,和看似是新艺术流派例如现成品艺术和捡拾物的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后者被我称之为“一般艺术”(art in general)(不带连字符)。对我来说,新体系和新体制是否应该被视为后现代,只是一种症候意义上的问题。12这种症候性(symptomatic)在于,实际上,后现代(postmodern)这个词,便是为了标明与现代性的分裂而杜撰出来的,以使后现代与高度现代主义比肩,这种杜撰完全无视以下这点,即在更广义的层面上,代为一个时代的现代性当然并不局限于那过渡和孵化的80年。
现代性作为一个长期的机制(longue durée “dispositif”),可以给出多种起源时间点。我的选择是18世纪,启蒙运动和康德的时代。作为一个关于历史动力的包罗性术语,它触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政治的、宗教的、科学的、技术的还是一般文化的方方面面。现代性当然不只局限于艺术领域。从美的艺术到一般艺术体系的过渡是许多诸如此类力量推动的产物。如果把杜尚看作这一过渡的起因、发起人、作者或代理人,仿佛个人就能实现这种巨大的改变,那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尽管人们常常以“影响”的名义犯这种错误。杜尚只是它的信使,吹口哨的人。这并不是要贬低他的功绩,更不是要否认他在风格和艺术运动的历史进程中的颠覆性的突然介入。揭露人们了解不受自身影响而改变的语境的真相,可以创造出一个事件,其变革性的力量比该事件本身更大,对于这些揭露者来讲,正如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所说——他们保证忠实于那一事件本身。13对于从克莱因、曼佐尼和劳森伯格那一代开始的许多艺术家来讲,特别是对于那些在个人层面上太晚知道杜尚的人来说,对于杜尚消息的收信确认,具有一种保证忠实于“消息抵达”这一事件的力量,这是一个比影响的概念(concept of in fl uence)更有力、活跃和更有创造力的力量,可想而知,被影响者的被动性,相对于那主动影响者的力量 ,要大得多。回顾这80年(1884-1964),这恰好与高度现代主义的全盛时期相吻合,作为一个过渡期和孵化期,这显然需要对艺术史进行一些改写。然而不需要对经典进行修改,只需要对艺术史学家的工具箱进行一些更新。这个更新,既不是从现代也不是后现代,而是从这里所勾勒的“后杜尚”的角度来进行更新。我希望新一代的艺术历史学家能很快担起这份任务。

2双页摘自《盲人》2号(1917年5月)传真版纽约:《丑小鸭报》,2017年左图© Association Marcel Duchamp / ADAGPParis / Artist Rights Society (ARS)纽约2018
几个试验性的最初用法语编写的版本,依次是先用荷兰语出版, 《杜尚之后的艺术界:一些对“艺术”一词的表征评论》;然后用英语出版,《后杜尚的处理:对几个艺术的特称的评论》,在《A-前6》(布鲁塞尔, 2001年秋季);法语版,《关于“艺术”一词的特称评论》,《十位艺术人物》(巴黎, 2006年1月);西班牙语版,《新艺术界与“艺术”一词的四个条件》,《雷蒙娜76》(布宜诺斯·艾利斯, 2007年11月);英语版,《后杜尚的处理:对几个艺术的特称的评论》,《哲学维斯尼克28》2号(卢布尔雅那,2007);最后又是法语版,《关于“艺术”一词的特称评论》载于《评判艺术》,克利斯朵夫 · 格宁,克莱尔 · 勒鲁,艾格尼丝 · 隆特拉德(巴黎:巴黎大学出版社,2009)。目前的版本在翻译上有几个重要的转变。
注释:
1.贾斯帕·约翰斯,《马塞尔·杜尚(1887-1968),欣赏》,《艺术论坛》1968年第11期。
2.亚瑟·丹托,《寻常物的嬗变》剑桥,M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1-2页。
3.蒂埃里·德·迪弗,《绘画唯名论:马塞尔·杜尚的作品》(巴黎:米纽伊特出版社,1984年);《绘画唯名论:论杜尚从绘画到现成品的转变》,戴纳· 波兰译 (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91);《艺术之名: 现代考古学》(巴黎:米纽伊特出版社, 1989);《现成品的共鸣》(尼姆:杰奎琳·尚本,1989)。后两本书(加上另一篇文章)的翻译构成了《杜尚之后的康德》(剑桥,MA:麻省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6)。
4.“我们永远不应该停止惊讶或担心,我们的时代认为一个人成为艺术家而不是画家、作家、音乐家、雕塑家或电影制作人是完全合法的……现代性会创造一般的艺术吗?”德·迪弗,《艺术之名》的封底。
5.我指的是时代广场,这是一个由马克斯·诺伊豪斯设计的永久性音响装置,位于百老汇四十五街和四十六街之间的步行岛北端,位于覆盖地铁通风系统的金属格栅下。这个装置创作于1977年,几乎不间断地运行到1992年,在迪亚艺术基金会的支持下于2002年成为永久性作品。
6.当然,这需要厘清其中的细微之处。卡尔·安德烈和理查德·塞拉是雕刻家,言止于此(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极简主义者)。另一方面,尽管罗伯特·莫里斯写了重要的“关于雕塑的笔记”,但他的作品更多地得益于绘画,而不是雕塑,尤其是贾斯珀·琼斯。
7.在《杜尚之后的康德》的两个章节——“现成品和喷漆管(Tube of Paint)”与“单色画和空白的画布”,组成“特称和通称”,我认为,杜尚的过渡从立体派绘画到现成品艺术的转变事关所有视觉艺术家,而喷漆管和空白画布——这两个现成品属于传统绘画的先验。杜尚当然没有实际制作,但以许多方式进行了暗示——提供了在绘画(特称)和艺术(通称)之间过渡时那缺失的联系。
8.2013年10月12日至2014年6月22日,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一场名为“永不沉默:约翰·凯奇的4分33秒”(There Will Never Be Silence:Scoring John Cage’s 4′33″)的展览。
9.詹姆斯·普里切特[约翰·凯奇的音乐(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3),59-60]追溯《4分33秒》(1952年)起源到一个未实现的方案——1948年的《默默祈祷》,是一段无声录音,凯奇打算出售给米尤札克公司(Muzak Co.),然而,一直承认劳森伯格1951年的《白色油画》为《4分33秒》的先驱。正如他在一篇关于劳森伯格的文章中所写的那样,“可能与之有关的人:白色的画先出现,我的无声作品晚出现。”约翰·凯奇,“论艺术家罗伯特·劳森伯格及其作品”,于《沉默》(康涅狄格州米德尔顿:卫斯理大学出版社,1961年),第98页。参见布兰登·约瑟夫,《随机次序:罗伯特·劳申伯格与新先锋派》(剑桥,MA: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03),42-46.
10.下面是对这一转变的一个极其扼要的总结。详细内容请参见我在2013年10月至2014年4月期间在《艺术论坛》上发表的6篇系列文章:《请原谅我的法国》(Pardon my French)(2013年10月);2013年11月的《不要枪杀信使》(Don 't Shoot the Messenger);《为什么现代主义诞生于法国?》(2014年1月);《非艺术的发明:历史》(2014年2月);《非艺术的发明:理论》(2014年3月);以及《这是艺术:语句剖析》(2014年4月)。下一章是对最后一章理论上论证的不同表述。这个系列的修订版和扩展版将会是《杜尚的电报》(Duchamp’s Telegram)的一部分。
11.作者未知,《激浪派广阔宣言》(Fluxus Broadside Manifesto),1965年,出自《激浪法典》(Fluxus Codex)乔恩·亨德里克斯(Jon Hendricks)编(纽约:艾布拉姆斯出版社,1988年),26.同样的句子摘自1964年5月乔治·布莱希特(George Brecht)在《即兴与激浪》(Happening and Fluxus)(科隆:Kolnischer Kunstverein, 1970)中的《关于激浪》(Something about Fluxus)。
12.不过,我还是要在《一般的美学》(Aesthetics at Large)第2卷中谈谈的后现代主义问题,“准时”。
13.参见阿兰·巴迪欧的《存在与事件》(Being and Event)(纽约:Continuum,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