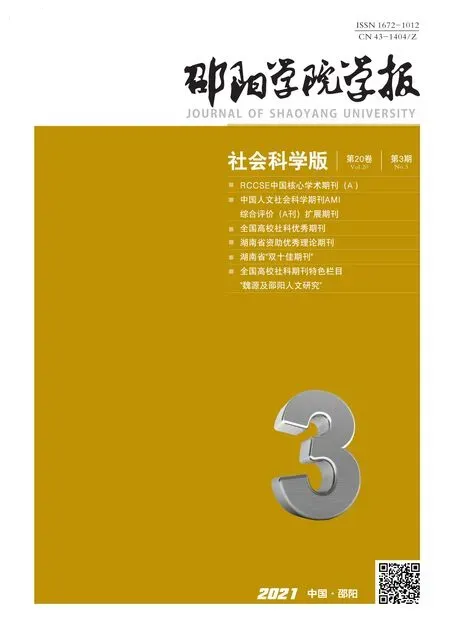从《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看物色观理论的发展
朱敏洁, 蒋振华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2)
《文心雕龙》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文学理论专著,具有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等特点。《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理论体系严密的文学理论著作,在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篇中评价《文心雕龙》的特点为“体大而虑周”,全书一共有五十篇,其主要文学思想包括儒家和道家的美学思想,较全面地总结了齐梁以前的文学与美学,也为后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其中,《物色》篇是全书中写得较为精彩的一篇,提出了一些描写自然景物的理论和要求,还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这些理论被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所继承。
一、《文心雕龙·物色》的渊源及内涵
“物色”一词在现代最为普遍的用法是作为动词使用,其意为寻找、访求之意。这一词义最早出现于西汉刘向的《列仙传·关令尹喜》中:“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有真人当过,物色而遮之,果得老子。”[1]21而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物色”并不是作动词使用的。
刘勰是首位将“物色”用于文学批评的名家,但“物色”一词由来已久。“物色”二字最早出现于《礼记·月令》中:“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2]57这句话是描写祭祀前的准备活动,“物色”在此处是指牲畜皮毛的颜色,这是它的本义。到了晋宋之际,诗人们开始将“物色”二字用于写作之中。颜延之在《秋胡诗》中写道:“日暮行采归,物色桑榆时。”[3]77与颜延之同时期的诗人鲍照也在《秋日示休上人》一诗中道:“物色延暮思,霜露逼朝荣。”[4]148这两首诗中的“物色”所指皆是景物,与《文心雕龙》中的“物色”是一样的。在《物色》篇中,“物”指自然万物,代表外境或者自然景物的名称;“色”则用以形容“物”的状态,包括了自然万物的色彩、声响、状貌等。“物色”在《文心雕龙》一书中阐释为自然景物及其状态。《物色》篇是专门论述景物和诗文写作关系的文章,也常常用于文学的鉴赏和批评。
《物色》篇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建立在前人的创作基础上的。刘勰的文论观扎根于魏晋南北朝之前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学作品。在《序志》篇中,刘勰阐述了他创作《文心雕龙》的缘由和基础:“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5]348由此可知,《文心雕龙》全书都是围绕着圣人、经典进行解读分析以及理论上的总结和提升。单独从《物色》篇来看,刘勰所选取的材料是《诗经》《离骚》、汉赋以及魏晋南北朝时的景物描写作品,“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5]320是刘勰对《诗经》写景的总结,他从视觉和听觉分析《诗经》中的景物,最后写到由景物而产生的内心感触。《诗经》中的用词简洁明了又恰当,而后,在《诗经》的写景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离骚》孕育而生。《诗经》描写景物的词语运用十分详尽。《离骚》的作者屈原自己创造出新的词语来形容景物,如形容山状是“嵯峨”,形容花草树木便是“葳蕤”,这些词是由表示景物名称的字词加工和修改而成的形容词。而后,司马相如之类的文人更是将华丽的词藻堆积在自己的作品中。刘勰对这些作品的褒贬态度也表现在《物色》篇之中:“所谓诗人丽则约言,辞人丽淫而繁句也。”[5]320他和扬雄持有相同的态度,认为《诗经》是浑然天成的文学作品,而《离骚》和汉赋则过于绮靡和淫侈,比不上《诗经》。
除却前代佳作的影响,刘勰所处的时代也是促使其文学理论形成的因素之一。刘勰生活的魏晋南北朝局势动荡不安,但文学艺术却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变化。曹操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其中颇为后人称道的《观沧海》中就有描写山水景物的名句:“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6]91这两句诗将曹操决心削平割据势力、统一天下的心怀抒发得淋漓尽致,一股豪情壮志回荡在字里行间。钟嵘《诗品》评价“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7]123,这与曹操亲历战争和民生疾苦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曹操的思想在魏晋南北朝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时文人的创作逐渐从汉代经学的藩篱中脱离,转而注重抒写人的真实内心,关注文学作品本身,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层出不穷。社会动荡、生民涂炭的现状让文人士子们的内心十分痛苦,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有很多文学作品写的是生死、游仙和寄情于外物的主题。游仙主题以郭璞为代表,寄情于外物的主题则主要分为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和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山水田园诗注重写景抒情,是《物色》篇理论来源之一。刘勰并非首个提出自然景物和文学写作关系的理论家,魏晋时期早有以王弼、荀粲和欧阳建为代表的言意之辨。陆机根据言意之辨在其著作《文赋》中阐述了关于自然景物和文学作品关系的观点:“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8]25他认为情感、景物和文学创作三者密不可分。陆机之后,刘勰接受了他的感物观,创作出了新的物色观。
在《物色》篇中,刘勰以“情以物迁,辞以情发”[5]319概括和阐述了“物”“情”“辞”三者的关系,情是依存于外物的,辞又依存于情,情是物的反映,辞是情的表现工具,三者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和内在统一性。《物色》篇从两个方面对外境景物和文学写作进行了讨论:一方面,刘勰博览群书,对前人的作品进行了总结和评价,对“模山范水,字必鱼贯”[5]320“若青黄屡出,则繁而不珍”[5]321的写作方式提出了批评,并对景物的描写提供了“以少总多”和“情貌无遗”的原则。“以少总多”就是用最简练的语言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而不是堆砌华丽词藻;“情貌无遗”则是指描摹景物既需要描摹其形态,又需要描绘其神态,形神兼备,二者缺一不可。另一方面,刘勰为后世提出了描摹景物的多种方法。第一种是“江山之助”。他认为屈原能够深切领会写景抒情的要领,是因为他获得了山川景物的帮助,细致地体察了山川景物的情状。第二种是“入兴贵闲”。刘勰用四季的变换为例来阐述这一种方法,认为四季无论如何变化,文学创作者的感物兴情的要点在于心情虚静。具体说来就是景物虽繁杂,但作者还是要用最为简练的语言对景物进行描绘。再一种是“志惟深远”和“功在密附”。这一种方法与托物言志的艺术手法有着极高的相似性。刘勰举出了刘宋以来作品中的例子,要求写景的作品不仅要在描写形态方面达到逼真的境界,更要超越景物本身的形态,力求幽深高远的情态。最后一种是“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的方法。这种方法指出描写外在景物并非无中生有,彻底的原创只存在于先秦时期的“风”“骚”之中。后世的文人进行景物的写作需要对前人的作品进行继承,但是继承不代表抄袭,文人在继承前人佳作的基础上应该要加入独属于自己的内容,将景物描写进行发展和升华。
总的来说,世间万千景象都是不停变化的,想要创作出好的写景作品,需要用视觉、听觉去观察外物,更要用心去感受,以物为友,将尘世万千当作知音,以简练且合乎规范的语言酬之。这便是刘勰在《物色》篇中主要阐述的观点。
二、《二十四诗品》的景物描写和物色观
继《毛诗序》后,钟嵘著有诗歌理论著作《诗品》。后来,唐代的《二十四诗品》直接沿用“诗品”二字命名著作。经过多个朝代的转述和书写,《二十四诗品》在中国诗歌理论著作上占有了不可取代的重要地位。《二十四诗品》不仅仅是一部有关中国诗歌理论的著作,其遣词造句之功力也是极高的。
《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是谁千百年来尚无定论、众说纷纭,几种主要的说法有虞集作、怀悦作、李嗣真作和司空图作等。邵盈午先生在《诗品解说》中提出的“《诗品》出自司空图的可能性最大”[9]14是目前最为人所接受的一种观点。司空图生活的年代处于唐末的动荡时期,他经历了唐懿宗、唐僖宗、唐昭宗和唐哀宗多个帝王频繁的更替。早年的司空图入朝为官,身居要职,有着宏大的政治抱负,想要济世安民,为李唐王朝效犬马之劳,却遭受了黄巢起义等两次重大的叛乱,流落于乱军之中,险些身首异处。为了逃避灾祸,司空图躲进中条山王官谷的祖传别墅中以度余生,唐昭宗多次欲召其复朝任职。经历了多次灾祸的司空图看到李唐王朝大势已去,丧失了最初的政治理想,多次称病请辞。虽然司空图后来拒绝了在朝为官的机会,但他一直心系李唐王朝,听说唐哀宗李柷为乱臣贼子朱温鸠杀后,他也绝食而亡。司空图有满腔抱负却生不逢时,唯有将一生情志寄托在山水景物之中。隐居后远离政治的他常和当时的名僧高道一同云游,这些对山水景物的游历和观赏对《二十四诗品》的创作具有重要意义。
司空图用四言诗的形式将其文学理论在《二十四诗品》中表现出来,他多次引用《诗经》和《楚辞》中描写自然景物的词汇,这足以证明司空图对《诗经》《楚辞》中景物描写的肯定态度。在此之前,刘勰《文心雕龙》的《物色》篇中便有对《诗经》《楚辞》中景物描写的评价,刘勰认为《诗经》中描写景物的词汇是“一言穷理”“两字穷形”“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5]320。《楚辞》则是“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5]320。通过这些带有褒义色彩的话语可知,刘勰和司空图对《诗经》《楚辞》景物描写的态度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
司空图将景物描写融入《二十四诗品》的每一首诗中。他的四言诗表面看似写景,实则包含了对文学风格和理论的阐释、评价和分类。《二十四诗品》关于意境和景物的理论占有相当的篇幅,主要是探讨实景和虚景的写作。
一方面,司空图认为实景写作的关键在于自然,其观点主要集中在《实境》《精神》和《形容》中。《实境》是最直接阐述实在景物的一首:“取语甚直,计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见道心。清涧之曲,碧松之阴。一客荷樵,一客听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泠然希音。”[10]151《二十四诗品》中所说的实境指的是真实的情境。本诗的开头两句就明确指出实境的含义就是文辞质朴和思想明洁,这是整首诗的总纲,较为全面地从思想和内容两个方面来概括实境。好的文学作品中的“境”是情和景交融的产物,司空图将《实境》整首诗的重点放在了作者情感上,他用写景的语言将“实境”中的情清晰明了地表现了出来。《精神》的关键在于“生气远出,不着死灰。妙造自然,伊谁与裁”[10]125四句。这四句强调了作品的生气和精神,司空图认为好的文学作品不能矫揉造作,而是应该将情感真切自然地涌出。只有将文学作品的创作和自然景物的特性完美贴合才能不被世人诟病。《精神》是《二十四诗品》中极富美学价值的一篇,它关注了文学本身的真实性问题。文学作品的真实性主要表现在作者的想象和描写都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具有真情实感的作品。唐代大诗人杜甫的《绝句》便将“生气远出”和“妙造自然”体现得淋漓尽致:“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11]201这四句将四个单独的景物在同一首诗中描绘出来,可以概括为一句一景。《绝句》没有用浮华的辞藻堆砌全诗,所用词句都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名词和动词,朴素的语句和朗朗上口的节奏韵律是这首诗能够流传后世并妇孺皆知的重要条件。《形容》中的主要观点则是“俱似大道,妙契同尘。离形得似,庶几斯人”[10]161。司空图在其中表明了文学作品要符合生活的正常情理,和自然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离形得似”是一种高境界的景物描写,这种境界不要求脱离现实景物的形态去描写景物的神态,而是在极尽描写自然景物形态的基础上对其神态进行刻画。《形容》篇所传达的是形似和神似的结合,这是司空图对前代文学批评和文学作品的总结,也为唐代及其之后文学作品的写作提供了更加具体的理论性指导。

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给唐以后的诗歌作家提供了许多写作的方法,他将这些方法的抽象和具象状态都描述得恰到好处,每首韵语中都包含着佛道之意,其玄学功底可见一斑。宋代文人苏轼受到了司空图的影响,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对其进行了高度评价:“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14]324总的来说,《二十四诗品》将诗的风格和境界分为二十四种,每种都以十二句四言诗加以说明,形式整饬。《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之“诸体毕备,不主一格”。《二十四诗品》包含了道家和佛家的美学思想,其中,以道家的哲学思想为主,全书呈现出一种自然淡远的风格,充斥着道家的气息。
三、结语
艺术来源于人民的现实生活,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产物。大千世界中存在着众多鬼斧神工的绝美景色,这些景物促成了物色观理论的形成。《文心雕龙》的《物色》篇极其重视客观景物对文学创作的作用,这样的观点表明刘勰拥有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这种重视客观景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在刘勰之前也出现过,陆机在《文赋》中的诸多诗句便包含了诗人对于自然景物的所思所想,涉及了景物和文学创作的关系,但其论述过于简略,且尚处于分散的状态,并没有形成系统化的理论,这和陆机所处时代的文学创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陆机所生活的西晋时期山水文学的创作尚未兴盛,所以他对于情景关系的论述是十分有限的。而南朝的齐梁时期,谢灵运开启新风,山水诗开始兴盛,丰富的山水文学作品是《文心雕龙》物色观理论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由此可见,物色观理论的成熟和系统化不仅要建立在对客观景物的重视上,也需要丰富的文学作品来支撑。
到了唐朝,文学理论进一步成熟,对于情景关系的论述也更加细致。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不仅继承了刘勰对《诗经》《楚辞》景物描写的肯定态度,更将情景关系的论述细化到了实景、虚景的文学创作中。这些细致的理论是《文心雕龙》未涉及的,是司空图对物色观的发展。
从对《文心雕龙》的《物色》篇和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的分析可以看出:从古至今,情、景、辞三者的关系是文学创作者不可忽略的话题。这与三者的本质是密不可分的,触景生情是人类的本能,文人墨客更将欣赏风景后的感想写入文学作品之中。物色观发展了上千年,到近现代仍被众多学者所探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三层“境界”的说法。“境界说”是《人间词话》中的核心理论,它的提出和物色观理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是《物色》篇理论的发展延续。此外,写景抒情、情景交融等写作手法也是当代作家最为常用的写作手法。由此可见,物色观的理论有着与时俱进的活力和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在文学理论界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