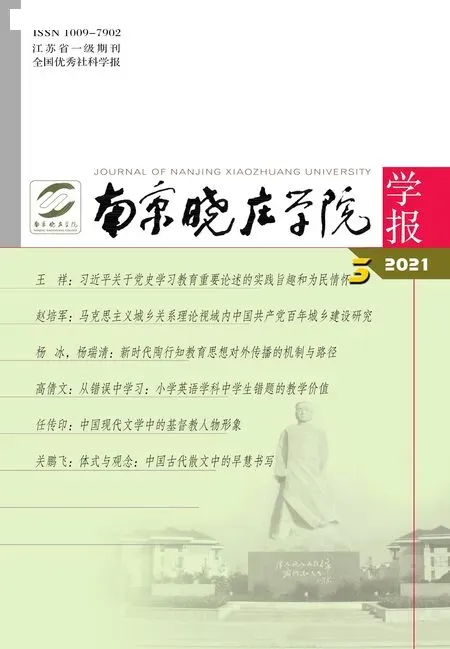体式与观念:中国古代散文中的早慧书写
关鹏飞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1171)
自1960年法国学者菲力浦·阿利埃斯出版儿童史专著(1)菲力浦·阿利埃斯著,沈坚、朱晓罕译:《儿童的世纪——旧制度下的儿童和家庭生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以来,西方儿童史研究获得较大发展(2)有些外国学者已涉及中国儿童的研究,如泰勒·何德兰和坎贝尔·布朗士著,王鸿娟译:《孩提时代——两个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儿童生活》,金城出版社2011年版。。中文世界的研究虽不丰富(3)如果以时间衡量,最早的中国儿童史著作早于菲力浦·阿利埃斯的著作,即王稚庵《中国儿童史》(儿童书局1932年版),但据王子今教授研究,该书“是一部模范儿童事迹综录”(《秦汉儿童的世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页),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内容更为丰富的儿童史。,亦有萌动,较系统的成果有熊秉真旧中国童年研究“三部曲”(4)指熊秉真所著《幼幼:传统中国的襁褓之道》(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版)、《安恙:中国近世儿童的疾病与健康》(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版)和《童年忆往:中国孩子的历史》(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版)。、周愚文对宋代儿童生活与教育的探究(5)周愚文:《宋代儿童的生活与教育》,师大书苑有限公司1996年版。和王子今对秦汉儿童生活的论述(6)王子今著《汉代儿童生活》(三秦出版社2012年版)、《秦汉儿童的世界》(中华书局2018年版)等。。从这些不多的成果来看,研究集中于儿童史、教育史等,从文学角度展开的研究较少,且集中于诗歌与小说(7)诗歌领域主要集中在儿童诗和童趣诗的研究上,前者如马秀娟《宋代的神童与神童诗》(《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年第3期)、高帆《中国古代儿童诗浅探》(《东北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李春桃《论唐代成人创作的儿童诗》(《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郭丽《唐代中原儿童诗与敦煌学郎诗的异同及教育成因论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1期)等,后者如孙亚敏《杨万里的童趣诗及其儿童观》(《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等。小说领域主要集中在宋元小说,以儿童形象的分析及其叙事体式的探究为主,如姚海英《论宋元小说中的儿童形象类型及艺术特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宋元社会生活的形象透视——以宋元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为视角》(《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等。目前均无相关专著问世。领域,中国古代散文领域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少之又少。所谓“中国古代散文”,学界分歧较多,这里取郭英德的观点,认为“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中国古代散文不能仅限于那些抒情写景的所谓‘文学散文’,而是要将政论、史论、传记、墓志以及各体论说杂文统统包罗在内”(8)郭英德:《论〈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的编纂宗旨》,《文艺研究》2015年第8期,第75页。。至于“早慧”(9)早慧,或作“早惠”,在类书编撰中,有时专指女童,如《北堂书钞》卷二五《后妃部三》、《渊鉴类函》卷五七《后妃部一》皆有“早慧”类,而对男童多称“幼智”,如《北堂书钞》卷七《帝王部七》、《渊鉴类函》卷四八《帝王部九》皆有“幼智”类。但亦有称男童为早慧者,如与《北堂书钞》时代接近的《毛诗正义》中,对《生民》诗后稷“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孔颖达便云:“能岐嶷,为早慧之势也。”又云:“后稷以上智之资,必当早慧。”其他类似资料甚多,则“早慧”非仅指女童,亦可包括男童。一词,崔建华指出,“现实生活中时常出现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心智发展比普通人超前,这便是所谓‘早慧’”(10)崔建华:《秦汉社会对早慧现象的认知》,《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1期,第68页。。正如郭英德指出,“散文具有鲜明的‘书写性’特征”,而“书写实践的需要促成历代文人乐此不疲地探究散文的写作体式(或表达方式)”(11)郭英德:《回归中国古代散文的世界》,《人民日报》2016年12月6日。,因此,早慧书写的研究,不仅涉及“展现了中国传统史学对人的成长过程的逻辑联系以及对社会影响的认知体式”(12)彭卫语,见王子今:《秦汉儿童的世界·序》,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页。,也需要从中国文学视角出发,努力探究其书写体式的形成、演变及背后的思想观念。本文拟对此作初步探索,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指正。
一、传记散文的早慧书写及其适用限度
在早慧单独成为类目之前,主要以历史名人传记为载体,其早慧书写的目的多是为印证日后的成就,此亦符合传记散文之特点,正如《册府元龟》中《幼敏》类序云:“《书》曰:‘惟人万物之灵。’若夫幼而慧,少而成者,益可贵矣。中古而下,英妙间出,乃有特禀异资,迥越伦萃,岐嶷兆于襁褓,颖悟发于龆龄,学疑宿习,动彰默识,或未就外传,已通群籍。甫及志学,即为人师。识洞于未萌,智表于先见。心计足以成务,口辩足以解纷。老成之姿,著于容止。赋笔之丽,成于俄顷。至行出于天性,玄谭绝于流俗。时辈推尚,英声腾骛,斯仲尼所谓生知之者欤?”(13)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8951页。亦强调早慧书写的正面价值(与日后成就相印证),其后所举事例无一例外。其实传记散文不乏反例者(与日后成就相冲突),但较少。
先唐早慧书写体式可分两类:正面早慧和反面早慧,以前者占绝对主流,后者偶尔出现,且多“互见”于他人传记。正面早慧书写体式的典范是《后汉书·孔融传》:“融幼有异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师。时河南尹李膺以简重自居,不妄接士宾客,敕外自非当世名人及与通家,皆不得白。融欲观其人,故造膺门。语门者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门者言之。膺请融,问曰:‘高明祖父尝与仆有恩旧乎?’融曰:‘然。先君孔子与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义,而相师友,则融与君累世通家。’众坐莫不叹息。太中大夫陈炜后至,坐中以告炜。炜曰:‘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融应声曰:‘观君所言,将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为伟器。’”(14)范晔:《后汉书》(简体字本)卷七十,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527-1528页。后文详例孔融“年十三”“年十六”等事。在孔融前亦有此类早慧书写(15)如五经、诸子中的后稷生有异禀(《诗经·生民》)、孔子东游所见两小儿(《列子·汤问》)和项橐七岁为孔子师(《战国策·文信侯欲攻赵以广河间》)等。这类事例,多有重出,如项橐,除了《战国策》,《淮南子·修务训》《淮南子·说林训》《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论衡·实知》等书亦有。柯马丁(Matin Kern)认为可视作“文本库”(Repertoire):“为什么在不同语境下会存在同一个故事或诗歌的多个版本?这对早期文本的稳定性和松散性意味着什么?像‘复合文本’和‘文本库’这样的概念是否可以变得意义深远?”(柯马丁:《我怎样研习先秦文本》,载傅刚主编《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黉门对话”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徐建委则把此类素材(包括故事、说理和短语)称为“公共素材”,比“文本库”概念更抽象(徐建委:《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无论如何定义此类素材,它们都有一个显著共同点,即很难确定其“书写性”。究竟是在广泛流传之后被作者写进文本,还是作者书写成型之后才流传开来?因此本文研究“早慧书写”时,把这类属于“文本库”或“公共素材”的部分作为背景处理,不专门探讨其书写体式等问题。,不够典型,且孔融与陈炜早慧观念的交锋,虽初露端倪,却以孔融获胜收场,对后世影响深远(详见第三节),故以此条材料为例论述。
反面早慧书写体式较简略,多放在“互见”部分,不在本传(或纪)出现。如范晔《后汉书》所记汉安帝:“帝少号聪敏,及长多不德。”(16)范晔:《后汉书》(简体字本)卷十六,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08页。据宋徐天麟说,汉安帝是“帝少号聪明,故邓太后立之;及长,多不徳,稍不可太后意。及太后崩,有诬告后兄弟悝等尝取废帝故事,谋立平原王。帝闻,追怒,邓氏五侯皆废为庶人,徙封隲为罗侯,不食而死”(17)徐天麟:《东汉会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47页。。《后汉书》把汉安帝的反面早慧书写“互见”到《邓寇列传》,若非像徐天麟那样仔细对读(司马光《资治通鉴》也有涉及,但不够完整,故此处引用徐说),汉安帝的劣迹便易略过。这类例子并非仅在帝王身上出现,如晋袁宏《后汉纪·后汉孝献皇帝纪》云:“有子曰修,少有俊才,而德业之风尽矣。至魏初,坐事诛。”(18)袁宏撰,周天游校注:《后汉纪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64页。杨修之少俊无善果,也非放在本传中说明,而是“互见”到《后汉孝献皇帝纪》中。这类处理并非特例,陈寿《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亦云:“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植益内不自安。”(19)陈寿:《三国志》(简体字本)卷十九,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17页。也作如是处理,只不过没突出其早慧特点而已。
正面早慧书写体式可细分四类:一是较笼统的年少时期某些方面早慧,二是具体某岁开始显现某方面早慧。前者如《张汤传》:“张汤,杜陵人也。父为长安丞,出,汤为儿守舍……父见之,视文辞如老狱吏,大惊,遂使书狱。”(20)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001页。虽未指出具体年龄,但诚如颜师古对“为儿守舍”之解释:“称为儿者,言其尚幼少也。”(21)班固:《汉书》,第2001页。后者如刘珍《东观汉记》云:“班固字孟坚,年九岁,能属文词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22)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56页。指出班固九岁有文才,后面详细介绍其学问。二者兼有是第三类,如上文所引《后汉书·孔融传》,既说“融幼有异才”,又写其“年十岁”时的具体事例,使早慧形象更饱满。第四类则比较特殊,表面看有反面书写成分在里面,但从全文看,反面所写不过是插曲,不构成主体,仍属正面书写体式之一,如《北齐书》云:“永安简平王浚,字定乐,神武第三子也……而浚早慧,后更被宠,年八岁时,问于博士卢景裕曰:‘祭神如神在,为有神邪,无神邪?’对曰:‘有。’浚曰:‘有神当云祭神神在,何烦“如”字?’景裕不能答。及长,嬉戏不节,曾以属请受纳,大见杖罚,拘禁府狱。既而见原,后稍折节,颇以读书为务。”(23)李百药等著:《北齐书》,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9页。永安简平王幼年早慧,知错就改,最终走上正途。反面早慧书写体式由于本身的独特性,体式较单调,没必要再细分。传记散文早慧书写体式可列表如下:

传记散文早慧书写体式分类表(先唐)正面早慧书写体式反面早慧书写体式较笼统的年少时期某些方面早慧具体某岁开始显现某方面早慧既有笼统早慧特点,又有具体某岁特长以反面书写为插曲的正面书写体式略附古文早慧书写体式(唐宋)正反合辙早慧书写体式(见王安石《伤仲永》部分)略
出现“早慧”类目后(24)如《世说新语·夙惠第十二》所载七则,数量虽少,已开先河。至《北堂书钞》则再细分,如卷七《帝王部七》“幼智”与卷二五《后妃部三》“早慧”,到《太平御览》则把“幼智”与“早慧”合并为“幼智”类,其“幼智”类亦包括“和熹邓后”可知。因此,这里的早慧类目,并非死扣字面,符合早慧的“幼智”“幼敏”(《册府元龟·总录部·幼敏》)等皆可。,由于编撰者有意识把早慧视作值得书写的事情(25)如《册府元龟·幼敏》序所云“若夫幼而慧,少而成者,益可贵矣”。尽管光“幼而慧”还不行,还需要“少而成”,即有所成就最好,但好歹强调“幼慧”“少成”,对早慧本身的记载与书写出现兴趣。,原来传记散文中几乎难以见到的以“早慧”闻名不知其终的事例,开始出现。以《册府元龟》为例,其中“幼敏”类有三卷(26)类书编撰也会出问题,比如遗漏在其他类目之中,如《册府元龟·兽部·鼠》中,就记载曹冲鼠啮之事。分类时亦纳入。此事又见《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但《册府元龟》只选取鼠啮之事,《魏书》则写其死后之追封追谥等事。由此亦可见类目与史传记载之差别。,其早慧书写按照内容可分三类:一是后为某某官,如“王弼,字辅嗣,幼而察慧,年十余岁,好《老子》,通辩能言,后为尚书郎”(27)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第8956页。,此类还有很多其他表述方式,如“终于”某官,或“位至”某官等,要言之,皆以宦达印证早慧,故不详录。二是不求名位,如“卢大翼……七岁诣学,诵数千言,州里号曰神童。及长,闲居味道,不求荣利,卒于洛阳”(28)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第8978页。。三是不录其后,此类又可细分三类:一是幼时已达,如“桑弘羊,武帝时以心计,年十三为侍中”(29)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第8953页。,没必要等长成后再去印证,故记载仅此而已。二是死时尚幼,如“终军少好学……后军死,世谓之终童”(30)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第8953页。,由于终军死时尚幼,且其早慧之事笼罩一生,故点出“终童”称谓,而不书其死之由(31)史传书写亦有“死时尚幼”类,但与类目中的有所不同,如《南史》云:“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简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宝元年,封建平郡王。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围台城,武帝素归心释教,每发誓愿,恒云:‘若有众生应受诸苦,衍身代。’当时大球年甫七岁,闻而惊谓母曰:‘官家尚尔,儿安敢辞?’乃六时礼佛,亦云:‘凡有众生应获苦报,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李延寿撰:《南史》,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43页)最终交待其“遇害”是提示结局,带有惋惜之意,而“世谓之终童”则以结局强调其“童”之特点,以呼应早慧。。三是其后未知,此类最应引起注意,如“刘祥,幼而聪慧,占对俊辩,宾客见者,号为神童。年十岁能属文,十二通五经”(32)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第8976页。等。成类目早慧书写体式可列表如下:

成类目早慧书写体式表后为某某官不求名位不录其后略略幼时已达死时尚幼其后未知
传记散文与成类目的早慧书写体式看似不同(可比较以上两份表格),实际上前者从书写目的区分,后者从书写内容区分,二者正好形成一定程度的互补。但这种互补并没完全解决早慧书写中的适用限度问题(33)“适用限度”一词用来形容书写文本相对于书写对象的有效性或适用性,参见徐建委对文献适用限度的追问(徐建委:《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4-87页),此处将之引申到文本书写之中。。从早慧的逻辑机制来看,会引出以下结果:一是早慧,后来有成;二是早慧,后来有害;三是早慧,后来成为普通人;四是早慧,亦早夭。第一类、第四类对应正面早慧书写体式,第二类对应反面早慧书写体式,都较有效。第三类与成类目早慧书写体式中的“不录其后”有关,却又不能形成完全对应。成类目早慧书写体式“不录其后”中的三个细目,并不适用于“后来成为普通人”的早慧书写,尽管不录的原因可能是平淡无奇(即“其后未知”),或资料缺乏(34)也有可能是类书编者遗漏资料,那属于个人作风问题,不具有普遍性。。早慧书写之所以出现这类现象,从成类目早慧书写角度而言,在于材料来源多是传记史书(35)由于《册府元龟》所引早慧书写资料不标出处,我们以在它之前编撰的《太平御览》为例,加以说明。《太平御览·人事部》有“幼智”类,分为两卷(三百八十四卷和三百八十五卷),所引史料,主要来自史书,统计如下:《左传》3条,《战国策》2条,《史记》1条,《汉书》2条,《后汉书》1条,《续汉书》4条,《东观汉记》10条,《英雄记》1条,《汉杂事》1条,《魏氏春秋》1条,《魏志》10条,《吴书》3条,《蜀志》1条,《晋书》6条,《晋中兴书》3条,《宋书》4条,《齐书》4条,《梁史》1条,《陈书》1条,《崔鸿十六国春秋》共3条(其中《前凉录》1条,《后赵录》1条,《夏录》1条),《后魏书》2条,《三国典略》1条,《唐书》7条。其他尚有《列子》1条,《尸子》1条,《鲁连子》2条,《郭子》1条,《周书》1条,其他又有别传如《李固别传》《孔融别传》《何晏别传》等共10部,《傅畅自叙》1条,《列子传》1条,《文士传》6条,《三辅决录》1条,另有家传、先贤传等若干。,传记散文的严谨性使其不能在缺乏资料的情况下自行补足,而就传记散文的早慧书写而言,史书立传的选择性也使那些“后来成为普通人”的例子不便书写,因史书是在人物事迹确定之后回溯其幼年是否“早慧”,有则更好,无亦无妨,因此史书中早慧者,无论正面反面,皆有结果(36)受此影响,某些古人认为“早慧”者要么成为优秀人物,要么成为奸恶之徒,很难成为普通人:“世言早慧者大未必佳,自孔文举小时,大中大夫陈韪已有是语,殆未必然。盖人性颖脱者,固易为善,亦易为恶,在所以养之耳。后人不论所养,而概喜其早慧,可怪哉。”(见彭大翼《山堂肆考》卷一百八人品“神童”类)其中说到“人性颖脱者,固易为善,亦易为恶”,而不涉及凡人。这实在是因果倒置。。
早慧书写的缺陷,受传记散文叙事目的影响与限制,只能在有限方面弥补。这一任务需要唐宋古文崛起后,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二、从杂传到古文:唐宋的两类早慧书写策略
除传记散文早慧书写体式的有效部分继续发展之外,唐宋时人的早慧书写策略主要分两类:一是以柳宗元为代表,通过选择比官修史书的史书性质弱一些的杂传体进行开拓,同时融入古文笔法,最后形成儿童传记,以儿童形象的文学塑造消解其成人负担,从而切断早慧书写体式中与逻辑机制矛盾的部分;二是以韩愈为代表,跳开传记散文无法剥离的史书性质,利用古文直接写作,但这类书写文体由于是新创,故迟至北宋王安石才开创新的正反合辙早慧书写体式,以适应书写对象的逻辑机制。
1.早慧书写策略之一:从杂传到柳宗元的儿童传记
虽然同为传记散文,杂传与史传相比,其史的责任与束缚都更轻一些(37)王夫之对史的责任有较为典型的概括,他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见《读通鉴论》)王夫之的说法并非个案,刘知几在荀悦、干宝的“五志”基础上更提出“三科”(见《史通·书事》),都说明史传的责任意识之强与束缚之大。。早慧书写体式适用限度的扩大,就传记散文内部而言,杂传的相对灵活更有开拓空间。与此同时,不少杂传作者也探索更为独立的杂传书写体式,到六朝时,“很多杂传,尤其是单篇散传,已基本不承载史的责任”(38)熊明:《论六朝杂传对史传叙事传统的突破与超越》,《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第62页。。这种变革其实在魏晋时期已出现苗头,如干宝、陶渊明等(39)这也跟当时杂传兴起的大背景关系密切,详情可参看刘湘兰《两晋史官制度与杂传的兴盛》(《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2期)。,他们利用杂传进行早慧书写,虽没有完全脱离“史的责任”,却也带来新的变化。柳宗元分别从二人的作品中受到启发,形成富有自己风格的儿童传记(40)儿童传记的概念,学界有不同看法,主要为两类。一类如王泉根所云:“以儿童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传记称为儿童文学传记。有的成人传记,因其中描写专注儿童和少年时代生活的部分,也可以作为儿童文学传记来阅读。”(王泉根主编:《儿童文学教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4页)另一类则认为:“儿童传记文学是以形象描绘的手法,具体、生动地记叙古今中外有贡献的伟人、英雄、学者、名人等风云人物生平事迹的儿童文学作品。”(陈世安主编:《儿童文学》,河海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8页)前者从写作内容的儿童属性考虑,兼顾成人传记中的儿童部分,后者则从阅读对象考虑,强调写给儿童阅读的手法要“形象”,在笔者看来,可以互补。因此本文所取“儿童传记”的概念,既包括以儿童为写作对象的作品,也包括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作品。,如《童区寄传》。为便于比较,现把干宝《搜神记》(41)《搜神记》一般认为是“志怪小说”,但事实上在《晋书》《隋书》《旧唐书》中都被列为史部“杂传”一类,可参看张永刚《〈搜神记〉之“杂传”论》(《兰州学刊》2005年第5期)。卷十九李寄传、陶渊明《庶人孝传赞》与《童区寄传》进行具体比较。
比较而言,《童区寄传》对干宝《搜神记》的借鉴更明显。首先,两位小主人公的名字相同,年龄、故事情节和发生地点都较相近,这不是偶然。尤其是名字都为“寄”,据卡尔维诺研究,“名字与通常被称为‘叙事风格’的东西是一体的,要和‘风格’一起确定,以判断它能达到的整体效果”(42)伊塔洛·卡尔维诺著,王建全译:《文字世界和非文字世界》,译林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如果我们从两篇文章的相同点着眼,不妨说寄女与区寄,刚好是不同性别的人物“同构”。当然,更重要的是柳宗元学习干宝叙述寄女事件的技巧,这对塑造人物最有利。遗憾的是,干宝没摆脱史学叙事尾巴(43)干宝本是史学家,故所受史学影响较深,这样也直接影响到该篇的现代接受。在《中国历代儿童故事选》中,此文被命名为《李寄斩蛇》,其《前言》将其评价为“歌颂舍己救人精神”的作品(江苏省儿童文学创作研究会编:《中国历代儿童故事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王泉根则认为,它是“中国古代儿童文学”中“最值得称道的著名童话”之一(王泉根:《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版,第18页),但朱自强却认为:“李寄这个人物形象,显示给我们的既非‘舍己救人精神’,也非‘为民除害’的‘善良的品质’,而是一个被封建思想道德深深毒害了的畸形儿。”(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究其原因,就在于干宝强烈的史学责任使其作品打上浓厚的封建色彩。,在文章最后说“越王闻之,聘寄女为后”,迫不及待要交待其后续人生,得出“记功司过”的史学结论,这在柳宗元的文章中亦有残留,如“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但立刻又在结尾处把时间点拉回到儿童身上,即“是儿少秦武阳二岁”的对话中(44)郭预衡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作者通过人物的语言、行动、表情,直接刻划人物形象,还用‘市者’自作聪明的心理活动反衬区寄的机智;用‘乡之行劫缚者’的‘侧目莫敢过其门’,反衬区寄的勇敢,有力地映衬出人物的性格。”(郭预衡主编:《中国历代散文精品》(第二版),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页)总之,是把《童区寄传》看作文学创作。在《中国历代儿童故事选》中,并没有选入《童区寄传》,可见编选者亦将此文看作柳宗元的文学创作,而非实录。。
在《庶人孝传赞》中,除廉范后有官位叙述外,另两位皆是儿童时事。陶渊明未能摆脱传记散文早慧书写适用限度的难题,但文中涉及议论,如“夫智者不惑,勇者不惧,陶孝于其亲,而智勇并彰乎弱龄,斯又难矣”等,这就使文中所写事迹具有典范性,成为提倡孝道的事例,使文中的早慧书写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即以杂传中的议论,截断早慧书写中具有的“后来成为普通人”的书写失效可能,使文中的早慧书写到此为止,因为文章的论点已表达清晰。柳宗元《童区寄传》的开场,即学陶渊明之议论,如“童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但更多的是在叙述故事发生背景,以更饱满地突出区寄的儿童形象,使其形象扎根于现实,从而获得比陶渊明说教更有效的感染力。
柳宗元从陶渊明处获得启示,早慧书写不一定要依附史学叙述传统,完全可以通过议论手段,使其形象独立。由于干宝本人为著名史学家,所以塑造完寄女形象后再次回归史学叙述传统,柳宗元则勇敢跳出来,但干宝毕竟为柳宗元提供了叙述灵感。通过对陶渊明和干宝的扬长补短,柳宗元《童区寄传》获得巨大成功。这种文学感染力的获得,使故事本身成为富有文学性的文本,而不必再依靠其现实成长之后的事迹,也就是说,使早慧的儿童形象获得独立于史学之外的艺术魅力,从而让原本属于成人故事中的一部分的早慧书写,获得自身的完整性,发展为儿童传记。这样一来,一方面儿童传记不必再承受原先早慧书写适用限度的焦虑(因为它已脱离成人故事,自成一体),另一方面又以其深入人心的儿童形象鼓励、感染读者,尤其是小读者们,使其自觉学习文中形象所具有的勇敢、机智、行动力强等早慧特点,把文中截然而止的区寄故事,化作读者们的学习实践,使文章塑造的“区寄”形象含有更深更持久的影响。
2.早慧书写策略之二:从韩愈的古文发端到王安石的合辙成型
与柳宗元完全切断早慧书写体式中与逻辑机制矛盾的部分的做法不同,韩愈则试图利用新兴的古文文体作有益探讨(45)柳宗元《童区寄传》实际上也在笔法上融入古文创作,这可以从其文章归类中看出来,清代学者沈德潜编撰《唐宋八大家文》,就把柳宗元此文选入(沈德潜选编,宋晶如注释,刘欣生标点:《唐宋八大家文》,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67-268页)。,他在《赠张童子序》中一反众人对早慧的赞颂,而代之以担忧,孙琮云:“此篇前幅历言科举之难,后幅言童子得之之易,此不是欣羡童子,正是规箴童子。”(46)韩愈著,闫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注释》,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页。可谓得之。韩愈希望“进童子于道”,使张童子在后续的成长中能够“勤乎其未学”的“成人之礼”。陈克明指出:“此处‘已学者’实指书本知识,‘未学者’实指社会磨炼。”(47)陈克明:《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64页。所云甚是。韩愈的担忧很有道理,毕竟儿童无论如何早慧,不至于连未经历的成人道理都明白,这只有在成长道路上切身体会才行。因此,韩愈书写的着眼点仍在成人上,这与传记散文中充满“史的责任”的史学叙事体式如出一辙,只不过在体裁上,选择古文书写而已。与此同时也有不同。韩愈着眼点是“成人”,史学叙事目的则是回溯名人(无论善恶)的早慧经历,如能发现二者的关联则更佳。成人与成为名人,二者之间的区别显而易见。
这种先成人(无论是名人还是普通人)的观念,在《伤仲永》中得到回应,王安石对方仲永的早慧书写,目的与韩愈接近,写法却有较大变化。韩愈写的时候,所针对的仍是文中的张童子,而王安石所写,已经有较明确的读者意识,诚如王水照所说:“这原本是一个关于天才沦落的故事,而世上多凡人,因而一般读者对于这类故事只感好奇有趣,不易产生一种与切身有关的警觉。但作者却从这则奇闻异事中剔发出普遍意义来,可见其思智笔力过人之处。”(48)王水照:《唐宋散文举要》,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51页。方仲永已成普通人,徒伤无益,王安石希望以此引发读者思考:像方仲永那样早慧的人,由于不学,最后仍是普通人,那如果大多数普通读者还不学,以后还能成为普通人吗?毫无疑问,在王安石这里,“众人”也不是好做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在写方仲永沦为普通人的过程中暗含对比。王兆鹏等指出:“方仲永可以说既是王安石的同乡,又是他的同龄。因为,王安石第一次在舅家见到方仲永的时候,安石十三岁,而方仲永看上去也是十二三岁。当他写这篇文章时,他和方仲永都是二十三岁。然而,方仲永乃为‘众人’,而王安石则已是进士及第、职任签判的少年英俊了。这种暗中的‘对比’,恐怕也是他作此文的一个重要依据。”(49)王兆鹏,黄崇浩编选:《王安石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176页。所云甚是。在《伤仲永》的早慧书写中,作为作者的王安石是隐含的形象,因为王安石亦是早慧者:“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50)脱脱等著:《宋史》,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461页。《宋史》本传中的王安石早慧书写,刚好是正面早慧书写体式。拿“见者皆服其精妙”(51)这段文字断句,若将“其文”以后内容归属“友生曾巩”,则“见者皆服其精妙”当在成年后,但学界一般将之归属于前,如《王安石评传》便评论说:“少年时的王安石,因其刻苦力学,才有这种‘过目不忘’和‘动笔如飞’的本领。”(张祥浩,魏福明:《王安石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且据蔡上翔辨析,“友生曾巩携以示欧阳修,修为之延誉,擢进士上第”之说为无根之谈:“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在庆历元年。至二年,再《上欧阳第二书》,及欧公《送曾巩秀才序》,皆无一语及安石,而子固遂归临川矣……本传一开卷而乖谬若此,则由元人修史,皆杂采毁者之言为之。”(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页)则“友生曾巩”之叙有误。故以“其文”属上为佳。与“其文理皆有可观者”对比,可知王安石早慧程度或不在方仲永之下。但出于对“一般读者”的警醒,王安石放弃正面早慧书写,代以反面早慧书写。作者本人早慧经历与所写早慧对象遥相呼应,使早慧书写出现正反合辙体式。
王安石通过《伤仲永》的早慧书写,一方面把传记散文中缺乏的第三类“早慧,后来成为普通人”的逻辑机制补足,使中国古代散文中的早慧书写与其书写对象的逻辑机制完全吻合,另一方面,王安石通过古文早慧书写,使传记散文早慧书写体式中的正面与反面融合,开创出正反合辙早慧书写体式。经过王安石之手,早慧书写在体式适用限度方面得到完善,在书写内容层次方面得到丰富。后世作者可以任选其中某一体式进行早慧书写,但在早慧书写革新方面,除非文体发生巨变(52)如文言文书写转变为白话文书写,但这已不属于本文“中国古代散文”范畴内的应有之义,故从略。,否则难以开辟出新的疆域。
三、早慧书写体式变化背后的儿童教育思想
书写内容与书写体式的选择,归根究底与时人的儿童教育思想观念密切相关。思想观念是复杂而充满矛盾的,很多时候并非没有某些思想观念,而是有更强有力的思想观念占据主导,从而掩盖次要者。因此,思想观念折射出来的文化变化,不可能是截然不同的野蛮生长,而是此消彼长的缓慢进程。早慧书写背后的儿童教育思想观念亦可如是观。先唐时期传记散文的早慧书写倾向于写“早慧,后来有成”的体式,对“早慧,后来有害”“早慧,亦早夭”稍有提及,对“早慧,后来成为普通人”则完全失效,原因就在于第一类体式是当时主流思想所重视的。
先唐古人对早慧现象持肯定态度,与孔子“生而知之上也”有关。《论语·季氏》云:“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53)刘宝楠:《论语正义》,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361页。崔建华对孔子此言理解有误,认为“生而知之者”也需要学习,这是从“合乎一个教育家的思维逻辑”出发,同时误读荀悦之言的结果(54)崔建华云:“作为尘世中人,只可能在某些方面‘生而知之’,不是神一般的全能,因此,生而知之者仍需要不断学习。这个态度才是合乎一个教育家的思维逻辑。”(崔建华:《秦汉社会对早慧现象的认知》,《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11期,第71页)飞按:某些方面生而知之者,非所谓“生而知之者”。。荀悦云:“或问曰:‘君子曷敦乎学?’曰:‘生而知之者寡矣,学而知之者众矣。悠悠之民,泄泄之士,明明之治,汶汶之乱,皆学废兴之由,敦之不亦宜乎?’”(55)荀悦撰,龚祖培校点:《申鉴》,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5页。此意《论语正义》所解甚确:“上、次、又次,皆言人资质之殊,非谓其知有浅深也。《中庸》云:‘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56)刘宝楠:《论语正义》,第361页。即“知之”是一样的,只不过人生资质不同,有的生下来已经知之,有的通过学习才知之。“生而知之者”既然已经知之,如圣人一般,自可不必再学,问题在于,即便孔子也不敢当圣人,《论语·述而》云:“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57)程树德:《论语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554页。孔安国解释说:“孔子谦不敢自名仁圣也。”此言得之。除谦虚之外,亦孔子好学所致。孔子都不敢说是“生而知之者”,其他人自然都要学习。换言之,若早慧者有“生而知之”资质,自然期待年长更加有成。
在肯定态度之下,否定早慧的暗流不绝如缕。如在《后汉书·孔融传》中,陈炜就说“夫人小而聪了,大未必奇”。只不过陈炜的意见被孔融反驳掉了。尽管出现两种争锋相对的观念,显示出东汉末年早慧观念的复杂性,但以孔融为主的东汉名士,认为早慧者必为“伟器”,对后世影响极大,孔融让梨的故事也成为经典范本,且与圣人孔子“弱不好弄”的记载吻合,因此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思想的后代形成压倒性优势,反过来促成传记散文早慧书写体式的形成,当然,由于忽略早慧过后的其他可能,也埋下适用限度的危机。
陈炜的观点虽长时期不占主流,但也得到有识之士的引申发展。如诸葛亮,就在“大未必奇”的基础上,提出“嫌其早成,不为重器”的观点,《三国志》云:“建兴十二年,亮出武功,与兄瑾书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58)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692页。尽管诸葛亮提出这一观点(59)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对裴松之的注非常看重,据王铚云:“东坡自海外归至南康军,语刘义仲壮舆曰:轼元丰中过金陵,见介甫,论《三国志》曰:裴松之之该洽,寔出陈寿上,不别成书,而但注《三国志》,此所以陈寿下也,盖好事多在注中。安石旧有意重修,今老矣,非子瞻,他人下手不得矣。轼对以轼于讨论非所工。盖介父以此事付托轼,轼今以付壮舆也。仆闻此于壮舆,尽直记其旧言。”(见《默记》卷上)则王安石对裴松之注极其熟悉,对《三国志》素有研究,则诸葛亮之观点,或对王安石有所启发。,不幸的是,即便《诸葛亮传》所附《诸葛瞻传》,也依然是以传记散文早慧书写体式来撰写的,最后诸葛瞻“美声溢誉,有过其实”,如王子今所云:“诸葛瞻显然非可以‘扶危’‘拒敌’的军政人才,诸葛亮‘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的预见是准确的。”(60)王子今:《秦汉儿童的世界》,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78页。但诸葛瞻最终还是成为蜀国忠臣,裴松之注云:“干宝曰:瞻虽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敌,而能外不负国,内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61)陈寿:《三国志》,第693页。作为史学家,干宝的意见有代表性,这从《蜀书》强调诸葛瞻“临陈(阵)死”等叙述可以看出。
在早慧者必成“伟器”思想观念主导下,早慧书写日渐流入形式化弊端。如庾信《周兖州刺史广饶公宇文公神道碑》云:“公弱龄早慧,幼志夙成。立必正方,言无剿说。青衿知(‘知’,《文苑英华》作‘智’)勇,即埋云梦之蛇;童子仁心,已爱中牟之雉。”(62)严可均:《全北齐文全后周文》,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8页。阎步克分析庾信的碑文后指出:“文武散号的同时拥有,都成了吹捧的口实或夸耀的本钱了。”(63)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99页。实际上所谓的“早慧”,也成可供夸耀之事,于是“早慧”在墓志中甚为常见,如《故侍中司徒建平王宏墓志》曰:“含荣幼耀,膺和早慧。徘徊天人,优游经艺。”(64)严可均:《全宋文》,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76页。早慧日渐带有夸耀之嫌,以至于某些作者使用早慧时不得不避嫌,如卢肇《海潮赋后序》:“愚以始闻方数,侧揆元黄。亦尝以大窦酬嘲,敢云早慧;既不用蛉胶习戏,自鄙童心。”(65)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9157页。卢肇“敢云早慧”“自鄙童心”的做法,与其《牧童》诗中所写矛盾:“谁人得似牧童心,牛上横眠秋听深。时复往来吹一曲,何愁南北不知音。”(66)王启兴主编:《校编全唐诗》,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3页。可见人们过度滥用“早慧”书写,以至于卢肇在涉及自身早慧书写时,尽量避免。
这种主导思想的转折,其实比卢肇更早,体现为韩、柳对“圣人之道”的重新认知,也即“道统”的重新确认,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云:“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气……道未极浑备。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风,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67)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423页。在这次思想转型中,韩、柳注意扩大可入圣人之道的人群基础,尤其是柳宗元,他在《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中说:“甚矣圣人之难知也!有吴郡人陆先生质与其师友,天水啖助洎赵匡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侈大矣哉。”(68)柳宗元著,曹明纲标点:《柳宗元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在柳宗元看来,“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而非只有早慧之类“生而知之者”,这无疑更理性。从区寄身上也可看出,他的早慧,并不像寄女那样,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显示出早慧特征,而是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完成的。
韩柳之道,在宋代得到呼应,古文运动获得成功,但真正接续韩柳之道并作出大发展的,首推王安石,邓广铭指出:“在北宋一代,对于儒家学说中有关道德性命的义蕴的阐释和发挥,前乎王安石者实无人能与之相比。由于他曾一度得君当政,他的学术思想在士大夫间所产生的影响,终北宋一代也同样无人能与之相比。”(69)邓广铭:《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第27页。并认为王安石才是真正的“内圣外王之学”。邓广铭主要从王安石一生的学术角度加以概括,实际上在庆历三年,王安石年二十三作《伤仲永》的时候,就已开始追求“圣人之道”。通过王安石当时的一些作品可知(70)其他如庆历三年《忆昨诗示诸外弟》云:“端居感慨忽自悟,青天闪烁无停晖。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材疎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同学一首别子固》《李通叔哀辞并序》等皆是,文长不录。,王安石专注于与友朋共习圣人之道,以成君子,庆历二年所作《送孙正之序》云:“时然而然,众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已也,圣人之道在焉尔。……予观今之世,圆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尧言,起而舜趋,不以孟、韩之心为心者,果异众人乎?”(71)王水照:《王安石全集》第七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489页。陈乐民指出:“此是安石一生行状注脚,有心者当深察之,毁之者、誉之者均不可忽也。”(72)陈乐民:《读书与沉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62页。所云甚是。王安石区分众人与君子之别,乃在于众人趋时,而君子独立;众人之所以趋时,源于心中无所守,而君子之所以有所立,是因为“圣人之道在焉尔”。这与《伤仲永》中的“泯然众人”的“众人”,语意一致。如何得“圣人之道”,关键不在模仿圣人言行,而在于“术素修而志素定”“以孟、韩之心为心”,这就引出学的重要性。从《李通叔哀辞并序》中可看出,王安石亦有成“众人”之焦虑,他说:“予材性生古人下,学又不能力,又不得友以相镌切以入于道德,予其或者归为涂之人而已邪?”(73)王水照:《王安石全集》第七册,第1513页。跟李通叔接触后,才知道“圣人户庭可策而入也”。因此,王安石在《伤仲永》之际,也有自警之意(详前)。可以说,王安石在切身学习圣人之道的过程中,经历焦虑与突破,实现韩愈未曾实现的对早慧书写适用限度的补足和对正反合辙书写体式的定型。而王安石之所以能超越韩愈,跟其独特的经史观有关,刘成国认为:“通过各种方式,将这种真理(来自儒家六经——笔者注)领悟、阐发出来,然后以此来评断史料,辨其真伪,这便是王安石的经史观。”(74)刘成国:《尊经卑史——王安石的史学思想与北宋后期史学命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108页。王安石尊经卑史的倾向,为他摆脱传记散文中带有浓厚“史的责任”的早慧书写体式,提供得天独厚的便利。
余论
由于早慧书写本身的“书写性”,故本文对书写性较弱而“共同材料”性质较强的先秦文献,只从思想观念的角度加以采用,未敢旁涉。秦汉以降,中经魏晋六朝,至唐宋,中国古代散文中的早慧书写体式已完成其书写的有效与成型。以后的情形如何?可略涉一二。书写体式的发展有其独特性,不会如历史发展般直线前进。如南宋陈耆卿的《赠刘神童序》(75)陈耆卿著,曹莉亚校点:《陈耆卿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23页。,该序与韩愈《赠张童子序》对读,可以明显感觉到陈耆卿在笔力铺陈与议论博辩等方面,都难与韩愈匹敌。这非个案。再如明代孙承恩《杜原吉像赞》(76)孙承恩:《文简集》卷四十二赞,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可与王安石《伤仲永》对读,二者皆是早慧书写的正反合辙体式,即书写对象与所写作者形成呼应,且二文的具体内容亦有相似,都是作者正面成长而书写对象成为普通人。但是阅读之后,除了为不得志的好友抱不平外,难以获得《伤仲永》的震撼力。因此,其文虽后出,其艺术魅力却大不如《伤仲永》。此类例证一方面说明文学书写并不总与历史发展正相关,另一方面也启示我们,在文体革新没有发生之前,一再重复旧有内容,确实难以取得新成就(77)当然,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从“中国古代散文”的范畴走出来,宋以后的早慧书写在诗歌领域获得蓬勃发展,出现大量神童诗、悼亡(尤其是幼儿早慧而夭)诗等,如刘克庄《后村集》卷三十九《凤孙,余第六孙也,早慧,忽夭,追悼一首》、江盈科《雪涛诗评·早慧三则》等。留待以后另撰文探讨。。